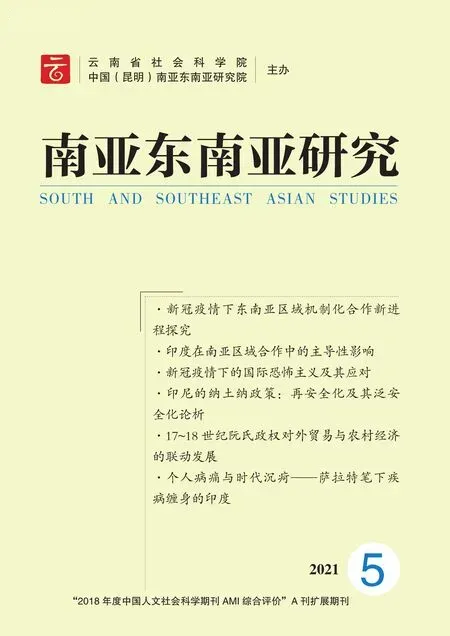日本当代文学中的“战国海商”与南洋
郭尔雅
对于历史上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史称“南海”“南洋”)的海外贸易及海外移民活动,史料上虽有记载,但失之粗略。现代日本“东洋学”家藤田丰八、桑原骘藏等曾做过一些研究,但因史料局限,历史现场感仍嫌不足。相对于历史记载的浮光掠影,反而是日本当代一些以战国时代南洋贸易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在史料的基础上合理想象、丰富了细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史料的一种补充与延伸。站在中国立场上,从东亚—东南亚区域交流的角度,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不仅可以考察日本当代作家的“战国海商”以及南洋想象,也可以从中寻绎特定历史时期日本与这一地区的特殊商贸方式以及日本人的“南洋/东南亚”观及亚洲区域意识的嬗变,对于我们研究历史上的东南亚(南洋)区域之形成,特别是研究东南亚区域形成中的中国因素,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日本“战国海商”及在南洋的“引込町人”
在日本所谓的“战国时代”①战国时代:日本历史上指应仁之乱(1467~1477年)至1568年织田信长入京的群雄割据的混乱时代。末期,出现了一批活跃于东海、南海商道上的“战国海商”,其中有一个特殊商人群体,叫作“引込町人”。他们本是武士,后因各藩混战失去或脱离了自己的家主,通过种种途径最终成为海商,往来于日本与东南亚之间进行海外贸易。他们是由武士“引込”(意即“挤入”“挤进”)商人的一群,甚至有些人还没有完全摆脱武士家臣的使命,而又受雇于官方特许的朱印船,从事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活动。他们行商人之事,身上却依然留存着武士的精神与特性,这可以说是特殊的历史时期所造就的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在16至17世纪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而又特殊的角色,正是因为他们在“海商”身份之下,又有着“武士”的精神内核,让那些位于四民制首末的“士”与“商”的身份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在同一个人物身上集中表现出来,两种身份发生轮转与碰撞,也让这一时期的日本海外贸易呈现出相当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对于这样一个在史料中并未有过多记载的商人群体,当代日本作家特别是历史小说家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例如,著名历史小说家南条范夫的《海贼商人》中的主人公弥平太就是一个典型的“引込町人”。弥平太的形象并非完全虚构,而是有历史原型的。作家南条范夫在小说后记中有书:“史书有记,永禄十一年(1568年)织田信长攻打近江箕作城时,守城部将建部吉保之子侥幸脱逃,关于他们逃往海上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但那之后的活动却已无考,《海贼商人》便是将史书无考的部分演绎成了小说。”②南條範夫:『海賊商人』(後記),東京河出書房1986年版,第237頁。在小说中,弥平太原是近江国蒲生郡箕作城的守城将领建部吉保之子,属于上层武士,自幼修习弓箭之术,涵养文艺之能,并与母舅三好日向守家的小姐津世订下了婚约,只待成年,成家立业,成为主君。不料箕作城遭袭,其父被困城内,弥平太仓皇逃往海上,其武士的身份也脱落了。弥平太曾在广州、吕宋一带做过海贼,后在马尼拉被捕,出逃过程中落海,为堺市著名贸易商人纳屋助左卫门所救,并被收作养子,跟随助左卫门学习商业知识并继承了纳屋及纳屋助左卫门的名号,从事日本与南洋间的贸易,在吕宋一带声名鹊起,又被称为吕宋助左卫门。至此,作为武士的建部吉保之子便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历史上有名的豪商吕宋助左卫门,是为典型的“引込町人”。在这部作品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贼商人”的活动区域,主要是从琉球到菲律宾至中国广州一带,这也是日本所谓的“南洋”的主要范围。
当时舍弃武士身份而充作海贼的人绝不在少数,《海贼商人》中所写的弥平太第一次加入的海贼集团,就是建部家的家臣志村佐五兵卫与大内家的遗臣右冢太郎左卫门所组建的海贼队合并而成的三百多人的海贼集团。正如小说所说:“昨日还是主君的公主,今天便成了某人的姬妾,即便如此,在这个时代,谁也不会感到奇怪。何况海上是一个完全靠实力说话的世界。……做海贼的人越来越多,船也随之扩大。然而不管船变得多大,等着乘船的人还是很多。此时此世,只有海贼才是无所托赖的人最自由的生活方式,对于做了浪人的武士,也是通向权力的最为便捷之路。”①南條範夫:『海賊商人』,第19~20頁。出逃海上成为海贼,等待日后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落魄武士的最好选择,而许多成为海贼的武士,在单纯劫掠过往商船的过程中,也会逐渐开始进行物品的贸易,慢慢转为海商,这也是“引込町人”的一大来源。
小说家久生十兰所著《吕宋的壶》的主人公大迫吉之丞,也是出身于武士之家。其父大迫吉次原是松永久秀的家臣,在主家灭门之后入狱,后被大名岛津贵久发现,得岛津贵久引荐开始在长崎做起了海外贸易,“和堺的木屋弥三郎、西类子九郎兵卫等一样,他从武士转变为商人,即‘引込町人’,直到七十岁去世的那年秋天,仍然掌舵挥橹,叱咤于南方的辽阔海域,犹如闲庭信步”。②久生十兰:「吕宋の壶」,縄田一男編『波濤風雲録』,東京新潮社1995年版,第188頁。在吉次去世后,海外贸易也转入吉之丞手中,主君也随之变成岛津贵久之子岛津义弘。大迫吉之丞作为商人,在第二次朝鲜征伐中曾随岛津义弘前往泗川,负责粮米战资,在枪林弹雨中奔走。庆长五年秋的关原之战,他尽管并未参与,但在义弘大败的万分危急关头前往堺市接应岛津义弘,并驾船将其送至鹿儿岛。关原会战之后,义弘隐居,大迫吉之丞的南洋贸易也不得不中止,只在琉球等地转运物产。直到庆长十五年(1610年)重新得到岛津义弘传召,命其前往南洋寻找茶壶,方得重新出海。大迫父子尽管以商人之名行商贸之事,但他们并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受雇于大名的“朱印船”贸易商人,即他们是得到官方许可、持有朱红印执照的海商,这一点与《海贼商人》中的弥平太大不相同。然而,无论如何,他们都有着“引込町人”显著的特点,见证乃至亲历了频仍混战中四民制的崩塌与武士阶层牢固主从关系的断裂,他们都是拥有着武士身份印记的商人,同时,又有着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海洋贸易中海商所具备的亦贼亦商的属性。
那么,这些武士由于种种原因转而成为“海商”的时候,其尚武的本性是如何表现的呢?诚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战国时代,有这样的说法:‘杀人越货,是武士的习气。’对于战国武士来说,吃或被吃,兴或亡,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在关系生死的战斗中,自我保存的本能就是武士的生存之道,这里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①李冬君:《叶隐闻书》(导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可见,对于武士而言,把在战场上舍生忘死的武勇作为最高荣耀,事实上也存在着另一面,即在脱离了武士的身份和环境,成为海商之后,在生存与利益凌驾于一切规则与道义之上的海上,他们就自然表现出了杀人越货的冷酷无情,而他们的武士训练和军事实力成为他们谋求个人利益和施加暴力的最有效手段。正是因为这一点,如小说《海贼商人》《吕宋的壶》中,由武士转而为海商的“引込町人”们,在行海贼之事时,才显得那样轻松而没有疆界。或者说,海贼烧杀抢掠的属性,只是武士本然人格的表现。
事实上,日本的战国时代由武士转而成为商人尤其是海商的那些“引込町人”,因其武士的秉性,更有能力应对这一时期经常伴随着暴力的海上贸易。如在《吕宋的壶》中,“引込町人”的主人公大迫吉之丞在前往南洋寻壶的过程中,在经过东沙岛的时候,就遭遇了葡萄牙人的海贼船并与之交火,保全了购壶的资金。实际上,在海洋贸易法则与制度尚未建立的16至17世纪,在浩瀚的南洋海域往来贸易中,“海商”与“海贼”、贸易与暴力两者,实际上往往是很难截然区分的。例如在《海贼商人》中,助左卫门在南海初遇弥平太时,弥平太尚且属于李马鸿的海贼集团,他们才刚刚为了获取财物而进攻了马尼拉城,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海贼。而助左卫门不管在历史记载还是小说描述中,都是以一个商人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助左卫门却邀请落败的海贼弥平太跟自己一起返回日本并从事商贸活动。他说:“你是海贼的话,我也是海贼。换个说法,我是八分商人两分海贼,而你是八分海贼两分商人罢了。”作者南条范夫紧接着评论道:“贸易商人都会因时而变,成为海贼。在与对方交易决裂、发生纷争的时候,便会诉诸武力。另一方面,即使原本是海贼,如果发现有利可图的交易,也会放弃无谓的武力,以求能够获得持久的利益。”②南條範夫:『海賊商人』,第48~49頁。这也符合小说《海贼商人》的题名。而且,通过小说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所有在海上活动的人,不论国别、不论主业,其实都多多少少具有“海贼”的性质。例如,受命驻守马尼拉北部的守军司令官卡利翁,他按理说属于西班牙政府委派驻守马尼拉的官员,但是在抓获前往吕宋进行贸易的弥平太等人之后,为了获得他们的货物,对他们严刑逼供,并对弥平太百般羞辱:“一个海贼,难道想受到骑士的待遇吗?”弥平太反唇相讥道:“你以为自己就不是海贼了吗?从你们的总督到西班牙的每一个人,难道不都是海贼吗?”③同上,第116頁。真是一语中的。随着新航路的成功开辟,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扩张和掠夺,而他们的扩张,则主要是通过垄断商路、建立商站、欺诈性贸易乃至直接的掠夺金银等方式完成财富的攫取。这事实上和海贼的确一般无二。
不过,至少在当代小说家的笔下,这些日本的“海商”与“海贼”在整个海上贸易的过程中,还是主张尽量避免使用武力。如小说所写的:“与草率的掠夺行为相比,以琉球为中介,将日本与南方这些地方的财货进行交换,可以获得长久的可持续的利益。”①南條範夫:『海賊商人』,第95頁。但“也不是完全不用武力,在商谈无法顺利进行的时候,性急的同伴不免会使用武力,而且,为了防止对方的不当行为,武力的威慑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碰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时候,经常会发生武力冲突。在航海途中,遇上敌对的海贼集团,也会屡有交火”。②同上,第95~96頁。但是,“弥平太不允许部下对原住民使用武力,他认为,与原住民进行和平贸易,赢得他们的好感”是最为重要的。③同上,第95~96頁。这应该就是“海商”与海贼最本质的区别之所在。小说中的这类描写是符合商人的价值观念的,但是与其说这是历史真实的描写,不如说反映的是作者对“海商”的理想要求。
对这些由武士脱胎而来的“引込町人”与“战国海商”的描写,实际上仍然体现着武士最高的价值观念——“忠”,亦即对主君绝对的服从。例如,在《吕宋的壶》中,主人公受主君之命携带巨额资金前往东南亚寻找一把茶壶,途中经历种种波折与危险,其实他也有过对此行意义的怀疑:“前往吕宋寻壶不仅异常辛苦,还会时常遭遇这样的海贼船袭击。即便如此,也要花上白银千贯去买一把看上去并不漂亮的陶壶,他实在不能理解。千贯银就是一万七千两……造一艘可乘坐三百九十人的朱印船都也不过十五贯银……可供一掌把玩的茶壶就要花上一万七千两,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④久生十兰:「吕宋の壶」,第195页。但是当这种念头萌生的时候,他就会将之当作邪念去驱散:“吉之丞嘟囔着,这种想不明白的事情还是不要想比较好,他像要把邪念甩掉一样使劲地摇头”,而后专注于主君命令的寻壶之事。及至后来,他为了寻壶,一路辗转,从马尼拉到安南、交趾、暹罗而后到柬埔寨,最后偶然发现,被日本各大名疯狂吹赞,捧为天价的茶壶,不过是柬埔寨普通人的日用家当,只值十文粗币而已。但他依然将壶捧回了日本,只可惜历时太久,当时遍寻茶壶的德川家康已经逝世。这里所表现的武士观念与商业价值之间的矛盾与调和,比起商业价值的追求来,完成主君的命令更为重要。归根到底,这些武士在南洋的行为,貌似是商业性的,但同时更是探险的,是他们展示武士价值观的场域。这就是在南洋的战国海商和“引込町人”的重要特性。
不过,像《吕宋的壶》这样的作品,对于我们了解日本的“战国海商”与南洋的关系,还具有特殊价值。那把被赋予无限价值的“吕宋的壶”,很可能也是中国所产,可以表明南洋地区的贸易自古就是以中国商品为中心展开的。小说中从日本到马尼拉,再到安南、交趾、暹罗而后到柬埔寨,几乎辗转了当时日本人所谓“南洋”的主要区域,即吕宋群岛及东南亚半岛地区各国。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南洋这一区域作为“亚洲的地中海”,早已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繁荣的贸易圈了。①参见弗朗索瓦·吉普鲁著,龚华燕、龙雪飞译:《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广东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而《吕宋的壶》所描写的这个贸易圈,也就是近年来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在《东南亚贸易时代:1450~1680年》一书中所描述的公元1450~1680年间的东南亚贸易网络。②参见安东尼·瑞德著,孙来臣等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二、南洋的“日本人町”
历史上日本与东南亚的商贸关系,在东南亚各地的所谓“日本人町”意即“日人街”上,也有鲜明的体现。所谓“日本人町”,就是16至17世纪日本海外贸易繁荣时期,伴随着包括朱印船在内的贸易船的活动,在东南亚地区出现的日本人聚居社区。“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当时东南亚各地有许多相当大的日本人的街镇。越南的土伦、会安,泰国的阿育他亚(大城府)等最为著名。在吕宋、爪哇、柬埔寨,也都有这样的城镇。”③梅棹忠夫著,王子今译:《文明的生态史观》,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2页。据记载,当时通过朱印船出入日本国境的日本人就有十万以上,而朱印船的活动遍及菲律宾、越南、柬埔寨、泰国等整个东南亚地区。伴随着这些朱印船的活动,随船的日本人在许多港湾城镇建立起了日本人的侨居地,即“日本人町”。④梅棹忠夫著,杨芳玲译:《何谓日本》,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可见,这些“日本人町”的形成与当时日本海外贸易及伴随的海外移民密切相关。
正如上述历史记载及相关历史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日本与南洋地区的交往,最早始于日本的海贼南洋冒险。他们挂着“八幡大菩萨”的长条旗,从日本出发,从中国的南方沿海到东南亚,抢夺过往商船和当地居民的财物。随后日本进入得到政府许可的朱印船贸易时代。随着葡萄牙人以马六甲为开端在东南亚各地营建居留地,从事贸易活动,日本的朱印船也进入东南亚进行贸易活动。在德川家康禁止日本人外出贸易的1635年之前,日本与东南亚之间曾经有过长达30年之久的密切贸易往来。据研究记载,从1604年到1635年,日本至少向东南亚派遣了299艘船只,而每年运往东南亚港口的货物价值白银约20吨,同时运回价值相等的中国丝绸和东南亚的鹿皮、生丝、苏木、蔗糖、安息香、棉花和香料。而且,此时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额甚至都超过了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额。“赴东南亚贸易的中国船数目是日本船的十倍,但它们所运货物的价值却可能稍逊几分。”①安东尼·瑞德著,孙来臣等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二卷),第37页。随着日本与东南亚之间贸易往来的频繁,在东南亚各地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固定的交易据点和在该地调集储备货物的坐商,基于与随朱印船而来的日本海商交流的需要,这些坐商主要由日本人构成,由此渐渐形成了“日本人町”。“日本人町”的日本人来源主要有三类:“乘坐‘朱印’大船携带货物而来的商人。逃避受迫害的天主教难民,大多数定居在马尼拉。在内战之后流亡的雇佣兵。”②弗朗索瓦·吉普鲁著,龚华燕、龙雪飞译:《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第104页。这里所说的雇佣兵,就是在混战中失去家主的武士,他们部分会直接由武士转而成为海商,即“引込町人”,在日本与东南亚之间进行贸易往来。也有一些会选择前往东南亚成为雇佣兵,这些久经沙场的浪人,很快就成为当时东南亚地区最受欢迎的轻步兵的来源。
“町”字,在日本指的就是居民区,一般由40户人家组成,是构成城市的单元。而且,除了作为指代居民区的生活单位之外,“町”更是具有独立自治权利的行政单位:“对于居民而言,町不仅仅是一同生活的地域共同体,更是由他们自行运营的自治组织,也是统治者眼中的独立行政单位。”③梅棹忠夫:『日本文明77の鍵』,大阪創元社1988年版,第122~123頁。位于东南亚各地的“日本人町”也是如此,它们在南洋各地都是以日本人为首领,行政与司法等也均是独立于当地而在“日本人町”内自治的,当然町内的自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受到当地政府权力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日本人町”基本可以作为一个自治或者至少是半自治的政治经济实体发挥着它们在南洋贸易中的作用。
关于南洋日本人町的史料记载,最早可见于西班牙人阿尔亨索拉的《摩鹿加群岛远征记》,其中的1603年部分就提到了位于吕宋岛马尼拉市的日本人町狄拉(Dilao)。但是史料中关于日本人在南洋出现的记载要更早:“葡人占领满剌加时,日本人业已与暹罗交通矣。交通既久,遂有居留者矣。由中国沿岸被驱逐之倭寇,逃至此地者,尤属不少。嘉靖末年,暹罗已有日本佣兵。……暹罗载籍中关于日本人最旧之记录,厥为甫拉那勒托斯安王之记录。一五五九年(嘉靖三十八年,日本永禄二年),暹罗被缅甸及老挝等所侵,因防备得宜而获胜,相传军中有五百名日本佣兵。甫氏谓此等日本人乃由葡萄牙人诱来者,当可视为掠夺中国沿岸之倭寇也。”④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页。可见,在作为政治经济体的日本人町形成之前,日本人主要是作为雇佣兵在南洋活动的。这是因为“日本人因天生尚武,故颇珍重之者,不仅暹罗一国。欧洲人在东方之殖民地,亦常雇为卫兵,如荷兰人在马加撒(Macasar)及安波衣拿(Amboyna)等处所用者,亦为其例,最显著者,首推斐律滨”。①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第132页。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南洋的日本人与当地政府、住民之间就是一种既相互需要,又相互防备敌对的关系。
关于“日本人町”,除了历史记载、现实遗迹之外,日本当代文学中以“战国海商”及“引込町人”为题材的作品,也有生动具体的描写。例如,在南条范夫的《海贼商人》中写道,当时的菲律宾有一处大约500人的日本人聚居地,亦即“日本人町”,他们是在西班牙人进驻之前就住在那里的,几乎和本地居民没什么两样,但西班牙人依然对他们十分忌惮。小说写到了一个西班牙派驻马尼拉的官员对日本人町所采取的迫降计策。驻守马尼拉北部的守军司令官卡利翁等人决定通过离间居留马尼拉的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并在日本人町的上游建筑要塞、设置大炮,使他们完全降服于西班牙当局。首先双方派代表进行了对谈,在对谈中,卡利翁提出吕宋岛在1570年已被西班牙占领,是西班牙的要地,不允许外国人居留,让他们在一个月内离开吕宋岛,离开的人可获得一些黄金作为补偿,而后赠给他们一樽葡萄酒,让他们好好商议,就离开了。日本人纷纷意动,两天过去,卡利翁又告诉他们,所给的黄金数量和每人过去五年来的收入总量相同,日本人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金,纷纷夸大自己的收入,低评别人的收入,彼此争论不休。卡利翁在此期间假称去上游考察,在那里修建要塞。一个月过去了,卡利翁带着五个日本人来到建好的要塞,让他们交出过去五年的收入表,日本人交出之后,他们却说,既然收入这么多,就不必给补偿金了,还要将所报收入中的一年的份额交作税金,并且留下了四个日本人作为人质。在西班牙人大炮与舰队的威压之下,等待日本人的,除了屈服,只有死亡。②南條範夫:『海賊商人』,第102~112頁。
通过《海贼商人》的这些描写,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这一时期西班牙驻守官与“日本人町”之间紧张的关系,而这也是符合史实的。而当地西班牙殖民政府排斥“日本人町”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尽管日本人町主要是在日本与南洋通商往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贸易集散调配交易中心,但随着一步步的发展,“日本人町”还是引起了西班牙人的警惕与忌惮。如前所说,“日本人町”的人员构成中有不少人是日本的落魄武士,他们凭借其绝对的武力和果敢成为当地的雇佣兵,虽为当地所用,但也为当地所警觉,而且这些雇佣兵往往还会卷入当地的政治斗争,那就更遭排斥了。对此藤田丰八在《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中亦有所记载:“惟因日本人勇敢,不特使暹罗上下异常尊敬,且又非常恐怖。据云,仅以五六百日本人,亦足震骇全国。职是之故,暹王有事则利用之,无事则驱逐之,易词言之,与其谓敬爱,无庸係畏敬也。”③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第131页。其二,日本自德川家康去世之后,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开始了全面的锁国政策,朱印船贸易也逐渐减少直至终止,原就是因日本与南洋之间的贸易往来需要而存在的“日本人町”,也就自然失去了依托,“日本人町”与当地发生冲突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如藤田丰八所记:“一六〇六年(庆长十一年)西班牙人因事杀一日本人,在住之日本人,欲诉诸干戈,然西班牙人乃以此为机,复送还日本人矣。闻当时其数达一千六百人以上。实即西班牙人,对日本人之勇敢,至为恐怖,视为勇敢好事之徒。职是之故,该地之日本人,不超过五百名。”①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第133页。正是由于日本人町的这种特殊属性以及其商贸功用的锐减,南洋当地的殖民政府开始对其大加排斥,日本人町也渐次衰亡。从16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日本人町”是东亚东南亚海上交通与区域贸易的产物,而到了17世纪中后期也正是“战国海商”与“引込町人”天然所具有的武家特性,加上与西方殖民者利益的冲突,而逐渐趋于衰亡。《海贼商人》等日本文学作品,通过小说的方式表达了一些日本人对“日本人町”的记忆与追怀。而从区域形成的角度来看,“日本人町”的存在,也成为历史上东亚—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时期的一种遗迹。
三、从“战国海商”看中国文化之于日本与南洋
站在历史上的南洋—东南亚区域形成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对“海贼商人”“引込町人”的掠夺贸易还是对南洋“日本人町”的描写,都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历史上东亚—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而其中自然而又必然地涉及中国背景与中国文化因素,客观上反映了东亚东南亚地区复杂的区域关联。
纵观日本的对外交流交往史,我们不难发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都是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贡赐关系之中的。这种关系是在中国强盛、四邻弱小的前提下,中国通过“怀柔远人”所建立的一种“华夷秩序”,这种华夷秩序往往以朝贡贸易的方式维持着,中国以其绝对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文化吸引力确立其宗主国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但是,到了明朝,日本不再甘心居于臣属中国的地位,试图以种种方式打破并重建其与中国、与亚洲近邻的关系,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不管是倭寇在东亚海域的寇掠行径,还是日本这一时期对中国、东南亚、朝鲜的海外贸易,以及具有移民性质的东南亚“日本人町”的形成,乃至于日本的锁国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都是日本为了对抗甚至扭转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而去“创造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②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著,巫怀宇译:《葡萄牙帝国在亚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所做的尝试。如《亚洲的地中海》一书中所分析的:“日本的这些亚洲海外经济关系确立了一种国际秩序,是中国在亚洲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复制。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基于中国与未开化国家之间的对立。……然而,日本并未附庸中国。在德川时代,日本认为自己与中国享有同等地位。……这种解释也突出了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独立于中国成功建立的世界秩序。”①弗朗索瓦·吉普鲁著,龚华燕、龙雪飞译:《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第100页。在我们看来,那时的日本试图对抗中国,却正是中国的东亚中心地位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影响力的表现。而且,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在南洋地区活动,就不可能脱离中国因素。正如当代日本学者梅棹忠夫所说,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相继进入东南亚建立殖民地,“日本政府彻底丢弃了从前的犹豫不决的态度,积极地开展对外贸易活动,不断把朱印船派往更为遥远的南方地区。这样,对日本人来说,东南亚地区便成了不只同中国商人,而且同来自欧洲的喜欢冒险的商人们进行交易的场所”。②梅棹忠夫著,杨芳玲译:《何谓日本》,第94页。对这种情况,小说《海贼商人》也多有描写。这表明,即便是在东南亚海域,日本人也在同中国商人进行贸易。
日本南洋贸易以及与东南亚国家的往来,不仅仅是作用于经济层面的,也是日本与中国及东南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在《吕宋的壶》中,主人公奉命去找的茶壶,价值一万七千两白银,可以建造六十多艘朱印船,大迫吉之丞后来发现这种被捧成天价的茶壶不过是东南亚居民的日常用品,只值十文粗币。那么,在日本,为什么茶器被捧到了它本身价值之上如此之高的价格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茶道之于战国时代的意义去看,而战国时代的茶道文化,又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日本学者角山荣认为,当时日本的堺市在与中国明朝的贸易以及南洋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获得了相当的繁荣,而这些财富除了用于寺院建设之外,有很大的一部分都用在了茶道上。这是因为:“当时那种连父子兄弟都要互相残杀的,人与人之间缺乏相互信任的战国时代,在犯上作乱的、不安定并且无秩序的社会状况中,茶室便成为和平以及生命安全得以保障的唯一的场所。换句话说,要进入茶室,不管是多么了不起的战将,刀必须挂在刀架上,任何武器都不能带入茶室。也不能穿戴着盔甲进入茶室,因为人必须从小屋子边上的四方形的洞口式门弯着身子进入茶室。在狭小的茶室中,主人在客人面前亲自为客人沏茶,然后为证明其中没有放毒,主人和客人轮流传喝。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相互间的信赖关系。我们在此必须强调的是,主人为了尊重客人,诚心实意地款待客人,不惜把所有财产都耗费在茶道用具上。”③角山荣:《15~17世纪日本最大的贸易都市堺市的繁荣及其财富去向》,《海交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59页。由此可见,茶道在战国时代不仅仅是一种饮茶交际的礼仪,更是人们在血与火之中寻得短暂的心灵慰藉的神圣之所,这也是日本的将军、大名乃至商人们愿意将巨额财富投到茶器上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生活、交际以及心理上的需求,茶道在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架起了一道文化交流的桥梁。
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吕宋的壶》的主人公自日本辗转东南亚各地寻找茶壶一事可见一斑。主人公所要寻找的那把茶壶,其实本身就是区域文化交流的结果。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吉普鲁曾强调指出:“海上亚洲远不仅是一个海上通道和商品交换的问题。它还是一个传播、交流新思想和宗教信仰的特殊地区……如果说商贸活动总是与战争相联系的话,那么它同样可以促进不同传统、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①弗朗索瓦·吉普鲁著,龚华燕、龙雪飞译:《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第339页。这在《吕宋的壶》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吕宋的壶》通过一把茶壶的寻购,充分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与魅力。书中写道:“上等的吕宋茶壶,是莲花王与清香真壶……所谓莲花王,就是在壶肩的莲花纹样中刻了一个王字,而清香真壶也是在壶肩上刻了清香二字。”②久生十兰:「吕宋の壶」,第193頁。茶壶上所刻“王”与“清香”皆为汉字,而且小说交代此种茶壶为东南亚普通百姓的日用品,可见当时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化已然通过贸易深入东南亚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而“王”字又刻在莲花纹样之中,众所周知,莲花是佛教的标志性纹样,《楞严经》便有云:“尔时世尊,从肉髻中,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坐宝花中,顶放十道,百宝光明。”《诸经要解》也说:“故十方诸佛,同生于淤泥之浊,三身证觉,俱坐于莲台之上。”可见,莲花在佛教中代表着出淤泥浊世而又得悟解脱的净土诸佛,而佛教发端于印度,经海路传往东南亚,成为老挝、柬埔寨等国的主要宗教。《吕宋的壶》中主人公奉命所寻的壶上刻着莲花纹样,显然是受佛教文化影响的结果。当然我们亦有足够的理由推断,此种陶壶本就是从中国经由海路贸易流向东南亚诸国的,因为古代中国海外贸易中主要的商品之一便是陶瓷。无论如何,小说中所寻的茶壶都可以说是中国、日本、东南亚乃至印度文化交流互通的载体,而主人公从日本辗转东南亚各地寻壶之事也可以说是16、17世纪以海外贸易为途径达成亚洲区域文化交流乃至文化认同的一个缩影。
四、结语
“战国海商”或“引込町人”是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的产物,也与当时东亚、东南亚海上贸易的总体情势有关。“战国海商”或“引込町人”在南海及南洋海域的活动,固然带有海贼的侵略属性,同时也有经贸往来乃至区域文化交流的意义,并在客观上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确认以中国商品及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其中所包含的南洋意识或东南亚观,也值得我们的东亚、东南亚区域研究者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