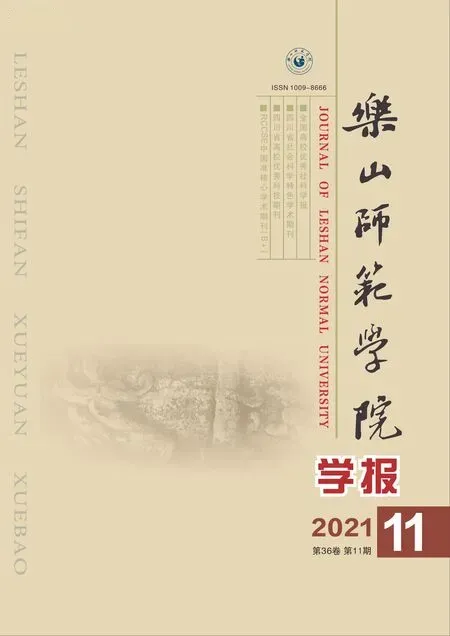论胡铨对苏轼的接受
仲 恒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苏轼是宋代最为杰出的文学家,代表了宋朝最高的文学成就,他在诗词上非凡的成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而他在贬谪中体现出的超脱旷逸、随遇而安、洒脱豪放、幽默诙谐的人生态度更是深刻影响了后代文人。胡铨作为南宋四名臣之一,与苏轼的时代相隔不过百年,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对苏轼的学习与继承,然而“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1]4,胡铨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对苏轼贬谪时期的文学创作与人生观念进行了改造,使其呈现出另一番图景。当前学界关于南宋文人对苏轼的接受研究业已形成一定成果,如杨胜宽先生的《东坡与放翁,隔代两知音——论陆游对苏轼思想和文艺观的全面继承》[2]一文系统地分析了陆游的思想价值观和文艺观对苏轼的全面继承,金欢的《张元干词对苏轼词的接受研究》[3]、范亚光的《苏轼与辛弃疾乡村词比较研究》[4]及张美丽的《论张孝祥对苏轼词的接受和推重》[5]等文章亦从个人入手,论述了张元干、辛弃疾、张孝祥等人对苏轼词风、词法的继承与学习,而蔡龙威的文章《论苏轼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坛的影响》[6]则论述了包括胡铨在内的南宋高宗朝文人对于苏轼的诗风与人格的继承,程千帆先生的《两宋文学史》中也提到“宋室南渡后,苏文盛行”[7]151。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进行胡铨对苏轼的接受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预留了丰富的空间。
一、胡铨对苏轼的继承与学习
胡铨对于苏轼的继承与学习是全面的,他不但仰慕苏轼文学作品中丰富的艺术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在文学创作上对其进行模仿;还倾心于苏轼高尚的人格品质,在人生观念、生活习惯上与其为同调。
(一)继承苏轼的人生观念
胡铨对苏轼的学习与继承首先体现在他对苏轼生活方式与人格精神的模仿与推崇上。苏轼重视养生,在《养生》一文中阐释了对养生“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的看法,而胡铨就追随着苏轼的理论写下了《继东坡三养说》,提出“少食以养脾,少噍以养齿,少味以养寿”[8]335的养生观念,和苏轼一起追求淡泊的生活,以此延长生命的长度,体现生命的价值。而且胡铨的《读坡文杂记》中记载:“宝朝议送瓦垄子……将烹食之。偶开东坡诗集,忽见《岐亭戒杀》诗云:‘我哀篮中蛤,闭口获残汁。’……戒余勿复杀耳。”[8]340胡铨在将烹蚶子之时,因为苏轼的一句诗,不但让仆人救出蚶子,而且改变了他往后的生活习惯,从此不再杀生,可见苏轼对胡铨影响之深。另外,苏轼在黄州时生活贫困,所以将俸禄分为三十份,挂在房梁之上,每天只取一份,而胡铨也神追此事,在次韵苏轼的《追和东坡雪诗》中写道“三百青铜落画叉”[9]21590,所谓画叉就是取高处之物的工具,胡铨以此化用苏轼“房梁挂钱”的典故,也体现了胡铨对于苏轼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慕。
对于苏轼的人格精神,胡铨也时时学习。苏轼在多年的贬谪痛苦与人生的两难选择中完成了对于生命的超越,将一切苦难淡化,以安然自得的心态让自己的灵魂得到解脱,呈现出一种乐天知命的旷达姿态。胡铨受到苏轼旷达心境的影响,在与李光讲述自己的贬谪经历时,有过“每念通判兄七十年归故里,苏子卿十九年归汉,万里辽东亦归管宁……自戊午被放及今……比东坡多十年……如厄运渐满……岂可便作死汉看,谓不生还待下哉?若厄运未满,更展十年,不然更展二十年,尚得如通判兄还乡,有何不可?”(《与振文兄小简》)[8]189的言论,胡铨认为自己的贬谪经历较之各位先贤不值一提,而若运数当转,则可立刻复起;若运数未转,即便是再过十年、二十年又何妨?这种旷达胸襟与苏轼“此道固应尔,不应怨尤人”(《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一)[10]4914的乐天知命态度十分相似,也是仿照苏轼的“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十月二日初到惠州》)[10]4440,将自己的贬谪与历史上先贤因贬谪而漂泊天涯时的命运和心态进行比照。另外,胡铨每每将以自己为中心,将包括李纲、李光、赵鼎等其他三位名臣以及郑刚中、王庭珪等同道的交游圈比作苏门:“东坡北归,叹范纯夫、秦少游已死。赵元稹、郑亨仲、陈少南、高彦先惜亦不见太平也。”(《与周去华小简》其二)[8]183胡铨感动于苏轼与苏门众人之间相濡以沫的深情,并在自己与其他主战派谪臣之间也挖掘出了这种同道之情,以此作为自己超脱苦难、坚持理想的支撑之一,让自己得以砥砺前行。
(二)继承苏轼的作品风格
胡铨不仅吸收了苏轼的生活方式与人格精神,还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苏轼的作品风格,有着与苏轼如出一辙的旷达、豪迈与幽默。苏轼在诗中书写自己的贬谪时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10]5130,而胡铨也把贬谪荒涯说成“万里投荒真细事”(《元夕与监务宋皋饮罢踏月观灯用坡老儋州上元韵》)[9]21585,苏轼在蛮荒之地没有魂惊魄悸,而是对自己得食荔枝的闲适生活感到满足:“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其二)[10]2312胡铨身处岭南时也以“今岁荔枝能好”让自己“休恼,休恼”(《如梦令·谁念新州人老》)[11]1613。同样是被贬谪到当时国家版图中环境最为恶劣的海南,但二人面对自己的悲凉身世时都能做到淡然处之、悠然化之,以乐观的态度将对苦难的被动承受转换为主动的接纳与超越,呈现出很高的思想境界。身处谪途的诗人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有更多机会接触秀美河山,而面对自然风景时,苏轼有过“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郁孤台》其一)[10]4378的诗句,胡铨承袭苏轼的胸怀,写下“山为翠浪涌,湖拓碧天开”(《登南恩望海台》)[9]21576。二人把层峦叠嶂比作奔涌的滔滔翠浪的同时,一人说河水如天外玉虹般流淌,一人说碧绿的天空倒映在湖水中伴着微波拓开。字里行间皆是旷远的天地和壮美的山水,一切景语皆情语,心中没有广阔的天地,笔下也就不会有奔腾的河流,二人笔下开阔宏大的天地里蕴含着他们一脉相承的豪迈意气。另外,苏轼和胡铨的作品中也充满了对生活本身的热爱,有着诙谐幽默的风格,苏轼的朋友得子时,他作的贺词中写朋友对自己说“多谢无功,此事如何着得侬”[12]82(《减字木兰花·惟熊佳梦》),用晋元帝生子,朝臣殷羡说自己无功受赏,甚是惭愧,元帝说“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13]129的典故来比照自己和喜得贵子的朋友,令人不禁捧腹。胡铨在得知朋友生孩子后和张庆符以孩子是男是女打赌,并作词记录此事,用了与苏轼相同的词牌和典故:“试问坡翁。此事如何著得侬。”(《减字木兰花》)[11]1611他和张庆符开玩笑说要问问苏东坡这事怎么能让你出力呢?二人的生活环境是十分艰险的,但他们偏偏能在其中发现生活的乐趣,并以诙谐幽默的笔法将其印拓在作品中。胡铨诗词中这些思想内容和苏轼一脉相承,说明胡铨对于苏轼的继承与因袭不单单体现在接受苏轼面对贬谪的人生态度和处世观念上,还把承自苏轼的超脱旷逸、豪迈不羁倾泻在自己的作品之中。胡铨在南宋初期江西诗派雕琢词句之风盛极一时的环境下坚定自己的选择,吸收苏轼作品的内蕴,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格。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胡铨创作诗词的过程中在语句结构上有意地模仿苏轼,苏轼写“九死南荒”,胡铨即云“万里投荒”;苏轼仿照张志和写“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浣溪沙·西塞山前白鹭飞》)[12]372,而胡铨也模仿着写道“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也须归”(《鹧鸪天·癸酉吉阳用山谷韵》)[11]1612;苏轼说“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10]4375,胡铨就借此以实例抒发感慨“北往长思闻喜县,南来怕入买愁村”(《贬朱崖行临高道中买愁村古未有对马上口占》)[9]21573。所以胡铨在诗词创作方面对苏轼的承袭也不单体现在有着和苏轼一样的旷达乐观、豪放洒脱与诙谐幽默上,还体现在对其语句构造和典故运用的学习上。
(三)学习苏轼的作词方法: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词作的显著特征,胡铨对此也有很明显承袭,其词作一洗苏轼之后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派绮艳柔靡的风格,继承了苏轼的作词方法。苏轼的“以诗为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胡铨的词作中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内容:首先,苏轼显著地扩展了词作的题材,无论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12]409的超脱雅趣、“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念奴娇·赤壁怀古》)[12]391的怀古幽思,还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12]131的悼亡伤怀、“醉笑陪公三万场”(《南乡子·时移守密州》)[12]69的酬唱情谊都可以成为他词作的描写对象,极大提升了“词”这一体裁的表现范围,而胡铨的词作也是如此:有描写自己狂放情态的“浩歌箕踞巾聊岸”(《醉落魄·百年强半》)[11]1612,还有在赠答之作中赞美友人的“雅歌长啸静烟尘”(《转调定风波·和答海南统领陈康时》)[11]1611,更有辛辣讽刺朝中奸党的“空惹猿惊鹤怨”(《好事近·富贵本无心》)[11]1614等,把丰富的生活体验融入词作,与花间词只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做法有云泥之别。其次,苏轼与胡铨等人的词作都是有感而作,缘事而发的,如诗作一般,直白坦率地表达情感,增强了词人的主体地位,而不像花间及大晟词派的作品动辄借他人之口,发无病之呻吟。苏轼的词作中如“老夫聊发少年狂”(《江城子·密州出猎》)[12]136、“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黄州中秋》)[12]262等词句皆是针对自己生活中的真实经历表达出不同的情感,而胡铨的词作中“弄琴细写清江引,一洗愁容”(《采桑子·甲戌和陈景卫韵》)[11]1613这样通过描写个人生活中的细节来表现自己心境的语句也比比皆是。
另外,苏轼与胡铨“以诗为词”一改旧词的“艳科”传统,营造出开阔超旷的意境,塑造了高妙的词格,他们的词作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的悲歌壮语、一个胸怀宽广的文士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苦难的超越与对理想的执著,而绝非花前月下小儿女的含情呓语或廷下词臣对太平盛世的粉饰之言。他们都是高吟“大江东去”和“云帆万里雄风”的慷慨豪士,而绝非低唱“玉炉香,红蜡泪”和“明映波融太液”的纤弱文人、御用词客。
最后,胡铨对苏轼“以诗为词”的继承还体现在对于词序的运用上,为词加词序是从苏轼开始运用的一种和诗序一样可以解释作品内容、交代创作背景、沟通作者与读者的创作手法,词序对于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词序,“以诗为词”理论中词作表达作者主观情感的“言志”功用就很难实现,故词序可以说是东坡词论中的核心内容之一。而胡铨总共存词十六首,其中十三首都用了词序,可见其对苏轼的学习。胡铨对苏轼作词方式的继承体现了他对苏轼全方面的学习与推崇,这种词作形式和内容的承袭更是说明二人心中同有豁达人格和高远境界,胡铨效仿苏轼,把“诗言志”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歌传统带进了词作之中,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透射出他人格的独立和理想的高昂。
二、贬谪时胡铨与苏轼不同的人生态度
纵然胡铨对于苏轼仰慕之情极其浓厚,受其影响十分深刻,然而毕竟生活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精神内核,所以二人虽然同样是被贬遐荒,但胡铨对贬谪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较苏轼有所变化。
(一)安贫和取义,达者与鸿儒
“重道”是儒家从孔孟时代就流传下来的核心思想,孔子的一句“君子忧道不忧贫”,很好地诠释了儒士们为了心中的理想而不计较个人生活境遇的安贫乐道的情怀,而孟子的“舍生而取义者也”则进一步体现了一个心怀天下的儒士为了道义不惜放弃生命的态度。这种“重道”的思想在胡铨和苏轼身上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二人贬谪的原因都是他们对于道义的坚守:苏轼敢于针砭炙手可热的新党为政之弊,全然不在乎个人荣禄,他的《山村五绝》[9]867-871尖锐地描摹出新党执政后,农村民不聊生的景象,这样的鲠语忠言后来也成为了乌台诗案中他谤讪朝政的罪证之一,苏轼“一肚皮不合时宜”,敢于为百姓说话,为道义发声,而不是一味地“识时务”。胡铨的“重道”则表现得更为激烈,在抗金形势一片大好之时,高宗朝廷主持了议和之事,他直接当朝上疏,针对主张议和的秦桧、孙近和王伦,表示自己“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戊午上高宗封事》)[8]47,这种不畏强权、挺身而出、抗言直谏的勇气千百年后依然清晰可见。
然而同样是“重道”,苏轼和胡铨二人在贬谪后对它的体现却有所不同:苏轼更多是一种经受苦难时的超脱与旷达,偏向于在贬谪生活中以淡然的心态和看破人生的智慧去化解痛苦,同时始终不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准则,体现出一种安贫乐道的精神;而胡铨则更多是对道义始终如一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可以为道义牺牲一切的舍生求道的价值取向。这两种不同表现的背后是苏轼和胡铨不同的精神内质:在苏轼的身上,儒家安贫乐道的思想与道家的逍遥思想、佛家的空幻思想相融合,体现出三教圆融的境界。在苏轼的作品中,“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醉白堂记》)[14]1072这样的话有着道家“超脱世外”之痕迹,而“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平山堂》)[12]237等又明显地流露出佛家“四大皆空”的思想,他将三教互证,以求内心宁静,通过佛老的空与静,实现了儒家所谓的“乐天知命”。而胡铨则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儒士,他的身上很少有佛道的空灵幻寂和超然物外,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佛道的排斥心理。绍兴十二年(1142),胡铨被贬至新州时,好友王庭珪作《送胡邦衡至新州贬所二首》为其送行,其中赞颂胡铨上书言斩秦桧等三人,羁押金使的壮举是“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9]16794,高度称赞胡铨清刚正直、心怀忠义之心,而胡铨在酬答王庭珪的诗作中也把王庭珪比作“万卷不移颜氏乐,一生无愧伯夷班”(《和王民瞻送行诗二首》其一)[9]21587的纯儒,说明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这种立志“致君尧舜”的忠臣、潜心孔孟之道的儒者才是最值得学习的。而对于佛道,他在次韵苏轼的《乙未元夕坐有用东坡上元韵二首》中曾经以“漫云学佛竟何曾”以及“见说燧人初改火,固知将圣信多能”[9]21585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学佛”前加一“漫”字,表达对佛家思想的不认可,而结尾将伏羲、女娲之父燧人氏与佛陀进行对比,得出“为人们带来火种的圣贤确实能力更强一些”的结论。所以苏轼和胡铨二人,在人生观念、生活态度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同时,又呈现出安贫的达者和取义的鸿儒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二)逍遥与执着、生命与家国
除了儒家“重道”的思想在二人身上表现出不同的两个方向以外,二人面对贬谪的态度在超然旷达、豪放洒脱的基础上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苏轼更加偏向于个人的超脱,他可以站在俗世之外,用饱经沧桑的目光去看待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以一种“游”的状态经历红尘,以逍遥游世的手段来消解贬谪中的痛苦,将万里投荒视作出游甚至是回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别海南黎民表》)[10]5119和“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郁孤台》其二)[10]5248等诗句,都蕴含着他做到了极致的随遇而安、淡泊世事的思想。他也可以让自己融入世间,享受生活的美好,赞美自己生活之地的风物人情,用日常中细小的欢乐来安慰自己,他在黄州体味着“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的美好生活,在惠州欣赏“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食荔支二首》其二)[10]2312的秀美景象。而且苏轼常将谪地比作自己的故乡,说自己虽像是贬谪,但其实是还乡,如“仿佛曾游岂梦中,依然鸡犬识新丰”(《十月二日初到惠州》)[10]4440就用汉高祖将新丰改造后,鸡犬依旧识家的典故来说惠州如家乡,而在儋州时更是直白地说“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10]4835,苏轼面对贬谪时,用这种心理层面的自我宽慰,使艰险困阻的谪途变得稍显通达。另外,苏轼贬谪的痛苦中还包藏对人生空幻的领悟,如“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黄州中秋》)[12]262等诗句,便抒发人生如梦幻的感慨。总之,苏轼面对贬谪时的种种旷达豪放之语,皆是为了消解自己的痛苦,让自己在心灵上得到自足,从而实现对生命的超越。
而胡铨面对贬谪时的超然旷逸则是支撑自己执着地坚持理想的一种方法,他学习苏轼的豁达从而让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使贬谪中的痛苦难以给自己带来悲戚之思,这样就能够以一种更加昂扬向上的姿态,来蔑视那些给予自己苦难的奸佞宵小,让自己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家国天下,胡铨的贬谪文学作品向我们展现的是他坚定的意志和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同样是化用张志和的《渔歌子》中“青箬笠,绿蓑衣”一句,苏轼《浣溪沙·西塞山前白鹭飞》说“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12]372,表达其随遇而安的心态,而胡铨《鹧鸪天·癸酉吉阳用山谷韵》则说“青箬笠,绿荷衣。斜风细雨也须归”,随后又表示虽然“崖州险似风波海”,但是“海里风波有定时”[11]1612,表达了他对南宋王朝海清河晏、政通人和的强烈信心。当时的主战派文人普遍认为他是穷途中愈发坚定、落魄中不改初志、心如劲箭、肠似钢铁的执着之士,如王庭珪说胡铨的贬谪是“朱崖万里海为乡,百谏不屈钢作肠”(《胡邦衡移衡州用坐客段廷直韵》)。胡铨也说自己“久将忠义私心许,要使奸雄怯胆寒”(《乾道三年九月宴罢》其二)[9]21577,其浩然正气、凛然英气跃然纸上。胡铨贬谪时对朝政臧否和家国安危的忧虑在其诗词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朝中措·黄守座上用六一先生韵》中“日下即归黄霸,海南长想文翁”[11]1613之句,说明他在万里之外的海南依旧渴望着出现黄霸和欧阳修这样的政治家,力挽南宋朝廷的颓势。心忧国政的同时,胡铨更是心系南宋王朝的危机,他切慕像岳飞这样“张皇貔虎三千士,支持乾坤十六年”的民族英雄,而认为最终的议和带来的是“万姓颦眉亦可怜”[9]21576(《题岳忠武王庙》)的结果;他还溯洄历史,时时神追曾经扬中原王朝雄风的人物,例如“龙勒殊勋标绝域,麟宫奇节障狂澜”(《送王嘉叟侍郎使虏仍用其韵》)[9]21583的苏武和张骞就是他热烈颂扬的对象;对于苏轼的家国情怀,他也在《临平道中用坡老雪中长韵答刘寺薄》中表达过自己的看法:“苏仙漫解赋晓浩,韩子亦徒歌晚澌。两翁句法岂不好,祗欠鲠语书安危。”他认为苏轼和韩愈虽然句藻华美,但终究少了对社稷安危的忧虑,而一个真正的儒士是“致君宜许尧相稷,活国未惭唐宰墀”[9]21584的以身许国之人,这样的说法对于苏轼和韩愈虽有偏颇,但也体现出了他对于国家安危的挂念。所以,胡铨在面对贬谪时,虽然有着和苏轼一样的豪迈豁达,对苏轼的生活观念、人格精神也颇有推崇,但他在绝境中依然挂怀国家与人民的骨鲠忠诚与苏轼有所不同。
三、胡铨接受苏轼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胡铨对苏轼的接受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转变,在面对贬谪的苦难时,体现出一些差异。这种继承和转变源于此二人所生活时代的背景、政治环境和人生境遇的同和异。
(一)继承的原因
关于胡铨为何如此全面地继承苏轼,大体上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南宋初立时“党元祐”的政治风尚引起了“崇苏热”。在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南宋人不可能把北宋亡国归咎于赵家天子,所以南宋时文人大多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前朝抗金战争失败的根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范冲入对时说:“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15]1487认为王安石变祖宗之法,使天下人心术不正,从而导致朝纲混乱,神州陆沉,这代表了当时主流文人的看法。而且北宋末年把持朝政的正是属于新党的蔡京等人,时人声讨以蔡京为代表的新党祸国殃民,而旧党的代表苏黄等人因为在政治立场上与新党对立,其著作在新党发动的“崇宁党禁”中被尽数焚毁,所以被视作受新党迫害的贤良。宋高宗在面对强敌环伺、百废待兴的局面时,必然要追求政治上的稳定以保证南宋政权的存息,所以选择了趋于保守的元祐旧党,这与文人们一拍即合,随即提出“最爱元祐”的政治口号,自此苏轼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力显著提升,所以,胡铨作为当时的朝中文臣,受苏轼的影响很深。
另一方面是胡铨有着与苏轼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是性格清刚正直、敢于指出朝政弊端、为国家和百姓说话的文人,苏轼在新党炙手可热之时作诗讽刺变法对百姓生活造成的影响:“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10]869,以辛辣的笔调展现民生疾苦;而胡铨在目睹朝中贵胄权臣奢靡腐化的生活后,也大胆指出他们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之际仍然“玉磊尘清闲擂鼓,玳筵风静细流觞”,整日耽于享乐,和“血蹴红凝箭”“苔欹绿卧枪”的“哥舒”与“子美”(《题崖州洗兵亭》)[9]21574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不畏强权的性格,必然会遭到强权的忌恨,所以二人都是在党争中被扣上了谤讪朝廷的罪名,苏轼因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湖州谢上表》)[14]2577而被新党之人大做文章,搜罗其讥讪国事的证据,从而引发乌台诗案,几乎将被赐死,虽幸得生还但也开始了他多年的贬谪生涯;胡铨在被贬新州后由于词中的“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好事近·富贵本无心》)[11]1614,被秦桧党羽张棣告发,以诽谤怨恨朝廷之罪,被贬至海南。胡铨另一点和苏轼人生经历重合的地方在于他们二人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选择,苏轼曾说:“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与李公择十七首》其十一)[14]5617,表示自己从未忘记自己的政治理想,随时可以捐躯许国;胡铨则对好友王庭珪说“非我独清缘世浊,此心谁识只天知”(《和王民瞻送行诗二首》其二)[9]21587,表达了对朝中乱象的讽刺和孤芳自赏的清高傲然。胡铨和苏轼的贬谪地点也都是当时最为偏远的海南,胡铨在孤悬荒岛之时可以继续保持坚定的斗争精神,以豁达的态度面对眼前的种种龌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胡铨知道在五十年前,有一位和自己境遇十分相似的先贤也曾在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经受着不亚于自己的苦难却依旧云淡风轻地微笑着,这让他产生了“了解之同情”,给了他极大的鼓舞,让他可以不改初心,坚定地走下去。
(二)转变的原因
对于胡铨与苏轼在贬谪时表现出的心态有所差异的原因,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点。
首先是南宋的时代环境发生了变化,靖康之耻像一根刺扎在了南宋有志之士的心中,北方沦陷的大片国土、被金人羁押的徽钦二帝、死在金人屠刀下的百姓以及金人再次南侵的威胁,都成了他们难以释怀的东西。所以这些主战派的文人以慷慨激扬的文字表达抗金的决心与对议和的反对,表现出强烈的忠君精神和忧患意识。岳飞满怀激愤地说自己一定要“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满江红·怒发冲冠》)[11]1615;胡铨追忆往事“微管闲思齐仲父,赐奴长价汉浑邪”(《次李参政送行韵答黄舜杨》)[9]21590,想起尊王攘夷的齐相和降汉的匈奴王,迫切希望有人扬大宋天威 ;陈与义以“ 庙堂无计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来批判朝廷昏庸无能、不思进取,导致“上都闻战马”和“穷海看飞龙”(《伤春》)[9]19554的恶果;陆游对北方“泪落胡尘里”(《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其二)[9]14780的遗民表示同情,并期盼可见到“王师北定中原日”(《示儿》)[9]15722。胡铨是南宋四名臣之一,作为南宋初年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的亲历者,他的作品是南宋初期时代精神的展现,必然有着与其相匹配的忠贞凛然的金石之声。
其次是南宋的政治环境与胡铨性格之间的碰撞,沈松勤先生认为南宋士人是“集官僚,学者和作家三位一体的性格类型和社会角色,于政争,学术和文学三个层面,则必有内在联系,三者是个有机的统一体”[16]321。高宗朝前期朝堂之上暗流涌动,宰相频繁更换;后期又是主和派掌权,奸佞小人秦桧一人独大,独相专权十七年,士风更加败坏。与此相应,高宗朝文网罗织,笔祸迭起,高宗与秦桧以高压政治钳制文论,为排除异己,履兴文祸、诗祸构陷忠义之士,动辄指其谤讪朝廷。胡铨即因“有豺狼当辙”一句词,被贬至更为偏远的吉阳军。而且南宋谪宦中贬至岭南并渡海者几倍于北宋,岭海之地历来是谪居或流放的绝地,是宋代除死刑外对文人士大夫最严重的惩罚,从此也可以看出南宋党争手段更为残酷。另外,最高统治者始终对主战派心存反感,高宗曾对秦桧说:“今者和议,人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若无赏罚,望其为国实难。”[15]2530由此可见,胡铨等主战派的生存环境何等艰辛。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与胡铨清刚正直的性格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胡铨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能允许他坐视朝纲混乱、苍生倒悬,同时宋高宗及秦桧等人也不能容忍像胡铨、岳飞这样力主抗金并且有能力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的贤良屡屡抗颜上疏,或倡导北迎二帝,或针砭混乱时政,来破坏自己的切身利益和不愿醒来的“天下太平、王业已安”的春秋大梦,随着宋金《绍兴和议》的签订、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震动朝野,二者的矛盾达到峰值,随后胡铨即遭贬黜,开始了长达32 年的贬谪生涯。“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的胡铨定是义愤难平,作品中便会有所体现,而秦桧书胡铨姓名于一德格天阁,誓必杀之以后快,亦定会借其诗文进一步进行打压,如此矛盾便绵绵不断地延续下去,从而让胡铨的诗词中充满了爱国忧民的精神和独守清高的人格。
最后,是“春秋之学”的影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对胡铨的人格精神与作品风格产生了影响的基础上,潜心于“春秋之学”导致其对克复中原念念不忘。胡铨的“春秋之学”师承乡贤萧楚,入仕前萧楚曾告诫他“学者非但拾一第者耳,身可杀,学不可辱,无祸吾《春秋》乃佳”(《清节先生墓志铭》[17]153),“春秋之学”也确实跟随了胡铨一生。在南宋民族矛盾日盛的局面下,《春秋》中最受人重视的观点就是“夷夏之防”,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并高度评价“相桓公,霸诸侯”、尊王攘夷的管仲,《春秋左传》也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汉朝时董仲舒提倡的“春秋大一统”更是发展了“华夷之辨”。胡铨学《春秋》时结合时代,自然最先想到的就是春秋大义中“尊王攘夷”的思想,他曾说“贾谊以中国为首,夷狄为足,而以首反居下,足顾居上为乱亡之基,此严中国夷狄之分也”(《讲筵礼序》)[8]252,表达其对和议停战,卑躬屈膝于蛮夷胡虏的行为辛辣地批判和深切地担忧。这样也就不难解释他身上为何有着对北伐抗金的执着和使命感。
总之,苏轼是胡铨面对贬谪时的人格典范,他的精神风范和生命境界成为了胡铨的榜样,为胡铨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但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终究不同,胡铨的知识结构与苏轼相比亦有所不同,所以苏轼的贬谪文学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超脱苦难的同时,还满怀忠贞气节的铮臣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