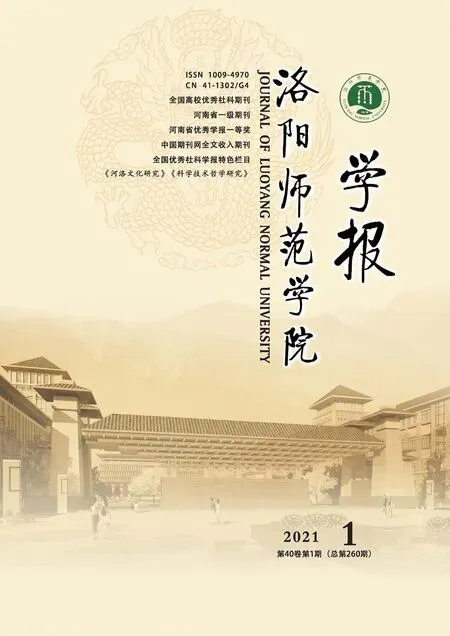从人物向人口的转变: 叙事学视域下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易 娟, 李作霖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7000)
1969年“叙事学”一词声名渐赫, 在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下, 早期叙事学家的 “开疆拓境”铸就了叙事学的知识模型。 1997年, 赫尔曼引出“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概念, 旧的叙事学探究方法由此得以丰富, 时至今日, 叙事学理论的发展已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研究领域上讲, 开启了跨媒介等方面的拓展。 从方法上讲, “技术”正在不断革新, 英国叙事学家图伦用语料库文体学的方法来研究短篇小说中的叙事进程。 曼尼用计算的方法来标示叙事文本内的时间, 同时还追踪叙事进程中的读者动力层面。 有学者言叙事学已由“理论的黄金时代”转向“阐释的银色时代”。[1]以文本研究为中心还是构建广义叙事学仍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矛盾在于叙事本身的复杂性与叙事学发展的不足性之间, 这使得全方位、 多途径的审视叙事成为必要。 弗朗索瓦兹·拉沃卡女士关于“虚构人口”的研究诚然为叙事学这门新兴的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一、 人口统计方法的可存在性
托多洛夫认为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是任意媒介的叙事(文字、 图画、 声音)。 然而, 学科的发展并未完全遵循这种设想, 它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叙事文本中。 弗朗索瓦兹·拉沃卡的研究旨在以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对叙事的讨论早在柏拉图时期就已开始, 作为叙事的要素, 人们对“人物”一词也早有探讨, 申丹在其著作《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对文学理论史中人物的研究作了总结与梳理, 将其划分为“功能性”的人物观和“心理性”的人物观。
“功能性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 情节是首要的, 人物是次要的。”[2]亚里士多德可视为“功能性”人物观的开创者, 他在《诗学》中定义: “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悲剧。 但没有‘性格’, 仍不失为悲剧。”[3]在这种定义下, 人物的性格仅仅在行动之时被附带表现, 而对人物的研究注重的是其叙事功能。 由此, 亚里士多德在最适合喜剧或悲剧情节发展的人物之间提出了一种道德上的区分:好的、 坏的, 和两者都不是的。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 普罗普最早系统地分析人物的“角色”功能。 他指出: “功能可被理解为人物的行动, 其界定需视其在行为过程中的意义而定。”[4]基于人物的某一行动与整个故事的关系, 他将作品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抽象地归纳成七类: 主人公、 假主人公、 坏人、 施予者、 帮助者、 被寻觅者和她父亲。 普罗普的分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开辟了道路, 因为就结构主义所采用的归纳法而言, 人物的行动比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更易着手。 布雷蒙提出不能局限于人物的功能, 还要研究由功能组成的序列(功能与行动相关, 一系列行动组成序列则产生故事)。 他认为“每个人物都是自己序列的主人公, 从不同的主人公出发, 同一人物在同一事件中可以起不同的角色功能”[5]。 格雷马斯借用语义分析, 在“音位”上将人物分为三对对立的行动者: 主体与客体、 发送者与接受者、 帮助者与反对者。 托多罗夫则从语法角度入手, 他指出文学仅仅是某些语言属性的扩展和应用, 并聚焦于指涉人物的专有名词。
“心理性”人物观恰与前者相反。 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某种心理实质的“人”, 人物的出现不是为了推动情节, 而情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则是为了揭示或塑造人物性格。 19世纪以来的传统小说批评家基本持此观点, 他们对人物的研究注重的是人物的心理和动机,也会探讨人物所属的社会以及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 其中以福斯特为代表, 福斯特认为人物至少在小说世界里是活生生的, 基于此, 他将人物分为“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 扁形人物性格单一, 圆形人物则性格丰满。
二、 人口统计方法的可操作性
人口统计是一种从“量”的方面去研究人口现象的方法或学问。 通过人口统计, 可以揭示人口现象背后的规律和本质, 这种方法通常用于现实世界的人口调查。 然而, 虚构世界里同样有数量庞大的人类和动物(据统计, 《红楼梦》中出场人物有983人; 《清明上河图》上共画人物1643人, 牲畜208头), 以人口统计作为观察角度, 无疑颇具新意。 2009年, 人口统计学家卡罗尔·布鲁杰勒斯和西尔维·克罗默展开了对法国儿童教科书的研究, 根据其中的性别分布和表现, 谴责儿童教育中的性别偏见。 随后, 另外两位人口统计学家罗曼尼·博福特和卢卡斯·梅利森特对《权力的游戏》(以图像、 声音为媒介的叙事作品)进行了研究, 并得出一系列结论。 比如其中胖人的死亡概率比瘦人高三倍; 受挫(喜欢的角色死亡)和奖励(出场时间最长的人物更不容易死)的频繁出现能够在受众心中造成惊讶、 好奇的效果。 两人认为, 只有统计学才能把我们从图像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由此可见, 虚构人口的统计事实的确能揭示某个时期或地域特有的潜意识偏见和某些特定的叙事逻辑。 除此之外, 用此方法对同一时期不同地域文学作品作横向比较, 以及对同一地域不同时期作纵向比较皆能在已有叙事学研究基础上有所收获, 弗朗索瓦兹·拉沃卡女士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三、 人口统计方法的具体操作
人口统计的科学方法以客观性展示为目的, 运用于文本的虚构世界, 它的技术属性要求跨学科协作(与计算机科学家和人口学家合作)。 但是迄今为止, 能够自动提取人物及有关信息的成熟软件还未面世, 研究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拉沃卡团队目前主要以畅销于19世纪上半叶英法两国的图书为研究范围, 她认为那个时代得到广泛关注的图书更具代表性, 其中法国22部, 英国39部。 之所以如此选择, 一是这两个国家19世纪上半叶文学产业较之同时期其他国家发达; 二是此时期两国崇尚现实主义, 小说家们认为小说应该是对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描述, 这使得虚构世界与真实世界具备一定的可比性, 从而扩宽了研究的维度。 除此之外, 拉沃卡又补充了27部女性作家的代表性小说, 旨在研究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笔下的人物有何不同。 另外, 因《人间喜剧》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之誉, 所以其中24部也尽数被纳入数据库。 拉沃卡的研究以此112部小说为基础。
由于文本中人物呈现的复杂性, 如回溯性人物、 梦境中的人物, 因此拉沃卡将文本中的虚构世界区分为主要的故事世界和可能存在的第二世界(对于这两个世界, 分别展开研究), 如果人物只是有所提及, 不属于二者任意其一, 则不被考虑。 随后的数据计算分作三类: “总体的人口状况(人口的发展、 数量、 增长或减少)、 人口繁殖方面的数据(死亡率与出生率、 流产数量)、 人口社会状况(贵族的比例、 男女的比例、 职业、 外国人数量)。”[6]对于人物社会背景及职业的分类则以1851年法国真实人口统计数据关于社会及职业的分类(略作简化)为准, 具体包括法官、 残疾人及住院精神病人、 樵夫等52类。 拉沃卡团队的研究自2015年开始, 为期5年, 截至2018年初, 已经有83部小说得到处理。 研究发现, 若将小说词语总数量与人物总数之比命名为人口密度, 法国小说的人物平均密度为2.8(每个人物平均2800个词), 英国为2.4, 就此层面, 英国小说的人物密度略大于法国。 其二, 实际人口与虚构人口之间出现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巧合, 1813年司各特出版《威佛利》之前, 英国畅销书大多呈现中等及以下人口密度的世界, 在此之后, 高密度人口小说蜂拥而出并大获成功。 而英国实际人口增长率得到飞跃正是司各特高密度人口小说产出的时期(1811—1821年)。 一两列数据的泛泛之比能尚不能说明问题。 但是, 对具体作品的大数据作比较, 的确为叙事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一)作家与人口风格
拉沃卡最先提出“人口风格”, 指的是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呈现出的人物密度设置、 人物再出现机制等方面的整体趋向。 拉沃卡认为, 作家叙事时会无意识地表现出某种人口风格, 比如司汤达的《红与黑》《巴马修道院》, 前者发表于1830年, 后者发表于1839年, 两者情节颇具区别。 但是, 两部作品具有相同的人口密度, 其中虚构人口的构成(有姓名人物的数量, 无姓名人物的数量)也颇为相似。 这种现象并不是个例, 巴尔扎克的作品同样呈现出某种人口风格。
数据显示, 如果按发表时间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24部小说的词语数量与人物数量作纵向比较, 作品中的人物数量在逐年递增, 人物密度也在不间断增长。 此外, 另一组数据则显示, 巴尔扎克不同作品中人物的社会背景呈现出某种重复的迹象。 据此, 拉沃卡提出, 随着《人间喜剧》写作计划的推进, 巴尔扎克确立了“人物再出现机制”(这种人物再出现机制并非巴尔扎克特意为之的“人物再现法”), 并且布置了若干系列准备插入未来作品的人物。 如“贵族系列 (格朗利厄家族、 勒农古尔、 勒托雷、 阿德居达·平托、 莫弗里浬斯、 旺德内斯、 拉斯蒂涅克、 德玛塞、 波当杜埃尔), 作家和艺术家(维尼翁、 卡纳利、 比多、 费里西代·德都什、 纳当、 达尔泰、 雷翁·德·里奥拉)”[6]。 巴尔扎克通过插入重复出现的人物来扩充小说, 这种情况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尤为明显, 如在《幻灭》(1844年发表)中, 重复人物占73%, 而在《人间喜剧》的最后一部《交际花盛衰记》中, 重复率达到了77%。 除了重复人物之外, 拉沃卡还发现巴尔扎克在许多作品中, 通过家族或者利益的关系网来扩展人物, 如在《农民》中, “正是成千上万的家族以及乡村之间的联合关系, 最后占领、 瓜分了美丽的阿尔戈城堡”。 不过, 在拉沃卡已发表的论文中, 由于课题还未截止, 因此并没有数据呈现。 如果得到有力的论证, 对于巴尔扎克及其他作家的叙事逻辑研究而言会是一大启发。
(二)性别与叙事差异
数据表明, 男性与女性作家的小说在人口配置方面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异。 首先, 中等及以上人口规模的小说(50人以上), 几乎没有一部是出自女性之手。 其次, 女性完成的小说中, 人物多为贵族(大多数作品占70%以上), 而男性作家的作品呈现出平民化趋势。 再次, 女性所写的小说中, 女性人口占50%, 但男性作家笔下, 比例往往低于20%。 最后, 女性所作的小说较之男性所作的小说往往出生率很低, 而死亡率很高。 以《克莱尔·达尔博》与《幽谷百合》这两部情节相似的小说作比较, 颇能揭示差异。 前者为索菲·柯丹所作, 后者出自巴尔扎克之手, 两者皆为书信体小说。 《克莱尔·达尔博》中只有8个人物, 算上无名姓的和略作提起的, 是27个。 而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 人物多达71个, 如果加上暗示群组人物数, 就是 1139 个。 索菲·柯丹的小说中, 女主人公行动的范围仅包括达尔博先生的城堡和周围的乡村, 而《幽谷百合》男主人公费利克斯的行动范围则广得多。 这种对比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性别(作者和人物)对情节、 行动、 人口规模因素的影响。 对于发展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而言, 拉沃卡的人口数据分析或许能提供某种便利。
四、 结语
如上文所罗列, 人物向人口转变的方法的确能为叙事研究开辟蹊径, 但是局限同样存在: 第一, 数据库仅以文学史中的畅销作品为基础, 是否存在某种缺漏? 虽然畅销书较之非畅销书更具扩充语料库的有效性, 但两者之间的区分又如何避免某种后来的主观性?第二, 拉沃卡将作品中的虚构人口与历史中的现实人口直接进行比较, 是否忽视了文学作品的虚构性? 即使作品基于现实, 但对于《变形记》等诸如此类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作品, 人口统计法又如何施行并奏效?第三, 拉沃卡在已有研究中强调性别差异对叙事的影响, 但此结论早已是叙事学领域之共识。 再者 “动态叙事”“物叙事”等多种维度层出不穷, 对巴尔扎克等作家的叙事探究如何创造独特价值, 觅得叙事学领域一席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