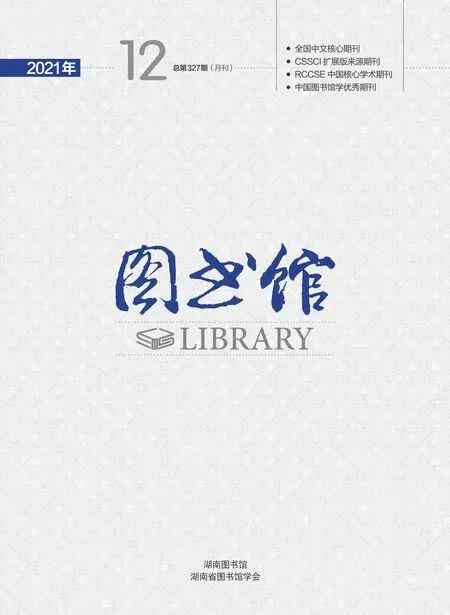澳大利亚高校数字人文中心调查与分析*
王利君 杨友清
(1.中南大学图书馆 长沙 410000; 2.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江苏无锡 214000)
目前,以数据密集型计算为基础的科学研究第四范式正在兴起,该范式以数据为核心,催生了数字科学、数字社会科学与数字人文科学[1]。数字人文把信息技术和人文学科方法论相融合,为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了新认识、新视野,吸引了文学、历史学、图书馆学等多个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研究热潮。数字人文获得快速发展,国外许多高校纷纷建立了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并开展和推进了大量的数字人文研究项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国际数字人文中心联盟网站(CenterNet)显示,截至2021年3月底,全球范围内共有203个数字人文中心在网站上进行注册登记[2]。
我国对于数字人文的研究起步较晚,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研究广度都需进一步加强,存在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规模小、资金支持渠道少等问题,但国内学者对于高校如何开展数字人文实践做了一些积极探索,多集中在数字人文教育、项目透视、数字人文服务等方面。如介绍国外典型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运作方式并进行项目分析,能客观反映国外数字人文发展的进程、模式,为我国数字人文发展提供有益借鉴。目前,已有诸多学者对国外数字人文实践情况进行了研究,如邓要然等[3]总结了美国高校数字人文中心的运作机制,为我国图书馆开展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了建议。杨友清等[4]概述了加拿大数字人文中心服务的开展情况,以期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人文服务提供参考。林泽斐[5]基于DHCommons项目,梳理和分析了英国数字人文项目的内容,为我国开展数字人文项目研究提供了相关启示。
总体而言,我国学者主要集中在对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欧美主要国家的数字人文实践进行研究,而对澳大利亚的数字人文实践研究缺乏关注。笔者以篇名和主题词在CNKI数据库里检索“数字人文AND 澳大利亚”,仅检索到2条相关的研究文献。事实上,澳大利亚较早就开展了数字人文实践,并于2011年成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国家级数字人文研究专业组织——澳大利亚数字人文协会(AADH,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for Digital Humanities),AADH是国际数字人文组织联盟成员之一,旨在加强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数字人文研究、交流,并设立了专门的数字人文奖——“约翰·伯罗斯奖”。除了AADH的大力倡导外,澳大利亚政府机构也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并投入资金,为数字人文研究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大环境,如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的“联动基础设施、设备和设施”计划投入大量资金资助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在线语言档案馆项目,激发了研究者参与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研究的热情。此外,澳大利亚高校也是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参与者,众多高校纷纷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与到数字人文研究的大浪潮中,纷纷成立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积极开展项目研究和教育培训,为澳大利亚数字人文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笔者选取了澳大利亚具有代表性的10所高校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特征进行归纳和分析,以加快我国数字人文研究步伐。
1 调研方法和研究对象
文章运用网络调研法和内容分析法作为调研方法。网络调研方法,在参考国际数字人文中心网络CenterNet上澳大利亚登记的7个数字人文中心的基础上,调研了澳大利亚排名前20的高校网站主页,一一访问,在高校主页搜索框中输入“digital humanities”,此外,还访问了澳大利亚数字人文协会(AADH)网站,了解澳大利亚高校开展数字人文研究的情况。最后选取了12个运营成熟稳定的高校数字人文中心作为研究对象。笔者通过对网站的多次访问和浏览,在12个数字人文中心网站中搜集了其机构隶属关系、数字人文团队情况、数字人文项目和教育职能等信息,利用案例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网页调查法,对项目的研究领域、工具技术和主题内容进行了分析,形成调查研究报告,总结数字人文中心的运营规律,探索数字人文项目的发展态势。
2 澳大利亚高校数字人文中心调研结果分析
2.1 组织隶属关系
12个高校数字人文中心的机构名称和组织隶属关系如表1所示,大部分机构名称包含或体现了数字人文的本质特点。澳大利亚的数字人文中心,往往在从事数字人文研究和项目管理的基础上,还承担着教学培训、研究成果出版管理、新闻宣传报道、召开学术会议、举办展览等职责,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和信息技术的交融。在组织隶属关系上,高校数字人文中心的隶属机构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隶属于学校院系。这是绝大部分数字人文中心的组织模式,在学校院系中,又主要集中在人文学科院系。本次调研中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纽卡斯尔大学、伊迪丝·考恩大学、悉尼大学、西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和堪培拉大学的9个数字人文中心都是隶属于艺术、教育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院系,只有莫纳什大学的Sesi实验室属于信息技术学院,偏向于信息学科。一类是隶属于图书馆,如墨尔本大学的eScholarship研究中心是由图书馆管理和运营的。一类是单独的研究机构,如科廷大学和昆士兰大学的数字人文中心属于学校独立机构,它们跨学科组建独立的团队来开展数字人文的实践活动。

表1 12个高校数字人文中心组织隶属关系
综上,澳大利亚高校数字人文中心的建设主体较为多元化,但基本以学校的人文学科院系为主,特别是艺术学院在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此外,高校图书馆、独立机构也积极参与了数字人文机构的建设。
2.2 人员构成
数字人文中心都跨学科和跨学校组建了团队,团队规模庞大,研究角色较多,如堪培拉大学团队有76人,西悉尼大学团队有73人,其他学校团队人数一般在20—40人之间。各数字人文中心团队构成类别,主要有负责人(主任)、专职员工、学科专家、博士生、兼职和访问学者等: ①主任。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研究角色复杂,存在学科文化隔阂,需要管理人协调好各方面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澳大利亚创新组织建设,实行中心主任负责制,主任一般是研究中心隶属学院的教授、院长或系主任等,研究领域交叉性强,具有较高的声望及丰富的跨学科项目研究经验,能把握组织发展方向。如伊迪丝 ·考恩大学数字人文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数字人文与社会科学系主任,专业涉及英语、传播和文化研究等多个学科,是澳大利亚和国际上数字人文科学领域的领先人物。②专职员工。专职员工是数字人文中心的全职研究人员,是核心员工,设置的职位有数字人文发展官、办公室行政管理人员、项目协调人员等,负责中心的管理、培训、项目协调、宣传等各项事务。③专业学科专家。学科专家是各团队的重要组成人员,人数较多,所占比例大,他们来自学校不同学院和机构,涉及历史、法律、设计、传播、计算机等多个学科,为开展数字人文项目汇集在一起,负责教学任务、研究活动。④博士。博士往往担任研究助理角色,一般也是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学生,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西悉尼大学、莫纳什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都开设了数字人文专业,开展数字人文教育。⑤访问学者。包括访问学者和客座教师,研究中心聘请的外部学者一般是在国际数字人文领域具有一定专长、经验丰富的行业专家,如西悉尼大学聘请了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开展数字人文研究的伦敦国王学院的教授作为访问学者[18]。
目前澳大利亚高校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人员结构较为完善,主要以中心的专业员工和各学科专家为主力军,以博士生、学术访问和交流人员等为辅助人员,组建一支可提供专业学科、信息技术、行政管理、学术交流咨询等多项服务为一体的多元化、跨学科创新团队,这种跨学科的团队合作模式将会有力促进数字人文研究的长远发展。
2.3 数字人文项目
2.3.1 研究学科领域分析
数字人文研究大部分通过项目的方式开展,项目将规划、管理、协商和合作等工作流程归入学术研究的形式和表现情形之一[19],项目一般通过团队协作的方式开展。笔者对当前9所高校的11个机构正在开展的114个项目进行梳理发现,项目数量最少的是伊迪丝 ·考恩大学,项目为2个;项目数量最多的是莫纳什大学,项目达34个;其他学校项目分布较为均匀,数量基本都在5—15个之间。
高校研究的这114个项目,在学科领域上,涵盖了人文社科的大部分学科,涉及地理、法律、图书馆学、考古学、艺术和语言等多个研究领域,部分项目内容涉及多个学科研究领域,这充分体现了数字人文的跨学科特点。例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罗马坎帕尼亚的数字制图项目。根据1600到1900年间描绘罗马坎帕尼亚的山水画来研究当时的地理环境,涉及历史、地理和艺术等多个学科领域[20]。研究发现,历史学、语言和文化学、艺术学、社会和心理学是澳大利亚高校数字人文项目的热门研究领域,文学、地理、建筑等学科也在数字人文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数字人文具有鲜明的工具属性,为了推进经典阅读、文化交流,项目使用了多种数字工具作为技术手段来实现文化资源的再利用和开发[21]。这些项目主要使用了数字化技术、文本挖掘技术、可视化技术、3D打印技术、3D建模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沉浸式技术和GIS技术等。其中,数字化技术、可视化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是当前项目中普遍运用的技术。
2.3.2 研究内容分析
学科领域分析可从学科的角度对数字人文项目进行归类,但无法全面揭示项目的内容特征。笔者通过对数字人文中心网站上这114个项目的题名和内容描述等信息进行梳理,归纳出澳大利亚高校开展的数字人文项目的主要研究方向。
数字历史研究项目。数字技术和历史研究相结合进行的研究,可叫作数字历史,数字历史是数字人文的一个关键分支研究领域。人们把数字化技术、可视化技术、GIS和3D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中,通过勾勒不同时空的地理建筑,对地理数据进行标示、抽取和有序化组织,对史料进行数字化保存,发掘其背后价值,进而推动人文学科的转型和创新。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传记中心的首批三支舰队和家属项目就是一个历史数据的分析与可视化项目,对当时舰队幸存下来的人及其家属后代生活进行跟踪和分析,通过数据挖掘、网络分析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制作人物出生地点图、死亡地点图、家庭关系图等,将地理空间和特定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用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出这些家属后代的网络关系图和生活轨迹图[22]。莫纳什大学Sensi实验室的中世纪大都会建模项目属于历史场景的视觉重建项目[23],从历史文献和考古研究中抽取数据信息,使用3D建模、3D动画以及虚拟现实技术来数字模拟重建一千年前的吴哥窟遗址,除虚拟重建外,该研究基于GIS数据集和考古学的机载激光雷达调查草拟了吴哥窟虚拟地图,可以身临其境对建筑群进行分析研究,体验历史重建虚拟场景。
语言与文化研究项目。计算机运用于语言学,最早开始于1960年的计量语言学领域,目前,数字化技术已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关键工具,采用文本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方法,构建数字档案库,探索语言原生特征,丰富语种多样性,拯救濒临灭绝的语种和保护文化遗产。悉尼大学的语料库实验室属于语料库建设项目[24],旨在澳大利亚推广语料库语言学,它是一个虚拟实验室和在线平台,开发了澳大利亚布朗语料库、澳大利亚预算演讲库、糖尿病新闻语料库和悉尼电视对话库四个语料库。语料库经过了词素化、词性标记和语义标记,支持用户通过CQPweb方式,对语料库进行搜索、频率分析、搭配分析、关键性分析。悉尼大学的PARADISEC项目[25],是一个语言研究项目,主要对亚太地区的濒危小语种进行数字化收藏和保存,收集的语言包括文本、音频和视频等类型。目前该项目收藏了1 200多种语言,创建了符合相关标准的元数据,提供访问和搜索服务,并开发出各种模型,支持用户使用Elan或Fieldworks等工具,对馆藏进行添加和分类。此外,高校的语言与文化研究项目还包括字典编撰、语言文学作品研究等方面的内容。
艺术研究项目。 澳大利亚数字人文项目中的艺术研究部分涵盖电影、音乐、舞蹈、戏剧、新媒体等领域,表现出种类多而分散的特征。其内容主要包括搜集数字化和可视化艺术作品资料,保存和恢复特殊的艺术作品等方面,利用可视化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将艺术与新技术相融合,透过艺术视角来揭示人类情感和社会变迁。如墨尔本大学的可视化特殊音乐作品项目,使用Sibelius对澳大利亚20世纪以前未出版的稀有音乐手稿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使之转换成数字音乐[26]。墨尔本大学的戏剧和舞台平台项目是一个数字归档项目,重点记录和搜集了澳大利亚及国际上重要剧场的舞蹈和戏剧现场表演资料[27]。
多数艺术研究类项目都编制了在线数据库,内容包含文本、照片、海报、音频和视频等多种类型,支持在线访问和搜索。少数项目使用数字工具展开了创新性的艺术研究,如莫纳什大学的学者利用AirSticks工具将电子音乐和身体的律动连接起来,把人类双手从键盘和鼠标中解放出来,为那些残疾人、自闭症患者和对音乐没有较好认知的人演奏音乐提供了方便,人们可以通过创新的手势控制器软件来控制和指挥音乐演奏[28]。
社会和心理研究项目。澳大利亚社会和心理研究项目主要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内容挖掘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沉浸式技术等来分析和研究人类的社会关系、社会情感、社交活动和心理感受,以更深层次地挖掘和描绘现代大都市生活下人们的活动和心理,更直观地反映人们情感,探索人物行为的因果关系。如莫纳什大学的SensiLab实验室通过建立虚拟现实电影院、实验性场地等[29],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和沉浸式技术使参观者体验孕产妇分娩的经历,感受和探索初为人母者的内心情感世界,用数字技术实现人类情感和心理感受的转移。通过开发一种类似家庭的虚拟环境,让自闭症患者在其中以玩游戏的方式与人接触、交流,训练和发展他们的认知和社交技能,这作为一种新型的心理治疗手段,辅助改善人类的社会关系。
此外,项目还注重挖掘数据背后人类社会行为的意义,如伊迪丝 ·考恩大学的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项目[30],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内容挖掘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澳大利亚接近投票选举年龄,即16—19岁之间的这部分青少年群体,在社交平台Twitter和Facebook上发布的有关政治方面的言论、观点等信息进行挖掘和分析,来了解这部分群体的政治观点,有助于政府和相关机构掌握澳大利亚的政治民意和民主格局,以通过数字技术来研究人们复杂社交活动背后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表现。
研究分析发现,澳大利亚高校数字人文项目主题较多元化,项目主题内容主要聚焦在数字历史研究、艺术研究、语言与文化研究、社会和心理研究等方面。这四方面主要反映了特定的人文研究主题,同时项目也注重对数字人文工具的开发,为研究提供了工具和技术保障。从数字人文项目的研究手段而言,澳大利亚高校一般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数据库建设、视觉重建等方式,并运用关联数据、项目网站和API等形式来实行项目信息和资源的分享。
3 运作模式
3.1 积极与校内外机构协调合作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进行研究的过程,会涉及项目、资源、平台、设备、软件工具等,是一项繁复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校内外多方人力、物力、资金和技术的支撑。为了更好地进行数字人文研究,澳大利亚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在人才培养、设备资源、项目研究和实践等方面,积极与校内外机构合作,充分整合、开发、利用校内外数字人文资源。如悉尼大学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与权利研究所、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研究中心、数据转化研究中心等校内研究机构一起合作举办数字人文研讨会、讲座和课程,并将贝克特数字手稿项目嵌入到学校的课程当中。此外,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还加强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与堪培拉国家文化和收藏机构进行合作,后者为其开展数字人文研究与教学提供场地、资源和培训等支持。
只有积极与校内外机构进行合作,才能引入高端的学术资源、汇集先进的软件与工具、争取数字研究项目和培训机会,营造良好的数字人文研究的环境,加强资源、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保障,促进知识创新,进而加快数字人文的发展。
3.2 一体化协作服务平台
澳大利亚高校的数字人文中心具备多种功能,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来推动计算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交融,是一个成熟的一体化协作服务平台。平台的资源与服务范围较为广泛,用户可实现对数字人文资源的统一访问,同时也能为师生和科研人员提供多方位的研究支持。平台具有多种功能,一方面,具有教育和宣传功能。如开设数字人文专业,招收和培养专业学生,举行数字人文领域的研讨会、讲座、培训班等活动。平台注重互动交流,新闻资源等信息更新及时,具有较强的时效性。笔者调研发现有10所高校都开通了数字人文的Twitter、论坛、播客和博客等社交网站,定期更新相关新闻、动态和研究,支持在线点评和互动交流,有效促进了跨学科交流和创新研究。另一方面,中心也是一个信息发布和存储平台,具有发布管理和成果分享,保存数字人文项目的功能,是一个信息资源的公共数据中心。另外,中心还提供软件、技术、工具、资源等支持。
此外,各高校平台普遍重视对资源的整合和深层次加工,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发的数字人文开放平台MetoDHology[31],对本机构和外部的数字人文资源进行了整合和分类标引,涵盖学习视频和教程、参考书目、软件工具、博客文章等各类型资源,并提供了对应的软件、资源下载地址,同时提供即时的线上交流和咨询。堪培拉大学的创意与文化研究中心对所收集的数字人文领域的资源进行分类,将资源按书籍、音频、报告、诗歌和研讨会等类别罗列出来,并提供对应的下载地址[32],还定期发布数字人文领域的年度发展报告。一体化的数字人文服务平台,可为人文学者开展数字人文研究提供有效的资源与服务保障,满足研究需求的多样性,能有效传播学科知识并创新人文研究。
3.3 “项目制”运作方式
“项目制”是数字人文中心运作的重要方式,数字人文中心是为有效开展数字人文项目,而提供项目整个生命周期阶段服务和技术支持的协同创新型机构。特定领域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应用要通过项目形式得以实现。澳大利亚高校数字人文中心以项目聚集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和各类资源,中心设有项目管理、行政、宣传培训、技术支持中心和信息服务等部门,各部门协同配合,在主任负责制下,为数字人文项目的运行提供必要的技术和管理服务。澳大利亚高校开展的项目一般是由人文学科专家带头发起,提供知识创新点,然后由中心和合作机构的其他人员提供技术、服务、资源或培训等支持。知识传播创新(Innovation in Knowledge Communication)项目[33]是科廷大学文化技术中心与该校计算研究所、知识解锁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项目,项目负责人是中心开放存取领域的专家教授,科廷计算研究所和知识解锁研究中心分别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和服务支持。项目成员中也包括数据分析与工具开发人员、图书馆员等,为项目提供技术和资源支持。
高校数字人文中心是各类数字人文项目的“孵化器”,为项目开展提供一系列的资源与服务支持。同时,项目制是数字人文中心的主要运行模式,项目通过实践来实施,团队在实践中得到不断锻炼,提高了科研综合能力,有效推动了数字人文中心的发展。
4 启示
国外高校的数字人文中心建设已较为成熟,我国相对比较落后,起步时间较晚,发展还很不全面。我国国台湾大学于2007年及武汉大学于2011年成立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两者都是centerNet成员,是我国建设较早的数字人文中心,这标志着数字人文服务在国内开始兴起。之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上海图书馆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数字人文工作坊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等机构相继成立,加快推动了我国数字人文学科的研究与发展。但总体而言,我国在数字人文中心建设方面还停留在探索阶段,各方面建设还不成熟,大部分高校的数字人文中心的工作集中在提供本校数字人文相关的资源与信息,开展工作坊等基础层面,开展的项目并不多,服务模式和服务内容也较为单一,缺乏突破和创新。因此我国可以借鉴澳大利亚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建设的成功经验,以促进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
4.1 组建跨学科团队合作,创新组织建设
大科学时代,知识创新的爆发点、涌现点越来越多集中出现在跨学科团队合作科研活动中[34],跨学科创新团队研究问题从多个学科角度出发,从多层面来协商合作,进行知识创新,在新的交叉研究领域,比如数字人文学科,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效用[35]。数字人文本身就是多学科的融合,是典型的文理交叉领域。澳大利亚12个数字人文中心,从中心建设的主体,包括图书馆、独立机构和人文学院,到研究人员的所属机构、研究角色和学科背景都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这样一支跨学科、跨部门、跨区域的学科团队,在共同协作、创新知识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学科文化隔阂、学术地位博弈等挑战。同时,数字人文中心集教学、项目研究、学术出版、技术开发等于一体,里面所有的环节都需管理人员与各部门进行沟通交流。基于此,澳大利亚高校开拓思路,研究中心统一实行主任负责制,由中心主任进行统一管理,把握整体战略方向,专业员工在主任领导下,明确各自岗位职责,负责培训、项目协调等活动,保证组织的有序运行。
有效的组织结构是跨学科研究合作高质量开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高校在组建跨学科团队进行数字人文研究时,应根据中心人员规模、研究角色分布、项目开展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创新组织建设。如果研究中心规模庞大、专业员工充足,可借鉴澳大利亚数字人文中心自上而下的组织架构模式,实行主任负责制。如果研究中心人员分布较散,只以开展项目为目标聚集在一起,或者有些学校并没有建立专门的数字人文中心,可实行矩阵结构制。矩阵结构是一个纵向和横向管理相结合的经典结构模型,学校可根据矩阵结构组建一支数字人文跨学科团队,按照项目的实际情况,灵活吸纳或聘请专家,待项目完成后,团队人员返回院系。矩阵结构模式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可以有效满足分散型数字人文团队的需求[36]。
4.2 建设数字人文一体化服务平台,注重对资源和服务的深层次加工
数字人文服务平台不只包含了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也包含了给数字人文研究学者提供系统化的数字人文学科领域相关的工具、资源、信息和服务的网络平台[37]。服务平台对相关领域信息资源的收集,能实现用户对数字人文学科资源的一站式访问,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资源保障。澳大利亚高校的数字人文服务平台资源丰富,服务范围较广,并注重对资源和服务进行深层次加工。如莫纳什大学的SensiLab开设的论坛模块[38],用户可利用论坛进行互动交流,并查询相关信息和在网上观看主题讲座、研讨会的视频。昆士兰大学的研究计算中心与学校图书馆保持密切合作,图书馆负责平台的元数据设计与管理、研究数据发布标准等工作。我国高校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如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中心网站缺乏在线交流和咨询栏目,互动性不强,资源和新闻更新不及时,平台在资源的深层次加工与服务方面较为欠缺。大多数平台仅提供了本机构内部的数字人文研究资源,并未收集数字人文领域外的信息资源,资源组织上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缺乏突破与创新。
图书馆在资源的提供和组织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馆员在信息资源的采集和加工上拥有一定的专业优势。首先,图书馆应充分挖掘内外部资源提供信息服务,促进数字人文知识的交流和传播,包括采集讲座、数字人文课程、项目案例资料、数字工具列表等相关数字人文资源,并对收集的资源进行评估、组织和存储,加工处理元数据,转化为可以规范引用的开放数据集。其次,图书馆应充分利用自身的数据管理能力,提供数据服务,创新人文研究。例如,图书馆可以对用户在使用平台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挖掘和分析,以发现潜在的和深层次的用户需求和用户行为进而提高服务质量。最后,图书馆可以发挥参考咨询工作的人才和经验优势,在服务平台上开展咨询业务,建立用户互动系统,通过FAQ、电子邮件、表单提交等方式来回答用户提问。平台还可以链接到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如南京大学的“零壹 Lab”、武汉大学的“数字人文咨询”微信公众号,与用户开展互动交流,促进深层次交流和合作。
数字人文学者从海量信息资源中获取可用的、与数字人文研究相匹配的信息能力有限。高校应充分认识到建设数字人文服务平台的必要性,图书馆可以借助高校的科研资源和人才优势,建设数字人文服务平台,对资源与服务进行整合和深加工,以管理者的身份参与到数字人文研究当中,为高校开展数字人文研究提供相应的服务和保障。
4.3 加强与校内外机构合作,深层次开发数字人文项目
从上文的数字人文项目的主题和内容可以看出,澳大利亚高校数字人文项目建设已较为成熟。澳大利亚高校运营的数字人文项目数量较多,研究主题较多元,实践性较强,且积极与校内外机构及学科专家合作推动项目开展。澳大利亚高校开展项目的合作机构主要包括国家相关部门、研究协会和学校三类,为项目开展提供各方面的支持。空气遗产项目[39]是堪培拉大学创意与文化研究中心开展的一个为期三年的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关联项目,该项目的合作伙伴包括澳大利亚航空服务局、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和民航历史学会等国家相关部门和研究组织。
数字人文项目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人力、物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目前我国数字人文中心开展的项目不多,且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古籍保护、古代诗词文学作品上,研究主题较为单一,研究内容不够丰富,合作力度不够。我国高校在建设数字人文项目时应积极寻求与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甚至不同国家的机构或研究团队合作,数字人文应用项目建设的初衷是加大对特色资源的开发与共享,势必要确保资源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兼容性[40]。
此外,澳大利亚高校建设的数字人文项目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在不断拓展,已深入到资源内容的知识单元,注重项目内容的细粒度,用数字人文技术方法实现了对资源的深层语义描述与揭示。如悉尼大学数字人文中心开发的语言档案项目PARADISEC[41],是由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共同建设的,项目注重资源描述,强化数据结构并突出元数据功能,元数据包括符合开放语言档案社区和都柏林核心元数据集的子集,元数据描述项较多,并且元数据著录标准灵活多样,完成了检索单元从粗粒度的模糊性检索到细粒度碎片化的精确化检索的过程,该项目的信息和数据以网站形式对外共享。目前我国高校数字人文实践项目缺乏对项目语义的深层次挖掘,在建设数字人文项目时应利用元数据著录方式对资源进行组织、描述与揭示,为数据库的建设提供内容与技术支撑。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项目实践应该把资源、技术和标准三者进行有效联合,对项目资源实行深层次开发和利用,才能将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通过结构化、形式化的方式提供开放的数据和知识服务,注重成果的呈现、宣传和展示,共享项目内容,进而推动数字人文领域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