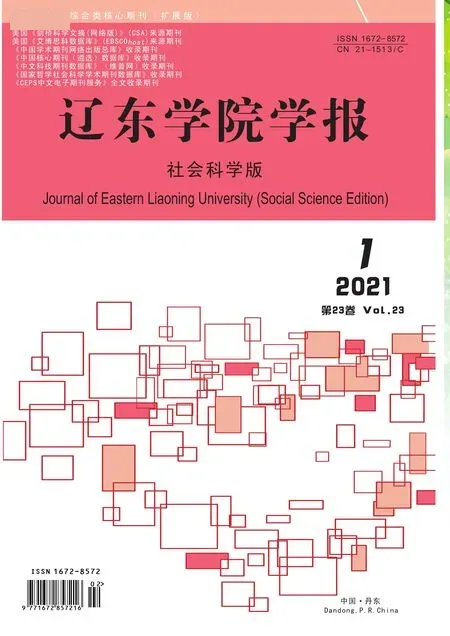西欧文学中的那耳客索斯母题*
——与主题学相关的几个问题
弗雷德里克·戈尔丁,著;王 立, 程铂智,译
(1. 纽约市立大学 城市学院,美国 纽约 10031 ;2.大连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 大连 1166223.大连外国语大学 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路易丝·文奇(LouiseVinge)撰写了一部清晰而全面的主题学著作,阐述从奥维德时代到19世纪初那耳客索斯形象(1)那耳客索斯(Narcissus):(希腊神话)河神刻菲索斯和水泽女神利里俄佩之子,是一个美少年。出生后,他的父母向著名预言家提瑞西阿斯询问儿子命运。先知告知:只要这孩子不看到自己的脸,就能长寿到老。那耳客索斯长成一位美少年,许多少女都渴望他的爱情,但他对任何少女都无动于衷。当自然女神厄科痴爱他时,他同样无情地拒绝了,致使厄科忧伤而死,只剩下她的声音(厄科,希腊语“回声”)。被他拒绝的少女们要求女神惩罚那耳客索斯,公正女神涅墨西斯听从了她们的请求。一次,那耳客索斯打猎归途,在一汪清水中看见了自己面容,便爱影自恋不能离开,最后憔悴而死。他死处生出一株水仙花(即那耳客索斯)(《变形记》Ⅲ,泡萨尼阿斯Ⅳ)。这是溯源神话,用以解释生长在希腊的冷艳的水仙花,实际上此词源自前希腊。神话的另一变体没有出现厄科,而是说那耳客索斯有一孪生妹猝死,那耳客索斯忧伤异常。一次在清澈水中看到自己影子,以为是妹妹,不忍离去,终致忧伤而死(泡萨尼阿斯Ⅸ)。另一传说称,阿弥尼俄斯爱上了那耳客索斯,遭拒,自杀而死。神怒,就让那耳客索斯自恋自影。他因知爱情无望,自杀而死,血中长出了水仙花。那耳客索斯大约是古代象征自然死而复生的植物神。佩尔塞福涅神话也谈到那耳客索斯,在死者身上放置水仙花(那耳客索斯)。这则神话也反映了原始人害怕看到自己影像的巫术观念。原始人认为,影像是居于“梦中”的第二个“我”,看到则不祥。那耳客索斯神话曾被卡瓦利、斯卡拉蒂、杜鲁克写成歌剧,由卡尔德隆写成剧本。英国许多诗人如乔叟、斯宾塞、马洛、弥尔顿、雪莱、济慈都曾写过这一故事。(参见鲁刚主编《世界神话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304页)的多重意义。当时她在该著导言中陈述,传统的阐释“已经到了瓦解的阶段”。她的研究范围遍及整个西欧学术界,几乎没有遗漏重要的文本或者批评性著作。除了不断地进行质疑,她还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做研究综述。结果不仅证明了这是一项有价值的学术性和解释性工作,也证明了主题学的确是一种研究文学的有效方法,尽管在方法选择的次序上还有所保留,而更详细的评价则在内容综述之后。
古典文学研究论作的开篇章节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奥维德(2)奥维德(Ovid,B.C.43—A.D.17):古罗马诗人,著有《变形记》《爱的艺术》和《爱情三论》。的故事分析。因为在这部分里,路易丝·文奇自己构建了一套术语,以此评价之后所涉及的作品。故事的两个主要情节,山中仙女厄科(Echo)的故事和美少年那耳客索斯(Narcissus)的故事,是由若干重复的母题组合在一起的;尽管作者已经决定按照数世纪的习惯安排其著作的顺序,但是通过对这些母题的持续性再思考,她的著作完成了它们的连续性并展示了她的观点。这里有三个母题需要提示:影像母题,首先出现在厄科故事情节的“听觉形式”中;错觉(或幻觉)母题和认知母题,则在第二部分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
当12世纪该主题被确立后,此后几个世纪里影像和错觉(或幻觉)母题得到了强化,而认知母题几乎被忽略了。那耳客索斯形象是骄傲的傻瓜,他被虚假的快乐和表象所欺骗,否则他就成为拒绝爱的危险的警告例证;或者,最后他是“他的原型,一个在自己的激情中做出了愚蠢的选择,以及一种强烈的激情之爱以至导致自身死亡”[1]71。在每种情况下,他都代表着自我认知理想的反面。同时,厄科的遭遇也很突出,常被呈现为故事的关节点。
在14世纪,围绕这个故事除了传统阐释,新的阐释也开始出现。在薄伽丘(3)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代表,人文主义作家,诗人。代表作《十日谈》《菲洛柯洛》《苔塞伊达》。薄伽丘与但丁、彼特拉克并称为佛罗伦萨文学“三杰”。的神话(奇异)谱系中,厄科成为农夫法玛,那耳客索斯则成为善于遗忘的男人。在接下来的15世纪里,菲奇诺(4)菲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牧师,哲学家。他是把柏拉图《对话录》翻译成拉丁语的第一人。他还翻译了普罗提诺和其他一些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作品。菲奇诺认为柏拉图的思想来自埃及一位传奇术士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他也翻译过他的作品。著有《论生活三笺》,提出“世界灵魂说”,即世界上的肉体以一种玄妙的方式相连。复兴了新柏拉图式阐释,此时那耳客索斯则成为那种关注美的物质形态的男人,因此无法进入真正永恒之源。
进入16世纪,虽然传统阐释依旧延续,但先前不被重视的古典材料被重新发现了,因而生成了新的意义,而这与当初奥维德的蓝本几乎无关。这是那耳客索斯主题从奥维德故事原型中获得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意义深远的一步。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象征意义的文学,例如《阿尔恰托斯的自由徽章》;路易丝·文奇声称,这是第一个将影像阐释为源自智力的幻想作品,与此同样重要的是通俗文学创作。卡塔芮(5)卡塔芮(Vincenzo Cartari,约1531—159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神话学家。画作《西方古代神像》,选择了一个未经编辑的特别关注的人物和各种神的视觉图像,通过一个迷人的、信息丰富的画廊去识别喜悦、服装、表情、姿势、属性、仪式和传说。将厄科(即那耳客索斯神话)与《毕达哥拉斯格言》(6)《毕达哥拉斯格言》,即《金言》。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道德格言诗,学界对此尚有疑问。联系起来,当风吹起之时,人们会向厄科祈祷。同样,亚历山大·法拉将厄科阐释为上帝的声音的“形象”。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主义(7)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主义:15世纪以后的柏拉图主义,比中世纪的思想更复杂难懂。代表人物有:15世纪拜占庭哲学家普莱桑、菲奇诺和米兰多拉,法国的“行为”哲学家布隆代尔、柏格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谢林,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诗人布莱克、浪漫主义诗人柯立芝和雪莱等。来说,厄科则代表了“事物的象征性特质”,即上帝与人之间的纽带。
在16世纪诗歌中,隆萨德(8)隆萨德(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法国诗人,法国的同代人称其为“诗人的王子”。的那耳客索斯符合中世纪的传统,他完全是一个错觉的牺牲品:“是美丽和幻想迷住了他,导致他的毁灭,而不是理性的自我观察”[1]161。在这个重要的节点上,路
易丝·文奇认为郎萨德像其他诗人一样,包括迪斯波茨(9)迪斯波茨(Alexandre-Fran ois Desportes,1661—1743):法国画家、装饰设计师,风格承袭佛兰德·斯奈德斯一脉,受王室贵族青睐的动物、静物画师,皇家学院成员。、路易丝·拉贝(10)露易丝·拉贝(Louise Labé,1524—1566):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女权主义诗人。同时代人把她比作萨福和海尔·拉贝,称其是第十位缪斯女神。、斯宾塞(11)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把进化论“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上,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作为一个怀疑论者,他的著作对很多学科都有贡献,包括规范、形而上学、宗教、政治、修辞、生物和心理学等。、马洛(12)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英国伊丽莎白时期最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无神论者。剧作有《帖木儿大帝》《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马耳他岛的犹太人》《爱德华二世》《迦太基女王狄多》《巴黎的大屠杀》,以及诗歌《激情牧人的情歌》。和莎士比亚,他们都在强调幻觉母题,延续中世纪的讽喻和道德传统。
在接下来的17世纪里,尽管通俗作品保留了传统的材料和阐释,但有明确的新证据。例如,在新编仿作的那耳客索斯悲剧故事中:“作家们厌倦了重复‘爱’的警告。”[1]194积极的阐释开始出现。马斯尼乌斯说,在那耳客索斯故事中有“自己的神的形象中,他爱上了这个男人并成为了肉身”。此外,当时许多叙事诗采用了田园传统。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可以更容易地摆脱道德传统的束缚,并强调这一形象的情色和感性元素。雪莱(13)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著名作家、浪漫主义诗人、哲学家、散文随笔和政论作家、改革家、柏拉图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颇深。著有叙事长诗《麦布女王》《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倩契》《西风颂》,恩格斯称他是“天才预言家”。的那耳客索斯和洛佩·德·维加(14)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1562—1635):西班牙黄金时代(15到17世纪)剧作家,创作了多达1800部戏剧和几百部较短的戏剧作品(现存431部戏剧和50部较短作品),确定了西班牙古典戏剧的形式,对欧洲尤其是法国文学影响巨大。的那耳客索斯是颇有意味的例子。
路易丝·文奇把自己的研究重点集中到17世纪吉安巴蒂斯塔·马里诺(15)吉安巴蒂斯塔·马里诺(Giambattista Marino,1569—1625):意大利诗人,意大利巴罗克文学的代表人物。作品有抒情诗集《七弦琴》《新婚诗》、童话诗和描写田园生活的牧歌集《风笛》等。其诗歌反映了17世纪意大利文学衰落时期贵族阶级趣味,此后体现这种风格的“马里诺诗派”在意大利盛行一时。的通俗诗歌。在她的行为主义理论框架下,她发现了一个严重的伦理要素和形而上学问题。在这方面,最具启发性的文本是《拉·格莱利亚》中的诗歌,它“描绘”了一幅不存在的油画,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马里诺的诗歌充分利用“幻象构设,唯一的机会”。因此,马里诺关注的是幻觉的多重效果:一个虚幻的形象会造成真正的痛苦,一种表象可以比它所假装的现实更真实。因此,幻觉是一种审美原则,它的“圆满成功”在那耳客索斯的痛苦和死亡中得到了证明。这一标志性主题的衍生作品,也吸引了17世纪的其他诗人,特别是特里斯坦·勒·埃尔米特(16)特里斯坦·勒·埃尔米特(Tristan L’Hermite):17世纪法国诗人,是剧作家弗朗索瓦·勒·赫米特(Francois L’Hermite,1676—1755)的化名,是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沃尔特·斯科特《昆汀·德沃德》、贾斯汀·亨特利·麦卡锡《如果我是国王》以及鲁道夫·弗里尔《流浪汉国王》中的人物,也是朱丽叶·班加尼的“凯瑟琳”小说《路探子》中的一个角色。和保罗·弗莱明(17)保罗·弗莱明(Paul Fleming,1609—1640):德国医生和诗人,有诗歌、赞美诗和情歌传世。(路易丝·文奇在她对菲尔丁的分析中再次提到了这一点)。
17世纪的寓言阐释比前一个世纪更为原始,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影响下的英格兰。在乔森(18)乔森(Ben Jonson,约1572-1637):英格兰文艺复兴剧作家、诗人、演员和评论家。代表作有《福尔蓬奈》《炼金士》,诗集《格言诗》《森林集》《灌木集》等。乔森写了18部戏剧,除两部罗马历史悲剧《西亚努斯的覆灭》和《卡塔林的阴谋》之外,大都是社会讽刺喜剧。的《辛西娅的狂欢》中,那耳客索斯成为拥有神圣灵魂的形象,摆脱了神话原型(乔森的一个杰作,厄科的愿望是融化为眼泪,成为他真实的镜子)和自恋状态。在当代法国文学中,通常避免这种模式。在马尔伯夫(19)马尔伯夫(Pierre de Marbeuf,1596—1645):法国诗人,与笛卡尔一起学习法律,有《巴洛克十四行诗》《诗集》传世,自然、生命和爱情是其诗歌主题。的玛利亚诗歌中,“一个中世纪的主题(不是作者所指出的)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神秘的书写”,就是“伟大的神的完美的那耳客索斯”在圣母的泉水中反映的自己。作者将其与梅森(20)梅森(Jacob Masenius,1606—1681):德国耶稣会士,在拉丁语中被称为多产作家,有诗歌、戏剧和历史、批评及神学等著作。的阐释进行了比较。17世纪的戏剧包含了两个最原始和最具启发性的那耳客索斯故事书写。卡尔德隆(21)卡尔德隆(Calderon de La Barca,1600—1681):西班牙黄金时代剧作家、诗人,与维加齐名,是西班牙黄金时期戏剧两大派之一的代表人物。他开创的戏剧新风格,一直影响了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的黄金时期后期文学。他的戏剧作品约120部,其中宗教剧80余部,幕间剧20余部,可分为悲剧、本国历史剧、外国历史剧、袍剑剧、神话传奇剧、哲理剧、宗教剧七大类。著名作品有《爱情、荣誉和权力》《人生如梦》等,主题在于阐明人生富贵之虚幻。他的剧作多以人的命运和人的荣誉为主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还表现出巴洛克风格,影响远及法国戏剧和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作品《厄科和水仙花》具有强大的审美统一性和心理深度。而《神圣的水仙花》,墨西哥修女胡安娜·德·拉·克鲁斯的基督圣体表演,采用了卡尔德隆的田园风格和人物形象,并将基督和那耳客索斯结合在一起。总的来说,路易丝·文奇发现把那耳客索斯故事放在田园环境之中,17世纪的作家不仅恢复了此故事许多原有的特征,而且促成了新的阐释,特别是关于幻觉的效果。
尽管18世纪的奥维德翻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表明了读者有持续不断的需求,但奥维德在作家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都有所下降,他经常受到批评(因为赫德他太过分了,矫揉造作),这个主题还有更多的戏仿和滑稽的处理。与此同时,神话和宗教的起源问题也受到严重的影响。从理性主义立场来看,例如神话历史论者阿贝·班尼尔(22)阿贝·班尼尔(Abbe Bannier):“神话即历史”派学者,著有《神话》。,他批评奥维德的超自然倾向,并且偏爱保罗尼乌斯之那耳客索斯故事的“双胞胎姊妹”版本,以及休谟(23)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不可知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著有《英格兰史》。他是怀疑论者,也是自然主义论者。休谟的哲学受到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法国作家的影响,他也吸收了各种英格兰知识分子如艾萨克·牛顿、法兰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等人的理论。和维科(24)维科(Francesco Vico):17世纪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画家。的心理学理论。这一理论出现在英格兰,以布莱克威尔(25)布莱克威尔(Isaac Blackwell,?—1699):英国作曲家和大教堂风琴手,曾在圣保罗大教堂供职。和泰勒(26)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英国人类学家。著有《阿纳霍克,或墨西哥与墨西哥人》《人类早期史研究》《原始文化》《人类学》《论调查制度发展的一个方法》,在学术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解释之后。与理性主义立场相反的是赫尔德(27)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德国文艺理论家,狂飙运动的理论指导者,同狄德罗、歌德和莱辛都有交往。对哲学、文艺、宗教、历史和语言学均有研究,提倡民族文化,重视民间文学,试图从历史观点说明文学的性质和宗教的起源,并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解释语言和思想的关系。著有《关于近代德国文学的断片》《批评之林》《论语言的起源》《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未完成),还编纂有民歌集《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他们认为神话既是艺术作品,同时也是最深刻的宗教真理的表达。
在“评价的转变”的标题下(即在18世纪那耳客索斯形象的意义),路易丝·文奇对卢梭(28)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民主政论家,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著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伊丝》《植物学通信》等。的《那耳客索斯》进行长时段的分析,或者是他文化基因的情人。卢梭宣称他之所以出版这部剧正是因为它的缺陷:科学和艺术的式微,源自人类的虚荣心。这部劣质剧作的出版,就是证明了他自己并不是被“布希式”虚荣心所驱使,而是为了寻求真理和改善社会。路易丝·文奇把卢梭的这部剧作及其序言放在“利己主义和自我认知的辩论”背景下,讨论两种自恋的区别:一种指向自我认知,并进而导致对人性的认识;另一种是导致贫乏和无知。雅克·阿巴迪(29)雅克·阿巴迪(Jacques Abbadie,1654—1727):法国新教教士,著有《基督教真理条约》。区分了“爱”和“爱慕者”;安东尼·沙夫茨伯里(30)安东尼·沙夫茨伯里(Anthony Shaftesbury,1671—1713):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英格兰政治家、哲学家和作家,英国经验主义者。在“自我情感”和“自然情感”之间进行区分;赫尔德区分“我”和“自己”。路易丝·文奇声称,在翻译沙夫茨伯里时,狄德罗(31)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戏剧家、作家,百科全书派代表人。更注重强调个人的自我认识,而不是一般人性的认知。
爱德华·扬格(32)爱德华·扬格(又译作:爱德华·扬,1683—1765):伟大的英国诗人。他的传世之作长诗《夜思录》(全名《哀怨,或关于生、死、永生的夜思》)对死亡的感伤情绪与关于生死的神学讨论交织在一起,忧郁和沉闷的情调激发了后世诗人以死亡、坟墓为题材的“墓园诗派”的产生,而扬格则是“墓园诗派”的创始人。推动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进一步发展,亦即极致的自我认知,他将此归因于那耳客索斯形象的完全积极价值。因此,那耳客索斯形象的意义似乎从一开始就达到了相反的极点:“爱德华·扬对研究人的个性本质的理论要求,以及卢梭对同一思想的实践影响了一个时代。现在那耳客索斯可以成为有意识的自我观察的象征和人类神圣的崇拜。”[1]288另一方面,关于那耳客索斯的消极观点,在赫德身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代表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贫乏性,与厄科所保存的“创造的合唱”相悖。
最后作者简要分析了19世纪作家,指出他们继续对克罗伊策(33)克罗伊策(Georg Friedrich Creuzer,1771—1858):德国古典神话学者,《大英百科全书》编辑,学识渊博。他运用先进理论研究荷马和赫西奥德神话的东方来源,以及希腊神话蕴含的古老启示的象征元素。《象征和神话》中的那耳客索斯形象予以重评:“新柏拉图神话的最后一个伟大丰碑”,将影像母题作为神话故事的核心象征,“这个象征以神秘的方式揭示了作为物质俘虏的人类灵魂的命运,被一种美丽的幻觉所欺骗”[1]329。克罗伊策的影响力最初是由瑞典的浪漫主义,特别是埃里克·约翰·斯塔涅利乌斯(34)埃里克·约翰·斯塔涅利乌斯(1793—1823):瑞典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著有《瓦拉迪米尔·登斯多普史诗》(弗拉迪米尔大帝)、浪漫主义诗歌《布伦达》、神秘抒情诗《莉尔乔·伊·萨伦》和十四行诗。所感受到的。在这个时期的其他地方,那耳客索斯主题仍然没有受到这种“形而上学悲剧”式灵魂遗存的影响;相反,它通常象征着对美的奉献(济慈(35)济慈(John Keats,1795—1821):19世纪初英国浪漫派诗人。有《伊莎贝拉》《圣艾格尼丝之夜》《海壁朗》《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等作品,与雪莱、拜伦齐名,被推崇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雪莱)。因为我自己已经写了许多中世纪的著作,与路易丝·文奇讨论,并得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我认为,如果现在根据我自己的观点批评她对中世纪那耳客索斯的评价,那对作者和读者都是不利的。路易丝·文奇对无数作品的讨论,大多是如此深刻和令人信服的,而中世纪时期在她的研究中所占的比例如此之小(集中在第16至18世纪),以至于我的任何分歧都不会影响她对于专著的评价。然而,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的优秀,它提出了一些关于“历史”主题的概念,以及关于题材史作为文学研究方法的价值的问题。而且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它更值得思考。
在随后的研究中,分歧主要发生在这些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耳客索斯主题摆脱了最初的说教和与奥维德的联系,而重点则从幻觉(错觉)母题转移到影像母题和认知母题。在故事主题呈现变化的同时,对那耳客索斯形象的阐释也发生了变化:他起初是一个缺乏经验和任性的青年,而他的错误是他的无知或骄傲所受惩罚的结果,此后发展成了为美所困的男人典型(随着教育元素的消失),最后又在主题“解体”之前,成为自我觉知的范型(由于影像母题和认知母题成为主导)。
因此,那耳客索斯主题的历史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与叙事本身的顺序惊人地相似。在开始的时候,那耳客索斯是盲目的骄傲,故事的中间环节,他被自己的美丽迷住了,而在浪漫主义运动的时期,他完全意识到他的错觉及其后果,尽管他的自恋并没有减少。根据这一逻辑,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那耳客索斯都没有真正觉醒。
但是路易丝·文奇的概念性偏见排除了最有益的比较性研究,而这种比较性研究却是最有价值的。这不是无稽之谈或者个人偏好问题,因为路易丝·文奇自己也承认至少在一部作品中,存在于12世纪的那耳客索斯,影像母题和认知母题都起着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她并不是很典型,她只是简单地把这个发现放在一边,而不去面对必然会出现的问题:这种主题的早期处理与后来的有何不同?还可以举出其他“例外”的例子。作者认为,艺术家将那耳客索斯作为表象这件事,首先发生在早期浪漫主义(就“发展”而言,它几乎不可能在更早时发生)。然而,正如G·F·哈拉柏(36)G·F·哈拉柏(G.F.Hartlaub):德国画家。所揭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也把那耳客索斯看作所有油画的祖先。艺术家本性和艺术意义在每一个时期都是如何解释的?又或者,海因里希·冯·莫伦根(37)海因里希·冯·莫伦根(Heinrich von Morungen,?—1222):德国中世纪诗人。和A·W·施莱格尔(38)A·W·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德国诗人、翻译家、评论家、剧作家和东方学家。受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伊曼纽尔·康德、提比略·亨斯特胡斯、约翰·温克尔曼和卡尔·西奥多·冯·达尔伯格的影响,翻译但丁、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对但丁、彼得拉克和莎士比亚颇有研究。施莱格尔还是欧洲大陆第一位梵语教授,翻译《薄伽梵歌》《罗摩衍那》,有剧作《爱雍》(Ion)、剧评《关于亚洲语言研究的思考》。都把情人形象摆在表面上并渴望把握它,但同时意识到,只要这样做都会立刻抹掉情人的形象和身份。然而,除了语言差异之外,每个人都会把海因里希的抒情诗视为中世纪文本,而施莱格尔则认为这是浪漫主义时期的。这一差异如何形成的,它如何有助于澄清每一时期的本质问题(我承认,在我自己读到的关于海因里希抒情诗的例子中,我也曾提到;但路易丝·文奇因为她只引用了明确提到的那耳客索斯模式,并没有把抒情诗当作统一的作品来看待。因此对这一作品的讨论将这种解读排除)。
路易丝·文奇坚持的理念与她的实际实践之间的冲突也反映在材料的组织上。对此,她解释说,她的历史划分是以百年为界限的。显然,关于历史时间机械性划分是有意的。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要表明当代及其之后的创新中依旧存在传统精神。如果以个体性“时代标识”的作品作为研究性著作的章节标识,那么在这一标题下,他们所罗列的文本则均是该理念影响下的集合体,而在一些情况下,这将意味着主题先行式地有意识地搜集聚结。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下,这将意味着在文本时间顺序上粗暴干预,并歪曲历史观点。
他们确信,这种方法与立场,是机械地划分历史或根据主体性“时代标识”的作品来划分历史的唯一选择。作者选择了第一种,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在第14世纪的那一章中,他们提到那耳客索斯后,彼此之间就没有任何联系了,同样状态的还有薄伽丘、但丁(39)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中世纪诗人,现代意大利语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者,以史诗《神曲》传世。在意大利,他被称为至高诗人和意大利语之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被称为“文艺复兴三巨头”(“文坛三杰”)。、德尚(40)德尚(Eustache Deschamps,1346—1406):法国中世纪诗人,以其讽刺妇女的诗闻名。、弗罗萨特、乔叟(41)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英国小说家、诗人。著有《特罗勒斯和克莱西德》《坎特伯雷故事集》,受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影响较大。他被公认为中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彼特拉克(42)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意大利学者、诗人,文艺复兴第一个人文主义者,获誉“文艺复兴之父”。他崇尚古典文化,把自己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想称之为“人学”或“人文学”,以此与“神学”对立。他以十四行诗为欧洲抒情诗发展开辟了道路,被尊为“诗圣”,与但丁、薄伽丘齐名。、佩雷斯·德·古兹曼(43)佩雷斯·德·古兹曼(Fernan Perez de Guzman,1332—1407):西班牙中世纪小说家。。在第18世纪的这一章的,导言和结语表明,世纪之初存在这种状态,后期则是另一种情况,这是浪漫主义运动冲击的结果。在令人鼓舞的那耳客索斯个人主义形象典型发展历程的分析当中,路易丝·文奇打断了自己对歌德“传统道德与现代认识论”陈述的评判,她用她一贯的尖锐性笔触来处理这个论题,但这个论题与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关系。在第13世纪这一章的结尾,她认为与第12世纪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换句话说,这种根据世纪演进的篇章划分已经不仅仅是“机械性”问题,而是毫无意义。除了使这本书的基本论点模糊,以及遮蔽它有论点这一事实之外,什么也没有完成。路易丝·文奇还进一步声称,在这些分歧中,她试图“系统地展示各种惯常模式的出现”,但却没有阐释为什么这些模式在一开始就不能成为本书的分类标准。事实上,整个研究都是对这些惯常模式的研究和观点的论证,它们在一个清晰的模式中发生变化——这一模式随后被反映在对特定作品的解释上。遗憾的是,该书的研究并没有揭示该母题的本质,并进而成为一篇阐释性论文。
但是这些遗留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证明了作者激发读者的能力,这只突出了她著作的一般性优点。经过全面深入的研究,路易丝·文奇创作出了一流的诠释作品,如此一来,评论家和文学史家都将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她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