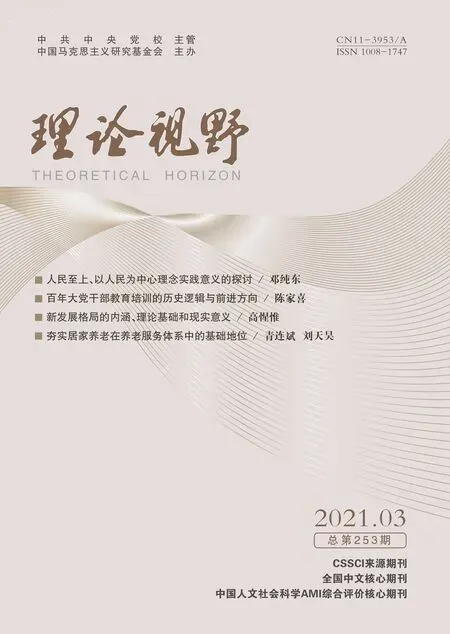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生成逻辑及哲学理路*
■戴科栋
【提要】马克思恩格斯的女性观确切地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女性观,它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并非一定是系统的理论。其中,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唯物史观基础,女性解放是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认识论目的,两性和谐是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辩证法诉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哲学归宿,这四方面内容互相依托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哲学理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体系。
女性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议题,私有制的出现是女性问题生发的酵素,私有制的发展和消亡直接影响着女性问题的更迭。马克思恩格斯的女性观隐现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中,它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反映,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因此,要深入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必须要立足原著,从原著文本中寻找其发生发展的理论依据。通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生成逻辑,进一步厘清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哲学理路,对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生成逻辑
(一)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早期阶段
马克思关于女性问题的早期论述有一种明显的哲学和象征语调。大学时期,他从黑格尔主义的年轻的浪漫主义观点,转到了被称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团体所持有的更哲学化的观点,后来,马克思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经济(与恩格斯合作)。这样,像许多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当马克思最初用女性的从属地位来表示一般社会状况时,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从属地位这一现实。
在马克思25岁时出版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讨论了代表社会发展程度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层面上,反映了私有制和所有权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表现出人的本质和自然界之间的相互转化。男女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男人超越自然状态的进步程度,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这种关系采取了异化的形式。马克思详细阐述了个体的“人”(公正的人)的概念——它不仅涵盖了所有人类,而且将性别属性赋予人类。在他所展示的程度上,女性即他者,在男性统治下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采用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观点,尽管论述内容并未触及家庭,但他把论述重点放在了女性对于男性的关系上,确切地说集中在女性身上。因此,马克思摒弃原有的逻辑思路,选取了女性的地位来作为社会发展的新标志。在《神圣家族》中,女性受压迫已不再仅仅存在于观念领域中。马克思强烈抨击了资产阶级对于女性观点的伪善性,实际上他指出了当前条件下女性受到非人的悲惨遭遇。
恩格斯在1888年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题出版了1845年的这些笔记,这个纲领几乎是意外地揭示了马克思最初对于家庭的纲领性定位。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不同的途径对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了暂时性的认识。《德意志意识形态》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对家庭的理论和历史的首次全面系统的阐述。他们认为,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形式是扎根于生产关系中的。他们认为,满足人类需要的是三种并存的社会活动。第一,人们生产满足基本需要的资料。第二,这种活动导致了新需要的产生。第三,人的再生产。因此在关涉女性问题的家庭关系中以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形式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表明,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根据所有能够获得的经验资料,对以往和当前社会中女性从属地位的确凿事实进行了仔细分析。与这些丑恶画面相对立,他们描绘了关于未来女性解放和家庭消亡的一系列图景,尽管这些图景显得还有些简单。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开始将自己关于女性问题的立场与早期社会主义者带有空想性质的观点区分开来。马克思恩格斯为女性受压迫问题确立了明确的理论起点和历史起点。从理论角度看,所有的社会关系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在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女性问题也不例外,女性受压迫最初是发生在对偶制家庭的奴隶制中,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将原始资料整理归纳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唯物史观女性观,并在他们的著作中体现出来。
(二)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成熟阶段
在马克思《资本论》这一经典文本中,女性境况、家庭、社会分工等的论断相继出场。他通过对工人阶级妇女以及儿童的真实处境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剖析,并集中关注机器使用带来的影响,辛辣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吃人本相。机器极大地降低了生产过程中对体力劳动的要求。在资本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客观现实下,妇女和儿童成为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最佳人选。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劳动力的样态和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机器化大生产的普及使得失业率直线上升,妇女和儿童纷纷加入劳动大军。在众多的生产部门中,妇女和儿童代替男人成为主要劳动力。而且,资本主义机器化工厂惊人的生产力使家仆(他们中90%是女性)的数量大为增加。尽管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机械化对于雇佣的影响,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严重损害了生产,降低了工资,导致了大量的失业,这一情况下女性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做的不单单是对女性的境况、家庭等的描述性评论,他对揭示这一历史发展所必需的理论也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在劳动力和工人阶级再生产范围内,女性问题得以脱离表象而本质浮现,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建立了其女性观的逻辑基点。尽管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和工人阶级再生产的论述还有些不明确之处,而且这些论述一般都是提纲式的、不完善的,但他的著作为女性和家庭与一般意义上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1878年,恩格斯出版了一部与社会主义者欧根·杜林辩论的作品,后来这部作品通常被称为《反杜林论》。这些观点包括对女性、家庭和工人阶级再生产(通常是扼要重述他本人和马克思早期的分析和看法)问题的评论。恩格斯也回顾了以往作品中讨论过的许多问题:劳动力价值的决定,机器对工人阶级家庭的影响,产业后备军的出现,作为卖淫合法形式的资产阶级婚姻的特征等,恩格斯坚持认为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关系的变革必然会伴随着家庭关系的变革。在这一语境下,他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陈述,得到了一个评论性的策略推论,即这些变化的基础是资本主义。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被看作是关于家庭问题、关于女性问题的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目的不是要提供关于女性、家庭和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全面分析,而仅仅是将问题的特定方面确定无疑地置于历史和理论语境中。恩格斯认为,向父系氏族制度的转变对社会和女性地位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它确立了一整套社会关系,不仅有益于私有制,而且有益于整个阶级社会未来的发展。在恩格斯看来,由于女性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机会和频率的逐渐增加,女性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加强,男权意识形态对其的影响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工人阶级家庭中的男性统治将日渐缺失其继续存在的基础。
由此可见,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家庭中女性地位的大多数简要论述,都是通过形式平等和实际平等之间的差异来表达的。他首先分析了婚姻契约与劳动契约之间的关系。从法律上说,二者都是可以自由缔结的,因此在形式上双方是平等的。在劳动契约中,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工人和雇佣者之间阶级地位的差异。婚姻契约中包含着同样的神秘性,因为在享有私有财产的家庭关系中,子女的婚姻通常是由父母决定,子女本身并不具有婚姻的实质决定权。事实上,婚姻双方在法律上的平等只是一张形同虚设的空头支票,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现实生活中婚姻双方的不平等关系。在父权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中,家务劳动变成了一种私人劳动,妻子劳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两种家庭形式都将女性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并使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状态,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恩格斯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1]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也只有无产阶级女性才有可能再次进入生产领域。恩格斯用几段话语简单概括了关于女性解放条件的结论,大体上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问题所做的同样简要的论述相吻合。恩格斯推断出,工人阶级和女性群体之间在许多方面有着同一性,假如这两者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平等、男女平等,他们首先就必须拥有法律上的平等。
二、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哲学理路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不断成熟,其哲学脉络也逐渐清晰,它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汲取思想精髓,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哲学理路。
(一)异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唯物史观基础
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凡是研究中涉及女性问题的几乎都绕不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其原因在于“异化理论是一种学术建构,在这种建构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人产生的毁灭性影响”[2]。可以说,异化理论是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条线索,其思想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唯物史观基础,成为整个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理论支点。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卢梭的权利异化、黑格尔的精神异化以及费尔巴哈所谓的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不同,但他却沿用了“异化”这一词汇。这个词汇,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除了经济学的让渡、转让之意外,更多地包含着剥夺、与主体分裂等的消极含义。正如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麦克莱伦所言:“马克思用两个德 语 词Entäusserung和Entfremdung,严 格 说来,第一个词强调了剥夺的意思,而第二个词强调了某物的疏远和外在。马克思似乎并没有区别地使用了这两个词,有时并用两者表示强调。”[3]
马克思深入阐述了异化劳动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可简要地概括为: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对于劳动产品的异化尤为关注,私有财产由此产生,他这样描述私有财产的实质:“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4]拜物教是以物或者物的符号的形式代替或掩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它以物化的形式表达了异化的内容。资产阶级商品社会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都要通过商品、货币这些等价物来实现,社会关系单一地表现为经济关系,人因此也成为仅仅关心切身经济利益的利己主义者。马克思认为,异化存在的必要条件是私有制、商品交换和剥削的普遍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女性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即使是儿童也不能幸免。女性面临着普遍的异化,她们的劳动是被强制的,并不是自由自觉自愿的活动。由于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机器代替了大部分手工工人,导致男性工人大量失业。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更青睐于雇佣更为廉价的女工和童工,反观其工作环境和条件是极其恶劣和丑陋的,女工长期从事高强度的工作,身体和精神是极度虚弱的,童工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对于家庭的依赖荡然无存,其人生观也是在一种畸形的环境下形成的,这一切埋下了道德败坏的种子。生产力越发达,这种境况就越严重,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大大增加了女性卖淫和青少年犯罪的概率。异化劳动在女性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人吃人的面纱被无情地揭开。想要打破这种黑暗的局面,就必须要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剥削。
(二)女性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认识论目的
女性解放是女性突破传统思想禁锢、争取自身发展和解放的现实诉求,同时是女性摆脱剥削和压迫的革命需要。诚然,女性解放在实践层面上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认识论目的。由于近代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其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使得女性解放这一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著名哲学家罗素认为,近代女性获得政治权利的速度之快主要取决于民主理论和女性劳动社会化的影响。天赋人权是人人应该具有的权利,然而却单独把女性排除在外,早期成文的法律条文保障的显然不是女性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实之于女性是不公平的。然而,仅仅有权利的保障对于女性解放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女性解放从观念到现实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指出,女性解放在遥远的狩猎和农耕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女性参与公共生活劳动实践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而处于附属于男子的地位。只有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社会,才能为女性参与社会劳动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资本主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在资本统治下,女性受到了来自社会和家庭等方面的残酷剥削,逐渐被异化、物化。女性生存本身受到了挑战,何以谈论解放?在现实生活面前,女性被物质彻底征服,成了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以及男性统治的奴隶。
政治解放是女性解放的前提条件,对于女性解放来说,政治解放是必须的,但是纯粹的政治解放是非常片面的,远不能满足女性彻底解放的需要。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梅扎罗斯指出,“尽管女性解放事业在19世纪和20世纪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妇女可以参加参政议政,针对妇女的一些歧视性立法也废除了。但是这些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结构不平等的物质权利关系”[5],在资本统治下,女性平等只能是象征性的、浮于形式的。
恩格斯十分注重经济独立对于女性解放的重要性,因此在女性政治解放的同时,经济解放也势在必行。他提出女性解放的首要条件是全体女性参与到社会生产活动中去,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从根本上消除女性对男性经济上的依赖,切断男性经济上统治女性的根源,从而为争取男女平等提供有利条件。女性的经济独立对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唤醒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女性不再被家庭所困,逐渐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成为“现实的人”。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本质的不同,资产阶级女性并没有机会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因此,她们没有机会摆脱其社会关系的狭隘性,依然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女性解放的阐述,其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已经由局部(女性解放)扩大到整体(人类全面解放)。从这一点出发,女性解放应被放置于全人类解放的框架中,以联合革命的方式寻求自身的价值实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女性解放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并且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女性解放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
(三)两性和谐——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辩证法诉求
两性关系作为一种悖论式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关系,两性和谐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在承认性别差异性的原则上实现两性和谐,在差异与和谐之间达成某种平衡,需要用哲学的方式来解答。两性和谐隐含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关系,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范畴中。因此,两性和谐不仅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辩证法诉求。
黑格尔在《美学》中,是这般描述“和谐”一词的:“比单纯的符合规律更高一级的是和谐。……和谐一方面见出本质上的差异面的整体,另一方面也消除了这些差异面的纯然对立,因此它们的相互依存和内在联系就显现为它们的统一。”[6]由此可见,和谐即对立面的相互统一、相互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和谐并不能完全和同一性画等号,而“对立是和谐的前提,和谐是对立的结晶,离开对立无和谐可言。对立造成多种多样的和谐”[7]。在这一层面上来说,和谐重点体现在对立面的相互斗争和协调之后达到的理想状态。因此,和谐是中和对立的两个方面的结果,是对立双方达到统一的外在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建立在排他、自由、平等的基础上的强烈而持久的爱情,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爱情是人类两性关系发展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两性和谐的基础,是人的社会本质的体现和肯定。两性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区别开来。它不仅具有社会性,还具有情感性。两性关系的情感性在两性和谐过程中起到了平衡、中和、化解两性关系社会性矛盾的重要作用。所以,这种意义上的两性关系是以个体本位论为基础的,诚然,个体本位实际上是指:“个体的类化,个体的人化。……每一单个的人都成为人,都具有了人的本质,获得了人格性。”[8]这可以看作是两性关系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跨越。虽然如此,这种两性关系依然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但其实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伴随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其追求自由个性的动机越来越成熟。
事实上,争取女性解放其价值诉求就是要实现两性和谐。两性和谐是衡量两性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指标,一定程度上它既相对保全了人的自由个性,又避免了两性之间的对立冲突。两性和谐是男女两性完成了本质的统一,其一体性关系尽现。“不过,这种一体关系不是直接性的统一,而是人们自觉建立的以差别和对立甚至否定为内容的统一。”[9]
(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哲学归宿
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具生命力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一种概念,更是一种观察、分析人与社会的方法。这种观念与方法所指向的“人”的发展,不是专属某一阶级或集团的特殊发展,而是涵盖着包括女性在内的一切受压迫阶级的“全人类”的普遍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观的哲学归宿。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10]。
马克思终生坚信,自由是人的本质,自由是人的本性和权利。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指人类的生产劳动摆脱了肉体的直接需要和物种繁衍的需要而进行的自由的、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劳动。如果人的劳动自由性被剥夺,其自觉性就无从谈起,更不用提创造性。这种意义上的劳动便是一种被迫的、痛苦的、重复的机械化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的现象普遍存在。女性在被异化充斥的环境下劳动,自己的精神和肉体都备受摧残,其本质力量并没有得到体现。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劳动实质上退化为动物性的劳动,主要体现在:人们仅仅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而进行生产,劳动的性质由自由、自觉转向了被迫、强制。由此可见,异化劳动是违反人性的。
对于女性而言,所谓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主要是指实现女性社会价值和生命价值的统一,让女性拥有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使其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实的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主要应通过打破与原有人群的狭隘的联系,超出原有的自然生存的需要,发展出新的历史需要,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塑造人的社会性和个性。具体来说,首先应该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过去的压迫、剥削女性的旧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下,女性可以得到和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社会待遇,获得经济独立的能力,摆脱对男性的经济依附,从而使女性和男性一样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恩格斯还对女性获得解放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允许女性进入公共生产领域;二是把私人生产领域收归地方团体。这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后来共产主义者的信条。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把女性解放置于整个人类解放之中,这也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谨性、完整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一种回归人的本质,引领全人类走向自由的理论,女性解放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一部分,也应遵循其思想导向,由女性解放到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2]【美】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王贵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3]【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5]【英】梅扎罗斯:《超越资本》(上册),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
[6]【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
[7]袁鼎生:《西方古代美学思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8]高清海:《哲学文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9]高清海、胡海波等:《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