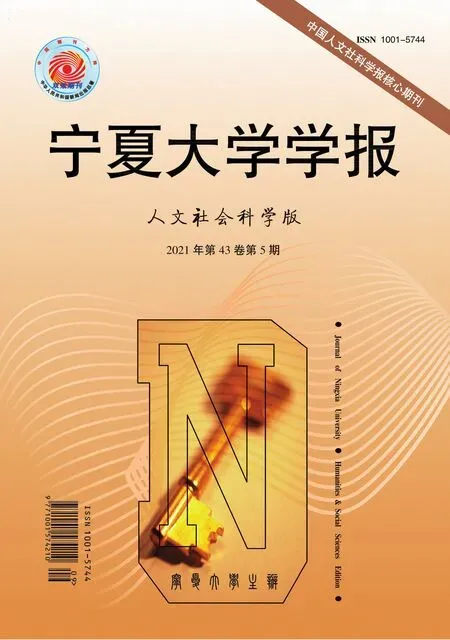作为书写策略的现代意识
——以贾平凹《暂坐》为考察对象
孙立武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贾平凹的第十七部小说《暂坐》首发于《当代》第三期,这部写了整整两年的小说以生病住院到离世的夏自花为线索,勾连起了十几个性格相异的女子,她们在西京这座充满欲望的城市,追求着经济独立、精神自由,同时也遭受着生活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困境。《暂坐》讲述了太多人的故事,但是却并没有把每一个故事讲得那么清晰;描写的是城市里的街道,却没有舍弃乡村的元素;用了太多的现代主义的笔法,却传达着现实主义精神。正如贾平凹在后记中所说:“写过那么多的小说,总要一部和一部不同。风格不是重复,支撑的只有风骨。”[1]《暂坐》的风骨在哪里?是三十个章节标题中众多地名勾勒出的西京,还是十几个女子在关系的脉络里所展现的复杂人性,还是游离于现实和非现实之间的奇异叙事逻辑,或者是人物的说话的艺术。概言之,《暂坐》所采用的现代主义策略给当下的现实主义写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 作为背景的城乡融合——焦虑、反思与留恋
城市与乡村一直以来被人视为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即便是在文学叙事中城乡也是一个关注的焦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路遥就提出了“城乡交叉地带”的概念,《平凡的世界》《人生》等作品全景式地呈现了中国当代城乡的社会生活,“城乡交叉地带叙事”逐渐成为文学叙事的一股潮流。何为“城乡交叉地带”?它应当是两个层面的结合,既把它当作一种物质时空的现实(即指转型时代的交叉和城乡的交叉),也将其作为一种心理现实,即指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人所产生的既非城亦非乡的异乡人的漂浮体验[2]。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间流动人口的大幅增加,城乡二元对立愈发地明显。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系列描写城乡这种变化的作品,他们或被归入“打工文学”,或被纳入“乡下人进城”系列,或者被冠以“新乡土叙事”的新名号,总而言之,“城乡交叉地带”作为一个充满矛盾的异质空间有着其生成—发展—消失—再到符号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贾平凹的《土门》《高兴》是这一异质空间书写中的典型代表,尤其是《高兴》既有城乡对立的表征的书写,又有人物心理上的矛盾书写。贾平凹在《暂坐》的后记中写道:“新世纪以来,城乡都交织在一起,人不是两地人了,城乡也成了我们身份的一个分布的两面。”[3]如果说《土门》描写的是一个城市侵蚀乡村促成“城乡交叉地带”形成的初始形态,那么《高兴》则描写的是一个形成的“城乡交叉地带”中正在发生的生活困境与社会问题。《暂坐》则是贾平凹写给城市的反思,写给乡村的挽歌,城市一次次地吞并乡村,在一个充满欲望的都市里,贾平凹时不时地把乡村的影子带入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气息之中,有叹息,有关怀,也有哲思。在“茶庄”“医院”“街道”“饭馆”“巷口”等城市意象中,贾平凹将“城中村”“农民工”“棚户区”这样的意象带入了欲望都市的叙事中。
《暂坐》里的西京是一个雾霾笼罩下的现代都市,高楼林立,店铺鳞次栉比,有着时尚的酒吧,典雅的咖啡屋,还有着一群靓丽的女子。海若有自己的茶庄,虞本温有自己的火锅店,向其语有自己的能量舱馆,陆以可有自己的广告生意,这一群经济独立的女性在城市里聚成了一个圈子。《暂坐》共三十四个小章节,每一节的标题都是采用“人物名称+地点”的模式,这些人物搭建起了小说的人物脉络,这些地点构建起了小说的叙事场景,同时这些叙事场景也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在这些城市景观的背后还有一些大的背景作为统摄,比如雾霾、城镇化等。
“雾霾”是工业文明和城市现代化的产物,在《暂坐》里,它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标签,它象征着城市的现代化,也象征着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压抑情绪。俄罗斯女子伊娃眼中的西京,是一个雾霾笼罩中的城市:空气里多是烟色,还有些乳色和褐色,初若溟蒙,渐而充塞,远近不知了深浅,好像有妖魅藏着,路面难以分辨斑马线,车辆似乎沉沦,所有的建筑一下子全失去重量,漂浮着,恍惚不定[4]。雾霾笼罩下的西京,是一种模糊和飘忽不定的感觉,也正如伊娃的身份一样,她是一个留学中国的异乡人。《暂坐》里发生的故事,她是游离于其中又飘忽其外的,因为终究她要离开,即便有这么多的友情留恋,还有着短暂暧昧的“情事”,正如西京里的雾霾一样,它属于这里,又不属于这里,伊娃是这个城市的过客,而不是归人。在小说的结尾,伊娃决定离开西京的时候,那个傍晚,空气越发地恶劣,雾霾弥漫在四周,没有前几日见到的这儿成堆那儿成片,而几乎又成了糊状,在浸泡了这个城,淹没了这个城[5]。伊娃从雾霾中来,又从雾霾中去,《暂坐》的首尾就这样在西京的雾霾中遥相呼应。
不仅小说的首尾是被雾霾笼罩下的发生,整部小说,凡是涉及天气的书写,几乎都会提及雾霾,都会是被雾霾笼罩的天空,据不完全统计,整部小说涉及“雾霾”的书写近20次,这就意味着“雾霾”这一关键词贯穿了整部小说的背景层面。小说的第二十节讲述的是茶馆的小唐花一千块买回一只乌龟,而后海若通知众姐妹曲湖放生。这一小节前后四次写到了“雾霾”,开头写雾霾使人的心情沉重,接下来写雾霾带来的混沌不清,如同噩梦里的场景,当众姐妹来到曲湖放生时,似乎雾霾的大幕中露出一丝丝缝隙:白天雾霾阴暗,晚上的湖北华灯齐上,万象反倒清明[6]。放生完之后,在景区管理处碰上管理人员,陆以可认为是这些人抓了鱼鳖之后再卖给游人放生,于是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唉,我初到西京时,那时多好的,现在是天变得雾霾越来越重,人也变坏了。大家还是没有作声,湖面上又恢复了平静,倒有了几许恐惧[7]。放生是一件善事,围绕着海若的众姐妹在乌龟回头的那一瞬间都有着自己的心事,她们讲到了佛门的皈依,讲到了各自的生意,大家在嬉嬉闹闹声中陷入了沉寂,所有的一切最终都消逝在西京的雾霾中。
雾霾是现实中国的写照,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大约在2011年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贾平凹把它写进了小说里,不同于《雾都孤儿》《福尔摩斯探案集》里的雾都伦敦,这里是古城西京,“雾霾”暗含着作者的一缕缕忧思,同时又是小说中十几个女子心境表现的承载物。
如果说雾霾是作家对于城市的忧思,那么乡村元素在小说中的呈现并非是一种格格不入,而是在城镇化进程加速的今天,20世纪90年代进城潮之后的“农一代”“漂一代”在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后已经渐渐老去,“农二代”“漂二代”们在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上似乎已经没有了困难,但是老去的人却对乡土有着留恋。贾平凹在《废都》和《白夜》中有意无意地虚构或预设了一个理想化的价值尺度,即纯朴美好的乡村文化,希望以此来批判和拯救日益沦陷的现代城市文明[8]。于是,在贾平凹的笔下,我们依然捕捉到了众多乡村的元素,尽管他声称这是一部突破乡村题材的都市小说。但是这些乡村元素并不同于那种纯朴美好,更多的是焦虑之中的惋惜与感叹。
海若去工艺品店找寻羿光感兴趣的廊鱼时,听到的是这样的怨声:城市发展已经使一代农民妻离子散着,再还要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吗[9]?!“雾霾”是环境污染的最直观的表征,不断加快的城镇化进程与环境污染息息相关,新晋的“城里人”抱怨着城市发展给农民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被迫进入城市的农民势必遭遇谋生、身份认同、子女教育等各种各样的问题。16岁就到西京打工的辛起可以说是一个“乡下人进城”的典型代表,手里有了钱之后总是先去买些衣服和鞋子,在穿戴上的花销是吃喝上的十多倍。当自己的好姐妹希立水劝说她要注意身体,好好吃饭的时候,辛起如此回答道:“我是乡下人么,必须表现为城市人啊。”[10]一个进城多年在经济上追求独立的女性,在其内心深处仍存在认同上的困境,即她认同的依然是自己乡下人的身份,只有用服装这样的外在装饰来不断地“宣称”自己是城市人,才会更接近真正的城市人身份。
认同上的困境是乡村难以融入城市的一个方面,乡村难以融入城市还表现在乡村有着被“污名化”的传统,应丽后被胡老板骗钱之后,因为王院长从中牵线的缘故,遂王院长答应几年内归还被骗钱财,后来应丽后还是找来了讨债公司去找王院长讨债,且看这些讨债人员的构成,他们的面容,在贾平凹的笔下十分生动、形象。他说雇了几十个乡下进城打工的农民,每人每天发三百元,连续打了横幅在人家的商店前高呼口号,进行示威。“海若说:这倒弄得满城风雨了!陆以可说:风雨就风雨吧,那也没啥;只是那些打工的农民都是穷极了的人,被他们一煽呼,担心债讨不回来,还会出别的事。”[11]进城打工的人,一部分是为了谋生而主动进入城市,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被征地而纳入城市的失地农民,这些人在经济上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身在城市却又不属于城市,且不说进城打工的那批乡下人,就连因失地转而成为市民的那部分人,也会受到现代化城市的排挤。如同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些打工的农民都是穷极了的人,他们也只能从事着暴力讨债这样不光彩的工作。除了这些,还有那些在街边等待零工的民工们:身上背着脚前放着大锤、长锯、电钻、泥刀和刷墙的滚子,他们大半天还没有雇主来招领,就一边嘲笑着甩长鞭的人使的那闲力气干啥,一边拿着各种吃食往口里塞[12]。城乡的融合自然还会产生带有“混杂性”的异质空间,比如“城中村”“棚户区”这样的场所:
那街算不上街,原本是个自然村,各家各户随意盖的房子,当城市不断扩张,高楼包围了这个村子,这些房子便改造成门面店铺,大多在卖吃食,生的和熟的,也有在卖各种日用杂货,地方特产,随后什么行当的全进来了,旅舍,酒吧,裁缝店,理发馆,洗脚屋,麻将室,歌舞厅,以及修鞋,掏耳,拔牙,按摩,刮痧,文身,染甲,算卦,能想到的都有,没想到的也有。而原先的耳房,土木架构的就拆掉建水泥结构的,原先是水泥预制板建的平顶房,便全在加盖,有三层的,四层的,还有五层六层,一律出租[13]。
乡村还未被完全吞噬,城镇化还未完善,有经济学家指出当前我们的城乡矛盾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城镇化本身,而在于城镇化的不彻底,所以才会产生这些问题,《暂坐》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方面在反思城市,一方面又在哀叹乡村。
二 作为策略的文体——故事的“碎片化”与“说话”的技艺
《暂坐》中,涉及的女主人公多达十几个,她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故事。如果说非要寻找一条线索来将这些故事串联起来,那便是生病的夏自花,因为整部小说大部分情节的展开都是围绕着生病的夏自花——这一唯一显在的中心展开的,十几个姐妹轮流照顾生病住院病情不断恶化的夏自花,直至她离世,再到冯迎失事的消息传来,十几个人物编织成的这张人物网随着人物的离去变得支离破碎。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支撑起整个小说的主线,《暂坐》的实验性尝试也恰恰在于人物塑造上和语言艺术上的创新,至少相较于贾平凹之前的小说创作有所突破。首先,在故事情节的处理上更偏重于主观色彩,并未呈现一个完整的能够统摄全局的故事线索,多个人物的杂糅,营造的是一种“碎片化”的感觉。其次,在人物塑造方面,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的描写,把海若、夏自花、陆以可等一众人物与社会、与自我、与他人放置在一起,她们存在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对话,她们或叛逆、或挣扎、或怀疑,在语言的狂欢中寻找自我。
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伊娃尽管一睁眼就面对的是西京城的雾霾与喧嚣,但是她对这座城市充满着爱恋,这里的姐妹,这里的食物,这里的街巷,都让她内心感到平静,伊娃一度觉得自己已经是西京人了。《暂坐》以这样一个“异乡人”的视角切入故事的发生现场——暂坐茶庄,又在异乡人离去的视角中来到了小说的结尾,伊娃扮演了故事之外的一个全知视角的角色,从另一个角度看,她又是故事里的人,她的归来,给茶庄增添了欢声笑语,她和羿光的短暂情事照亮了她身上的那份属于女性的光辉,也给才子羿光的风流韵事增添了一份神秘。辛起的故事或许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影子,为了钱搭上了70岁的香港老头,欲和自己的丈夫离婚,并找来希立水给自己出谋划策,自己一心想着去香港找那个富商并意图设计怀上他的孩子,后来众姐妹帮其搬出了家里的财产,结果呢?辛起和伊娃在被雾霾浸泡的那个傍晚,在准备离去之前,感叹曾经发生的一切。海若作为众姐妹眼中无所不能的人,最后被纪委带走了,从“织网的人”变成了“网上的猎物”。还有严念初和大学教授的故事、冯迎意外失事的故事、陆以可找寻父亲身影的故事。这些故事各自独立成形,并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宏大叙事,而是在平铺直叙中,把这些碎片化的故事串联起来,营造了一种“碎片化的大暴发”。本雅明在论述现代性的时候,曾提出“星丛”的概念,现实也不过是由微小对象和碎片化小构件构成的某种“星丛”,而非抽象整体主义思维方式所能把握的空洞整体和宏大体系[14]。现代性的一个很直观的特征就是碎片化的大暴发,本雅明引入寓言来重组碎片以发现置于他处的意义,《暂坐》里故事的碎片化是作家意图构建的一个现代主义图景,有意将意义深藏于故事的言说之中,当然,其方式不仅仅是让故事碎片化,其采用的策略还在于让“说话”填补叙述,让人物的言说代替作者的言说,说话的技艺填补的并非是意义的空缺,而在于其占据了意义的位置,其目的不在于被掩饰的意义,其本身就是目的。
“碎片化”的故事给人造成的一个错觉就是没有中心,为了弥补这种错觉,“说话”的技艺便发挥了作用,形式的丰满拯救了内容上的松散。“某某说”这样的字眼几乎遍及了小说的每一个段落,仿佛把读者带到了一个被话语充斥着的世界,在这话语的世界里,有着作者不同人的言说所构建的语言策略。“说话”亦是《暂坐》里的人物对话,占据了21万字的一大部分,羿光全知视角的言说、辛起和伊娃的彻夜长谈、海若的喋喋不休……所有的描写都沉浸在“说话”的技艺里。
贾平凹一如既往地重视方言的书写,来自俄罗斯的伊娃时不时地卖弄着自己不标准的西京话,外国留学生的身份挡不住她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在暂坐茶庄的第一次出现便“秀”了一把不标准的方言。
伊娃问:海姐呢?她也称呼海若是海姐,尾音上扬,倒显得亲昵好听。小唐翘着舌头说:海姐一早出去办事了,过一会儿可能就回来吧。伊娃说:你学我?小唐就说:方言说得不地道?!普通话是四声,西京话只有平声和仄声,最后一字要下坠。伊娃不好意思了,耸耸肩,作了个鬼脸[15]。
在本地人小唐看来伊娃那引人发笑的西京方言在这里表现为一种语言的错位,语言的错位更是意味着一种身份意识的错位,伊娃是一个求学于异国他乡的学生,更是一个女子,她更是碎片化的故事脉络中的一脉。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16]伊娃的言说会与观众想象中的言说存在着错位,产生滑稽感的同时也注定被排除在了西京之外,在西京,她只是一个过客,终究要离去。
羿光是众多女子的故事脉络中出现次数最多的男性,他的每一次出现也多是以“羿光说”的形式在言说。羿光是贾平凹在《暂坐》中塑造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既能写书又能写字,且其字的价钱很高,备受人们尊敬,所以其在众人中的话语也最有分量。他说“在中国,权力面前艺术都是雕虫小技”“这个社会说是妇女翻身,其实仍然是男性的社会”“女人要什么天才,长得好就是天才”“我告诉你什么是艺术,把实用的变成无用的过程就是艺术”。羿光的一系列言说或针砭时弊,或富含哲理,或境界高深。总之,贾平凹笔下的羿光是众女子依仗的所在,是一个德高望重但又不能免于世俗的知识分子形象。
众多主人公编织的故事脉络构成了一场语言的狂欢,贾平凹用“说话”的策略重新将碎片化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狂欢现场。“‘现场感’是一个可以带来希望的把握现实的能力、路径与方法。”[17]将语言诉诸“现场感”,事实上是放弃了“真实感”,读者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故事发生的现场的语言言说,却有可能在“现场感”中迷失,从而停留在“现场感”之中,读故事的人被小说的文本策略征用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贾平凹曾这样自述:“小说是什么?小说是一种说话,说一段故事,我们做过的许许多多的努力——世上已经有那么多的作家和作品,怎样从他们身边走过,依然再走——其实都是在企图着新的说法。”[18]本雅明曾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讲道:“口口相传的经验是所有讲故事者都从中汲取灵思的源泉。那些把故事书写下来的人当中,只有佼佼者才能使书写版本贴近众多无名讲故事人的口语。”[19]掌握“说话”的技艺是能够把故事讲得好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能够左右故事脉络甚至是深层意涵的策略。
《暂坐》里的“说话”是在这个人云亦云、众说纷纭的时代,具有独特风格的“说话”,他们的言说构建起了对这个时代的反思,人们都在说,在说什么,说来说去为了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问题构架。一旦我们回到小说的语言构成层面,语言只是在能指和所指的对立中实现了其指涉功能,在读者和世界之间搭建一种拟真关系,所以说语言并非现实本身。既然语言不能拷贝现实,那么问题的提法就变成了下面的形式:不再是“文学是如何拷贝现实?”而是“它如何让我们相信它在拷贝现实?”用何种机制拷贝现实[20]?作家作为小说的表现形式——语言的掌控者,其在语言上的策略包含了其对世界的更深层次的认知。在《暂坐》里,“说话的技艺”冲破了模仿和再现的限制,更多具有现代主义意识的笔法在制造“真实效应”的同时,也穿越了指涉的幻象,零零散散的语言策略一旦综合起来便具有了不一样的效应,从语言本身去突破语言的局限,真实感与在场感之中蕴含着时代的反思,且不说讲的故事的真实与否或者是不是现实主义创作,至少在创作方法上,现代主义被利用了起来,这也正是《暂坐》在文体层面上的策略书写。
三 既问苍生亦问鬼神——来自实在界的荒诞
《暂坐》里那个名为“暂坐茶庄”的二楼,是海若收拾出来迎接西藏活佛的,海若一直期盼着活佛的到来,可是直至小说结尾,海若也没有等来活佛,活佛也没有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这不禁让人想起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是一个“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的荒诞剧,两个流浪汉等待着从未到来的“戈多”,喻示着人生就是一场没有希望的等待。《暂坐》里的等待亦有些许的此种内涵,茶庄始终在那里,海若的期望被安放在“活佛会到来”这样一个消息上,这里的等待是一种延宕,活佛是那个一直在到来却从未到达的存在。
活佛在众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值得敬畏的能够给人带来安宁的形象,吴老板出于对佛的虔诚,一度闭关;伊娃见了海若精心布置的佛堂,看得入神,不觉双手合十,静默半天;海若经常去吴老板的佛堂礼佛,得知吴老板邀请西藏活佛后特地计划安排活佛居住。她们的虔诚面对的却是一个永远没有到来的对象,她们把心中的苦闷寄托在活佛身上以带给自己心灵上的慰藉,只是活佛的永远不能到来,让故事的发生带上了荒诞感。荒诞是把所面对的现实理解为一种不合理状态、不符合逻辑状态的意识。面对不同的现实范畴,也就有不同的荒诞,政治法律荒诞、精神文化荒诞、语言荒诞、生存荒诞,等等。现实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逻辑,这都是人类理性范围里的事情,当作家把现存的事物、关系、规范、秩序理解为、表现为逻辑性、必然性荡然无存的不合理状态时,他就是在持一定的理性尺度进行批判[21]。从这个意义上讲,荒诞成为作者叙事策略的一种风格,也是叙事策略所要达成的一个阅读效果。类似于这种荒谬的等待的书写,还有关乎“再生人”的奇妙书写,还有情节上的神秘巧合。
《暂坐》的第三节中,海若、伊娃、陆以可三人去吃饭的路上,陆以可向伊娃讲述了自己遇到父亲的故事,一个街头偶然遇到的鞋匠,长得和自己去世三十多年的父亲一模一样,陆以可当时对此感到诧异,在奇怪地连病三日之后,再去寻找鞋匠的身影已经难觅其踪。陆以可觉得这是去世的父亲给她的昭示,父亲在这里,她也应该留在西京。第二十四节“向其语庵前”中,向其语和陆以可专门谈起了“再生人”的话题,这让陆以可对自己在这座城市的去留再一次产生了疑问,陆以可把父亲当成了人生的指路明灯,在现实中搜寻已经离世了的父亲的身影来给自己的去留做一个决定,无论是“再生人”还是鬼神附体这样的书写,都是在精神层面上去填补一种欲望的短缺,父亲的离世给陆以可造成的内心创伤,构成了陆以可的欲望空缺。陆以可一直在现实中寻找一个父亲的形象来弥补父亲的离世所带来的情感创伤,也正是“再生人”“鬼神附体”这样带有神秘意味的书写,让陆以可存有希望并得到慰藉。当然,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分析陆以可的遭遇有其合理之处,但对于读者来说,这样的叙事策略,荒诞感大于创伤感。
除此之外,冯迎的故事,最能让人体会到《暂坐》的书写在现实和非现实之间的游离感。冯迎在小说中的出现一开始就给人带来一种神秘感,冯迎随团出国后就失去了联系,章怀却意外地见到了冯迎并带话给海若。到后来,羿光得知冯迎早就失事的消息,人们才恍然意识到章怀所见到冯迎的时候,冯迎已经在前一天失事了。虽然这是一段读起来令人感到诡异甚至是毛骨悚然的书写,但在现实中却有类似的新闻报道:
范伯生报告确切的消息,那个书画家代表团出访期间,他们都没有和家属联系过,家属里有人拨打过电话,也是关机,便认为是他们没有开通国际漫游业务。而半个月前,一架马来西亚的飞机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坠毁,新闻在中央电视台都播了,但谁也没有和书画代表团想到一起。代表团中有两人属于文联机关单位,一位是大画家王季,他是代表团团长,一位就是冯迎[22]。
这是作家笔下的情景,众所周知的是在2014年3月8日,由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马航MH370失事,它的失事带来了一系列的悲伤以及谜团。
《暂坐》的书写就是这样在鬼神、幽灵和新闻事件之中穿插,作家用幽灵、鬼神来“爆破”言语制造的狂欢,把现实事件再一次带入众说纷纭的“现场”,荒诞的笔法使得读者在现实和非现实之间游离,从而陷入“现场感”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制造“现场感”的事件,让故事的主人公穿越了幻象,直面实在界的创伤内核。“人总有一天会死亡,但是我们的死亡比想象的要来得快,正因为如此,我们总是无法承受死亡带来的震撼和痛苦。”[23]陆以可所面对的那个已经逝去的父亲的身影,一方面是离世的父亲给她造成的心灵的创伤,一方面是她聊无意义的现实生活对父亲的死亡的难以接受。面对父亲的死亡这样一个终极命题,陆以可的不愿意或者说不接受,是她在自我的世界里编织了父亲的影子或者鬼魂这样的形象,来逃避或者抵抗“死亡”。
之所以说“死亡”是一个终极意义上的命题,是因为在小说的架构中,无论是陆以可离世的父亲,还是早已失事的冯迎都与死亡相关。尤其是冯迎的死亡消息得以确认之后,众女子编织起的故事脉络以及说话的狂欢变得黯然失色,故事没有了活力,故事里的人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生活似乎没有了意义。《暂坐》用原本属于精神分析的“死亡驱力”这样一个概念,把由“说话”和“碎片化”的叙事编织起来的故事脉络建构成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无中心无意义的倾向。《暂坐》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具有“寓言”意义的文本,贾平凹试图用这种方式告诉人们,虽然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时代,但是关于这个世界依然有着太多的困惑,十几个女子为什么不结婚或离异,她们为什么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圈子,或许把不能言说的事情都交给鬼神、幽灵这样不可及的载体,也不失为“拯救现实”的一种尝试。
四 现实有多远?——现实主义的“新出路”
贾平凹在《暂坐》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在这个年代,没有大的视野,没有现代主义的意识,小说已难以写下去。这道理每个作家都懂,并且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在让自己由土变洋,变得更现实主义。可越是了解着现实主义就越了解着超现实主义,越是了解着超现实主义也越是了解着现实主义。”[24]新世纪已经过去了20年,现实主义书写究竟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如果我们把视角投射到新时期,我们发现,新时期的现实主义发展经历了革命话语式微、现代主义入侵、现实主义的过度调整、现实主义的多元化等阶段。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面临的是一个大众文化盛行、世俗化倾向明显的语境,多元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更具体地讲,21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书写走向的是泛化、神化甚至颠覆之路。
在这样一个现实主义发展背景下,《暂坐》的书写给多元化的文学时代带来一些新的尝试。首先,小说构建了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城镇化的加剧、城市的焦虑、乡村的忧思,这些最为现实的面貌并置在文本中并借用“雾霾”“民工”这样的意象表现出来。其次,在这样一个贴近现实的背景之下,作者塑造了一群远离底层民众的都市女子,她们的故事是碎片化的,她们的情感多是充满忧郁的,她们是喋喋不休的,这些文体策略,带人们走进了故事的发生现场。最后,作家还设置了一些关乎鬼神、幽灵的奇异叙事逻辑,游离于现实和非现实之间。显然,《暂坐》是一部充满现代主义意识的现实主义创作。
何为现实主义?在文学中何以发现现实?现实是否等同于真实?这些疑问是创作界和理论界一直在探索但又没有统一结论的话题。2018年,《长篇小说选刊》用整整两期开辟“新时代与现实主义”专栏,刊发了作家、评论家、学者们的60多篇文章来探讨现实主义问题,既有“反映”“典型人物”“高于生活”这样的老议题,也有“现实感”“泛化”“数字化”这样的新议题。新世纪已经过去20年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聚焦于现实主义这一经典命题,我们的写作也在试图寻找新的途径来寻找真正的现实主义,《暂坐》可以说是现代意识和现实主义相互碰撞后在新时代的自发融合。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它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有着独有的风骨。《土门》中的任厚村、《高兴》中的池头村、《暂坐》里的西京,跨越20多年的书写是巨变中国的缩影。《暂坐》里我们读到的不再是村民的抗争,也不是城乡接合部乡下人进城的窘境,而是一个现代化都市里的一群现代女性。贾平凹在后记中写道,作家们都明白在这时代的书写需要具备现代意识。《暂坐》里我们读到了不同于以往的文体策略,读到了不同于以往的叙事逻辑,也读到了荒诞的意味,那么这些现代意识能拯救现实主义泛化所带来的问题吗?这是作家和评论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如果非得给《暂坐》的书写下一个定论,那么可以回到现实主义的话语维度上,即现实主义是一种具有自己规则和规约的话语,一种编码,一种既不比其他编码更自然,也不比它们更真实的编码[25]。《暂坐》的现实主义书写,是一种借助于现代主义意识勾勒的充满在场感但又指涉现实的策略书写。
《暂坐》在文体策略上所呈现的现代意识,离不开现实生活,离不开众生之相,只是在新的维度上开启了现实主义篇章。《暂坐》回到了那个永恒的命题:生活长在,现实主义长在;生命常新,现实主义长青[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