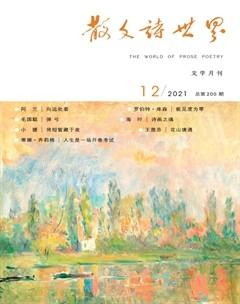一个声音
邱枫
一个声音,刚刚摆脱了苹果的形体,像一份神谕倏然掉落在秋天的大地上,她从远方飘来,穿透了温暖的空气和一个人的衰老的身体,又向远方逃逸而去。
一个声音,或许是一棵正在开的植物——花朵的呓语,纷动的叶子,或许来自空荡荡的马路上一个旅人疲倦的叹息声。
一个声音,来自遥远的时间,带着灰色的尘土,暗淡的光芒,带着某个故事的结尾,来到这儿,或许,被我听到;又或许,根本也从未觉察得到。
一个声音,或许来自一个偏僻的房间,一个颓丧的中年人,消磨掉茶水、寂寞和词语的声音。他低头,声音就跃出了窗子,从一片贫穷的屋顶上飞过来,然后又蓦然消失。
一个声音,秋天的土地里,繁忙的机械遗失的那个声音,染着一缕夕阳的暗红,携着冷凉的味道,跃过一截断渠,一片蒿草洼地,然后来到这里,进入一个停下来、观看田野的人的肉体里。
一个声音,秋天、旷夜、空院子,玻璃透进半边月亮,红尘渐渐退去的声音,或许来自一个女人的啜泣声,某一个孤独灵魂的叫喊声。
一个声音,黑暗的铁锈味,午夜的一颗心的碎裂声,一颗心扩散开来,像果实、星辰,像一个梦,它来到人世,人世生息皆无,人世单薄、贫瘠。一棵树和一堵墙,来回地走走停停,最后又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
一个声音,冬天的深处,雪的声音,白茫茫的声音,覆盖枯槁的人心和无梦的大地,覆盖一个时代走过去的脚步声。
一个声音,来自衰老者的回忆,来自对故土的怀念和怅惘,来自一个人的躺在黑暗的角落里的辗转反侧,夜不成寐。
一个声音,衣物的摩挲声,晚餐的渐冷声,生活的落幕声,火的熄灭声,和黑暗的倾转声、酒瓶空空的嗡嗡声。一个声音,从某人的手中逃掉了。
一个声音,村庄的呼吸声,落魄人的沙哑声,冷雨的声音,马车驶过街道的声音,店铺忽闪的声音,最后一盏灯灭了,最后一盏灯的声音,被一个流浪者捕捉到了。
一个声音,众人合一的声音,一个嗓音,亘古而至,带着艺术气、星辰光,在高空下停留,然后又消失在冬天的麦地里。
一个声音,苹果被销蚀的声音,熟肉被腐化的声音,刀叉断裂的声音,一个人缺席的声音,光色走掉,柜子倾斜的声音,它溜出了房间,然后走向别处。
一个声音,浑浊的思绪和苍茫的双手,味觉淡下去的声音,岁月的最后影像,在门口就这么一闪,就消失在无名的角落里了。
一个声音,我触摸一幅画的声音,我想象的声音,我看画中的雪,我走在雪地里,我走进了画中那扇门里的声音。
一个声音,鸽子的声音,在阁楼上,翅膀扑打的声音,汩汩的水,寒霜降临的声音,蓝色夜空,蓝得纯粹的声音,翅膀弯曲,小兽挺立身子的声音,秋天纯洁的声音,压过房梁,落在失眠人的眼睛里。
一个声音,一个听不到的声音,被窒息,被溺亡的声音,一具尸体,一枚风干的果子,一块铁生锈的声音,一只手越来越远的声音,一个人的影背模糊、消失。
一个声音,思想支起的声音,聆听宇宙的声音,聆听大洋深处的声音,梦都死了,我们该向什么伸出手去。
一个声音,来自春天的声音,值得被纪念的声音,一朵红,一朵绿,一朵黄,一朵可能什么都是的声音,春天,水的时间,阳光绽开的声音,大地忙碌的声音,梦里梦的声音,一个人抬眼,望过去的声音。
一个声音,我记得谁,某某某粲然惊现的声音,她闪在大野上的人群中,像一个黄昏的身影,只能遥望或悼念。
一个声音,丝丝缕缕,再也抓不住;一个声音,我还在这个声音里独守,深坐、相迎,但我已没有了信心和热情。一个声音消失了,因为又一个冬天就要到了。
我想靠回忆活着,但我没有回忆,我只能向前走,我被一个声音带着走向另一个声音,我走过了岁月、红尘,走过了寡淡的人世,走过了动荡的命运。
我还未放弃掉天边的那颗星,我还一直在看着它,每每宇宙穷竭的时候。
我仍旧得回到自己的界域里,隔绝、苑囿、孤独、贫穷,红尘不值得眷念,但人间的烟火味仍让我泪涌不止。
我看夕阳落下,坠入泥土,我看清明上升,展现另一幅图景,我知道,我还有救,因为我永未泯灭自己那一颗向上求美的心灵。
我曾沉溺于浑浊的暗水里,绝望的空气里,陷落的深渊里,我又一次挣扎着浮了上来。我倾听每一个经过的破空而来的那一个声音,我把它握住,听得深切、细致、入心入肺入骨,听得泪热力竭。人世虚渺,但一个又一个的声音确切,我因为聆听而更加纯净,因为聆听而更加懂得生之幸福、留连,我怀念过,我更向往前程上每一個经过的声音
愿一切美好仍如旧时年华,来生还这样可以触摸每一个经过了的令人怦然心动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