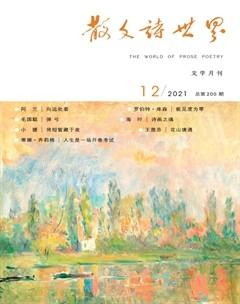给来世的信
2021-12-17 19:19
散文诗世界 2021年12期
有一种生活,可以让所有的诗人不必再言说?
——朱朱 《越境——致宋琳,1991年》
姐姐,今夜我辗转难眠,抬眼望
窗外的枇杷树和小菜园全无平日的生气
蔫蔫地耷拉着枝叶,像每个步履匆匆的青年人
在步履匆匆中慢慢丧失了野心,像我们
困于天气的燥热,过多的繁芜
一次次在七月的迷宫外反复兜圈
姐姐,你曾说厦门无疑是颗海的蓝色心脏
天然的白鹤和浅滩和碧空,和诗歌多么匹配
我却觉得,在厦门写诗是多么难产
想说的话前人皆已说出,想写的诗悬在半空
久久不肯落下,和这里的雨一样踌躇
其中的缘由一样不足为外人道也
姐姐,我的语无伦次总是用错了地方
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时代竟会令人如此费解
人們热衷于互相侵犯,为诗歌举办葬礼
小丑和烈士仍然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诗人的名号被无限透支,忙于生产廉价的赞美
诗歌难以把尊严和人类互相介绍*
如今写诗难道果真是自取其辱?——我不明白
姐姐,我所了解的诗人
总是肩负隐匿的痛苦,深藏人间
只在恰当时出现,在镜中与自己交换意见
被所爱所厌的万物一同割伤
比野草更低矮,比流水更寡言,比孤石更寂寞
所以我觉得可笑,姐姐,冥冥中激情得而复失
一个夜晚的坍塌,常令一个人和黑洞的距离越近
我曾经消逝在怀念中,现在你让我醒来
重新活着,凝视一首诗的诞生到腐烂
保持同朋友的隔阂,在枕头下伪装在别处
翻身后荒谬的肉体与他人在夜里拼命地奔逃
*引自海子的诗《祖国,或以梦为马》
*引自康城的诗《溢出》
猜你喜欢
廉政瞭望·下半月(2022年4期)2022-05-12
作文与考试·小学高年级版(2022年4期)2022-03-08
青年文学家(2020年31期)2020-11-30
广西文学(2020年10期)2020-10-29
辽河(2020年8期)2020-09-02
文苑·经典美文(2020年3期)2020-04-19
VOGUE服饰与美容(2019年10期)2019-12-02
东坡赤壁诗词(2019年1期)2019-04-30
思维与智慧·上半月(2016年12期)2016-12-16
作文与考试·小学低年级版(2016年19期)2016-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