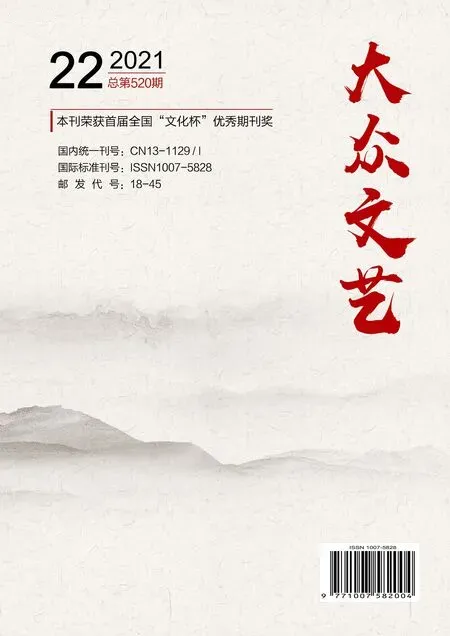从《鼠疫》透视新冠疫情的创伤叙事*
陈雅婷 刘奕晨 黄颖 梁倚梦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000)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是对现实的反映,2020年肆虐横行的新冠疫情对现实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对创伤书写和疫情文学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但因文学创作具有时序性和延迟性,文学创作在新冠爆发后虽然紧跟时事,但截至目前,作品并不多。同样,在世界文学的历史上,直接描写疫情的优秀文学作品也是屈指可数的,而加缪的《鼠疫》就是少有的直面描写疫情的作品。在病理上,新冠同鼠疫一样,均为呼吸道疾病,故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分析《鼠疫》和2020年发表的以新冠疫情为主题的作品,如柳长青的《小区战役那些天》、熊育群的《苍生在上》和《第76天》等,来探究相似境况的不同书写。
鼠疫和新冠具有跨时间、跨文化的相似性——它们都是人类大规模的群体性灾难,为人类塑造了相似的境遇:未知的疾病和蔓延的死亡。加缪在《鼠疫》中虚构了一座因鼠疫爆发而被封锁的城市奥兰,而现实中武汉也因疫情而短暂封城。境况虽然相似,但对创伤以及人物的书写却有着很大不同。加缪是法国存在主义大师,他的“介入”文学观体现在《鼠疫》中对荒诞思想的反抗;新冠疫情中的文学创作主体也跟紧时事,发挥文学的力量来对抗疫情。虽然同是“介入”文学观,但两者在文学如何“介入”现实的处理方式上存在很大区别,主要体现在以象征的方式发表议论以及表达内容的选择与剪裁上。
一、委婉的议论:象征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和个体经验无关,是因遗传保留的普遍心理。”人类面对创伤都有一种蜷缩的畏惧心理,因此人对于创伤往往采取迂回的方式。除了隐含在人类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外,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作家的创作理念也影响着文本的书写。加缪虽然认为文学应该“介入”现实,但是他不主张过于直接的“介入”,而是以委婉的方式介入以寻求文学现实性和艺术性的平衡。由于与新冠疫情暴发的时间相距太近,且疫情发展形势不明,发表于2020年的文学创作大多弱化了情感的宣泄和个性化的表达,不直接介入事件,辅以含蓄的方式来表达作者对疫情的看法。在文本中,作家的创伤书写都经过了锐化处理,这是因为作家对事件都有自我的立场,但自我立场不能在议论事件的时候表现出来,否则倾向性会过于明显。韦恩布斯曾说:“这种对事件的直接议论很可能显得比对人物的议论更为介入…作者们就经常通过把议论戏剧化为场面或象征来隐藏它”。在文本中,作家就是将议论融入艺术化的象征和场面中,以实现委婉性和倾向性的平衡。
在《鼠疫》中,“海”是贯穿始终的意象。在小说开头,加缪就描写了奥兰是一座滨海的小城,海洋隐约带来疾病的气息,且小说中曾三次具体描写海。第一次是在疫情刚刚有迹象,当局不作为的情况下,“海”颜色的变化映照着里厄医生心情的转变,“丧失了那种幽深的蓝色”暗示着里厄医生内心的忧虑。第二次是在疫情大爆发的时候,“看不见的大海波涛汹涌”象征着鼠疫杆菌的汹涌来势,而“海藻和盐的气味”使人联想到死尸的气味。第三次是在疫情过后,书中写道“悬崖脚下的大海涛声更为喧响”,喧响的大海涛声表面呼应了城中人的欢呼,但对于里厄医生而言,在这场战斗的最后,他是悲凉的,因为他的战友塔鲁和自己的妻子在疫情中溘然长逝。加缪很少直接描写里厄医生的内心,而借助“海”这一固定意象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来映射里厄医生内心的所感所想。
而在以新冠为主题的文学创作中,“春天”“寒冬”“空旷街道”和“灯火”等意象频繁出现于多篇作品,仔细阅读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意象不仅仅指向现实出现的场景,在其背后亦有象征意味,如“是啊,这是一个需要修复的春天,也是一个值得赞美的春天。”;“这里天色阴暗,像有一场雨雪随时降临,无处可挡的阴冷。”;“严寒时节的首都街头没有什么行人。”;“九省通衢的繁华都市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景象——一边是救人如救火的医务人员,如潮的患者,一边是空荡荡的街巷。”;“现在她每天扫的只有满街的落叶。”;“那一盏盏点亮的路灯显得如此微弱。”…作家普遍使用“春天”象征希望和疫情退去的时节,“寒冬”指眼前遭受疫情影响的生活,“空旷的街道”意味着被破坏的欢乐,而“灯火”则指昔日热闹的生活。而作家对春天的呼唤,在寒冬季节里的坚守,在“空旷街道”上的伤感和对昔日“灯火”的怀念与期盼,无不是借着象征来曲折表达自己对新冠疫情的看法。
《鼠疫》和以新冠为主题的文学创作都使用象征来表达作者含蓄的议论,但不难看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费洛姆象征理论将象征分为:偶然象征、惯例象征、普遍象征。具体到文学领域,象征则分为偶然象征和普遍象征。贯穿《鼠疫》的“大海”就属于偶然象征,它是个人创造性的象征展示,起到了联系和想象的作用。《鼠疫》中使用“大海”作为鼠疫的象征,感受主体是里厄医生,即大海的象征指向了里厄医生,它具有私密性,更加凸显个人创造和个人感受。与《鼠疫》不同的是,新冠主题文学中的意象大多属于普遍象征。正如乔治•桑塔耶那所说:“文学作品中有些象征手法是被一直长期沿用的,他们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格局。”普遍象征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比如“春天”“冬天”等自然象征,是基于一个国家对同一意象的常识性联想,代表着一个国家对自然的共同感受;“空旷街道”和“灯火”等社会象征,经过了漫长的积淀,深深地根植于人们脑海之中,是为社会所公认的。与偶然意象不同,这些约定俗成的普遍象征指向的不仅仅是书写者,还有读者,具有开放性和大众性。
二、表达内容的选择与剪裁
在叙述上,《鼠疫》使叙述者戏剧化,叙述者就是故事中人;新冠主题文学则使用了非戏剧化的叙述者,虽然以日记的形式书写,但却经过了隐含作者的精心剪裁。韦恩布斯认为:“作者借助于确保读者以潜在作者感受到的超然或同情的程度来看待题材,从而实际上正在精心地控制读者涉入或离开故事中事件的程度。”日记体文学之所以区别于普通日记,是因为它必然存在艺术加工。日记体文学作品的书写者会对原有的材料进行选择和剪裁,对叙述内容有意地弱化或强调,从而对读者的理解产生重大影响。《鼠疫》特意在开头设计一个从未出现的叙述者,是因为作品的实际叙述者里厄医生亲身经历了一切,倘若由他讲述故事,读者易对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从而影响读者对故事的接受。而在新冠主题文学书写中,喜用日记的书写形式,这样当读者阅读日记时,会自然觉得这是未经加工的、朴实的作品,但实际上它是被精心处理过的。
在新冠疫情的文本中,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不多,关于苦难的书写也较少通过自己来直接叙述。更多的是通过讲述自己听到的故事,以侧面来描写苦难。用类似“我有一个朋友”的形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是受到创伤后常用的叙事手段,受创者面对曾经的创伤记忆会出现躲闪、逃避的心理机制,而通过别人的名义讲述自己的故事能够降低自我所受的心理冲击。除了这一点外,由于这些作品都是刊登在重要文学杂志上,作者必须谨慎地考虑自己言语。在社会心理学中,有意识地控制他人对自己留下某种印象的现象被称为印象整饰。如果直接谈论个人的问题,难免会心有顾忌,而借他人经历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整饰自我的经验,就不必担心叙述是否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另外,新冠主题作品在选材上,有强化积极方面、弱化苦难方面的倾向。纵观新冠主题文学,疫区内的创作比疫区外的创作少了很多。疫区外的叙事者在表达悲悯之余,更偏向于传达积极的态度、袒露无畏的斗争精神;而来自疫区的作品则更倾向于用压抑迷茫的笔调描写生活的琐碎,用较为平静简短地语言书写周围人的生死无常。其中《武汉人的悲伤安了消音器》一文就阐释了武汉人的“失声”:那些直面灾难的人,所受的创伤越多,越是令人难以发声——创伤的首发表征就是禁锢废绝受创者的言说能力。正如福克纳所说:“过去的从未消逝,它甚至并没有过去。”新冠疫情中高质量的文学创作不多,但在简略、客观的表达背后,隐藏着无以言表的巨大伤痛。在疫情面前,很多创伤文学的书写者试图将自我与残酷的现实相分离,具体表现为感情上的麻痹漠然和语言上的贫弱枯槁。
基于以上原因,受创者的叙述能力受阻,因此,在创伤叙事的文本中,往往会出现混乱、掩盖、扭曲等情况。尽管受创者无法清晰地描述所发生的一切,但那些记忆片段却已烙印在他们的无意识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在解读文本时,更加关注那些掩盖在文本背后被压抑、被扭曲的声音,关注文本呈现出的关于受创的种种“症候”。阿尔都塞认为:“症候阅读则是在措辞、句法或话语层面找出不连续之处,这些不连续之处昭示着对原文的暴力改写,是对目的的语文化的策略性干涉。这种干涉既依赖本土价值观,又攻击本土价值观。”这种矛盾的创作心理可以从文本的断裂之处被体会出来,在新冠疫情的文本中,我们仔细分析了作者选择和剪裁内容,挖掘到了隐藏在文本背后被忽视的部分:有人认为“我有一个朋友”的书写就是非虚构书写,但恰恰是透过“朋友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到更加真实的观点。而透过文本里弱化和缺失的部分,我们就更能感觉到书写者内心深处所害怕被触及的伤口。平静笔调的背后隐藏着武汉人纠结的内心——无法摆脱现实的苦难,而苦难沉重又难以言说,于是在创作中就采取了弱化的方式。
无论是《鼠疫》,还是在新冠疫情的书写中,作家都采用了委婉的表达方式来表现苦难,对惨痛的直接描写除了会带来不可避免的艺术快感外,还会要求作家更加细致地描绘受难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艺术的加工和渲染是难以控制的。倘若渲染过多,作者是否在这一真实事件里会逐步丧失客观性呢?无论是加缪设计的未出场的叙述者,还是新冠书写多采用日记的书写形式,都表达了作者对文本真实性的追求。本雅明认为,过于具有倾向性的作品会影响文本质量,从而导致文本对现实的作用减弱,而通过艺术加工的形式能够平衡文本的倾向性与读者接受的效果。委婉的表达让作者不至于陷入对现实的渲染和可能的亵渎,且保持了客观的态度。而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文本真实性的高低程度也左右着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和判断,影响着阅读的效果。倘若文本真实性过低,读者很容易察觉到隐藏在文本背后作者的主观判断和意图,很容易本能地排斥文本。真实性的创伤文本借助委婉的表达,打破了灾难下受创群体的“失声”,见证其所经历的这段历史,从而使创伤经验完成了从个体性到群体性的转化,并构建起了人类群体的文化创伤,使每一个体承担起对人类集体性灾难应尽的责任。
三、结语
《鼠疫》作为一部具有预言性的、超越时空的文学著作,在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时,又一次重新被大众高度关注。本论文从《鼠疫》透视新冠疫情,重点分析整理出两次重大灾难后所出现的创伤叙事,并使用文本细读和症候阅读的方式挖掘文本背后隐藏的内容。通过对文本创伤书写的比较,探究创伤过后我们应该如何书写的问题,企盼文学穿过“灾难之门”后,仍能发挥超越时空的积极意义。正如《黄冈封城日记》中说:“灾难给人教育,死亡和爱,而这正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如果新冠最终成了与人类长期共存的病毒,那么,借着这次大危机、大混沌,我们应当使关于新冠的创伤叙事文本成为传递人类经验的火把——混沌之处,叙事与言说是存在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