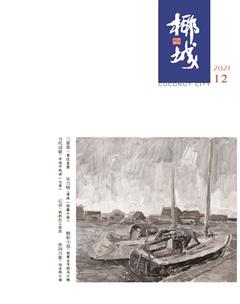但少闲人
作者简介:王中举,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成都某高校。先后在 《人民日报》 《文学报》 《读者》 《星星》 诗刊、《草堂》诗刊、《诗歌报》月刊、《飞天》等刊物发表散文和诗歌作品若干。
真正的闲人,如暮云春树,如花晨月夕,静静地散发着柔光,让周遭的一切安然。
有个女诗人曾说:“神在我们喜欢的事物里。”
一个活得有趣的人,喜欢玩味的事物多了,身上往往会具有一种让人讶异的审美力,其有趣的活法,可以明心见性,使你心生欢喜,我们因此窥得到这个人的真髓。
比如我的好友罗永明,已届退休年龄,既是同一所大学的同学,又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见多了也颇烦,隔久了又想见,即使狭路相逢,也要鸣笛示意。之所以成为我的好友,也是很多其他人的好友,是因为他懂生活、爱钻研、有童心、察雅意、解风趣、敢担当。总之一句话,他身上“可爱者甚蕃”。
我原来戏称他“罗大爷”,最近他喜得孙儿,已是名副其实的罗大爷了。你别看这家伙长得五大三粗,浓眉阔脸,膀肥腰圆,活脱脱一个伟丈夫。其实,他慈眉善目,成天开心乐呵,活脱脱又是我们身边的一尊弥勒佛。
去年冬天,北风一阵紧似一阵,估计成都周边的山中已纷纷扬扬开始下雪,体弱的我,一天到晚瑟缩着。见此光景,他居然心花怒放,眯着一对小眼睛,小孩儿一般高兴地拍着两个肥厚的手掌,一个劲儿地撺掇我:走,我带你上鸡冠山去踩雪!
我的天,他这番提议令人匪夷所思,却惊艳了我,让我不禁莞尔。你可以想见,两个粗糙的大老爷们,相约去山中踩雪,与其说是去“踩雪”,不如说是去“采雪”,这该是从唐诗宋词里走出来的高人韵士才有的举动,被他毫无遮拦地脱口而出,不知有多风雅、多孟浪。
在万物凋敝的冬天,还能够有一番看雪的心境,太逗了!我对眼前这个大男人肃然起敬。我一下子想到了另一个“疯子”,号称台湾“诗魔”的洛夫,写过一首惊世骇俗的大美小诗《葬我于雪》:
用裁纸刀
把残雪砌成一座小小的坟
其中埋葬的
是一块炼了千年
犹未化灰的
火成岩
罗大爷就是一座“火成岩”,历经人间烟火,不但没有一身油腻,反而依然天真爛漫,“顽童”心性犹存,实在难能可贵。
他看我有些畏缩不前,进一步劝勉我:我们只是在雪地里随意走一走,留下几行脚印,发一会儿呆,很快就回来。
这又有点儿像恋爱中人的罗曼蒂克,他却丝毫不觉滑稽唐突。天底下没有哪个“理工男”会有他这般奇思妙想,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亦风亦雅的文艺青年。
我心里想:他真的可爱,也真的有趣,他给我描绘的,其实就是一幅古意盎然、纯白纯美的“雪泥鸿爪”图。人生一世,很多美好的事物容易随风飘逝,最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雪泥鸿爪”虽也只是一个诗意的图景,但它毕竟留下了一串实实在在的美丽印记。
因为怕冷,我们到底没有去成,但这段浪漫佳话恐怕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
今年暑假,为躲避高温天气,我们几次相约进山避暑。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垂钓碧溪,我则乐于当他的“随从”“跟班”,帮他提拖鞋、拿草帽、打手电筒、端茶递水、照管摊位。晚上,我们闲看山坡的萤火虫编队飞行,听大肚子林蛙的大合唱,观星星们在天幕上冷艳燃烧,而后在深山峡谷的暗香疏影中枕溪而眠,着实过了几天神仙日子。
在凉沁沁的白云沟,他玩兴大发,像是回到了童年,忘乎所以地沉醉于野钓,不惜冒着烈日,挥汗如雨,在鞍子河里弯腰弓背搬石头,那上面附着了一种名叫“石蝉子”的水虫,可以用它来钓雅鱼和三文鱼。他的钓鱼技术委实不敢恭维,但他活像一个野人,纵情山水,痴迷其间,怡然自得,这就够了。
有一天,我们上午驱车前往西岭雪山,下午转战朝阳湖,誓要钓出一番丰功伟绩,哪知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一整天,连一只小虾米也没钓着。到了晚上,钓鱼的雅兴烟消云散,吃鱼的兴致倒是涌上心头,两个人不由分说,点了一盆麻辣鲜香的雅鱼大快朵颐,打着饱嗝,心满意足。虽然一条鱼也没钓到,但我俩装着一肚皮的鱼满载而归。
夏天在蝉的噪声中渐行渐远,处暑之后,秋雨连绵,我们的秋季学期也开始了。某天我正在办公室干活儿,罗大爷忽然来电,让我赶紧到校园的柳湖边去。去干啥?看鸟。
当时我还有些气恼:这家伙真是闲得慌,没点儿正经,还要打扰我公干。伸出窗外,探头一看,他正站在稀疏的细雨中眼巴巴地等着我。我不禁噗嗤一笑:雨中观鸟,怕是他身上的风雅病又犯了。
这一回,他貌似幼稚的奇怪之举,还真不是什么附庸风雅,我看到了一个大男子身上极为细致的生命情怀。
我们冒雨漫步到尔静桥桥头的那片丛林。他一路走,一路跟我唠叨,说他昨天就看到有一只十分怪异的鸟,口衔一枚果子,站在枝头一动不动,像是静等自己的大限之期到来。一夜风雨之后,不知那鸟的命运如何。他还说,鸟的死亡很神秘,从未见过鸟是怎样告别这个世界的,云云。
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难道鸟也有圆寂一说?莫不是一只(个)得道的高鸟(人)?这听上去颇有几分“鲁智深浙江坐化”的诡异和玄妙,倒是让我回想起我曾写过的一首小诗《一生歌唱》:
我只看到过鸟的诞生
从未见到过它们如何死亡
被它们隐去的这最后一笔
让我误以为生命还可以继续浪费
我只听到过鸟的鸣叫
很少见到过它们如何发声
它们的肺活量只有那么一丁点儿
一辈子也只穿着那一件衣裳
我今天才恍然大悟
它们倾其一生只为给我们歌唱
那片小树林笼罩在水汽中,偶尔传来三两声鸟叫,之后就是零星的雨声嘀嗒。秋天的树林,静穆,黯淡,沉郁,肃杀,目力所及,别有一番感时伤怀的况味,容易平添一种行将就木的“物哀”之感。说实话,我也牵挂着他说的那只垂死的鸟,在没有良弓捕杀的太平盛世,飞鸟是怎样自然而然地走到生命尽头的?
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找到。难道昨夜就死了?掉落树下,被猫叼走了?亦或今晨被清洁工扫走了?
正在我有些失望又失落的时候,眼尖的罗大爷惊呼:快看,那两只鸟像是又不行了!
我费了老大的劲,终于真切地看到了让人心生悲悯的一幕:
在一棵不大不小的小叶榕树上,两只比麻雀略大的鸟,肩并肩地站在枝头,一动不动,泥塑一般。周围的鸟,不时雀跃、啾鸣,生气十足,精神抖擞,唯独那两只鸟,相向而立,神情凝重,彼此厮守,纹丝不动。看样子它们应该是一对夫妻,不离不弃,正在举行某种仪式,静候着一个特殊时刻的到来。
罗大爷又开始揣想:世上的鸟,命有定数,鸟之将尽,它们或许早有感知,于是精心挑选涅槃之地,择一枝以终老。结束生命是一件很庄严很神圣的事情,它们不想被打扰。
我实在不愿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一幕凄凉,便拖住一截枝丫使劲摇,起初那两只鸟还是不见动静,后来左边的那只动了动,右边的依旧不动,好像左边的鸟忠实陪伴着右边的鸟。再后来,两只鸟都有了动静,甚至扑棱了几下,换了一个位置,继续相守。
原来它们没有死,明明白白地活着!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它们传递出来的是生的信号和生的希望。这片树林是它们死后的墓园,更应是它们生活的天堂。
带着几分欣喜,我们渐渐离开了那个地方。但我开始无端迷信起罗大爷,两天之内他居然兩次见到了鸟之将死,我觉得他有通天地通万物的神秘本领。
他平常无事喜欢闲逛校园,看看柳湖的鱼、鸭、鹅,操心里面下落不明的乌龟、黄鳝,甚至放生了几尾草鱼,说是为了调节一下柳湖的生态环境。他还曾约我去湖边捡鸭蛋,也曾畅想给鹅鸭们修建一座漂亮的“湖畔公馆”。
他真闲,但不是那种闲得无聊,而是闲得很有创意,也很有风致,把闲暇变成了乐趣,把日子过成了乐子,把生活搞成了有几分犯二犯傻的逗比之旅。有人说,闲能生慧,他虽然看上去傻乎乎的,但他其实非常聪明智慧。我有时还讨厌他话多(他喜欢跟人理论,甚至追着人家发表长篇大论),说他像个婆娘,是个“话贩子”,他嘿嘿一笑,赶紧闭嘴。现在想起这些,觉得全都是他的可爱。
现在而今眼目下,惜乎忙人太多,闲人太少,忙人们不舍昼夜地奔腾不息,“郎啊郎,你太忙”,跟忙人打交道,有被裹挟的追命之感;闲人们湮没在滚滚红尘中,四散零落,不知藏身何处。这年头,已经很少听闻有人“秉烛夜游”,更无人“扪虱而谈”了。而大千世界,风月无边,“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所以,我们此时此刻不得不万分佩服千古雅士苏东坡,这个最擅长“忙里偷闲”的奇趣之人,他在《记承天寺夜游》中绝妙地写道: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东坡的旷达,决定了他所到之处皆风景,那真是“一路繁花”;但让他深感遗憾的是,鲜有与之“为乐”者,缺乏和他一起欣赏风景的人, 所谓“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由此也可窥见东坡的三点心思:一是要时时处处“为乐”,找乐子,保持心情的“欣然”;二是要有“闲”的松弛与情致,把心放缓,并舒展开来,“闲”看水穷云起;三是遇到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要懂得与人分享,身边最好能有“张怀民”一样的“闲人”共诉心曲。
世上“帮忙”的多,“帮闲”的少。“帮忙”追求的,是一个“利”字,“帮闲”追求的,是一个“趣”字。真正的闲人,如暮云春树,如花晨月夕,静静地散发着柔光,让周遭的一切安然,我们就这样被温情、良善和美好包围却不易察觉,那是多高的人生妙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