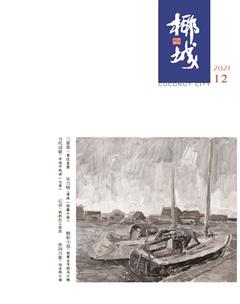远去的小海
作者简介:林兴民,籍贯海南万宁,1973年4月生。大学时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 《九州诗词》 《海南日报》 《海口日報》 等刊物发表作品多篇。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母亲逝世十五周年。——题记
老家村口紧依着一个内海,村里人祖祖辈辈都称之为“小海”,这个在村民眼中的小海,其实是中国最大的潟湖内海,面积约43平方公里,周长约43公里。小时候,站在老家祖屋门前的石桥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对岸密密麻麻的海防林。在离堤岸不远处,几块大石头露出海面,远远望去,可以看到海浪拍打石头激扬起洁白的浪花。
小海以盛产鱼虾出名,盛产的和乐蟹、港北对虾、后安鲻鱼声名远扬,尤其是和乐蟹,在海南四大名菜中,价格、品质和营养价值都是最好的。
记忆中,夏天的傍晚是小海最热闹的时候,这时候海里的鱼虾特别多,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这个短暂的捕虾季节带给了人们莫大的快乐。
盛夏的夜晚,月亮初上,柔和的月光洒在乡间的小路上。这时候,白天劳累了一天的人们也顾不上休息,纷纷带上竹篓披星戴月相邀下海捕虾。白天满海的虾都躲藏起来睡觉去了似的,到了夜晚纷纷成群涌向近岸来,却又都挣扎在淤泥中。竹篓是人们捕虾的唯一工具,因为太穷,村里人买不起鱼网,更甭说船。所以捕虾的过程艰苦而有意思,不管男女老少,大都只穿着一条短裤衩,泡在齐腰深的海水里,用自己的双脚在海底的淤泥中搅,那些钻在淤泥中的虾就会拼命逃窜,这时候捕虾人赶紧用脚板压住它们,再蹲下身子用手伸进去一抓,就会抓到一大把,迅速把抓到的虾往身后挂的竹篓里一扔,那些活蹦乱跳的虾就成了人们第二天的盘中美餐了。
男人们一边搅淤泥一边大声胡乱地喊歌,引得女人们大声地笑骂。有人因抓到特大的虾捏在手里狂喊,有人因到手的虾跑了而“大骂”,有人因为踩到螃蟹被咬得呱呱大叫。最开心的要数那些脱得光溜溜的小孩子们,他们在浅海处尽情地嬉戏打闹,月光之下平静的小海因他们而变得热闹而喧哗。
母亲的娘家就在小海对面,坐船走水路要几个小时,而走陆路至少要花上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而且那时候走陆路凭的就是双脚,要带行李又要带小孩那是很累的一件事。但是娘家总是要回的,走水路便成了母亲首要的选择。于是我六七岁之前常常随母亲坐船穿越小海到外婆家去,这在我脑海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村里能够到达对岸的大概只有属于公家的那艘简易的木帆船而已,由于装载货物太多的原因,坐在船舷上的屁股几乎要触到海水了,而在我眼里这已经是很大很大的船了。因为要考虑风向、海浪等问题,所以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开船的。母亲十分挂念外公外婆,加上父亲远在他乡工作,常年不在身边,对亲人的无尽的思念,纵有无边的海的阻隔,也丝毫阻挡不了母亲似箭的归心。
因为这些缘故,每次坐船到海对岸的外婆家,母亲都十分兴奋和紧张。早在几天前,就要开始计划,得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临近出发前的那天晚上,母亲是不敢睡的,因为船都是在凌晨四五点就要启航的,管船的人要出发了,就撕开喉咙喊母亲的名字,几声长长的“走——啰——”,听不见不及时登船就会误船。管船的是不会等的,因为一旦错过风向,船就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艰难靠岸。还有怕我饿着,得早早起来给我做点吃的,母亲因此不敢睡着,就在床前打个盹,守着我,听见喊声了,赶紧轻轻地拍着我说:“阿侬,醒来了,要走啦!”
天空还是一片灰蒙蒙,船出发了,我静静地躺在母亲的怀里,数着头顶的点点繁星,听着尖尖的船头撕破平静的海水发出哗哗的声音,跟着船轻轻地摇啊摇,偶尔回头看看渐行渐远的海岸。
船到小海中央的时候,天就蒙蒙亮了。这时候,就数我最高兴、最兴奋了。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总是爱趴在船舷边上,海水清辙透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底的水草一摆一摆的,有时候突然就有一群群小鱼从船舷边上穿梭而过。更多时候,可以看到很大的水母浮在水面上,我试图探身下去,用小手去捧那些水母上来玩,母亲赶忙劝阻我,说那些水母会把小手弄痒痒的。我不听。有时候那些船工就会用网兜从海上捞起一个水淋淋、软酥酥的大水母放在一个大铁盆里,任由我用木棍去摆弄。有时候会捞起几只大螃蟹扔在船仓里,任由我去挑逗它,要是不小心被螃蟹咬到了,母亲就会心疼地一边帮我抚摸,一边笑骂那个给我螃蟹玩的船工,然后一本正经地吓唬我说,以后不准玩螃蟹,那种青螃蟹咬到你了是死也不会松口的,除非天上雷公打雷了,它才会松口。也不知道母亲是从哪里得来这种莫明其妙的说法,但是也没有因此把我唬住,反倒在脑海里不停地想,要是真被那种青螃蟹咬到了,那雷公是怎么个打开它的口的,但是任由怎么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那年,与母亲一起从对岸嫁过来的兰姨,因为思乡心切,有一天找到一条小木板船,满心欢喜邀请母亲一起乘船回娘家。母亲反复打听船的安全状况,掌船的人信誓旦旦地说,绝对没有问题。于是母亲便带上我,一只小船,五六个人分坐船舷两边,我兴奋地躺在母亲的怀里,船在雾气蒙蒙中朝对岸出发了。一船的人有说有笑,谁也没有想到,船到小海中央,船底竟然渗水了,海水不断地涌进船仓里来,大人们拼命往漏洞里塞椰丝,可是不一会儿海水又把椰丝冲开,海水重新涌进来,母亲站在船仓里拼命往外舀水。眼看着仓里进水越来越多,母亲几近崩溃,丢掉水桶,一把把我搂在怀里,撩起衣角不停地擦拭我脸上的海水,我看见母亲紧咬着嘴唇,眼里噙满泪水。
好在最终堵住了船的漏洞,在惊心动魄中靠岸了。母亲牵着我的小手,全身湿透,一路跌跌撞撞到了外婆家,刚进家门,行李还没有放下,母亲已经泣不成声。外婆紧紧地搂着我,屋里寂静无声,只有母亲的抽泣,伴着外公无声的叹息。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坐船穿过小海。
而今,小海也伴随着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迎来了开发建设的大潮,环海公路修到了老家的门口,建起了雄伟的跨海大桥,半岛与对岸之间的往来也无需走水路了。
可惜母亲没有等来这一天,当年那些用船载着我们过海的船工也已经不在人世。那些灰蒙蒙的小海的印象,那些清晰可见的轻摇的水草,那些漂浮在水面状如降落伞的水母,在记忆中渐行渐远,但每每想起,总会唤醒心中无数的思念和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