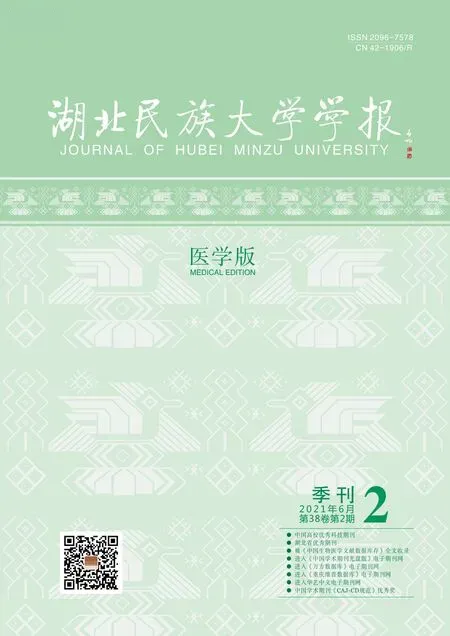基于古代防疫理论探讨中医药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治策略
米 婧,惠建荣*
1.陕西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陕西 西安 712046)
2.陕西省针药结合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2046)
于2019年12月起,武汉市出现数例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其病情发展迅速,且具有相似症状的患者在短时间内剧增,防控难度骤升。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大爆发,及时有效的防控措施成为了世界难题。研究表明[1]肺炎由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且目前无特效药。中国中医药专家组迅速出击,接管武汉部分重病区,实地开展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的诊治工作。截止2021年4月3日,全球累计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为130 704 318例,累计死亡2 845 539例。据国家及各地卫健委发布的疫情实时追踪数据显示,我国累计确诊患者为102 838例,累计死亡4 851例。本文鉴于古代防疫理论、中医药对疫病的深刻认识,及中医药防疫成功典例,以探讨中医药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治策略。
1 关于2019-nCoV感染的现代研究
1.1流行病学特点冠状病毒[1](coronaviruses)是一类主要引起呼吸道、肠道疾病的病原体,属于β属冠状病毒,有包膜、颗粒呈圆形或椭圆形,除了感染人类以外,还可以感染猪、牛、犬、猫、蝙蝠等多种哺乳动物以及多种鸟类。2019-nCoV的传染源主要是2019-nCoV感染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飞沫传播是其主要传播途径,亦可通过接触及气溶胶传播。人群普遍易感,老年人及有基础疾病者感染后病情较重,儿童及婴幼儿发病较少。临床表现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鼻塞、流涕、腹泻等上呼吸道症状少见。重症病例多在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道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1]。
1.2疑似及确诊病例的诊断标准疑似病例的诊断标准[1]需综合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来具体分析,其中流行病学史主要为:①发病前14 d内有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旅行史或者居住史;②发病前14 d内曾接触过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③有聚集性发病或与2019-nCoV感染者有流行病学关联。临床表现为:①发热;②具有以下肺炎影像学特征:早期呈现多发小斑片影及间质性改变,以肺外带明显;进而发展为双肺多发磨玻璃、浸润影,严重者可出现肺实变;胸腔积液少见;③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有流行病学史的任何一条,符合临床表现中任意2条,均可诊断为疑似病例。确诊病例的诊断在符合疑似病例标准的基础上,呼吸道或血液标本行实时荧光RT-PCR检测2019-nCoV核酸阳性;或病毒基因测序,与已知的2019-nCoV高度同源。
2 中医防疫概要
2.1历史背景关于“疫”字,最早可以在先秦的记载中看到。《礼记·月令》记载:“则其民大疫”“民殃于疫”“民必疾疫,又随以丧”。[2]《周礼·夏官》载有“以索室欧疫,大丧。”[3]由此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疫病的灾难性,但没有明确对疫的定义。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提到“疫,民皆疾也。”《素问·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症状相似”。[4]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5]明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说:“疫者,以其延阖户,如徭役之疫,众人均等之谓也。”[6]综合上述,古代疫病类似于现代的传染病,都具有起病急、传变快、病情凶险,且具有较强的传染性,易引起大规模流行的特点。“疫病”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甚至摧残生命的一类疾病,也是造成古代人民健康水平低,高死亡率的原因之一。中国古代医家和人民在同疫病斗争的数千年间,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对疫情的病因病机、发病规律和预防措施、治疗方法方面,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和优势的中医疫病学体系。
2.2主要思想
2.2.1 顺应自然,整体防疫 整体防疫思想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体各局部内部、人体身心四大整体的和谐共处。人应顺应四时变化,遵守自然演变规律,《素问·百病始生篇》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能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贼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即当人体自身防预能力下降或气候反常时,机体难以适应,抗病能力下降或人不顺应四时,致使发病。那些素体虚弱且不避虚邪贼风之人更易患病。部分医家继承了内经中“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和于阴阳,调于四时”的思想,有了“冬夏衣被过暖,皆能致病,而夏月为尤甚……亦勿过于贪凉,迎风沐浴,夜深露坐,雨至开窗,皆自弃其险而招霍乱之来也,不可不戒”的论述。[4]保养正气的关键则为顺应自然,一年四季,有其自己的气候演变规律: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因此,人们理应避风寒,适当饮食,勿在暑天贪凉喜冷,更不要在寒冬之时,过于滋补,渐助病气生长。此外,在顾护正气同时要修身养性,遇事平和,人的机体与精神互相依存,互相滋生,只有养神护精,乐观平善,清心宁神才能使全身气血通调,脉络畅通,颐养天年。
2.2.2 调养先天,扶正固本 中医学将肾称之为“先天之本”,肾藏精,构成维持生命的物质基础。《景岳全书》卷十三《瘟疫论》中提到:“温疫乃天地之邪气,若人身正气内固,则邪不可干,自不相染。”肾精充足,正气存内,使阴阳相互滋生,化生无穷,则邪气不可入内,无生病痛。张仲景提出“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的观点[7],这便是“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先见之明。自此未病先防的思想得到广泛流传,也有适服药饵,扶正补虚的保健之法。扶正固本类中药根据现代药理研究有着调节免疫系统、抑菌、抗肿瘤等作用。如黄芪能升高白细胞,有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及抗肿瘤功效[8]。党参有抑菌、抗炎、抗瘤之效。助阳类药物,如肉苁蓉、仙灵脾能增强人体免疫功能,促进T、B淋巴细胞的增殖,诱生干扰素,以抑菌、抗病毒[8]。养血类中药,如何首乌、桑葚、白芍都具有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及抑菌功效。此外,滋阴类中药天门冬、麦门冬有增强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抑菌、抗疱疹病毒及抗肿瘤的效果[8]。现今研究证实[8],大多数清热解毒类药物均具有抗菌抗病毒的作用。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9]说明适当运动可以促进食物消化,同时也利于各个脏腑功能发挥,还可以通畅气血,从而起到顾护正气,提高抗御病邪的能力。
2.3有效措施
2.3.1 隔离辟邪,卫生避疫 疾病的发生是机体“正”“邪”斗争的结果,当邪气疫毒强盛,超过人体御邪能力,即会致病。在中医药发展史上,早有将传染病患者隔离的记载,如《肘后方》中提到:“赵瞿病癞,历年医不差,家人乃斋粮弃送于山穴中。”[10]《保生要录》中记载:“土厚水深,居之不疾。”[11]这便是说环境的清洁、水渠不污畅通,空气保持清新的重要性。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是预防传染、切断传染源的重要措施之一,勤换洗衣物、不随意吐痰唾液、保持手卫生等,在古书上早有写录。不好的饮食习惯也将造成各类疾病的发生,不贪生冷辛辣刺激,不嗜烟酒,不暴饮暴食,注意食物卫生,均是个人防护的重要举措。
此外,消毒杀虫也为避其毒气的一种方法。从古至今,这种经验屡屡凑效,如熏蒸消毒、蒸煮消毒、涂擦消毒、驱虫灭害等经典防疫措施均是消毒杀虫的具体体现,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天行温疫,取出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12]《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皆有涂擦式消毒防疫的记载,如雄黄散碾成细粉,水调涂五心、额上、鼻人中及耳门等处,因雄黄、丹砂含汞、砷等成分有强烈杀菌、抑菌作用。古人对鼠害、蚊蝇皆可传播疫病早有认识,此后,消灭虫害也为防疫辟邪的重要手段。如明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载:“昔人谓暑时有五大害,乃蝇、蚊、虱、蚤、臭虫也。”[13]还提出用百部、藜芦、雄黄、柏子等药物来驱蝇灭蝇及将艾草、苍术、菖蒲等药物单独或混合燃烧以熏蚊除虫。佩挂药物亦是中医药防病避疫的独特之处所在。佩挂药物法是指将具有挥发性的一些中药制剂佩挂于身边,利用其可持续释放药物气味的特点,来防疫辟邪的一种独特方法。《太平圣惠方》中早有“治时气瘴疫,辟除毒气”“以皂囊盛一丸,系肘后”[14]的记载。
2.3.2 针灸防疫,保养正气 针灸防疫思想早就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所体现,首见于《内经》,《灵枢·刺法论》中根据五运六气的异常变化特点,制定了针对五种可能出现的疫病的“刺疫五法”[15],认为针刺有理气疏郁、扶弱抑强,除湿化饮,补虚泻实的独特作用,因此,机体气血运行无滞,经络脉道通畅无瘀,虚者有补,实而有泄,故正气充足,邪气难侵。灸法即运用一些药草燃烧所产生的温热之性同时配合药草本身特性,在体表局部或特定穴位上产生温通经脉、助阳补气、扶正祛邪等作用,以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用艾灸来预防疟疾传染,这是首例采用艾灸来预防疟疾传染的医案。《外台秘要》中记载:“天行病,若大困,患人舌燥如锯,极渴不能服药者,宜服干粪汤”,同时配合灸巨阙穴“三十壮”。[16]这便是灸法配合汤药治疗疫病的明确论述。
2.3.3 药食同补,固脾胃气 金元时期的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学说,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是正气生化之源,正气足,则邪气不易成疾。服用保健药食以预防疫病,养护正气的方法亦是流传于世。但民间还有“药补不如食补”的说法。脾胃乃后天之本,自然要养护得当,切勿随意、盲目服用药物。机体气血充足,畅通无滞,阴平阳秘,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气血为生命的根本,气血不足,则机体各脏腑功能下降,可适服补气养血类药物以补益气血。阴阳为人体之根,助阳滋阴有助于机体恢复,阴阳平衡,如《内经》所载:“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道理。食物性味甘平可口,既可以缓解药味苦涩,又有养护脾胃,勿使药物伤脾胃之效。
3 中医药防疫成功典例
3.1中医药在防治非典型性肺炎中发挥的作用根据非典型性肺炎的发病特征及传播规律,中医认为此病属“温病”范畴,古人称“温疫”“戾气”,其传染性强,普遍易感。疫戾之气从口鼻而入,直侵犯肺,故出现干咳、呼吸困难、气促胸闷等症,同时,疫戾之气外犯加之机体抵抗力减弱,使其发病过程迅速,进展较快,危及生命。中医认为在科学预防非典的同时,维护正气,增强机体抵抗力为关键。首先要调摄情志,稳定心态,不恐慌,保持充足睡眠,合理膳食,适当锻炼;第二,进行空气消毒;其三、提高机体抗病能力,预防用药,三因制宜。于2003年中医药管理局及中医药专家还拟定了一些预防处方[17],如:蒲公英15 g,金莲花12 g,大青叶10 g,葛根10 g,苏叶6 g,主要功能为清热解毒,散风透邪,主要适用于内热偏盛,易感风热者。
3.2中医药在防治甲型H1N1流感中发挥的作用甲型H1N1流感主要通过近距离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人群普遍易感,属于中医“温疫”范畴。外感时邪疫毒,患者病初多表现为发热、咳嗽、食欲不振,腹泻等症,故可推断此病可能先有伏邪,如素体阴虚,邪伏于肺,合于外邪以发病。中医药对于预防甲型H1N1流感主要预防措施如:规律生活起居,饮食有节,适当药物预防,外部环境可进行熏蒸或烟熏消毒。
4 中医药防治2019-nCoV感染的初步探究
根据以上典例,本次中医药防2019-nCoV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可基于中国古代防疫思想探讨出中医药防治2019-nCoV的新思路。2019-nCoV传染性较强,属中医“疫病”“温疫”范畴,从其病发生季节及爆发地区推测,该病机以湿邪为核心,病位在肺,脾胃盛衰为病情转化的关键,脾胃功能的好转与衰败往往能反映一个疾病的预后。
2019-nCoV辨证论治整体上可以概括为两期十二证[18],即急性期和恢复期;急性期又可根据卫气营血理论及《伤寒论》分为邪在肺卫、邪初入气分、湿热内蕴、湿毒闭肺、湿毒逆陷心包、阳明腑实、寒湿疫毒直中太阴、手足太阴同病、湿热内陷胃肠及内闭外脱10大证型。恢复期又分为肺脾气虚证和脾肺阴虚证。同时更要重视情志调摄和饮食起居。如急性期之湿毒闭肺证,常见高热无汗、气喘胸闷、口渴尿黄等症,在这种重症情况下,西医治疗基础上配合中医药可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并缩短病程,促进恢复,中医治疗应以宣肺解毒除湿为主,常用方药以麻杏石甘汤加减。总体来看,中医的及早介入,有利于对疾病整体趋势的掌握,发展方向的严格监控,促使疾病转折点的提早到来,预后良好、缩短病程。
5 结语
中国古代防疫思想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堪称医学经典,其独特的防疫思想为现代医学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各类名方效验、中医药防疫成功典例更是为医学的发展夯实了基础。中医药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中表现出的突出优势,正是基于古代防疫理论的深厚底蕴和时代使命,使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期待后辈们能从中医药发展历程中寻求到更多的符合现代医学发展水平的新思路,新技术,新观点,更期待中医药在未病先防、轻证早治,重病急控,促进恢复及中西医结合全面诊治方面取得更大突破。但目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疗过程中,还未研制出特效药,中医药的介入时机和其独特作用有待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