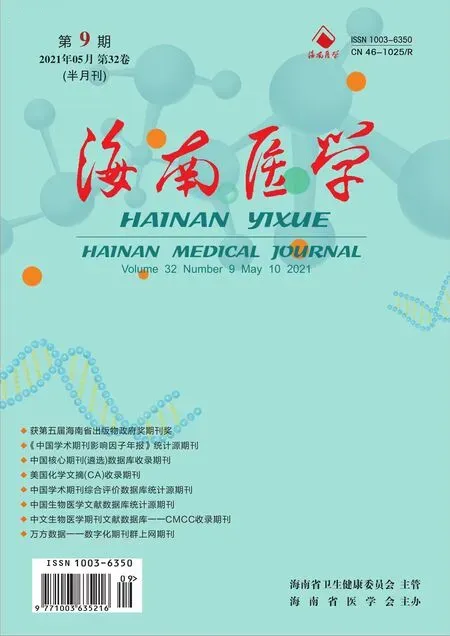寻常型银屑病的免疫学机制与中医药调控
余杨,张喜军,盛平卫,诸婧
上海市金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外一科,上海 201501
银屑病是一种在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作用下发生的与免疫有关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疾病。据统计,世界范围内银屑病患病率为0.09%~11.43%[1]。银屑病根据临床表现可分为4 型,且以寻常型占绝对多数。寻常型银屑病典型的组织病理学特征包括表皮角化不全伴角化过度、炎症细胞浸润和血管扩张[2]。目前,关于寻常型银屑病的发病机制,学界广泛认为是多种免疫细胞、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共同参与的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T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3]。本文重点综述寻常型银屑病免疫学机制中较为关键的免疫细胞和细胞因子的作用,并总结近年来中医药治疗寻常型银屑病免疫学调控机制的研究进展。
1 寻常型银屑病免疫学机制
1.1 概述 20 世纪70 年代前后,寻常型银屑病被认为是角质形成细胞(keratinocyte,KC)功能失调所致,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揭示KC 的增殖机制。到20世纪80年代,T淋巴细胞抑制剂——环孢素被发现可显著改善银屑病后,学界开始认识到活化的T 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可能是银屑病的核心机制。随着大量的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等研究的开展,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寻常型银屑病的发病机制主要是:在多基因遗传背景下,KC受到诱发因素刺激后,释放自身RNA或DNA、抗菌肽及一系列细胞因子,促使未成熟的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活化;活化的DC在将抗原呈递给初始T 淋巴细胞的同时分泌细胞因子,促使初始T 淋巴细胞分化为辅助性T 淋巴细胞(helper T lymphocyte,Th) 1、Th17、Th22;后者分泌的细胞因子不仅具有炎症效应,还反过来促使KC 异常增殖分化并分泌更多的细胞因子、抗菌肽等。以上过程形成了正反馈强化回路,最终导致银屑病皮损形成,并不断恶化,经久难愈。
1.2 KC KC 异常增殖分化是寻常型银屑病的特征性病理学改变,此外,KC 还通过分泌抗菌肽、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等与其他免疫细胞相互作用参与寻常型银屑病的炎症过程。在寻常型银屑病启动阶段,KC 受到刺激发生凋亡,释放包括自身DNA、RNA 在内的细胞内容物,同时分泌LL37、S100A7、S100A8、S100A9、β-防御素等抗菌肽聚集在皮损处,参与炎症反应[4]。其中,LL37 与DNA、RNA 结合形成的复合物DNA-LL37、RNA-LL37[5]激活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pDC),后者分泌干扰素(interferon,IFN)-α激活髓样树突状细胞(myeloid dendritic cell,mDC),mDC 在细胞因子的作用下,诱导初始T淋巴细胞分化为Th1、Th17、Th22,从而引发寻常型银屑病的核心细胞免疫机制。除了IFN-α,KC分泌的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IL-6、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也参与了mDC 的激活[6]。LL37还能反过来促使KC分泌IL-36γ、IL-1α,继续刺激自身增殖[7]。KC还分泌趋化因子(C-C基序)配体[chemokine(C-C motif)ligand,CCL]17、CCL20、CCL27、趋化因子(C-X-C 基序)配体[chemokine (C-X-C motif) ligand,CXCL] 9、CXCL10、CXCL11 使Th1、Th17、Th22移行到银屑病皮损中,分泌CXCL1、CXCL3、CXCL5、CXCL8募集中性粒细胞进入皮损中[6]。其他免疫细胞能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刺激KC 持续发挥效应,如活化的T淋巴细胞分泌的IL-17能诱导KC合成β-防御素、S100A7、IL-8、CXCL1 等;IL-22 能促进KC 增殖[8-9]。KC与其他免疫细胞之间的这种正反馈回路不断放大免疫效应,这可能是导致寻常型银屑病病情持续的原因之一。此外,KC还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和血管生成素(angiopoietin,Ang)在寻常型银屑病血管增生进程中发挥作用[6]。
1.3 DC DC是白细胞的异源细胞,因其具有强大的抗原递呈功能而成为人体最重要的抗原递呈细胞。DC 在寻常型银屑病中参与T 淋巴细胞的分化与慢性炎症反应。皮肤中的DC 包括朗格汉斯细胞(langerhans cell,LC)、pDC和mDC。
1.3.1 LC 目前关于LC在寻常型银屑病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不尽一致。有研究提示LC 可能对银屑病皮损的形成无影响:小鼠皮肤中如果缺乏IL-34,LC 数量就会明显减少;而利用IL-34 缺陷小鼠仍然可以构建银屑病样模型,并且其表型与野生型小鼠无显著性差异[10]。这与RIOL-BLANCO等[11]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而有研究表明LC可诱发寻常型银屑病的炎症反应:LEE等[12]利用咪喹莫特诱导敲除LC的人源Langerin-白喉毒素亚基A 小鼠构建银屑病样模型后,发现模型皮损显著减轻,IL-17A、IL-22、IL-23等细胞因子的表达也下降。还有研究发现LC在寻常型银屑病中起抑制作用:在银屑病样小鼠模型中,LC表面的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 (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表达增加,同时分泌更多的IL-10,而PD-L1和IL-10在银屑病中均抑制炎症反应;并且去除LC后,银屑病的病情加重[13]。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课题组所使用的模型不同有关,也可能与LC 的双向调控作用有关。LC 在银屑病中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1.3.2 pDC pDC 通过分泌IFN-α来参与寻常型银屑病的启动。在银屑病病变早期,成纤维细胞表达大量的趋化因子,募集pDC迁移到真皮中[14]。如前所述,KC 释放自身DNA 或RNA 与抗菌肽LL37 结合形成复合物DNA-LL37、RNA-LL37,后两者被pDC 内吞,分别通过Toll 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 9、TLR7依赖的信号通路刺激IFN-α的释放[15]。IFN-α可使mDC 活化并分泌IL-12、IL-23 等细胞因子,继而诱导Th亚群分化,引发一系列T淋巴细胞诱导的免疫反应,导致银屑病斑块形成。在正常情况下,pDC 并不会对坏死细胞释放的DNA 或RNA 产生反应,但后两者与LL37 结合后便可使pDC 活化,引起IFN-α释放,从而破坏了机体的稳定状态[5]。因此,上述机制被认为可能是银屑病的始发点。
1.3.3 mDC 活化的mDC向初始T淋巴细胞呈递抗原,同时分泌各种细胞因子,如IL-12、IL-23等,诱导初始T淋巴细胞分化增殖,最终引发银屑病皮损形成。在小鼠中,mDC 分为CD11b+mDC 和CD103+mDC,分别与人类的CD1c+mDC和CD141+DC相对应[16]。在银屑病中,CD11b+mDC被活化后倾向于分泌IL-23,后者在Th17 的分化增殖中起重要作用,Th17 分泌IL-17、IL-22 等细胞因子促进银屑病炎症进展[17];活化的CD103+mDC则是IL-12的主要来源[18],IL-12通过促进Th1分化和分泌IFN-γ、TNF-α等在寻常型银屑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效应[19]。银屑病皮损处的真皮层中,有一组高表达TNF 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成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的mDC (TNF and iNOS-producing DC,TipDC)[20],这些细胞不仅分泌炎症因子TNF、IL-6 等,维持银屑病的炎症反应[21];还释放iNOS产生NO,诱导血管扩张、加重炎症反应。
1.4 T 淋巴细胞 目前,研究发现在寻常型银屑病中起关键作用的T淋巴细胞主要是Th1、Th17、Th22和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22]。
1.4.1 Th 初始T 淋巴细胞在IFN-γ、IL-12 的作用下向Th1 分化,后者释放IFN-γ、TNF-α等细胞因子不仅参与局部炎症反应,还作用于KC,使其进一步分泌趋化因子,向皮损处持续募集炎症细胞[23]。而Th2的分化与IL-4 有关,Th2 分泌IL-5、IL-6、IL-10 等细胞因子促进B淋巴细胞增殖分化,生成IgE和IgG发挥抗炎效应[24]。在正常情况下,机体Th1/Th2 保持着动态平衡,而在银屑病患者中,Th1是显著增加的[23],Th2及相关因子是呈低表达的[25],将免疫环境从Th1 为主向Th2推移时,银屑病炎症反应会减轻,皮肤症状能够得到改善[26-27]。这种Th1/Th2的平衡失调被称为“辅助性T细胞亚群偏移”,是较早时期的关于银屑病发病机制的观点。在银屑病皮损中,Th17 的分化由IL-6、IL-23、转 化 生 长 因 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等共同参与[28-29],IL-23还能促进分化后的Th17增殖及大量分泌炎症因子[30-32],加重银屑病炎症反应。近年来逐渐认为,相较于经典的Th1/Th2 细胞途径,IL-23/Th17 轴对银屑病发生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关键[33]。Th17 分泌IL-17、IL-22、TNF 等诱导KC 分泌更多的炎症因子、趋化因子。IL-17诱导KC合成抗菌肽如β-防御素、S100A7 等[34],促进KC 分泌IL-8、CXCL1等趋化因子向皮损处募集中性粒细胞。IL-17 与TNF可协同作用,提高KC对CCL20的表达,从而募集分泌IL-23 的mDC,进一步诱导初始T 淋巴细胞向Th17 分化[35]。Th22 的主要效应细胞因子IL-22 则直接干预KC 的分化,诱导KC 增殖[8]。可见,在寻常型银屑病中,虽然IL-17 和IL-22 均对KC 产生效应,但IL-17 主要参与炎症效应,而IL-22则主要促进表皮增殖。
1.4.2 Treg Treg是一组发挥免疫抑制作用的细胞群[36],与Th17 同源于CD4+T 淋巴细胞,Th17 具有致炎作用,而Treg 则通过直接诱导细胞凋亡、释放细胞因子抑制免疫应答来发挥效应。现有研究表明银屑病患者皮损与外周血中均存在Treg 功能受限现象[37]。并且,在IL-6 和TGF-β的作用下,患者来源的Treg 趋向于分化为Th17[38],当体内Treg 与Th17 比例失调——向Th17倾斜时,银屑病皮损更加严重[39]。
1.4.3 固有类T 淋巴细胞 固有类T 淋巴细胞包括自然杀伤T 细胞(natural killer T cell,NKT)、γδ T 细胞,这些细胞通过分泌炎症因子和趋化因子参与寻常型银屑病的发病。在小鼠模型中[40],活化后的NKT通过分泌IL-17、IL-22,增大Th17和Th22的效应;同时,还表达趋化因子(C-X-C 基序)受体[chemokine(C-X-C motif) receptor,CXCR] 3、趋化因子(C-C 基序)受体[chemokine(C-C motif)receptor,CXCR]5 和CCR6 等,促使自身向皮损处的聚集。与Th17细胞一样,γδ T细胞也表达IL-23R、CCR6,使其自身能在IL-23 的刺激下释放IL-17,故γδ T细胞可能是IL-17的来源之一[41]。
1.5 中性粒细胞 尽管表皮Munro 微脓肿的形成表明中性粒细胞与寻常型银屑病有特异性联系,但中性粒细胞并不是皮损的必备特征,故学界认为它们不是寻常型银屑病发病的主导原因。现有研究表明,中性粒细胞通过分泌细胞因子、抗菌肽,脱颗粒,释放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NET)在寻常型银屑病的进程中发挥作用。中性粒细胞移入角质层后,分泌IL-1α、IL-6、IL-12、IL-23、TNF-α、IFN-γ、CXCL8、α-防御素等细胞因子及抗菌肽[42];中性粒细胞活化后脱颗粒,分泌组织弹性蛋白酶、组织蛋白酶G活化IL-36家族细胞因子[43],以上过程均进一步促进了寻常型银屑病的炎症过程。NET 是一种新发现的细胞死亡程序,在中性粒细胞死亡后能继续发挥免疫效应。NET 参与寻常型银屑病启动和进展的途径包括:释放IL-17A[44],激活pDC,继而引发T 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45-46],最终导致银屑病斑块形成。
1.6 巨噬细胞 巨噬细胞分泌各种细胞因子影响KC增殖分化、参与新生血管形成、诱导和加重炎症反应,从而参与寻常型银屑病的发生发展。在银屑病样小鼠模型中,巨噬细胞分泌IL-12、IL-23、TNF、iNOS,发挥Th17细胞样效应[47];分泌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 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ion factor,MIF)、IL-20 等诱导KC 过度增殖[48-49];分泌前动力蛋白(prokineticin,PK)2、TNF-α、TGF-β、VEGF 等来调节皮损中血管生成[50-51]。其中,PK2不仅能促进血管生成,还能诱导KC 和巨噬细胞自身分泌IL-1,后者能进一步促进其他细胞因子释放,其中包括PK2。这种正反馈回路在寻常型银屑病中普遍存在,其在维持和促进银屑病皮损中的炎症反应、KC 异常增殖分化以及血管增生中具有重要作用[52]。除此之外,巨噬细胞还分泌趋化因子CCL19 募集表达趋化因子CCR7 的Th 细胞和DC到血管周围发挥效应[6]。
2 寻常型银屑病的中医药调控
寻常型银屑病,中医学无此病名,但古代文献中对“白疕”、“松皮癣”、“干癣”等的描述与之相似。在病因病机上,多认为其由外感邪气,内伤血燥所致。如巢元方认为本病“皆是风湿邪气,客于腠理,复值寒湿,与血气相搏所生”。《医宗金鉴》提出“白疕”、“固有风邪客肌肤,亦有血燥难外荣”。《外科大成》云:“白庀……俗呼蛇虱。由风邪客于皮肤,血燥不能荣养所致”。现代医家多认为其发病与血分密切相关,由血分热盛,灼血致虚成瘀,化燥生风,肌肤失养而成[3]。治疗上,现代医家多“辨血为主,从血论治”,以血热证、血燥证和血瘀证为基础证型,选用多种治疗方法,如清热凉血、活血、养血中药组方内服、外涂、熏蒸、湿敷,或结合火针、走罐等方式[53]。目前关于中医药的作用机制,主要涉及对KC、DC、T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的调节,以及对VEGF的抑制等。
2.1 对KC 的调控 中药提取物可通过调节KC的增殖分化来发挥作用。牛蒡子苷元能够通过激活5'磷酸腺苷依赖的蛋白激酶,下调角蛋白17 的表达,来抑制KC 的增殖,促进KC 的凋亡,最终缓解银屑病样小鼠模型皮损的发展[54]。外涂芍药苷能够抑制银屑病样小鼠模型KC异常增殖,从而发挥治疗作用[55]。
2.2 对DC的调控 中医药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抑制DC的活化及其产生细胞因子的能力来发挥作用。体外实验发现,银屑病样小鼠模型给予丹皮酚灌胃后,骨髓来源的DC 表达的IL-23 mRNA 水平降低,提示丹皮酚可能通过下调IL-23 mRNA 表达来抑制DC 的功能而发挥治疗作用[56]。凉血解毒方(土茯苓、生槐花、紫草、赤芍、白茅根、生地黄、苦参、金银花、草河车、白鲜皮)不仅可以减少银屑病样小鼠模型皮损中IL-23、IL-12p40、TLR7 的数量,还能降低DC 细胞上清液中IL-23、IL-1β水平和细胞表面IL-23、IL-1β、IL-12p40 mRNA的表达[57]。
2.3 对T淋巴细胞的调控
2.3.1 Th1 和Th2 中医药可通过减少Th1 及其细胞因子、增加Th2 及其细胞因子的表达,调节Th1/Th2 平衡来发挥作用。如泡服消银解毒免煎颗粒(生地黄、赤芍、牡丹皮、玄参、大青叶、金银花、苦参、蝉蜕、牛蒡子、防风、红花、当归、白鲜皮等)可使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患者外周血Th1水平降低、Th2水平增加,将Th1/Th2失衡环境向Th2推移[58]。在土槐饮煎服、湿毒软膏外涂基础上联合清开灵注射液静脉滴注,可降低银屑病血热证患者血清Th1 型细胞因子TNF-α、IFN-γ水平[59]。温阳和营,凉血化瘀中药(黄芪、桂枝、白芍、麻黄、生石膏、丹参、生槐花、生地黄、牡丹皮、连翘、白花蛇舌草、土茯苓、生姜、大枣、甘草)煎服联合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静脉滴注,可下调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清TNF-α水平[60]。在阿维A胶囊口服基础上加用背俞穴针刺联合香丹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血热型寻常型银屑病,可降低患者血清Th1 型细胞因子IL-2、TNF-α和IFN-γ水平,上调血清Th2型细胞因子IL-4、IL-10水平[61]。
2.3.2 Th17 中医药通过抑制寻常型银屑病患者外周血Th17 型细胞因子的表达发挥作用。口服芩珠凉血方(珍珠母、灵磁石、丹参、紫草、黄芩等)治疗寻常型银屑病之血热证,可下调患者血清IL-17、IL-23 的表达[62]。凉血活血类中药(羚羊角粉、紫草、白茅根、赤芍、茜草、板蓝根等)可有效抑制咪喹莫特诱导的银屑病样小鼠的皮损增厚,其可能的机制是下调IL-23/IL-17轴相关细胞因子蛋白和微小RNA(microRNA,mRNA)及维甲酸相关孤儿受体(retinoic acid-related orphan receptor,ROR)γt mRNA的表达[63]。
2.3.3 Th22 中医药可下调寻常型银屑病患者外周血IL-22水平发挥治疗作用。白芍总苷口服联合窄谱中波紫外线(narrowband ultraviolet B,NB-UVB)全身照射能明显减少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清Th17、Th23数量,降低血清IL-17A、IL-22水平[64]。中药汤剂退银汤(生地黄、土茯苓、当归、女贞子、何首乌、黄精、麦冬、白蒺藜、乌梢蛇、蜈蚣、金银花、丹皮、桃仁、红花、甘草)煎服联合NB-UVB皮损局部照射治疗后,中/重度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清IL-22水平下降[65]。
2.4 对中性粒细胞的调控 中医药可抑制中性粒细胞分泌细胞因子而发挥抑制KC 增殖和抗炎作用。体外实验中,中药银屑1号(土茯苓、白花蛇舌草、板蓝根、半边莲、蜂房、川芎、车前草、泽泻、白鲜皮、地肤子、牡丹皮、生地黄、大青叶、生大黄、甘草)含药血清可下调寻常型银屑病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TNF-α、IFN-γ的表达,从而抑制KC的增殖及相关炎症反应[66-67]。
2.5 对血管增生的调控 中医药可通过下调血管增生相关因子水平发挥抗血管增生作用。NB-UVB照射联合中药蒸汽疗法(中药熏蒸方:蛇床子、土茯苓、败酱草、金银花、连翘、炒槐米、虎杖、艾叶、侧柏叶)治疗后,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清VEGF 水平降低[68]。八宝五胆药墨联合依匹斯汀口服治疗后,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清VEGF、bFGF水平均降低[69]。
3 结语
目前,对寻常型银屑病的治疗,国内外均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西医学方面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单个免疫细胞或细胞因子为靶点的生物制剂上,但往往伴随价格昂贵、使用不方便、诱发感染等不足。在辨证论治、整体观念的核心思想指导下,中医药治疗银屑病已表现出了多途径、多靶点的作用特点。但由于中医和西医存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诸方面的差异,现阶段中医药对寻常型银屑病调控机制的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如在基础实验研究中,仅在重复阐释西医学治疗机制的基础上,证实中医药治疗的疗效,对临床研究无建设性指导作用,临床转化价值不高;临床研究多为小样本、单中心研究或经验总结,所选观察指标大多相似而单一;干预措施主要为中药内服,而对中医外治法及特色疗法作用机制的研究相对匮乏,且本身理论依据尚不清楚;等等。近年来,中医证候学、生物分子网络学等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相信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步与运用,中医药作用机制将会被逐渐揭示,并为应用中医药治疗寻常型银屑病提供可靠的理论和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