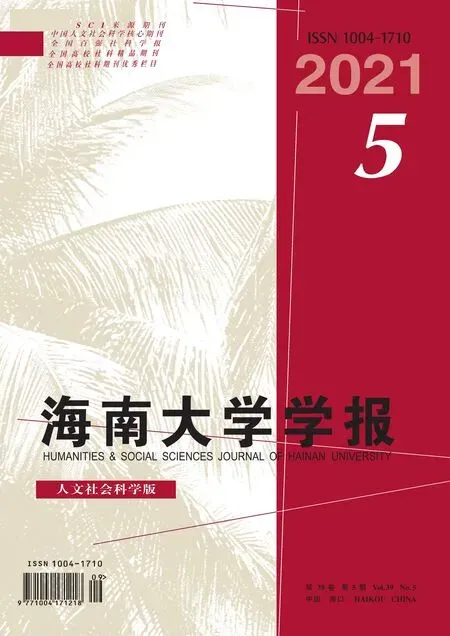廊下派如何缔造“世界主义”?
徐 健
(1.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2.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300387)
在人类历史上,世界主义堪称一股强劲的思潮。据说它早在荷马史诗中就已露端倪,但真正说来,源头应追至古希腊晚期—罗马时代。由于泛希腊世界的马其顿的崛起,破碎的泛希腊城邦政治状态逐渐结束,最终,亚历山大开创了西方史上第一个帝国。这个帝国横跨欧亚非,覆盖诸多种族和文化,可谓普世帝国。与此同时,一股世界主义思潮开始凝聚成形并逐渐席卷天下。然而随着亚历山大的突然早逝,希腊帝国旋即由于尚未形成中央集权建制而陷入“三国志”式的混战局面。两百年后,泛希腊世界之外的罗马在希腊语作家的“天下想象”的推动下①刘小枫:《亚历山大与西方古代的“大一统”》,《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14页。,接续亚历山大的未竟事业,打造了一个制度设计较完备从而跨时久远的天下帝国。帝国更替为世界主义的传播和推进提供了极有利的政治条件,因为此时,兼容并蓄的罗马帝国似乎就是世界主义理想的现实版本。
无论亚历山大是否怀有一种自觉的世界主义观念,他所仰慕并拜访过的大犬儒第欧根尼确实是最早持有这种观念的人。也正是因为与犬儒的师承关系,廊下派才能系统构建出一种世界主义理论。学界对廊下派世界主义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是宇宙城邦(cosmos-city)研究,主要针对罗马廊下派;二是圣贤城邦(city of sages)研究,指向廊下派创始人芝诺的《政制》(Politeia)。这容易让人以为廊下派持有两种世界主义立场,但本文将证明,相继提出的圣贤城邦和宇宙城邦尽管有所区别,但在城邦治理以及圣贤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上却共享同一套原则,并且都是对世界所作的不可实现的真实描述。为此,本文将首先讨论作为廊下派世界主义之共同源泉的犬儒世界主义。
一、超越犬儒派的世界主义:从“消极型”到“积极型”
约公元前312 年,亚历山大驾崩后的第十一年,刚二十岁出头的芝诺为贩售紫袍,从小亚细亚的腓尼基渡海前往当时作为西洋文明中心的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尽管这票生意终因货船失事而告吹,但芝诺并未因此抱怨命运,反而在抵达雅典后在一家书店中歇息。大概是因为自幼痴迷圣贤苏格拉底的缘故,他捧阅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并在读到第二卷时迫不及待地寻觅书中所描述的那种人。此时克拉特斯(Crates)刚好路过,经书商指引,芝诺就欣然舍弃家业而跟着这位犬儒学哲学。考虑到克拉特斯的非正式业师乃第欧根尼,而第欧根尼又师从苏格拉底的犬儒门生安提司忒涅斯(Antisthenes),我们就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师承谱系:苏格拉底——安提司忒涅斯——第欧根尼——克拉特斯——芝诺。那么,芝诺从犬儒处学到了什么本领呢?
据拉尔修记载,有人曾问第欧根尼打哪来,他说“我是世界公民(kosmopolitēs)”。由此或可推测,“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cosmos/world)或“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的概念源于第欧根尼。此人还以肃剧的形式这样描述自己:“无国则无城(apolis)、无家,日复一日似一个乞丐、一个流浪汉那样过活。”①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270,281 页;本文引用时酌情改动译文(依据D.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trans.R.Hick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如果将这两段文本合起来看就能发现,apolis 并非如少数学者认为的那样与kosmopolitēs 相对,从而反映出第欧根尼所谓的“世界公民”具有积极的内涵②M.L.Moles,“Cynic Cosmopolitanism”,in R.B.Branham,Marie-Odile Goulet-Cazé eds.,“The Cynic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p.105-120.;相反,它是“否定性的”,即“反礼法的”(antinomian)。据说,第欧根尼也写过以《政制》为名的著作,并且可能在其中最集中地嘲讽了城邦(polis)生活:
万物属于诸神;诸神是智者的朋友;朋友之间有物共享。所以万物属于智者。关于法律,他主张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政治体制,因为他说:没有城邦,文雅就没有用处;城邦是文雅的,并且,没有城邦,法律就没有用处;所以法律是文雅的。他会嘲笑高贵的出身、声望等所有这类东西,说它们是用来掩饰邪恶的东西。他说,唯一正确的政制是宇宙的政制。他还主张女人应当共有,认为婚姻只是那进行说服的男人和被说服的女人共同生活;因此儿子也应当是共有的。
在他看来,从神庙里偷东西或吃任何动物的肉都不是荒诞不经的事,甚至尝尝人肉也不是不圣洁的事,这从一些外邦习俗中显示得很清楚。……他轻视音乐、几何学、天象学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既无用处也无必要。③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第285-286 页。
其中关于法律和政制的观点似乎不符合我们对第欧根尼世界主义所作的判断。按文本中的说法,第欧根尼像是非常关心法治和(最佳)政制的问题。不过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拉尔修的这篇文字和他对芝诺《政制》的记述之间高度相合;那么很有可能的是,这篇文字在某些方面具有廊下派的痕迹。据考证,在关于法律的三段论中,第欧根尼原是为了驳斥某些思想对手,他们反感城邦及其礼仪,并主张法治是不可或缺的;而关于政制的说辞无非是对kosmopolitēs 的廊下派式转化,第欧根尼的意思只是他真正属于的地方只有宇宙本身,换言之,他仅仅利用了“公民”含义中的“属于”要素,而去除了政治共同体或政制的要素④斯科菲尔德:《廊下派的城邦观》,徐健,刘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2-183,192-195 页。。总之,他的世界主义依旧具有反礼法的本质,其书名《政制》本就是对作为传统政治术语的“政制”的戏谑式改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拉特斯称自己是“第欧根尼的公民同胞”:亚历山大曾问克拉特斯是否想重建他那被亚历山大所毁的国,克拉特斯说没必要,因为“屈辱与贫穷是他的不为命运女神蹂躏的国,他是抵挡复仇女神之阴谋的第欧根尼的公民同胞”。克拉特斯的这种世界主义集中反映在他的某部肃剧中:“我的国非一塔楼一屋舍,整个大地就是壁垒和广厦,预备给我等度过一生。”
世界主义规定着犬儒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显得极为乖张怪诞,背离礼法习俗。据说,第欧根尼曾因“伪造货币”(paracharassō to nomisma)而流亡。nomisma 指习惯所承认的东西,货币只是其中一种,因此,“伪造货币”就暗指改变城邦的习俗,从而极端地反衬出自然对律法的优越性,或者说个人自足和自由的重要性。亦如克拉特斯在一首描绘理想城邦“佩瑞”(Pērē)的打油诗中所示,理想公民们或犬儒们的“口袋”(pērē)里“只有百里香、大蒜以及无花果和面包。于是人们不会为了这些东西相互争斗,也不会为了金钱和声望而准备长矛铠甲”。也正是凭靠自己夸张的“自然”,克拉特斯赢得了熙琶姬娅(Hipparchia)的芳心,并将其教育成“佩瑞”的女性公民。
这一切就是芝诺从克拉特斯那儿学到的贬低城邦的本领,因为他那本集中阐发世界主义的论著《政制》被人戏称“写在了狗尾巴上”⑤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第263,285,294,297-298,301-302,308 页。。但很快,芝诺因不满恬不知耻且缺少理论建树的犬儒生活而离开了克拉特斯,转而聆听麦加拉派和学园派的课,直到公元前300 年左右创建廊下派。有证据显示,《政制》很可能写于他成为学园派珀勒谟(Polemon)的学生期间或之后①A.Erskine,“The Hellenistic Stoa”,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9-15.。倘若如此,芝诺就是要赋予世界主义本身以明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内涵,从而构建一种“积极的”世界主义,最终超越犬儒世界主义。
二、圣贤城邦:芝诺《政制》
如同第欧根尼的《政制》,芝诺的同名作品也只有辑语传世,因此该书的详细内容已不可考。但普鲁塔克在《论亚历山大大帝的机运或德性》中说,芝诺《政制》的“要点”在于:
我们不该居住在各个城邦或民族中,它们被各自的正义原则所界分,相反,我们应该将所有人视为民众同胞和公民同胞,只应存在一种生活方式和秩序(kosmos),就像牧群一块吃草(sunnomou),受共同法(nomō koinō,共同牧场)养育。芝诺写到这儿,仿佛在勾画哲人的一个良序政制的梦想或图景;然而,却是亚历山大让这个理论变成了现实。②H.von Arnim,“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Vol.I”,Leipzig:K.G.Saur Verlag,1964,pp.60-61.
看来,芝诺似乎旨在构建一个由“所有人”组成的世界城邦。但据拉尔修所述,芝诺在《政制》中说“唯有好人才是公民”,而其他人因为不具智慧从而是“敌人”(polemious)。这种观点或许源于安提司忒涅斯③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第257 页。。那么,公敌岂能作为世界城邦的(全权)成员?不妨推测,惯用修辞笔法的普鲁塔克为了将芝诺的思想与亚历山大的伟大行动勾连起来,故意以“所有人”来取代“所有智者”或其他类似表述。而且,即使芝诺果真使用了“所有人”这样的措辞,他也很可能像第欧根尼那样认为只有智者才是真正的人:第欧根尼曾在大白天举着灯笼到处转悠,说“我在找人”④J.Sellars,“Stoic Cosmopolitanism and Zeno’s Republic”,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Vol.XXVIII,No.1,2007,p.15.。
可见,只有圣贤才配称世界公民,也只有他们才真正遵守“共同法”,从而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秩序。既然智慧或德性是公民身份的唯一标准,我们就能理解芝诺在《政制》或其他论著中设计理想国的具体制度时,为何宣称普通教育毫无益处,并取消神庙、法庭、体育场,废除货币,宣扬两性的道德能力平等,甚至主张特殊情势下的乱伦。廊下派思想的大成者克律希珀斯(Chrysippus)不仅赞成老师的这些观点,同时还鼓吹武器的无用性和特殊情势下的食人。据前述可知,以上措施基本源于犬儒派尤其是第欧根尼;但我们也不难发现芝诺的措施与柏拉图《王制》之间的关联——难怪普鲁塔克略显夸张地说:芝诺撰写《政制》是“为回应柏拉图的《王制》(Politeia)”⑤徐健:《芝诺〈政制〉中的“悖论”》,见刘小枫主编:《古典学研究》(第一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31-48 页。。无论如何,芝诺与柏拉图最根本的差异在于,他反对封闭的城邦及其阶级体系,而强调所有智者是真正的公民。根据希腊语作家阿忒奈俄斯(Athenaeus,大约活跃于公元200 年)的转述:
芝诺将爱若斯视为友爱和自由之神、和谐之提供者,此外无他。所以在《政制》中他说,爱若斯是促进城邦安全的神。⑥A.A.Long,D.N.Sedley,“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Volume 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430.
芝诺为何选择爱若斯作为圣贤城邦的守护神?或者说,爱欲如何能够生成友爱、自由、和谐以及安全?芝诺在《政制》中说过,“智者会爱那些从外表上显出德性禀赋的年轻人”。从芝诺的《清谈录》(Diatribai)中可以看出,如同智者中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为智者所爱的“年轻人”亦不排除女性。芝诺就像柏拉图笔下的护卫者那样,革新了古希腊尤其是斯巴达以教化为宗旨的男同性恋实践——无论是同性(男或女)之间还是异性之间,都能拥有某种高尚的爱欲⑦斯科菲尔德:《廊下派的城邦观》,徐健,刘敏译,第46-69 页。。年长的智者在爱上年幼者由“相”而现的美好的“心”之后⑧“真正可爱的”相比如“竖耳聆听逻格斯”“表情纯净”“举止动作无放纵之象”。H.von Arnim,“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Vol.I”,p.58.,便向其教诲灵魂的上升之道。芝诺《政制》中说,只有好人是朋友和自由人。因此,一旦被爱欲者有幸在一定年龄习得德性,这种爱欲关系就将终止,并萌生出一种真正平等的“自由”和“友爱”。在圣贤城邦中,所有公民都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自由,相互间没有任何的“从属”关系,正如廊下派所说:“自由是一种独立行事的权力”。同时,依据廊下派的观点,这些自由人又在道德上“彼此相似”从而彼此互爱①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第320,352-353 页。,“即使他们没有待在一起,甚至没有机会相互认识”“如果随便一个什么地方的某位圣贤明智地动动手指,这整个被居住的世界的所有圣贤都要受益②Plutarch,“Moralia XIII:2”,trans.H.Chernis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730-733.”。所有智者之间通过德性及其行动而彼此同等互惠,既如此,他们便能够和睦相处,因为在廊下派看来,“和谐是共同善的知识”③斯科菲尔德:《廊下派的城邦观》,徐健,刘敏译,第70-73,175-177 页。。并且也正是因为充分的友爱,巨型的智者城邦完全实现了一种免于内乱的“安全”。
总之,芝诺构建了一个由天下全体圣贤组成的城邦,其治理是靠友爱和共同法。但据现有文献记载,在芝诺城邦观的基础上,克律希珀斯利用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对世界重做构思,明确打造了一种宇宙城邦。
三、宇宙城邦:克律希珀斯及其之后
克律希珀斯在《论自然》中写下了一些与赫拉克利特以及与荷马等诗人的学说相类似的东西,比如在第三卷中,他说:
宇宙是一个单独的、由智者组成的实体,对于其公民权,他说,则由诸神与人类共同持有,以及战争与宙斯是同一的,正如(他说)赫拉克利特也这么说。④奥宾克:《宇宙城邦中的廊下派圣贤》,时宵译,见程志敏,徐健选编:《廊下派的苏格拉底》,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 年版,第97-119 页。
克律希珀斯的世界主义与赫拉克利特的“战争”学说有何关系?据赫拉克利特辑语53:“战争是万物之父,是万物之王,它显明这些是神,那些是人,它使这些成为奴隶,那些成为自由人。”战争不仅区分了诸神和人类,还是他们共同的父和王,此乃荷马笔下作为人神之父的宙斯的真实意涵;正是这种辩证原则启发了克律希珀斯对神-人共同体的思索⑤斯科菲尔德:《廊下派的城邦观》,徐健,刘敏译,第107-109 页。。赫拉克利特还在辑语30 中说“这个宇宙对万物同一”;又在辑语2 中说“逻各斯就是共同的,但大多数人却活着像是有着自己的智虑”⑥基尔克,拉文,斯科菲尔德:《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聂敏里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77-279,289,294-295 页,译文稍改。。唯有具备真正智虑的人才会遵守宇宙的逻格斯或秩序这个共同的东西。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克律希珀斯会说宇宙是一,但其成员“诸神与人类”必须被智慧所限定。不过,他也对赫拉克利特思想作出了关键的推进。诸神和圣贤具有平等的公民身份,正如《论自然》第三卷中指出,好人“在任何事情上均不会被宙斯胜过”;或者像他在别处所言:“当其中一位遇到另一位的行动,二者就因都是智慧的而相互同等受益。”⑦Plutarch,“Moralia XIII:2”,trans.H.Cherniss,pp.454-457,788-791.由此,克律希珀斯表明宇宙本身可以作为一个城邦来理解。
可见,克律希珀斯提出了一种宇宙城邦,该城邦的公民不只有智者,还有诸神。不仅如此,他还对作为完美城邦的两个支柱之一的共同法进行了阐发。他说“共同法是那贯穿万物、且等同宙斯的正确理性(right reason)”⑧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第340 页。。这意味着共同法的权威源于其理性的本质。另据克律希珀斯在《论法律》开篇所言:
法律乃一切属人和属神之事的国王。它必须作为统治者和作为引导者,掌管高尚或卑贱之事;因此还必须是正义和不义之标准,为本性是政治的动物规定他们应该做的,禁止他们不应该做的。⑨H.von Arnim,“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Vol.III”,Leipzig:K.G.Saur Verlag,1964,p.86.
作为万物之“国王”或“标准”的共同法或宙斯的理性实质最终体现在,共同法或宙斯凭着“规定”与“禁止”,“统治”并“引导”政治动物过一种共同的生活。但事实上,人类中只有圣贤才是真正的守法者,亦如第二任廊下派掌事克勒昂忒斯在《宙斯颂》(Cleanthes,Hymn to Zeus)中所说,败坏或不幸之人“不看也不听神的共同法”⑩A.A.Long,D.N.Sedley,“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Volume 1”,p.327.。
或许直到巴比伦的第欧根尼,早期廊下派哲人始终认可克律希珀斯的宇宙城邦观;第欧根尼说:“愚人中间是不会有城邦或法律的,在诸神与圣贤所组成的组织结构之中才会有。”①H.von Arnim,“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Vol.III”,pp.241-242.而至稍后的西塞罗或中期廊下派时代,在罗马凭政治法律和重装步兵横扫天下的背景下,克律希珀斯的宇宙城邦得以改造,变得更加温和,能够覆盖诸神和全人类。奥古斯都宫廷的廊下派哲人狄都谟斯(Arius Didymus)讲道:
城邦有两种含义,一指居所,二指由其居民和公民组成的组织结构(sustēma),同样,宇宙如同(hoionei)一个由诸神与人类组成的城邦,其中诸神作为统治者,而人类作为其臣民。他们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因为他们分有理性亦即自然法;并且其他一切事物都是为他们创造的。②A.A.Long,D.N.Sedley,“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Volume 1”,p.431.
在廊下派看来,宇宙之所以像城邦,首先因为它是诸神和人类的“居所”,其次因为它是他们所组成的“组织结构”。这两项界定明显呼应西塞罗的《论神性》(卷二,154)。但与西塞罗不同,狄都谟斯不仅没有在神-人隶属关系问题上沉默,反而说所有人都受诸神领导。不过,既然圣贤具备完美德性,我们就不妨与克律希珀斯一样认为诸神和圣贤共享公民权。因此,他们共同支配常人。如果说狄都谟斯严格区分了“公民”和“居民”,那我们可以推测,圣贤和诸神是作为统治者的公民,而作为被统治者的常人则是居民或潜在公民③K.M.Vogt,“Law,Reason,and the Cosmic City”,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91-93.。巴比伦人第欧根尼继续说道,圣贤“会真正地被认为是将军、舰队统帅、司库和托收代理人,他还会被认为能够很好地执掌其他的官职,因为治国者必然要具备所有这些事务的知识”。
也正是西塞罗或中期廊下派将早期廊下派的“共同法”视为“自然法”,并将早期廊下派的“友爱”转化成“博爱”(philanthrōpia)或“人道”(humanitas)。自公元前2 世纪以降,“博爱”和“人道”这两个术语经常出现在有关廊下派的原典中。phil-anthrōpia 由philos(友爱的)和anthrōpos(人)复合而成,字面意是“爱人类”。我们或许能从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约公元前465 年上演)开场中发现该词的最初用法:据述,普罗米修斯由于“爱人类”,偷盗天火给凡间,以致犯下不敬宙斯的大罪。然而在廊下派那里,“博爱”或“人道”非但与僭越无关,反倒是值得推崇的大爱,因为无边无际的宇宙城邦在不同程度上覆盖了每一个人。
从此在廊下派观念里,所有的人和神都共同生活在一个受普遍法律和爱欲支配的宇宙城邦中,尽管晚期廊下派“哲人王”马可·奥勒留并不完全认可这种世界主义。他在《沉思录》中说,人类因为共同的理性进而还有共同的法律而共享同一个社会,所以宇宙城邦“如同”(hōsanei)“由全人类分享的共同政治体”④M.Aurelius,“The Communings with Himself”,trans.C.R.Hain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6,pp.70-73.。西塞罗在《论法律》(卷一,23)中也有相近的论证,但他认为理性为神和人共有,可见对马可·奥勒留而言,诸神不属于宇宙城邦。看来,奥勒留否定克律希珀斯的人神亲缘论,正如《沉思录》满篇的谦卑立场所示。
四、世界主义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吗?
公元前1 世纪,围绕芝诺《政制》中的犬儒“遗毒”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据当时的伊壁鸠鲁派斐洛德谟斯(Philodemus)记述,有些廊下派哲人为了替芝诺辩护,甚至妄称他并不在意自己的政制能否实现。如我们所见,稍后的普鲁塔克认为芝诺就像在描绘一个“梦想或图景”。看来,圣贤城邦在古代就已被当作“乌托邦”⑤现代力主《政制》具有乌托邦性质的研究尤推D.Dawson,“Cities of the Gods”,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3-52.。然而正如斐洛德谟斯指出的,如果芝诺的立法是一些“不可能的假说”,那他就“忽视了那些实际存在的人”;但芝诺一开篇就表明自己的立法“适用于他所出现的地域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⑥斯科菲尔德:《廊下派的城邦观》,徐健,刘敏译,第12-36,198-199 页。。倘若如此,芝诺的政制又为何在此时此地便能实践?
据前文所述,在圣贤城邦中,任何具体的制度或机构都是无关紧要的,真正重要的唯有成熟的德性。显然,该城邦能否实现依赖于人能否获取德性。廊下派深信“德性是可教的,从恶人变好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来”。犬儒派也这般认为,但“犬儒学说是通往德性的捷径”;而学习廊下派德性则需更高的理论素养。在芝诺笔下,通过同性或异性爱欲的训练,可达到这种德性。简言之,正是通过反对“德性不可教”这一古典教诲,芝诺将圣贤城邦塑造成一座“实在”的城邦。那么宇宙城邦又如何?拉尔修讲道:
廊下派说动物拥有的最初驱动(hormēn)指向自我保存,因为自然从一开始就亲近(oikeiousēs)它,克律希珀斯在《论目的》第一卷中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对于每个动物而言,最初亲己的(oikeion)事物是它自身的构造以及对此的意识;因为自然不可能使动物疏远它自己,也不可能在制造它之后,既没有使它疏远自己,也没有使它亲近自己。……因此,动物拒绝那些有害的事物,接受那些亲己的事物。
在克律希珀斯或廊下派看来,与其他动物一样,人类的“最初驱动”是“自我保存”,易言之,人首先“亲近”自身的构造以及维系构造所需的事物,而“疏远”相反的事物。但是,人还被赋予理性。当理性渐趋成熟,它就成了驱动的“匠师”①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第306,339-341 页。。在西塞罗的《论至善与极恶》中,廊下派卡图说,亲近自我保存是一种“合宜官能”(kathēkon)或具有罗马意涵的“义务”(officium)。这类行为无关善恶,因为它针对的自然事物是介乎善恶之间的更有“价值”的“中性物”。而在理性或“智虑”的作用下,合宜官能可转化为“正确行为”(katorthōma)或“高尚”,因为前后的区别只在于是否具有道德意图。如此,内在德性即“唯一的善”才是更“可欲”的事物。
但随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增多,理性化的驱动就不仅指向自爱,还指向爱他。卡图讲道:“明白自然产生父母对儿女的爱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我们力图实现的人类普遍共同体的起点。”“生育是一项自然所具有的原则”②A.A.Long,D.N.Sedley,“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Volume 1”,p.348,pp.361-362.,人类就像其他动物一样,不该疏远自己的子嗣——正如克律希珀斯在《论正义》第一卷中所说③Plutarch,“Moralia XIII:2”,trans.H.Cherniss,pp.454-455.。人甚至要比蜜蜂等动物更加自然地去爱自己的同类,就像身体的某些部分如手脚是为了服务于其他部分而创造的。因此,“我们在天性上就适合组成联盟、社会和国家”,乃至“如同”城邦的宇宙。晚期廊下派希耶罗克勒斯(Hierocles)在《论合宜官能》中,利用同心圆比喻,详细勾勒了驱动的延展过程:
第一个也是最近一个圆被一个人画得好像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他的心灵。这个圆围住身体以及为身体而取的一切。因为它实际是最小的圆,几乎触及中心本身。接着,第二个圆更远离中心,但围住了第一个圆;它包含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儿女。之后的第三个圆中有叔伯舅和姑姨、(外)祖父和(外)祖母、兄弟姊妹的儿女,以及堂(表)兄弟姊妹。下一个圆包括其他亲属,其后是乡亲组成的圆,然后是部落同胞组成的圆,接着是公民同胞组成的圆,类似地,再是邻镇人组成的圆和国民同胞组成的圆。最外围和最大的圆围住其他所有圆,它由全人类组成。④A.A.Long,D.N.Sedley,“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Volume 1”,pp.349-350.
这充分揭示了廊下派所说的人是自然的政治动物的最终含义。人在天性上不仅是封闭城邦的动物,更是开放世界的参与者。不过真实说来,只有具备“完美”理性的人方能心怀德性和博爱,但具有理性能力的常人亦可效法之。希耶罗克勒斯接着规定:“将圆以某种方式向中心拉拢,并一直热切地将那些把其他圆围住的圆中的项,移至被围住的圆中。”基于血缘伦理之上的有差别的爱即使是自然的,也是不符合理性的,我们要像尊重自己一样平等地尊重其他所有人。恰如希耶罗克勒斯所言:“尽管血缘越远,关爱就越少,但我们仍必须尽力使他们变得相似。”
事实上,廊下派不仅从驱动论还从神学宇宙论来证明宇宙城邦的自然性或非乌托邦性。廊下派似乎通常认为,宇宙如同城邦;并且,前引西塞罗《论神性》中的文段紧接着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例来佐证对宇宙城邦所作的界定。这是否意味着宇宙虽然在根本特征上与雅典和斯巴达无异,但却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构成一个城邦?西塞罗和狄都谟斯的相近描述很可能都受到克律希珀斯某部作品的启发,因为狄都谟斯将定义归在克律希珀斯名下⑤斯科菲尔德:《廊下派的城邦观》,徐健,刘敏译,第96-97 页。。若是如此,我们就能利用赫拉克利特辑语30 来回应上述问题,既然该辑语对克律希珀斯有过重要影响。这个宇宙(kosmon tonde):
既不是某个神(tis theōn),也不是某个人创造的,而一直总是并且现在是而且将来是:永恒的活火,一些分寸上点燃,一些分寸上熄灭。
theōn 指诸神,所以宇宙并非源出于“诸神中的某个神”,当然亦非出自属人的技艺。正如tonde 这个词所示,宇宙原就“在此”,是“这个”且独一的宇宙,而所有人和神都身属其中。它是“永恒的活火”,恒常地处于燃烧和熄灭的规律更变之中。类似地,廊下派一般认为,神或宙斯贯穿整个宇宙,是一种“有技艺的火”,能通过元素间的转化,有条不紊地推进世界的创生;但宇宙在被周期性大火燃尽后,就复归于火,如此实现永恒轮回。可见,如同城邦的宇宙是自然的、实在的,始终受变化和不变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原则支配。因此或可揣测,“如同”一词只是意味着宇宙城邦并不像一般的城邦那样由人所立,而只能为圣贤所发现。
五、余 论
尽管圣贤城邦和宇宙城邦都不属于乌托邦,但它们却是不可能实现的。毕竟圣贤“就像凤凰,每逢五百年才出现一个”①Seneca,“Epistles:Volume I”,trans.R.M.Gummer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279.。即使是罗马,它也不是真正的世界国家,因为它终究属于秩序已然溃散的尘世,且“以霸道政治显赫于世”②靳凤林:《西方霸道政治的历史由来及实践逻辑》,《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3 期,第6-8 页。:廊下派说地上的一切城邦都徒有其名,它们并不正派或“文雅”③H.von Arnim,“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Vol.III”,pp.80-81.。
亚历山大开启了世界的视野,而廊下派则通过深入人的灵魂,尝试为新世界奠定普世的内在秩序。这一艰难的立法尝试本身足以堪称伟大,其中涉及的诸多思想延续了智术师时代以来与城邦疏离的智、识精神,对后世尤其对18 世纪后的人类共同体构建这一启蒙理想始终发挥着重大影响。但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安抚充满血与泪的苍茫大地,开创出一个“文质彬彬”的博爱世界?纵观整个廊下派,它自始至终都抱持着通过个人主义的灵魂改造而成就的世界主义秩序的理想,但在面对罗马这个世界头号强国时,又不得不做出相应调适:在急迫认可罗马那充斥着斗争和阴谋的“大一统”秩序的前提下,转而关注罗马施政者的具体政治行为。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体的两面。对此,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深刻总结道:“在亚历山大之后几百年里,廊下派思想对政治共同体的召唤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影响。就当时的政治而言,它能够做的,顶多是规劝为政者尤其是国王们加强个人的品行修养,使之成为智慧者和世界公民的品行。政治实在之本体须来自别的地方。”④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段保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20-12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