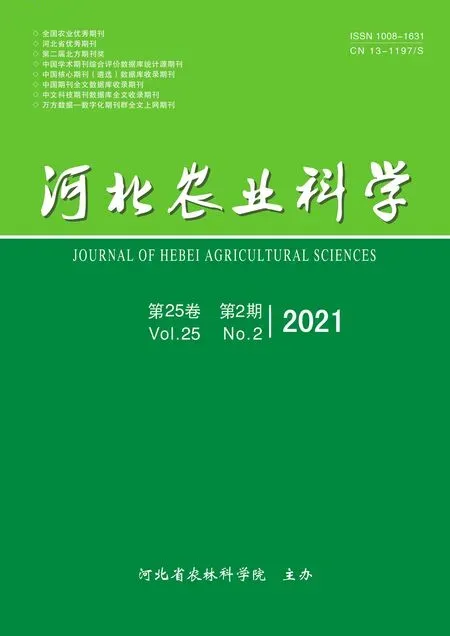我国农村居民点整理研究
刘鹏举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究院,北京 100101)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指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整治、改造其空间结构和布局以及土地产权调整,使其达到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一项综合的土地利用工程[1]。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涉及人类活动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国目前约有60万个行政村,250万个自然村,特别是平原地区,绝大多数分布在耕作区,自然村内部结构不合理现象严重,同时存在“空心村”“两栖占地”等现象,土地浪费问题严重。自2000年以来,土地整治工作快速进行[2],并取得了显著成果。201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8〕16号)指出“三区三州”及其他深度贫困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由国家统筹跨省域调剂使用[3],这一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区域间共同发展,并为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了政策支持。对农村居民点进行整理与规划,有利于提高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度;有利于推进区域城镇化发展进程;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配置;有利于提高农民幸福感。以此进行的“美丽乡村”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都有效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科学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系统探讨农村居民点整理过程中理论指导、潜力测算、模式选择和优化布局等相关研究,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1 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基础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土地综合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产物,受自然、经济、社会和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农村居民点整理包含区位理论、土地可持续利用理论、城乡一体化理论、人地协调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
1.1 区位理论
“区位”意为站立之地,由德国农学家杜能(J.Thunen)于1826年首次提出区位论概念,区位实质目的是要求土地利用应合理布局,以求达到集约节约用地和产生最大效益。区位理论主要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市场区位论等,具体包括位置、场所和定位、布局2个含义[4]。
1.2 土地可持续利用理论
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研究源于土地适宜性评价,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土地评价领域的体现[5]。春秋战国时期就提出了“永续利用”的思想,是可持续理论的雏形;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可持续利用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有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6]可持续利用的重点是自然环境的持续能力,在土地利用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环境问题和环境效益。
1.3 城乡一体化理论
城市和乡村是对立统一关系,保持适当平衡关系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前提[7]。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学家刘易斯·芒福德[8]指出,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学者Ole Gade[9]提出“城乡融合区”概念。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乡一体化成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变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1.4 人地协调理论
人地关系是人类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一种客观关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有关人地关系理论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可能论、适应论、人类中心论、生态论、文化景观论、生产关系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环境感知论、文化决定论、“天人和一”观和协调论等。人地关系协调主要取决于人[10],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处理好人与地的关系,同时协调好因人地关系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解决人地关系协调问题的关键。开展土地整理是协调人地关系、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之一[11]。
1.5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缘起与发展是基于对股东中心理论的质疑与创新[12],是企业伦理学或者商业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属于管理学和社会学的一个交叉学科。近年来,学者们对利益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13,14],并且广泛应用于公司管理、生态管理、公共管理、教育领域等。因此,在土地整理过程中,要统筹考虑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
2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研究
我国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以整理规划为指导,充分分析土地开发整理潜力[15],具体包括有效潜力、聚落优化潜力、生态环境潜力、土地增值潜力4个方面[16,17]。师学义等[18]、宋伟等[19]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是指通过对现有农村居民点改造、迁村并点等,可以增加耕地、其他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面积。吴小红[20]、孙钰霞[21]认为,在一定时期、一定生产力条件下,通过行政、经济、法律和技术等一系列措施,使农村居民点土地在提高利用率和产出率的基础上挖掘用地潜力。
2.1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来源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用地降低、建筑容积率提高、闲散土地再利用、自然村向中心村迁并以及村内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的配套和完善[22]。具体措施为:(1)控制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将超标建设用地复垦。(2)整理闲置宅基地。(3)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建筑容积率。(4)内部废弃的建筑物再利用和部分基础设施的整理规划[23]。
2.2 居民点整理潜力面积的测算方法
目前,居民点整理潜力面积测算方法主要有6种。(1)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依据国家规定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在预期规划期末的人口数量的基础上,计算得到农村居民点的理论用地面积,并将其与现状面积计算差值。(2)户均建设用地指标法。户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是通过现状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与理论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之间的差值测算潜力。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定面积为户均宅基地面积与户数的乘积。(3)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闲置率法。这种测算方法考虑了农村居民点内部闲置土地的整理潜力,这部分整理潜力几乎可以全部转化为现实的潜力。(4)以人均城市用地标准测算整理潜力法。这种方法适用于临近城市郊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以公寓楼代替原有的住房,整理潜力巨大。(5)城镇体系规划法。用现状面积与规划期末居民点面积的差值衡量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潜力[24]。(6)实地调查法。实地调查法是采用走访调查的方法,依据潜力制定指标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方法。陈荣清等[25]通过实地调查法,测算了4个层次的潜力,包括闲置宅基地潜力、一户多宅潜力、宗宅基地面积降低潜力、人均居民点用地缩减潜力。
3 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研究
部分学者根据农村居民点整理实践经验,对整理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叶艳妹等[26]提出农村城镇化、自然村缩并、中心村内调型、异地迁移4种模式;高建华等[27]提出了迁村腾地模式和改造集并模式;廖赤眉等[28]针对广西的特点提出了迁村并点、缩村挪地、迁村上山、重建家园4种整理模式。徐燕[29]针对景区周边居民点用地,提出搬迁、城中村改造和示范村建设模式。
3.1 村庄内部改造模式
村庄内部改造模式是指对村庄进行内部改造,改善布局,并控制其对外扩张的模式,包括基础设施配套、农村道路整治、内部宅基地整理。该模式主要适合于村庄废地、空闲地较多,设施不完善,区位条件差的地区。
3.2 迁村并村、社区化模式
迁村并村、社区化模式是把分散于大村庄以外的自然村并入,形成集聚,或把村庄异地搬迁到区位优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地区进行社区化改造。采取迁村并村模式一方面可以集约用地,利用节约的土地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29];另一方面可以优化村庄布局,发展中心村建设,有利于推动农村社区化改造,提高生活质量。该模式适用于分散的农村居民点,有利于集约用地,综合地区资金、基础设施、交通等优势。
3.3 城镇化整理模式
城镇化整理模式是针对经济水平较高、城镇周围的居民点或者“城中村”,把村庄整理与城镇规划相连,完善基础设施,实现“城市化”的一种整理模式[30]。该模式有利于统一规划、成片开发[31],适合城郊地区的农村。在实际工作中,土地权属、启动资金[32,33]是最大的难点。
3.4 局部搬迁与整体搬迁模式
搬迁模式包括局部搬迁和整体搬迁,搬迁过程中农户最关心的是搬迁距离[34],局部搬迁最大搬迁距离为2 000 m[35],适宜远离城镇、整理后保持传统农耕的村庄;整体搬迁最大搬迁距离为3 000 m[36],适宜城镇郊区、地点集中安置。
4 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化布局
4.1 优化布局遵循原则
农村居民点是农业人口因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活动形成聚集而出现的定居场所[37,38],在规划布局过程中,应遵循以下3个原则。
4.1.1 经济服务半径合理,区域布局完整 经济服务半径是指居民点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范围。农村居民点布局要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合理确定居民点经济半径。
4.1.2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一体化进一步深度发展,小城镇居民具有半工半农的职业特点,在农村居民点布局时,既要便于进城打工,又要便于务农生产。
4.1.3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尽量少占耕地 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点规模小,细碎化严重,因此在农村居民点布局时,要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发挥聚集效应,尽量少占或不占用耕地。
4.2 优化方案
4.2.1 向交通干线聚集 交通设施完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农村居民点布局中应该向交通干线聚集,充分发挥交通运输的聚集效应,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4.2.2 向附近规模较大的中心村聚集 中心村具有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且能对周边一定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带动和辐射作用。向附近规模较大的中心村聚集,有利于充分利用中心村发展资源,优化农村劳动生产力区域空间配置,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
4.2.3 向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聚集 基础设施是社会先行资本,是地区发展的基础。向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聚集,有利于节约建设成本,为农户提供便利的服务。
4.2.4 向自然资源优越的地区聚集 大多“三区三州”及其他深度贫困县自然环境恶劣,耕地资源、水资源短缺,不利于长期发展。向自然资源优越的地区聚集,切实做到农民有地,有产业,有就业机会。
5 结语
我国农村居民点整理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理论研究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宏观背景下农村居民点整理内涵的研究,逐步形成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加强对农村居民点整理后有关治理和管理问题的研究。在实践工作方面,要加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规划、实施和后期管理工作,充分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情况以及农民的意愿,做好权属调整工作,加强农村居民点发展的规划与管理[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