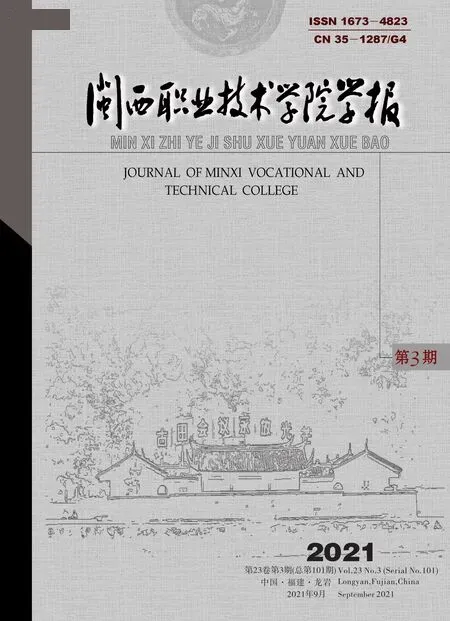薇拉·凯瑟小说的生态伦理意义
——以《啊,拓荒者!》为例
刘莹莹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430079)
薇拉·凯瑟(1873—1947)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曾获普利策奖、美国妇女奖以及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学位。20世纪初,在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萨拉·奥恩·朱厄特的影响下,薇拉·凯瑟接连创作了《啊,拓荒者!》(1913)、《云雀之歌》(1915)、《我的安东妮亚》(1918)、《我们自己人》(1922)、《一个迷途的女人》(1923)、《教授的住宅》(1925)、《莎菲拉和女奴》(1940)等优秀作品,从各个侧面描写19世纪末美国中西部拓荒者与大自然搏斗的艰苦生活,歌颂他们顽强的创业精神和高尚情操。其中,被称为“草原三部曲”的《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云雀之歌》集中描写了拓荒时代欧洲移民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移民之间的文化冲突和人际交往,具有十分深远的生态伦理意义。
《啊,拓荒者!》是薇拉·凯瑟的代表作,被公认为近代美国经典作品之一,自1913年出版以来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小说以瑞典移民后代亚历山德拉在内布拉斯加高原上的拓荒经历和思想感受为主线,以其他人物的矛盾纷争、情感纠葛为副线,呈现人的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描绘人、自然、社会三者的生态平衡与稳定发展。
一、自然生态危机与生态伦理关系建构
19世纪中后期,欧洲许多国家出现美国移民热,许多欧洲人不远万里前往美国中西部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薇拉·凯瑟9岁时跟随父母迁居内布拉斯加州,她目睹了移民们艰苦卓绝的拓荒经历和举步维艰的生活,见证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人与自然的斗争。于是,薇拉·凯瑟通过《啊,拓荒者!》揭示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通过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展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
(一)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
作品开篇就呈现自然环境的恶劣:“三十年前一月里的一天,内布拉斯加高原上狂风怒号。汉努威小镇好像一条停泊在那里的船,挣扎着不让自己给风吹跑。濛濛雪花围绕着一簇簇灰暗、低矮的房子打转,下面是灰色的草原,上面是灰色的天。”[1]大自然通过糟糕的天气,拒绝移民的闯入,发泄对拓荒者的不满,给予他们警示。拓荒者对土地过度开发,拼命向土地索取资源,不给其休养生息的机会,导致土地严重退化,正如罗所说“我们的地现在已经长不出六年前那么多东西了”[1]。由于土地不能给拓荒者带来丰富的物产,拓荒者对这片土地失去信心,纷纷选择离开,没有深入思考土地产量下降、自然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他们看来,他们脚下的土地无非是野性未驯,“不时要发发怪脾气,谁也不知道脾气什么时候来,或是为什么而发。它上面挂着灾星,那神灵是和人作对的”[1]。拓荒者秉持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一心想着征服自然,想方设法从自然中为自己谋取利益,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发生危机。
(二)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建构
聂珍钊指出,“人类征服和战胜大自然的努力只能给自身带来悲剧,我们不得不从伦理的角度思考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并认识到人类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同大自然和平相处”[2]。薇拉·凯瑟通过塑造亚历山德拉和艾弗这两个人物,建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伦理关系。
在其他拓荒者对土地失去信心时,亚历山德拉带着爱和渴求对待土地,“她觉得这土地太美了,富饶、茁壮、光辉灿烂。她的眼睛如痴如醉地饱览着这广阔无垠的土地,直到泪水模糊了视线”[1]。她以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观察力接收到土地传递给她的信息,感受到这片土地涌动着旺盛的生命力。亚历山德拉和土地融为一体,和土地上的自然万物平等、和谐相处。因为热爱土地、了解土地,亚历山德拉没有像其他拓荒者一样毫无止境地滥用土地,而是根据土质和地势选择合适的作物进行种植,在她的科学种植和细致管理下,土地恢复了生机和繁殖力,并给亚历山德拉一家带来丰收的喜悦。“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能伦理越位,不能毫无限度地入侵大自然留给其他生物的领域。从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关系来说,不能伦理越位就是不能入侵、破坏或占领不属于自己的领地。”[2]亚历山德拉虽然管理着大片土地,名义上是土地的所有者,但是她心里明白,土地并不属于她,也不属于任何人,土地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是这里的过客,而土地是常在的。真正爱它、了解它的人才是它的主人——那也不过是短暂的”[1]。亚历山德拉没有以高高在上占有者的姿态去蹂躏土地,而是细心呵护它。
“在自然界,一切生物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和环境,相互之间并行不悖,形成了自然伦理或生态伦理,即自我调整、和谐相处、共生共存的伦理关系。这也是整个自然界必须遵守的伦理秩序或者自然法则。”[2]艾弗虽然迁居到野外,但是并没有破坏当地的自然环境,而是让周围的一切保持原生态,他敬畏自然,爱护自然的一鸟一兽、一草一木。在他看来,野生动物是属于上帝的,人们没有权利捕杀它们,他不允许别人手持猎枪在他周围捕杀野生动物。艾弗擅长医治生病受伤的动物,将它们视为自己的同伴,设身处地为它们着想,关心、照顾、理解它们,他总是用“妹子”“姑娘”称呼马儿,把动物当作和自己平等的人。艾弗与自然万物建立和谐友好的关系。此外,对艾弗而言,邻居越少诱惑就会越少,所以他尽量远离人类,居住在远离社会是非纷扰的地方。艾弗将自己的欲望降到最低,吃喝住行极为简朴,亲近自然,体会自然的美与和谐。“生态批评家认为,人类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对物质的无限制欲求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生态批评所倡导的原则之一就是简单的生活观。”[3]艾弗通过自己的简朴生活,揭示人类只有把自身的欲望限制在自然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才能与自然和平相处,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只有在人意识到自然物作为自立的个体而不是人的对应物、象征体、喻体——表现人的工具,意识到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位置,进而以人类个体的身份与这些非人类的个体进行平等的交往,人与自然的交互主体性才能真正实现。”[4]亚历山德拉、艾弗尊重自然,体悟自然生命的真切,和自然进行无声而平等的交流,和自然建立和谐的伦理关系。人类只有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才能得到自然的馈赠。
二、社会生态危机与社会伦理秩序建构
人类社会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整体主义不仅要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还必须突出强调人类这个子系统的内部关系对于母系统的平衡稳定的重大作用,把人类子系统内部关系的改善——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人权的保障、人与人关系的改善、社会公正的实现、生态正义的实现、全人类的和平与合作等,这些对整个生态系统生死攸关的重大影响凸显出来。”[4]
(一)社会成员关系的异化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愈演愈烈,金钱、物质成为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利己主义、物质至上的社会,很少有人关心弱势群体,给予他人一定的关心与照顾。薇拉·凯瑟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反映人情淡漠、世态炎凉的社会现状。在《啊,拓荒者!》中,艾米的小猫爬到电线杆顶,5岁左右的他十分担心却又无助,过路的人行色匆匆,没有人注意到他,更没有人停下来关心他。他不敢向外人求助,因为在他看来,“这里的人衣服都那么讲究,心肠又都那么硬。他在这里总是感到不自在,怕生,怕人笑话,总想躲到什么东西背后去”[1]。薇拉·凯瑟通过一个孩子对社会的感受,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也难免陷入物质崇拜的漩涡,亚历山德拉和她的弟弟、弟媳之间发生财产纠纷。弟媳安妮常常通过和女佣聊天,打探亚历山德拉的家业情况,并加以利用,占点便宜。弟弟奥斯卡、罗担心幼时的玩伴卡尔侵占他们的家产,阻止亚历山德拉嫁给他,为此和亚历山德拉发生激烈的冲突,毫不顾及她的感受。
此外,社会群体对异己的排斥,漠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部分人的社会存在感。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认为,现代社会“鼓励人们泯灭自己的个性,放弃独立的思考,一切希望保持个人独立而不愿顺应潮流的人,由于越过了现代文化的保护线,由于经济上的无能为力,就会被划为多余的人、精神上怪僻的人,而被这个社会所遗弃”[5]。艾弗便是一个被社会所排斥的人,他不穿鞋、不理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喜欢住在有人的地方。因为他生活方式独特,众人冷眼瞧他,把他当成疯子,甚至要把他送进疯人院。李老太太同样如此,家里的人要求她在大白缸里洗澡,不让她戴睡帽,不允许她喝啤酒。她喜欢住在亚历山德拉家里,因为只有在那里,她才能自由地做自己。薇拉·凯瑟通过《啊,拓荒者!》,揭示社会压抑一部分人的个性发展,不让他们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他们无法和别人建立平等、自由和愉悦的社会关系。
(二)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看,文学是由于人类最初表达伦理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学的产生是为了把伦理文字化,建立社会的伦理秩序。因此,文学从起源上说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2]薇拉·凯瑟在《啊,拓荒者!》中通过塑造亚历山德拉这个道德榜样,传达建构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美好希冀。
“道德榜样是文学作品中供效仿的道德形象。道德榜样一般都是理性人物,依靠身上的美德感动人。”[2]亚历山德拉身上闪烁着道德的光辉:她平等对待自己的雇工,在没有客人时,总是和雇工们一起就餐,鼓励他们讲话,并用心听着,为自己和雇工们创造一个轻松愉悦的氛围;她乐于助人,总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不仅收留失去土地的艾弗,还专门在草料库给他装修一间屋子;她尊重社会个体的权利,不对任何人心怀偏见,其他人都把艾弗当成疯子,但是她始终认为“艾弗跟我们有同样的权利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穿衣服、想问题”[1]。她与人融洽相处,总是尽力去理解他人,因为她清楚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至关重要,人与人之间能够给予的惟一真正帮助就是理解。
“道德榜样能够通过人性因子控制兽性因子,通过理性意志控制自由意志,在伦理选择中不断进行道德完善,因而能够给人启示。”[2]在自己最爱的弟弟艾米尔被弗兰克枪杀之后,亚历山德拉伤心欲绝,一个是她最爱的弟弟,一个是她最喜欢的朋友。但是,她并没有让自己内心的悲伤与痛苦转变为对弗兰克的仇恨与报复,而是在人性因子和理性意志的引导下,对弗兰克加以宽恕,甚至抱以同情。因为她深知艾米尔有错在先,是艾米尔的行为造成伦理悲剧。“在人类文明之初,维系伦理秩序的核心因素是禁忌。禁忌是古代人类伦理秩序形成的基础,也是伦理秩序的保障。”[2]艾米尔和已婚妇女麦丽之间的不伦之恋触犯了伦理禁忌,扰乱了社会伦理秩序,这是亚历山德拉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她去监狱看望弗兰克时,理智地对他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不是来怪你的,弗兰克。我认为他们比你更该受责怪”[1]。亚历山德拉有着强烈的伦理意识,她是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者。
三、精神生态危机与个体伦理身份建构
鲁枢元这样定义精神生态学,“这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6]。同现实世界一样,《啊,拓荒者!》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伦理身份焦虑和迷失,由此带来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追寻稳固的伦理身份成为他们寻找精神家园的必由之路。
(一)伦理身份焦虑和迷失
聂珍钊认为,“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2]。伦理身份的不明确会让个体陷入精神的迷茫和焦虑,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归宿。
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三次陷入个体身份的迷失中。第一次发生在知道父亲身患重病时日不多时。因为没有明确的个体身份定位,她满怀忧虑与不安,觉得生活一片虚无,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我们一向事事靠父亲,所以我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我甚至觉得也没有什么可值得过下去的了”[1]。第二次发生在弟弟奥斯卡、罗和她发生严重家庭财产纠纷时。亚历山德拉作为姐姐,一心经营家庭产业,但是她的两个弟弟觊觎她的产业,不理解、不关心她,无视她为家里所做的一切努力。为此,她内心极为痛苦,“早知到头来得到的是这个,我还不如别活到今天”[1]。第三次发生在艾米尔离世后。为了艾米尔可以自由地去外面闯荡,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亚历山德拉一直努力奋斗着,当知道艾米尔去世的消息后,她的精神彻底崩溃,对生活充满了厌恶,觉得世界不过是一个广阔的囚牢。
卡尔则更多的是对职业身份的焦虑。卡尔跟着家人来到内布拉斯加高原,成为一名拓荒者。但在他看来,这片土地很难被人们驯服,他极为讨厌从事拓荒这一职业,为此倍感苦恼。艰难的拓荒岁月再次来临时,他们一家决定离开内布拉斯加高原。卡尔选择做自己喜欢的蚀刻,但当他进入这一行时,蚀刻已经过时,并不能让他获得巨大的成就。紧接着,他又决定试试金子行业。在这段时间,他一直为自己的职业身份感到焦虑和忧郁,四处漂泊,摇摆不定,无依无靠,没有一个稳固的职业身份。所以,他告诫艾米尔“匆匆忙忙进入一项你不喜欢的职业是很容易的,要出来可就难了”[1],他希望艾米尔不要步他的后尘,和他遭受同样的精神痛苦。
麦丽和弗兰克在婚姻关系中迷失了自己的家庭伦理身份。麦丽是一个活泼可爱、美丽热情的年轻女孩,弗兰克曾是年轻有为、积极乐观的绅士,但婚姻给他们的精神生活笼罩了一层阴影。麦丽不认可自己的妻子身份,觉得自己不是弗兰克最理想的妻子。在与弗兰克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她懂得弗兰克的理想妻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她做不到,为此陷入焦虑、孤僻和忧郁之中。而弗兰克在这场婚姻中也迷失了自己的丈夫身份,他把麦丽当成自己的奴隶,将对生活的不满发泄在麦丽身上,从不尊重麦丽的主体地位。
此外,拓荒者在异国他乡失去自己的故乡身份认同,他们在内布拉斯加高原上的住房修盖得十分简单、粗糙、随意,不打算长久居住。这些居无定所的拓荒者常年迁徙,始终处于漂泊的状态,物质家园的不固定使精神家园也遭到破坏,这些拓荒者的移民身份让他们处在故乡身份的迷失和焦虑中,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融入当地的生活,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移民身份。安妮作为瑞典人,害怕别人撞见自己讲瑞典话,只是有时在家里和丈夫讲一些瑞典话。他们不让家里的李老太太按过去瑞典的方式自由地生活,使老太太常常感到压抑。他们作为移民,努力保持生活方式上和别人一致,潜意识里感到自卑,没有建立自己的故乡身份认同。
(二)伦理身份建构
伦理身份的建构可以为人们伦理选择提供警示和教诲,帮助人们摆脱精神上的苦闷和挣扎。稳固的伦理身份可以帮助个体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使命,避免产生人生的幻灭感,增强个体精神上的归属感。
亚历山德拉在不断重建自己伦理身份的过程中,从一次次的精神迷茫和痛苦中走了出来,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希望。父亲临终前,将家庭的重担交给亚历山德拉,并希望她成为这片土地的管理者和守护者,这一身份让她重拾生活的责任、勇气和信心。在其他拓荒者纷纷离开时,她没有放弃父亲留下的产业,而是全身心投入对荒原的调查和了解中。作为姐姐,艾米尔是她的生活目标和奋斗源泉,她一直为艾米尔的未来而努力。艾米尔离世后,她孤苦无依,对生活已然绝望。但是卡尔的归来让她从黯然神伤的过往中走了出来,她不在乎众人的眼光,听从自己的内心,心甘情愿成为卡尔的妻子。这一身份的建构给了她巨大的安慰,让她摆脱孤独,重振精神。卡尔虽然一直在为自己的职业身份焦虑,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重建自己的职业身份,最后和朋友一起从事金子行业,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艾米尔和麦丽恋人身份的公开让弗兰克和麦丽之间的夫妻关系瓦解,虽然麦丽的婚外恋违背了社会伦理,但也让她和弗兰克从痛苦的婚姻关系中得到解脱,对他们曾经在家庭中的身份角色有了深刻的认识。麦丽流血至死时,“她的脸上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心满意足的表情”[1],她摆脱了让自己备受煎熬的妻子身份,在恋人身份中获得精神上的安宁和愉悦。而弗兰克也回归儿子身份,决定在出狱后重回老家,看望母亲,承担作为儿子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作为瑞典移民的柏格森太太虽然一直对远离故乡、跟随柏格森来到内布拉斯加高原的遭际耿耿于怀,但她没有和其他移民一样在异国他乡遭遇故乡身份认同危机,而是始终不忘故乡,保持着原来的生活习惯,打鱼、做果酱、腌东西,致力于建构自己的故乡身份。亚历山德拉同样如此,她一直不忘自己的瑞典人身份,她决心送米丽钢琴的原因是米丽学会了弹柏格森过去常唱的一本古老的瑞典歌曲集。将李老太太接到家里住,整天听李老太太说家乡话,对亚历山德拉来说也是一种享受,故乡的一点一滴让她们找回故乡身份认同,获得精神上的归属感。
薇拉·凯瑟通过揭示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之间存在的生态问题,给人们敲响警钟。但是,薇拉·凯瑟没有停留在对问题的揭示上,而是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生态思考,呼吁人们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关系、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的社会伦理秩序以及自身明确而又稳固的伦理身份,指明走出生态危机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