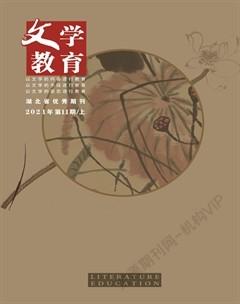宋初古文运动背景下柳开的文道观念
章炳煜
内容摘要:文与道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概念,唐宋时期对于“文与道”的辩论尤为突出,这同唐宋提倡文学复古的古文运动有莫大的联系。综合唐宋两代来看,“文与道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文以明道、文道合一、文必害道”i。其中,柳开作为宋初最早提倡从古风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首次提出了“文道合一”的思想ii。因此,本文旨在以柳开的文道观为切入点,细致考察其所谓的“文”与“道”以及“两者关系”,深入刻画宋代文道之间冲突加剧的趋势,并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柳开 文道关系 道学家 文道合一 以文承道
柳开(947-1000),宋大名人,原名肩愈,字绍先,后更名开,字仲涂,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为宋代倡导古文之第一人iii。并且,他在《补亡先生传》一文中也阐释了其改名的原因,即用以表达自己“开古圣贤之道,开今人之耳目”iv的决心。由此可以看出,柳开在宣扬复古思想上的积极态度。柳开作为宋代提倡古文运动的先驱,他的文道思想对后代文论家探讨“文与道”具有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宋代“道学家”的理论源头。然而纵观学界,目前对于柳开文道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其中绝大部分的论著并非专门讨论,而是在谈及唐宋古文运动等相关内容时顺带捎上几段,论述上往往比较宽泛、不成系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针对柳开的文道观念就没有详细的研究,例如: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胡杰的《柳开的圣人天命观与言道观述论》等v都有专门的去探讨柳开的文与道。不过,总览上述学者有关柳开文与道的细述,笔者发现他们对于柳开文道思想的阐释更多的是偏向于“道”,表现其重道、复古的一面,而对于他的“文”则是一笔带过。同时,关于柳开的文道观也多是从两者的关系着笔,而具体的“其文”、“其道”是什么却没有细说;且柳开首次提出文道合一的想法,文与道本应该是水乳交融、和谐共存的状态,然而事实则是文、道之间的冲突、对立更加强化,这种现象是极其吊诡,其成因也是值得我们去深入分析的。因此,笔者欲通过下文来详细论述柳开的“文是什么”、“道是什么”以及两者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在文道趋合的背景下造成文与道隔阂加剧的原因。
一.柳开的文与道
柳开在其《应责》一文中提到:“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vi。这表明了柳开的文、道思想都是来自于对孔、孟、杨、韩四人文道观念的承继,他的文统与道统来源相同,为其后来“文道合一”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难道柳开的文道观就是对孔、孟、杨、韩四人观点的机械复制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柳开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同时也进行了筛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道观。
1.柳开的“文”
在谈论柳开的文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孔子、孟子、杨雄、韩愈四人“文”的观念。孔子《论语·雍也》中写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vii这里的“文”是指广义上的文,即不限于文字、文采、文章典籍,还包括制度、礼仪、文化等一切关于人类社会的观点言论。孟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经常以孔子思想的继承者自居,他在承袭了孔子“文”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viii其后,杨雄在谈论“文”的时候说到:“文以见乎质,辞以瞩乎情”ix以及“圣人文质者也:车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声音以扬之”x。由上观之,孔、孟、杨三人在“文”的观念上其实是一脉相承,他们的“文”都是独立存在的,与“道”相分离,但是对于“文”的态度上却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两汉以后魏晋时期,文风变得浮靡绮丽,到了中唐时期骈文兴盛,由于文体本身属性的问题,骈文成为贵族阶级的专属品。韩愈等一批庶人身份出身的士大夫对此感到不满,于是发起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倡导遵从古文、古道。同时,安史之乱以降,地方藩镇势力日益增强,中央权力被迫压缩。在这一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儒家思想中强调上下秩序的理念成为维护中央政权的重要工具。由此,韩愈提出了他的文统观点,即:“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騒》,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xi。柳开在“文”上的思想综合了上述四人的观点,其中以韩愈的“文”为主。此外,柳开在传承“文统”思想的过程中也进行了发展,在《应责》中提到“古文者,非若辞澁言苦使人难诵读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xii,表现了其“以文传道”、主张“文从字顺”的态度;并且相比韩愈而言,柳开的文与道同宗同源,文与道合二为一,这也侧面反映了“文”的独立地位的消失。
2.柳开的“道”
柳开的道,即韩愈所言的道统,也就是儒道。“道”这个观念,我们一般会认为是专属于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儒家也讲道,不过儒家的“道”与道家的“道”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例如,在《论语·公冶长》中提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xiii再如,《论语·述而》中写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xiv由此看来,孔子所谈论的“道”是人道,往往与人类社会相关。而道“道”则不同,道“道”注重研究的是抽象的道,是一种外化于物的无形的原则、规律。
柳开《应责》开篇通过别人的质疑,来表达自己“好古文与古人之道”xv的决心。其后,他又反问到:“道之不足,身之足,则孰与足”xvi,认为道是构建人的修养的关键之物,体现了他重道的思想。同时,他在《名系》中还提到:“人于道罕得同日而为者,必有先后耳,先者知之,告于后者古人之道也。圣人作经籍以至书传,记录在于简册,皆告于后之人者也。同其时,见其人,言其言,亦告之者也,知而不告之,非君子也,非古人之道也。”xvii这也就是说,道很少有被同日悟得,一定有先后的顺序。先知道的人一定会告知后人,历代的圣贤制经做传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如果得道后却不传授给后世的人知道,这不是君子应该做的,也不是古人所倡导的道。所以,在柳开看来,“道”于今之世而言很重要,将道传扬给今之世亦很重要。
那么柳开的道到底是什么呢?“古之贤者同其道,愚者亦同其道,非其称名同于身也”,柳开在《名系》中用尧、舜、禹作例,表明了他们名字不同但是所宣扬的“道”相同,从而证明了古之贤者的“道”的统一性。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道”是儒道,对道统一性的理解要以儒家思想为基本点。柳开倡导古圣贤之道,他在《应责》篇中曾言:“俾知圣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长,孝乎父,慈乎子,大道斯道,非吾一人之私也,天下之至公者也”xviii。因此,柳开的道是尊君敬长、讲求长幼上下顺序的儒家道德伦理。
3.柳开的“文道关系论”
承上,柳开所倡导的古文、古道也就是他的文统与道统思想,它们的理论渊源都来自于孔、孟、杨、韩四人,所以构筑了他“文道合一”的理念。正如柳开《应责》中说的:“欲行古人之道,反类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可乎哉?”xix这也就是指古道必须用古文来传,如果用今文来承载,就如同骑马在海中游泳,是不可行的。同时,柳开在《名系》一文中提到,效法古之圣贤的根本点在于学习古代贤人的道,只有真正把握了他们的道,才算真正的效法贤人;否则,单纯的仿效贤人之名,就犹如东施效颦,没有实质上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柳开“以道为本”的思想。
重道思想并非到了柳开才开始,反观其重道思想的根源,可以发现这种观念正是来自于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他们虽然都重视道,但是他们也并没有轻视文。例如:杨雄在“明道”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重质尚用,反对过度文饰的观点”xx,然而他在《法言·寡见》中又谈到:“言不文,典谟不作经”xxi,表明杨雄反对过度文饰,却没有轻视“文”本身的作用。再如:韩愈在其《题欧阳生哀辞后》以及《上兵部李侍郎书》中写到自己对文学的喜爱,并且经常诵读古代的经、史之作,来探究古文之特征,这也说明了韩愈“文道并重”的思想。
孔、孟、杨、韩四位大家的文与道还处于二分的状态,“文”、“道”相互独立,两者之间自然会存在对立冲突。其后,柳开在四位大家的基础上将文与道合二为一,本来以为这样能够促成文与道之间的平衡局面。然而,实际情况却令人意外,“文”在同“道”混合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文与道之间的矛盾激化。恰如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中最后写到的,“文章为道之筌也”xxii,这里的“筌”是指古代一种捕鱼的竹器。由此可以看出,在柳开的文道观念中,道是根本,文是传道的工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笔者认为前人称柳开的文道是“合一”的关系或许有些不妥,因为如果是“合一”的话,那么文与道之间应当尚存相互的独立性才对,而事实却是文失去了独立性成为了道的附庸工具。
二.原因及影响
诚如上文所言,柳开文与道合一后出现了两者矛盾加剧的吊诡情形,这种情形产生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本身可以视为是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不同文论家的文学批评思想势必会受到所处时代的文学风气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因此,下文我将从宋初的文风和历史背景出发,详细阐释造成上述吊诡现象的原因;同时,进一步讲述柳开的这种文道观念对后世的辐射作用。
1.原因
唐代,佛老思想兴盛,儒学式微。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大不如前,地方藩镇势力渐强,各地军阀混战,中央权力被大幅削弱。这种情况下,韩愈、柳宗元等人看到儒家思想中“上下有序”的观念,于是主张恢复儒学,排斥佛老。反映在文学上,即是发起了著名的“古文运动”,提倡遵循古文、古道。然而,尽管韩愈、柳宗元针对当时的社会思潮做出了反抗,但是仍然未能将唐朝从灭国的边缘拉回来。唐朝灭亡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五代时期。这一时期,文风上依然是延续中唐以来的文学潮流,崇尚骈文写作,风格绮靡、华而不实。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五代时期的各国政权的存续时间基本上都很短。后来,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了各国,建立了宋朝。宋太祖吸取了前代的教训,为了防止地方藩镇割据现象的再次出现,提出了“重文轻武”的政策,这也就造就了宋代文坛的活跃氛围。由此,这一时期文伦家的思想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宋初,以柳开、王禹偁为代表的一批文论家,在考究前代文风时,发现前代绮丽靡艷的文学风潮是导致唐朝和五代各国灭亡的重要因素。于是,他们继承了中唐以来的古文运动的思想,强调古文、古道。并且,他们认为前代的灭亡与文的过分华丽、道的缺失有莫大的关系,尤其是道的缺失。因此,宋初的一批文论家开始重视道的作用,突出道在文中的地位,不过他们也并没有全面抛弃文,这是同后世道学家的“文必害道”的观点相区分的。所以,在上述思想的作用下,虽然“文”与“道”合二为一了,但是这种合二为一的进程并非是兩者的自主结合,而是在“道”的强化过程中,“文”被迫去依附于“道”,成为承载“道”的工具。
2.影响
柳开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一生倡导古文、古道,原名肩愈,意思是要向韩愈学习。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柳开从因循韩愈的文道思想转向自主发散出新的文道观念,遂更名为开,有开宋代“道学”之风尚的意味。相比韩愈而言,柳开对于“文”的态度明显变弱,并且这种弱化已经呈现出轻“文”的态势。与此同时,“道”在两者关系中被突出强调,“道”成为“文道关系”中的主体,而“文”则成为附着物。
柳开的重道思想对整个宋代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道学的发展上,可以说柳开是宋代道学的滥觞。其后的欧阳修在柳开的基础上,再度强化了对“道”的重视度,提出了“道”是作为“文”的先决条件而存在的。周敦颐作为宋代道学派的开山鼻祖,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念。这之后,周敦颐的弟子,程颐和程颢彻底抹杀了“文”的作用,阐发了“文必害道”的道学思想。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重道轻文思想并非贯穿了整个宋代。以苏轼、江西诗派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和文论家,仍然看重“文”的作用,对文辞展开了细致的研究与实验。不过,总览整个宋代,可以看出“道”的地位是显著提高的。
文与道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最基本、最本源的概念,其它的文论概念,诸如情、理、气、性、自然等都会与文、道产生或多或少的纠葛,所以历代文论家对文、道两者的讨论甚多。唐宋时期,受到独特的时代背景的影响,文道关系的辩论尤为精彩。柳开作为宋初重道思想的代表人物,其观点对后世具有广泛影响。然而,学界对于柳开的研究似乎不甚深入。因此,笔者欲通过上文,系统的梳理一下柳开的“文道观”,并对前人用“文道合一”来总结柳开文统、道统趋合现象的做法发表自己的一点愚见。当然,对于柳开的研究尚未穷尽,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挖掘。
参考文献
[1]胡杰,《柳开的圣人天命观与言道观述论》,《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2020年01期),页37-41.
[2]馮仲平,《唐宋的文道论》,《东方丛刊》[J],(1998年第3辑总第二十五辑),页227.
[3]查洪德,《文道合一:一个伪命题》,《文化周刊:国学》[J],(2012年6月,第015版),页1-3.
[4]张兴武,《宋初百年文道传统的缺失与修复》[A],(杭州: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2005年),页173-186.
[5]郭预衡,《北宋文章的两个特征》,《社会科学战线》[J],(1985年第3期).
[6]沈松勤,《从南北对峙到南北融合——宋初百年文坛演变历程》,《文学评论》[J],(2008年第4期).
[7]王运熙、顾易生编,《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9]蒋凡、顾易生着,《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0]成复旺、黄保真、蔡钟翔着,《中国文学理论史(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页166-212、页281-538.
[11]周勛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张撝之,《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注 释
i冯仲平,《唐宋的文道论》,《东方丛刊》,(1998年第3辑 总第二十五辑),页221
ii冯仲平,《唐宋的文道论》,《东方丛刊》,(1998年第3辑总第二十五辑),页227
iii张撝之,《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1708
iv原文:遂易名曰开,字曰仲涂,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摘自:宋.柳开,《补亡先生传》,《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河东先生集十六卷》,(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页13)
v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王运熙、顾易生编,《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24-29;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页161-162;胡杰,《柳开的圣人天命观与言道观述论》,《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01期),页37-41;冯仲平,《唐宋的文道论》,《东方丛刊》,(1998年第3辑总第二十五辑),页227;查洪德,《文道合一:一个伪命题》,《文化周刊:国学》,(2012年6月,第015版),页1-3;张兴武,《宋初百年文道传统的缺失与修复》,(杭州: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2005年),页173-186等
vi宋.柳开,应责,《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河东先生集十六卷》,(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页10
vii春秋.孔子,《论语·雍也》,《论语集注(卷三)》,收录于:宋元人注,《四书五经》,(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页24
viii.战国.孟子,《孟子·万章上》,《孟子集注(卷九)》,收录于:宋元人注,《四书五经》,(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页71
ix.汉.杨雄,《太玄·玄莹》,收录于:宋.司马光,《集注太玄经(第二册)》,(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卷七,十
x汉.杨雄,《法言·先知》,收录于:贾谊,《杨子法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20
xi唐.韩愈,《进学解》,《韩昌黎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四版),页77-78
xii宋.柳开,应责,《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河东先生集十六卷》,(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页10
xiii春秋.孔子,《论语·公治长》,《论语集注(卷三)》,收录于:宋元人注,《四书五经》,(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页19
xiv春秋.孔子,《论语·述而》,《论语集注(卷四)》,收录于:宋元人注,《四书五经》,(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页27
xv宋.柳开,应责,《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河东先生集十六卷》,(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页9
xvi宋.柳开,应责,《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河东先生集十六卷》,(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页9
xvii宋.柳开,《名系《,《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河东先生集十六卷》,(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页6
xviii宋.柳开,应责,《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河东先生集十六卷》,(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页10
xix宋.柳开,应责,《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河东先生集十六卷(卷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页10
xx蒋凡、顾易生着,《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537
xxi汉.杨雄,《法言·寡见》,收录于:贾谊,《杨子法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16
xxii宋.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河东先生集十六卷》,(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页31
(作者单位: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