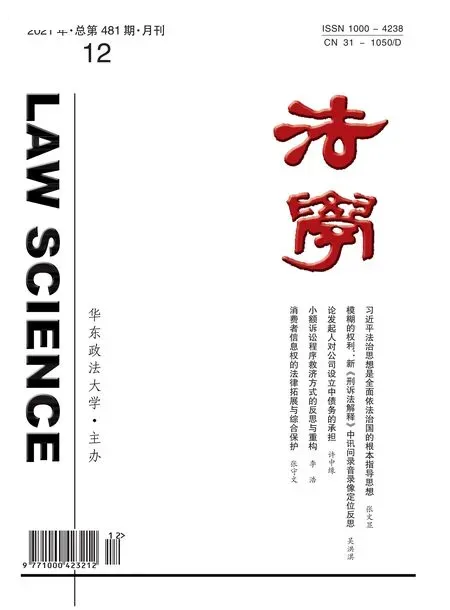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合法性考辨及因应
●陈红彦
2021年3月10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与WTO相符的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决议》(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March 2021 Towards a WTO-compatible EU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以下简称CBAM决议),〔1〕European Parliament, P9_TA(2021)0071-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March 2021 Towards a WTO-compatible EU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2020/2043(INI))(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BAM Resolution).原则上同意在欧盟建立碳边境调整机制。随后的7月1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碳边境调整机制条例(建议稿)》(以下简称CBAM建议稿),〔2〕欧盟委员会认为,采用条例的形式可大大增强规则适用的直接性、统一性和连续性。See European Commission, COM(2021)564-final-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Establishing a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BAM Proposal), p. 5.由此,近年来持续受到舆论关注的欧盟“碳关税”立法进入了快车道。然而,作为一种基于环境诉求的单边贸易措施,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的合法性取决于与全球气候法治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第二大经济体及欧盟最主要的经贸伙伴,CBAM的最终施行无疑事关中国的切身利益,必须要谨慎对待和积极应对。
一、欧盟建立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因由及要点
(一)碳边境调整机制的立法动机
解读欧洲议会CBAM决议和欧盟委员会CBAM建议稿不难发现,欧盟建立碳边境调整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应对新形势下削减直至取消欧盟碳排放交易制度中的免费配额问题,这是一直困扰欧盟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老大难问题。
2003年欧盟制定《碳排放交易指令》,2005年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以下简称欧盟ETS),现已实施到第四阶段(2021-2030)。根据制度安排,欧盟ETS运用总量控制和交易手段来管控受监管企业的碳排放,后者需要在配额范围内进行碳排放,一旦超出配额,只能通过市场交易向配额有盈余的主体购买。尽管《碳排放交易指令》要求企业初始配额的获得应以拍卖取得为原则、免费获取为例外,但在ETS实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2005-2012年期间),欧盟几乎是以完全免费的方式发放初始配额的,此举不仅难以有效促进受监管企业减少碳排放,甚至还会让不少企业因此获得意外之财,〔3〕根据欧盟ETS,如果一个部门很难通过提价向下游传导其承担的ETS成本,那么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弱,就需要通过免费配额加以保护。然在实践中,某些已经获得免费配额的部门却依然以ETS为借口而提价,这部分获利就被称为“意外之财”。导致质疑与批评声不断。〔4〕See European Court of Auditors, Special Report: The EU’s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Free Allocation of Allowances Need Better Targeting, European Union, 2020, p. 19-27.
实施免费配额的初衷,一在减少制度实施初期的政治阻力,二在解决碳泄漏问题。到今天,目的只剩下后者。欧盟认为,在欧盟和其他市场所在地的气候目标、环境标准、气候政策不一致的情况下,企业为了利用欧盟境外更宽松的监管标准,而将碳密集型生产和服务从欧盟迁出,或者欧盟的产品被碳密集程度更高的进口产品所替代的做法属于碳泄漏。〔5〕See CBAM Proposal, p. 2.为了应对这一风险,欧盟ETS为碳泄漏部门量身打造了一套特殊规则,即根据“碳泄漏清单”确定的碳泄漏部门,将在免费配额的发放方面受到专门照顾;未进入“碳泄漏清单”的其他部门,则须加快对其免费配额的改革。
为了落实2016年11月4日起正式实施的《巴黎协定》中确立的自主贡献目标,欧盟修改了ETS第四阶段的免费配额规则。依据新规,不受碳泄漏影响部门的免费配额将逐步削减,至2030年完全取消;遭受碳泄漏影响的部门,则加快免费配额的改革。2018年是改革完成的最新时间,但欧洲审计院的统计数据显示,改革的力度十分有限。详言之,改革后第四阶段虽然遭受碳泄漏风险的工业部门的数量会显著减少,即从第三阶段第二期(2015-2020年)的153个部门减少到第四期的50个部门,但是这50个部门的工业排放在全部工业排放中的占比只是从改革前(2015-2020年)的98%降至改革后的94%,未见明显降低。〔6〕同前注〔4〕,第29页。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工业排放依然受到碳泄漏制度的庇护,对清单内的这50个部门来说,只要是达到欧盟实施排放产品基准的产品,依然可获得100%的免费配额。〔7〕See Directive (EU) 2018/41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4 March 2018 Amending Directive 2003/87/EC to Enhance Cost-eあective Emission Reductions and Low-carbon Investments, and Decision (EU) 2015/1814, Article 10a and 10b.可见,改革中的免费配额问题依然突出。
随着传统经济领域竞争力的进一步衰退,欧盟内部逐渐形成了以绿色经济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的共识。2019年《欧洲绿色协议》 通过,从经济、能源、建筑、交通、农业等多角度倒逼欧洲的绿色转型。根据该协议,2030年要在基准年的基础上将削减温室气体的目标从之前的40%提高至55%,2050年实现碳中和。〔8〕See European Commission, COM(2019) 640 final-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European Council,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 The European Green Deal.其中2030年目标已被更新为欧盟的自主贡献目标,成为其在《巴黎协定》下有约束力的承诺;而2050年的碳中和目标也将被纳入《欧盟气候法》而具有约束力。
面对新一轮的改革压力,免费配额问题再一次凸显。欧盟认为,当受碳泄漏威胁的部门不能再被免费配额制度保护时,就必须要有其他制度作为填补,而CBAM就是这个制度。如果说免费配额意在为欧盟企业减负,那么CBAM则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增加欧盟外企业的排碳成本,来拉平境内外企业的碳定价成本,用以避免碳泄漏。对于这一立法初衷,CBAM建议稿第1条作了明确表态:“该机制通过对进口产品适用与欧盟ETS相当的一套规则,构成欧盟ETS的重要补充。它将逐步取代欧盟ETS中的免费配额制度,防止碳泄漏。”〔9〕See CBAM Proposal, Article 1.
(二) CBAM建议稿中的几个关注点
CBAM建议稿共11章36条,另有5个附件,涵摄如下值得关注并需要作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1.适用范围
根据建议稿第2条的规定,该条例仅适用于从第三国进口的清单内产品。该清单被规定在条例的附件1中,目前的清单内产品仅包括水泥(含4个子类别)、电力、农药(含5个子类别)、钢铁(含12个子类别)和铝制品(含8个子类别)这五大类别。受监管的温室气体主要为二氧化碳,同时,对农药类产品还包括氧化亚氮,对铝制品还包括全氟化碳。与CBAM决议相比,所确立的总体调整范围明显偏小,没有囊括炼油、造纸、玻璃、化工等部门。〔10〕See CBAM Resolution, para. 12.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解释,适用范围的选择考虑了不同部门碳泄漏的风险,风险越高,越应该纳入适用范围。同时,还纳入了实施的复杂性及监管成本的考量。比如,由于目前的技术很难对有机化工、炼油产品准确界定其排放含量,所以暂时不纳入CBAM的适用范围。〔11〕See CBAM Proposal, p. 20, paras. 32-33.后续会逐步扩大适用范围,达到与欧盟ETS的覆盖范围相当。
在适用地域上,附件2明确排除了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等四国。前三个国家都属于欧洲经济区,也是欧盟ETS目前所覆盖的范围;而瑞士国内的碳交易市场已在2020年正式与欧盟ETS连接,〔12〕See European Commission,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U ETS),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_en, last visit on August 1, 2021.所以四国的企业已经承担了与欧盟ETS相一致的碳定价成本,故而被排除适用。按照欧盟委员会的思路,如果今后有其他国家的碳定价制度与欧盟ETS发生连接,那么也可以纳入附件2的适用范围,从而免于适用CBAM。〔13〕See CBAM Proposal, p.18, para.15.
2. 操作流程
根据建议稿的要求,条例的执行由每个欧盟成员国指定专门的主管机关负责。〔14〕See CBAM Proposal, Article 11.1.一般而言,涉及纳入清单管理的产品,进口商需在产品进口前向企业所在地的CBAM主管机关申请授权,获得授权后,才能够进口。〔15〕See CBAM Proposal, Article 5.1.作为申报人,获得授权的进口商应当记录和保留有关进口产品数量、排放含量等相关文件,以留待查验。每年的5月31日前,进口商需向主管机关提交上一年的CBAM申报书,主要涉及前一年度清单内进口产品的数量、这些产品的排放含量、根据排放含量确定的CBAM进口许可的数量等内容。〔16〕See CBAM Proposal, Article 6.1 and 6.2.尽管建议稿允许进口商在任何时间购买进口许可备用,但仍须注意两点:一是每年5月31日前自有账户上必须有足够支付上一年度所有进口产品排放含量所需的进口许可;二是确保每季度末自有账户上的进口许可数量要达到按照默认值计算的自年初开始全部进口产品排放含量所需的进口许可的80%。〔17〕See CBAM Proposal, Article 22.2.对于每年多余的进口许可,条例允许进口商按原价向主管机关提出回购申请,但最多只限于其所购进口许可总量的三分之一。〔18〕See CBAM Proposal, Article 23.未经许可进口清单内产品的,或者在申报中虚假陈述的,或者未在规定期限足额购买进口许可的,进口商都将面临一定的处罚。
3. 确定进口许可的具体方法
与欧盟ETS中的配额相类似,建议稿中确立的进口许可属于产品所需承担的碳定价成本。进口商最终缴纳的进口许可成本由产品的排放含量、单位进口许可的价格两个变量决定。为此,建议稿附件3规定了产品排放含量的一整套计算方法。从总体看,只有直接排放才会被计算在内,〔19〕直接排放是指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商可以直接控制的排放。与之对应的是间接排放,指的是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因用电、加热和制冷而间接产生的排放。See CBAM Proposal, Article 3.15 and 3.28.之前CBAM决议有关同时纳入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建议,〔20〕See CBAM Resolution, para. 12.并未被建议稿所采纳。此外,建议稿还对电力产品和其他产品排放含量的计算方法给予了差异化处理,即电力产品原则上采用附件3规定的默认值来确定,除非进口商主动提出申请才会据实计算其排放含量;其他产品则正好相反,原则上应当根据附件3的方法确认其真实的排放含量,只有当真实的排放含量无法确定时,才会考虑使用附件中的默认值。〔21〕See CBAM Proposal, Article 7.2, Article 7.3.
至于排放许可的价格,则由欧盟委员会依据欧盟ETS配额拍卖收盘价的每周均价确定。〔22〕See CBAM Proposal, Article 21.1.另外,结合建议稿第2条第12段和第9条的规定看,如果进口产品在其产地已经承担了碳定价成本,包括碳税和排放贸易下的排放配额,那么在提供一系列的证明材料,包括没有取得出口返还或其他形式的出口补偿后可以主张CBAM的扣减。
由是可见,虽然CBAM的进口许可在总体上与欧盟ETS配额高度关联,但两者在价格的计算、可否交易及时间的有效性等方面,依然存在明显差异,这主要是基于兼顾CBAM作为防止碳泄漏的制度工具属性、灵活性和运行成本等的多重考虑。〔23〕See CBAM Proposal, p.18, para. 20.条例自2023年1月1日开始实施,2023年至2025年是其过渡期,在该期间进口商主要承担报告义务,无需购买进口许可;过渡期结束后,从2026年1月1日开始,所有规定将正式生效。〔24〕See CBAM Proposal, Article 36.
二、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与全球气候法治的相符性
欧盟实施CBAM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逐渐替代免费配额制度,以阻止碳泄漏。其认为,CBAM将使欧盟境内和境外的产品处于相同的碳价格水平,由此可确保欧盟的气候目标不会因为企业向其他地区转移生产而受到减损,这有助于《巴黎协定》控温目标的实现。〔25〕See CBAM Proposal, Explanatory Memorandum, p. 1.
然而,从气候变化法的角度观察,欧盟的CBAM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欧盟试图以单边措施矫正各国之间差异化的气候政策,这违反了现行的全球气候法治。欧盟实施CBAM的逻辑起点是各国的气候目标、环境标准、气候政策的不一致,〔26〕See CBAM Proposal, Explanatory Memorandum, p. 2.其行为的实质就是要推翻这些不一致,力图实现整齐划一。然而,作为全球气候法治的两大基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从未为各国设定统一的气候目标、环境标准和气候政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3.1条规定:“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各自能力原则因此成了全球气候法治的基本原则。《巴黎协定》不仅再次重申了这两个原则,而且通过国家自主贡献的制度设计,确认了每一个缔约国有权个性化地承担《巴黎协定》的义务。也就是说,现有的国际气候条约从未为缔约方设定统一的环境标准和气候政策,各国有权利根据本国实际设定具体的减排目标,采取适当的气候政策。
其二,欧盟CBAM偷偷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概念转换,进一步带来了合理性危机。“碳泄漏”是欧盟实施CBAM的主要原因,“碳泄漏”概念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 2007 年的评估报告中提出的,指的是没有采取国内减排行动的国家增加的碳排放与采取国内减排行动的国家减少的碳排放的比值,〔27〕See IPCC, 2007: Climate Change 2007: Mitigation.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B. Metz, O. R. Davidson, P.R. Bosch, R. Dave, L.A. Meyer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and New York, NY, USA, p. 665.其所强调的是因不同国家减排行动不一致而可能带来的碳排放在国际间的转移。然而,欧盟CBAM则将上述“不同国家减排行动的不一致”偷换成了“不同国家碳定价的不一致”,在其看来,CBAM可以使欧盟境内与境外的产品处于相同的碳价格水平,如此可确保企业不会因减排成本的差异而进行产业转移。
事实上,企业承担的减排成本绝非只简单地通过碳价格体现出来;各国的减排行动也决不仅仅是设立碳定价机制。在促进低碳转型的过程中,除了要依靠技术手段外,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也为各国所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具有强制性特征,如各种排放标准、技术要求等,至今依然是各国治理环境污染的最主要手段。即便是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如美国,在碳减排领域,目前也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比如,在对气候问题相对友好的奥巴马政府时期,曾力推在全美实施碳排放交易制度,但受两党政治的影响而流产。〔28〕参见高翔、牛晨:《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进展及启示》,载《美国研究》2010年第3期,第39-51页。随后又力推《总统气候行动计划》,强调通过行政手段大规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便绕开当时由共和党占主导的国会的牵制。〔29〕参见温宪:《奥巴马宣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新举措》,载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626/c57507-21983934.html,2021年8月5日访问。现任总统拜登从竞选开始就向选民承诺了所谓的“拜登计划”,表示从上任起,就动用一切行政手段促进碳减排的最大化。比如,通过行政手段对油气的甲烷排放进行限制;利用联邦政府采购体系促进清洁能源和零排放;通过更严格的新能源经济标准,促进运输业的减排;制定更严格的建筑能效标准;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运营和供应链中的气候风险和温室减排等。〔30〕See The Biden Planfora Clean Energy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https://joebiden.com/climate-plan/, last visit on August 1, 2021.经济手段则主要通过“污染者付费”原则,将污染成本通过某种形式转化为价格,并内化于产品或服务中。在碳减排领域,经济手段主要包括碳税和碳排放交易两种主要形式。
从实际效果观察,无论是行政手段还是经济手段,都会构成市场主体的成本,并不是说,只有直接以价格形式表达的经济手段才构成企业的减排成本,而不直接以价格表达的行政手段不构成企业的减排成本。比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曾宣称,通过废除奥巴马政府时期推动的主要行政减排措施《清洁电力计划》,到2030年相关市场主体将会因此节省因执行规定而额外产生的330亿美元的遵从成本。〔31〕参见林小春:《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将废除〈清洁电力计划〉》,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0/11/c_1121786263.htm,2021年8月5日访问。于政府而言,究竟是采用行政手段还是经济手段,是各国政府的选择,当下并不存在一个国际条约限制政府的这一选择权。相反,《巴黎协定》第6条第8款明确肯定了各国采用非市场化的合作机制来促进各国实现国家的自主贡献。这样看来,出口国完全可以自主决定采用何种手段来促进减排,即便出口国没有采用市场化的碳定价手段,也决不意味出口国的企业不承担碳减排成本,也决不必然意味各国减排行动的实质差异。可以说,欧盟以境内外产品处于不同的碳价格水平为由主张碳泄漏,是一次精致利己的概念偷换。
三、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与WTO的相符性考察
近年来,有关“碳关税”的报道一直不曾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32〕比如,2007年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称将努力推动在欧盟边境征收碳关税,以免受到环境倾销的不利影响。又如,2009年美国众议院审议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2009》,宣称自2025年开始实施碳关税,该法案虽后来未能在参议院通过,但还是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震动。再如,2012年欧盟修改ETS,计划对进出和过境的国际航班征收碳关税,招致各国批评,但即便如此,欧盟一直未予放弃,最终倒逼国际社会于2016年达成了全球第一个行业市场减排机制——国际航空碳抵消与减排计划。此番欧盟的CBAM是对此的又一次重要尝试。学界更多地是将碳关税视为一种单边贸易手段,关注其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合法性问题。对此,欧盟显然是心知肚明的。正因为如此,欧洲议会直接使用了《与WTO相符的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作为决议的标题,并在总共49段正文文本中使用了15段来阐明CBAM与WTO相符的重要性和关键点。〔33〕See CBAM Resolution, paras. 7-21.而在7月的CBAM建议稿的解释性备忘录中,也专门表达了CBAM与WTO相符的观点。〔34〕See CBAM Proposal, Explanatory Memorandum, p. 3.客观来看,目前CBAM建议稿的规则设计,欧盟委员会确实在此方面做出了细致的安排,但即便如此,仍难掩其与WTO不符的疑虑。
(一)针对与WTO的关系,CBAM建议稿所作的特别考量
欧盟非常清楚,作为一种在进出口环节创设的单边机制,其主要的国际法约束来自WTO。而从国内外学者有关碳关税的先期研究成果看,单边CBAM对WTO的胜算主要来自WTO第20条有关环境保护例外的规定。所以,只有强调CBAM的环境保护属性,才有可能扫除实施的法律障碍。
对于此,欧盟方面至少做了如下的努力:一是,将CBAM嵌入欧盟一揽子气候措施之内,强化其环境保护的属性。从CBAM决议到CBAM建议稿,欧盟反复强调了CBAM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而不是单边贸易保护的手段。其坚称CBAM的出台在国际层面有两个主要的支撑——《巴黎协定》和联合国环境署的《排放差距报告2019》(该报告敦促G20国家为实现《巴黎协定》1.5度的控温目标而采取更多的有效措施);〔35〕Se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19), Emissions Gap Report 2019, UNEP, Nairobi.在欧盟层面也有两个主要的支撑——《欧洲绿色协议》和欧洲审计院的《欧盟排放贸易:免费配额需要更好的定位》,前者全面强化了欧盟在《巴黎协定》下的自主贡献目标,提出了2050年实现碳中和。为此还制定了一揽子计划,其中立法层面的改革主要包括制定并实施欧盟的《气候变化法》、修改《能源税指令》、加快对欧盟ETS免费配额的改革及实施CBAM,而欧洲审计院的上述报告专门针对了欧盟ETS免费配额改革的问题,并由此进一步论证了引入CBAM的合理性。上述四个文件构成了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在决议和建议稿中所宣称的CBAM出台的主要背景。〔36〕See CBAM Resolution, Preamble; CBAM Proposal, Explanatory Memorandum.相比于2012年欧盟强推航空领域的碳关税,此次推出的CBAM可谓是布局周延,心思缜密。其反反复复地向国际社会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欧盟是《巴黎协定》最积极的践行者,是大国中最负责任的气候引领者。欧盟CBAM的出台正是对上述角色的再一次证明和诠释,只和气候变化议题有关,与贸易保护无关。
二是,CBAM的设计与欧盟ETS更加协调,体现出从生产端到消费端全方位地促进减排的整体性原则。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CBAM其实存在很多种可能性。西方经济学者曾经认为,相比于承担了碳定价成本的进口国产品而言,未承担碳定价成本的第三国产品构成了倾销产品或者受补贴产品,〔37〕See Joseph Stiglitz, A New Agenda for Global Warming, Economists’ Voice, July 2006, http://www.bepress.com/cgi/submit.cgi?context=ev, last visit on August 6, 2021.因此可以将CBAM直接设计成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这一方案显然未被欧盟采纳,因为它与WTO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规则相去甚远。〔38〕参见陈红彦:《气候变化制度引入边境措施的现实困境及应对》,载《法学》2015年第1期,第27-28页。之前更多的学者建议将欧盟ETS直接扩大适用于进口产品,并且认为这是WTO所允许的边境调整机制,〔39〕See R. Ismer and K. Neuhoあ, Border Tax Adjustments: A Feasible Way to Address Non-Participation in Emission Trading,Cambridge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CMI Working Paper 36, 2004); Charles E. McLure, Jr., The GATT-Legality of Border Adjustments for Carbon Taxes and the Cost of Emissions Permits: A Riddle, Wrapped in a Mystery, Inside an Enigma, Florida Tax Review, Vol.11, No.4,2011.其背后所依据的逻辑是,欧盟ETS对境内产品的收费在本质上和对境内产品的征税无差别,而且构成一种流转税,而非所得税。而WTO允许成员国对流转税进行边境税收调整,以体现流转税的目的地征税原则。但是,这种设计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欧盟ETS所产生的“费”是否构成WTO边境调整制度所允许的“税”?〔40〕参见陈红彦:《碳关税的合法性分析——以边境税收调整的适格性为视角》,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4期,第90-91页。欧盟CBAM的设计虽与欧盟ETS保持了高度的关联性,但其实是一套专门适用于进口产品的制度。这种制度设计不必再纠缠于CBAM是否构成“税”这一先决性问题。依据欧盟的逻辑,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欧盟应该勇做标准的制定者,〔41〕See CBAM Resolution, para. N.要强调消费者在能源转型中的中心作用。〔42〕See CBAM Resolution, para. 4.通过对境内生产的产品适用ETS,对进口产品适用CBAM,可以同时从生产端和消费端促进减排,这将进一步落实欧盟的气候义务,也是《巴黎协定》所倡导的减排方式。〔43〕《巴黎协定》前言中写道:“又认识到在发达国家缔约方带头下的可持续生活方式以及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对应对气候变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是,CBAM建议稿中未规定出口返还的问题,这将进一步强化该制度的环境保护特性。欧洲议会在CBAM决议中建议欧盟委员会为了保护欧洲企业竞争力而考虑出口税费的返还,但必须充分阐述其对气候的积极影响以及与WTO的相符性。〔44〕See CBAM Resolution, para. 29.显然,欧盟委员会目前暂未找到一个可以兼顾企业竞争力、减排及WTO规则的税费返还方案。尽管在出口环节返还欧盟企业已经承担的ETS成本的确有利于提升这些出口产品在第三国的价格竞争力,但这明显与欧盟的气候义务和WTO义务产生矛盾。
从气候义务的角度看,欧盟有义务促进境内的生产和消费环节减少碳排放。因此,无论产品是否出口,只要它的生产性排放达到了欧盟ETS的适用标准,就应该承担碳定价成本。出口退费将使得一个气候制度瞬间跌落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从与WTO的相符性角度看,尽管WTO允许的边境税收调整包含了进口征税和出口退税两个环节,因为它们都符合间接税的目的地征税原则,但显然WTO所允许的边境税收调整并非欧盟所设计的CBAM,理由是WTO所允许的边境调整只针对间接税,WTO规则无非是再一次确认间接税的目的地征税原则这一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而欧盟的CBAM显然不具有这种特质,它并非欧盟ETS制度的自然延伸。退一步说,即便它构成欧盟ETS的制度内涵,但欧盟ETS本身是否能构成针对企业的间接税,也是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欧盟委员会显然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因此选择不纳入出口返还的规定,这反倒进一步增强了CBAM的环境特性。
除了刻意强调CBAM的环境特性外,在具体规则的设计方面,CBAM建议稿也尽可能地符合WTO的要求,尤其强调与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契合。比如,在CBAM最初的6种设计方案中,存在对进口产品的排放含量是以默认值为基础还是以实际值为基础的讨论,最终选择了以实际排放为基础的方案,〔45〕See CBAM Proposal, p. 8-10.这当然是有遵守WTO非歧视原则的考量;在进口许可价格的确定问题上,CBAM坚持与欧盟ETS的配额拍卖价格相关联,以每周收盘的均价作为定价依据;同时,针对2026年CBAM正式实施后欧盟ETS可能依然存在对某些部门的免费配额的问题,建议稿专设第9章对此作出了规定,即进口商提交的许可应该根据欧盟ETS有关免费配额的规定作出对应性的扣除。这些规定都意在保证进口产品的待遇不低于欧盟境内的产品。
(二)CBAM建议稿存在与WTO不符的疑虑
WTO副总干事让-马里•波冈在出席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有关CBAM的听证会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WTO并不阻止成员国采取卓有抱负的环境政策,只要它不构成不合理的歧视或者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46〕See WTO, DDG Paugam: WTO rules no barrier to ambitious environmental policies, September 16, 2021,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ddgjp_16sep21_e.htm, last visit on Oct. 6, 2021.然而,欧盟CBAM恰恰在上述两个方面,依然面临重重疑虑。
1. 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
承前所述,CBAM建议稿非常关注与非歧视原则的契合性,并为此做出了努力。然而,在最根本的矛盾即对“同类产品”的界定问题上,CBAM建议稿依然面临巨大挑战。GATT第1条第1款和第3条第2款分别规定了针对“同类产品”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要求进口国在不同出口国的“同类产品”之间,以及与本国的“同类产品”之间遵循非歧视规则。从GATT1947对第3条第2款的注释和目前的WTO争端解决实践看,是否构成“同类产品”,主要关注产品本身是否具有竞争或替代的关系。如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Processing & Product Method, PPM)不一致,并不会导致最终产品本身呈现差异,即所谓的与产品无关的PPMs,那么这种差异不会影响“同类产品”的判断。这种规则和判例的现状将会陷CBAM于困境之中,因为CBAM强调的恰恰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足迹这种难以对产品本身产生影响的因素。换言之,依GATT的规定,碳足迹不同的产品是同类产品,它们之间应保持相同的待遇;而CBAM恰恰要给予它们不同的待遇,碳足迹高的产品需要缴纳更高的进口许可费用。
2. CBAM构成任意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是对国际贸易的一种伪装的限制
GATT1994第20条第2款和第7款规定的环保例外,具体是指基于“保护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需的措施”或者“与养护可枯竭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从前文的论述看,欧盟在将CBAM刻意打造成环保措施方面下足了功夫,因此将其认定为与第20条第2款或第7款相符并不存在实质困难,但也未必全无风险。比如,根据欧洲议会的保守估计,CBAM的财政收入约为每年50-140亿欧元,〔47〕See CBAM Resolution, para. 35.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都建议将这部分收入用于“下一代欧盟计划”所产生的融资本金和利息的支付。〔48〕“下一代欧盟”计划是欧盟成员国为应对新冠疫情而通过的一个大规模的市场融资计划,融资规模约7500亿欧元。有关CBAM财政收入的使用,See CBAM Proposal, Explanatory Memorandum, p.11.由于“下一代欧盟计划”的实施范围过于广泛,若欧盟无法证明CBAM收入将被用在环境保护领域,则外界就会认为其实施CBAM的真实目的在于增加财政,而不在于环境保护。
可见,CBAM所面临的更大困难是难以满足第20条引言的要求。该引言构成了第20条适用的前提,即主张适用环保例外的措施不能在相同条件下的国家间构成任意的或不合理的歧视,不能成为对国际贸易的伪装的限制。从WTO争端解决的实践看,恰恰是这个引言要求,成了第20条适用的真正难点。
在相关案件中,WTO上诉机构曾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即要求另一成员国采取与该国境内实质相同的综合管理计划,而不考虑其他成员境内可能存在的不同情况,这种做法并不足取。严格而僵化的标准本身其实已经证明了歧视的任意性和不合理性。〔49〕See United States-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WT/DS58/AB/R, Oct. 12, 1998, paras. 163-164.WTO副总干事在上述CBAM听证会上也认为,如果不考虑出口国采取的碳排放交易以外的减排政策和努力,比如严格的排放标准或者创造碳汇等,欧盟的行动显然会引起极大的争议。〔50〕同前注〔46〕。反观欧盟CBAM会进一步发现,进口产品是否需要承担以及承担多少进口许可成本,取决于欧盟ETS规则;进口产品是否可以免除进口许可成本,取决于该产品的出口国有没有和欧盟ETS相同或相连接的碳市场。可见,CBAM的实质就是以自我体制为中心,强行要求他国采取与其相一致的碳定价制度。在平权的国际社会中,这当然构成一种任意的、不合理的歧视,为一种不能被接受的制度傲慢。
当然,欧盟若能证明其ETS标准构成了某种国际标准,各国都有义务照此标准行事,并且有权对不守规则的国家实践进行矫正的话,则CBAM的性质将会发生实质改变。然而,从欧洲议会的决议文本,到欧盟委员会的建议稿,欧盟一直都在试图证明这种想法:既然《巴黎协定》成员国皆负有积极行动实现控温目标的义务,而欧盟在此方面身先士卒,当然有权让其他国家配合并且敦促其他国家向其靠拢。这显然属于一厢情愿。为了实现控温目标,《巴黎协定》 首次不再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要求所有国家根据本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履行减排义务并接受核查,但从未将某一国的标准认定为国际标准,从未将某一国的实践确立为各国都应当遵照的国际实践,尤其是欧盟CBAM一直强调碳定价这种市场化减排手段的核心地位。申言之,《巴黎协定》从未为成员国设定在本国实施碳定价制度的义务,相反在第6条还特别强调了基于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两条路并进的国际减排合作实践。也就是说,《巴黎协定》一方面鼓励各国运用多种灵活的机制促进减排;另一方面,用“国家自主贡献+核查”的方式,为各国设定气候义务。所以说,有没有完成气候义务,不是欧盟说了算,更不是欧盟ETS说了算。前任WTO总干事拉米曾明确表示,WTO拥有多种手段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但只有当环境机制提供了明确的环境指标和指示时,这些手段才可以被使用。一个包括主要排污国的多边协定,才是指导WTO如何将环境的负的外部性进行内化的最好方法;也只有这样的机制,才能对有关国家在边境实施的措施是否是环境所必需的问题作出适当的裁判。〔51〕See Lamy, Doha Could Deliver Double-win for Environment and Trade, December 9, 2007, 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sppl_e/sppl83_e.htm, last visit on August 7, 2021.欧盟试图用CBAM倒逼各国采用与其相一致的市场机制的做法与《巴黎协定》有关国家自主贡献的规定相悖,当然构成一种武断的、不合理的贸易限制。
四、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因应
CBAM是欧盟下的先手棋,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和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CBAM一旦实施,对中国的影响无疑将是全面而深远的,对此必须要稳妥而积极地加以应对。当务之急,我们首要的工作应当立足于对CBAM下一步发展趋势的研判,这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欧盟接下来会如何推动CBAM;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对CBAM的态度,这将决定中国的压力是仅仅来自欧盟,还是来自整个发达国家俱乐部。
(一)欧盟的进一步努力
CBAM建议稿的出台,反映出欧盟在此问题上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接下来,其会加快内部的立法进程,敦促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议通过成为正式法案。同时,欧盟会进一步加强国际造势,为CBAM的实施创造国际氛围。
首先,在气候变化领域,欧盟会通过《巴黎协定》和G20这样的多边场合,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对碳定价机制的共识,目标是将碳排放交易制度逐渐绑定为各国的制度必选项,进而形成一个国际统一的大市场。自《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创设强制性的减排义务开始,全球气候减排的规则性已日益清晰,约束力日渐增强,这意味着对建立在传统化石能源基础之上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体系需要重新洗牌。这一变化被欧盟非常敏锐地捕获,于2005年建立了全球第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欧盟ETS毫无疑问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碳市场,欧洲事实上成了全球碳交易的中心,无论是碳市场的定价权,还是具体规则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欧盟都占尽先机。〔52〕参见陈红彦:《自由贸易协定:提升我国全球气候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新路径》,载《法学》2020年第2期,第164页。然而,时至今日,仍然困扰欧盟的是,全球碳市场的规模总体依然有限。这主要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京都议定书》只为发达国家设定了减排义务,导致强制减排的全球规模受到很大限制;二是发达国家对于运用碳税或碳交易等价格手段解决减排问题在认知上存在不统一。而且,相比于传统的行政减排手段,碳税或碳交易的引入需要立法程序,这在奉行分权制约的所谓西方民主国家,往往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目前,采用碳税制度的主要是部分欧洲国家;〔53〕参见陈红彦:《碳税制度与国家战略利益》,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85页。而采用碳交易制度的发达国家主要包括新西兰、瑞士、日本和韩国。〔54〕See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markets_en, last visit on August 7, 2021.
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这种局面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这同样基于两大主导因素:一是《巴黎协定》之后,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承担条约意义上的减排义务,尤其是在中国、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都开始实施碳中和计划后,全球低碳发展会加速推进,各国的制度工具因此会更加广泛;二是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已于2021年7月正式启动,这无疑使得全球碳交易规模陡增。尽管中国毫无疑问地将取代欧盟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但欧盟因先发优势而累积的制度优势,事实上将使其获得更多的机遇。于欧盟而言,借力碳交易市场的扩容,扩大其既有的碳交易规则和碳定价的主导权,符合其利益的最大化。也正因为如此,欧盟CBAM建议稿明确表示,只要出口国的碳市场与欧盟ETS相连接,其产品就可免于欧盟的CBAM。如此设计规则其实是在倒逼国际社会形成一套以欧盟ETS为核心的碳定价制度。
其次,在国际贸易领域,欧盟会同时在WTO和双边或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 下称FTAs)两个方向发力。首要的,其会极力促进WTO向有利于CBAM的方向改革。尽管欧盟对CBAM的许多设计都虑及与WTO的相符性,但对于CBAM与WTO不符的这个结论,其实还是有心理预期的。正因为如此,欧洲议会在其决议文本中明确敦促欧盟委员会要促进WTO改革,并且还明确提及GATT的三个条款,即第1条最惠国待遇原则、第3条国民待遇原则和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55〕See CBAM Resolution, paras. 24-27.这都表明,欧盟明确知晓CBAM在WTO中的主要法律困境,也期待通过修改WTO规则,进一步扫除CBAM实施的最大法律障碍。
最后,欧盟会加速双边层面的努力,将CBAM纳入欧盟FTAs的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章节中,〔56〕See CBAM Proposal, p. 3.以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来侧面呼应其对WTO改革的诉求。近年来,由于WTO改革乏力,发达经济体纷纷开始转向FTAs,以期实现其改革意愿。在环境与贸易问题上,欧盟是最早将气候议题明确纳入FTAs的主要经济体,尤其是2010年后,欧盟缔结的FTAs均明确通过专门条款来规范气候变化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明确纳入各方必须遵守的“多边环境协定”的范畴之中;二是加强各方与贸易相关的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尤其是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等领域的合作;三是消除气候友好型产品、服务与技术的贸易壁垒。〔57〕同前注〔52〕,陈红彦文,第162页。上述三项与气候相关的议题,既包括对既有国际共识的确认,也涉及对欧盟气候影响力的外扩,但总体而言,并不直接损害缔约对方的利益,但如果将CBAM纳入FTAs,那么情境会完全不同,它将极大地突破欧盟FTAs的现有实践,因为欧盟在已缔结的FTAs中明确支持各国在环境标准问题上的自主权。〔58〕Eg. EU-Central America Association Agreement(2012), Article 285;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of the one part, and Colombia and Peru, of the other part (2012), Article 277.而CBAM恰恰是对出口国自主制定气候治理政策和标准的否定。更重要的是,由于该做法严重损害出口国的经济利益,必然会招致出口国的强烈反对,所以FTAs是否能如欧盟委员会所愿,成功引入CBAM,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态度
此次欧盟在CBAM问题上的加速行动,除了自身利益诉求的推动外,其实还受到来自大西洋彼岸美国的呼应。对此欧洲议会在其CBAM决议中直言不讳,并称双方可在此方面加强合作。〔59〕See CBAM Resolution, para. R.被欧盟寄予希望的是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在其竞选中提出的《清洁能源革命与环境正义计划》。在该计划中,拜登宣称将不再把贸易政策与气候目标区分开来。对于那些未能履行气候和环境义务的国家,其碳密集型出口产品将要被征收碳调整费或配额,同时还将根据合作伙伴在气候保护方面所作的承诺来制定未来的双边贸易协议。〔60〕同前注〔30〕。
拜登不是第一个提出碳边境调整构想的美国总统。早在1993年,克林顿总统就提出了英热单位税(Btu tax),即对能源产品按其能源含量进行征税的立法建议。同时,为了确保美国产品的竞争力,草案规定了边境税收调整措施,对进口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征收与国内产品相同的税收,而美国出口的能源产品将被免税。〔61〕See Stefan Speck,The Design of Carbon and Broad-based Energy Taxes in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Reality of Carbon Taxes,Western Newspaper Publishing, 2008, p. 9.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也设计了边境调整措施,即所谓的“国际配额储备计划”,旨在对限额排放体系所涉及产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实施保护,对来自尚未承诺具体减排目标国家(尤指发展中大国)的相应产品适用。〔62〕参见王谋、潘家华、陈迎:《〈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的影响及意义》,载《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0年第4期,第308-309页。尽管上述两部立法草案最终未获通过,但至少其边境措施的展开是以对国内产品实施污染者付费制度为前提的。反观拜登的《清洁能源革命与环境正义计划》,其重点是发展清洁能源和技术,通篇未提及设立碳税或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努力。在此背景下,拜登贸然提出边境调整措施的计划,这显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可能性,说到底只是一种政治宣传。尽管拜登的竞选宣言只是一场“政治秀”,但美国对边境调整机制的态度其实是明确的,因为无论是早期的英热单位税法案,还是近年来颇具影响力的《利伯曼—沃纳法案》《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草案)》〔63〕参见王慧:《美国气候安全法中的碳关税条款及其对我国的影响》,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第21-24页。都规定了边境调整措施。可以大体肯定地说,一旦美国要实施全国范围内的碳税或碳排放交易,对进口产品进行边境调整将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其实,这种态度也代表了发达国家的一种普遍心态。作为发达国家的俱乐部,经合组织(OECD)很早就建议各国在有关碳税或者其他环境价格措施方面采取如下的基本策略:一是消极观望。只要其他国家没有引入,那么本国也可以无所作为;二是提供普遍性优惠,如税收返还、边境税收调整等。〔64〕See OECD,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Fiscal Reform: Income and Sectoral Competitiveness Issues, February 11, 2003, 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COM/ENV/EPOC/DAFFE/CFA(2002)76/FINAL&docLanguage=En,last visit on August 20, 2021.此次,在欧盟CBAM的压力和刺激之下,不能排除像G7(Group of Seven)这样的发达国家俱乐部会抱团促进CBAM的发展,〔65〕据媒体报道,英国现任首相约翰逊就考虑在2021年的G7峰会上明确表达此种观点。See U.K.’s Boris Johnson Considers G-7 Bid on Green Border Levies, February 4, 2021, https://financialpost.com/pmn/business-pmn/u-k-s-boris-johnson-considers-g-7-bid-ongreen-border-levies, last visit on August 20, 2021.因为这样做会有多重收益。
一“得”环境收益。CBAM实施的基本前提是对本国产品进行碳定价。当前,在实现碳中和的中长期压力之下,发达国家急需采取更多的举措来加快二氧化碳减排。而无论是碳税还是碳交易,这种基于价格信号的手段原本就是市场机制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的制度强项,不存在引入的制度门槛问题。一旦引入碳定价制度,将会进一步促进发达国家的减排,落实在《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二“得”财政收益。财政收益至少涵盖两个方面:一是节流,即避免本国产业被进口国征收CBAM而导致税费落入他国口袋,相反,通过本国实施碳定价制度,企业的碳定价成本被保留在了本国的财政之中。二是增收,如前文所述,据欧洲议会的保守估计,欧盟CBAM的财政收入约为每年50-140亿欧元。这笔数额不小的进账对于依然还在新冠疫情中苦苦挣扎的发达国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诱惑。
三“得”产业收益。产业利益也至少涵盖两个维度。一是避免本国产业竞争力受损。发达国家普遍担忧,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碳定价的实施会让原本已经危机四伏的本国产业更加被动,而CBAM恰恰针对性地解决了上述担忧。二是促进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回流。事实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反思实体经济流失、产业空心化等问题。而此次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发达国家对全球产业链的担忧。如何促进产业回归,保证供应链的安全,让本国经济更具弹性和自治能力,是西方政治精英们都在思考的问题。CBAM通过进一步缩小工业企业境内外环境定价成本的差异,有助于产业回归。此次欧盟CBAM的出台显然有这方面的考量,这在欧洲议会CBAM决议中被清晰地传达出来。〔66〕See CBAM Resolution, para. K.
四“得”竞争收益。近二十年,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发达国家通过所谓的产业微笑曲线,将除研发和营销以外的产业链大量外包至发展中国家,不仅获得了整个产业链两端的最高附加值收益,而且大量的能耗型生产环节因此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成了世界工厂。CBAM的实施必然会对基于此种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五“得”国际声誉。CBAM若设计得当,不仅不会损害发达国家的国际声誉,甚至可能反向加分。比如,《巴黎协定》明确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从而帮助后者减少碳排放及适应气候变化。尽管《巴黎协定》没有规定资金援助的具体金额,但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曾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但至今未能兑现。〔67〕参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敦促七国集团履行气候资金承诺》,载央广网,http://news.cnr.cn/native/gd/20210615/t20210615_525512642.shtml,2021年8月10日访问。设想一下,如果发达国家决定将CBAM收入转而用于上述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那么将会是一个超级划算的决定:发达国家不用掏一分钱腰包,而是从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大肆搜刮,再转而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向发展中国家“慷慨”捐赠,此举不仅会为发达国家赢得国际声誉,也将在CBAM问题上进一步瓦解和分化发展中国家。
(三)中国应对的具体策略
总体来看,CBAM将不仅是欧盟的努力方向,也可能是发达国家整体的努力方向。基于此,中国的应对策略应该做两个问题维度的区分,即针对CBAM本身,以及针对发达国家为CBAM铺路而在气候和贸易问题上的可能动议。
针对欧盟的CBAM,我国已经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68〕中国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在2021年7月的例行记者会上已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参见《中国明确反对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载中国有色网2021年8月5日,https://www.cnmn.com.cn/ShowNews1.aspx?id=429523,2021年8月10日访问。这不仅因为CBAM与全球气候法治和多边贸易体制存在明显的法律鸿沟,而且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出口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69〕据初步测算,中国的钢铁和铝行业将受到重要冲击,钢铁对欧盟的出口成本可能增加约25%,铝出口成本增加约9%。同上注。尽管我国正在形成并不断完善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这意味着能源和工业产品的碳排放在我国也将被定价,可能也将面临发达国家所谓的国内产业竞争力受损的问题,但依然应该坚定不移地反对CBAM,这至少是出于如下的考虑,即目前我国的进出口结构具有鲜明的特点,进口主要以国内短缺的大宗商品和高科技产品为主,出口主要以机电产品为主,〔70〕参见《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20年秋季)》,载商务部网站,http://images.mofcom.gov.cn/zhs/202012/20201209112029503.pdf,2021年8月10日访问。这种国际贸易结构意味着即便我国引入CBAM,对国内产业的保护效果并不会非常明显。进一步说,我国实施碳排放交易并不是出于某种国际压力的被迫行为,而是真正践行新发展理念,为后代、为人类减少碳排放的内生性行为。申言之,因碳定价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产业并不符合我国的新发展理念,也不应额外提供CBAM等保护措施。更重要的是,我国正在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以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71〕参见《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18-05/19/c_1122857688.htm,2021年8月10日访问。气候问题已然成为我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抓手,是树立中国国际声誉的重要制度性载体,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而对于发达国家可能的抱团,我们的策略当然也是抱团,即尽可能多地团结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旗帜鲜明地反对CBAM。当然,在发达国家抱团的问题上,一个最大的障碍来自美国。当前,气候问题在美国已经被高度政治化和标签化,否则不可能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而拜登上任第一天就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因此,从短期观察,在全美境内通过统一的碳税或碳交易法案的可能性不大,CBAM也因此无法找到实施的基本制度依托。当然,中国即将取代欧盟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的事实是否会对美国构成外部刺激,从而促成两党合力制定出美国的碳定价制度,有待进一步观察。
同时,我们也须清楚地意识到,CBAM客观上将进一步分化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差异。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同,出口结构不同,因能源禀赋、技术手段、生产路径等差异导致的产品碳足迹的不同,CBAM的实施将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差异明显,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能难以形成一个整体来对抗发达国家实施CBAM的企图。对此,中国应尽可能地引导发展中国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CBAM。因为随着发达国家碳中和目标的日益逼近,不仅是传统的能源密集型工业,包括交通运输业、农林畜牧业等也可能被陆续纳入其碳定价的范围,换言之,CBAM的适用范围一定会被不断调整和扩大的,所以不能仅看一时得失。更主要的是,CBAM的核心是让发展中国家丧失对本国环境标准和规制的自主权,是对“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的单方面突破。一旦该原则被有效突破,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将会受到严重损害。
而对于欧盟可能提出的涉及全球气候法治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建议,不能因为欧盟夹带私利就全盘否定,而应加以综合判断。承前所述,通过CBAM推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接受碳定价制度,进而形成一个以欧盟ETS为核心的全球市场,是欧盟的重要目标。为此,欧盟会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机制的谈判。2018年联合国卡托维茨气候大会近200个《巴黎协定》缔约方达成了除第6条之外的协定的实施细则,而直至今日,第6条的谈判依旧未有突破,反映出各国在此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第6条是整个《巴黎协定》中与市场结合度最高的条款,其核心是运用国际合作机制促进各国履行国家自主贡献,并设计了三种自愿合作方式,即第6条第2款的“使用国际转让的减缓成果来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第6条第4款的新机制和第6条第8款的基于非市场方法的协调合作,但是由于条文本身都过于抽象而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所以必须要作进一步的细化和落实。《巴黎协定》之前的《京都议定书》创立的市场机制是所谓的京都三机制,即碳排放贸易、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约机制。因此,《京都议定书》的市场机制与《巴黎协定》第6条的关系问题是第6条实施机制讨论中的重要问题。由于欧盟ETS已经成功地将京都三机制联合起来使用,欧盟事实上在京都三机制中具有制度的先发优势和话语权,所以其坚持《巴黎协定》第6条对京都机制的承袭性。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很多欧洲学者也都持此立场。〔72〕See Daniel Klsin,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Analysis and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78-195.
对此,中国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中国已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在脱碳的道路上开足马力。长期以来,中国不仅习惯而且善于运用行政手段促进减排。但近年来,中央已多次明确市场化减排手段的重要作用。2021年7月16日,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上线,即将取代欧盟ETS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因此,发展基于市场手段的减排机制,促进全球碳市场的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京都三机制是经过实践验证并已充分暴露优缺点的较为成熟的机制,因此,《巴黎协定》第6条如能承继其优点,完善其不足,是有利于促进全球气候治理发展的。但也应看到,市场化减排手段绝非减排的金科玉律,甚至无法成为各国减排工具中的支柱性手段,〔73〕市场化减排机制交易的是污染物或减排量。从逻辑上讲,随着环境治理的不断推进,污染物会不断减少,减排空间会不断压缩,市场交易量会不断萎缩。从现实角度看,全球减排的根本出路在于技术进步,失去技术进步的减排,必然以牺牲现代化的生活质量为前提。同时,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减排,在面对一个确定性的环境危机时,也是一个比市场机制历史更悠久、运用范围更广也更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且还有制度门槛。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在市场要素的培育、市场规则的设计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短板,采用市场化手段事实上对这些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极大考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化的减排机制未必是一条平坦甚至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在促进基于市场手段的全球减排合作中必须要充分考虑和挖掘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换言之,中国应关注并积极促进《巴黎协定》第6条第8款基于非市场方法的合作履约机制的规定,尤其关注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升履约意愿和履约能力的重要意义。
而从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视角观之,将包括气候在内的环境因素更充分地融入WTO规则,符合WTO的改革方向。但中国对于欧盟等发达国家在WTO具体规则下的诉求,则应该有必要给予区别对待。具体而言,在有关GATT第1条和第3条对“同类产品”的修改问题上,中国应持谨慎的态度。现有规则对“同类产品”的界定是从产品本身出发的,有其合理性。因为一旦抛开产品本身而开始涉及产品的生产过程,那么就不仅仅是气候等环境问题了,诸如劳工、宗教、文化等问题都有可能被裹挟进来,这就等于“打开了一个装有诸多问题的潘多拉盒子,并将在GATT中开凿一个巨大的漏洞”,〔74〕John H. Jackson, World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Congruence or Conflict?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Vol.49,Issue 4, 1992.无疑将会为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如此一来,WTO所致力的贸易自由化目标也会遭受极大的破坏。与此同时,处于贸易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文化发展上的自主空间,也将受到严重挤压。而对于GATT第20条的解释问题,中国应坚持条约的边界性,贸易协定与环境协定不能混谈。即便议题本身具有交叉性,但在运用贸易手段促进气候问题的解决上,依然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边界,诸如CBAM这类以单边贸易手段来评判他国气候政策并试图以自身标准对他国进行矫正的做法,显然是失当的。各国在气候问题上是否完成了本国的承诺,贸易协定无权评价,这本应交由气候条约来完成,也只有当气候条约得出明确的评价结果之后,贸易协定才能用来作为辅助手段敦促违约国纠错,而此时单边贸易手段才可能不构成一种武断的、伪装的贸易限制。事实上,为了促进全球减排事业的发展,WTO当前最应该做的工作是进一步削减低碳产品、服务和技术的贸易壁垒,为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减排、适应全球变暖方面提供更多的能力支撑,同时兼顾低碳产品和技术优势国家的贸易利益,进一步促进低碳技术革新。
除了WTO,《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也已明确纳入气候议题,主要包括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义务的重申,对气候友好型投资的支持以及双方在气候投资问题上的相互支持。〔75〕See 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CAI)-Section IV, Invest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uropa.eu), Sub-Section 2: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 Article 6.事实上,在利用双边或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以促进气候议题的发展问题上,中国一直保持积极的态度,并且努力将其塑造成提升我国全球气候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新路径。〔76〕同前注〔52〕,陈红彦文,第164页。笔者认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目前并不存在任何可能为CBAM合理性背书的条款。尽管协定纳入了双方努力提高环保标准的条款,〔77〕同前注〔75〕,第2条。但在“投资与环境”章节的第1条即明确了各国在环境保护的标准、相关法律政策的制定和修改问题上的自主决策权利。〔78〕同前注〔75〕,第1条。坚持环境标准和法规的自主权将是中国在接受和推进贸易投资协定融入气候议题时的底线和原则。
五、结语
气候变化问题虽起因于环境问题,但本质上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如果说蒸汽机开启了西方直至全球以化石能源为特征的工业文明的话,那么气候变化问题将世界引向以清洁能源为特征的低碳文明。这无疑要求经济和社会生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变革的进程,必然伴随着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激烈的低碳发展竞争。所以说,欧盟出台碳边境调整机制,并不仅仅是基于单纯的环境考量。作为《欧洲绿色协议》的一部分,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对低碳规则话语权的争夺,帮助欧盟抢占低碳经济的发展先机。然而,气候变化问题虽然事关各国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战略,但它首先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危机,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因此,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说到底必须依靠国际社会整体,而不能以邻为壑地搞小圈圈、小团体;也只有在全球化的立场上思考法治化的问题,气候法治才能真正促进国际社会在不可预知的未来风险与现实的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