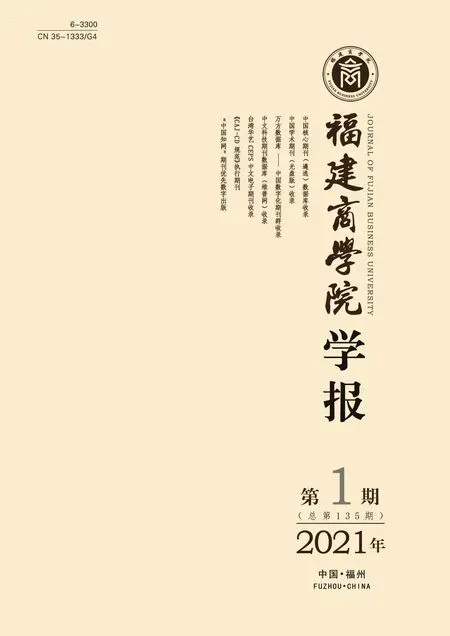客体论到主体论的转向
——新时期“文学是人学”命题论争及其反思
刘皇俊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人,文学表现的对象是人,文学接受的主体依旧是人,文学史是一部“人”不断发现自身、认识自身、表现自身、定义自身的历史。五六十年代社会话语的禁锢,割裂了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传统,也遮蔽了文学表现的多种可能性。1978年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开创了中国社会的新时代,随之而来的新启蒙主义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新纪元。思想文化的“祛魅”是政治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是新时期历史语境下同质异构的结果。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是新启蒙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文化部门一起,担负着实现现代性文化目标、推动中国摆脱思想禁锢的宏大使命。“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伴随着时代的洪流,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在历史“合力”的作用下,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开启了从客体论到主体论的转向。
一、新时期思想禁区的解封
(一)文学观念的解禁
从社会历史角度来看,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观念解禁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思想文化层面对政治改革的呼应。文学观念的“祛魅”是作为政治改革、思想文化解放系统之下的一个“子系统”呈现的。厘清了这一点,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就显得尤为重要。
文学的发展同政治文化息息相关,政治文化规约了文学的发展向度。“1949年7月2日召开‘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一致确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指导文艺的总方针,‘工农兵方向’为文艺运动的总方向。”[1]随后,全国范围内的文学创作、研究、运动都要在这“一观”“一话”的指导之下进行。客观上这一指导思想做出过巨大贡献,影响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实践,但“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极左思潮却一步步将它‘漫画化’僵化”[1]46,也致使整个中国的文学创作走入了困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一话”所倡导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学反映论”,是一种强调客体而非难主体的文学观。“反映”是对主客体关系的理论概括,尽管它宣称主体是能动地对客体进行反映,但是在极“左”思潮和主流社会话语的影响下“能动的反映”被消解了,创作主体不可能也不允许自由地选择反映对象。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被僵化、禁锢、制约,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就是“高、大、全”“假、大、空”式的人物形象和模式化的革命样板戏。这一时期的“文学反映论”实际上是以客体为中心,遮蔽了主体能动性的机械反映论。
1978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伴随着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和思想的空前解放,文学创作也迎来了新的春天。早在五十年代,中国的理论家们就曾试图打破理论“禁区”,纷纷著文从人性、人道主义、阶级等各方面论证文学“人”的本质,试图将文学从“规制”中解放出来,但都以失败告终。客观上“打破禁区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也为下一次论争积累了经验,奠定了理论基础。乘着政治改革和新启蒙主义的历史之势,人性与人道主义在七十年代迎来了新的曙光。
新时期的文学观念解禁以对“人”本质的重新思考为逻辑起点,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认识为理论基础,从“阶级论话语体系”内部为人性存在的合法性寻找法理依据。1979年朱光潜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问题》一文,开宗明义,当前文艺界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放思想,冲破极左思想凭空为创作设置的种种禁区。“首先就是人性论这个禁区”[2],朱光潜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本质力量的论述为基础,肯定了“人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合理性。他指出:“人性论和阶级观点并不矛盾,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无产阶级服务。”[2]39-42虽然从论述中不难看出,朱光潜并未完全脱离时代阶级论的话语体系,他从阶级的角度入手为“人性”辩护,并从法理上消除了“人性”与“阶级的对立”。但是,这是历史时代所决定的,他不得不从“阶级斗争话语体系”内部寻找“人性”存在的合法性,援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并以此为辩护基础。由此可见,即使在思想解放开始后,理论家们突破“禁区”的尝试依旧是小心翼翼的。随后,汝信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一文,支持朱光潜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入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关注,从哲学层面呼应了朱光潜的观点。哲学、文艺界相继发声、互相呼应,文学观念的解禁以哲学认识为理论基础,哲学认识的解禁又以政治改革为先决条件,社会各个领域的“解禁”尝试最终开启了文学观念的解放大潮。
(二)文学实践的解禁
一个时代的言说方式和表达主题暗藏着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曾经不可触及的言说禁区,在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的双重外力下被打破,人道主义与人性这块荒芜已久的文学沃土正待开掘。
新时期的文学实践诞生于“文革”的创伤之中,并以五十年代人道主义文学的萌芽为基础,乘着新启蒙主义的历史浪潮,在新一轮的“西学东渐”中展现出多元、开放、自由的姿态。“伤痕”“反思”“人性”都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热心表现的主题,作家们热心歌颂人性、揭露创伤、批判迫害,践行着“人”的文学观、创作观、价值观。
卢新华《伤痕》讲述“进步”青年王晓华和“叛徒”母亲划清界限,一别多年后母子天人相隔,抱憾终生的故事;冯骥才《啊!》、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与《芙蓉镇》描写阶级斗争和政治迫害致使社会扭曲、人被异化的荒诞现实;鲁彦周《天云山传奇》以罗群的悲剧命运为叙事主体,揭露政治迫害对人性的摧残;张贤亮《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戴厚英《人啊,人!》等作品通过叙写知识分子遭受的非人待遇,反思极左思想,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抚慰伤痕累累的“人”;刘克《古碉堡》从藏族女性曲珍的悲剧上升至对整个民族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观照。作家们向人们展示出一个个“非人”的世界、一个个“骇人”的故事,以“非人”的描写呼唤人性、人道、人伦,他们是对苦难有着切身体验的作家,他们写于受难、痛于悲剧,但不陷于苦难和悲剧,而是以此为武器反思苦难背后的逻辑。
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在文学实践的解禁中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作家们在文学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人的理解,将同情、宽容、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灌注于文学实践。他们不仅仅停留在“情感叙事”的层面,还灌注了新启蒙主义所带来的“启蒙精神”,以“受难者”的视角,揭露文革迫害、批判极左思潮、表现新的启蒙要求,将思想启蒙与文学创作相结合,接续了五四“人的文学”传统,真真正正实现了文学实践的解禁。
二、“文学是人学”的命题
(一)“文学是人学”命题之源
文学是人类特有的精神创造的产物,是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是人性对世界的馈赠,它的孕育生长必然受到人的灵魂、情感的滋润和规约,而这种滋润和规约概括起来就是人道主义。因此,文学应该是“人学”。
1957年《文艺月报》刊发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钱谷融从文学表现的对象、题材论述了“人”之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热情歌颂、赞扬了“人”的文学,呈现出鲜明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倾向。他将文学的作用归纳为改善人生,提高生活以至于达到“至善至美境界”[3]。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令人敬佩,是因为他们在作品中“赞美”“润饰”“歌颂”了“人”,使得“人”的形象高大了。
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中表述的观点与高尔基的观点十分相似,甚至直接援引高尔基所用的概念、词义。显然,钱谷融试图从前苏联那里继承“人学”命题立论的法理性。在阶级斗争占据话语权的年代,将理论之源诉诸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似乎是最稳妥安全的做法。高尔基也是从创作主体、表现对象、价值取向等方面对“文学是人学”进行了阐释。他曾坦言自己毕生从事的工作是“人学”,文学是“创作典型”的工作,文学要塑造“大写的人”[4]。此外,钱谷融还援引季摩菲耶夫语“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3]3,以此为基础批判文艺反映观基础之上的“主体工具论”,即文艺家将表现人当作其实现反映“整体现实”的手段和工具。在钱谷融看来,“主体工具论”既不符合艺术创造的逻辑,也不符合文艺家创作的实际情况,季摩菲耶夫“整体现实”的概念界定是含糊不清的、空泛的。如果说作家将反映“整体现实”作为创作任务,那么作家势必“削足适履”,以消解人物形象的独特性为代价,反映所谓的“整体现实”。但是文艺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并不会依照此种思维逻辑,反而是以人物的独特性为核心,追求人物形象的灵性,而这也正是文学作品价值之所在。钱谷融的论断是合理的,他从反映论内部寻找到了“人学”命题立论的合法依据。
新时期“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内涵不仅限于文学表现的客体和创作接受的主体。从本质上说,它是“人道主义”的文学表达,是五四“人的文学”传统的延续。“五四”时期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文艺批评家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灌注于新文学,热心提倡文学关注人生、表现人生、净化人生。新时期重提“文学是人学”命题,不可能绕开这一文学传统。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5],而在这一点上钱谷融是与其一脉相承的。在钱谷融看来,文学的价值在于惩恶扬善、塑造人性、表现具体的人,文学表现对象是“具体的在行动中的人”,作家应该“写出他的活生生的、独特的个性”[3]3。而“个性”一词指的是单个“人”的独特性、个体性。换言之,文学所关注的对象——“人”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写的人,又是具体意义上的、个体的人。
(二)“文学是人学”命题之辩
早在五十年代“双百方针”提出之时,中国的文艺家们就曾对“文学是人学”命题进行论争。但由于极左思想和主流话语的规制,这场打破“禁区”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他们遭遇了来自两方面的批判和打击:一方面来自文艺界内部,主要以张学新、柳鸣九、蒋孔阳为代表,从革命与反映、阶级与人性的角度、人道主义的理论漏洞等方面对巴人等人的观点予以批判;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于政治领域。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指出:“资产阶级人性论,是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来调和阶级对立,否定阶级斗争和革命,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1]276。随后,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场关于“人性与文艺”的论争也就戛然而止了,一直到七十年代才被重新提起。如果说来自文艺界内部的批判还算是学术领域的理性探讨的话,那么来自政治领域的压力便是在学术之外的阶级斗争。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以阶级论囊括人性,以至于否定了超越阶级的共同人性,以阶级的解放代替个性的解放”[6]。错误将两个话语体系的概念强行放到一起,将人道主义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将其纳入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中,从根本上宣判人道主义的“非法”,这显然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1980年伴随着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历史潮流,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一文揭开了新时期“文学是人学”讨论的序幕,标志着人道主义文学的回归。钱谷融在文中表示,既然文学表现的对象是人,那么“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7]。“人性”是读者接受的兴趣所在,也是作者创造的中心。文学作品之所以能跳出历史时空的限制,在千百年之后还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性”二字。质言之,文学的价值尺度在于“一切都是为了人 , 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7]13。
值得注意的是,重提“文学是人学”实际上是一种“主体论”复归的表现。在反映论、客体论的话语时代,主体一直处于被压抑、被忽视、被遮蔽的状态。主体自由的高扬在极左思想家看来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是修正主义复燃的导火索,必须彻底铲除。随着七十年代“人学”命题的复归,主体获得了新生,中国文艺界正由客体论转向主体论,而这也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因为文学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独创性,而独创性取决于充满能动性的“人”(即主体),没有人自由独立的精神创造,文学艺术无从谈起。古希腊柏拉图讲“诗兴的迷狂”“神灵凭附”,中国古代讲“性情”“性灵”,都是对文艺之中独创性的阐释。“人”是天地间自由的灵长,而由“人”所创造的文艺势必包含着人的审美意识、情感体验、人生体验,这是文艺的生命之源、价值之源、魅力之源,抽去了“人”便空无一物。
三、新时期“文学是人学”命题论争的反思
(一)新时期“文学是人学”命题的贡献
新时期重提“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结果,更是五十年代被压抑的人道主义文学回归的结果。在历经种种苦难之后,“人学”命题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参与到中国新时期“现代性”叙事的历史建构之中,并为之贡献了核心的精神基因。
首先是人道主义的复兴。随着“文学是人学”讨论的开始,人道主义作为文学讨论的“副标题”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在“十七年”与“文革”时期,人道主义被视作资产阶级思想而纳入阶级斗争的话语体系中被大加批判。新时期重提“文学是人学 ”,立论的逻辑起点就是“人道主义”。据此理论家们纷纷从各个角度予以论证,在客观上扩大了人道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丰富了人道主义的理论内涵。而人道主义在中国“现代性”叙事的历史建构过程中,又贡献了人性、本我、自由、情感、人道等重要的价值内涵。
其次是文学主体论的复归。人既是文学创造的主体亦是文学表现的客体。作为“人”特殊的精神创造,文学创作是“人”主体性的最佳呈现,强调文学创作的独特性也就是强调主体性在文学创作中的核心地位。如前所述,五十年代后文学主体性被社会话语遮蔽了,“能动的反映”似乎是痴人呓语,在极权的规制面前苍白无力。文学创作的主体性陷入了无尽的深渊,“假、大、空”的人物形象、淡乎寡味的革命样板戏便是最好的例证。“文学是人学”的重提、人道主义的复归无疑再一次将“人”(即主体)置于文学的中心,主体性从“深渊”回到了文学创作的舞台中央。
最后是启蒙精神的复现。“五四”文学革命先哲们将启蒙的要求与新文学相连,奠定了新文学现代性的重要价值维度和审美传统。而这一切在“十七年”至“文革”期间被中断了。新时期重提“文学是人学”,重塑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作家在文学实践中热心表现人情、人性、人道,揭露文革迫害、批判极左思潮,表现出新启蒙的要求、思想解放的要求、个体自由的要求。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实际上继承了“五四”的启蒙传统,将中断已久的启蒙精神线索重新接入中国新时期“现代性”叙事的历史建构之中。
(二)新时期“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局限
不可否认,新时期“文学是人学”命题论争在客观上纠正了“阶级论”“工具论”等有失偏颇的文学观,将文学创作从阶级、政治话语中解放了出来,促进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但是当离开历史现场数十年后,重新冷静全面地审视新时期“文学是人学”命题便会发现其局限性。
首先是命题定义的窄化。“文学即人学”并非严格的代换关系。将文学定义为人学,从表面上看似乎为文学的定义找到了完美的答案,实则陷入了“概念循环”的谬误之中。从字面上看,文学与人学并不相等,一为语言艺术的范畴,一为社会学的范畴。从内涵上看,文学确实是表现人生、人性、人情,但其价值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它还可以表现社会、历史、政治、审美。显然,将文学定义为人学,有窄化文学价值的嫌疑。
其次是“人学”在此等同于“人性”。如上文所述,文学与人学的词义其实是不对等的。在“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中,“人学”的意义更多接近于“人性”“人道”“人情”,而并非是学术研究的意义。钱谷融等人将人道主义精神当作批判“阶级论”“工具论”的强大武器,以前苏联高尔基“人学”论为语言表达的物质外壳,忽略了“人学”词义的模糊性,也造成了“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理论漏洞。
四、结语
文学与生俱来的“主体性”使其每时每刻都带有“人”的印记和尺度,在这一逻辑之下,“文学是人学”。新时期的“文学是人学”命题是五十年代“人学”论争的余绪,是新启蒙思想和政治“祛魅”之下的产物,是理论家批判“阶级论”“工具论”的强大武器,是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兴起的标志,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从客体论到主体论转向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