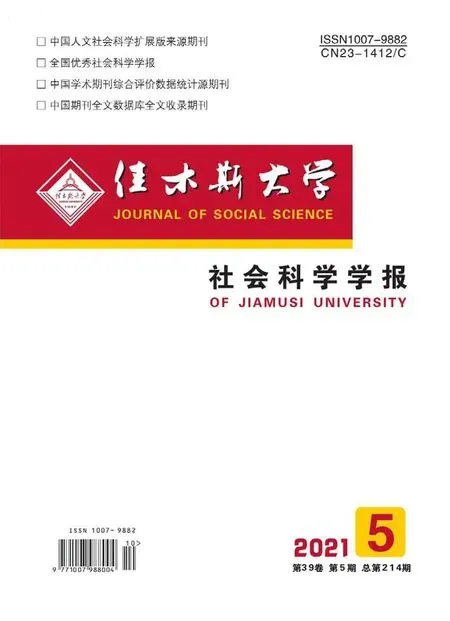余华文学小说“疼痛”美学的几重维度 *
王 燕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商贸学院,安徽 合肥 230051)
余华是当代中国最为重要、极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家,他直击现实的疼痛书写,对个体、群体、社会疼痛的深刻反映,为中国当代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人文写作向度。如果对余华的“疼痛”书写进行总体审视,会发现其在美学上具有三重维度,第一重维度在于揭示疼痛是他者无法理解的私人言说,第二重维度在于描述疼痛使主体陷入的失语困境,第三重维度在于倡导用一种温情的力量来治愈疼痛[1]。从这三重维度,阅读者可以更好地注视余华在写作上对于人性、社会现实、历史现实的观照,能深刻地体会到他强烈的写作使命感。
一、疼痛是他者无法理解的私人言说
20世纪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个体的疼痛是个性化的、私密化的,只有自己才能知道自己是否在疼痛,而他人只能猜测。换而言之,疼痛作为个体内心层次的感受,是很难被他人真正关注到和引起他人关怀的。而余华作为一名对人性的洞察上具有高超敏锐度的小说作家,其非常善于在自己的作品中发掘人性深处这种极为私密化的疼痛感,而后会试图在伦理语境中对其进行审视,最后向读者传达出了人类的疼痛是不可能被感同身受的残酷事实[2]。例如在其小说《黄昏里的男孩》中,主人公小男孩的饥饿感就一直没有引起水果商贩孙福的关注,哪怕当身无分文的小男孩用本真、气息微弱的话语很清晰地表达出自己非常的饥饿,孙福也没有给予小男孩一丝关怀,竟是狠狠地呵斥他,最后用一句“走开”中断了男孩的言说,这意味着孙福完全拒绝去聆听、体会小男孩的“疼痛”。忍受不住饥饿的小男孩只能抓起一个苹果就跑,孙福追上后先打掉了他的苹果,然后当着一堆围观人群使劲地掐住他的脖子,逼着小男孩将吃进去的苹果吐出来,结果小男孩吐到连一点口水都吐不出来了,直至奄奄一息。
该小说在一种异常冷静的文字叙述中用残忍的画面展现和审视了施暴者的人性之恶,但人性之恶的背后却是留给读者的一连串问题与思考:孙福本身就有过丧子之痛,为何无法关注和关怀到一个流落街头、饥饿的男孩的“疼痛”?为何围观者也如此麻木不仁,不能感受到弱者的“疼痛”?这些问题也说明了余华关于对个体疼痛议题的描述和探讨,不是基于疼痛的内在心理事实,余华希冀在伦理学语境的人际交往关系中,来不断拓展个体的疼痛议题的探讨空间,展现出人际沟通间的一种深层隔阂:面对别人的疼痛,旁观者匮乏某种去给予其关注、关怀的伦理义务,所以才会表现得或残酷,或冷漠,或沉默等,这就导致在人际沟通交往上,别人的疼痛成为了一种大家都不愿去主动聆听和理解的私人言说。如在《一个地主的死》中,当众人看到曾经拯救过大家的英雄王香火,即将奔赴死亡的时候,他们的表情上几乎毫无波澜,一个个都显得极为平静,仿佛英雄的死是他自己的事,跟大家毫无关联。总之,无论是在《黄昏里的男孩》还是《一个地主的死》里,余华对“疼痛”旁观者残酷、麻木、冷漠的展现,实质上是在勾勒一幅集体精神虚无的图景,以拷问和审视他们匮乏人文关怀的灵魂。不过余华明白,想让旁观者们主动去关注、关怀别人的疼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于是余华想探索:如果强行让旁观者体会疼痛,是否会令他们通过将心比心,觉察到内心匮乏的人文关怀光辉?在《西北呼啸的中午》中,余华对此进行了回答。主人公“我”跟随朋友参加了一位死者的葬礼,在朋友的安排设计下,一群疼哭流涕的人开始做戏包围了“我”,而死者跟“我”素不相识,所以面对这样的情景,“我”感到异常的无可奈何与压抑,很被动地成为了一位疼痛的在场者。而朋友不顾忌“我”的感受,甚至从道德的高度逼迫“我”屈服于他的安排,去对死者表达悲痛。可是“我”在被强制的状态中,根本无法被周围的悲伤气氛感受,也无法对一个毫不认识的人哭泣,“我”只能假装在悲痛。足见,让旁观者强行去关注、参与他人的疼痛,不仅无法产生关怀心理,甚至还会让旁观者陷入一种困境,使其更难去深切关注他人的疼痛[3]。
那么,既然旁观者无法在主动中,真正去聆听、体会别人的疼痛,又无法在被动中接受对别人疼痛的移植,于是余华更是将疼痛视为一种极为私密化的私人言说,所以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余华完全放弃了对如何让旁观者能够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别人疼痛的探索,而是在不断地放大这种疼痛的私密性、不可理解性。例如在《河边的错误》中,当一个疯子对一位老婆婆施虐的时候,邻居们却以为这不过是两人在玩一场游戏。如此的熟视无睹,甚至会将异常的施虐行为看作是一种合理的游戏行为,这不仅意味着旁观者根本就不会去真正注视到他人的疼痛,也揭露了旁观者是一群异化的群体,有着虚无的灵魂。可以说,余华作品里的疼痛实质上指涉的是一种精神性创痛,而非单纯的肉体上的疼痛,余华通过入木三分的笔刀,刻画了旁观者在面对他人疼痛时候所暴露出的人性深处的麻木不仁与暴力。然而余华并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对此作任何价值批判,其只是通过对他人疼痛困境以及旁观者精神图景的客观叙述和还原,以让读者独立地去挖掘背后的价值空间并进行某种深刻的反思。
二、疼痛使主体陷入失语困境
疼痛是他者无法理解的私人语言,但疼痛的主体总是试图将这种私人语言传达给外界,那么疼痛主体就必须要使用公共的语言系统来对自己的疼痛进行“翻译”,或者说是重新表述。但是对于这种过于私人化的疼痛经验,用独白式的公共语言是无法精准捕捉到它,甚至由于不能被意会,会使其成为他者眼里的呓语。余华就非常善于在作品中,描述私人疼痛“言”到“意”间的传达障碍,以揭示疼痛主体的失语困境[4]。如果认真分析会发现,公共语言难以传达主体疼痛的主要原因是:疼痛主体这一疼痛的言说者和疼痛的聆听者之间缺乏相通的情感投射和知识结构,因而导致疼痛的言说很容易产生歧义,会被误读,甚至还会导致言说者与聆听者彼此间的对话出现中断。在余华的作品里,有很多对话情节就是因为疼痛主体和疼痛聆听者的“不对位”才出现了对话中断。例如在《祖先》中,当男主人公“我”因为被父亲充满汗味的棉衣裹得太紧,所以觉得非常难受,于是“我”开始模仿青蛙“呱呱”的声音来提醒父母,而父亲根本就没有在意到,母亲却对“我”会模仿蛙叫而感到欢喜。最后“我”面对这种语言传达障碍,陷入了片刻的沉默,而后只能无奈地哭了起来。还有在《现实一种》中,孩子皮皮因为年纪不大,所以对“疼痛”没有任何正确认识,可以视为是小说里毫无疼痛体验的一个象征符号。当他对自己的堂弟进行施虐的时候,堂弟因疼痛而发出的哭声竟使他莫名兴奋,于是皮皮没有停手,直至堂弟哭不出来。在这个情节中,堂弟就是因为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剧烈的疼痛而导致被皮皮失手致死。如果这里疼痛经验的不可传达,还有童稚无知的原因的话,那么小说中关于山峰儿子死亡的情节,却将疼痛主体失语的困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山峰妻子被带到了死去的儿子身边的时候,她先喊了几声自己的儿子,可儿子没有反应,不过她好像不以为然,甚至表现得有些安心,仿佛那就不是她的儿子。在如此荒诞的场景中,山峰儿子在自己母亲面前一直张着嘴巴,但他永远也没法说话。这种画面深刻地刻表现出了疼痛主体在疼痛言说中陷入失语困境的无力感。
余华还善于通过在作品中构造一种异化的外部世界来剥夺疼痛主体的话语权,让其堕入失语困境。例如在《十八岁出门远行》这部寓言式的小说中,刚年满十八岁,驶向象征成人世界的柏油公路时,路上的陌生化图景简直就是一个异化的空间,让“我”倍感压抑,无所适从。“我”对这样的世界既表现得不可理解,又无法对其进行准确言说,就像无法言说那些遍体鳞伤的车辆的疼痛与“我”自身的疼痛一样。在这部小说中,余华为青春期少年所构造的异化的成人世界充分反映了疼痛主体与外部陌生世界难以进行有效沟通的现实,甚至疼痛主体在与自我沟通中,当试图对于自我的疼痛进行描述的时候,居然也陷入了一种无法传达的失语困境。总之,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余华将年轻人由少年到成年的最开始历程中所表现出的不适应、挣扎、压抑等心理状态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从而唤起了大家对青春期少年在人生蜕变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可言说的疼痛的关注[5]。
在余华的作品中,疼痛主体在对自己的疼痛进行传达的时候,往往还会在宿命论语境中对自己的疼痛回忆和疼痛经验进行悬置或是选择性遗忘,从而在不幸的生存环境里展现出一种疼痛局外人的生存姿态。例如在《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的人生不断遭受意外,身边的亲人接二连三地离他而去。面对这样悲剧的一生,福贵在向旁人叙述的时候,仿佛自己置身于疼痛的记忆外围,他在对疼痛的言说中忽略了自身对疼痛的深层次反思。福贵会把自己一生疼痛的根源完全归咎于不可预知的宿命,而不去怪罪于自己的性格缺点和青年时期的错误行为。不仅福贵,他周围的所有人也是如此,疼痛虽然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或身边,但好像却在他们的内心之外,所以面对疼痛,他们其实都是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中,他们的语言一直与疼痛保持着绝缘。而正是如此,所以人们很难真正传达出自己的疼痛和洞察到他人的疼痛,于是就很容易对自己的疼痛和他人疼痛产生误解。从某个层面看,在《活着》等小说中,余华会刻意从生存困境这一宏大的命运视角来审视个体或群体的疼痛,并揭示疼痛主体遭遇的失语困境。
三、疼痛需要温情的治愈力量
余华总是试图将个体疼痛或群体疼痛放在一个壮阔的历史文化背景里进行探讨,以对疼痛进行更深刻地观照与反思。在这样的叙述下,个体或群体的疼痛显然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疼痛。例如在余华的小说《第七天》里,小说除了描绘了个体的疼痛,还会通过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的反应来将这种个体疼痛升华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疼痛,从而达到对某一特殊历史阶段现实社会反思的目的。这部小说里,余华借鉴了现实生活中很多极具社会影响的热点事件,如医疗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城管执法问题等,然后通过对它们进行文学化的改造,向读者展现了贴近社会现实的诸多荒诞性社会乱象与文化症候,揭露了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人性迷失给社会带来的一些阵痛。当然,余华并没有毫无理性,极端地在批判现实,其虽然竭力刻画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小人物的疼痛,以敏锐的视角放大社会中的小部分阴暗面,但这是为了更好地唤起人们重新审视高速发展的社会,提醒我们在面对他人疼痛时应当具备温情。尽管余华认为旁观者几乎难以能够感同身受地体会和理解到他人的疼痛,但这不是人们丧失温情关怀的理由。即使我们温情的目光无法真正注视到别人的疼痛,但温情的力量还是会给他人疼痛带来某种程度的治愈。所以在《第七天》中,余华会通过各种温情的情节来治愈他人甚至自我的疼痛。例如小说中杨金彪对自己养父的爱,尽管他们一直处在一个充斥着冷漠、功利的人际大环境中,尽管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更多的时候也无法真正体会彼此内心的苦楚,但是并不影响内心善良的杨金彪总是温情地对待自己的养父,这种温情让他们实现了互相治愈。还有伍超,即使在社会遭受过很多不公,没有人正视过他遭遇的疼痛,但他依然保持初心,没有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扭曲心理,后来为了能够让自己的爱人可以安息,他甚至选择去卖肾,结果却丢了自己的生命。在小说中还有诸多这类感人的温情人物,余华对他们之所以进行极力刻画,实际上是为了展现一种人类共同的悲悯情怀,因为正是有它,人性深处才会绽放出温情的光辉,才会照耀到他人疼痛,甚至自己疼痛。
在小说《活着》中,余华通过对家庭温情的描述将温情的治愈力更是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无论是主人公福贵的母亲还是妻子、子女,他们总是用自己的温情关怀着福贵。例如面对年轻无知,总是在外花天酒地、赌博的儿子,福贵的母亲虽然深知儿子不对,但从未责怪过他,只是进行劝诫,虽然这表现得比较溺爱儿子,但是让富贵感受到了母亲的宽容和悉心爱护。富贵的妻子家珍更是包容福贵,这位米店商人的女儿总是默默承受着福贵的各种荒诞行径,哪怕福贵在最开始的时候从未关注和理解到自己的伤害给她带来的疼痛,但她对福贵依然不离不弃,甚至在福贵被人欺诈陷入人生低谷的时候,愿意陪他一起承受苦难[6]。还有福贵的女儿凤霞,一旦看到爷爷生气要训斥父亲,她就会通知福贵赶快躲起来,后来身为人妻后,她还总是常常来看望自己的父亲母亲,会给自己的父亲带来他最爱吃的东西。正是因为家庭的这些温情,才治愈了福贵一生所遭遇的疼痛。如果我们放在《活着》这部小说宏大的历史语境中,来审视福贵这一生的疼痛,可以看到,福贵作为一个小人物在时代波澜中遭受的疼痛,与其说是属于个体的疼痛,倒不如说是特殊社会历史时代历程中大部分个体所遭遇的苦难疼痛的缩影和典范。但是当福贵面对一切疼痛,面对他人对自身疼痛的残忍漠视,哪怕是面对亲人接二连三逝去的现实,他还是选择坚强、乐观地活下去。就是因为他的生命曾被亲人珍惜过,温情以待过,他的生命已不仅是属于自己,也属于亲人。所以他必须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哪怕亲人们都走了,他也要咬牙替他们活下去。在福贵的晚年生活中,福贵总是向别人诉说自己的亲人故事,这也是为了让自己通过活在记忆的温情中,以治愈自己的疼痛,让自己对生存、对现实社会继续充满希望。足见,在《活着》中,温情的力量已经变成了一种对大历史洪流中,个体漂泊命运的关怀和救赎。它不仅能抚慰个体的疼痛,甚至还能抚慰一个时代的社会群体疼痛。总之,在余华看来,如果人类彼此之间都给予温情的光辉,那么人类现实社会、人类历史困境中的那些疼痛都将会被治愈,人类社会也将因此会变得更加美好、光明。
四、结语
在余华的作品中,阅读者都会被其真实、深刻的疼痛书写所震撼到,其笔下个体不可言说的,不能被他者关注、理解的疼痛、最后让个体陷入失语困境的疼痛,仿佛像子弹一样能直击到阅读者的灵魂,引发大家对人性、对社会现实、对社会历史等进行独立审视与反思。但直面现实的、残忍的疼痛书写背后,是余华对温情力量的倡导,余华希冀用温情的力量来抚慰他人疼痛、社会疼痛,来净化现实社会,以让高速发展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当前,在中国当代文学纷纷堕入平庸的日常书写和先锋式的语言狂欢实验中,阅读者应该更能体会到余华“疼痛”文学的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