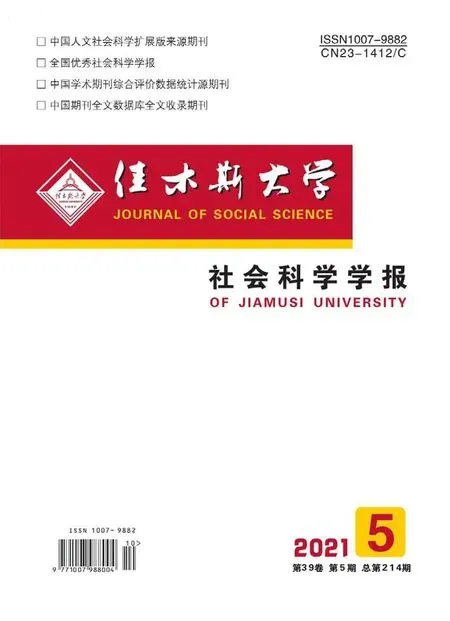憬悟者·启蒙者·落伍者 *——韩北屏现代小说人物形象研究
董卉川,张 宇
(1.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2.青岛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3.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韩北屏,原名韩立,笔名有露珠、宴冲、欧阳梦等。韩北屏的现代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紧紧围绕抗战这一时代背景展开叙述。他擅于在作品中塑造抗战时代多样的人物形象,凭借对憬悟者、启蒙者、落伍者形象的勾勒描摹,揭示抗战时代复杂的社会世相,暴露抗战时代的社会问题,人生、人性、国民性的理性沉思,渗透着作者本人强烈饱满的时代感、责任感、使命感。
一、憬悟者形象的勾勒
抗战时代的憬悟者,是韩北屏在其现代小说中着力勾勒的一类人物形象,寄寓了作者本人对社会、国民、时代、未来的热切期望。在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下,憬悟者形象的勾勒给读者与民众以巨大的鼓舞和激励。韩北屏主要从乡村——城市两个维度勾勒抗战时代的憬悟者。
《狙击手方华田》的方华田和《花素琴》的花素琴是乡村中憬悟者的代表。方华田是一个庄稼汉,抗战爆发后主动参军。他既有农民的质朴真诚,同时由于自身阶级的局限性,政治觉悟极低,“性情温顺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好商量,要是暴躁起来,溜缰的野马似的,真是难于驾驭”[1]。恰逢家中老母生病、田地闹纠纷,他无视军纪,未请示便直接离开部队,被哨兵抓回。在“我”——指导员的悉心教导和帮助下,他的政治觉悟逐渐提升。当家中再次发生困难时,他主动请示,并在规定时间赶回部队。方华田前后的转变,标志了他的觉醒,他成长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与方华田相比,花素琴觉醒憬悟的过程极为复杂艰难。她所处的环境尽是黑暗与污浊,没有人能够为她提供启蒙和帮助。花素琴原本在农村过着贫穷的生活,经受不住城市的诱惑,自甘堕落,抛弃丈夫沉沦都市,“染上了一身和花柳病同样可怕的大病。到最后,却又使她受到抛弃的痛苦”[2]。引诱她堕落的社会渣滓张三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试图将花素琴送给东洋人,但花素琴深知民族大义,没有丝毫妥协,她十分愤怒地将他们赶出家门。小说结尾,她最终决定离开黑暗城市,回到广阔农村。回归乡村,意味着她从物欲的深渊中脱身,意味着她勇敢地走向了新的人生阶段,通过对花素琴形象的勾勒,寄寓了韩北屏对这类女性群体的深切同情与美好期望。
《临崖》中的蒋小姐、《没有演完的悲剧》中的萱、《学步》中的梅佩君则是都市中憬悟者的代表。《临崖》中的“我”在前线工作,重病后来到大后方的医院治疗,在这里偶然结识了一位女病友蒋小姐。蒋小姐虽是汉奸的女儿,但她痛恨侵略者、痛恨自己的父亲,孤身出逃,来到大后方。此时的她对前路充满了迷茫与困惑,“一个人想把一切精力甚至生命贡献时,却遇不到机会,这种失望的痛苦,比之有了机会而不能胜任的痛苦尤为难堪”[3]。最终,在“我”的鼓励启迪下,蒋小姐作出了新的人生抉择,她与“我”共同奔赴前线。《没有演完的悲剧》中的萱深受父亲的压迫,被父亲送给江家瑶作填房,来到江家后又终日遭受打骂,她无法忍受,最终决定出逃。在给妹妹鸾的信中,她表明了自己决绝的态度,“现在,我走了……可是我不管这一些,我不能为他们而牺牲了我自己。”[4]143这封信象征了一个被压迫女性的反抗。
梅佩君是一位侨商的女儿,美丽大方,受人欢迎,众多男子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却对看不惯自己的辛耀中颇有好感。“九一八”事变后,辛耀中积极投身时代浪潮之中,在抗战中奔赴前线。梅佩君逐渐对自己堕落的生活产生了厌倦与疑问,她想要过新生活,却没有勇气向前迈出一步,“我现在缺少一种力量”[5]。梅佩君主动联系了辛耀中,辛耀中成为了她的启蒙者和引路人,他邀请有相似境遇的魏菁一同劝说梅佩君。在辛耀中和魏菁的感染引领下,她发出了强力呼声:“我能改!我一定能改……我从今天改给你们看!从此刻改给你们看”[5]。她的呐喊象征着她勇敢地迈向了人生的全新阶段,“她的脚步,和他们慢慢合一了”[5]。原本贪图享乐、自甘堕落的富家女实现了蜕变与新生。
方华田、蒋小姐、梅佩君,他们的觉醒,均是在外力——启蒙者的帮助指引下实现的。花素琴、萱的觉醒则没有任何外力的启迪牵引,而是由一种反作用力——封建男权的桎梏、邪恶势力的压迫、罪恶社会的压榨所导致。两种模式共同铸就了韩北屏现代小说中憬悟者的艺术形象。
二、启蒙者形象的描摹
韩北屏笔下的启蒙者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抗战爆发后,他们投笔从戎、走向战场、保家卫国。同时,又用自己的言行去启迪、鼓舞、帮助被启蒙者们。
《临崖》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喜欢阅读契诃夫和巴尔扎克的小说。抗战爆发后,“我”弃笔从戎,在前线从事工作,因病来到后方休养。在医院中,“我”结识了正处于迷惘状态的蒋小姐,并对她进行了启蒙,使她觉醒,与“我”共同奔赴前线。《学步》中的启蒙者是辛耀中,他是一个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抗战。在他的引导下,贪图享乐、迷惘无知的摩登女性梅佩君觉醒,走向前线。《狙击手方华田》中,“我”在部队担任指导员的工作。“我”成为了方华田的启蒙者,他逐渐克服了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摒弃了小农意识,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狙击手。《临崖》《学步》《狙击手方华田》采用了现代小说中经典的启蒙模式——男性为启蒙者,女性为被启蒙者;现代知识分子为启蒙者,普通民众(农民)为被启蒙者。
韩北屏在采用传统启蒙模式建构文本的同时,还采用了新颖的启蒙模式。《神媒》中的启蒙者为某乡镇的小学教师乔钢,人如其名,他有着钢铁般的顽强意志。小说中的被启蒙者既非女性,也非普通民众,而是一个与乔钢同样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外国牧师毕克。毕克十分钦佩乔钢的精神和言行,不自觉地想要接近他,想要让他加入教会,但屡次都被拒绝。二人还经常就人生问题、信仰问题进行讨论,各执己见。抗战爆发后,乔钢并没有撤离本地,而是决心“为了爱人类,我准备随时献身”[6]。在乔钢的启蒙下,毕克决心与乔钢一道,去帮助所有的民众,不再囿于宗教身份的区隔。五四以来,中国社会中涌现出的启蒙者们——现代知识分子,多受到过西方现代思想的洗礼与影响。而在《神媒》中,原本应是启蒙者的西方人毕克反而成为了被启蒙者,实现了启蒙权的反转。
韩北屏的现代小说还描摹了大量女性启蒙者的形象,这些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的羽翼之下,而是一个个独立、自强的个体。面对时代乱局,她们或参军作战,或乐观坚韧,为抗战默默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学步》中的魏菁、《被称做太太的女同志们》中的“女同志们”、《锤炼》中的周柔宜、方淑云是参军女性的代表,她们有着超乎常人的勇气,抗战爆发后积极投身抗战事业。魏菁与梅佩君类似,家境优渥,她却选择放弃安逸的人生,参军作战,同辛耀中一道,成为了梅佩君的启蒙者。《被称做太太的女同志们》中的“女同志们”是驻扎在某乡村的部队中的一群女战士,她们一直试图对乡村中的民众,尤其是妇女进行启蒙。在《锤炼》中,北大营干部训练班来了一个沉默寡言、忧郁冷淡的光头女学员周柔宜,她终日孤身一人,“忧悒”神秘[7]。她在参加培训班之前就加入了抗战部队,作战时因自己的冒进与不成熟,导致战友廖侃牺牲。她无法原谅自己。后来意外发现廖侃生还,她终于战胜了自己的心魔,从忧郁中走了出来,变得成熟稳重,得到了锤炼与成长。周柔宜在抗战伊始,就已经是一个启蒙者,随着锤炼,她最终成长为自我的启蒙者。
《邻家》中的梅健虽未像魏菁、周柔宜、方淑云等女性那样弃笔从戎、投身革命,但她默默为家人付出,同样是一个富有牺牲、隐忍精神的知识女性。梅健是报馆编辑刘君来的妻子,育有两个孩子阿环、阿珠。梅健与君来是平等的,君来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之时,还是梅健的安慰劝解令他重拾生活的信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梅健甚至成为了君来的启蒙者。梅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同周柔宜类似,是自我的启蒙者。她没有被苦难的生活击倒,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乐观坚韧、富有牺牲奉献的精神,刘君来和梅健,像无数青年工作者一样,忘记了一切的狂热的工作着,陶醉在工作中,陶醉在胜利的信心中,而且也陶醉在同志爱的真诚亲切的氛围中”[8],既给了丈夫君来以安慰,又给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以激励和启蒙。
韩北屏的现代小说,以塑造了新颖的启蒙者形象。韩北屏笔下的启蒙者,不同于鲁迅等人笔下的启蒙者那样孤独无助、茫然彷徨,他们践行了自我的使命,实现了自我的价值,给读者与民众以希望。
三、落伍者形象的刻画
韩北屏承继了五四学人改造国民性的殷切期望与历史使命,因此,抗战时代那些自甘堕落、麻木愚昧的落伍者成为了韩北屏现代小说竭力批判的对象,以此审视暴露人性、国民性,反思社会问题。
《邻家》中,韩北屏在描写君来和梅健这对恩爱夫妻的同时,还呈现了他们邻家那对一胖一瘦夫妻的面貌。“胖男人”在某机关工作,平素中饱私囊、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走私赚钱。“瘦女人”与“胖男人”实乃一丘之貉,他们的灵魂早已被金钱腐蚀,他们的人性早已堕落扭曲,夫妻二人互相猜忌、互相攻击,为金钱大打出手。反而对战争形势不闻不问、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两个相邻的家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抗战时代两种家庭、两种人生的缩影。《狙击手方华田》中,方华田第二次请假回家的缘由是本家叔父和村长见方华田参军后,家中只剩弱妻老母,便想瓜分他的田地,本村流氓时常骚扰他的妻子。方华田为国参战,村中的乡邻非但不伸出援手帮忙照顾,反而为非作歹、落井下石。韩北屏将人性之恶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揭示的不是某种个例,而是一种超越历史和时代的社会问题与社会世相,在当下仍具有启示之义。
在《没有演完的悲剧》中,全篇氛围极其压抑,令人窒息。张实甫、江家瑶分别是封建父权和夫权的代表,他们专制冷酷,只关心自己的社会声誉。当萱离家出走后,他们只担心自己的名誉被破坏,受到亲朋好友的耻笑。“一个不要脸的丫头逃走倒不在乎,我这一生的名誉非保全不可”[4]146。为了安抚女婿,张实甫竟冷血地决定将二女儿鸾再送给江家瑶作填房。在《花素琴》中,同样充溢着黑暗与邪恶,以张三为代表的堕落魂灵,他们在战前欺男霸女、逼良为娼,将女性视为牲畜般贩卖。抗战爆发后,则投靠侵略者,心安理得地做起了汉奸。韩北屏通过对“胖男人”“瘦女人”、张三、张实甫、江家瑶以及方华田的乡邻们,这些落伍者的刻画描写,揭示和批判了抗战时代的堕落灵魂、丑陋人性、黑暗世相。
《魔术的医道》则以反讽的笔法讽刺批判了抗战时代,那些耽于享乐、不问世事、自甘堕落的富太太们无病呻吟的可笑人生。“我”是一位后方医生,某日接诊了一位“饱受各种病痛”折磨的赵麦慧玲女士,她称自己“病不离身,身不离病”[9]。实际上,赵麦慧玲没有任何的疾病,只是迁徙逃难中遭遇波折,“他们医生不懂得我的痛苦,难道你还没有看够我所受的磨难吗?”[9]她无病呻吟,关心的只有自己的“病体”。小说嘲讽了以赵麦慧玲为代表的一类自私冷血、无知冷漠的群体。
在《雀和螳螂》中,韩北屏刻画了战争中常见的一类群体——间谍。小说的主人公是驻守南京的中校刘戒非,他在青阳港度假时偶然结识了一位风度翩翩的贵公子方效庄。回到南京后又在方效庄的引荐下,结识了美丽大方、优雅高贵的张小姐和宋小姐。方效庄、张小姐、宋小姐实则是日本间谍,他们已经窃取了南京城的多个重要情报,最近又盯上了位居要职的刘戒非。刘戒非虽然开始时对他们颇有防范,小心谨慎,但终究没有抵挡住他们糖衣炮弹的攻击,醉倒在宋小姐的石榴裙下,“刘戒非看着宋小姐明亮的眼睛,衬着绯红的两颊,就像在枫叶林子后面的一泓秋水,着实令人陶醉”[10]。这些特务即将得手之时,终被南京城的特务机构和宪兵抓获。方效庄、张小姐、宋小姐,还有《临崖》中蒋小姐的父亲,均是被侵略者收买的中国人,他们甘愿出卖自己的灵魂、民族和国家,自甘堕落,认贼作父,是无耻的堕落者,令人唾弃。
在《被称做太太的女同志们》中,韩北屏通过启蒙者与庸众之间的接触,极尽描摹病态的国民精神。当军中一对青年男女在河边相谈之时,村民们早已将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对部队中男女军人的住宿问题尤为感兴趣,“在他们的宿营地向外,常有很多农民窥探着”[11]。“窥”字尽显他们无知、愚昧。当女兵想要与孩童亲近而抚摸他时,“那个孩子怀着憎恨似的摇了摇头,朝女的衣服上吐了一口唾沫,脱缰小犊似的飞跑了”[11]。幼小的儿童却已然变得麻木愚昧,这是最为令人痛心与惋惜的。部队住宿所在地的屋主一直恳求部队的青年男女在元宵节烧香点炮,因为女兵们住进了堂屋,将洗过的衣服挂在了神堂之中,犯了“大忌”。由此揭示了女性地位的低下、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
通过对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落伍者形象的刻画描绘,韩北屏展现了抗战时代的种种社会世相社会问题,令人警醒、发人深思。人性、国民性的呈现与外部的社会关系、社会现实紧密相连。韩北屏试图通过对堕落麻木的灵魂、病态国民精神的暴露批判,去揭示黑暗的社会现实,去剖析复杂的社会关系,探寻社会问题的根源。
四、结语
韩北屏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江苏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韩北屏现代小说人物形象的深入研究和综合阐释,钩沉韩北屏的文学创作生涯,不仅能还原他的文学创作风貌,重审他的文学史地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韩北屏的重新“发现”,亦是一种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