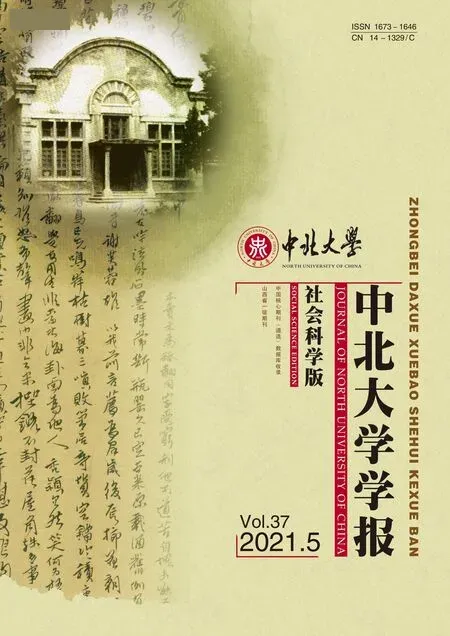中晚唐唱和诗心态变化阐析
——以通江唱和、松陵唱和为对照
陈必应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唱和诗是由两首及以上的诗组成的相互酬唱、赠答的诗作。在唱和诗中,第一首为原唱,接下去的为附和,其形式多样,有联句、依韵(同韵)、用韵、步韵(次韵)、和诗等。宋刘攽《中山诗话》云:“唐诗赓和,有次韵(先后无易)、有依韵(同在一韵)、有用韵(用彼韵,不必次)。”[1]289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和韵诗有三体:一曰依韵,谓同在一韵中而不必用其字也。二曰次韵,谓和其原韵而无先后次第皆因之也。三曰用韵,谓用其韵而先后不必次也。”[2]109早在梁萧统《文选》中,已有“赠答”类收录赠答诗80余首,内含部分唱和之作。《文选》卷二十九所收西汉苏武《苏子卿诗》与李陵《李少卿与苏武》、东汉佚名《客示桓麟诗》与桓麟《答客诗》、东汉秦嘉《赠妇诗》与其妻徐淑《答秦嘉诗》为唱和诗发展早期之作。至唐朝,文人雅士以诗唱和之风大盛,元稹、白居易间的“通江唱和”与皮日休、陆龟蒙间的“松陵唱和”是唐代唱和诗风的高峰。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中唐以还,元、白、皮、陆更相唱和,由是此体始盛。”[2]110宋严羽《沧浪诗话》言:“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3]193-194虽然严羽批评以和韵而斗工的现象,但是,同徐师曾一样,都指出唱和之风始盛于元白皮陆之间。可见,元白“通江唱和”与皮陆“松陵唱和”在唱和诗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虽然元白 “通江唱和”与皮陆 “松陵唱和”皆是唐代唱和诗风中的典型,然元白处中唐之时,皮陆在晚唐之际,因社会背景、政治状况、士人境遇的不同,“通江唱和”“松陵唱和”诗作之间的心态亦多有别异,对照解读“通江唱和”“松陵唱和”,可一窥中晚唐间唱和诗中所体现的士人心态之变化。
1 “通江唱和”“松陵唱和”诗作概况
李肇《国史补》云:“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4]197这种“侈于游宴”的习气使得唐代社会风貌大变:“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5]30“时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6]3976实则这种社会风气并非仅在贞元之后方才流行,在唐代开放活泼的社会氛围之下,有唐一代文人雅士交往、唱和之风流行,自初唐至晚唐,文人雅士间交往唱和之风不绝。而在整个唐代文人间的交往唱和之中,“通江唱和”与“松陵唱和”堪称唐代文人交往唱和之典范,在唱和诗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1.1 “元白”与“通江唱和”
唐代诗人的交往唱和唐初已显端倪,及至中唐,政治斗争与党争倾轧日愈激烈,文人身上的政治热情逐渐消散,往往转而耽溺诗酒之间:“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7]4043《旧唐书·穆宗纪》云:“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6]485-486据刘昫《旧唐书》载:“(元稹)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稹量移通州司马。虽通江悬邈,而二人来往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婉。”[6]4331-4332又云:“时元稹在通州,篇咏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6]4345“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6]4360元稹、白居易并显于元和诗坛,又因政事被贬通州、江州,虽相隔遥远然仍酬唱不绝,正如白居易所云“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8]1908,形成了“通江唱和”这一令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元、白通江唱和时期的诗作情况,据吴伟斌《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述略》统计:
元白通江时期(元和十年三月三十日至十四年三月十日)的唱和诗计79首。其中白居易诗42首(不包括其酬唱元稹江陵时诗《放言五首》),元稹诗37首。在这些唱和诗中,元白对应唱和共有24个诗组,计诗61首(其中次韵相酬21个诗组,计诗55首);仅有白氏寄赠而无元氏答赠的诗歌12首,元氏有寄赠而白氏无诗答赠者6首。就白居易来说,有元稹对应唱酬诗30首,另12首现存元集无元稹对应唱酬诗;就元稹来说,答酬白氏的诗篇 31首(其中次韵相酬27首),另有《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水上寄乐天》《得乐天书》《相忆泪》《寄乐天》《凭李忠州寄书乐天》6首寄赠,而白氏似无诗酬和。[9]
所谓“唱和诗计79首”是仅指元、白在“通江唱和”这一时段的唱和诗,而元白平生之间的唱和诗作则较此更多。据赵乐《元白唱和诗研究》统计,元稹诗集中与对方唱和数为182首,唱和占诗歌总数的33.7%;而白居易诗集中与对方唱和数为212首,唱和占诗歌总数的7.3%。[10]对于通江唱和这一时期的元白唱和诗作,李汉南《元白唱和诗统计分析》认为:“元白现存可考的和韵唱和诗107组,占到了所有唱和诗总数的79.2%,即元白唱和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的和韵唱和。”[11]2这种现象与元白唱和之间喜长篇排律、次韵相酬有关,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有云:“居易雅能为事,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12]1450-1451又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12]1280-1281元稹所称之“元和诗”,即当时“自衣冠士子,自闾阎下俚,悉传讽之”的“元和体”。此外,在通江唱和时期,元白之间除了诗歌唱和外,尚有书信往来。(1)如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元稹有《叙诗寄乐天书》。元和十年(815年)十二月,白居易有《与元九书》。元和十二年(817年)四月,白居易有《与微之书》。
1.2 “皮陆”与“松陵唱和”
皮日修与陆龟蒙交好,又皆有诗名,相互唱和,以“皮陆”并称于世,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云:“皮陆以萍合唱和吴中,因而齐称。”[13]272《松陵集》共收录咸通十年(869年)到咸通十二年(871年)间唱和诗作680余首,绝大部分为皮、陆诗作,皮陆之外尚录崔璐、崔璞、颜萱、张贲、司马都、郑璧、李毅、魏朴、羊振文等诗人作品。松陵即松江,又称吴江、笠泽等,为皮、陆等晚唐士人活跃地区,《松陵集》亦是以吴中地望而得名。因《松陵集》唱和诗之内容不外乎酒、樵、渔、茶、花等琐物碎事,多注重于日常生活中器具、景物、人事之间闲情逸致的表达,故而自来多受非议。明赵执信《谈龙录》认为:
元、白、皮、陆,并世颉颃,以笔墨相娱乐。后来效以唱酬,不必尽佳,要未可废。至于追用前人某诗韵,极为无谓,犹曰偶一为之耳。遂有专力于此,且以自豪者,彼其思钝才庸,不能自运,故假手旧韵,如陶家之倚模制,渔猎类书,便于牵合,或有蹉跌,则曰韵限之也。转以欺人,嘻,可鄙哉![14]16
赵执信此段虽然旨在批评“后来效以唱酬”“专力于此且以自豪者”,然而言元白、皮陆“并世颉颃,以笔墨相娱乐”,毕竟已有批评意味。又如《唐诗别裁》云:“龟蒙与皮日休倡和,另开僻涩一体,不能多采。”[15]144甚至在清人许学夷眼中,这种唱和诗风到了大坏诗体的地步,其《诗源辩体》云:“陆龟蒙皮日休唱和,多次韵之作。七言律,鼓吹所选,仅得一二可观,其他多怪恶奇丑矣。”[16]297“夸新斗奇,大坏诗体,二子(皮、陆)复生,吾当投畀豹虎。”[16]299鲁迅则认为:“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17]591
对于皮陆及其唱和诗的评价之所以出现不同的态度,实则是因于看待问题的角度及观念有所不同,亦与皮、陆所身处的晚唐之际的社会现实相关。晚唐之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朝臣党争愈演愈烈,唐王朝的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幻灭感与绝望感笼罩着整个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诗人诗风亦开始分化,或注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呈现悲凉抑郁的感伤色彩,或逃避现实而追求自在自得的隐士生活,而皮日休与陆龟蒙无疑是后者的代表。虽然元白“通江唱和”与皮陆“松陵唱和”皆是文人雅士间的交往酬唱,但因中晚唐时代背景的变化及元白、皮陆身份的别异,导致人们对于元白“通江唱和”与皮陆“松陵唱和”批评的不同。也正是因为中晚唐时代背景与社会现实的变化,导致通江唱和、松陵唱和诗作中所呈现的士人心态同中有异,体现出中晚唐诗人唱和诗中的心态变化。
2 通江唱和与松陵唱和诗中的心态异同
诗言情,然而这种情是受诗人的心态影响的,就通江唱和与松陵唱和而言,元白、皮陆之间的唱和诗在心态上既有共通之处,又有别异之分。一方面,唱和诗作为诗人间交往酬唱的诗歌创作,在本质上都是言诗者之情,以诗歌的酬唱来表现友人情怀,这一点无论是元白之间的通江唱和还是皮陆之间的松陵唱和都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元白固是知己,皮陆亦为密友,然元白与皮陆之间志趣却是难以相同的。因此,元白、皮陆各自之间的唱和诗在情感与心态上固然高度类似,但将元白与皮陆两相对照,则多有别异之处。
2.1 心态之同:诗者情性与友人情怀
元白相识30余年,来往通信1 800多封,互赠诗篇近1 000首,可谓中唐诗人间交往的代表。辛文房《唐才子传》云:“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毋逾二公者。”[18]34而在《松陵集》中,虽然所收录诗人达10余人,而皮陆二人之酬唱占其绝大部分,以至于甚至可将《松陵集》视为皮陆二人之酬唱集。据皮日休《松陵集序》云:
(咸通)十年,大司谏清河公(崔璞)出牧于吴,日休为郡从事。居一月,有进士陆龟蒙字鲁望者,以其业见造,凡数编。其才之变,真天地之气也。近代称温飞卿、李义山为之最,俾陆生参之,未知其孰为之后先也。太玄曰:“稽其门,辟其户,眼其键,然后乃应,况其不者乎?”余遂以词诱之,果复之不移刻。由是风雨晦冥,蓬蒿翳荟,未尝不以其应而为事。苟其词之来,食则辍之而自饫,寝则闻之而必惊。[19]1310
正因二人兴趣相投,往往“苟其词之来,食则辍之而自饫,寝则闻之而必惊”,相交之深,由是可见。故清余成教《石园诗话》言:“晚唐诗人之相得者,以陆鲁望龟蒙、皮袭美日休为最。”[20]1776虽然“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然而在元白、皮陆身上所能看到的却不是文人之间的“相轻”与攻诋,而是以诗言情的诗者情性与同声相应的友人情怀。在元白、皮陆相互唱酬之诗中,真挚之情溢乎字间。如元白唱和诗云:“自我从患游,七年在长安。所得唯元君,乃知定交难。”[21]37“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21]1373“行逢贺州牧,致书三四封。封提乐天寄,未坼已沾裳。坼书八九读,泪落千万行。中有酬我诗,句句截我肠。”[12]160“十载定交契,七年镇相随。……况乃江枫夕,和君秋与诗。”[12]169又如皮陆唱和之中诗句:“我志如鱼乐,君词称凤衔。暂来从露冕,何事买云岩。”[19]1422“珍重双双玉条托,尽凭三岛寄羊君。”[19]1431“如何世外无交者,一卧金樽只有君。”[19]1430“不知桂树知情否,无限同游阻陆郎。”[19]1440无论元白还是皮陆之间的唱和,这种以诗言情的诗者情性与同声相应的友人情怀是一致的,这种诗者情性与友人情怀虽有时代之别,而在情感上却一样具有打动人心的美,这也是通江唱和与松陵唱和并为美谈的原因所在。
2.2 通江唱和:志同道合的挚友情感
在元白通江唱和与皮陆松陵唱和表现诗者情性与友人情怀的共同心态外,通江唱和与皮陆唱和在心态上亦有着不一致的地方。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认为:“作为北宋文人的延续,南宋文人也是以参政主体为主要角色的,多数还具有了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学术主体三而合一的复合型主体特征。”[22]实际上这种“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学术主体”合一的复合型主体特征并不仅仅表现在北宋与南宋文人身上,而是中国古代文人所具有的主体共性。就白居易、元稹而言,在“元和主盟”[6]4360的诗人身份外,在二人一生奔波仕途、宦海浮沉中更重要的是作为“参政主体”的官员身份。因元、白二人都热心政治而又政途乖蹇,故而往往有志同道合、君子同困之感,这是元白唱和的重要情感根基所在。张永丽《唐代唱和诗研究》在对元白之间的分析中认为:
唱和主要分为四个阶段:一为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和五年(公元810年)间。二为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间。三为长庆三年(公元823年)—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间。四为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大和五年(公元831年)间……整体来说,元白唱和的高峰期均是二人仕途不得意的时期。正如导师周围先生在《元稹唱和诗考述》中所言:“元稹的唱和诗创作随着仕途的升降而有所不同,仕途顺利时创作较为低落,而仕途堰蹇时则出现高潮,但总的趋势是逐步走上成熟的。”[23]67-73
通观元白“通江唱和”这一唱和阶段内的诗作,这一时期元白“(元稹)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稹量移通州司马”,正是二人仕途的低落期与唱和的高潮期,故而这种志同道合、君子同困基础上的惺惺相惜的挚友情感是较平时唱和更为浓厚的。如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2)《东南行一百韵》诗全名为《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云:“穷通应已定,圣哲不能逾。况我身谋拙,逢他厄运拘。”[21]1247“时遭人指点,数被鬼揶揄。兀兀都疑梦,昏昏半是愚。”[21]1247而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则和诗曰:“我病方吟越,君行已过湖。去应缘直道,哭不为穷途。”[12]366“倍忆京华伴,偏忘我尔躯。谪居今共远,荣路昔同趋。”[12]367元白二人对于君子同困的苦闷通过相互酬唱得以抒怀,而志同道合的挚友情感也在相互的唱和中得以体现。
通江唱和时期,元白皆喜长篇排律,其中,一些随性之作则往往感人更深,如白居易《舟中读元九诗》云:“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21]1224元稹《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和曰:“知君暗泊西江岸,读我闲诗欲到明。今夜通州还不睡,满山风雨杜鹃声。”[12]624在贬迁的政治境遇下,二人诗中皆弥漫着压抑苦闷的气氛,两相对读更显得这种政治上“志同道合”情感的动人之处。正如元稹《得乐天书》所云:“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12]611元白在通江时期酬唱频繁,不仅把中唐唱和诗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顶峰,也把这种“志同道合”的挚友情感塑造成了文人交往唱和的永世典范。
2.3 松陵唱和:潜逸山水的隐者情志
相对于元稹、白居易“仕人”与“诗人”的复合型主体身份,皮日休、陆龟蒙虽然在现实中也有着这种具有古代文人普遍性的“复合型主体特征”,但至少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皮、陆身上的“隐士”色彩较之“政治主体”的色彩更浓,故而在皮陆“松陵唱和”的诗作中其表现的内容不同于元白“通江唱和”中那种志同道合、君子同困的挚友情感,而更多是体现一种潜逸山水、诗酒唱和的隐者情志。皮日休《松陵集原序》云:“苟其词之来,食则辍之而自饫,寝则闻之而必惊。凡一年,为往体各九十三首,今体各一百九十三首,咱体共三十八首,联句问答十有八篇在其外,合之凡六百五十八首。”[19]1310皮、陆仅一年期间,相互唱和诗作竟达558首之多,或许正是由于在这种潜逸山水的隐者情志之下少却诸多牵扰与烦恼,在轻松自在的唱和心态下才取得了这样高产的效果。据张永丽统计:“从咸通十一年(870年)到十二年(871年)仅1年左右的时间里,皮日休和陆龟蒙创作的和诗达269组,占晚唐全部和诗的28.83%,唱和俱存的262组,占晚唐全部唱和俱存诗的83.7%。”[23]80。
皮陆松陵诗作的内容大多为生活中的日常事物,如皮日休《公斋四咏》咏小松、小桂、新竹、鹤屏,而陆龟蒙《奉和公斋四咏次韵》也以四物为题和之;陆龟蒙作《渔具诗》15首,皮日休则有《奉和渔具十五咏》;皮日休有《添渔具诗》5首,陆龟蒙则作《奉和添渔具五篇》;此外还有如《樵人十咏》《奉和樵人十咏》《酒中十咏》《奉和酒中十咏》《添酒中六咏》《奉和酒中六咏》《茶中杂咏》《奉和茶具十咏》等大规模的唱和诗。在皮陆松陵唱和诗作中,无论是长篇唱和、组诗唱和还是短篇唱和,酒、茶、渔、樵一类表现隐者情志的事物是诗作内容的主体,在诗句之间体现出“富贵如疾颠,吾从老岩穴”[19]1381“满此是生涯,黄金何足数”[19]1399-1400的孤傲之气与隐逸之趣。
皮日休《松陵集原序》云:“昔周公为诗以贻成王,吉甫作颂以赠申伯,诗之酬赠,其来尚矣。后没为诗,比多以斯为事。”[19]1310皮陆在松陵唱和诗的创作中,不仅对于数量有着自觉的追求,而且在内容上亦有着独特的表现。王锡九《皮陆诗歌研究》认为:“皮日休、陆龟蒙对有关渔具、樵事、酒事、茶事的直接吟咏。它们具有较高的文化史、民俗史认识价值,也很深致地表达了皮、陆的隐逸趣尚。”[24]119相对于元白通江唱和中那种志同道合、君子同困的失落文人与贬迁官员酬唱,皮陆松陵唱和则呈现出诗酒茶樵、潜逸山水的隐士生活画面,元白通江唱和与皮陆松陵唱和诗作中的这种心态别异,是多方面因由影响造成的。
3 晚唐唱和诗中文学心态变化因由探析
刘勰《文心雕龙》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5]693“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5]675文学心态的变化往往是多方面造成的。从元白通江唱和中那种志同道合、君子同困的挚友情感,到皮陆松陵唱和中的诗酒茶樵、潜逸山水的隐者情志,中唐到晚唐之间这种唱和诗中的心态变化亦是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
3.1 中晚唐的时代变局
“安史之乱”后,唐朝繁荣稳定的大盛世局面不再,中唐时期虽出现过短暂的中兴时期,然而,在朝廷党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变乱不断的影响下,唐朝内外局面业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凋敝与民生之苦甚重,孟郊《寒地百姓吟》便是一个生动的写照:“无火炙地眠,半夜皆立号。冷箭何处来,棘针风骚劳。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26]125虽然唐朝的没落已不可避免,但大唐盛世所去不远,士人心中仍保持着“兼济天下”的进取精神与济世情怀。而同为“元和主盟”,白居易不仅对当时“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袭封爵,门承勋戚资”[21]88-89的黑暗现实深感不安,而且无论是著《策林》75篇以救时弊,还是仕途上关切民生的具体作为及“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21]78的从政态度,皆是以一颗济世之心投身其间的。元稹同样有这样的政治热情与进取精神,其在《说剑》中云:“剑决天外云,剑冲日中斗。剑隳妖蛇腹,剑拂佞臣首。”[12]56“自我与君游,平生益自负。况擎宝剑出,重以雄心扣。”[12]56其政治热情、凌云之志跃然纸上。
到晚唐之时,政治危机较中唐更重。一方面,朝廷对于藩镇所能起到的控制极其微弱,使得朝廷名存实亡;另一方面,在本已衰弱的朝廷之中,党争之害与宦官之祸越发严重,特别是宦官专权甚至达到了诛杀大臣、废立皇帝的地步。《新唐书·仇士良传》云:“(仇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7]4486其跋扈之状如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晚唐文人的政治热情消退、进取精神不再,或归隐山林以避祸、或半官半隐以安身,故而诗作之中中唐那种报国无门的苦闷与挣扎愈发少见,而多了作为隐士的闲适与淡雅。正是中晚唐间的这种时代变局,使得中晚唐诗作的关注侧重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在中唐时期的元白通江唱和与晚唐时期的皮陆松陵唱和的对照之下体现尤为明显。
3.2 境遇与性情的不同
据《旧唐书》载:“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稹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为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制下,除右拾遗。”[6]4327元稹家族久居洛阳,世代为官,元稹亦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路线。“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既居谏垣,不欲碌碌自滞,事无不言”[6]4327,元稹因为官正直而一贬江陵、二贬通州、三贬同州、四贬武昌,虽多受贬黜而为官以报国为民之心不减。白居易生于“世敦儒业”的官僚家庭,不仅政治上与元稹一样多不得意,而且在忠君爱国之心上也和元稹一致。故而《新唐书》云:“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7]3409元稹与白居易无论是在仕途还是性情上总能保持惊人的相似,故而在交往唱和之间亦往往引为知己,在相互酬唱中一抒不得志的抑郁苦闷与志同道合、君子同困的挚友情怀。正如《旧唐书》所言:“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6]4360元白之间的通江唱和不仅仅是一种知己老友之间的慰藉,更是一种政治上同道的欣慰与相互勉励。
相较而言,皮日休和陆龟蒙则没有了元白身上的那种政治参与感,皮日休对晚唐之际的黑暗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古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古之用贤也,为国;今之用贤也,为家。古之酗醟也,为酒;今之酗醟也,为人。古之置吏也,净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27]64-65“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27]55“古之所谓贼民,今之所谓贼臣。”[27]62正是在这种看清现实黑暗而又看不到希望和出路的苦闷感和绝望感中,皮日休自号“间气布衣”“醉吟先生”“醉士”以寄情诗酒、逃避现实,甚至其后参加黄巢起义之事亦当与这种看不到出路的绝望感有关。而陆龟蒙举进士不第,历任幕僚从事,在士风凋敝官场污浊的环境下转而以高蹈隐逸的狂狷之态行世,又加之陆氏本醉心于农学实业方面,有《耒耜经》《茶书》等著作。在晚唐的历史背景下,看穿现实感于绝望而以诗酒逃避现实的皮日休与喜于农事山水的陆龟蒙之间的交往唱和,是两个士人在政治热情和进取精神褪灭后的无奈选择,是一种苦闷与绝望后的闲适与淡然。虽然元白通江唱和与皮陆松陵唱和并称唐代文人交往唱和之典范,然而,境遇与性情的不同使得通江唱和与松陵唱和呈现出不同的唱和心态,是中唐与晚唐诗人心态变化的极好对照。
——通江县多措并举推进优秀年轻干部递进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