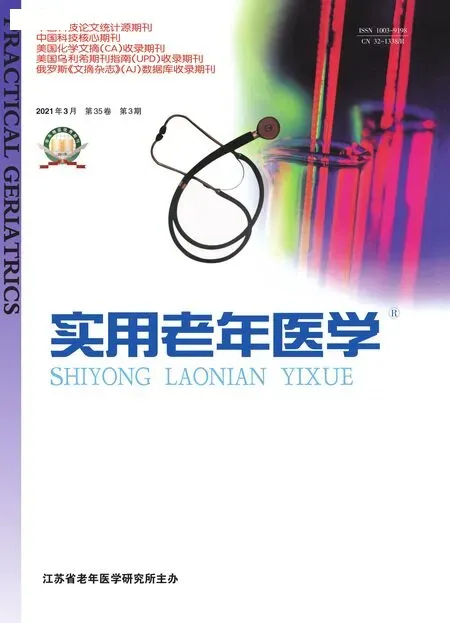外泌体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研究进展
于馨蕊 王莹
1 概述
AD是一种以认知功能障碍和行为损伤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其病理特征是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病理生理级联反应,包括β淀粉样蛋白(β-amyloid, Aβ)的异常聚集和源自高磷酸化tau蛋白的神经原纤维缠结的形成。作为痴呆症的主要原因,AD约占所有病例的60%~80%[1],而痴呆症又是AD晚期不可逆和不可治愈的综合征。因此,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来确诊高风险或临床前AD人群,以便尽早干预和改进治疗方案。外泌体是细胞外囊泡的一种纳米级亚型,其可以携带小的遗传片段和有毒蛋白质,并在细胞和细胞外液之间运输[2-3],这可能是神经退行性疾病进展的机制,因此也提出了基于外泌体检测和干预的AD早期诊断和生物学治疗的新途径。本文综述了外泌体在AD中的研究进展。
2 外泌体的生物学特性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外泌体参与调节神经元发育、再生和突触功能,并且可以被大多数细胞类型,如神经元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和小神经胶质细胞释放[4-5]。一旦释放到细胞外环境,外泌体便可以充当信使,被邻近的细胞捕获或被一定距离的细胞内化,或者进入体液被不同的组织吸收[6],进而发挥消除细胞废物,调节免疫应答等生理作用[7-8]。此外,外泌体也参与神经炎症和氧化应激,并在病理作用下,参与传播错误折叠的蛋白质,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和传播[9]。
此外,修饰的外泌体静脉给药可成功地将外源性RNA传递到小鼠的脑组织中,这表明修饰的外泌体可能会跨越生物屏障,例如血脑屏障[10]。由于其内含各种各样的分子,例如蛋白质、脂质和遗传物质,因此可以利用外泌体含量检测和外源性遗传物质修饰技术将外源性遗传物质传递至神经细胞的作用部位,并为疾病生物标记物检测和神经系统疾病(如AD)的治疗创造新的途径。
3 外泌体参与AD的发病进程
AD的第1个病理标志是Aβ在脑实质的异常聚集。Dinkins等[11]通过5xFAD小鼠模型研究证实了外泌体可以促进Aβ聚集并加速淀粉样斑块的形成。为进一步研究, Sinha等[12]首次通过细胞内Aβ的毒性寡聚体(Aβoligomers,oAβ)与外泌体共定位的方法,证明AD脑源性外泌体可以介导oAβ完成在神经元之间的扩散,进而在AD的发病进展中发挥作用。
AD的第2个病理标志是神经元内神经原纤维缠结,这是由于过度磷酸化的微管相关蛋白tau的积累。而多项研究表明,tau可以通过外泌体从神经元中分泌出来[13]。在AD中,tau的病理过程以明确的模式发展:首先涉及的区域是内嗅皮层(Braak Ⅰ~Ⅱ期),然后发展到边缘区域(Braak Ⅲ~Ⅳ期),最后到达新皮质区(Braak Ⅴ和Ⅳ期)[14]。多年来,人们已经讨论了这种扩散模式在人类大脑中的传播机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病理性tau蛋白以类朊病毒的方式聚集、复制和扩散,继而被受体细胞摄取,导致单体tau蛋白错误折叠聚合[15-16]。但由于tau蛋白缺乏分泌途径的信号序列,无法进行神经细胞之间的传播,便需要通过外泌体介导的途径来完成有毒蛋白质的传播[17]。
此外,AD的重要特征是慢性神经炎症和氧化应激的活跃,进而导致不可逆的神经元功能障碍和细胞死亡[18]。而外泌体也参与神经炎症和氧化应激的过程,两者又均是Aβ积累和tau蛋白过度磷酸化的触发因素[19]。外泌体可释放炎性因子,使其从一个细胞扩散到另一个细胞,近而引发炎症级联反应[8],而除释放炎性因子外,外泌体还可以通过响应病原刺激而转移炎性介质,近而影响其他细胞[8]。因此,外泌体是传播炎症进而影响AD病程的关键因素。
除神经细胞相互作用外,受损细胞的外泌体还可与神经胶质细胞相互作用。因此,星形胶质细胞不仅不能支持保护神经元,而且会通过促进邻近细胞的二次凋亡而产生有害于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本身的毒性环境。AD中星形细胞凋亡的机制可能与分泌蛋白酶活化受体4 /神经酰胺的外泌体有关,星形胶质细胞倾向于与外泌体更多地相互作用并积累大量的Aβ原纤维,随后,这种积累导致体内溶酶体系统改变,进而诱导细胞死亡[20]。此外,研究发现中性鞘磷脂酶2 (neutral sphingomyelinase 2,nSMase2)可以调节外泌体的分泌,缺乏nSMase2的星形胶质细胞可以免受Aβ诱导的细胞凋亡[21]。
尽管外泌体参与了AD的发病进程,但在神经系统中他们是活跃的使者,可以保护神经元免受氧化应激[22]。在AD研究中,发现外泌体既在毒性蛋白的扩散中起作用,又在Aβ的清除上起作用,可减轻神经系统的损伤。在细胞外液中,源自N2a细胞的外泌体可以消除来自AD大脑衍生的Aβ造成的突触可塑性的破坏。这主要因为外泌体表面蛋白(PrPc)对Aβ低聚物具有高度的亲和力,使得外泌体可以结合并隔离小的oAβ[23],进而防止Aβ干扰神经元功能。
4 外泌体作为AD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在有明显的临床症状表现之前,生物标志物对提高AD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以及监测AD的生物学活性是必要的。外泌体是各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细胞与细胞外液之间特定毒性蛋白质的载体,并且其中的毒性蛋白质可以在疾病的早期阶段被检测到。因此,从体液中检测外泌体中的特定毒性蛋白有望成为诊断早期AD和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一种方法[24]。
外泌体具有通过胞吞作用穿越血液屏障的能力,且致病状态下主要含疾病特异性或失调的微小RNAs (microRNAs, miRNAs),这使得miRNA在疾病诊断中占据优势,并有望成为新的 AD诊断生物标志物。Lugli等[25]通过对比AD病人和健康对照者血浆中miRNAs的差异表达,发现共有20个miRNAs被下调,4个miRNAs被上调(miR-548at-5p、miR-138-5p、miR-5001-3p和miR-659-5p)以及7个明显下调的miRNAs。其中miR-342-3p被认定是诊断AD的独立生物标志物。Cheng等[26]的一项研究对血清外泌体miRNA进行了测序分析并发现14种可能用作生物标记物的miRNAs明显上调:miR-361-5p、miR-30e-5p、miR-93-5p、miR-15a-5p、miR-143-3p、miR-335-5p、miR-106b-5p、miR-101-3p、miR-425-5p、miR-106a-5p、miR-18b-5p、miR-3065-5p、miR-20a-5p和miR-582-5p;3种可能用作生物标记物的miRNAs明显下调。综上所述,外泌体中的miRNA可以为AD提供准确的早期诊断。
数项关于早期检测AD病人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CSF)和血浆中Aβ1-42的研究表明,比起血浆中的Aβ1-42,CSF中的Aβ1-42更适合用作AD生物标志物[27-30]。由于CSF中Aβ主要来源于病变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因此检测CSF外泌体中的Aβ1-42有望改善AD的诊断敏感性。在联合检测CSF P-tau和Aβ1-42的研究中,CSF外泌体中Aβ1-42和P-tau蛋白的联合检测对AD的早期诊断可能更有价值[31]。Fiandaca等[32]进一步研究发现,血浆中神经细胞来源的外泌体中P-S396-tau、P-T181-tau和Aβ1-42的水平可以预测在临床发病前长达10年的AD发生。此外,外泌体中Aβ1-42的表达水平还可以作为检测AD病程进展的标志物。
5 外泌体对AD的治疗作用
多项研究表明,间充质干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可促进神经元功能恢复[33]、神经血管可塑性[34-35]以及修复脑外伤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受损伤组织,实现神经保护的作用。因此,有可能使用间充质干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对AD进行治疗。此外,通过大脑内给药的方法,可利用外泌体表面糖鞘脂上富集的聚糖使外泌体与Aβ结合,从而起到有效清除Aβ的作用[36],这为AD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
由于外泌体RNA的转运能力、在体液中的稳定存在以及穿越血脑屏障的能力,其可以用作载体,通过递送核酸片段(例如miRNA和siRNA)来治疗AD。多项体外和体内研究表明,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能将功能性miRNA转移至神经细胞并促进神经元重构,抑制细胞凋亡,从而促进神经元功能恢复[35,37]。例如,Xin等[35]证实富含miR-133b的外泌体可促进神经血管可塑性,从而大大增强了神经细胞的生长。在另一项研究中,通过外泌体递送miR-124a增强了星形胶质细胞表面兴奋性氨基酸转运蛋白2的表达,从而调节突触活性并改善谷氨酸的吸收[38],该方法也有望减轻AD的神经元凋亡。
6 小结
综上,由于外泌体的细胞起源和形成条件的不同,外泌体可能对AD的发病过程产生“双刃剑”作用:既可以传播有毒蛋白质和诱导AD进展,又可以清除毒性蛋白,减轻神经系统的损伤。此外,由于其独有的生物学特性,外泌体可能还将成为AD早期诊断和治疗的新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