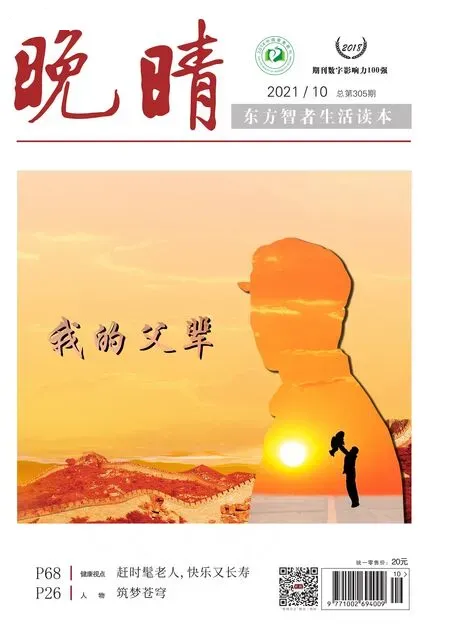父亲的算盘
文 鲍海英
小时候,父亲是村里的会计。那时候,村里是大集体,队里收获多少担粮,谁家挣了多少工分,每户应该分多少粮,全凭父亲来算账。没有计算器,每逢算帐,父亲总要随身带一个算盘。在我学珠算前,我对父亲的算盘非常好奇,什么数字只要经算盘一算,又快又好,准是错不了。直到今天,在我家里,父亲还珍藏着一个边框早已被磨得发亮的红木算盘。
这个红木算盘,由一个横梁和四个边框组成长方形,分上下两档,共有13个档。梁上每档有两颗珠子,梁下每档有5颗株子,共有91个黑珠子。算盘的四个角,被用古老的铜片箍着,被父亲擦得锃亮锃亮,看上去显得既美观,又结实。
后来农村分田到户,父亲从村里会计退下来后,除了种地,父亲就在家做杂货店生意。做杂货店生意,经常要盘货,几十年来,这个算盘一直和父亲寸步不离,如影相随,并被父亲一直当着心爱宝贝,使用至今。
对于算盘,也许我天生缺少悟性。记得上小学时,学到珠算那一章,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带一个算盘。母亲给我买了一个比较便宜,重量又轻,塑料珠子做成的算盘。当我把那个塑料珠子做成的算盘,带到学校,岂料不少同学投来羡慕的眼光,因为这样的轻便算盘,更符合小学生学珠算使用。
学珠算,需要背口诀,对数字天生木讷的我,自然学的不很精通。小时候的珠算课,很快就糊弄过去了,学会学不会,老师也不怎么计较。回家后,父亲倒是很在意,常常逼迫我一遍又一遍,让我学着书本的样,把一道道算术题,用算盘反复演算给他看。
也许因为父亲在村里当会计久了,在父亲的眼里,算盘就是吃饭的工具,我必须学会熟练使用。
我高考那年,正当我为学什么专业犯愁时,父亲看见桌上摆放的红木算盘,当即一拍脑袋,就帮我选定了会计这个专业。其实,在我的骨子里,我对那些枯燥无味的数字,比较反胃。我更崇尚的是成为作家,我喜欢的是诗歌和文学。
上大学后,我对会计终于有了兴趣。那年我毕业后成功应聘到一家工作单位,晚上我回到家里,父亲兴高采烈,拿来他心爱的红木算盘,让我把杂货店的账目,一笔笔帮他算算。之后我再用计算器复核,我发现我用算盘算出来的数字,与计算器毫厘不差。看着账目上结余的钱,操劳一生的父亲,欣慰地笑了。
——珠算系列介绍 新中国珠算
——珠算系列介绍 清代珠算
——珠算系列介绍珠算与《数术记遗》
——珠算系列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