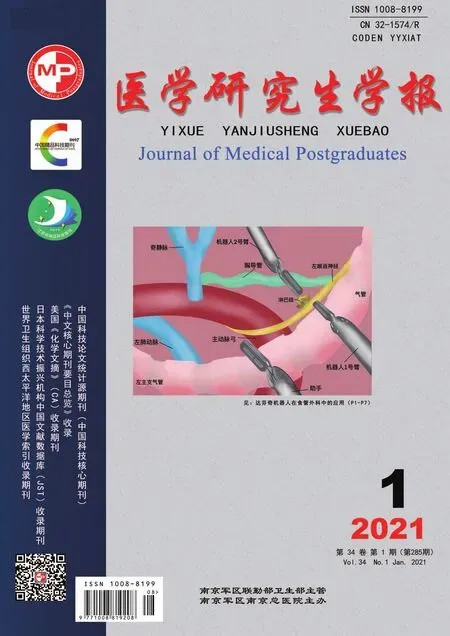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蔡金原综述,朱传龙审校
0 引 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已在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大流行[1],其病原体被命名为SARS-CoV-2,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近距离接触传播,可能存在气溶胶传播等[2]。最近有流行病学报道为SARS-CoV-2在家庭和医院的人际传播提供了证据[3-4]。随着全世界科学家争相研究SARS-CoV-2,其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的相互作用关系日趋明朗。ACE2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 system,RAS)的重要调控因子,与冠状病毒感染和致病过程密切相关,因此有望成为目前防治COVID-19最重要的潜在靶点之一。本文就ACE2的生理功能、ACE2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作用及靶向ACE2的防治策略作一综述,以期对COVID-19再认识与药物研发提供帮助。
1 RAS与ACE2的功能
RAS是由一系列酶促级联反应组成的体液调节系统,主要参与调节血压、水、电解质的平衡。其主要生理过程始于肝介导合成血管紧张素原(angiotensinogen,ATG)[5],随后肾产生肾素并以ATG为底物生成无活性的血管紧张素Ⅰ(angiotensin Ⅰ,Ang Ⅰ),Ang Ⅰ在ACE的作用下转化为AngⅡ,后者主要与AngⅡ1型受体(angiotensin Ⅱ type 1 receptor,AT1R)结合,成为ACE发挥促进血管收缩、增加血管通透性与介导炎症反应作用的主要效应分子[6-7]。AngⅡ还可激活解整合素-金属蛋白酶17(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17,ADAM17),ADAM17作为脱落酶可切割ACE2,使ACE2丧失功能[8]。
自2000年有研究从心力衰竭和淋巴瘤患者的cDNA库中鉴定出了ACE2,对RAS通路的研究有了新方向[9-10]。在2003年SARS暴发后,ACE2被证实为SARS-CoV的功能性受体[11],一度成为焦点。ACE2是一种具有单羧基肽酶活性的金属蛋白酶,虽与ACE同源,但生理作用却截然不同。ACE2主要通过裂解AngⅡ生成Ang-(1-7)并与受体Mas结合,发挥血管扩张、抗血栓、抗增殖和抗纤维等作用[12]。以ACE-AngⅡ-AT1R轴和ACE2-Ang-(1-7)-Mas轴的拮抗作用为核心,ACE2在多个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 ACE2与SARS-CoV-2感染
SARS-CoV-2与SARS-CoV同为β科属冠状病毒[13],具有79.6%的序列同一性[14]。有报道显示COVID-19患者的临床和病理特征与SARS-CoV感染的表现较为接近[15],表明SARS-CoV-2与SARS-CoV确有一定实质性的相似之处。SARS-CoV表面的刺突糖蛋白(S蛋白)介导对其受体ACE2的识别和膜融合[16-17],在感染过程中,S蛋白被切割成S1和S2亚基,S1包含的受体结合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RBD)可直接与ACE2的肽酶域结合[18]。有学者推测ACE2可能也是SARS-CoV-2受体,现已充分证实[14-19]。最新的研究解析了ACE2和SARS-CoV-2 S蛋白三聚体的高分辨率结构[20],揭示SARS-CoV-2两个三聚体S蛋白与ACE2二聚体结合,并利用ACE2蛋白酶裂解S蛋白,促进细胞内吞作用。SARS-CoV-2与ACE2的结合力为14.7 nm[21],比SARS-CoV强10~20倍,这一结果有助于解释SARS-CoV-2为何具有超强的感染性。在病毒结合ACE2的过程中,跨膜蛋白酶丝氨酸2(transmembrane protease serine 2,TMPRSS2)对病毒S蛋白进行剪切激活的辅助作用同样必不可少[22],TMPRSS2还能剪切ACE2的C末端片段,加强病毒的入侵[23],换言之ACE2和TMPRSS2共表达是新冠病毒进入细胞所必需的。此外,ADAM17对ACE2有削弱作用,可能也在SARS-CoV-2侵入宿主细胞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总体上看,ACE2在体内的表达水平并不高,相较而言TMPRSS2分布更广泛[24],基于此,可认为ACE2是SARS-CoV-2初次感染的限制因子。而SARS-CoV-2几乎可利用所有(除外小鼠)的ACE2蛋白作为受体进入可表达ACE2的细胞,却不能直接进入不表达ACE2的细胞[14],同样提示病毒感染与ACE2的分布密切相关,据此可推测ACE2高表达的部位可能是病毒感染的主要靶器官。之前有单细胞测序显示,ACE2在人回肠、心脏、肾、膀胱、食道、肺和气管中从高到低表达[25],但在临床上,COVID-19患者肺部系统症状更多见,呼吸道与外界连通带来更多的肺组织暴露是较为肯定的一个因素。与之相对的,消化系统症状发生率却远低于呼吸系统。在早期的一项临床研究中,38例COVID-19患者仅发现1例有腹泻[15]。最新的Meta分析显示,与发热和咳嗽相比,腹泻、恶心和呕吐等症状相对较少[26],表明肠上皮实际上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容易被感染。众所周知,肠上皮长期以来直接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为应对微生物威胁,肠道细胞进化生成大量的抗菌肽并不断增强黏膜屏障。有鉴于此,王军平等[27]最近发现,肠道潘氏细胞特异性分泌的人类防御素5以39.3 nm的高亲和力结合ACE2,并妨碍随后的SARS-CoV-2 S1的募集,发挥呈显著剂量依赖性的防御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解释为何COVID-19患者消化道症状不常见;另外,ACE2与肠上皮细胞与氨基酸转运载体B0AT1的结合可覆盖ACE2被TMPRSS2剪切的位点[20],相较于肠上皮,肺部B0AT1的表达水平很低,这也是肠道不如肺部易感的另一个可能原因。
由于编码ACE2的基因在X染色体(Xp22.2)上,理论上女性可能更易感,但大量中国的临床数据显示男性患者比例更高且更易重症化。Zhao等[28]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亚裔男性肺中表达ACE2的细胞类型和占比高于女性从而具有更高的ACE2表达丰度,提示ACE2表达可能存在性别差异。此外,一项美印联合研究显示,男性感染SARS-CoV-2后,其体内病毒清除较女性有明显延迟。该研究还发现ACE2在睾丸中表达极高,在卵巢中却几乎检测不到,推测睾丸可能是潜在的病毒储存库[29]。然而,另有中美联合研究称其男性受试患者被感染1个月后精液中并未检出新冠病毒[30],此后亦有其他研究得到男性COVID-19患者睾丸和生殖道并未受到感染的结果[31]。考虑到上述研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样本量相对较小、可能存在选择偏倚等[29-31]。SARS-CoV-2感染是否存在性别“偏好”有待于更大规模的人群数据加以验证。
近来,ACE2被鉴定为一种干扰素刺激基因,是细胞天然抗病毒系统的一部分[32-33]。换言之,SARS-CoV-2感染人体宿主细胞后,人体免疫系统为抑制病毒而激活的干扰素通路反而有助于新冠病毒突破免疫屏障,即SARS-CoV-2可以通过劫持人体天然抗病毒通路,诱导人类细胞表面受体ACE2的表达,进一步增强其感染力。
3 ACE2与SARS-CoV-2致病
由于SARS-CoV-2的受体ACE2在人体组织器官中广泛存在,COVID-19很可能累及全身多个系统。与SARS相似,COVID-19一方面引起肺部和心血管系统的损伤,另一方面,病毒刺激免疫系统掀起细胞因子风暴,加剧肺和血管内皮系统的炎性病变,甚至诱导T细胞大量凋亡引起免疫耗竭和二次感染[34],这可能是COVID-19重要的病理生理机制。
ACE2缺乏可导致呼吸衰竭,见于败血症、肺炎、SARS等[35-36]。以往的研究表明,SARS-CoV感染下调ACE2从而导致体内AngⅡ水平升高[37],肺血管通透性增加,引起渗出、水肿等,严重者还可通过激活免疫和炎症相关信号通路,进一步加剧组织损伤。有研究发现感染SARS-CoV的小鼠肺内ACE2的表达明显减少,AngⅡ明显升高,ACE无明显改变,而用重组人ACE2(rhACE2)可改善ACE2敲除小鼠肺水肿等症状,提示ACE2表达降低可能在SARS-CoV介导的肺损伤中起重要作用[36-38]。另有研究显示,AT1R表达基因缺失的小鼠相较于野生型小鼠肺功能显著改善,且肺水肿程度更轻[39],AngⅡ2型受体(AT2R)失活的小鼠则急性肺损伤加剧。可确定的是,ACE、AngⅡ和ATlR的高表达加重组织损伤,而ACE2和AT2R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症状。有研究者报告,SARS-CoV-2感染确诊患者的血浆C反应蛋白和AngⅡ均高于健康对照者,且升高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正相关[40],这一发现为COVID-19的发病机制提供了一定依据。
临床上,SARS-CoV-2感染除典型呼吸道症状之外,还有相当比例的患者有心肌损伤表现,可能与RAS失衡和肺损伤造成的缺氧及代谢障碍诱发原有心血管疾病加重有关。而病毒入侵所致ACE2表达下调引起的内皮功能受损、血压升高、心肌收缩力减弱与因AngⅡ增多激活转化生长因子-β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上调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而加重的氧化应激、炎症和纤维化可能对心肌损伤也有一定影响[41]。此外,刘映霞等[34]的报道显示,有1例患者发病后5d发展为暴发性心肌炎,心脏生化指标显著升高伴左心功能急剧下降的同时体内病毒载量非常高,持续1周以上,有学者据此认为心肌细胞可能受到病毒直接攻击,但目前缺乏更多证据。
大多数学者同意COVID-19危重患者的严重症状与细胞因子风暴有关,如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目前已有部分病理学证据[42]。据报道,首批确诊COVID-19的严重感染者中至少有1/3遭遇过细胞因子风暴[15],患者的血浆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不同程度地升高,病情更严重的患者其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重组人干扰素诱导蛋白-10、单核细胞趋化因子-1、巨噬细胞炎症蛋白-1A和肿瘤坏死因子-α等Th1型促炎细胞因子水平更高,而这一结果早在十多年前的SARS患者身上就已有所体现。ACE2对细胞因子风暴而言不可或缺,一方面,病毒通过ACE2入侵激活了免疫系统诱发细胞因子风暴,一份SARS患者尸检报告指出,促炎细胞因子在表达ACE2的细胞中高表达,在无ACE2表达的细胞中则不表达[43],与前文所述SARS-CoV只进入表达ACE2的细胞这一研究结果互相印证。另一方面,ACE2的降低负调其肺内底物脱精氨酸缓激肽(des-Arg9bradykinin,DABK)的失活,增强了缓激肽受体B1(bradykinin receptor B1,BKB1R)的信号传导,进而降低DABK/BKB1R通路的失活效率,促进炎症因子释放[44]。除此之外,亦有类似研究显示AngⅡ可上调肾内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合成[45-46]。靶细胞释放的促炎细胞因子活化免疫细胞(包括单核-巨噬细胞、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并促使这些细胞向肺和血管壁趋化聚集引起局部炎性反应以清除病毒,同时释放细胞因子刺激免疫细胞形成正反馈,引发细胞因子风暴,导致 T细胞大量凋亡造成细胞免疫缺陷。有回顾性研究发现,SARS-CoV-2感染可引起外周血淋巴细胞减少,特别是CD4+和CD8+T细胞数量减少,CD4+T细胞产生IFN-γ也受到抑制,提示体内存在明显的免疫功能受损,可能与COVID-19的严重程度有关[47-48]。
然而,目前无研究能确切证明SARS-CoV-2感染宿主细胞会引起ACE2的表达下调,ACE2对于COVID-19发病机制的具体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虑SARS-CoV-2与SARS-CoV在基因序列、临床症状、感染过程等方面有较高的相似性,两者很可能共享相同或十分相似的致病机理,至少在入侵宿主细胞后下调ACE2表达并上调ACE-AngⅡ-AT1R轴的机制上应该是一致的。此外,并非所有SARS-CoV-2诱导的炎症反应都与ACE2有关,亦可能存在其他通路参与细胞因子风暴,换言之,ACE2与COVID-19的细胞因子风暴有多大程度的相关性目前仍无法定论。
4 ACE2与防治新策略
基于上述可能的机制,靶向ACE2的防治策略应运而生。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可抑制ACE的激活以阻止AngⅡ升高,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ARB)可通过阻断AT1R,减少AngⅡ与ACE2的结合,理论上二者均有减轻或延缓肺损伤的作用,动物实验证实,氯沙坦可减轻SARS的肺损伤程度[49],但同时不应忽视ACEI/ARB对ACE2-Ang-(1-7)-Mas轴的激活作用,有学者因此质疑其反射性地上调ACE2可能会加速SARS-CoV-2扩增,继发更严重的肺衰竭,目前仍需要大样本量的流行病学证据以明确合并心血管事件的COVID-19患者能否从ACEI/ARB获利。如前所述,动物实验显示rhACE2可改善ACE2敲除小鼠肺水肿等症状,故补充外源性ACE2可能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有研究发现,接受rhACE2治疗的ARDS患者体内AngⅡ很快下降,Ang-(1-7)水平迅速回升[50],表明其肺部ACE/ACE2平衡得到改善,但由于样本量较小,结果说服力还不够。目前rhACE2已投于临床试验,初步结果较为满意。有鉴于此,直接补充大剂量Ang-(1-7)可能疗效更佳,但Ang-(1-7)在体内半衰期过短(仅有数秒),目前尚未开展临床试验。
Kruse等[51]提出可向患者体内输注分离出的RBD以预先占据ACE2,但动物实验发现,排斥反应加剧了小鼠的肺水肿,研制ACE2抗体可能有助于达成这一目的。之前有报道称,重组ACE2与免疫球蛋白Fc片段的融合蛋白(rACE2-Fc)在小鼠的急慢性AngⅡ依赖性高血压模型中均显示出持久性的器官保护作用,且未发现不良反应[52]。受此启发,雷长海等[53]构建了一种由人ACE2的胞外结构域与人IgG1的Fc片段相连的融合蛋白,并发现其能强力中和SARS-CoV-2,对COVID-19的预防和治疗有巨大的潜在价值,目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此外,卡莫司他能够靶向针对TMPRSS2,巴利替尼可结合内吞调节因子AP2关联激酶1,抑制病毒入胞和细胞内组装,还可与细胞周期蛋白G相关激酶结合,降低病毒感染细胞的能力[54],但这些潜在的靶向治疗药物真实疗效与价值仍需开展随机临床试验方能明确。鉴于SARS-CoV-2的致病机制仍不明确,在确定药物抗病毒活性、控制不良反应的前提下,联合应用不同机制的抗病毒药物可能是更合理的选择[55]。
针对SARS-CoV-2的治疗性中和抗体的开发可能是获得控制COVID-19的标准化药物的相对较快的方法[56]。基于既往流行过的一些冠状病毒的疫苗动物实验显示出了可抑制病毒感染的多克隆抗体强应答[57-58]。此类概念验证试验结果表明,抗RBD抗体对SARS-CoV-2应有一定的抵御作用。最近发现,SARS-CoV抗体CR3022亦可与SARS-CoV-2 RBD结合[59],且CR3022的表位不与ACE2结合位点发生重叠。SARS-CoV-2与SARS-CoV虽具有高度基因同源性,但二者RBD并无明显抗体交叉反应性,一些已知的SARS-CoV治疗性中和抗体也不能有效地与SARS-CoV-2结合[22,59]。鉴于SARS-CoV与SARS-CoV-2在RBD上有所差别,基于SARS-CoV动物实验得到的结论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SARS-CoV-2,明确其中差异或为疫苗研发成功的关键所在。据WHO统计,当前疫苗研究已涵盖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等形式,目前尚无有效疫苗的出现[60]。值得一提的是,荷兰学者报道已鉴定出一种完全人源的单克隆抗体,可阻止SARS-CoV-2感染培养的细胞[61]。SARS-CoV-2中和抗体或可成为疫苗之外控制COVID-19的又一希望。
5 结语与展望
ACE2是目前已知的多种冠状病毒入侵人体的重要受体,与冠状病毒感染、致病和损伤密切相关。针对ACE2及其相关靶点设计防治策略是目前的最有望取得突破的研究焦点之一。迄今为止,ACE2与感染风险之间的相关性仍未明确,其他受体或因子参与的具体机制、炎症介质级联反应的具体过程、免疫系统在其中的具体作用亦是未知。但随着全世界科学家全力投入研究,ACE2在COVID-19中的作用终将被阐明,更有针对性的防治手段也将被发掘应用。COVID-19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历史表明这很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冠状病毒大流行,对其更深层次机制的探究无论对当下还是对后世都将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