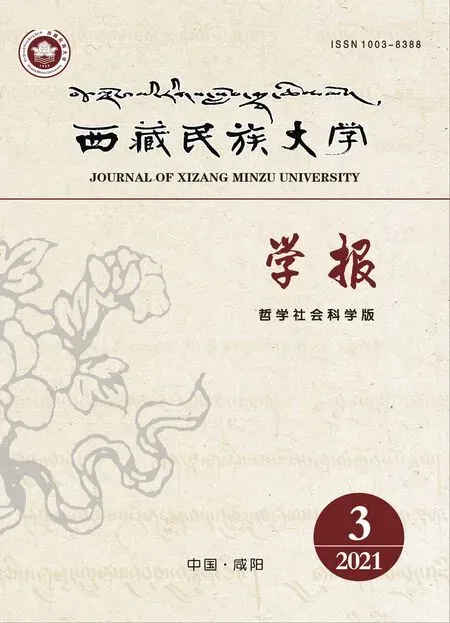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奴”等群体社会地位考述
冉永忠,李博
(1.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陕西 咸阳 712082;2.陕西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46)
关于敦煌陷蕃之后的社会变化,目前有不少学者从社会组织结构、民族成分结构、政权组织结构、土地分配政策等多个方面展开研究,笔者以为探讨敦煌陷蕃之后社会的深刻变化还应考虑当地居民变成吐蕃属民以后的身份地位是否有根本性变化,尤其是是否转变为社会地位较低的“奴”等群体①,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可以厘清吐蕃在敦煌地区的施政措施,也可以由此管窥吐蕃本土的相关社会制度。
一、吐蕃占领敦煌之后的人口掳掠现象
781年,吐蕃占领敦煌,敦煌进入吐蕃统治时期②。一般认为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地区汉人地位是低下的、悲惨的,其主要证据在于《全唐文》的记载:“臣尝仕于边,又尝与戎降人言。自瀚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聚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及霜露既降,以为岁时,必东望啼嘘。其感故国之思如此,陛下能不念之?”[1](P7851)这段记载成了人们界定吐蕃占领下敦煌百姓地位的有力证据,但需要注意的是,沈下贤的记述不一定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他作为唐朝的一名知识分子,比一般人拥有更强烈的荣辱感,所以当一直处于唐朝统治下的敦煌突然被称之为蛮夷的吐蕃所占领,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接受的,甚至是屈辱的,其所记载的相关历史必然会充满个人感情,损贬“攻陷者”和夸大吐蕃统治下敦煌地区人民的悲惨生活也是难以避免的。
吐蕃在进攻河西、陇右和攻陷敦煌的战争中,确实俘掠过一些唐朝士兵和百姓,用来为吐蕃统治者服务。如787年,吐蕃攻汧阳、华亭(今甘肃华亭一带),“虏又剽汧阳、华亭男女万人以畀羌、浑,将出塞,令东向辞国,众恸哭,投堑谷死者千数。”[2](P6097)可见,当时掳掠汉人的规模不小。直到吐蕃占领敦煌以后,他们仍从其统治下的敦煌地区抄掠汉人。S.3287《吐蕃子年(九世纪前半)五月沙州左二将百姓氾履倩等户口状上》(以下简称《氾卷》)记:“户(氾国珎)死。妻(张念念)在。男(住住)在。男(不採)在。小妇(宠宠)出度。奴(紧子)论悉□夕将去。奴(金 刚)□。婢(落娘)已上並论悉□息将去□。”[3](P377)P.T.1083《禁止抄掠汉户沙州女子牒》载:“往昔,吐蕃、孙波与尚论牙牙长官衙署等,每以配婚为借口,前来抄掠汉地沙州女子。其实,乃佣之为奴。”[4](P52)可见,这一时期的抢掠现象仍有发生。但需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如从S.3287《氾卷》所记的五户百姓来看,被吐蕃官吏抄掠的只有氾国珎一户,而且被掠之人也只是其家庭成员中原本就属于奴或婢身份的人。
二、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奴”等群体考析
(一)“奴”等群体的相关记载
在关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文献中,经常出现“奴”“婢”“奴仆”“奴户”“奴隶”等词,这些称谓无疑表明了这部分群体在当时社会中较低的身份地位。但他们的地位低到何种程度?群体规模有多大?是否是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生产形式?对此需要加以认真考证和分析。这是判断当时敦煌地区社会形态的依据。
“奴”。P.T.1071号文书《狩猎伤人赔偿律》中,有大量关于“奴”[4](P9-30)的记述。P.T.1080号文书《比丘尼为养女事诉状》:“你比丘尼如能收养,视若女儿亦可,佣为女奴亦可。”[4](P48)P.T.1083号文书《据唐人部落禀帖批复的告牒:禁止抄掠汉户沙州女子》载:“……其实,乃佣之为奴。”[4](P52)S.3287《氾卷》载:“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户(氾国珎)死。妻(张念念)在。……奴(紧子)。奴(金刚)□。……[]部落已后新新旧生口、(定国)妻(王)死……奴(定奴)奴(弁奴)”[3](P377-378)等。
“婢”。S.3287《氾卷》记载“户(索宪忠)妻(阴)……婢(目目)……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户(氾国珎)死。妻(张念念)在。……婢(落娘)已上並论悉□息将去。□婢(善娘)婢(□□)……[]部落已后新新旧生口、(定国)妻(王)死……婢(宜娘)(荣娘)婢(星星)”[3](P376-378)。由此可见,婢作为索宪忠和氾国珎的家庭成员与其妻子儿女同样登记于户册之上。
“奴仆”。P.T.1081号《关于吐谷浑莫贺延部落奴隶李央贝事诉状》文书载:“张纪新禀:辰年,我从吐谷浑莫贺延部落之绮立当罗索(人名)处以五两银子买了名唤李央贝的男性奴仆。”[4](P49)《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记载:“南面直达卡果江多邦(Khar-go-ca(ng)-do-spong)之奴仆的耕地,两地间有手砌圆石堆作地界标记。”[5](P316-317)“由此向前,沿着水渠直达以陡峭山石分开的吉笑加卡水渠的山谷,又有一个手砌的圆石堆为标志,穿过沙漠沙地,进入东南线上,直达达热·席义奴仆的耕种地。”[5](P318)“十八个人一伙,有母亲、父亲、孩子、主人和奴仆,都生了病,或许他们因此身死,他们要求人们离开(dgol)(或译:他们恭敬地要求人们与他们隔离)。”[5](P324)《吐蕃简犊综录》中记载了“论努罗之奴仆已在……冬季田租之对半分成于兔年。”[6](P37)
“奴户”。P.T.1071号文书中,有大量关于“奴户”[4](P9-30)的表述。《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载:“及至狗年(玄宗天宝五年,丙戌,公元746年)……征四茹牧场之“大料集”,收集已摊派之一切奴户之赋税,明令奖谕论·结桑达囊。是为一年。”[7](P118)
“奴隶”。《古藏文文献中关于新疆的资料》中有:“在大斗军(Dang-to-kun),墀扎、穷空、桑空三人已经分到了奴隶(Brang)”[5](P40)和“沙州比丘尼瓜氏吉玲之女奴瓜氏丹丹;比丘尼通吉”[5](P64)的记载。
(二)吐蕃社会“奴隶”相关问题的探讨
关于吐蕃社会的“奴隶”问题探讨,事关对吐蕃社会基本形态的认知,也关系着对吐蕃占领敦煌地区后社会性质变化的研究。
1、吐蕃社会的奴隶来源
奴隶通常指失去人身自由并被奴隶主任意驱使的人,其来源主要是战俘、罪犯、破产平民、奴隶的后代等,他们在成为劳动工具的同时也被当成一种有价值的货物进行赠赐与交易。关于吐蕃奴隶的文献记载不在少数,但多在于统治阶级向下属赏赐的名录,关于奴隶来源的直接记载几乎很难见到,仅在敦煌出土的一些文书中能见到零星记载。
在关于吐蕃时期的文献记载中,战俘成为奴隶的记载并不多见。吐蕃政权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先后征服了青藏高原上的许多部族,如苏毗、象雄、吐谷浑、党项等,但并没有将被征服的民众变为各贵族的奴隶,而是保留其原有治理模式,对地方首领进行任命。如吐蕃征服苏毗、象雄后,仅按茹、千户进行重新编制,使其与吐蕃五茹的体制相类似,而且苏毗还保留了小王。吐谷浑被吐蕃攻灭后,吐谷浑被编为万户部落,受吐蕃调遣,吐谷浑小王还成为吐蕃的高级官员。可见,大规模将战俘变为奴隶的现象较少发生,而是派官员或者委托原来的统治者对征服地的居民进行管理。姜伯勤指出“官配手力一般由战俘或罪人充当,其地位略近唐代的杂户”[8](P17),也可以理解为战俘和罪人一般都变成了身份类似于唐代杂户的群体。如此,吐蕃社会鲜有战俘变为奴隶现象的原因也就更加明朗了。
关于吐蕃社会文献中零星出现的奴隶来源记载主要有以下几种:
附作奴③。据P.3774《丑年(821年)十二月沙洲僧龙藏牒——为遗产分割纠纷》(以下简称P.3774号文书)载:“大兄初番和之日,齐周附父脚下,附作奴。”[9](P284)该文献中明确交代了“奴”的一种来源,即“附作奴”。此处主动“附作奴”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里,是没人愿意当奴隶的,更无人自愿变身为奴隶,故此处的“奴”应该比奴隶的地位要高。从其后文“便有差税身役”的说法来看,这种“附作奴”的“奴”应该是不用承担差税身役的。所以,逃避差税身役应是他附作奴的主要动机。
将收养子佣为奴。P.T.1080号文书载:“你比丘尼如能收养,视若女儿亦可,佣为女奴亦可。”[4](P48)此处记载了一贫人将无力抚养的女婴送于一位比丘尼,至于送给比丘尼以后女婴的身份地位,将由比丘尼来决定。通过后文“彼女亦不似以往卖力干活”[4](P48)的记载来看,该女名为收养子实则为奴仆,但此处又隐隐透露了该奴的特殊身份地位,即主人对已佣为奴的女子另谋出路而不卖力干活这一情况采取了上诉,而不能直接行使主人的生杀大权。官府最后的判词“按照收养律令,不得自寻主人,仍照原有条例役使”[4](P48)也再次证明了她被役使的奴仆身份。
卖身为奴④。P.T.1081号文书载:“李央贝自证:我当初属莫贺延部落,卖身契为幼年九岁时所立,名叫李央贝。”[4](P49)该文书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李央贝卖身为奴的时间(九岁时)和方法(立卖身契)。针对这一诉状,最后的判词为“严格按照卖身契所书内容处理。”[4](P50)足见这种卖身为奴的行为是受统治阶层认可的,也是受当时法律保护的。而这种保护从另一方面说明,若某人想要卖身为奴,是需要严格按照一定程序来完成的,并不能随意而为。
将抄掠的汉户佣为奴。P.T.1083号文书载:“……每以婚配为借口,前来抄掠汉地沙州女子。其实,乃佣之为奴。”[4](P52)该文书记载了吐蕃、孙波与某些尚论长官衙署等将抄掠来的汉户女子佣为奴的事件。从这一记载来看,将抄掠对象佣为奴的数量应该不少,但统治集团对此类现象进行了禁止,并强调说“不准如此抢劫已属赞普之臣民”[4](P52),不能抢掠已属于吐蕃占领地方的臣民为奴。
总体来看,以上几种来源的奴隶数量都非常有限,而且有些来源途径还受到当时统治阶层的严格限制甚至禁止。
2、吐蕃社会奴隶身份的解除
通常,奴隶可以通过逃亡、赎身、立功等行为重新成为自由人,但这种机会一般都比较少。在吐蕃社会的文献记载中,关于奴隶重新成为自由人的现象大致有以下几类。
自由选择。从文献记载来看,吐蕃社会中的某些情况下,奴是可以自由选择其归属的,如P.T.1071号文书中多处记载:“在放箭杀人者被处死后,另一半奴户,愿为何人之奴,何人之民,可听其自愿。”[4](P11)文书中交代了在有限的情况下,即在放箭杀人者被处死之后,奴户可以自由选择为何人之奴,何人之民,获得更为自由的身份。而在P.T.1080号文书的判词中,特别强调“不得自寻主人”[4](P48),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自寻主人的情形是存在的。这与奴隶制社会的残酷统治是不符的。
析出为户。P.3774号文书载:“大兄初番和之日,齐周附父脚下,附作奴。后至佥牟使上析出为户,便有差税身役,直至于今。”[9](P284)这里交代了“奴”的一种解除,即“析出为户”。从文献的叙述来看,析出为户的目的在于摊派差税身役以增加统治阶级的收入。毫无疑问,这表明统治阶级已经不需要依靠严酷的奴隶制劳作来实现剥削,而是变为更加隐秘的剥削方式,如此一来,奴隶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社会大环境。
3、吐蕃社会被称为“奴”等群体的权益
拥有土地。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建立在土地资料占有制基础上的劳动关系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性质。吐蕃社会,被称为奴的群体很多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如前文所述的“奴仆”条中出现了奴仆拥有土地的现象,还指明了所拥有土地的类型即耕种地。
从敦煌文书的记载来看,吐蕃占领敦煌以后,大量汉族百姓不仅没有被迁往他处,或者变成统治阶层的奴隶,反而通过一些政令确保他们拥有住房和土地等,保持其小生产者的地位,如S.5812《丑年令狐大娘诉状》载:“论悉诺息来日,百姓论宅舍不定,遂留方印,已后见住为主,不许再论者。又论莽罗新将方印来,于亭子处分百姓田园宅舍,亦不许侵夺论理。”[10](P116)这表明,在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当地百姓因房屋和土地产权等问题发生过一些纠纷,吐蕃也曾派员进行处理。从文中也可以看出,处理纠纷的原则为“见住为主”,即基本上维持现状,这是有利于实际居住者的,也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
在S.9156号文书《吐蕃年次未详(九世纪前半)沙州诸户口数地亩计簿》中[3](P417-418),因有大量百姓拥有土地的具体记载,一些学者将这份文书定性为写于吐蕃占领时期的田册残卷,主要记录了元琮、武朝副等21户敦煌百姓的占田数。此外,S.4491号文书《吐蕃年次未详(九世纪前半)沙州诸户口数地亩计簿》[3](P418-420)也登录了至少26户⑤人家的田亩数。这些文献中均记载的是某一户百姓的占地情况,而不是某一奴隶主的占地面积。可见,以每户人口为单位的土地分配是当时敦煌地区土地分配的主要形式。
拥有劳动工具。吐蕃社会的“奴仆”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的这些土地一般不会由别人来耕种,只能靠自己。如此,拥有耕种所必需的劳动工具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这种情况还尚未在文献记载中发现相关记载,但却是可以肯定的。
拥有剩余的生活资料。吐蕃社会的“奴仆”既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也拥有相应的劳动工具开展自由劳作,那么他们在劳作后就会有产出,就能生产出些许剩余农产品,这可以从他们要承担田租和赋税的记载中得以证实,如“论努罗之奴仆已在……冬季田租之对半分成于兔年。”[6](P37)和“狗年……收集已派之一切奴户之赋税。”[11](P24-25)这两个记载表明,“奴仆”“奴户”是有能力靠自己的劳作生产一定数量农产品的,并且在完成田租和赋税后还有部分产出以满足自己的生存生活需要,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完成田租和赋税这类任务,也不可能满足上一阶层的剥削,上一个阶层更不可能将土地租给或分给他们耕种。当然,若没有多余的产出,他们自己也无法继续生存下去。
拥有家庭。“在大斗军(Dang-to-kun),墀扎、穷空、桑空三人已经分到了奴隶(Brang),并为他们领取的奴隶及其家庭,登记了各自的名字,以及如何纳税(或受惩罚,或强制服役),均写于一份共同的契约中……”[5](P40)从该文献中“奴隶们”的表述来看,它记载了墀扎、穹恭、桑恭3人均分得了一定数量的奴隶,具体数量虽无从考证,但至少说明这批称之为“奴隶”的人是不少的,而且他们还有家庭,更为关键的在于奴隶们的家庭是被统治阶层认可的,否则没必要对其进行登记。另外,在P.T.1071号文书《狩猎伤人赔偿律》中,有大量关于“奴户”的称呼,这表明“奴隶”拥有家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马克思认为:“在古代世界,城市连同属于它的土地是一个经济整体;而在日耳曼世界,单独的住宅所在地就是一个经济整体,这种住宅所在地本身仅仅在属于它的土地上占据一个点;这并不是许多所有者的集中,而只是作为独立单位的家庭。”[12](P481)由此可见,这种拥有家庭的“奴隶”是一种拥有较大劳作自由的劳动者。S.5812《丑年令狐大娘诉状》也明确记载了吐蕃占领敦煌以后为保障仍居住在敦煌地区居民住房的具体做法,即“见住为主”。可见,吐蕃占领敦煌以后,并不是将大量汉族百姓变成统治阶层的奴隶或者迁往他处,而是通过政令确保其拥有安身之处,维持社会生产的稳定。
受到法律保护。《西藏通史》记载:“……后来,子松那布之妻巴曹氏对娘氏奴户骄蛮横暴,威吓时加,恣意侮辱,且以妇女阴部辱咒之。娘·曾古心中不服,来到森波杰赤邦松面前,含冤负屈而诉苦,道:‘我实不愿为念氏之奴’”[13](P39)。从此处可见,吐蕃的“奴”是具有申诉权的。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文书中载:“另一半奴户,愿为谁之民,谁之奴可听其自择。”[4](P21)该文书是吐蕃时期的法律文书,其表述具有普遍的社会认可性,在对被处死者的奴户进行处理时,允许其自由选择为何人之奴,何人之民,说明在当时的法律规定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一定的自由选择权,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奴隶所不能享有的权利。敦煌吐蕃文书中关于此类现象的记载不在少数,说明其覆盖的群体范围是相当宽泛的。P.T.1083号《据唐人部落禀帖批复的告牒:禁止抄掠汉户沙州女子》文书中载:“……每以婚配为借口,前来抄掠汉地沙州女子。其实,乃佣之为奴。为此,故向上峰陈报,不准如此抢劫已属赞普之臣民。”[4](P52)可见,政府明确规定不允许吐蕃统治者抄掠被征服地方的居民作为奴隶,而要将其当作赞普的臣民一致看待。
4、吐蕃社会被称为“奴”等群体的义务
缴纳赋税。吐蕃本部很早就建立起了基于牲畜和土地的赋税征收体系,最具代表性的税种为牛腿税、田地贡赋和关卡税,如“及至牛年(高宗永徽四年,癸丑,公元653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于‘祜’定牛腿税,(肉类赋税)。达延莽布支征收农田贡赋。”[7](P101)“及至龙年(高宗显庆元年,丙辰,公元656年),赞普驻于美尔盖,大论东赞于‘仄木’之玛尔地方,征收牛腿税。”[7](P102)“及至蛇年(高宗总章二年,己巳,公元669年),赞普驻于悉立之都那,吐谷浑诸部前来致礼,征其入贡赋税。”[7](P103)“及至龙年(中宗嗣圣九年,太后长寿元年,壬辰,公元692年),多思麻之冬会于甲木细噶尔举行,收‘苏毗部’(孙波)之关卡税。”[7](P107)
吐蕃社会的纳税主体较为明确,一般以户为纳税单位,主要为牧户和奴户。如“及至鸡年(中宗景龙三年,己酉,公元709年),赞普驻于泥婆罗。……征调腰茹牧户大料集。”[7](P110)“及至狗年(玄宗天宝五年,丙戌,公元746年),……征四茹牧场之‘大料集’,收集已摊派之一切奴户之赋税,明令奖谕论·结桑达囊。”[7](P118)当然,还有其他的土地租佃户类,如“及至马年(玄宗开元六年,戊午,公元718年),……冬,赞普驻于札玛牙帐。征三茹之王田全部地亩赋税、草税。”[7](P112)“及至羊年(玄宗开元七年,己未,公元719年),征集“羊同”与“玛尔”之青壮兵丁,埃·芒夏木达则布征集大藏之王田土地贡赋。”[7](P112-113)以上记载中没有明确纳税主体的户类,但明确交代了他们耕种的是王田,而且需要纳税,这肯定不同于牧户和奴户。另一材料中还提到“宫廷直属户”,“及至虎年(玄宗开元十三年,丙寅,公元726年),春,大论芒夏木于岛儿集会议盟,订立岸本之职权,征宫廷直属户税赋。”[7](P114)虽然此处的“宫廷直属户”具体范围不得而知,但肯定有别于牧户和奴户。千佛洞的材料中有“并为他们领取的奴隶及其家庭,登记了各自的名字,以及如何纳税(或受惩罚,或强制服役),均写于一份共同的契约中……”[5](P40)的记载。可见,除了普通百姓需要承担贡赋外,奴户也要承担相应的赋税,并且以契约为凭,这一点从他们拥有土地的事实可以肯定。因为“除去户税外,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官府又向部落民户征收‘地子’……这时的‘地子’实际上就是土地税。”[14](P180-181)。
吐蕃在赋税征收方面有一套较为成熟的流程,即先确定贡赋,然后再行征收,如“及至狗年(中宗嗣圣三年,太后垂拱二年,丙戌,公元686年),……冬,于查玛塘集会议盟。定襄·蒙恰德田地之贡赋。”[7](P105-106)“及至猪年(中宗嗣圣四年,太后垂拱三年,丁亥,公元687年),……冬,定大藏之地亩税赋。”[7](P106)“及至虎年(中宗嗣圣七年,太后天授元年,庚寅,公元690年),……噶尔·没陵赞藏顿与巴曹·野赞通保二人征收腰茹之地亩赋税。”[7](P106)随着赋税承载主体的不断变化,赋税征收一段时间以后,政府还会对赋税情况进行清查,“及至兔年……清理土地赋税并统计绝户数字。”[7](P106)从“及至狗年……严切诏告,减轻庶民黔首之赋税”[7](P118)可见,吐蕃统治阶层为了缓和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曾采取过减税的措施,这对维持以税赋为基础的剥削方式是极其重要的。
以户为单位支差。文献记载中出勤、应征户、户差等词汇清晰地表明了当时一种以户为单位的剥削方式,如“一头空(stong,不能驮)的怀孕驴折银四两,一头公驴银三两,一头小驴银二两。雇费从出勤之日起,每天(per diem)粮一藏升(bre),如不付粮,也可折作应征户的户差。姜孜(rgyangrtse)处的公牛和驴子(已死),赔偿价如上述。支付雇费粮半驮。”[5](P326)这种以户为单位的剥削方式有助于理解吐蕃文献中为何会有相当数量关于奴户的记载。
三、吐蕃对敦煌的人口管理
吐蕃政权在敦煌确立统治地位以后,不久便开始清查户口和统计人口,并编订名簿,敦煌遂出现不少关于户籍的名簿,如官府役人名簿和寺院僧尼名簿等。这表明,吐蕃政府在敦煌地区的人口管理政策是比较严格和完善的。
清查户口。P.3774号文书载:“大兄初番和之日,齐周附父脚下,附作奴。后至佥牟使上析出为户,便有差税身役,直至于今。”[9](P284)“番和之日”,即“丙寅年”,即786年[3](P398)。文中所言“佥牟使”,即吐蕃清查户籍的官员,齐周也因吐蕃官员开展户口清查而析出为户,开始承担差税身役,其具体时间可据S.2729号《吐蕃辰年(788)三月沙洲僧尼部落米浄詟牒》(筭使勘牌子⑥历)所载“辰年三月五日,算使论悉诺罗接谟勘牌子历”[3](P358)做出初步判断。陈国灿指出,“此勘牌子的‘接谟’,实即‘佥牟’,……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即780)至贞元十五年(己卯即799)间,唯有一个辰年——戊辰,即公元788年。”[14](P6)故而,齐周析出为户,开始承担赋税身役的时间应该为公元788年。这说明吐蕃在这一年开展了对敦煌居民户籍的清查工作。
编籍造册。S.2729号文书中详细记载了僧尼名、僧尼数、僧人总数、尼姑总数及所属寺名和部分死亡僧尼的死亡时间[3](P358-362),这是吐蕃占领敦煌之后,进行僧尼统计和造册的记录,是较早的户口勘查原始档案。由此看来,吐蕃占领敦煌后还是高度重视对当地人口管理的,尤其是从一开始就对敦煌居民的户口进行清查和造册。
后来,吐蕃在敦煌的户籍制度随着乡里制度的废除和部落制度的确立而有所改变,即户籍制度按照“部落的体制编制”。《氾卷》对此进行了记载,并以午年为界线,将在籍人口分为新、旧口,如“午年擘三部落已后新生口”[3](P376)、“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3](P377)等。说明午年曾针对擘三部落的居民编制“牌子”,即敦煌陷蕃初期擘三部落的户籍。金滢坤认为S.3287《氾卷》是一件擘三部落左二将五户百姓的户口状,明细各户主对户口变动情况的申报,相当于唐代的手实[15](P120)。关于《氾卷》记载内容的时间问题,藤枝晃认为《氾卷》写于公元832年[3](P378)。文书题目中“子年”和内容中“午年”所对应的具体时间,杨铭认为“午年”为790年,“子年”则以808(戊子)年为妥。”[16](P64)可见,此时关于户籍中的内容更为丰富和详细,管理也日趋完善。
在户口清查和编籍造册的基础上,为了保证户籍册中人口的稳定,吐蕃当局在处理敦煌居民住房和土地纠纷方面采取了有利于居民稳定生活的做法,即S.5812(G.7371)号文书⑦中记载的宅舍以见住为主和田园宅舍不许侵夺论理[10](P116)。这一方面使易主后的敦煌社会纠纷解决有章可循,另一方面也保障敦煌居民能在一定范围内稳定生活。
对P.3774、S.2729和S.3287号文书所载内容的分析,可见吐蕃在占领敦煌以后近30年的时间里,先后开展了清查户口工作、将吐蕃本部的户籍制度和敦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建立了适应“部落——将”的编户制度,进而对居民进行分部落编籍造册,内容大致包含居民现在的将籍、户主姓名、新旧口之别、新增或减少人口及其原因、户内成员关系等;另外,在开展户口清查统计时,要求居民必须如实申报,不得隐漏,而且还要作保证,足见吐蕃当局在敦煌地区的户籍制度之完善。通过加强对敦煌居民的户籍管理,吐蕃当局有效地控制了敦煌地区的居民,进而为其征发赋税、派遣劳役提供了基础支撑,也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吐蕃政权对寺院属户进行编户,推行寺户制度,使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寺院经济得到了稳固发展,从而也有效地把敦煌佛教纳入其统治体系之中。
结语
吐蕃占领敦煌这一历史事件,在沈下贤等一些以中原王朝为正统的文人看来,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他们认为吐蕃在其占领下的敦煌必定推行野蛮的奴隶制度,但是通过多方面分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从吐蕃本土社会来看,吐蕃在征战过程中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战俘奴隶;劳作过程中也并非主要役使奴隶,剥削形式主要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赋税征收。关于“奴”等群体,非但在文献记载中未找到有力的证据说明他们就是严格意义上会说话的工具,且发现他们有家庭、有财产,还要承担赋税,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社会状况来看,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就非常重视人口管理,开展户口清查,编制户籍,调解财产纠纷,并用法令的形式将处理纠纷的原则固定下来,确保当地居民的稳定;针对部分吐蕃贵族抄掠敦煌原住民的现象,吐蕃统治阶层还以政令的形式严格限制甚至禁止抄掠被占领地方的居民为奴,并强调他们“已属赞普之臣民。”[4](P52)故而才有“流沙僧俗,敢荷殊恩,百姓得入行人部落,标其籍信,皆因为申赞普,所以纶旨垂边”⑧的赞语。诚如陈庆英所言,“盖因此处唐人所谓‘奴婢’,乃是指被占之地的唐人在异族统治下被奴役的地位而言,并不能与科学意义上的‘奴隶’画等号。”[17](P106-107)尽管当时的唐朝臣民从情感上不接受吐蕃占领敦煌地区这一事实,对此有所贬损,但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吐蕃在占领敦煌以后,并未在当地实行践踏之能事的政策——将原住居民变身为奴,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敦煌地区进行有效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注 释]
①此处仅指被称为“奴”“婢”“奴仆”“奴户”“奴隶”的群体。
②有关敦煌何时陷于吐蕃,历来有多种说法,而学术界采用较多的有两种,即:戴密微的787年“陷蕃”说和藤枝晃等认为的“建中二年(781)陷于西蕃”说。笔者在参考各家之说的基础上,对部分事例进行分析后认为吐蕃于781年攻陷敦煌较为合理。
③笔者理解为依附于某户或某人的“奴”。
④笔者理解为通过某种官方认可的程序将某人卖身为奴。
⑤此处26户包含能明确户主名字的22户,22户中又有3个户主下被标为“两户”,前半部文献不全的按1户统计。
⑥史书中将这种记载详尽的户籍称之为“牌子”。
⑦关于S.5812号文书的年代问题,藤枝晃认为文书所落丑年是指公元833年,笔者结合文书中“今经一十八年”的表述,大致判断论悉诺息和论莽罗新两位官员解决宅舍、田园纠纷的时间为公元815年左右。
⑧P.2449号卷子背面录释子文。《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录其正面,题作《元始应变历化经》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