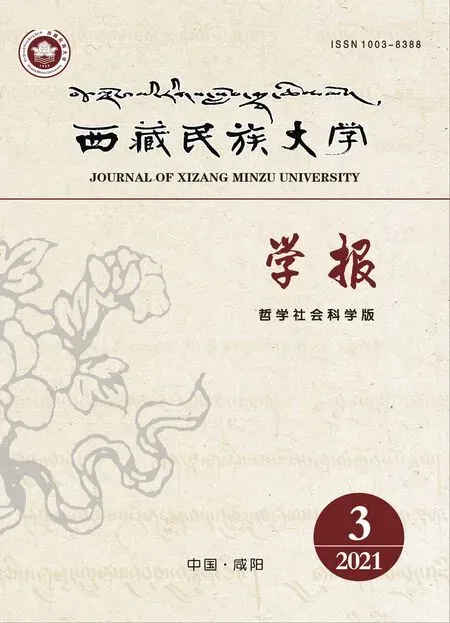关于青海化隆丹斗地区佛教遗迹的几个问题
陆离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97)
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丹斗(dan tig)地区位于甘肃永靖县西,东北与青海民和相接,西与青海乐都、西宁相邻,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发源地。在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灭佛之时,三名藏族僧人藏·绕塞(gtsangs rab gsal)、尧·格迥(gyo dge vbyung)、马尔·释迦牟尼(dmar ban shavkya mu ni)经阿里、西域回鹘地区到达青海东部地区,三人在丹斗地区修行时遇到喇钦(lha chen,即格瓦饶赛Ge wa rab sel),收其为徒,开始向他传授佛法。喇钦学成后在此地及周边地区传法,影响日增,吐蕃本部卫藏六人到丹斗地区从喇钦学法,学成返回本部,佛教复兴于卫藏,藏传佛教后弘期随之拉开序幕[1](P72-76,P79)。喇钦于940年定居丹斗,广建寺塔,弘传佛法,丹斗寺成为青海东部地区及安多地区藏传佛教的中心。近年先后有学者对丹斗地区的佛教洞窟壁画和题记以及收藏于民间的藏文佛教文献、文物等进行了调查,并对这些佛教遗迹和文物的年代、内容做了探讨[2][3]。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一部分佛教遗迹和佛教文献、文物再进行一些探讨,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唐代发愿文题记
根据藏族学者伯果调查,旦斗(即丹斗,下同)寺峡谷西端的旦斗寺龙王殿岩窟(编号第1窟)被龙王殿建筑遮盖,现存壁画主要在殿西侧崖壁,壁画题材以千佛为主,有藏文佛名及佛弟子题记,还有藏文经咒,应为9世纪以后书写。在龙王殿后墙窟壁发现一些壁画残迹,其中一处供养人题记较为完整,可辨文字104字。转录如下:
“1:□亨四年……2:五月……□□……3:前旅……郭□……4:佛……5:□微……6:良□□□永……7:□……8:之苦□法门之□永□石……9:停悲□驹之易□□是□10:愿□起菩提之心□□□□11:超逾峭岭思欲□□生普……12:慧□遍明六□□□依……13:绝□□之俗是□□香顶礼□秋追14:献供施心愿□陁未□□□见存家卷15:□兜率之偕父母及身咸寿生天……16:果又愿□途解脱六趣回迷八界四□17:同登正觉18:佛弟子□行感供养”[3]
题记处有一唐装供养人像,头戴黑幞头,身穿圆领袍服,足穿黑靴。虽然这部分壁画与龙王殿西侧摩崖壁画连成一体,但从零星壁画残部看,无论是造像内容还是风格与前者差别较大。第1行为“□亨四年”,该年号据考证应该是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因为历代使用年号中有“亨”的有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大亨年号,但只使用1年,而且东晋政权偏居江南,没有统治过青海丹斗地区。还有唐高宗李治咸亨年号,曾使用5年,另外还有辽景宗耶律贤乾亨年号,也曾使用5年,但历史上辽朝势力并没有进入青海丹斗地区,所以题记年号只有唐高宗咸亨四年合适[3]。
壁画题材以千佛为主,残存千佛图像11排,共200身,排列有序。每尊小佛旁边有竖长方形墨书榜题,文字漫漶无法辨识。千佛右侧绘供养人一排七身,有比丘、男性供养人和女性供养人。供养人头侧有供养人题名,字迹漫漶。供养人下有竖行墨书发愿文,除每行首字较清晰外其他字荡然无存,从右往左为:“世……/皇……/安……/父……/下……/俱……”[3]。
伯果等认为第1窟的千佛造型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有关特征跟炳灵寺敦煌莫高窟唐代同类造型相似,飞天造型特征跟莫高窟初唐飞天样式较为一致,符合唐代飞天风格。故初步推断第1窟壁画的绘制年代应当在初唐。
另外,在当地人称“拉色囊”(lha sa'i nang)的旦斗寺峡谷下游有三个岩窟(编号第2、3、4窟),第2、3、4窟三个窟的壁画内容与风格较为一致,可以断定同一批所绘。壁画以千佛为主,千佛中间加以佛法图和供养人,与麦积山、敦煌北魏壁画和云岗石窟造像同类题材有类同处,结合着装样式,第2、3、4窟壁画的年代应在北魏后期[3]。
青海化隆丹斗地区在十六国时期先后曾归属南凉和西秦统治,佛教在此时已经进入南凉和西秦传播,而隋唐时期化隆丹斗及其周边地区更是佛教兴盛之地。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实际上传世史籍多有记载,而且佛教遗迹甚多,而伯果先生文中尚未论及,仅提及《水经注》和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的记载(详后),笔者这里再做一些补充论述。梁慧皎《高僧传》卷十《释昙霍传》记载了南凉兴佛的故事,云:
“释昙霍者,未详何许人。……时河西鲜卑偷发(即秃发之异译)利鹿孤僭居西平,自称为王,年号建和。建和二年(401)十一月,霍从河南来,至自西平,赐一锡帐……并奇其神异,终莫能测,然因之事佛者甚众。鹿孤有弟傉檀,假署车骑,权倾伪国,性猜忌,多所贼害,霍每谓傉檀曰:‘当修行善道,为后世桥梁。’檀曰:‘仆先世以来,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违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颜色如常,是为佛道神明,仆当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无饥渴之色。檀遣沙门智行,密持饼遗霍。霍曰:‘吾尝谁欺,欺国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节杀兴慈。国人既蒙其祐,咸称曰大师,出入街巷,百姓并迎为之礼。……至晋义熙三年(407年),傉檀为勃勃所破,凉土兵乱,不知所之。”[4](P375)
僧人释昙霍从河南来,河南当指西秦政权,当时西秦国主据黄河以南之地,号河南王,自建和二年(401)开始,昙霍得到南凉国主秃发利鹿孤之弟秃发傉檀的信任和支持,秃发傉檀放弃原始信仰改信佛教,并支持昙霍在南凉境内传布佛教,昙霍被官员及百姓奉为大师,地位很高,直到407年南凉转衰之时才下落不明。
乞伏鲜卑所建西秦政权境内有麦积山和炳灵寺两个著名石窟,其开凿兴建均与西秦有关,炳灵寺第一六九窟内,还保存着西秦建弘元年(420)的墨书题记。西秦统治者曾经聘请僧人讲经,著名僧人玄高、秦地高僧昙弘在麦积山修行,还有一个著名外国僧人昙无毗在西秦传法,炳灵寺第一六九窟供养人像下方有题记:“□国大禅师昙摩毗之像。”[5]昙摩毗即昙无毗。
《高僧传》卷十一记载僧人玄高受到乞伏炽磐父子的崇奉,西秦国主和臣民夹道欢迎,“内外敬奉,崇为国师。”[4](P411)地位极高。炳灵寺第一六九窟是石窟精华所在,其壁画和塑像具有较高艺术水平,完成年代正是西秦之时,对于探讨中国石窟艺术的源流和发展,对于中国雕塑史和绘画史,都是十分珍贵的资料[6](P235)。法显《佛国记》记载东晋隆安三年(399),僧人法显及慧景等,从长安出发,赴天竺游学,“度陇至乾归国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褥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7](P3),陇即陇山,乾归国指西秦,时都苑川(今甘肃榆中东北),经苑川经过凤林关渡黄河,西北至乐都,又溯湟水而至褥檀国(南凉)国都西平。然后法显等一行从西平北过养楼山(今养女山),过浩门水(今大通河),从扁都口(大斗拔谷)穿越祁连山,到达张掖。走此路线应与当时南凉强盛,法显等可以在南凉弘法或与南凉境内佛教徒聚会有关。法显一行在炳灵寺一带(风林关)渡过黄河,向乐都、西平进发[6](P109-110),应该经过化隆丹斗附近地区,此时佛教可能已经传入这一地区。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记载:“湟水又东迳土楼南,楼北倚山原。峰高三百余尺,有若削成。下有神祠,雕墙故壁存焉。”[8](P49)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亦云:“佛教盛行于鄯州(今西宁),曾作佛龛于土楼山断崖之间,藻井绘画。”郦道元记载西宁土楼山所建神祠中有可能包括有佛龛、佛窟,可能始建于南凉时期,当时南凉接受佛教,在此兴建佛教寺窟。
青海西宁市东30公里互助白马寺摩崖石雕佛像具有中国佛像早期造像的特点,有学者考证认为其年代大约在5-6世纪,属于北魏时期,早于白马寺藏传佛教寺院的建立时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遗存[9](P115,117)。《元和郡县图志》记载:
“鄯州,……合川郡守捉,州南一百八十里,贞观中侯君集置。管兵千人。……管县三:湟水、鄯城、龙支。……龙支县,……本汉允吾县也,属金城郡。后魏初于此置金城县,废帝二年改名龙支县,西南有龙支谷,因取为名。”[10](P991-993)
唐前期丹斗地区属于鄯州龙支县,汉代为允吾县,北魏为金城县,后改现名。唐朝在龙支县附近还设有合川郡守捉,驻守军队千人。唐人崇奉佛教,隋唐时期佛教继续在当地传布。
永靖县境内的炳灵寺在唐代是唐蕃交聘使者的必经之路,当时被称为灵岩寺,也是著名的佛教胜地,炳灵寺石窟保存有多处唐蕃关系的史料。第64龛上方有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十月刑部侍郎张楚金的《灵岩寺记》,当年九月唐将李敬玄、刘审礼与吐蕃在青海作战,张楚金参加了此次作战,然后在炳灵寺撰文刻石记事。炳灵寺永隆二年列龛位于炳灵寺下寺区中段,共十龛,造像主为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唐朝派出的陇右巡查使官员和陇右节度使治下河州安乡县的陪同官员,他们出巡目的当与唐蕃关系有关,可能是在678年唐蕃青海之战唐朝战败后巡查唐蕃边境,加强对吐蕃的防务,防御吐蕃侵袭。第148窟外面北壁有魏季随撰《灵岩寺记》,记载了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春唐朝鸿胪卿崔琳使团出使吐蕃的有关情况和使团成员姓名,魏季随为使团副使。张楚金、陇右巡查使官员、崔琳使团等都是在炳灵寺渡过黄河,向西经过鄯州龙支县再向鄯州(乐都)、鄯城(西宁)进发[11]。这些都反映了这一地区佛教的兴盛和唐朝官员普遍信佛。
安史之乱爆发后,鄯州龙支县及附近地区都被吐蕃占领。《新唐书》卷196《吐蕃传》记载:
“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己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过石堡城,崖壁峭竖,道回屈,虏曰铁刃城。右行数十里,土石皆赤,虏曰赤岭。”[12](P6102-6103)
821年唐朝使者刘元鼎从长安赴逻些参加唐蕃长庆会盟,从兰州南下炳灵寺附近渡过黄河,然后向西经过原唐朝龙支县(辖境包括今丹斗地区)治龙支城,有落蕃唐人父老千人夹道迎接,当时该地居住的落蕃唐人及其后裔还很多。由于十六国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先后统治丹斗及附近地区的南凉、西秦、北魏、西魏、北周及隋、唐诸政权都崇信佛教,与之相邻的炳灵寺石窟一直是佛教圣地,丹斗周边地区佛教活动频繁,所以在丹斗地区保存有北魏、初唐的壁画图像和唐高宗咸亨四年(673)礼佛祈愿文题记及供养人造像是自然而然的。该地区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应该也是一个佛教兴盛之地,建有寺院和佛窟,而且也留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佛教信徒的礼佛祈愿文和供养人画像,他们应是唐朝龙支县的官民。
二、dan tig与dan tig shan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自西向东陆续占领河陇西域,丹斗地区也归入吐蕃政权统治。成书于12世纪的藏文教法史籍《弟吴宗教源流》(Rgya bod kyi chos vbyung rgyas pa)记载有吐蕃境内重要寺院:
“(吐蕃)八大禅修处(sgom sa):伍如(dbus)有青浦(vching bu)、扎叶尔巴(yer pa)、娘氏(nyang)建造的谐拉康(zhwa)、曲沃日(chu bo ri)四处;多康(mdo khams)有丹斗山(dan tig shan)、炳灵(vbum gling)、阿隆(a lung)、龙塘阿雅隆(klong thang arya gling)。
十二修心寺院(blo sbyong gi grwa):卫地(dbus)有钦布(vching bu)、扎耶尔巴(yer pa)和谐拉康(zhwavi lha khang)三;康地(kams)有丹斗山(dan tig shan)、炳灵(vbum gling)、阿琼(an chung)和帝卫拉蔡(de bavi bla tsal)四座;在多麦(mdo smad)有龙塘阿雅隆(klong thang aryavi lung)、美雪僧林(mes shod seng gling)的静修地(dben gnas)……总的静修地有三十个。”[13](P176)、[14](P357)
许德存先生将丹斗山(dan tig shan)译为丹斗。才让先生则认为丹斗(dan tig)和丹斗山(dan tig shan)是同一所寺院,在青海化隆县境内[15](P856)。和炳灵(vbum gling)寺一样,丹斗山(dan tig shan)也属于吐蕃王朝八大禅修处(sgom sa)和十二修心寺院(blo sbyong gi grwa)。英国学者Sam van Schaick(沙木)和Imre Calambos(高弈瑞)先生认为出现在《弟吴宗教源流》和英藏敦煌藏文文书IOL Tib J 754号中的dan tig shan即青海省化隆县的丹斗(dan tig)山谷,此处与藏传佛教后弘期高僧格瓦饶赛(Ge wa rab sel)密切相关连,是10世纪藏传佛教后弘期复兴之处,dan tig得名自《太子须大挐经》(Sudāna Sūtra),此经是一个关于流放与回归的故事,汉文《太子须大挐经》记载太子须大挐流放地为檀特山,该故事直接与从吐蕃中心卫地逃难来到该地(丹斗地区)的僧人们的志愿相联系,檀特与dan tig发音相同[16](P1211).[17](P40-43).[18](P475-491)。
成书于12世纪的藏文史籍《底吾史记》(ldevu chos vbyung,此书被认为是《弟吴宗教源流》的简本)记载吐蕃有十二禁语修心寺院(smra bcad sems vchods kyi dra),多思麻康区(mdo smad khams)有“丹斗吉祥清静地(dan tig dpal gyi yang dben),炳灵(vbum gling)……”[19](P136),这个丹斗吉祥清静地(dan tig dpal gyi yang dben)应该是指丹斗山(dan tig shan),该书将shan遗漏,记为dan tig。
成书于14世纪的藏文史籍《奈巴教法史-古谭花蔓》(sngon gyi gtam me tog phreng ba zhes bya ba)则称吐蕃境内重要寺院有:“断语修心之十二所寺庙(smra bcad sems vchos kyi sgom grwa bcu gnyis)是:……康区(khams)有丹斗山(dan tig shan)、炳灵(vbum glung)、昂龙(ang lung)、安穷(an chung)四寺。”[20](P25)、[21]
德国学者Helga Uebach认为这里的khams(康区)即bDe khams,是吐蕃对其占领的河陇等地区的统称。而《底吾史记》中出现多思麻康区(mdo smad khams)、《弟吴宗教源流》中出现了多思麻(mdo smad,一般指青、甘、川三省交界处黄河上游河段以东地区)和khams(康区),多思麻(mdo smad)和khams(康区)这两个地区都应处于吐蕃大臣bDe blon(德伦)的控制之下,地理位置相邻。《奈巴教法史-古谭花蔓》和《底吾史记》、《弟吴宗教源流》中关于吐蕃王朝境内30所寺院的记载应该有相同的史料来源,《奈巴教法史》提供了关于这些寺院最详细和准确的书写形式。而另外两部史籍的简写形式则导致了书写错误和误解。通过使30所佛教寺院制度化,吐蕃赞普赤祖德赞(khri gtsug lde btsan)把寺院活动统一组织到吐蕃的政府体制中,并极力使佛教得到传播兴盛[22](P393-407)。
另一部早期(成书于12世纪)藏文史籍《娘氏教法源流·花蕊蜜汁》(chos vbyung me tog snying po⁃vi sbrang rtsivI bcud)中记载:11世纪藏传佛教后弘期“三贤者”曾经到过黄河谷地(rma lung)的多杰扎(rdo rje brag,金刚崖)、有汉式屋脊的安琼南吉阳宗寺(a chung gnam gyi yang rdzong,安琼天堡)和丹斗显吉阳贡寺(dan tig shel gyi yang dgon),后来从丹斗显吉阳贡寺发展出来汉式屋脊具鹏鸟首(khyung mgo can)的佛殿(lha khang)一百五十一座。[23](P409)、[24](P20)、[25]成书于14世纪的《西藏王统记》则记载佛教后弘期“三贤者”到达了丹斗显吉扎浦(dan tig shel gyi bra phug,即丹斗显的岩洞),即今青海化隆的丹斗(dan tig)[26](P142,224),才让先生也认为《第吾贤者佛教源流》与《娘氏教法源流·花蕊蜜汁》中记载的dan tig shan和dan tig shel就是今天青海化隆县的丹斗(dan tig)寺,shel是shan的异写[24](P20)。
但是dan tig shan和dan tig并不能完全等同,丹斗对音为dan tig,至于shan则无从对应。《奈巴教法史》和《底吾史记》《弟吴宗教源流》并未记载dan tig shan在黄河谷地(rma lung)。而藏文dan tig shan的发音正好就是凉州天梯山,二者完全吻合。唐朝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凉州》记载:“姑臧县,……天梯山,在县南二十五里。”[10](P1019)姑臧县在凉州东部,天梯山则在姑臧县境内。
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开凿于北凉时期,据说为北凉国主沮渠蒙逊亲自设计开凿兴建,以后历代都有开凿兴修,是河西地区的著名佛教圣地,目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北凉至明代洞窟多处。天梯山石窟第17窟右侧残壁上有壁画3层,其中第2层20世纪50年代清理时剥出吐蕃供养人像4身,身穿翻领宽袖长袍,长巾裹头,掩耳修发,斜垂脑后,下穿紧口裤,足蹬长筒乌靴。其中一人头戴大红色头巾,身穿浅黄色长袍,头巾后面向上翘起一角,并饰以圆形花纹,头部上方竖起一柄卷起的绿色伞盖,伞盖顶上镶嵌有巨大宝珠,下边垂挂各色璎珞,冠带、服饰与其他三人不同,显示地位较高,当为吐蕃高级官员或王者。另外三人则分别在前、后方位围绕此人,整个构图与敦煌莫高窟第159窟所画吐蕃王子及其侍众基本相同。第17窟也是天梯山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窟,所处位置极其突出显赫,窟内遗存也较为丰富,保存有北魏至明代壁画遗存。另外天梯山石窟中还有几处洞窟残存有中唐时期壁画,也应该属于吐蕃统治时期[27](P121-122)(彩版三九、四六、七零、七一、七七、七九、八零)。所以《奈巴教法史》和《弟吴宗教源流》中记载的吐蕃境内重要寺院dan tig shan应该就是吐蕃统治下的凉州天梯山石窟寺,吐蕃占领河陇后崇信佛教,吐蕃凉州节度使(khar tsan kyi khrom)设于凉州,该地是吐蕃统治河陇地区重镇,管辖甘、凉等州,凉州附近天梯山石窟寺继续兴盛发展,成为吐蕃全境30所重要寺院之一,是当时汉藏佛教交流的重要场所。英藏敦煌藏文文书IOL Tib J 754号中的一组藏文书信(年代在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具体内容是关于唐蕃长庆会盟后唐朝五台山僧人经过吐蕃占领区赴天竺礼佛朝圣之事,书信中提到其经行路线为凉州(leng cu)-嘉麟(ga lu)-天梯山(dan tig shan)-宗哥(tsong ka)-甘州(kam cu)-沙州(sha cu)[28](P245-274),唐朝五台山僧人在天梯山(dan tig shan)、宗哥(tsong ka)等吐蕃统治下河陇佛教圣地巡行礼佛。
至于《娘氏教法源流·花蕊蜜汁》记载11世纪藏传佛教后弘期“三贤者”曾经到过黄河谷地的丹斗显吉阳贡寺(dan tig shel gyi yang dgon),此寺应该是指今天青海化隆县的丹斗(dan tig)寺,位于黄河谷地,但是dan tig shan和dan tig shel不能等同,两者并非指同一寺院,没有证据能够证明dan tig shel就是dan tig shan的异写,并且dan tig shan也在黄河谷地。前面提到在12世纪成书的《底吾史记》中也将dan tig与dan tig shan混同,故在12世纪藏文教法史籍中已经将这两个地名误认为一地,而《西藏王统记》中关于后弘期三贤者到达dan tig shel的记载应源自《娘氏教法源流·花蕊蜜汁》等史籍。根据伯果等调查丹斗地区佛教遗迹,其中并未发现有中唐时期即吐蕃统治时期佛教遗存,他们甚至认为吐蕃统治时期吐蕃僧团没有到达该地活动,丹斗佛教石窟第1窟的藏文佛名及佛弟子题记,还有藏文经咒可能书写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3]。成书在18世纪的藏文史籍《如意宝树史》记载藏传佛教后弘期的重要领袖喇钦即格瓦饶赛(Ge wa rab sel)在丹斗(dan tig)的活动:“他(喇钦)来到丹斗,这里有许多持和尚摩诃衍那顿入成佛之见的人,他为置这些人于善道而往生喜足天界,遂设供养发愿道……。”[29](P302-303)
这一记载表明在10世纪中后期,藏传佛教后弘期重要寺院青海地区的丹斗(dan tig)寺曾经受到汉传佛教禅宗的影响。青海化隆丹斗地区地理位置较为偏僻,虽然离黄河岸边很近,但地处山中,交通较为不便,吐蕃鄯州节度使驻节地在鄯州(今青海乐都)、河州节度使驻节地在河州(今甘肃临夏),与丹斗地区之间的交通都不太便利。所以丹斗寺地区虽然一直存在佛教活动,但在吐蕃统治时期并非全境30所重要寺院之一,并不是《奈巴教法史》和《弟吴宗教源流》中记载的dan tig shan。《娘氏教法源流·花蕊密汁》记载11世纪藏传佛教后弘期“三贤者”曾经到过黄河谷地的丹斗显吉阳贡寺是指今天青海化隆县的丹斗寺(dan tig),该书作者将丹斗寺(dan tig)写成丹斗显(dan tig shel),但dan tig shan(天梯山)与dan tig(丹斗)、dan tig shel并不是同一个地方。
三、丹斗地区发现的西夏铁钟及寺院遗址
丹斗地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源地。喇钦(lha chen)·贡巴绕赛(dgong pa rab sel,即格瓦绕赛,Ge wa rab sel)在丹斗寺居住数十载,修建寺院,授徒传法。《青史》记载:
“大喇嘛(贡巴绕赛)受旦斗铁让本勾(鬼神九兄弟)之邀,到此地作供养三宝之业……大喇嘛为了破除所谓“顿入瑜伽”不作任何善法的邪知见,他修建了很多寺庙和佛塔。颜料也出自本地,建筑的工艺也出自他手……大喇嘛住锡旦斗三十五年之久,享寿八十四岁,于乙亥年逝世而往生兜率。”[30](P45-46)、[1](P74-75)
《安多政教史》记载:“喇勤(lha chen)于四十九岁时来到丹斗寺,一直住锡三十五载,晚年,在彼处圣地上修建佛殿,与眷属诸比丘众居于彼处,直至涅槃。”[31](P25)
前文提及在丹斗寺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藏文经咒及佛名题记,应当是后世所写,也有可能属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佛教后弘期喇钦·贡巴绕赛在丹斗寺传法时期所遗留。
根据藏族学者伯果、叶拉太等调查,在旦斗峡口离科那卡村不远处发现有古寺遗址一处,被称为啼口佛寺遗址,该地出土西夏铁钟1口(该钟现藏于当地一户藏民家中),铁钟表面刻铸有西夏文,但生锈严重,字体模糊不清。旦斗寺僧人介绍,十几年前,峡口时有瓦当、青砖出土,他们还捡到几尊金铜佛像,作为装藏物将其藏于寺内佛塔。当时有好多村民在此地挖出各类文物,有佛经、陶制品、瓷器、尊像、丝织品、金饰、木碟等[2]。现代藏族学者才旦夏茸撰写之《才旦夏茸文集3·旦斗寺简志》记载和旦斗寺僧人们口传,现旦斗寺未建之前,在现址下游曾有过一个规模可观的汉传佛教寺院。伯果等结合第4窟出土的西夏文经书残页和“擦擦”(伯果、谢继胜等认为形制和属于西夏时期的宁夏拜寺沟方塔和阿里托林寺出土“擦擦”较为接近),基本认定藏文文献中提到的旦斗古寺确实存在,其遗址就在离“拉色囊”岩窟群约1公里的旦斗峡口,属于西夏佛寺[3]。另有学者认为自12世纪起,丹斗地处河湟吐蕃政权范围内,但与西夏相距不远,受到西夏藏传佛教影响。西夏与河湟吐蕃政权和平相处,河湟吐蕃政权、西夏王室都极力推崇佛教,在这种文化互动的情况下,丹斗地区发现西夏文铁钟也就不足为奇了,即该寺院遗址并非西夏寺院遗址而是河湟吐蕃政权佛寺遗址[2]。总之,目前学界对旦斗峡口离科那卡村不远处发现的佛寺遗址的年代存有争议。
实际上根据汉文史籍记载西夏确曾占领丹斗地区,具体时间是南宋初年金人占领中原,宋人南渡之时,当时青海地区宋军守备空虚,西夏乘虚而入,而此前关于啼口佛寺遗址的研究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史籍记载1136年(夏大德二年,宋绍兴六年)七月,西夏又取西宁州(青海西宁),“守将弃城遁”[32](P400)[33](P227)。1137年(夏大德三年,宋绍兴七年)九月,夏主乾顺派遣使者“以厚币如金,表乞河外诸州”。金将乐州(青海乐都县)、积石州(青海贵德县境)、廓州(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西南黄河北岸)割给夏国[33](P227)。
《金史》卷91《结什角传》记载:“天会中(1123-1137),诏以旧积石地与夏人,夏人谓之祈安城。”[34](P2017)《金史》卷3记载:天会九年(1137),金始“抚定巩、洮、河、乐、西宁、兰、廓、积石等州”[34](P63)。《金史》卷78《刘筈传》记载:“初,以河外三州赐夏人,或言秦之在夏者数千人,皆愿来归。诸将请约之。筈曰:‘三小州不足为轻重,恐朝廷失大信。’”[34](P1772)此处所载为金皇统七年(1147)之事,金割河湟西宁、乐、廓、积石四州军与西夏的时间,应该在宋金绍兴和议(1141)之前,两军酣战之时[35](P667)。此后西夏就占领了西宁(青海西宁)、乐州(青海乐都)、积石州(青海贵德)、廓州(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西南黄河北岸)地区,丹斗地区也正在其中,直至1227年西夏被蒙古灭亡,此四州一直在西夏统治之下。所以旦斗峡口发现的佛寺遗址应该是西夏佛寺遗址,年代在1137年之后,1227年之前,为西夏占领该地区后修建的佛寺。西夏人同样尊崇佛教,吐蕃僧人在西夏境内具有很高地位,受到西夏君臣百姓的崇敬礼遇,藏传佛教后弘期各教派在西夏都有传播,《青史》记载喇钦曾去西夏统治的甘州学习佛法[1](P73),西夏政权在其统治区域内的藏传佛教后弘期发源地之一旦斗地区修建佛寺是自然而然之事,遗址出土的西夏铁钟和在第4号岩窟发现的西夏文经页残片、擦擦(据考证形制和属于西夏时期的宁夏拜寺沟方塔和西藏阿里托林寺出土“擦擦”较为接近)等也明确显示了这一点。
总之,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丹斗(dan tig)地区的旦斗寺龙王殿岩窟等岩窟保存有北魏、初唐的壁画图像和唐高宗咸亨四年(673)礼佛祈愿文题记及供养人造像,有关史料记载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其周边地区佛教活动频繁,遗迹众多,故该地在当时也应该是一个佛教兴盛之地。成书于12世纪的藏文史籍《弟吴宗教源流》等记载有吐蕃王朝境内三十所重要寺院之一的dan tig shan,是指凉州地区的天梯山石窟及寺院,并非青海化隆的丹斗(dan tig)。南宋初年,西夏政权在金人占领中原之时乘机占领了西宁、乐州、积石州、廓州地区,丹斗地区也正在其中,此后直至1227年西夏被蒙古灭亡之前,这一地区一直被西夏占领。所以旦斗峡口发现的佛寺遗址应该是西夏佛寺遗址,遗址出土的西夏铁钟和在第4号岩窟发现的西夏文经页残片、擦擦等也明确显示了这一点。丹斗地区自南北朝隋唐时期就是一个佛教兴盛之地,在10世纪末期又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发源地之一,12-13世纪又曾被西夏政权管辖,并在此修建寺院,该地区佛教遗迹众多,在中国佛教传播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