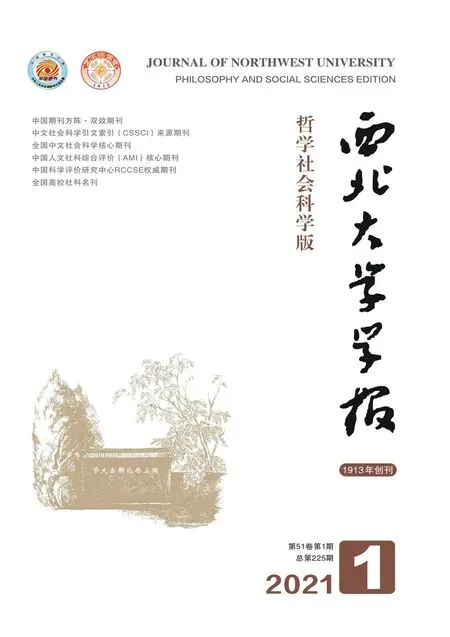论杨一清四入陕西及其边塞书写的意义
杨遇青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在明代中叶台阁文学盛行的语境中, 杨一清的边塞诗书写别开生面, 他从台阁体的成员走向江山朔漠, 随之而来的是诗歌题材重新选择与诗风的转进。随着政治语境与自然环境的改变, 他的创作潜能得以充分释放, 从而影响到文学复古运动的开展和创作趋向。杨一清是明代中叶重要的政冶家和诗人。他虽官至首辅, 一生事业, 却尽在关西。从弘治四年(1501)开始, 杨一清四入陕西, 先后在关陇边塞苦寒之地度过了十五年, 在明代政治史和军事史上烙下极深的印痕。“登坛还是一书生”[1](P473), 杨一清在戎马倥偬之间, 不废诗书, 建正学书院,鉴识李梦阳等于寒微之际, 皆为明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佳话。其诗集《石淙诗稿》十七卷, 依编年体的形式分为凤池类、省墓类、禫后类、西巡类等十四种, 为我们研究其经历与创作提供了直接材料。其中西巡类、行台类、制台类和督府类,是其四入陕西所作。从凤池类到禫后类, 是杨一清人生的准备期和诗歌的发轫期;从西巡类开始, 杨一清开始书写其宏伟的人生画卷。李梦阳在杨一清《闻陕西命下有述》一首后批曰: “此以后作意气健畅。”[1](P391)正是北方峻伟的山川和百战沙场的边塞生活, 为他的诗歌增添了如许英雄气。本文以杨一清的边塞书写为考察中心, 以杨一清四入陕西的文学唱和与创作为线索, 通过其文学交往及对边塞题材的选择与书写, 管窥明中叶文学从中央到地方、从馆阁到江山朔漠、从台阁体到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动态及其内在逻辑。
一、从京国到边塞的诗学互涉与转进
杨一清与李东阳私交甚笃,李东阳被作为神童举荐的故事流播广远。杨一清也是他们序列里的一个。他八九岁时以神童荐入翰林,读中秘书。成化八年(1472),十八岁举进士,授中书舍人,为内阁属官,“职务清简,横经授徒,从者日益众”[2](P522)。自此至成化二十一年(1485)出任山西按察佥事,在阁中办事十余年,所交游者多为翰林院的一时俊乂,如李东阳、谢铎、陆釴、倪岳、傅翰和杨守陈等。杨一清《石淙诗稿》卷一“凤池类”有《和杨镜川先生游南园诗韵》,其中说:“诸公不我弃,枉驾同郊游。”即是与杨守陈等一起郊游之作;杨守陈批语云:“佳作!佳作!当与西涯争衡。”[1](P379)“西涯”即李东阳,此时正在翰林院担升编修或侍讲的职务。李东阳与杨一清往来密切,仅李东阳集中所存唱和之作就超过二十首,他称许杨一清、严宗哲、柳拱之为“文章同时不易得,三杰古称吴富尹”[3](P169),比之为初唐“以经典为本”的富吴体(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富嘉谟吴少微传》:“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嘉谟与少微在晋阳魏郡,谷倚为太原主簿,皆以文词著名,时人谓之北京三杰。”(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13页)。弘治四、五年间,杨一清、严宗哲先后赴陕,李东阳分别赋《寄应宁提学用留别韵二首》《次严宗哲太守留别韵兼寄应宁》;又有《送柳拱之宪副之岷州兼柬应宁提学、宗哲太守》等,可见作为一个唱和群体,他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
杨一清第一次入陕在弘治四年(1491)至十一年。据焦竑《熙朝名臣实录》卷十二,杨一清“服阕补陕西提学副使, 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凡八年在陕。大作士类, 士有博记诵者、修文辞者、专攻举业者, 所学不一, 皆诱而进之”[4](P187)。杨一清选拔培植人才不拘一格, 有教无类, 他这一时期的工作对陕西文教事业的发展尤为重要。提学副使的主要工作场所在安定门内侧的西安贡院。强晟《汝南诗话》记载了他们在贡院里的讲学活动: “越明年癸丑,杨邃庵先生时为提学宪使, 檄予等入贡院会讲五经。……时在会者生徒几二百人, 皆关中之杰。邃庵程督既严, 而予五人者奉约惟谨, 故一时科第之盛, 实前后之所不及。时诸生有为诗者云: “堂上杨夫子, 堂前董五经。长安人夜望,应讶聚文星。’”[5](P54)该年为弘治六年, 李梦阳即将参加会试, 康海、吕柟等已成秀才, 如果他们厕身于诸生之列并非奇怪的事儿。杨一清“西巡类”有《读李进士梦阳诗文喜而有作》一首说: “细读诗文三百首, 寂寥清庙有遗音。斯文衣钵终归子, 前辈风流直至今。剑气横秋霜月冷, 珠光浮海夜涛深。聪明我已非前日, 此志因君未陆沉。”[1](P411)杨一清这时刚满四十,但已说自己聪明不再,对风华正茂的李梦阳充满期待, 预言他是斯文的担当者。他还声称“康之文辞, 马、吕之经学,皆天下士也”, 于是关中诸子“身未出里中, 而名已传海内,动京师矣”[6](P47)。
当然,书院教育是一种意识形态教化,诗歌创作却是一种介于私人生活与公共交往之间的文化形态,是儒家官员文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学者与诗人的双重身份在杨一清身上相得益彰,朱诚泳评价他“喜以经学开士类,而海内从游者日益滋,诗文其绪余耳”[7](P337)。作为学宪,杨一清也是程朱理学的拥趸。其《临潼留别西安三学诸生》《秦州谒太昊宫》《正学书院落成有作》等诗有浓厚的理学气。而与秦王朱诚泳的唱和显示了杨一清作为诗人的积极面相。杨一清主持陕西学政的八年,也是他与朱诚泳狎主长安诗坛的时期。杨一清在《小鸣稿序》里曾谈到他与朱诚泳的关系:“岁时偕三司进见,必留坐与谈,所谈惟诗,不及他世事。”[8](卷首)“所谈惟诗”和“世事”之间界限分明,表明他与藩府的交往分寸极严。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朱诚泳《小鸣稿》看,他们的唱和是频繁的,既有咏雪的唱和之作,也有赏菊的联句之作。在他们的唱和中,联句诗与禁体诗得到普遍采用。
一是联句诗。《小鸣稿》第八卷全为联句诗[7](P318-319),如《二月二十二日与杨应宁宪副、宋惟寅宪佥、强景明伴读城东泛舟同作二首》为郊游泛舟之作,如《淡香亭赏菊与丘仲玉少参、杨应宁宪副同作》《赏菊与严宗哲太守、长史吴元素乔思孝、伴读强景明同作》等皆九月赏菊之作。九月赏菊是文人雅集的重要传统,朱诚泳也往往“九日招文士,东篱醉菊花”[7](P316),其联句尤以赏菊诗为主要题材。这里既有前文涉及的严宗哲、杨一清和强晟,还有右副都御史戴珊、安抚使阎文振、王府长史吴元素、纪善汤潜等,构成了一个陕西文学尤其是秦藩文学唱和的一幅剪影。这种联吟方式在成化以来京师馆阁文人圈子中甚是流行,顾璘说:“成化以来,李文正翔于翰苑,倡中唐清婉之风,律体特盛;其时罗、谢、潘、陆从而和之,声比气协,传为联句,厥亦秀哉!”[9](P18)认为李东阳等的倡导是联句唱和诗滥觞流行的源头。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也明确以为:“联句诗,昔人谓才力相当者乃能作。韩、孟不可尚已。予少日联句颇多,当对垒时,各出己意,不相管摄,宁得一一当意。惟二三名笔,间为商确一、二字,辄相照应。方石尝谓人曰:‘西涯最有功于联句。’若是则予恶敢当。”[3](P1523)可见,这种联句唱和形式构成了馆阁文人争奇炫才的重要面相。因而,朱诚泳与杨一清、严宗哲等人在长安所开展的联句唱和并非孤立的文学现象。这种唱和活动与馆阁文学生态桴鼓相应,是这一时期自上而下的一种诗歌生产机制。
二是禁体诗。禁体诗向来以咏雪为主要题材。今朱诚泳集中有四首与杨一清的咏雪和韵之作,如《和杨应宁佥宪咏雪韵》与杨一清《诵雪诗》都押“肴”韵,无疑是相和之作,其中说:“驿途来往亦良苦,驱驰不异蓝关道。推敲马上有新诗,象外神游劳腹稿。形容变态步今古,大笔端能补天造。”[7](P231)用轻松写意的笔调勾勒出了杨一清的诗人形象。在另一首《咏雪和杨应宁宪副韵》中,他颂美杨一清为“争似风流豸史,聚星独擅诗才。”[7](P287)禁体诗,也称为聚星堂禁体诗,据宋欧阳修《雪》诗自注及宋苏轼《聚星堂雪诗叙》所记,禁体诗的写作不得运用通常诗歌中常见的体物字眼,如咏雪不用玉、月、梨、梅、练、絮等熟字,意在难中出奇(2)禁体诗创自欧、苏。欧阳修《雪中会客赋诗》诗自注:“在颍州作,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字皆请勿用。”元祐六年,苏轼祷雨得雪,与客会饮于聚星堂,修欧公故事,“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苏轼《聚星堂诗并叙》,《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14页)。今杨一清和朱诚泳集中各存有一首《和苏长公聚星堂禁体韵》[7](P229);杨一清写了《和欧阳公禁体雪诗韵》[1](P406),朱诚泳则写了《咏雪诗和欧阳公禁体韵》[7](P219)。事实上,创作禁体诗的风气其来有自。黄佐《翰林记》曰:“成化丙申十二月十日,祷雪致斋于翰林之东署。侍读倪岳、侍讲程敏政、修撰陆釴、编修陆简同宿,是夜雪大作,逐用欧公禁体故事,相与阄韵联句以志喜。”[11](P1025)这些人大抵是李东阳、杨一清的诗友,他们在杨一清、朱诚泳唱和前的三十年,就在翰林院“用欧公禁体故事”,即兴咏雪,而倪岳所作即为《岁暮祷雪致斋柬李东涯学士》,甚至李东阳也不乏同类作品,如《雪用坡翁聚星堂禁体韵》[3](P188)。杨一清《诵雪诗》中说: “欧公禁体多大篇, 等闲脱略前人稿, 后来效者苏长公, 真觉暮年有深造。”[1](P402)李东阳评价此诗如“老吏供案,赞欧似未尽”, 认为这是杨一清对其诗学门径的自供, 但其中以“等闲脱略”等语评欧公禁体, 却未必准确。可见, 他们的咏雪诗创作的确是对欧、苏禁体诗的自觉承继和发展。禁体诗创作原本体现了北宋诗人推陈出新的创作意图, 衍为明代京国翰林文士们炫才争奇的诗才竞技, 而从京城文坛中成长起来的杨一清, 把来自翰林圈子的审美趣味带到了边疆之地。[12](P112-130)
显然,京国的翰林文学相对地方文学的优势是明显的,朱诚泳曾向杨一清言:“余生长藩服,强自为诗,无所质正。子尝从馆阁诸老游,凡予所作,有所未安,虽一字一句,为我指疵,毋有所避。”[8](卷首)对避居长安的朱诚泳来说,馆阁文学的新风气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但京国文学与地方文学的影响并非单向度的,边疆的人文地理也为杨一清的诗风注入新意。提学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巡视地方、考核学子,“先生之按部,则虽祁寒炽暑无倦色”[7](P337),所以这一时期的杨一清还创作了不少的行役诗。如《还至庄浪》写道:“平少落日路漫漫,千里风光一色看。刚到雨来翻见雪,偶然热后忽生寒。城非据险兵犹少,地屡经荒食更难。稍喜沿边诸将吏,肯甘清苦慰凋残。”[1](P409)刚才还是空濛雨,忽然变作缤纷雪;刚才还酷热难耐,瞬息就沁骨生寒,这是经行北方的独特感觉。当杨一清走出书斋,走向江山大漠,我们看到了一个洋溢着英雄气的诗人,这为日后的出将入相埋下伏笔。由此可见,出身馆阁的杨一清的确把馆阁文学中盛行的联句、禁体之风注入了秦藩唱和之中,而边塞风物与感受也赋予杨一清诗歌以新的风格面貌,改变着其书写形态。这种改变随着杨一清的边塞体验的不断深入和政冶身份的变化而有了全幅的展开。
二、经营西北的诗史实录
杨一清第二次入陕是在弘治十六年,以左副都御史的身份,督理马政。其《入关》曰:“手提文印七年还,五载乘轺又入关。化雨三千秦子弟,秋风百二汉河山。”[1](P436)“七年”指弘治四年到十一年在陕西任提学副使,“五载”指弘治十一年至十五年在朝任太常寺少卿、太常寺卿。此后的弘治十八年,杨一清升任陕西巡抚兼经理边务;正德改元,又以右都御史的职位被委以三边总制的重任。其《行台稿小引》曰:“越二年丙寅,今上皇帝以陕西虏患方殷,三边权无专制,无充成功,诏廷臣议举堪任总制大臣,一清乃复误被登简,进右都御史。”[1](P435)但一年后,他因病请辞,退隐镇江。
明代北方的鞑靼人侵扰内地,从燕北至甘陇烽火不断。杨一清投笔从戎,战而能胜,实现了其经略西北的宏图。这一时期,他的诗歌有金戈铁马之声,有奋马扬鞭的英雄气象,更有忠诚恻怛的忧患意识,李梦阳以之为“自负自矜,卒践其言,伟然乔岳,屹然长城”[1](P439)。其集中诸作颇可以作诗史观之。例如《弘治十二年冬十二月,北虏大举入寇,有诏臣一清经略防御兼理巡抚,受勅之明日督军赴边》曰:
拜罢纶音便启行,边头豺虎正纵横。非才敢道宽西顾,仗节安能避北征。将士几人称善战,关山何地是长城。主忧臣辱心应苦,愧有涓埃答盛平。[1](P437)
杨一清《自讼稿序》说:“甲子冬十二月,北虏潜伏河套间,拥众入寇,宁夏守臣失利,遂入犯环庆、固原,宁夏、陕西两镇守臣交章告急于朝。我孝宗皇帝从本兵之议,命臣兼巡抚陕西地方经略防御。乙丑春正月,臣始拜敕,即驰至固原,以便宜处置战守。未几,虏遁归河套。”[1](P453)这种记事诗全篇议论,写自己临危受命、义无反顾的使命感和赤胆忠心, 出之肺腑,沉稳严整,忠诚恻怛,受杜甫的影响为多。
杨一清以书生戍边, 投笔从戎。作为明王朝经略西北的总负责人, 他熟稔边情,深谋远虑, 以为“善战何如不战高”[1](P438), 践行了自己战略思想和大局观。他经营边关的思路和作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筑城。筑边城是抵御北虏的基本思路。杨一清莅临三边,即“以宁夏花马池系要害地,虏数由以入。公率官属沿边巡视处方略,上疏极陈战守之策:修濬墙堑以固边防,增设卫所以壮边兵;经理宁夏以安内附,整饬韦州以遏外侵”[2](P527)。其安边策强调修缮长城,以巩固边防硬件,并在长城沿线重点区域增设卫所。他所规划的战略重镇,一是宁夏,一是韦州。
明成化、弘治年间大规模修缮长城有两次,一次是余子俊修建榆林段长城一千一百五里,一次是徐廷章修建宁夏河东长城从横城堡至花马池三百余里。由于河东长城处于明蒙战争的要冲,杨一清首先对河东段进行了加固改善,“正德元年,总制杨一清修筑徐廷章所筑外边墙,高厚各二丈,墙上修盖煖铺九百间,墙外濬旧堑亦深阔各二丈,于是外边之险备矣。”(3)魏焕撰《皇明九边考》卷一镇戍通考:“今按,河套边墙自国初耿秉文守关中,因粮运艰远,已弃不守,城堡兵马烽堠全无。成化八年,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奏修榆林东中西三路边墙崖堑一千一百五里。十年,巡抚宁夏都御史徐廷章奏筑河东边墙黄河嘴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已上即先年所弃河套外边墙也。弘治十五年,总制尚书秦纮奏筑固原边墙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虏营花儿岔,止六百余里;迤东至饶阳界止三百余里,已上即今固原以北内边墙也。正德元年,总制杨一清修筑徐廷章所筑外边墙高厚各二丈,墙上修盖煖铺九百间,墙外濬旧堑,亦深阔各二丈。于是外边之险备矣。”(中国基本古籍库扫描明嘉靖刻本)方孔炤辑《全边略记》卷六:“(正德)二年四月,总制杨一清奏:顷因建议修筑边墙,挑濬濠堑。自宁夏横城起至延绥定边营迤东石池宁静墩界止,边墙三百余里,连濠堑六百余里。原拟人夫九万余名,若一并起工,则督视不周,将应起人夫分为二班,布政司支八万运贮庆阳籴粮,顷因西安平凉久旱,暂停。二月以来,时雨连降,又令宁夏起取本镇平凉、固原兴工。查得西安等府及各卫所护卫等应起军民共八万名,比之原拟,十去其一。每班各赴工三月,每夫日给口粮一升五合,仍令户内助路费银二两。每十夫共备车一辆,装载煤炒器具,每二夫出席一片,掾一根,到彼列车为营,覆以椽席,用蔽风雨。其汉中府卫栈道之外地方,既不征夫,量征其价,运送工所,月犒二次,茶马项下官银动支一二百两,置买药饵,选备医疗。自延绥宁塞营起至定边营止,添造墩台一百四十二座,兴筑铲削边墙壕堑共三万七千二百六十丈五尺。合用拨木已于雪山采办,共三十余万。运至边,迨墙完即令建营房煖铺,其横城以北次第举之。大司农已给二十六万,责以垂成,而清以病归,得旨边役姑寝之。”(中国基本古籍库扫描明崇祯刻本)《国朝献征录》卷十五谢纯《华盖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襄杨公一清行状》又谓:“公以三月兴工筑边墙,刻期奏绩。时刘瑾憾公,公遂乞休,工亦罢。仅筑四十余里,至今屹然巨障。”[2](P528)在此基础上,杨一清在河东长城沿线增设卫所,加固堡垒,如兴武营“本汉朔方郡河南地,旧有城,不详其何代何名,惟遗废址一面,俗呼为‘半个城’。正统九年,巡抚都御史金濂始奏置兴武营,就其旧基以都指挥守备。成化五年改守备为协同,分守东路。正德二年,总制右都御史杨一清奏改兴武营为守御千户所,属陕西都司。城周回三里八,分高二丈五尺,池深一丈三尺,阔二丈,西南二门及四角皆有楼。”[13](卷三)杨一清曾登楼赋诗云:
簇簇青山隐戍楼,暂时登眺使人愁。西风画角孤城晚,落日晴沙万里秋。甲士解鞍休战马,农儿持劵买耕牛。翻思未筑边墙日,曾得清平似此不。[13](卷三)
表达了对筑城政策的自负。一清在总制期间还“创城平虏、红古二处,以援固原,筑垣濒河二带,以捍靖虏,虏遂不敢渡河。”[2](P522)杨一清《豫旺城》写其在平虏所见:
冰霜历尽宦情微,又上高楼坐夕辉。野草烧余胡马瘦,塞屯开尽汉兵肥。沙场估客穿城过,草屋人家罢市归。不谓荒凉今得此,当年肃敏是先几。[1](P438)
豫旺城即是韦州平虏所,处在从花马池到固原大通道的关键位置,杨一清在此构筑了从河东长城到固原之间的第二道防线,以捍卫固原及关中腹地。尾联的“肃敏”指成化年间左副都御史余子俊,其战略思想颇为杨一清所推重和汲引。这首诗颈联以胡马与汉兵对比,写明军之以逸待劳,有备无患,颔联写边地居民的平安喜乐,皆是筑城带来的积极后果(4)方孔炤辑《全边略记》卷四:“十六年,刘天和奏固原为套虏深冲,前秦纮修筑边墙延袤千里,然虏每大举尚不能支,及杨一清筑白马城堡而后东路之寇不至,王琼等筑下马房关而后中路之患得免。”。
二是积粟。如其《闻河套有警》曰:“百二秦关故可凭,延、宁千里险堪乘。黄河下绕还成套,虏骑冬来惯踏冰。塞上烟尘嗟未息,胸中兵甲愧无能。粟刍山积君休羡,民力年来已不胜。”[1](P438)颈联尤为警拔,尾联“粟刍山积”也是杨一清镇边时的政绩之一。此前,边城积粮甚少,兵无战力,杨一清建议在边关增开盐引,引导民商运粮支边,遂使得边地粮储充足,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虽然这首诗末句表现了作者的忧患感,但这可以视为士大夫民胞物与情怀的习惯性表达,其“自矜自负”的襟怀一望可知。
杨一清也亲临战场,身先士卒,颇具胆识。谢纯在为杨一清所撰行状中以生动洗练的笔法记下了弘治十八年的一次战争:“乙丑冬,虏数万入宁夏,乘胜直抵固原,远近危疑,公率帐下五十余人,趋会总兵曹雄议方略。众遮道不可,参政安惟学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狥国,成败利钝非所计也。’竟去。贼围各马营见原选新兵军容甚整,贼骇之。又闻公且至,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先是已聚城中人,裹毡乘城,连发火炮,响应如数万人。酋长疑我大兵至,遂掣众此走。公发平凉时,道无行人,关中震恐,众谓与郭子仪单骑见虏相类。”[2](P522)杨一清文武全才,所谓“扶危定倾,奏效安攘之绩,并足以为国家重。”[14](卷二六五)《明史》以为“其才一时无两,或比之姚崇。”[15](P5231)但其传记作者显然认为他更具有郭子仪之风范。杨一清的《广武吟》,写战争情形颇为惊心动魄:
广武城西边堑边,黄沙白草何茫然。我行旌旗耀天日,千骑弓马相后先。须臾直北风尘起,炮火络驿随双烟。毳衣氊帽胡为者,百数十骑声喧阗。我士衔枚寂不语,卒然相逢彼魂褫。便遣轻骑略追逐,奔北不敢回头视。山高日暮追难穷,小丑何足当吾锋。不闻周诗咏薄伐,况我素不希边功。下令收兵入去去,且秣吾马橐吾弓。人言“此地此常事,不道我公天上至。吾侪幸脱虎口中,前日遗骇犹野弃”。中原无处无良田,此辈流落真可怜。为王戍边良不恶,何止要贪生处乐。[1](P474)
他是明代较早使用火器取得战功的将军,徐光启说:“夫火器之来也,自永乐间征安南始也。其稍盛也自嘉靖间御倭始也。用而效之者,若杨襄毅、曾中丞、郭文定、周尚文、戚继光之属,非一人也。”[16](P54)杨襄毅,即指一清。诗中生动中展现了一场伏击战的场景,明军策略得当,大炮火器的使用初见成效,北虏望风而遁。诗风流丽俊伟,夹叙夹议,开阖自然,堪称力作。
杨一清这次入陕,行台在平凉,远离了关中士大夫的文学圈子。但他仍有师友唱和之乐。弘治十六年,状元及第的康海,送母返回武功,即驰平凉拜见恩师。杨一清《翰撰康德涵谒予平凉行台》曰:“冀北千金收骏骨,关西多士有龙头。”[1](P436)又有《送康状元还京》:“相马自超形色外,看花须及未开时。”对自己能识骏马沾沾自喜。他一方面对康海寄予厚望:“状元忠孝男儿事,不独文章要擅场。”另一方面,也对康海在文行出处方面的特立独行予以警告:“羞随世态翻疑拙,力去陈言恐近奇。”[1](P439)正德元年,何孟春、乔宇先后以公务至陕,杨一清皆有酬答。乔宇是杨一清在山西学政任上的弟子,这年冬奉祀华岳,遂与王云凤偕至邠州。杨一清《邠州与乔希大夜话》说:“行台深锁一灯明,坐听高城报五更。今夕何夕见吾子,似醉不醉今人惊。青山梦里归未得,白发年来添几茎。不须理问投簪事,愧有尺寸虚平生。”[1](P440)可能面对这些宦海经年的早期弟子时,杨一清更愿意敞开内心里细腻的部分吧!他的诗里多了几分温情,也多了几分戎马经年的疲倦感。在与乔宇等相会后一年,杨一清果然解甲归田,回到他不曾忘却的梦里青山。
三、边塞诗风与诗坛风气的开拓
杨一清第三次入陕在正德五年,首尾仅六月。其《再出关》诗自注:“正德庚午十月,敕起驰驿赴京。”[1](P559)这次入陕虽然时间短暂,却促成了正德政局的大逆转。入关的原因是寘钅番之变。当杨一清临危受命之际,寘钅番之变已折戟沉沙。但杨一清到陕后除了缮后恢复外,还结交宦官张永,授意其发刘瑾之奸,导致了刘瑾集团的覆灭。焦竑《熙朝名臣实录》云:“众但知瑾之诛为张永所发,不知永实受算于一清,遂成之耳。”[4](P189)
杨一清《石淙诗稿》卷十有《五月二日拜征命,有赦小过用贤才之谕,感而有作》《初四日拜总制陕西之敕越二日雨中渡江》《五月二十八日,拜提督军务敕书及白金文绮之赐,时闻元恶何锦等已就擒斩》等,沿续了他“道故实,纪诗史”[1](P587)的作风。李梦阳以为“以下六篇,浑浑之作,虽欠警拔,然记事变,心迹皎然,勃然不可无之作也。”[1](P473)如其《将至宁夏》:
奉诏西征驻节时,元戎奏凯已先期。苗民自逆三旬命,猃狁何劳六月师。灯火家家开夜户,弓马队队卷秋旗。益兵加赋休重道,财力于今两不支。[1](P473)
诗风严整清切,颈联写出战事结束后宁夏兵民重整旗鼓的场景。尾联是大议论,既是政治上的深谋远虑,也是诗人对和平的美好祈愿。以下两首《宁夏书事》也体现了同样的情怀:
华戎一统载升平,何物潢池敢弄兵。陆贽诏颁人泣下,令公师出虏魂惊。阴云扫尽天终大,璘火消余月正明。受命独惭来已后,敢辞心力为经营。
贺兰设险自天成,河水西来半绕城。边堠弃余多虏警,塞屯量尽少人耕。山前钲鼓黄云乱,帐下貔貅白日明。却恐路人闲指议,登坛还是一书生。[1](P473)
老将临边,挥毫作诗,少藻饰而气象正大,沉著顿挫。这是将军之诗,有文人所不能望其项背之处:一者格调高亢,不作无病呻吟之状。如“阴云扫尽天终大,璘火消余月正明”之深远,如“贺兰设险自天成,河水西来半绕城”之辽阔,如果没有对北方生活的沉浸,没有出将入相的胸怀,很难写出这样的诗句。二者作为政治大员,杨一清的诗歌善于大议论,往往于寻常处犹见警拔。如“边堠弃余多虏警,塞屯量尽少人耕”,不仅仅写出边城萧条景象,也是对明代九边治理的深刻反省和痛心,李梦阳在诗后批语以为“西夏之弊,正坐撤堠废比耳。人之不知,安能道之。”不用说不谙边事的文士,如果没有丰厚的政治经验与亲力亲为的边关经验,如何能有舍身处地的共鸣?
杨一清“制台类”里有《过盐池悼盐法之衰有作》《平凉悼马政之废追忆先皇帝成命志感》诸篇,他当年治陕的善政,现今都已荒废了。他在《阅旧筑边墙自红山堡至横城高厚坚完俨然成一巨障,惜成功之难,叹前志之未遂,感而赋此》里写道:
经过旧筑边墙路,俨作金汤百里雄。岂为人言妨大计,只缘身病废成功。长山巨浸抛来久,白草黄沙望未穷。老去寸心犹不死,仗谁经略了余忠。[1](P474)
《(嘉靖)宁夏新志》卷三:“横城堡东至红山堡二十里,西逾河至宁夏二十里。正德二年,总制右都御史杨一清奏筑,周回一里许,置旗军三百名、操守官一员、守堡官一员。副使齐之鸾《登横城北眺杨邃庵所筑边墙》诗:‘新墉山立界华夷,元老忠谋世莫知。流俗眩贞人异见,宏规罢役岁兴师。万夫版筑忧公帑,千里生灵借寇资。试问迩来胡出没,何缘不自横城窥?”[13](卷三)所以我们知道,所谓“边堠弃余”、所谓“塞屯量尽”,都是杨一清当年戍边时惨淡经营的事业,所以当他看到这一切毁弃无余,心痛之感,又岂是他人所能领会!
杨一清在行台时期和制台时期的诗风苍健老辣,边塞风物在他的诗中烙下深深的印痕。边塞诗或战争诗在盛唐时代蔚为大宗,衍为流派,但在唐代以后,随着国土日蹙和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此类诗歌便不再是诗歌书写的主流形态。但在明代,由于明王朝与蒙古的长期对抗,九边重镇的边塞书写一直是文人、特别是复古派文学创作的重要面向。这一方面,杨一清的弟子李梦阳颇负盛誉。如其《秋望》:“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韬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17](P1170)这类型的诗歌感激时事,苍茫寥落,全是杜诗风格。穆敬甫称其“如云屯高岭,风涌飞流”。李梦阳的边塞书写与杨一清颇有相通之处,即喜欢就重大时事发表议论,如《秋怀》其五:“胡奴本意慕华风,将校和戎反剧戎。遂使至尊临便殿,坐忧兵甲不还宫。调和幸赖惟三老。阅实今看有数公。闻道健儿今战死,暮云羌笛满云中。”[17](P994)弘治十七年五月,和硕诸部犯大同,都指挥郑瑀御之。《明通鉴》曰:“战久力屈,犹手刃数人而死。敌就前支解之。”[18](P1385)李梦阳闻而作《秋怀》其五,实是有感而作。据《明通鉴》,“先是,鞑靼诸部上书请贡,许之,竟不至”,和硕部遂“入大同杀掠墩军”。此之谓“胡奴本意慕华风,将校和戎反剧戎”。嗣后,明孝宗屡次征召刘健等议边务,《明史》曰:“辛巳,召刘健、李东阳于暖阁,议边务。”[15](P195)时在六月十七日。《明通鉴·考异》曰:“据《明史》本纪,召刘健、李东阳在是月辛巳,而墎军败问,越三日癸未至,似阁臣召见不止一次。”[18](P1385)此是“遂使至尊临便殿,坐忧兵甲不还宫”,盖时事之实录也。章宪文《白石山堂诗话》对李梦阳的歌行再三致意:“明诗惟献吉创古,亦惟献吉称大家。如《松窗读易图》《石将军战场》《豆莝行》《土兵行》诸篇,直上下少陵,于鳞、元美诸君不觉瞠后。”[5](P247)其战争行役诗,感慨时事,音节激昂,传诵海内。和杨一清同类边塞诗和战争诗相比较,诗歌中炽热饱满的情绪与民胞物与的家国情怀是桴鼓相应、一脉相承的。
李梦阳重视诗歌的艺术表达,认为诗歌的色泽其实是生命力的呈现,尤需斟酌。谢榛《四溟诗话》说:“黄司务问诗法于李空同,因指场圃中绿豆而言曰:‘颜色而已。’”[19](P1170)但就李梦阳的主要风格而言,其所谓“色”并非隐逸诗人那种底于平淡,也不是六朝诗人那种鲜艳明媚,而是苍茫浑厚的古朴之美。他偏爱以黄、白着色,黄是黄沙、黄河、黄云,白是白雪、白月、白日,例如:“沙寒白日蓬科转,风起黄河木叶稀。”[17](P1094)“隘地黄河吞渭水,炎天白雪压秦山。”[17](P1173)“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17](P1170)“黄河白草莽萧萧,青海银州杀气盛。”[17](P1175)“白豹寨头惟皎月,野狐川北尽黄云。”[17](P993)甚至是“城边白骨借问谁?云是今年筑城者。”[17](P573)边塞山水构筑了其诗歌的底色。而我们重新检视杨一清的边塞诗,就会发现他们的格调如出一辙。如《宁夏书事》中“山前钲鼓黄云乱,帐下貔貅白日明”[1](P473);如《阅旧筑边墙》和《广武吟》中的白草黄沙;如《中卫道中》的“落日平少远西风,白草新野猪场稼”[1](P474)。即使李梦阳在书写艺术上可以后来居上,但杨一清诗歌中的原生性和真切感,却是李梦阳不能企及的。因此,认为李梦阳的边塞书写受到杨一清的影响应当并不为过。
总之,杨一清莅临西事,横槊赋诗,以政治家的格局写西北风物与边地战事,高屋建瓴而有英雄气。这种边塞书写是明代中叶明蒙战局深化的逻辑结果,促成了杨一清诗歌在题材与风格上的重要转进。这种关注边地战事、书写边塞情怀的创作趋势也成为以李梦阳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重要题材。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是时代政局在弘正时期诗人作品中烙下的共同印记,但杨一清的英雄事业和边塞书写对李梦阳的示范性也显而易见。
四、余论:文章衣钵与盖棺定论
杨一清第四次入陕是在嘉靖四年(1525)至五年元月。正德十一年(1516),杨一清在吏部尚书任上引退,蛰居镇江十余年。嘉靖四年正月,“授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陕西诸边军务,命巡抚都御史即家敦遣启行”[2](P254)。
这次出山,杨一清已年过七旬,虽壮心未已,但也没有能像前三次一样建立不朽功勋。他需要为自己的身后事作打算了。因此,他这次往返途中,两晤李梦阳,委托其评定诗稿,视其为身后桓谭。《石淙诗稿》卷十七《中牟公馆与献吉提学话旧用前所寄诗韵二首》再次重提三十年前的话题:“三十年前曾让子,知言窃比宋欧阳。”“斯文衣钵自吾人,出处平生各任真。”[1](572)要把文章衣钵授予梦阳。次年元月二日,杨一清于乾州留别另一弟子康海,飘然出关。从此,关中再无杨石淙。
这一时期的诗歌仍然奋发踔厉。《塞上曲》十首是堪称其绝句的代表作:
连年铁甲戍穷边,霜里栖身草上眠。为王戍边良不恶,忍冻妻儿还可怜。
花马池连兴武营,东有清水西横城。上得边墙望环固,千里沙场如砥平。
玉门金垒势崔嵬,百二秦关亦壮哉。天为华夷限疆域,河湟一水故西来。[1](566-567)
其六写塞上生活,感同身受而不沮丧,“妻儿”一句翻过一层,情思细腻婉转;其八皆用地名连缀成句,结句一笔荡开,视通万里,便觉豪气生辉;其十是诗人擅长的大议论,他的这类型作品往往令人有高屋建瓴之感,体现了政治家的襟怀。他在庆阳拜谒了寇准祠,并赋诗云:“半亩荒基数尺墙,宋家贤相表新坊。楼台不用生前起,祠宇能延没后香。未拔一丁真负国,纵为孤注已尊王。后人不建新征荣,和议终成祸靖康。”[1](P559)前四句写实,后四句论史,却虚实相生,不即不离,发人省思。诗歌写得气氛庄重,没有虚美。世无完人,寇准如此,杨一清何尝不是如此,诗中“未拔一丁”应也是杨一清的政治遗憾,“尊王”攘夷则是他一生的事业,因此,“楼台不用生前起”一句,杨一清可以引之自况了。
关于杨一清的诗风,李梦阳云:“先生诗矜持严整,俊拔典则,七言律为最工,虽唐宋杂,瑜瑕靡掩,然所谓千虑一失。”[20](P632)这个概括基本是准确的。只是李梦阳站在宗唐的立场上批评杨一清的诗歌杂以宋调,却是见仁见智的。朱彝尊说:“邃庵古诗原本韩、苏,近体一以陈简斋、陆放翁为师。”[20](P632)认为杨一清诗歌有陈与义和陆游的风格,这颇符合杨一清的自我期许,他的集中不但有诸如《和苏长公韵》《雪中用苏长公韵四首》等和苏诗,也有一首《阅陈简斋诗集》,诗云:“诗到晚唐人已厌,末流谁遣又西昆。简斋故出坡翁派,蹊径真超老杜门。端瑟尚馀高雅调,天机全谢剪裁痕。君看香色如花喻,不是须溪未易论。”[1](P467)从苏轼到陈与义,皆能在老杜以外,不落蹊径,被他视为“高雅调”。或许陈与义和陆游在靖康罹乱后所写的英雄悲歌更让杨一清充满共鸣吧!
作为馆阁领袖,李东阳对杨一清“奇气勃勃”[1](P401)的西巡诗也颇感惊艳。杨一清出将入相,戎马一生,其诗虽多,但往往不修边幅,有时夹以道学气,也有良莠不齐之病,而西巡事业无疑开拓了杨一清的诗境,他的诗作在北方山川与边塞苦寒中得到历练,有金戈铁马之声,有奋马扬鞭的英雄气象,更有忠诚恻怛的忧患意识;他的诗风雅健雄整,风骨遒上,重节义、好议论却有卓见,拔戟自成一队。李梦阳以之为“自负自矜,卒践其言,伟然乔岳,屹然长城”[1](P439)。事实上,杨一清的西巡诗风的雅健与北京李东阳主导的馆阁文风的流易迥异,与关中朱诚泳一派近于晚唐哀艳的作风也颇为不同,正是这种感激时事、雄肆苍健的作风让杨一清与李梦阳代表的关陇学子们有了其内在的联系。
正德初年,李梦阳在写给徐祯卿的长诗里说:“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17](P566)以杨一清与李东阳并列为文学宗师,这虽不无溢美,但至少表明杨一清在弘正时期的文坛有其地位和影响。钱谦益对李梦阳的这一评论很不满意,认为“盖当成弘时,长沙为一世宗匠,献吉并举杨、李,不欲使专主齐盟,轩杨正所以轾李也。文章千古事,非一家私议,而献吉之用心如此,于两公则何所加损哉!”[21](P2855)但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力贬七子、推尊长沙的文学史叙事,其“用心”不也应予省察和商榷吗?清初另一大家朱彝尊则说:“献吉送昌谷诗云:‘吾师崛起杨与李,力挽元化回千钧。’初意杨非李敌,不过为师同耳。及观《石淙集》实有高出李者,乃知文士以千秋自命,类不轻许人也。”[20](P632)邓显鹤《沅湘耆旧集》也认为杨一清“诗才力不减涯翁,晋楚匹敌,未易低昂。而世知有《怀麓堂》,《石淙集》鲜有能称述者,殆以功名掩与”[22](P589),这其实也不无道理。杨一清的诗歌是在边塞事业中自我证成的文化生命,其诗以北方山水与军旅行役为题材,意气健畅,包蕴广大,彰显了北地文学的风骨,不仅在弘正时期的文坛独树一帜,对文学复古运动也有其示范意义。同样“自负自矜”的李梦阳始终把杨一清视为知音和引路人,这是不无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