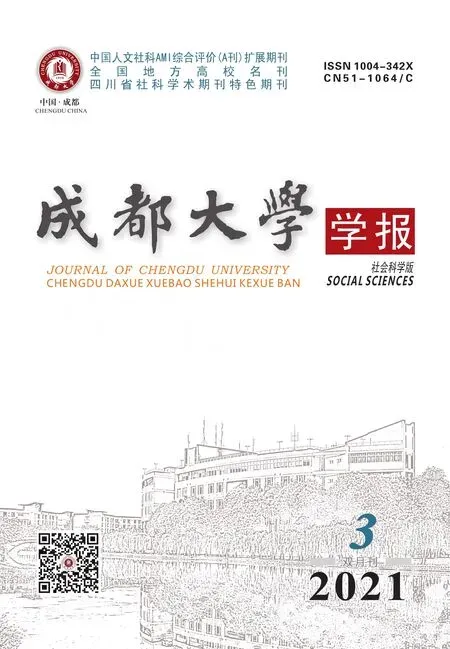《水浒传》“玄女授书”情节的构建*
张传东
(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玄女授书”情节在宋人所作《大宋宣和遗事》中已经出现,但只以寥寥五十余字粗陈梗概:宋江为躲追捕避入玄女庙,在拜谢玄女娘娘后“则见香案上一声亮响,打一看时,有一卷文书在上”[1]。而《水浒传》中的“玄女授书”则用整整一回的篇幅来详写宋江进庙、入幻、与玄女宴饮、获赐天书、离开幻境等过程,并在后文用天降石碣来照应天书的内容。情节设计精细,小说意味浓厚,有力地推动了故事发展。这两部作品中的“玄女授书”设计思想导源于汉代谶纬中神授天书的观念,如《艺文类聚》所引纬书《龙鱼河图》中关于玄女助黄帝战蚩尤的故事:
黄帝摄政时,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仁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黄帝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2]209
但是从《大宋宣和遗事》到《水浒传》,情节的重新设置和细节增饰明显是《水浒传》作者文学创作的功劳。这一创作却并非毫无根据,乃是借鉴了古代志怪小说尤其是人神遇合型小说的叙事模式和特点。目前学界涉及《水浒传》“玄女授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九天玄女形象渊源的探究以及天书在水浒人物设置上的作用等,但专门讨论该情节具体构设情况的研究并不多。本文拟从情节的结构设计、细节设置等方面考察其生成条件,并从叙事的角度观察它实现神话人物功能的内在原因。
一、人与庙神遇合型叙事对“玄女授书”结构设计的影响
金圣叹批注《水浒传》“玄女授书”一段时曰:“常叹《神女》《感甄》等赋,笔墨淫秽,殊愧大雅,似此绝妙好辞,令人敬爱交至。”[3]779金圣叹认为《水浒传》中对宋江与九天玄女接遇的描写不同于《神女赋》等赋作中的人神遇合,两者存在雅俗之别。这段话也启发我们,《水浒传》“玄女授书”情节与人神遇合型叙事赋在构思上的相似性,即皆属于人神接遇结构。《水浒传》中宋江所遇之神乃还道村九天玄女庙之“庙神”,所以在众多叙事赋中《高唐赋》的影响要更大一些。《高唐赋》云,巫山神女乃是楚国先王游巫山时所接遇并为之立庙的女神“朝云”,而立庙之事在《神女赋》中先有详细交代,可知《高唐赋》所写实乃最早的人与庙神接遇的人神遇合故事。由此可见《神女赋》与“玄女授书”之间的密切关系。
人神遇合型赋作的内容在六朝及唐代的志怪小说中得以延续和丰富。六朝即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关于女性庙神与人间男子接遇缱绻、临别赠物的小说。这些故事根据情节可细分为两类。第一类,写女性庙神主动到男子住所宴乐留处,一夜缱绻后天明自去。如吴均《续齐谐记》之“青溪小姑”条,写青溪庙神即青溪小姑到男子赵文韶的住处歌诗酬唱,“相伫燕寝,竟四更别去”,离别时小姑“脱金簪以赠文韶”[4]1009;《八朝穷怪录》之“萧岳”条,记述萧岳于毗陵泊舟望月而偶遇“东海姑之神”,“岳因请舟中,命酒与歌宴,及晓请去”[5]2357;《八朝穷怪录》之“刘子卿”故事,写庐山“康王庙”的两位女神均喜欢刘子卿,并至刘住所与之分夜缱绻,“常十日一至,如是者数年。后子卿遇乱还乡,二女遂绝。”[5]2353第二类,写男子出游之际受人相邀相导进入女神居所,与神女接遇绸缪之后携赠物离去。如《八朝穷怪录》之“萧总”条,写萧总“因游明月峡”而“误入”巫山神女的世界,受神女之邀“一夕绸缪,以至天晓”,后获赠神女之玉指环而还[5]2355-2356;《八朝穷怪录》之“刘导”故事,写刘导和李士炯共游南京,在一青衣女童邀引下进入西施的居所,后各获赐礼物回归人世。[5]2357-2358其中第二类小说在结构上和《水浒传》“玄女授书”情节有着较强的对应性,尤其是“刘导”的故事对“玄女授书”情节构建产生的影响应该更为直接。这两类作品尤其是《八朝穷怪录》的作品已经对小说结构、叙事有了较高的艺术追求,接近于唐传奇的体式,所以对人神相遇的过程、宴饮之乐、离别赠物,以及人物出离幻境后的心理等的描写均细致而生动,所以这些故事的结构设置和细节描写应该也是“玄女授书”构建过程中重要的借鉴对象。
虽然上述人神遇合型小说中庙神所赠均非书籍,但这一稳定的叙事范式很自然便可发展到“庙神授书”的层面。因为魏晋小说集《列异传》之“汤圣卿”条已经出现了“庙神授书”型故事:
大司马河内汤蕤,字圣卿,少时病疟逃神社中。有人呼:“社邸!社邸!”圣卿应声曰:“诺!”起至户口,人曰:“取此书去。”得素书一卷,乃谴劾百鬼法也。所劾辄效。[6]16
“社”在汉代为从事祭祀活动的宗教场所,其中有鬼神的供奉,实与“庙”有着相似的性质。此事在《幽明录》也有记载,但比较简略:“河南阳起字圣卿,少时病疟,于社中得书一卷,谴劾百鬼法。”[7]160《广弘明集》卷八《辩惑篇·周沙门释道安二教论》引李膺《蜀记》记录了道教领袖张道陵在“丘社”之中获得“天书”的传说:
张陵避病疟于丘社之中,得咒鬼之术书,为是遂解使鬼法。后为大蛇所噏,弟子妄述升天。[8]
汤圣卿、张道陵的故事中虽没有说明庙神是否是女性,但都用相似的叙事方式讲了庙神主动与凡人接触且赠送天书的故事。这类故事与《水浒传》玄女庙神授书于宋江的情节多有相似:汤圣卿、张道陵等均是为了逃避病疟而被迫潜至神社之中,宋江则是被官兵追捕而逃至九天玄女庙中,两类故事发生的缘由、地点皆存在相似性;汤圣卿和张道陵获得天书相助后均法力大增,成就大事,而宋江在获取天书后按书行事也是多有应验,并最终执掌梁山。可以推测,汤圣卿、张道陵这类粗陈梗概的志怪小说对《大宋宣和遗事》“玄女授书”情节的生成曾有过直接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水浒传》的情节设计。
六朝时期既然有了“神女赠物”和“庙神赠书”两类成熟的叙事模式,自然就会有“神女授书”型故事。并且“神女授书”早在小说《汉武内传》中就出现过,其中王母与上元夫人“下降于武帝,王母授帝《五岳真形图》《灵光生经》,上元夫人授六甲灵飞招真十二事”[9]157。典型的“神女授书”型故事,乃《幽明录》之“河伯嫁女”条。该小说讲述了一男子出游时因躲避溽暑而潜入水中,忽经一女郎引导进入华丽的河伯庙府,受到河伯隆礼款待,并与河伯神的美丽女儿结成姻缘。男子离开时河伯女赠予其多卷“天书”,后在人世凭“天书”之神验安度生活。[7]56可见,在六朝时期“神女赠物”和“庙神授书”两类故事合流后自然出现了“神女授书”型作品,形成了一个“男子避祸——侍女引导——男子入幻——人神宴饮——神女赠书——人神离别——天书应验”的叙事模式,并且对每个环节的描写都非常细致生动。而“玄女授书”情节之结构与《幽明录》“神女授书”故事基本吻合。所以从情节的相似度看,《水浒传》“玄女授书”情节的构思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河伯嫁女”小说的影响。
二、“玄女授书”细节设计对志怪小说叙事元素的借鉴
《水浒传》“玄女授书”情节在很多细节的设计方面也借鉴了传统人神遇合型小说叙事中固化下来的叙事元素。很多叙事情节因为在志怪叙事中出现频率高,便自然具有了象征神鬼意境的内涵,其中常用的桥段也因此具有了固定意义。在“玄女授书”情节的构建中,玄女呼名“星主”、宋江仙界食枣的经历、坠河出幻的方式、出幻后的惶惑心理等四个方面均是对志怪小说叙事元素的灵活借鉴。而这些细节均未见诸《大宋宣和遗事》及其他水浒故事,当是《水浒传》作者在借鉴基础上进行的文学创作。
(一)呼官职:神女对“星主”的呼唤
宋江在玄女庙中忽然被九天玄女的侍者青衣小童唤作“宋星主”,且在宴饮过程中一直被九天玄女呼作“星主”。后来他方有所悟:“这娘娘呼我作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闲人也。”[10]542所以这一称呼就有神化宋江、预叙宋江作为梁山泊头领命运的作用。在志怪小说叙事中,神鬼突然称呼某人为某个职官名称,常常是作者交代人物未来身份和命运的重要方式。前述汤圣卿故事中汤圣卿被神灵呼作“社邸”(即社神),就是作者对其命运的交代。试以六朝志怪小说为例察看此种叙事在模式上的相似性。
《幽明录》之“阿奴”条:
陈仲举微时,常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妇夜产,仲举不知。夜三更,有叩门者,久许,闻里有人应云:“门里有贵人,不可前,宜从后门往。”……仲举后果大贵。[7]98
《列异传》之“华歆”条:
华歆为诸生时,尝宿人门外。主人妇夜产,有顷,两吏诣门,便辟易,却相谓曰:“公在此。”……歆乃自知当为公。[6]12-13
《搜神后记》之“掘头船”和“阿香”二条:
临淮公荀序,字休玄。母华夫人,怜爱过常……序出塞郭,忽落水……母拊膺远望。少顷,见一掘头船,渔父以楫棹船如飞,载序还之,云:“送府君还。”荀后位至常伯、长沙相,故云府君也。
永和中,义兴人姓周,出都乘马,从两人行。未至村,日暮。道边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门……谓曰:“日已向暮,前村尚远。临贺讵得至?”周便求寄宿……后五年,果作临贺太守。[11]18、34
祖冲之《述异记》之“孔静”条:
宋高祖微时尝游会稽,过孔静宅。正昼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谓之曰:“起!天子在门。”既而失之。[12]
刘敬叔《异苑》一则:
刘曜隐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一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13]
这六则志怪小说中的主人公接触的均是异界鬼神,他们分别被这些鬼神唤作“贵人”“公”“府君”“太守”“皇帝”等,且后世皆被应验,体现了传统的命运前定思想。除第四则“阿香”条主人公无从查证外,其余诸则中主人公的发迹均有史可证,所以这些小说的创作可能是出于某些政治人物自我神化的需要。《三国志·华歆传》裴松之注亦引《列异传》华歆故事,裴氏按语:“《晋阳秋》说魏舒少时寄宿事,亦如之。以为理无二人俱有此事,将由传者不同。今宁信《列异》。”[14]说明晋代也有关于魏舒遇鬼的传说。可见同结构的志怪传说在六朝时期不一而足,极可能是模仿了同一小说作品,逐渐固化成为一种神灵泄露天机、交代人物未来命运的叙事模式而深刻影响了后世小说的创作。
(二)食枣:宋江入幻遇仙的标志
“玄女授书”情节中宋江在饮宴时吃仙枣后将核攥在手中,此情节极似《汉武内传》《汉武故事》之中武帝在王母盛宴上食仙桃而留桃核之事:西王母款宴汉武帝,“因出桃七枚,母自啖二枚,与帝五枚,帝留核著前。王母问曰:‘用此何为?’上曰:‘此桃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15]并且,在我国传统的入幻遇仙模式的叙事中“枣”已经成为仙境中的必备品:《史记·封禅书》载李少君言曰“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16],可见方仙道士均认可“枣”乃神仙之重要食物。中国最早的本草类药籍《神农本草经》“大枣”条亦言:“大枣,九月采,日干。补中益气,久服神仙。”[17]说明枣的“神仙”效用已得到中医药学家的肯定。并且枣在志怪小说中也属仙品,如《汉武内传》描述的天宫“盛斋”中陈列有“玉门之枣”[9]141。再如任昉《述异记》中,王质进入仙境后“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18]。刘守华先生总结凡人偶入仙山故事的特点时指出,“该类型故事绝大部分发生在桃林茂密的山中,且砍柴人常吃仙人递过来的蜜枣,这两种植物都是道教所推崇的。”[19]所以后世诗文中常借桃或枣唱咏神仙之事,如庾信《道士步虚词》曰:“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枣花。”元稹《和乐天赠吴丹》曰:“冥搜方朔桃,结念安期枣。”因此,《水浒传》作者借鉴食枣情节强化了宋江入幻遇仙的经历。
(三)坠河还魂:宋江出离幻境的方式
在《水浒传》“玄女授书”情节中,宋江辞别玄女后随青衣侍婢下殿出门,在一石桥边被推落桥下,大叫一声,头撞在神厨内,觉来乃是南柯一梦。从传统小说的叙事看,不管是入冥类还是入仙类的志怪小说,在描写人脱离异境时往往会采用一种相似的方式,即主人公在惊慌之中主动或被动跌入深渊,在恐惧中梦醒后回归现实。且不管这种方式的形成受到何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它很早就成为众多小说家喜爱的叙事手段,并在不断地重复使用中渐渐模式化、定型化了。如南宋洪迈《夷坚丁志》卷第二十记述乌山媪被冥府误摄,她被遣回阳间时的方式为:
(媪)失脚堕桥下,乃苏。[20]708
明代的其他神怪小说也常借用“坠河”情节来描述人物脱离幻境的情况。譬如《西游记》第十一回写唐太宗完成地府游历还魂阳世的方式即是坠河:
唐王只管贪看,不肯前行,被太尉撮着脚,高呼道:“还不走,等甚!”扑的一声,望那渭河推下马去,却就脱了阴司,径回阳世。[21]
《警世阴阳梦》三十一回中,徐思省游历阎罗地府后被遣返阳世的方式是,他“到水潭边,(李王)推徐思省下去,便醒了,睡在床上”[22]191。《梼杌闲评》中魏忠贤进入“西山幻境”受一僧一道一番点化后脱离幻境:“忠贤吓得往外就跑,不觉失足跌下池去,大叫一声,忽然惊醒,看时,仍旧坐在书房床上,吓出一身冷汗来,战栗不已。”[23]甚至《红楼梦》第五回也采用此模式来写贾宝玉脱离太虚幻境的经过。所以,“坠河还魂”已经成为小说家安排人物脱离幻境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凡人入仙的标志。
(四)惶惑迷离:由幻界入现实的心理转变
“玄女授书”情节中宋江在幻界接受了玄女的天书馈赠返回现实后有一段“幻也真也”“似梦非梦”的恍惚,并将幻境的经历和现实的存在相对应以证其经历之真:“宋江把袖子里摸时,手里枣核三个,袖里帕子包着天书,摸将出来看时,果是三卷天书,又只觉口有酒香。……揭起帐幔看时,九龙椅上坐着一位妙面娘娘,正和方才一般。”[10]542《水浒传》之前的人神遇合型小说中男子走出幻界时,也都有一些阴阳两隔、是也非也的恍惚,并且极力以现实来印证其经历的真实,因此这种描写方式也逐渐定型化。试依次看“萧总”“刘子卿”“青溪庙神”“萧岳”诸小说中对男主人公恍悟心理的描写:
总下山数步,回顾宿处,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环至建业,因话于张景山。景山惊曰:“吾常游巫峡,见神女指上有此玉环,世人相传云:是晋简文帝李后曾梦游巫峡,见神女,神女乞后玉环,觉后乃告帝,帝遣使赐神女。吾亲见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与世人异矣!”[5]2356
庐山有康王庙,去所居二十里余。子卿一日访之,见庙中泥塑二女神,并壁画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5]2357
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庙歇,神坐上见碗,甚疑;而委悉之屏风后,则琉璃匕在焉,箜篌带缚如故。祠庙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细视之,皆夜所见者,于是遂绝。[4]1009
萧岳入延陵庙中,见东壁上书第三座之女,细观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画壁题云:“东海姑之神”。[5]2357
也正是由于“恍悟”情节在人神遇合型小说中的大量运用,使得它成为仙境描写和神化叙事的重要桥段。
总之,“呼职官”“食枣”“坠河还魂”“惶惑迷离”等情节在中国传统人神遇合型志怪小说中的使用源远流长,并在不断地重复和模仿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人物神化功能,也逐渐演化为一类具有神秘感、暗示性和象征性的叙事符号。这些情节单元若被植入到其他故事中便会成为仙境描写的基本材料,也便自然承担起人物神化的功能。它们在文学作品中一出现,读者便能明白其中包含的意义。《水浒传》作者显然对于这些叙事符号了如指掌,灵活而不露痕迹地将这些元素植入到“玄女授书”情节之中,让该情节更富于玄幻色彩,同时也增强了神话人物的效果。
三、“石碣”的“天书”设计
《水浒传》中的“石碣”是“天书”的另外一种形式或者注脚,是宋江和吴用第一次正式对“天书”内容进行的公示,所以天降石碣实际是“玄女授书”情节的一部分。《水浒传》作者在书中也清楚点明了石碣的天书性质:第七十一回的开场诗交代石碣所刻是“堂堂一卷天文字”,还在行文中以“诗证”称石碣为“蕊笈琼书”,来喻指其天书性质。《水浒传》四十二回中九天玄女告诫宋江,天书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后来“宋江日日与吴用研究天书”。说明宋江所得天书中有天罡地煞的记载,其中“天机星”正是吴用。因此石碣所刻乃天罡地煞之星与一百零八将之对应,这与宋江所持之天书在内容上是一致的。
《水浒传》作者还将石碣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使之符合传统“天书”的一般形式,这种设计思想正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天书”样貌的认识:
方才取过石碣看时,上面乃是龙章凤篆蝌蚪之书,人皆不识。众道士内有一人,姓何,法讳玄通,对宋江说道:“小道家间祖上留下一册文书,专能辨验天书。那上面自古都是蝌蚪文字,以此贫道善能辨认。”[10]895
为何石碣上的文字人皆不识,为何不直接呈现天书内容?因为只有这种设计方式才符合古人对“天书”形式的一般认识。在传统小说中“天书”多指非现实世界中的机密性簿册,是常人不知的天机所在,因此在形式上有难辨识、难理解、意义模糊等特点。《水浒传》之前很多小说中的“天书”文字都难以辨识:唐代小说《宣室志》之“郄惠连”条曰,郄惠连进入冥界见到了“阎波罗王之册”,其上皆“用紫金填字,似篆籀书,盘屈若龙凤之势”[5]3003,非世人所能识。宋洪迈《夷坚志》甲志卷十四“妙靖鍊师”条还对“天书”形式之一——命运簿册的模糊性进行过说明:“即仙官持簿来,五百年过去未来皆知。恐泄天机,姑以风花雪月为咏,而吉凶寓其中。”[20]123有明一代,很多小说继承了这种“天书”文字的设计方式,即多设计成战国籀文。如《西湖二集》卷十六韦固所见月老之“婚姻簿籍”,“都是篆籀之文,一字也识不出”[24];《警世阴阳梦》“阴梦”第九回写长安道人游天堂所遇之“天书”,上面“都是蝌蚪文书,是凡人不识的”[22]191;再如冯梦龙改编本《平妖传》第十一回中,蛋子和尚所见天书,也是“多是雷文云篆,半点不识”[25]。可见,难辨、难解便成为天书在形式上的一大特点。虽然这是一种文学作品的艺术设计,故意突出异界不同于人世的奇幻特征,但此类叙事传统对“天书”的形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规范,当这种范式出现时即暗示其具有非凡的“天书”性质。所以说《水浒传》中的石碣也是作者根据传统小说的叙事特点而精心设计的。
四、“玄女授书”情节人物神化效果的实现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玄女授书”情节有着明显的人物神化功能,而《水浒传》正是借助于该情节的构建顺利完成了两次主要人物神化任务,推进了小说情节的发展。第一次是四十二回宋江在还道村九天玄女庙中接遇了庙神九天玄女并受赐三卷“天书”,以此“神化”了宋江;第二次是七十一回天降石碣,其上刻有梁山众好汉与天罡地煞诸星对应关系,以此将一百零八将神格化,让人安归其位,心悦诚服。该情节之所以能顺利实现人物的神化,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实现人物神化得益于传统神异叙事固有的人物神化功能。“神女授书”情节其实导源于“天神授术”型的宗教神化或政治神化的叙事模式。在中国的原始宗教及道教发展过程中,宗教首领多以编造入幻遇仙故事以自我神化。葛洪《神仙传》便记载了道教张道陵接遇天神受赐天书的故事:“忽有天人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5]56葛洪同时指出“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将为此文从天上下也”,揭穿了张道陵自我神化的目的。北魏道士寇谦之也是道教领袖之一,他在后秦弘始十七年也曾假称太上老君曾授其“天师”称号并赐天书令其“清整道教”[26],显然也是自我神化的故事编造。社会上的方士、巫觋也会编造自己遇神仙获赐灵宝的故事以自神其术,骗取民众信任以贩售其“法术”,“借着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27]。譬如,王充《论衡·道虚篇》所载,方士曼都自称曾入仙界,饮仙人所赐流霞后回归人世,于是世人始称其为仙人[28];《搜神记》“贺瑀”条,贺瑀死后三日复苏,自述得剑于上天之神,从而自我包装成世人心中的“社公”[29]182-183;同书“戴洋”条,术士戴洋死而复生后自述进入天界,“天使其酒藏吏,授符箓”,游历蓬莱、昆仑后被遣归,他从此“妙解占候”[29]182。诸如此类,皆为利益驱动下的自我神话故事。《水浒传》“玄女授书”的记述也俨然是一次方士自我神化的过程,很有道教意味。宋江在接遇玄女获赠天书后似乎也成了神仙方士,第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五、八十六等回目中梁山遭遇战役、困难时,宋江便取玄女天书焚香占卜。第五十二回梁山泊人马与高廉斗法,宋江“打开天书看时第三卷上有回风返火破阵之法,宋江用心记了咒语并秘诀”[10]675,这揭示了天书的方术意义。所以对宗教类神化叙事方式的借鉴,使得“玄女授书”情节成功发挥了神化宋江及梁山众将的目的。
“天降石碣”的设计思想来源于“瑞应”传统,《西京杂记》记录陆贾言曰:“瑞者,宝也,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30]在史书“符瑞志”中,瑞应皆伴随某项政治变革而出现,也逐渐固化为政治人物自我神化的重要手段。如《三国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即揭露过这种“石碣”神话的欺骗本质:
历阳县有石山临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骈罗,穿中色黄赤,不与本体相似,俗相传谓之石印。又云,石印封发,天下当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时历阳长表上言石印发,皓遣使以太牢祭历山。巫言,石印三郎说“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诈以朱书石作二十字,还以启皓。皓大喜曰:“吴当为九州作都、渚乎!从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复谁?”重遣使,以印绶拜三郎为王,又刻石立铭,褒赞灵德,以答休祥。[11]1171-1172
所谓“历阳山石文理成字”等祥瑞,皆是巫祝配合帝王实现其政治目的的表演而已。所以《水浒传》“天降石碣”式的自我神化乃是对历史上政治神化型叙事的借鉴。
其次,实现人物神化是小说叙事的需要。小说的“外部层次又称第一层次,指包含整个作品的故事;内部层次又称第二层次,指故事中的故事,它包括由故事中的人物讲述的故事、回忆、梦等。相应的,我们将外部层次的叙述者称为外叙述者,内部层次的叙述者称为内叙述者”[31]。从叙述层次的角度看,《水浒传》的外部叙事和内部叙事都有神化宋江、神化梁山众将的需要。从外部层次即《水浒传》的作者角度看,“神化宋江,为其入主梁山奠定心理、舆论基础”,“将妖魔升华为天神,赋梁山造反以正义性”[32]。所以神化宋江为后续情节的展开做了铺垫,具有结构全书的重要意义。“天书”所蕴之天机是不可轻易泄露的,但小说作者利用传统神异叙事在合适的时机泄露天机,让读者快速领会到作者人物神化的目的,既适时推进了情节发展又不让读者感到过分的跳跃和突兀。
从内部叙述层次看,宋江和吴用也有神化自己以及梁山弟兄的实际需要。从这个角度看,“玄女授书”和“天降石碣”的设计者实为宋江和吴用,他们不失时机地对两大故事进行积极宣传,为宋江登上寨主之位及其改革的推行制造舆论。宋江自身怀有极强的领袖欲望,这在其所题反诗“敢笑黄巢不丈夫”已经显露,所以“玄女授书”极可能是其为达到自我神化之目的而精心编造的故事,并且努力传播以博取梁山弟兄的信赖。所以金圣叹认为“天书非玄女所授”,玄女授书“悉是宋江权术”[3]780。这种认识正是基于内部叙述层次上的合理解读。同时,负载天书文字的石碣恰逢在宋江新晋为梁山头领、意欲改革之际出现,这场戏自然是宋江宣示其政策如排座次等上应天道的手段,所以宋江把梁山众将领的名字故意设置成为“龙章凤篆蝌蚪”之文,目的就是炫惑众人相信石碣文字乃出天意。故《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之七十一回末总评曰:“吴用石碣天文之计,真是神出鬼没,不由他众人不同心一意也。”[3]1273这些以《水浒传》人物的心理为出发点进行的评论,都指出了内部层次叙事层面人物自我神化的需要。
小 结
总之,《水浒传》构建的“玄女授书”情节有神化梁山人物、结构全篇、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同时小说中的宋江、吴用等人也有自我神化实现个人目的的野心。在这种目的驱动下,“玄女授书”情节在结构上借用了具有宗教色彩和政治色彩的人神接遇叙事模式,同时借鉴了其他人神遇合型故事叙写细腻生动的特点。在细节的设置方面,作者灵活植入了大量神话人物常用的元素,对仙境、幻境进行了精心的布置,让“玄女授书”的情节更加丰富合理。但是在总体效果上,“玄女授书”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及其自身的文学性、审美性功能要更胜一筹。譬如作者借助前代众多神异叙事因素描绘的九天玄女居所就是一个独特的环境创造,对《红楼梦》太虚幻境的设置有较为直接的影响。所以在继承基础上进行的伟大创新是成就《水浒传》文学地位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