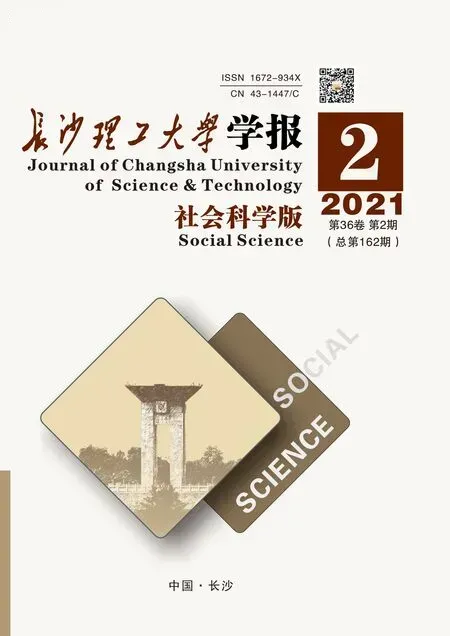技术史视域下人的“赛博格化”研究
姚 禹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科学史系,北京 100084)
赛博格并非是一种新奇的理念。事实上,关于人与机器结合或者人类用机器来改造身体这种技术幻想,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早在1843年,爱伦·坡在短篇小说《被用光的人》(TheManThatWasUsedUp)中就描绘了一个装配着机械假肢的男人。而法国作家拉耶(Jean de La Hire)在1911年的科幻小说《火星上的夜盲者》(TheNyctalopeonMars)中塑造了第一个赛博格英雄的形象。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创造的技术文明已经足够强大,使得人类第一次有能力将赛博格从幻想转换为现实。正因如此,赛博格问题也就在技术史与技术哲学视域下被重新审视。
一、从赛博格的身份到赛博格的身体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赛博格概念最早由美国NASA的航空工程师曼弗雷德·克林斯(Manfred Clynes)和医学博士内森·克莱恩(Nathan Kline)于1960年提出,这两位科学家从“cybernetic organism”(控制论的有机体)两个单词中各取前三个字母构造了一个新词“Cyborg”(赛博格)。赛博格的提出背景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愈演愈烈的“太空竞赛”(The Space Race),当时NASA向美国的科研人员征求能够让宇航员实现远距离太空航行的方案,克林斯和克莱恩提出了一种结合了工程学与医药学的大胆设想。他们认为,要想让人类在严酷的外太空环境下生存,必须借助技术设备和生物学改造。他们在文章中写道:“如果人类在太空中(活动),除了驾驶其载具外,还必须仅为保证自身的存活而不断地检查设备并随时做出调整,那么他就成了机器的奴隶。而赛博格的目的是使人类拥有一种组织化的稳态系统(homeostatic systems)。在这种系统中,各种问题能以类似机器人的方式被自动和无意识地处理,从而使人类自由地探索、创造、思考和感觉。”[1]囿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对于NASA来说,赛博格还仅仅是一种带有科幻色彩的技术构想。但无论技术能否实现,赛博格概念中蕴含的一个基本逻辑已经非常明确,即自然人类为了适应非自然的生存环境,唯一的实现方式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对原初身体进行改造。
当今人文领域关注更多的是文化批评意义上的赛博格。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是研究赛博格问题无法回避的人物,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跨学科学者,同时是影响力巨大的左翼思想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哈拉维在1985年发表的论文《赛博格宣言》堪称是赛博格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哈拉维把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控制论的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生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生物。”[2](P5)在哈拉维的研究中,她认为赛博格的重要意义是突破了人类文化中三个古老的界限,即人与动物的界限、人与机器的界限以及自然与非自然的界限[2](P10-12)。她认为,赛博格将会成为生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人的一种无可避免的生存样态,这种赛博格化的人模糊了种族、性别、阶级这些传统社会中建构个人身份的边界,从而形成了一种多元的、混沌的新主体。“在20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全都是奇美拉,是理论化的和拼凑而成的机器和有机体的混血儿;简而言之,我们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2](P7)基于这种新主体的立场,所有传统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和社会伦理都需要被重新建构,因此在《赛博格宣言》中,她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我宁愿成为赛博格而不是女神。”[2](P68)
显而易见,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并非指某种具体的技术,而是借助这种技术幻想来完成一种后现代的政治身份建构。哈拉维明确写道:“《赛博格宣言》我是为《社会主义评论》撰写的一篇近乎唯美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声明。通过它我试图思考如何进行批评、铭记战争及其后续,使生态女性主义和技科学(techno-science)在同一具肉身中融合,并向逃避不良起源的可能性致敬。”[3]而她的追随者、后人类理论家凯瑟琳·海勒(Kartherine Hayles)也认为,赛博格的出现可以打破传统社会中基于生理差别的性别意识,从而建构一种超越性别的新型政治主体。她指出,“事实上,一旦男性和女性被连接到同一个控制电路之中,起源的问题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两者变成了相互构成的关系。在朝向这一认识的过程中,文本得以超越性别政治的前提,尝试性走向一种赛博格主体性。”[4]
然而,哈拉维的批判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哈拉维虽然在表面上批判了笛卡尔式二元论立场,但是她实际上仍然把人本身视为一种现成的抽象之物,这就依旧没有彻底脱离笛卡尔式的哲学人类学的窠臼。因为人并非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诸如种族、性别等政治身份,都需要建立在具体的身体之上。赛博格并非是某种现成之物,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具体的技术实践过程。事实上,只有首先实现了赛博格的身体,赛博格的身份才是可能的。哈拉维重视作为身份的赛博格,但是却忽略了作为身体的赛博格。正如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说,“技术史就是人类史”[6](P158),脱离了技术史的视域,赛博格概念最终只能沦为一种时髦但空洞的后现代身份的政治幻想。
二、义肢理论:人与技术的共同进化
斯蒂格勒将卢梭视为传统哲学人类学的代表人物,认为“卢梭处于哲学人类学问题和科学人类学问题的连接点”[6](P113)。斯蒂格勒引述尼采的批判,“所有哲学家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缺陷:以为能从现代人出发,通过对现代人的分析达到目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幻想‘人’是一种永恒的事实,一种在漩涡激流中保持不变的存在。一种衡量万物的可靠的尺度。哲学家关于人的一切言论,其实都只是关于一个非常有限的时段中的人的鉴定。缺乏历史意识乃是所有哲学家的遗传缺陷;有些哲学家甚至将在某些宗教、某些政治事件作用下产生的最新的人的形象也视作定式,认为必须以这种定式为出发点。”[7]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斯蒂格勒认为卢梭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一书中描绘的“集一切于一身”的“高贵的野蛮人”,只不过是一个作为“文明人”镜像的虚构形象。卢梭将他设想的人的原始状态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认为“人类的一切进步都在不断使人离开他的原始状态”[8]。卢梭将这一过程视为人类的沉沦,而斯蒂格勒则将这一过程视为人类的创造与进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折射出的是两位哲学家对人与技术关系完全不同的理解。
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的诞生和人类的起源是一体两面的现象,我们只有同时展开两个维度的视域,才能把握到人类与技术的真正关系。斯蒂格勒认为人类拥有两个起源,所谓“第一起源”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起源,即人类作为一个灵长类物种通过漫长的进化,在与自然环境的残酷博弈中逐渐演化出身体各个器官的确定形态。这种进化的终点就是卢梭设想出的可以不使用任何工具而在自然中存活的原始人,这个生物学进化过程也被称为种系生成过程。与此同时,人类还拥有生物机能之外的“第二起源”,斯蒂格勒指出,“由东非人向新人的过渡,即人化的过程。这个大脑皮层的分裂和石器随着石制工具的技术的漫长进化和演变的过程是一致的。”[6](P157)人类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者,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技术演变的进程中被逐渐发明出来的。技术现象就是人类历史的第二起源,这种人与技术共同演化的过程被称为后种系生成。在同时拥有了两个起源之后,人类才开始了作为人类自身(而非仅仅是一种动物)的进化之旅。生物学进化是一个外在影响内在的过程,通过自然选择确定适应生存的生物性状,然后沉淀到基因之中形成稳定的遗传。而人类由第二起源展开的进化则是内在影响外在的过程,是一种“通过技术实施的器官外在化的独特人类现象”[9]。
基于此,斯蒂格勒重新阐释了《普罗塔戈拉篇》中的人类起源神话,将技术的诞生和人类的起源紧密地耦合在一起,认为技术源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在柏拉图记载的神话中,爱比米修斯的任务是给万物分配属性,使万物可以依照自己的属性生存,但是这位神祇却忘记了给人类分配一个属性,“至于人赤身裸体,一无所有,所以人缺乏存在,或者说,尚未开始存在”[6](P135)。普罗米修斯为了弥补兄弟的过失,从工匠之神那里为人类盗取了技艺。从此,人类就可以通过技艺来制造各种各样的义肢(prothèse)①以弥补先天的缺陷。“与动物获得的各种属性相对应,人的那一份就是技术,技术就是义肢性的,也就是说,人的技术属性完全是人为的……人没有属性,所以也就没有宿命。人必须不断地发明、实现和创造自己的属性。”[6](P277)斯蒂格勒把这种人类的先天缺陷以及对于技术的绝对依赖称为人类的“义肢性”(prosthetics)。在技术史的视域下,并不存在一种人的先天本质,人的本质是在人与技术的相互塑造过程中实现的。“技术发明人,人也发明技术,二者互为主体和客体。技术既是发明者,也是被发明者。”[6](P162)
在义肢还不够强大的阶段,人的两个起源之间会呈现出一种含混而微妙的平衡,使得这种共同进化的过程并不具有一种明确的趋势(这就是为何我们能在前现代社会中发现如此丰富的技术多样性的原因)。然而,当人类技术进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类肉体进化的速度之时,人与技术之间的脆弱平衡就被打破了。斯蒂格勒基于勒鲁瓦-古兰(Leroi-Gourhan)的研究,把记忆划分为遗传记忆、后生成记忆以及后种系生成记忆,通过三种记忆划分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失衡过程的必然性。遗传记忆保存着进化而来的人作为一个独立物种的先天生物学性状,后生成记忆则保存着每一个生命个体在后天生存过程中积累的一切知识和体验。然而,一般生物的后生成记忆总会因为生命个体的死亡而消失,但是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能够保存个体的后生成记忆,从而使人类族群产生了所谓的后种系生成记忆。人类个体的生命总会终结,而技术却可以不断传承和发展。在当前的时间尺度内,人类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已经停止了演变,生活在后工业化时代中的现代人的遗传基因与我们三万年前身为采集者和猎人祖先其实没有任何区别[10]。换言之,我们的遗传记忆已经完结了,而后种系生成记忆仍然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着。在不断进化且永恒存续的义肢面前,作为终有一死的我们终究无法和技术建立一种平衡的关系,这就是技术史的宿命。
三、人的赛博格化进程:技术系统与器官投影
经过斯蒂格勒的阐释,我们认识到人并非是先天的抽象之物,而是始终与技术协同进化,生存在特定的技术环境之中。斯蒂格勒继承了法国技术史家伯兰特·吉尔(Bertrand Gill)的技术观,认为“技术”并非是一个个孤立的技术人工物,而是始终作为技术系统(système technique)中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一个技术系统构成一个时间统一体。它意味着,技术进化围绕着一个由某种特定技术的具体化而产生的平衡点,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6](P33)作为一名技术史家,吉尔以技术系统作为自己编史学的核心概念,将技术发展史分为希腊技术系统、中世纪技术系统、现代技术系统(主要指工业革命)、当代技术系统等几个部分。与此同时,每个技术系统之间并非是平滑的过渡,而是类似于范式转换般的断裂性更新,“技术的发展表现为破坏原有的系统,在一个新的平衡点上重建一个新的技术系统。新技术系统产生于旧技术系统的极限,这种进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不连续的”[6](P36)。
技术系统与同时代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深度交织渗透,吉尔强调,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总是存在着趋于稳定的倾向。从技术史上看,某些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可能会在短期内对现有的社会系统造成巨大的冲击,但是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社会系统必然会朝向技术系统发展和进行调整,形成新的制度和文化。“由于技术进步总是以不确定的或者看似不确定的方式发展而来的,新的技术系统与其他系统的调整总是以一种暂时性的模式进行,通过一些自由作用力的互动,并伴随着所有必要的错误和逆转,直到出现令人满意的平衡……那么,这个进程必须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直到在经济(这是最经常提到的)、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实现所有必要的兼容性。”[11](P66)
碍于自身时代的限制,②在1978年出版的《技术史》一书中,吉尔在论述所谓“当代技术系统”时,所列举的代表前沿水平的是大型计算机、航空航天技术和工业自动化等。吉尔在书中坦言道,“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物质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但是由于这些技术革命尚未完成,因此我们尚无法对这些影响做出明确的说明。”[11](P875)不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这些当时的“前沿技术”在今天早已深刻内嵌到我们这些“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并成为我们生存方式的一部分。在当下这个时代,吉尔所观察到的那场自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技术革命仍然在迅猛地推进着,以互联网和数码产品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造着我们的社会系统,正在形成一种与工业革命时代迥然不同的全新的技术系统。而当下这个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时代,被斯蒂格勒称为超级工业时代(hyper-industrial age)[12](P25)。
评注:不等式在区间上的恒成立问题常常转化为f(x)≤g(x)⇔f(x)max≤g(x)min;f(x)≥g(x)⇔f(x)min≥g(x)max即求函数在区间上的最值问题。应用该方法思路简单,过程简洁,值得学习。
随着技术以几何级的速度积累,人的两个起源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且无可挽回的失衡状态。在这个超级工业时代,不只是人类所栖居的生存环境已经被彻底地技术化,更进一步的是,与技术系统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对自然人类的身体机能与认知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斯蒂格勒所说,“人类越是强大,世界就越是趋向‘非人化’发展。”[6](P97)现代人不得不承认,哪怕人类可以进一步地调整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形态,但我们继承自第一起源的生物学身体已经逐渐无法和技术系统相适应了。按照技术史的宿命论,这种失衡与错位是根本无解的。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勒瓦鲁-古兰就已经从技术人类学的角度颇具预见性地表达了当外化的技术发展到某种极限之后,必然会试图改造人类自身的隐微忧虑,“值得担心的是——即使只是稍微有点——在一千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耗尽了自我外化的可能性,将会感到被旧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老的骨骼肌肉装置所束缚”[9](P249)。这便导致了一种在人类技术文明中前所未有的情况:为了与技术系统建立新的平衡,人类不仅仅要调整原本的社会系统,更是要从根本上对人类的身体进行技术化的改造,即实现人的赛博格化(Cyborgization)。
化用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名言,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技术史的技术哲学是空洞的,没有技术哲学的技术史是盲目的。作为技术史家,吉尔只是相对客观地描述了不同时代技术系统之间的更替变化过程,但是他并有对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作出更进一步的解释。而与之相对的,技术哲学家们追问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技术为何会以如此的方式实现自身?这种追问在技术哲学的开端便开始了,“技术哲学”这个术语的创造者、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第一次回应了这个追问。卡普提出了著名的“器官投影”(organ projection)理论,强调技术与人体器官之间的相关性,把技术视为人体的延伸。技术哲学学界大多把卡普的理论视为一种技术哲学的朴素先驱,把器官投影简单地理解为在人体器官与技术人工物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线性联系。比如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史家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em)便持这种观点,在解释器官投影理论时,他有限地引用了卡普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关于工具与器官之间关系的论述:“关于工具与器官之间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本质的关系,以及一种将要被揭示和强调的关系是——与其将其说成是一种有意识的发明,不如说成是一种无意识的发现——人类正是在工具中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由于作用和力量日渐增长的器官是控制性的因素,所以一种工具的合适形态只能起源于那个器官。”[13]
但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注意到了器官投影理论的丰富意涵,特别是其中涉及到人对自身的理解的部分。卡西尔认为,虽然器官投影理论的表面意思是在人体结构与技术人工物之间建立联系,“但这还没有穷尽器官投影理论最核心和最深远的意义,只有我们考虑到精神过程与人对自己的身体结构的知识的增长是平行发展的,考虑到人只有通过这种知识到达自身、他的自我意识,这种意义的事实才会变得明显。人们发现的每一种新工具都标志着迈出了新的一步,不仅朝着外部世界的形成,而且朝着他的自我意识的形成。”[14]
事实上,卡普在使用“器官”(organ)这一术语时并非单纯地指人体器官,而是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一书中的器官(organon)概念,带有鲜明的认识论意味。所谓的“投射”并非是一种对现成人体器官的线性模仿,而是关于包含人类对于自身的理解在内的、始终处在动态和生成的“图像”(bild)的反映。对于卡普来说,技术并非是投影的结果,而是投影的过程本身。回到卡普那个著名的“手臂与手斧”的例子,手斧是手臂的投影,并非是指手斧是以手臂为原型制造的,而是指人通过技术的方式实现了被建构在图像之中的手臂与手斧之间的意义关联。卡普如此解释道:“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所说的‘图像’并不是我们已经在以上几点提及的寓言式的。也就是说,‘图像’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人随意进行各式各样比较的纯粹的比喻,相反,它是独一无二的‘具体图像’(sachbild)和投影的反映。”[15](P101)
那么,如何理解卡普所谓的图像呢?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如此地解释德文中“图像”(bild)一词,“‘图像’在这里并不是指某个摹本,而是指我们在‘我们对某物了如指掌’这个习语中可以听出来的东西。这个习语要说的是:事情本身就像它为我们所了解的情形那样站立在我们面前。‘去了解某物’意味着:把存在者本身如其所处情形那样摆在自身面前,并且持久地在自身面前具有如此这般被摆置的存在者。”[16](P77-78)如果说技术是“图像”的投影,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在工程传统的视域下来理解卡普的技术哲学。卡普所论述的技术并非是一种现成之物,而是与人对世界的领会息息相关的。“技术是展开世界的方式,是世界展开的具体化。”[17]美国学者基克伍德(Jeffrey Kirkwood)和韦瑟比(Leif Weatherby)也指出,“卡普描述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没有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技术’一词的现代含义。卡普所谓的技术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两者共同出现的前提。”[15](PXVI)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所谓器官投影的本质是通过技术的手段将一种世界图像(weltbild)具体化。
世界图像源自人作为主体对自然的摆置(vorstellen),而当世界图像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摆置将反作用于人本身。在科学革命之前,人的形象是镶嵌在世界图像之中的,是整个有限封闭且秩序井然的世界(cosmos)的重要一环,“对于中世纪来说,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宇宙的中心。整个自然界被认为在目的论上从属于人及其永恒命运”[18]。而当世界图像转变为均一而无限的宇宙(universe)之后,人类也在世界图像中失去了位置,人的形象失去了神圣性,甚至变得无关紧要了。在卡普提出器官投影理论的19世纪末,虽然普遍盛行一种机械化的世界图像,但是哪怕是拉·梅特里式的最激进的唯物主义立场,也只是认为人类的身体是一台精密的机械,并没有明确地诘难人类身体结构的不合理和身体功能的不健全。而在超级工业时代的技术系统中,在一种数字化的世界图像之下,人类的身体因为其无法彻底的可计算与可控制,反而变成了人类自身发展的阻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激进的后人类主义者凯瑟琳·海勒和未来学家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设想赛博格时,会把人的赛博格化的终点设定为意识上传。因为在这种数字化的世界图像之下,人的身体形象甚至是人的身体本身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赛博格技术的独特性在于,这项新兴的技术将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直接干预人类的生物学身体,让人类的“第二起源”彻底遮蔽了“第一起源”,使得拉马克式获得性遗传(即作为后种系生成记忆的技术)成为了人类唯一的遗传方式。赛博格技术使得“义肢”从一种哲学隐喻最终转变为一种工程学实践。人的赛博格化逆转了卡普的器官投影理论,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将器官投影理论的逻辑推演到了极致:人类不再是以图像为原型改造世界,通过“投射”构建与之相称的技术系统,而是图像反向“投射”到人类自身,过于强大的技术系统倒逼人类通过技术改造我们原初的生物学肉体。
德裔犹太哲学家京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在他著名的技术批判著作《过时的人》中提出了“普罗米修斯的羞愧”概念,意指当作为技术发明者的人类,在面对近乎完美且功能强大的工业造物时,反而会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卑微渺小与无所适从。“令T先生感到羞愧的是:他是生物进化而来的,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与完美的、设计到最后一个细节的机器设备相比,人的存在则完全依赖于盲目的、不可预知的、最原始的繁衍方式和分娩方式。T先生的耻辱原因在于他是一种‘自然出生本质’(natumesse)。”[19]赛博格技术,就是生活在超级工业技术系统中的人类对于“普罗米修斯的羞愧”的回应。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到“普罗米修斯的羞愧”,在技术史视域下,两者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前后呼应。
四、成为赛博格是我们的命运
克林斯与克莱恩设想用赛博格技术改造人类身体的原初目的,就如同让鱼获得在陆地上行走的能力一样,让人类可以在一种完全非自然的环境下生存。而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不断通过技术将机械化的世界图像乃至如今的数字化的世界图景转换为现实,我们所栖居的世界早已与作为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类的原初生存环境相去甚远。整个世界已然是技术化的和人工化的,在当前的技术系统中,整个世界必然变得更加技术化和人工化。作为一个生活在超级工业技术系统中的现代人,一旦脱离了技术义肢,我们就和在陆地上行走的鱼没有任何区别。
斯蒂格勒指出,“义肢不是人体的一个简单延伸,它构成‘人类’的身体,它不是人的一种‘手段’或‘方法’,而是人的目的。在此不要忘记,人的目的的另一个含义,即‘人的终结’。”[6](P78)正如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视为形而上学的终结,在相同的意义上,人的赛博格化也可以被视为义肢的终结。这并非意味着赛博格作为一种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尽善尽美、至臻完满的最高境界,恰恰相反,“终结作为完成乃是聚集到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20]。作为义肢的终结,所呈现出的实际上是现代技术在最极端的可能性中无止境的自我增殖。赛博格在抹平自然人类在技术系统面前所有缺陷的同时,也遮蔽了人类进化的一切其他可能性,使得现代技术的本质最终彻底替换掉了人的本质。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作为一种命运性存在的历史现象,“现代技术之本质居于集-置之中。集-置归属于解蔽之命运(geschick)”[21]。斯蒂格勒继承了海德格尔观点,进一步地认为,经过资本力量几十年间的疯狂推动,集置已经从一个形而上学概念被现代技术具体化为了一个以可计算性(calculable)和可编程性(computable)为核心特质的超级工业技术系统[12](P25)。而对这个被超级控制技术和算法治理术控制的时代,斯蒂格勒称之为“人类世”(anthropocene)[12](P16)。面对前所未有的超级工业技术系统,我们将迎来“自然人类精神表达系统的崩溃”[22](P76)。生活在人类世中自然人类已经成为了一种“过时的人”,人类世的最终结局注定是一个“没有人的世界”。
“因为‘人类世’意味着技术工业造成的自然人类文明断裂以及一个新的世界——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的形成,意味着自然人类向技术人类的转换。”[22](P102)在这种意义上,赛博格不只是一种技术,赛博格更是未来人类的一种可能的存在方式。如同现代技术是这个时代的命运一样,在技术史视域下,成为赛博格是我们的命运。从自然人类转换为技术人类,不论未来迎接我们的是乌托邦还是敌托邦,我们唯一能做的或许只有保持一种泰然让之(gelassenheit)的态度,以迎接命运的来临。
[注释]
①prothèse一词在法文中的原意是指医疗中用于人体修复的各种假体(如假肢、假眼、假牙等),汉语学界的斯蒂格勒研究者最初多把这个词翻译为“代具”,但这几年来已经逐渐翻译为更加贴合原义的“义肢”。因此,在本文所引用的中文版《技术与时间》中,笔者都把“代具”一词替换为了“义肢”。
②吉尔1929年生于法国巴黎,1980去世,享年60岁。《技术史》一书原名为《技术通史》(HistoiregénéraledesTechniques),上下两卷分别出版于1962年与1965年。而后全书于1978年经修订后重新编辑出版,改用了《技术史》(HistoiredesTechniques)这个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