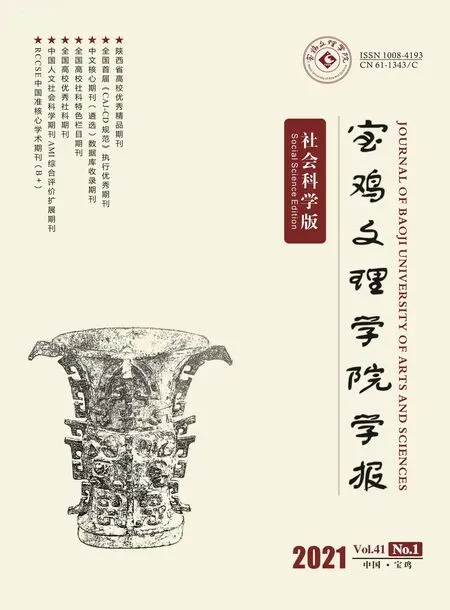从印绶鸟看王世充的政治伦理*
张同胜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旧唐书·列传第四》记载,隋末唐初,王世充僭称皇帝之前,广造社会舆论,采纳道士桓法嗣的“王继羊(杨)后”之图谶,“罗取杂鸟,书帛系其颈,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有弹射得鸟来而献者,亦拜官爵。”[1](P2231)或以为王世充此举是好德放生,或以为王世充自信神权天授而广而告之,或以为王世充神神鬼鬼、荒诞不经。其实,这是琐罗亚斯德教印绶鸟信仰在中原的本土化表现。当然,印绶鸟与此处的“书帛系其颈”之杂鸟存在着差异,即前者没有文字书其上。可是,文化符号的跨民族旅行,它总是发生在地化的。西域文化环境中自有物的言说;汉文化又有天书降谕的传统:变异的、变形的、被尘封的图像符号在异文化生态中于是就往往被视若无睹。前贤时俊既然对此尚未予以关注,本文试发覆之,并进而论及王世充的宗教伦理和政治生命,解释历史书写内在的因果逻辑。
一、印绶鸟的宗教内蕴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是西域古老的宗教,而印绶鸟(又名戴胜立鸟、衔绶鸟、系带鸟、含绶鸟、戴绶鸟、戴胜衔绶带鸾鸟、立鸟、衔物立鸟、鹘衔瑞草、雁衔绶带等)是琐罗亚斯德教中的吉祥鸟。据波斯式吉祥鸟图像,吉祥鸟的特征是“有头光、戴胜”。有头光,是因为琐罗亚斯德教崇尚光明,因此宗教叙事中重要的神祇或帝王大多拥有头光。这里的“戴胜”,是姜伯勤在其《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中的命名。其实,戴胜是两条印绶带子。姜伯勤将颈后飘着两条带子的鸟命名为吉祥鸟。印绶鸟颈系波斯式绶带,“表达的是伊朗‘好运’概念hvarenah”[2]。
(一)印绶鸟的吉祥物
吉祥鸟的伴随物式样颇多,或者是颈绕印绶,或者是戴环,或者是衔铃或衔环。依据“在安息艺术中,戴环鸟(ring-bearing bird)是表达一种hvarenah式的繁盛或好运的概念”,我们也可以将它命名为戴环鸟。环或者圆圈,在琐罗亚斯德教中表征着承诺,如琐罗亚斯德教典型的标志法拉瓦哈(Faravahar),其中的象征形式的阿胡拉·马兹达手中拿着一个圆环;再如太阳神密特拉给大流士一世授环的塑像等。
早在帕提亚时代,波斯就出现了衔环鸟的艺术形象。一件公元前2世纪的帕提亚石刻雕塑在伊朗西南的阿拉美德Elymaide的Khung-i Nauruzi出土,上面有一只鸟,它口衔圆环,飞向右侧的人像。飞鸟象征着“神的荣光”[3](P174)。康马泰说:“在帕提亚波斯时期,人们就用含绶鸟来表现神赐福于英雄,那么不难想象,在此后的萨珊波斯时期‘森木鹿’用含绶鸟来表现。”[3](P174)阿扎佩认为,“6至8世纪,布哈拉的瓦尔赫萨以及片治肯特的粟特壁画中,也常见口衔圆环的飞鸟盘旋于武士装扮的国王头顶,或参与到宗教祭祀的场景中。”[4](P174-175)衔环鸟应该是表达吉祥的一种隐喻。
衔铃鸟是印绶鸟的一种表现形式,还是说它们具有相同的表征意义,即都是吉祥、好运的符号展现?在粟特人及其后裔的墓葬图像中,我们所多见的是脖子上系着两根带子的印绶鸟。这两根带子是不是源自琐罗亚斯德教典型符号即有翼日盘中的两根带子?姜伯勤将其命名为吉祥鸟,安息艺术的研究者又将印绶鸟称之为瑞鸟。印绶鸟、戴环鸟、衔铃鸟都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瑞鸟或吉祥鸟的不同表现形式。
夏名采曾将青州北齐傅家画像石中的印绶鸟编号列出。在九块画像石中,出现有印绶鸟的共有五块,分别是商旅驼运图上空有两只颈后有二绶带的瑞鸟,商谈图中上空有一只颈后有二绶带的瑞鸟,车御图上空有一只颈后有二绶带的瑞鸟,出行图之一上空存有一只瑞鸟,出行图之二上空有一只颈后有二绶带的瑞鸟。[5]夏鼐在《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中说:“我们这次在阿斯塔那的发掘中……在332号墓(公元665年)叶楚有颈绕绶带的立鸟文锦。……颈有绶带的立鸟纹,也和我国旧有的鸾鸟或朱鸟纹不同。它的颈后有二绶带向后飘飞。”[6]在太原隋代虞弘墓椁壁浮雕上,天空中飞的就有印绶鸟,两条印绶飘在颈后。
(二)作为好运的印绶鸟
印绶鸟应该是senmurv(音译作森木鹿或森穆夫)母题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Senmurv具有典型的琐罗亚斯德教宗教意味,是一种有翅膀的鸟、兽或者几种动物的组合,表征着hvarenah即“照耀人的神之光辉”[7](P112)。在法尔西语中,Senmurv被翻译为Simurgh (又写作simorgh, simurg, simoorg or simourv, Angha)。魏庆征认为,它是“古伊朗神话中预言未来之鸟”[8](P458)。杨瑾考察的结论是:“在现代波斯语中,森穆夫特指一种法力无边、能预测未来、乐善好施的神秘飞鸟类生灵,其图像见于伊朗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以及中世纪阿塞拜疆、拜占庭帝国和受波斯文化影响地区的历史遗存中。”[2]
H.W.Bailey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认为,hvarenah(音译为赫瓦雷纳)意谓“生命中的吉祥”,转义为幸运,使好运实现的幸运事业,与光明的性质相联系的好运,最后是关于“王家无上荣光”的思想。[9](P69)Bailey指出,Hvarenah又写作Xvarenah,此字相当于中古波斯语中的farn,意为“福运、财富”,蕴涵“福运”的灵体。[10](P334-335)Farnah本义为“神圣本质、永恒光明、灵光”,引申为“神赐灵光”,多为王家或祭司阶层所有。[11](P1-77)张小贵认为,琐罗亚斯德教“以有翼的飞鸟形象来表示‘神赐灵光’。”[12]赫瓦雷纳,即福运之鸟。
赫瓦雷纳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如印绶鸟、衔铃鸟、衔环鸟、隼、鹰等都是其表征,其中一种是人头鹰身(一说人头鸡身,鸡公与鹰隼在琐罗亚斯德教都是善禽)。姜伯勤认为,这种“人头鹰身赫瓦雷纳(Xvarenah)鸟即是圣鸟Senmurv之一种。”[9](P104)Xvarnah/Khvarenah为“光耀”之义,即光神,又称之为灵光神,是“王者灵光”。所谓“王者灵光”,王小甫认为是“古代波斯浮雕上那种带翅膀的和鸟尾的光盘(Faravahar/Farohar/Farrah),上部为一个男性显贵的形象。”[13]人面鸟身的现象,时见于《山海经》。葛洪《抱朴子·对俗篇》云:“千秋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而鸟身,寿亦如其名。”[14](P41)中国古代的千秋、万岁鸟亦为人面鸟身,表达着人们追求长生久视的理想。佛教中的迦陵频伽也是人面鸟身的形象。张小贵认为,虞弘墓室椁浮雕上的人身鹰首图像,或受佛教迦陵频伽的影响。[15](P121-135)但是,黎北岚认为,琐罗亚斯德教中的人首鸟身祭司形象与紧那罗、迦陵频伽不一样,可能受中国朱雀观念的影响。[16]中国古代,五行方位文化中,朱雀表征着南方,也是一种祥瑞之鸟。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载:“四方取象,苍龙、白虎、朱雀、龟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鸟谓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云,鸟即凤也。”[17](P57)墓室魂门或神门之上都有朱雀图像。孙机认为森穆夫与中国的飞廉有关联。[18](P166-169)其实,有翼神兽与朱雀、飞廉皆无内在关系,它是西域神话东传的结果。
阿扎佩在《粟特绘画中的若干伊朗图像程式》中指出:“在波斯的语境中,与动物形式相联系的hvarenah,意味着一种盛大的好运随之而来。”[19]阿扎佩发现,hvarenah表达好运的时候,总是与兽身鸟、光线、头光、光焰等表现形式联系在一起。他又说:“在安息艺术中,衔铃鸟表达伊朗的‘赫瓦雷纳(Hvarenah)’的概念,表达运气、好运的概念。”[19]
由以上可知,印绶鸟即琐罗亚斯德教中hvarenah之一种鸟形象的显现,是预言未来的吉祥鸟。王世充作为一名西胡的后裔,猎捕野鸟,颈绕帛带,自言符命,放其飞到空中,虽然是一种就地取材的中国版吉祥鸟告天,但依然可以以之宣扬“王家无上荣光”。他要登基称帝,希望祥瑞的鸟儿能给他带来好运,以此希冀皇图永固。而印绶鸟的这一宗教符号意识,华夏文化中不曾有,从而表明他所信奉的是琐罗亚斯德教或中国化的祆教。
(三)胜利之鸟
鸟在琐罗亚斯德教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言说着特别的宗教意义,表征着该教的宗教特色。例如,鹰是祆教战神巴赫拉姆的化身之一[20](P249)。而琐罗亚斯德教的象征符号法拉瓦哈(Faravahar)也表现为带着老鹰翅膀的人。古埃及神话中有人身鹰首的神祇。西亚、中亚神话中也多见鹰神的叙述。《阿维斯塔》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经典,其中表达“好运”的符号就是鸟。《阿维斯塔·亚什特》卷第19篇第7章第34—35节云:“当他(按:指的是第一位人依玛Yima,即印度的阎摩,波斯人、印度白种人都是雅利安人的后裔。)开始以虚假的谎言为乐时,灵光神就现形为一只鸟飞离了他……伊玛惶恐不知所措,羞愧得无地自容。……灵光神离开了伊玛,化身为一只Varaghan/Vareghan鸟。辽阔牧场的主公密特拉(Mithra)神捉住了灵光。”[21](P30)密特拉同时还是法律公正之神、太阳神。Varaghan鸟之于密特拉是不是犹如中国太阳神话叙述中的三足乌?
在《阿维斯塔》中,Vareghan鸟并非只是灵光神的象征,它同时也是胜利之神Verethraghan/Bhaarm的化身。《亚什特》第14篇是对胜利之神得悉神的颂歌,胜利之神有十种化身:一阵猛烈的狂风,一头长有金角的公牛,一匹长有金耳和金蹄的白马,一匹发情的骆驼,一头公野猪,一个15岁的青春少年,一只Vareghan鸟,一只弯角的公绵羊,一只尖角的野山羊和一个武装的战士。[22](P212)Verethraghan的化身之一即Varaghan鸟,中文有多个翻译版本:隼、鹰、鹖等。
《伊朗学百科全书》“Bahram”(音译为巴赫拉姆,意谓斗战神)条把Vareghna鸟解释为隼或猛禽(falcon or bird of prey)。斗战神颂歌第7章第19—21节略云:“(19)第7次阿胡拉创造的斗战神(向他的求助者)赶来,化成一只Vareghan鸟急速前进,下面抓,上面撕,这最敏捷的鸟,这最快的飞行物。(20)它是唯一能赶上飞箭的生物,无论那箭射得多好。天刚破晓,它舒展羽毛飞翔,为避离黑暗追寻日光,为徒手者寻求武装。(21)它在山岭峡谷上空滑翔,它掠过一座座山峰,它掠过一条条河流,它掠过林梢,聆听着鸟儿们的喧哗。斗战神就这样来了,带着马兹达创造的善惠灵光,那马兹达创造的光华。”[21](P31)奥马尔·凯扬编写的《新年书》赞颂隼道:“古人云:隼(falcon)是肉食鸟类之王,犹如马是草食四蹄动物之王。它天生具有其他鸟类所没有的威权(majesty);鹰(eagle)虽然体大,却无它的威严。”[23](P17)Saena在《吠陀》中指的是自然界中的老鹰。在《阿维斯塔》中,它最初指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龙,潜入水中成为占卜鸟。在《耶斯特》中,它是一种神秘的鸟。它是不是Senmurv的一种?Senmurv栖息在湖中岛上的Hom圣树上,随云化雨,减轻人们的痛苦。[24](P205)
琐罗亚斯德教对鸟特别崇拜,因此在其神话叙述中不仅多有自然界存在的鸟,而且有出自于想象中的神鸟。例如Pesho-Parena就是一只了不起的神鸟。《亚什特》第14篇第14章对这只超凡的神鸟进行了衷心的赞颂。
(四)作为圣禽的公鸡
在琐罗亚斯德教中,公鸡是善禽、圣禽。琐罗亚斯德教崇尚火,它认为太阳是天上的火,因此崇尚太阳。公鸡被视作太阳鸟,又,“雄鸡一唱天下白”,夜晚是恶魔的时间,晨曦时恶魔就潜遁到地下,从而鸡鸣是恶魔的丧钟之声,因此它在琐罗亚斯德教中地位崇高。裁判桥(The Chinwad Bridge)桥头的灵魂审判者之一斯劳沙(Sraosha),其化身之一就是公鸡。
据《阿维斯陀》,公鸡可驱除恶魔,阿胡拉·马兹达指定其来协助天使长斯劳沙神共同引导死者灵魂升天。[25](P118)杨巨平指出,“雄鸡和鹰都是祆教崇拜的对象,是阿胡拉·马兹达为与群魔和术士对立斗争而造的。据说,有两种名为‘阿绍祖什特’(即‘佐巴拉—瓦赫曼’)和‘索克’的鸟,被赋予了《阿维斯塔》的语言,它们一旦讲述,‘群魔就胆战心惊,无可逞其伎’。”[26]《阿尔达·维拉兹入地狱记》记载:“人们称呼公鸡为正直的斯罗什之鸟,当他鸣叫时,会驱走不幸,使之远离奥尔马兹达的造物。”[25](P118)斯罗什(Srōš)是斯劳沙的另一音译。《创世纪》记载:“公鸡乃是被创造出来对抗恶魔的,与狗合作;正如天启所示,在世上的造物中,与斯罗什合作共同抵御邪恶者,正是狗和鸡。”[27](P202)在帕拉维文《阿达希尔事迹》中,胜利之火阿杜尔·法恩巴格,就曾幻化成“红色公鸡”,打翻阿达希尔手中含有毒药的酒杯而救了他。[28](P212-213)
王小甫认为,“金鸡应即斗战神和灵光神共有的化身Vareghna鸟。”[13]自北齐以来,朝廷建金鸡大赦,其中的金鸡口衔红幡条,飘坠而下。笔者认为,金鸡“衔绛幡”,其原型或许就是河南安阳北齐石棺床、西安北周安伽墓石棺床、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椁、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棺等石刻葬具图像中的“衔绶鸟”。金鸡大赦中的绛幡,是不是祆教中的印绶鸟之印绶的一种变异?
二、王世充的宗教伦理
据《旧唐书》载,王世充“字行满,本姓支,西域胡人也。”[1](P2227)西胡,一般指的是东部波斯人,即粟特人。《隋书》记载,王世充“豺声卷发”[29](P1894)。从其身体特征之卷发,可以印证他的确是具有西胡血统。而王世充本姓“支”,从其姓可确知,他的祖先是大月氏人,即后来的贵霜人。不管是粟特人还是贵霜人,作为西胡当年他们都信奉琐罗亚斯德教。
大唐武德元年(618),王世充拥立洛阳留守越王杨侗为皇帝。二年(619),彗星行天。王世充利用彗星出现则除旧布新的说法,在洛阳逼迫杨侗禅位于他。杨侗坚决不同意,王世充则直接借口国乱时期须长者治理,他以救时为理由强行受禅。以星象说法,一方面是天人合一政治理念的阐释机制,另一方面,琐罗亚斯德教里面充斥着长篇累牍的天文星象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言说着人天关系。王世充的宗教信仰,从他僭号亦可以补证。《旧唐书》记载,王世充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开明,国号郑。”[1](P2231-2232)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崇尚圣火、光明。而王世充的郑国建元为“开明”,从而表明汉文化程度很高的王世充确实是从骨子里信奉拜火教。
程知节曾对秦叔宝说:“(王)世充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此巫师老妪耳,岂是拨乱主乎!”[1](P2503)王世充“多咒誓”,这恰恰证明王世充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因为宗教相信语言的力量。许多民族的神话中都有语言创世的叙述,《圣经》就是上帝通过言语创世的。上帝创世的时候,说“让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杜佑《通典》卷四〇《职官》二二记载:“祆者,西域国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30](P1103)《儿郎伟驱傩文》“赛祆”咒文云:“今夜驱傩队仗,部领安城大祆,以次三危圣者,搜罗内外戈铤,趁却旧年精魅,迎取蓬莱七贤,屏及南山四皓,今秋五色红莲。从此敦煌无事,城隍千年万年。”[31]几乎可以这样说,所有的驱傩祈祷都是“咒诅”。从而可知祆教教徒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经常“咒诅”。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现实政治的或实用实践的一种相信,王世充的祖先虽然是西胡,但是从文化上来看他已经中土化了。王世充,字行满。从其名与字以及其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可知,他的名字不是随随便便起的,而是不仅符合汉文化的取名规范,而且反映了其家族的华化程度极其高。《旧唐书》记载,“(王)世充欲乘其弊而击之,恐人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乃立祠于洛水,遣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疫死。(王)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众皆请战。”[1](P2230)周公制礼,在儒家思想中他是圣人谱系之首。王世充竟然撒谎说他梦见了周公。然而,他是将“敬鬼神而远之”的周文与巫觋鬼神道杂糅来诓骗楚兵。在洛水旁立祠,安排巫觋代己宣言,宣布军事命令和发出瘟疫恐吓。楚人佞鬼,王世充此举表明他亦深谙华夏文化。
宗教的真谛是信仰。然而,宗教之于王世充,却是政治利用,而不是虔诚信奉。据《资治通鉴》载,王世充率领淮南兵大败刘元进、朱燮。“(王)世充召先降者于通玄寺瑞像前焚香为誓,约降者不杀。散者始欲入海为盗,闻之,旬月之间,归首略尽,世充悉坑杀之于黄亭涧,死者三万余人。”[32](P371)王世充如此言而无信、“沉猜诡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杀降不吉”,而王世充先盟誓后杀降,哪有一点宗教教徒的信仰慈悲之心!从他经常咒诅、盟誓而不恪守信约可知,无论是巫术、儒教、道教还是祆教,对王世充而言都是一种功利性利用,都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赤裸裸展现,从而表明他的宗教伦理实质上是政治伦理。
王世充“明习法律”,为了勾结盗贼罪犯,他“皆枉法出之,以树私恩”[29](P1894-1895)。此乃王世充之政治行径,也体现了他的伦理身份。从字面来看,他是文法小吏,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实际上,王世充在法律上的天赋和惯习,渊源有自。粟特人是商业民族,法律意识非常强烈。他们的神话中都有契约之神密特拉。梅涅特认为,古代的契约被视为一种宗教行为,具有“盟约、圣约”的宗教意味。“信守盟约”且不用说是信徒的约定,即以普通人来说,它也是应该遵守的美德。但是,这位谙熟法律的官吏,竟然将律法人情化,可谓是入乡随俗,自私自利。
太原虞弘墓图像中的印绶鸟,颈绕两条绶带。有一种说法,印绶表征的是皇权、王家。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上国王端坐,其中一匹马的马腿扎着印绶。学者一般将其解释为这是国王的马,用来祭祀密特拉。以此来解读虞弘墓图像石椁壁浮雕之三、之七、之九,似乎都可以说得通,即可表明其中人物的身份为王者。可是,虞弘墓图像石椁壁浮雕之五,姜伯勤将其命名为“天宫祭祆图像”,并将墓室主人对饮旁边的四位解读为六永生圣者中的四位,右边为阿梅雷达特女神与胡尔伐达特女神,左边为赫沙斯拉·伐利亚与司本特·艾买提。这四位永生者难道是死者的侍从或奴仆?“其下有琵琶、箜篌、笛、腰鼓、筚篥、铙钹及舞人等天宫伎乐供养”[9](P134),这些艺人大多有头光,脖子上也缠着印绶。
三、现象描述性证据的类型学意义
如果仅仅迷信白纸黑字的明文证据,并利用搜索工具查找、确认这些证据,以此作为理性判断的依据,其结论往往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或有偏差。物的部分借代,可否作为有效的证据?物可能有多种变相,其中的一种如果与公知中的标准不一致,可否成为物的表象之一?从王世充的政治作为来看,本文依据史文中的相关现象描述断定其信奉祆教的证据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即明文证据之外的现象描述性书写也是一种重要的证据。
人们一谈中国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张口闭口总是以及只是儒、释、道。固然,儒、释、道当然是中国文化的砥柱,它是西方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所说的文化之大传统,然而,儒、释、道仅仅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小传统即民间文化尤其是其中的民间宗教,由于民间话语的文字文献相对来说匮乏,因此总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是无视。可是,如果不正视民间宗教的在世性、丰富性和隐藏性,中国很多社会现象和问题就得不到如其所是的理解和解释。
即以王世充的宗教伦理来看,他信奉什么?他的宗教伦理中有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道教、巫术,这些都是明摆着而显而易见的。王世充在宗教上似乎完全中土化了,他什么都信,什么都不坚信。他是一位政治仕途上的实用主义者。然而,他骨子里信奉的却是祆教,现实版的印绶鸟即其证据。但是,由于没有明文的书写记载,这一点则从未有人进行发覆,从而就从未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即使是历史学家,读到王世充往空中放野鸟,仅仅认为是荒唐行径,不予以关注。于是,王世充心底里的真正的宗教信仰就不会浮出水面,不为人所知。
以此而论,中国历史文献包括正史,其中关于事实一鳞半爪的现象性描述,其背后书写着后人理解历史真实的证据。它们虽然不是白纸黑字的明文言说,但是却在言说着历史的政治伦理、宗教伦理和文化记忆。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仅仅通过关键词的搜索与统计,就不能真实地获取历史的图景。从而,诸如某某社会现象的何时最早出现,仅仅依据文字文献中的明文书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文字文献行文背后的冰山水下的八分之七景观进行观照和透视。
文字文献行文中的龃龉、怪异、不正常之处,其实背后都有其内在的合理的因果逻辑关系。也就是说,任何不正常的叙述,其背后都潜藏着正常的因果关系。本文对《隋书》《旧唐书》等史书中王世充的诡异行径做了宗教学的意义解读,具有社会学、类型学的方法论意义。例如,窦建德建国号“五凤”是由于“有五大鸟降于乐寿,群鸟数万从之”[1](P2237),大夏政权对鸟的崇奉,其背后也有祆教的宗教意味。再如,北周皇帝登基或改年号的祥瑞多为赤雀、赤乌、三足乌等,其内在的因果也是祆教的吉祥鸟文化为其底蕴。又如,《北齐书》记载高润年已15岁尚且与乃母同寝,从汉民族礼仪文化看是淫秽不伦,但是如果从北齐皇室信奉祆教而祆教践行血缘婚则从中得到何以如此的缘由。如此种种,皆说明看上去不正常的叙述背后都有合乎情理的因果逻辑;现象表征性证据亦言说着历史的事实真相;间在系统性思维可以发覆尘封的事物间性关系。
无实物想象性链接证据、现象描述性证据或残缺文物证据的意义其实亦不容忽视。如果从本文所提倡的描述性现象证据的有效性来看,这些证据虽然历来为人们所无视,但是在文本间性与他者间性的视域中,它们实际上是历史事实的另一种言说。证据的如何采用及其有效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应该予以反思的学术性问题。
结语
孙武军在《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文化与审美研究》中总结道,入华粟特人葬具中多有鸟类图像,都是由于他们颈部没有系飘带,故没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而系带鸟、含绶鸟则表征着祥瑞、吉祥、好运、王家无上的荣光。[33](P182-186)王世充将“书帛系其颈”的野鸟放飞天空,是祆教教徒信仰印绶鸟“神灵佑护”、预言吉祥在中土的变异性展现,表明了他的家族世代宗教信仰的西域传统。从印绶鸟与王世充宗教伦理关系来看,历史学视域中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的中国研究,可能以一种变相、尘封或遮蔽的方式在场。然而,事实性表征的本质透视,更表明了古代中国的宗教伦理主要是指向政治生命;知识认知是对政治伦理揭蔽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具体到王世充的政治伦理,可以发现以文化论民族身份亦有其局限性,因为一个人的文化涵容是多方面的、杂合的、变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