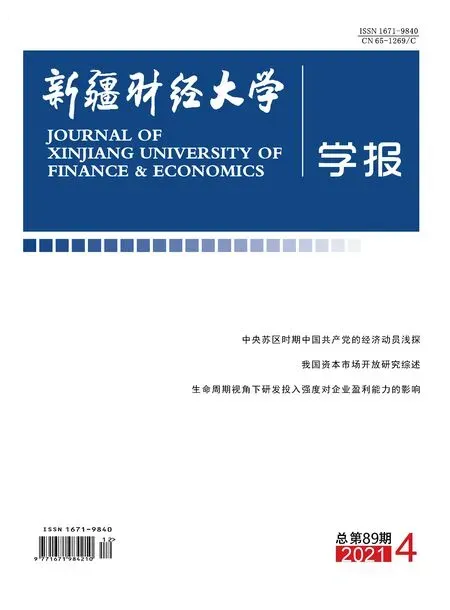刘亮程小说对边疆生态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
陈秋录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20世纪末,西部乡土作家刘亮程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作者在书中用浪漫诗意的语言搭建了一个“天人合一”的村庄。评论者大多肯定了其散文浪漫诗意的一面,却忽略了作家在散文中对新疆地区现实生活的深入思考与忧虑。这些思考与忧虑在其2006 年—2018年的小说创作中更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出版于2006 年的《虚土》是刘亮程由散文家向小说家转型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述了一种“形而下的活泼泼的虚土村的生态”①详见姜广平著《我不慌不忙地叙述着人类久违的自然生存——与刘亮程对话》,原载于《文学教育》2011年第3期,第6页。,其落脚点是大地和大地上生命个体的现实遭遇。2010年出版的《凿空》是刘亮程“第一次面对现实生活写的一部书”,“其意绪是承接《虚土》的,是一种对消逝的忧虑”②详见姜广平著《我不慌不忙地叙述着人类久违的自然生存——与刘亮程对话》,原载于《文学教育》2011年第3期,第9页。,包括对生存家园的消逝、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消逝、人与动物相互依存关系的消逝、村庄古老事物的消逝、简单生活方式的消逝等的忧虑。而出版于2018 年的《捎话》则是一部孤悬于现实之外的寓言,“但无论多么天马行空的表达,立足的还是人在现实中遭遇的各种问题”③详见《一部万物有灵的书》,原载于《工会博览》2019年第12期,第56页。。这几部小说有一个共同点——没有过多的故事元素和人物重大行动,但尤为重视对声音、意象、感觉、色彩等的描写,并以此构成了刘亮程小说独特的叙事技巧,呈现出作家对生态问题的反思与批判。
一、“万物有灵”: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认同
刘亮程的小说是一个个声音的世界。《虚土》呈现出一个被自然万物声音所包围的世界;《凿空》中自然万物的声音遭到压抑,大工业的声音打破了村庄的寂静;《捎话》更是一部“对声音(语言)的理解之书,思考之书”④详见《一部万物有灵的书》,原载于《工会博览》2019年第12期,第56页。,在这个作家营造的人与万物共存的声音世界里,风声、驴叫、人语、炊烟、鸡鸣狗吠都在向远方传递着话语。这些声音或意向背后体现了刘亮程“万物有灵”的思想,即非人生命体的话语同人的话语一样重要,人与自然万物是平等互利、和谐共生的。在此思想下,作家以人与动物的温情相处、人与动物之间的“善”呈现出一个人畜共居、“人物合一”的村庄①如《一个人的村庄》中的黄沙梁,《虚土》中的虚土庄,《凿空》中的阿不旦村,《捎话》中的毗沙国。。村庄中,人与动物长久形成了一种“你养我保护我,让我群体繁殖,我给你肉吃”②详见刘亮程和高方方著《西域沙梁上的行吟歌手——刘亮程访谈录》,原载于《百家评论》2013年第5期,第50页。的互利共生关系,人的呼吸和自然节奏交相呼应,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沟通延续不断。
在作者笔下,人与物的命运具有一致性。《虚土》中,虚土庄人住在一座声音的村舍里,“密密匝匝的狗吠声是这座村庄四周的围墙。驴鸣是中间的粗大立柱。鸡叫是漏雨漏星光的顶棚……牛哞是深褐色的土地……马嘶是向外推开又关上的门和窗户……人的声音住居其中,被层层包围”③详见刘亮程著《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页。。不同的声音呈现出村庄物种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人在清晨被这些不同的声音叫醒,“有的人被鸡叫醒,有的人被狗叫醒”。人醒来的方式不一样,生活和命运也不一样,“被马叫醒的人,在远路上,跑顺风买卖,多少年不知道回来。被驴叫醒的人注定是闲锤子,一辈子没有正经事。而被鸡叫醒的人,起早贪黑,忙死忙活,过着自己不知道的日子。虚土庄的多数人被鸡叫醒……被狗叫醒的人都是狗命,这种人对周围的动静天生担心……最没出息是被蚊子吵醒的人”④详见刘亮程著《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这种人与自然万物命运的一致性体现了作者万物平等的思想。
小说中,人与物的命运不仅具有一致性,而且不同生命形式之间能相互转化。如在《虚土》中,虚土庄的生命分三层,“上层是鸟,中层是人和牲畜,下层是蚂蚁和老鼠。三个层面的生命在有月光的夜晚汇聚到中层:鸟落地,老鼠出洞,牲畜和人卧躺在地。这时在最上一层的天空飞翔的是人的梦。人在梦中飘飞到最上层,死后葬入最下一层,墓穴和蚂蚁、老鼠的洞穴为邻。鸟死后坠落中层。蚂蚁和老鼠死后被同类拖拉出洞,在太阳下晒干,随风卷刮到上层的天空。在老鼠的梦中整个世界是一个大老鼠洞,牲畜和人,全是给它耕种粮食的长工。在鸟的梦中最下一层的大地是一片可以飞进去自由翱翔的无垠天空”⑤详见刘亮程著《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作家将鸟、人、牲畜、蚂蚁、老鼠的生命等而置之,人与其他动物没有明确的区别,不同生命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因此虚土庄人可以有很多次诞生和死亡,如小说中的“我”,某些年“我”变成了一只鸟,某些年“我”变成了一只老鼠,最后也许变成树叶和泥土,回归大地。这些变换无从触摸,看起来虚幻且毫无根基,却呈现给读者一个不同生命体自由自在、和谐共处的乡村世界。而在《捎话》中,各生命体之间的转化则呈现出一种荒诞的形式——人畜鬼杂居,灵魂附体。比如,被谢附体的库⑥《捎话》有两种叙事视角:一种是人的,主要是翻译家——库的视角;另一种是驴的,主要是以一头小母驴——谢的视角看人世间。在历经艰难后终于在临死之际听懂了驴的语言,并作为使者返回人间,再将驴的声音捎给人。这种不同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正是作者“万物有灵”思想的体现。
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提倡“和,故能生万物”,“和”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更是作家向往的理想状态。在刘亮程的小说中,人与其他非人生命最初相处融洽,甚至达到了“人物合一”,只是后来“合一”的平衡状态被人打破。下文以小说中人与物的相处模式为例说明这种“合一”。
先看人与老鼠的相处。在《虚土》中,“人抢收时,老鼠在地下清扫粮仓。老鼠不着急,它清楚不管地里的还是收回粮仓的,都是它的食物。人也知道躲不过老鼠,人种地时认真,收割时就马虎,不能收得太干净,给老鼠留下些,老鼠在地里吃饱了,就不会进村子”⑦详见刘亮程著《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虚土庄人对老鼠的态度体现了他们的生存智慧——没有以人为中心的全然占有,也没有对老鼠不劳而获的道德谴责,有的只是对生命的宽容。同样,在《凿空》中,阿不旦村民也曾有意识地与老鼠和平共处:“老鼠和人一样喜爱麦子,喜爱就会珍惜,至于它吃的那一点粮食嘛,就算工分好了”,“生产队时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一大窝老鼠,年年偷麦子吃,从没人动过它。生产队都没敢动它,我动它干啥?大小也是个邻居呢”①详见刘亮程著《凿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页。。久而久之,人与老鼠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人不需要把老鼠赶尽杀绝,老鼠和人能共存于大地之上。
再看人与家畜的日常相处。在《凿空》中的阿不旦村,驴是最重要的家畜。在人与驴春播秋收的角色定位中,小说呈现了二者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按驴师傅阿赫姆的说法:“村子一半是人的,一半是驴的,人的院子也是驴的家。”②详见刘亮程著《凿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页。阿不旦村的每种牲口都有一个师傅,马师傅、牛师傅、羊师傅、鸡师傅、狗师傅、骡子师傅,最出名的是驴师傅。作为人与动物之间的“使者”,这些师傅能和动物交流,能给动物看病。如驴师傅就能听懂驴话,会调教驴,还会给驴治病:“掰开驴嘴看看,往驴肚上踹两脚,割破驴皮放一点血,然后在驴背上拍两巴掌,驴就好了”③详见刘亮程著《凿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通过长久的接触和沟通,人与家畜能相互配合,达到默契。如赶驴人“熟悉驴比熟悉车需要更长时间……好的赶驴人会聪明地把有些事情交给驴,遇到难走的路,人动一半脑子,让驴动一半脑子”④详见刘亮程著《凿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196页。。这种人和驴的相互依存是人和其他动物间少有的,这种依存一直延续到小说《捎话》。唯一不同的是,《捎话》中有一半的驴超越了家畜的角色,比阿不旦村的驴更具有主体性,它们作为一种独立的生命体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中,对人的生存和精神生长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不难看出,作者赋予物以主体性,精心设计了“动物看人、看世界”的叙事视角,描写了一群善于察言观色的动物并极力突出动物的生存权利、生命意识和生存智慧,从而呈现出一种物与人的“对话”关系,体现出作者“万物有灵”的思想。如,“大多数驴都具备了听懂人话的能力,它们只是不会说人话”⑤详见刘亮程著《凿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页。,“驴和狗能看见人的表情,它们通过看和听,懂得了人说话的意思”⑥详见刘亮程著《凿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驴、鱼、狗、老鼠等动物通过揣摩人的习性,学着如何与人“打交道”,这既是动物的生存本能,也是一种主体性的体现。
但同时,作家笔下“人与动物的权利是有差别的”⑦详见余谋昌著《生态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以家畜为例,它们生来各具使命。刘亮程曾强调:“我写的动物不是宠物,是家畜,是人的帮手和陪伴,也是食物。人和那些动物是共生关系,相互依存。人养猪养羊,养肥了宰吃,猪和羊也同意。这是从动物被人家养那时起就建立的契约关系,你养我保护我,让我群体繁殖,我给你肉吃,你养的越多,我的群体越大,你可吃的肉也越多。”⑧详见刘亮程和高方方著《西域沙梁上的行吟歌手——刘亮程访谈录》,原载于《百家评论》2013年第5期,第50页。他对动物生存权利的理解区别于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他们宠狗就只爱护狗,不管其他动物的死活。或者嘴里说着珍惜保护野生动物,却一巴掌拍死落脸上的蚊子。蚊子不是野生动物吗?或者不吃任何动物的肉,你不吃羊肉就是害羊呵,都不吃了,羊就没人养,灭绝了”⑨详见刘亮程和高方方著《西域沙梁上的行吟歌手——刘亮程访谈录》,原载于《百家评论》2013年第5期,第50页。。在他看来,动物有生存权利且并不是贵生贱死,保护动物也并不等同于不吃肉食。生活在庄稼地、家圈里、自然界的动物是有别于城市中的宠物的,前者因为近于土地,根性是孤独而完整的,村民对它们的态度不是宠,而是各取所需、共生共存。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亦是如此,人对生态系统的依恋不光是对自然资源的索取,还在于人在生活上对其他生物的依赖、在情感上与其他生物的共融以及在心灵和精神上对其他生物的需要。
历史实践证明,在孟子身后的古代中国,是荀子的武德思想成为国家层面治理原则的主流[10]。如梁启超甚至说:“二千年政治,既皆出荀子矣……然则二千年来,只能谓为荀学世界,不能谓之为孔学世界也。”[11](P57)而至于武德的集体层面,尤其具有儒家社会理想的知识阶层共同体内部,孟子反躬自省与仁义当先的思想重新焕发其活力。
作家赋予物以主体性在《捎话》中更进一步,主要以物的视角呈现了对人的反向启蒙,从而揭示人类认知的局限与可笑。毗沙国有一半的驴在给人安心当牲口,另一半则不然,后者有一种“驴类中心主义”立场,“毗沙驴早就认为自己站在世界中心,南来北往的人和驴汇聚到毗沙城,再走向四面八方。世界围着毛驴转。毗沙驴天生知道自己的每一声驴鸣都会被大地上的驴和人听见”①详见刘亮程著《捎话》,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且它们“固执地认为毗沙城是给驴修的,世界是驴的,人是驴的牲口,人虽然骑在驴背上,但驴叫声骑在人的声音上,驴在天上的位置比人高”②详见刘亮程著《捎话》,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而人类对此并不自知,人不知道自己生活的毗沙城在驴世界里叫大驴圈。在《捎话》设定的世界中,驴的认知比人的认知更接近事实。比如,在谢看来,“人因为说不同的话才长成不同地方的人。因为话不同,说话的嘴就不一样,脸上表情也不一样,脑子想的事情不一样,头也不一样”,而“全世界的驴都叫一个声音,所有驴长得也都一样”③详见刘亮程著《捎话》,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35~36页。。由此推断出:首先,人的语言是分裂的,人类至少有几十种语言,声音因此不同,众声喧哗,不同的声音只能呈现局部的认知,而不同的认知代表着不同的观念、文化与信仰,人类很难“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因此这些不同常常会在人心和人心之间制造迷途或战争;其次,没有一种语言能够准确地感知、传达天的真言,也不能与天沟通,正如天庭守门人对库所说,“人声高不过麻雀的翅膀”,无法传到天庭,“上天把真言给过人,被人传歪。唯独驴叫没有走形”④详见刘亮程著《捎话》,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309~310页。。驴的声音自始至终只有一种,与人类纷繁走形的声音相比,前者能感知世界的全貌,能直达天庭,能与天的真言相通,“这其实是驴尚未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与人相比,它与自然(天)的关系更和谐,因而更具有神性,更接近真理”⑤详见王晴飞著《驴鸣与人声——读刘亮程〈捎话〉》,原载于《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6期,第46页。。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作者“万物有灵”的思想。
刘亮程笔下的村庄各自呈现了一个丰富的自然生态系统,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处乃至情感深厚标志着生态的和谐、家园的和谐。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总是如此,尤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愈加严重,人与自然对立矛盾的一面更加突显。
二、“人类中心主义”:对人征服自然的批判
在刘亮程的小说中,人对自然的征服体现在两方面,即人对万物的主宰和人对土地的征服。
(一)人对万物的主宰
人对万物的主宰依旧可从“老鼠”和“驴”切入。老鼠是刘亮程在《虚土》《凿空》两部小说中成功创作的一个生态灾难预警意象⑥胡志红指出:“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创造生态的意象,想象世界末日的恐怖图景,对生态灾难进行预警,其根本目的是警示人们对自然的关怀和对人类命运、前途的关注。”这既是生态文学肩负的一大重任,又是它在艺术架构和表现形式上的一个鲜明特点。详见胡志红著《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通过这一意象,作家巧妙地呈现出人与动物从和谐共生到竞争对立关系的演变,从而揭示了人类已经或将要面临的生存危机,以引发人们疗救的注意。虽然丰收之年人与老鼠能够和平共处,但一到灾年,人与老鼠绝不会“同舟共济”,为了争抢有限的生存资源,二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演变成一种“竞争作用”⑦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认为物种种群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有9种,其中,竞争作用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形式,主要表现为物种之间竞争生存空间、阳光和食物。详见余谋昌著《生态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的对抗关系。比如,人与老鼠之间出现了“抢收”,“那一年干旱,人和老鼠都急了,麦子没长熟,老鼠便抢着往洞里拖。人见老鼠动手,也急着慌忙开镰,半黄的麦子打回来。其实不打回来麦子也不会再长熟,地早干透了”⑧详见刘亮程著《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再如,村民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对老鼠集体投毒,走投无路的鼠辈们只能选择“集体自杀”:或上吊或跳河——“让张旺才吃惊的是,在老鼠洞不远的一墩矮红柳上,挂着四五只死老鼠,全部脖子夹在红柳枝杈间,吊死在那里”,“浓重的农药味熏得老鼠头晕……老鼠肚子空空的,洞里也空空的,老鼠知道过不去这个冬天,就集体跳河自杀”①详见刘亮程著《凿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老鼠“上吊自杀”“跳河自杀”表面上是一种拟人化描写,但实际上是一种警示人类命运的后现代预言:人与动物之间长期的对立紧张关系,最终也会影响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尤其随着人口的膨胀,人的生存压力也会增大,这一方面会加剧人类群体内部的竞争②用当下比较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内卷”。“内卷”是一个被普遍使用至各领域但仍具有争议的概念,国内最早因黄宗智教授的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面世而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受到关注,其基本含义是指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概括为“无发展的增长”。本文借“内卷”表示一种面向人类群体内部的、不断增大且无限循坏的竞争,包括恶性竞争。,另一方面也会加大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只顾眼前利益、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且人口众多所造成的巨大资源需求,会加重人对其他生物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的占有。
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初,西部现代化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尺度从某种角度上说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人与动物比较的独特性”③详见余谋昌著《生态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绝对的主客二分导致人只认为“人有价值,生物和自然界没有价值”,“道德只涉及人对人的行为,只对人讲道德”④详见余谋昌著《生态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不涉及自然及其他生物。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关于人主宰自然的观念,鼓励了人对自然界其他生命的主宰,加剧了人与物关系的僵化,致使万物沦为人的附属品,最终只剩下工具价值。以《凿空》中龟兹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遭遇为例,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龟兹政府提出了“驴政策”,即在较短时间内杀掉驴,推行三轮车等现代交通工具。
驴是刘亮程创作的另一生态灾难预警意象。在《凿空》中,人对物的绝对主宰使得驴开始群起而反抗,它们不约而同地上演了“万驴齐鸣”,“仿佛约定好时间,几万头驴齐声鸣叫,龟兹河滩瞬间被驴鸣的洪水涨满。驴叫是红色的,几万头驴的鸣叫直冲天空,驴鸣的蘑菇云在天空爆炸”⑤详见刘亮程著《凿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首先,红色在传统文化中代表欲望、反抗、流血、牺牲等,这是一种希望与绝望并存的色彩,红色的驴叫声充满了反抗和悲剧意味,昭示着龟兹驴在现代化进程中为自身遭遇不平而鸣叫。其次,驴对色彩和声音的感受异常敏感,从驴的声音进入,展现出驴的反抗和绝望,“这种对声音的高度敏感,调动身体最原始的感官体验,用直觉式的表达方式,反而最深切地道出了人类对动物的亏欠之情”⑥详见彭超著《主体性、日常生活与信仰危机——论刘亮程〈凿空〉的现代性反思》,原载于《文艺评论》2016年第12期,第88页。。机器和驴的矛盾体现了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村落生存的冲突,刘亮程并未偏袒一方作出道德评价,只是借书中裴教授之口道出了他对现代化可能改变的人与动物关系的生态隐忧,“机械时代的到来,使人和其他动物维系了千万年的依存关系被彻底打破,动物从人的伙伴、帮手、相依为命的朋友,变成单一的人的肉食。机械把前者都替代了,只有后者它无法替代,机器不能吃,驴最终对于人只有肉体意义”⑦详见刘亮程著《凿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页。。作者借用这一生态预警想引起读者深思的是,如果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对人而言只剩下工具价值,这个世界又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以上,刘亮程成功利用老鼠和驴两个生态灾难预警意象呈现了人与动物关系的僵化,并揭示了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在他看来,想要改善人和物之间功利且对立的关系,就必须打破“人作为万物之灵”的观念,转向“万物有灵”,后者是一种“超越人是独特的、地球是供我们享受及任人处置而存在的观念,超越狭隘的自我意识,通向一种更包容的生态意识”⑧详见格伦·A·洛夫著、胡志红等译《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作家坚信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皆有灵性、皆有智慧,有感受痛苦和幸福的能力,有生存权利和天赋价值。乍看刘亮程对动物的态度,似乎有些动物崇拜的意味①如刘亮程的驴崇拜意识。详见陈静著《高亢的驴鸣——论刘亮程散文中的“驴崇拜”意识》,原载于《当代文坛》2005年第2期,第89~91页。,实际上它体现了作家对一切非人物种的敬畏与观照,并从中透露出美学和哲学意义。黑格尔曾说:“动物崇拜应理解为对隐蔽的内在方面的观照,这种内在方面,作为生命,就是一种高于单纯外在事物的力量……这时动物形象,就不是单为它本身而被运用,而是用来表达某种普遍意义。”②详见黑格尔著《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2页。具体到作家创作,如刘亮程对驴朴素、警觉、敢于反抗等“驴性”的崇拜,对老鼠智慧、生命力顽强等“鼠性”的赞扬,实际透露了他对非人生命体价值的认同以及对一切生命等量齐观的伦理关怀。
(二)人对土地的征服
在刘亮程笔下,人对土地的破坏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粗暴开垦荒地。逃荒者初到虚土庄,盖好房子,剩下的事便是烧荒,“开地前先要把地上的草木烧光”,等到草木完全干黄,再“把东边西边南边北边的荒野全点着,火从村边的虚土梁下向远处烧。最远的天边都烧亮了”⑤详见刘亮程著《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9页。。二是过度开发土地。如村民过度放牧,超出土地承载力,“一户人靠放牧为生。有人看见过他家羊群留下的蹄印,踩遍七八座沙包。羊群过处寸草不生,连草根都刨吃光了,非有数百只羊头顶屁股地过去才会这样”⑥详见刘亮程著《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不合理的土地开发还导致土壤盐碱化、荒漠化、贫瘠化,“有一些年西边的地荒掉了,朝西走的路上长满草,人被东边的河湾地吸引,种啥成啥……又过了几年,人们撂荒东边的地,因为常年浇灌含碱的河水让地变成了碱滩,北沙漠的荒滩又成了人挥锨舞锄的好场所”⑦详见刘亮程著《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时间一久,“有些土地撑死了,有些饿死了,土地就这样死掉了”,“我们老家的地,就是被人喂得撑死了,多少代人,都喂给它了,它消化不了”⑧详见刘亮程著《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页。。三是对业已破坏的土地缺乏足够的保护或拯救意识,致使土地无法可持续利用。如对用坏的地搁置不理,“我们把一块地吃穷整坏后,跑掉了”⑨详见刘亮程著《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页。。人类缺乏对土地的敬畏与爱惜,许多人“把收获叫抢收,跟风抢,跟鸟和老鼠抢,其实在跟土地抢”⑩详见刘亮程著《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98页。。
值得反思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并非所有人都在一味地破坏土地,始终有人在与破坏土地的力量进行抗争,如虚土庄王五的背土之举①王五觉得虚土庄因为短时间内增加了很多人和牲口,脚下这一块地显得比别处重了,必须背一些土出去,让地保持以往的平衡。人口和需求的增加破坏了村庄原有的生态,王五的背土之举意在尝试挽救这种不平衡的状态,然而,他的这一行为又显示出一种反讽的张力,因为“地的平衡是地上的生灵保持的”,而非通过物理上的平衡去达到。如果说王五的行为代表了一部分现代人对生态被破坏有意识的反思和探索,那么这种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无效的,因为人类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生态危机从深层上说是人性危机,人的素质危机,是人的不合理的生存模式和发展观念所致。显然,作家借用王五的背土之举批判了一部分现代人的反思途径,也构成了作家对反思的反思。详见陈秋录著《生态批评视野中的〈虚土〉》,原载于《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75~79页。,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人们的出发点并不是出于敬畏,而只是为了生存和征服。因为有人明白“如果一下把地整死了——每一粒土都死掉,它就再缓不过来。一块死地上草不长,虫子不生,连鸟都不落”②详见刘亮程著《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只是大部分人都只顾眼前利益,涸泽而渔。通过“土地”这一意象,作家意在批判人类急功近利、不计后果的唯发展模式,而“人类中心主义”正是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源所在。此外,小说还进一步呈现了这种唯发展模式背后复杂的人为因素,如经济政策失误、科技成果滥用等。
三、过分“有为”:对经济至上政策的质疑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发展经济,全面开创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但一些地方政府为加快区域现代化步伐,出台了一些激进的经济政策,同时又因为忽略地方资源环境的可承受能力从而导致自然生态恶化。在《凿空》中,作家透过艾疆这一小人物十几年的经历,向读者展示了经济政策频繁变换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利益损害和生存困境。
阿不旦村早年只种麦子和玉米,村民虽没钱花,但白面、苞谷面掺着吃,也不会饿肚子。后来干部为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动员农民少种粮多种经济作物。于是,阿不旦村的杏树被高产量的苹果树所替代,可等到丰收之际,到处都是廉价的苹果,或烂掉,或成为家畜的食物。过了两年,干部又动员农民把苹果树换成苹果梨嫁接树,结果更糟——长出的果子连牲口都不吃,全部烂掉。如此折腾了十几年,艾疆他们在以前挖掉老杏树的地方又种上了杏树。后来人们听说,负责苹果梨嫁接树这一项目的王副书记“已经调走,在别的县当正书记了。……几个干部倒卖果树苗发了财。还有一个实木家具厂,靠制作高级果木家具赚了钱”③详见刘亮程著《凿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几年后,实木家具厂借龟兹县推行“驴政策”转产做驴肉加工和阿胶生产,又一次满赚而归。“好企业是政府的帮手,政府想干啥它马上就去配合干”④详见刘亮程著《凿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页。,反讽的语言指向以权谋私的干部们将“中饱私囊”自我美化成“互利互惠”。此外,随着“西气东输”工程的推进,以及“一黑一白”战略的实施,龟兹县也变成了棉花大县,艾疆他们用好几年时间接受和学会了种植棉花,头几年村民靠种棉花赚了钱,可当他们拿出更多土地种棉花时,棉花价格下跌,许多人亏了本,没粮食吃。从艾疆的经历可见,政府在推行经济作物种植的过程中走了些弯路,或不顾现实条件而过分“有为”,或违背经济规律而急于求成,不但没能帮助农民脱贫,反而破坏了村庄原有的经济系统和土地生态,“倒腾来倒腾去,土地没安宁过。结果呢,倒霉的是农民。地倒腾坏了,农民被倒腾得吃饭都成了问题”⑤详见刘亮程著《在新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
在刘亮程看来,一个真正的好政府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首先,决策者应该因地制宜,帮助农民了解政策,加强农民与政府间的沟通,否则会造成农民与政府间不必要的误会。如《虚土》中,上级领导到虚土庄做有关人口、土地、牲畜等的调查,村民的各种猜疑、恐慌以及一系列荒诞的应对措施——谎报数据、故意把地块整得方不方圆不圆、用酒精兑水灌醉工作人员、试图用开水煮坏皮尺等等⑥详见刘亮程著《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228页。,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地农民对政策的无知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其次,政策的推行应该是科学合理、循序渐进而非不切实际、盲目求快,后者只能事倍功半,最终导致农民对地方政府、对政策、对现代化“置身事外”或“无所适从”。如《凿空》中政府在清除龟兹驴、推广三轮车这件事情上绕过农民的实际需求、急于求成,使得农民在短时间内无法调整、转变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以适应政策与社会的变化,反而不利于推进现代化进程。
刘亮程并没有将造成生态灾难的原因归咎于现代化,小说只是试图表达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失误是人为导致的,是可以减少或避免的。以经济决策为例,即使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若只考虑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和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最终可能只会加重生态危机和农民的生存困境,这也是造成环境问题和农民问题更为广阔的社会因素。以《凿空》中龟兹“驴政策”所引发的“万驴齐鸣”事件为例,从阿布都县长、张副书记到裴教授再到普通民众,不同的反思立场皆有所提及。其中,裴教授可以说是“动物伦理”的践行者,他关注动物的生存权利和生存处境,以驴的命运为例指出生物多样性减少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具体危害,也从龟兹的长远利益出发指出保留驴和驴车的实际益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不同立场、不同程度的对政策的反思和批判有助于社会力量对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进行监督,从而促进政府和管理机构制定更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规划。
总体来看,刘亮程提倡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缓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富有启示性。但同时也要看到,“有所不为”不同于“无为而治”,前者是指在一定时期受制于发展条件而“不可为”,或由于发展策略的原因而“不必为”。当然,在刘亮程的小说中,人们确实不难解读出老庄思想的某些影响,不必讳言,它体现了一种落后的小农意识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这在新疆由传统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当口尤其值得警惕。
四、机械主义泛滥:对科技至上倾向的反思
科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要素和内在原动力,但人类在利用科技的同时也会导致对自然的袪魅、自然物种的灭绝或非自然变异,甚至导致人自身的异化,使人最终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鄙行为的奴隶”①详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页。。西部边疆现代化进程比较缓慢,农民对现代科技成果的认识和运用也相对滞后,从《虚土》到《凿空》可以看到农民对科技成果的逐渐接受和包容,但科技成果的滥用和技术理性的膨胀也给乡村和自然带来了新的问题和危机。
首先,科技成果滥用会对自然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在《凿空》中,某些干部动员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时一味督促农民按技术要求施用化肥,“一棵树一年上二十公斤化肥,上不够树长不起来”②详见刘亮程著《凿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有的干部为了一己之私,不顾农民的经济情况和实际购买能力,强行要求农民以人工化肥代替天然肥料。而施肥方式的改变对土地的影响是长期的,过分依赖工业化肥会导致土壤板结、肥力下降,以致形成恶性循环,破坏土壤生态。几十年后的今天,当社会经济开始提倡“有机”——有机蔬菜、有机水果、有机大米……人们发现曾经的唯技术模式既盲目也不科学。虽然我们也应当避免“时代错置”——不能用今天的发展观念来质疑曾经的现实需求,在尚不能解决温饱的年代,人类首先考虑的只能是产量而非品质问题,今天人们对绿色食品的追求是在解决温饱问题基础上的进步,但我们仍需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避免滥用科技成果。
其次,大量使用生物药剂可能导致物种灭绝或非自然变异,如《凿空》中阿不旦村民用老鼠药集体灭鼠。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灭鼠战斗日益升级,老鼠也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威胁,但它们总能承受来自恶劣环境的不利因素,并在逆境中增长应对风险的能力,甚至通过基因遗传的方式将这些后天生成的能力传给了后代:阿不旦村的老鼠能够区分食物与毒药,有些老鼠甚至对生物药剂免疫。所以,不管村民如何干预,老鼠不但没能被彻底消灭,反而发生“变异”——体型增大、数量剧增。而其结果就如同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描绘的,一系列生物药剂,如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不但没能杀死害虫、清除杂草、提高粮食产量,反而误杀了鸟类、益虫,甚至引发人体中毒、水污染、土壤破坏等一系列连锁反应。阿不旦村的老鼠药也引发了类似的连锁反应,药死了老鼠的天敌——猫,还意外毒死了两个小孩儿。地球是一个由岩石、水、大气、土壤、生物等子系统构成的生态系统,各子系统既独立存在又相互作用,人类的任何一个决策都可能影响到整个生态。作家的担心不无道理,从长远来看,人类确实应该反思,使用生物药剂是否为平衡物种数量或解决相关问题的最佳方式。
再者,将科技应用于现代化发展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导致负面效应,如产生大量的生活和工业垃圾、破坏植被和土地、造成高消耗等。先进机器替代落后畜力、科技产品更新换代本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利用不当就会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最终不仅不能增加人类福祉,反而会危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刘亮程在小说中对科技的态度是含混的,并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或肯定,而是通过呈现科技成果使用中的负面影响扩展读者对科技力量两面性的认识。他所批评的不是科技而是滥用科技,指责的不是现代化而是技术理性的无限统治,从而引发读者对机械主义科技至上观念的多面反思,提醒读者勿以一己之私滥用科技,并启发读者为减轻科技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和干扰作出个人努力。科技的使用应以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立足于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利用科技改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才是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科技观。
五、结语
刘亮程的写作几乎都是围绕农村、农民,其小说中的生态书写拓宽了西部乡土小说的表现领域,呈现了作家丰富的生态哲思,诸如“万物有灵”思想、“和谐自然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崇尚自然美与整体美、提倡“有所为有所不为”等等。从某种层面上说,这些生态哲思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和农耕智慧,其审美追求更是与道家美学一脉相承。作家曾说:“庄子、屈原、《山海经》、唐诗宋词、明清笔记,还有翻译过来的一些西方经典,都影响了我。”①详见何英著《刘亮程论》,原载于《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1期,第7页。“我非常喜欢《山海经》,喜欢古人坐在大地某个角落里,无边无际地冥想,更喜欢庄子‘与土地精神独往来’的气息。……庄子的哲学早已深入民间,或者说庄子的哲学,本身来自古老的民间”,他甚至相信“村庄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活成庄子”②详见姜广平著《我不慌不忙地叙述着人类久违的自然生存——与刘亮程对话》,原载于《文学教育》2011年第3期,第7页。。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对自然审美的自觉追求,使得刘亮程的生态哲思在某些方面具有弥补西方生态思想不足的可能,从而有助于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美学与生态智慧。
但同时,刘亮程也是一位具有鲜明人文主义情怀和民本主义态度的作家,而西部农村和其民粹立场难免会限制他的视野与价值判断。从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刘亮程对生态危机解决之道的探索一直停留在一条回归自然、回归传统乡村的道路上,正如有论者提到:“刘亮程以现代资源开发代表的现代化建设与乡民乡村关系为突破口,表达了他民粹却是面向传统的彻底回归,这个回归有合理也有消极,这反映了边疆地区走向现代化过程的一种极端心理,它既是对近现代以来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民主国家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关系辩证余响的回应,也是立足于新疆、民族、乡村的回归自然和传统极端化思考”③详见何莲芳和瞿晓甜著《以乡村自然之子的立场顿悟人生、思考现代文明进程——再读刘亮程小说〈虚土〉〈凿空〉》,原载于《新疆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15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小说体现了一种“向后看”的文化姿态。
我们必须看到,人类走向现代化是大势所趋,在这一进程中,传统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传统文化与观念也会不可避免地在震荡中被扬弃或传承,在一定时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也是难以完全避免。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以乡村、传统为资源的生态哲思固然能在某些方面给人们以启示,但并不能以此说明,我们需要向“小国寡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向淳朴原始的“天人合一”的社会回归。实际上,人类在发展中、在科技进步并被广泛运用中遇到的各种生态问题乃至危机,最终只能通过更高层次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得以解决。自然,在此过程中,离不了人文精神的弘扬与支撑,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以此为基础实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一定是超越了古代智慧的更高层次的和谐。在这样一个向度上审视刘亮程的小说,就不难发现欠发达地区的生活以及较缺乏现代性品质的文化观与生态观对作家创作的制约,从而削弱了作家对生态问题反思的深度与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