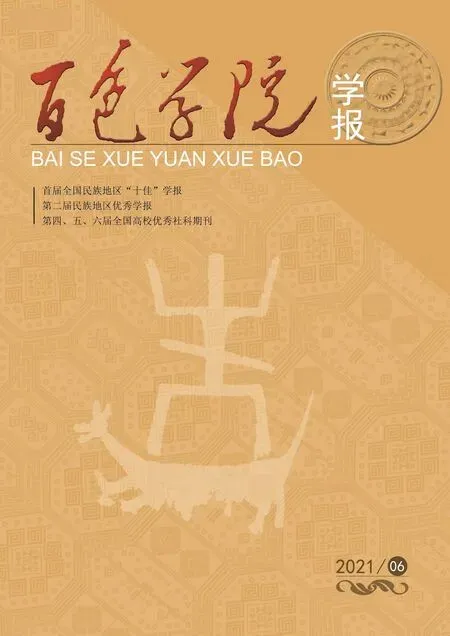《六道轮回图》的“人观”表述
王 艳
(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2.西北民族大学,甘肃兰州 710030)
一、人类学的人观视野
人类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它所关注和解答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点,即人的存在及其在世界(自然-社会)的位置和演变。[1](P1)人类学试图从人的生物性(即自然属性)和人的文化性(即社会属性)两个层面相结合,整体上研究完整的人。也就是以“人观”为核心,反思“生命精神化和精神生命化”[2](P54)两者的统一。自古希腊开始,对于人的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兴建于公元前9世纪的德尔菲神庙墙上刻着“认识你自己!”的箴言。苏格拉底服从德尔菲神①德尔菲神(Delphic god)即阿波罗神,其神谕为:“认识你自己”。的要求开创性地把这句箴言作为自己的哲学原则,专事探讨个体的人,实现了哲学主题由神到人,由自然到社会的转变。在人类学诞生之前,西方哲学家一直担任着解答“人是什么”这一伟大而永恒的主题。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人类学转向,哲学人类学作为西方哲学晚近的一个学派,即以回答“人是什么”为核心命题。在基督教神学体系中,“人论”是教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是20世纪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他在《人是什么?从神学看当代人类学》一书中提出神学如何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相融构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现在“生活在人类学的时代”,因为只有人类学可以和神学对话。
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带有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的特质,涉及语文学、生物学、史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要素,以人类学作为基督神学的对话者,实际可达到使神学参与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面对话之效,以显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限度和科学思想在学术领域中的合理性。[3](P3)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实证主义的思潮,很多哲学家称之为“人类学的复兴时代和人类学的灾难时代”,因为“实证主义”阻止了人向神圣性接近,使人背离了生命的意义和终极关怀,而造成这样一个潮流的罪魁祸首就是人类学。[4]中国的人类学自从西方引进之初就肩负着“了解中国,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5]正如徐新建教授所分析:
近代以来,由于工业化社会与殖民主义实践的负面影响,人类学越来越在各地具体的应用中显现出自我离散的趋势。其中,生物人类学中的“科学主义”和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国族主义”(Nationalism)日益膨胀,而作为其学理基础的哲学人类学受到忽略。于是,对“人”之存在的追问与解答逐渐从形而上意义的终极思考,跌滑到现实对策的功利性应变和价值游离的相对主义阐发,从而致使自古希腊时代以来此学科长期积累的整体性学术资源和实证材料不断跌入被实用主义者任意肢解的陷阱。[1](P1)
人类学研究中“人”的缺失从“实证主义”思潮开始蔓延,使人类学这门涵盖了哲学人类学、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三大分支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质的学科逐渐走向文化人类学单一的学科,文化人类学的发展甚至遮蔽了哲学人类学和生物人类学两大分支。人类学在后期其实逐渐放弃了人类学关于人性的自我理解,放弃了神圣性的思考和关照,这其实是消解了人存在的意义、丧失了人的价值和“人”的失落。人类学研究不应以寻求人性的普通特征为己任,而应在差异性与特殊性中认识“人”本身。由于一个人的先天构成中就包含了文化和生物的进程,所以,根本就不存在独立于文化的、先在的人类本性,对“人”本身的认识,必须在对文化进行细致而深入地打量中完成。[6](P75)
二、《六道轮回图》的宗教内涵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追问“人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人类对认识自己的迫切愿望,更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怀,吸引着无数哲学家、神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无穷无尽的思考与探索。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海德格尔认为“人是理性的生物”;卡西儿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弗洛伊德认为人是社会性和生物性、理性和非理性、意识和无意识的辩证统一;康德认为“人能够具有‘自我’的观念,这使人无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个人”。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曾描绘了这样一种人的形象:“人是生命冲动与精神本质的双重存在结构;他在宇宙中占有特殊地位,他向世界开放着,他推动和引导历史发展,他与上帝同生共存。”[2](P55)完整的人就是“生命精神化和精神生命化”两者的统一。无论是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人观”,卡西儿的“符号论人观”,还是舍勒的“生成论人观”[6](P52-64),都在各自的描述中把“存在”“符号”与“精神”视为人的本质存在的特性,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回答“人是什么?”这个人类学的元问题。藏传佛教的《六道轮回图》是人类学人观的物化表述。本文将进一步从“人观”的角度切入,对藏传佛教的《六道轮回图》进行人类学的解读,从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三个维度表述人观。
《六道轮回图》也叫生死轮回图,是藏传佛教对婆娑世界及生死轮回的图像表述。佛教“轮回”的梵文为“Samsara”,意为辗转、流转的世界,指一切众生由于惑业所致,生死于三界六道之中,如车轮般地流转不息,永无穷尽。佛教将一个世界分为“三界六道”,三界即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而有六种生灵在此三界轮回,即天、非天(梵语为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三界之外有佛国净土,往生于净土者可从佛闻法,获得觉悟,免除轮回之苦,超越了生死,可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7](P390)从藏传佛教寺院入口处的壁画到僧人绘制的唐卡,从敦煌莫高窟到重庆大足石刻,《六道轮回图》从古至今流传千年,从西到东跨越万里,超越了时间、地域、民族、宗教的界限,成为藏传佛教代表性的宗教符号。
笔者曾于2018年8月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龙树画苑的田野调查中拍摄了一幅《六道轮回图》(图1)。从整幅图来看,大背景上为蓝天白云、日月星辰,下为高山丘陵、黄土大地,左上角是月亮象征四圣谛的灭谛,即清净涅槃,右上角是佛陀,象征指路人,中间有一个头戴五骷髅冠、面目狰狞、身着虎皮的阎魔王口咬并双手握持生死轮。阎魔王,梵文“Yamaraja”,他是古印度神话中掌管阴间的王,在佛教里又被称为“无常鬼”,无常意为世间万物、瞬息万变,由他来掌握这个转世轮盘,意为大千世界一切皆流,无物常住。阎魔王手里握着的生死轮便是六道轮回图,它分为四圈,从里到外是一个同心圆的结构,飞如轮回的本性一样,轮转不息,无始无终。当你现在受昔业的果报时,你正在造未来的业图,一切都是同时发生,无始无终。[8](P493)
第一圈中画着三个动物——鸽子、蛇、猪,分别代表着贪、瞋、痴三毒,这三毒是使人产生痛苦和不满足的根本原因,而三毒的基本则是无明。佛陀认为人可以通过修习佛法净化三毒,获得完全解脱轮回之缚的方法,断除贪、瞋、痴,从而根绝轮回的痛苦。
第二圈从中间一分为二,分别为黑、白二色,象征恶与善两道,道上有修行中的芸芸众生。在白的半环中,有3个头部朝上的图像,代表将生于天道、阿修罗道及人道的中阴身。在黑的半环中,有3个头部朝下图像,代表了将投入畜生、饿鬼和地狱道的中阴身。中阴是指此生与来生之间的间隔,人死后就进入了中阴状态,进行新的投胎,他们根据生前的行为分别进入六道之中。
第三圈便是六道轮回中的“六道”,指凡俗众生因善恶业因而流转轮回的六种世界,即天道、阿修罗道、人道、饿鬼道、畜生道、地狱道。其中,天道、阿修罗道、人道为三善道,饿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为三恶道。佛教认为“三界六道”中的各种生灵皆有寿限,寿尽依业力进入轮回,生死交替、因果循环、皆在六道之中。天道位于最高处,居六道之首,即世俗世界所说的天堂;左上方的是阿修罗道,亦称“非天”,阿修罗在佛经中是好战之神;右上方是人道,六道之中以人道为尊,因为人可以修行。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盛。左下方是畜生道,此道众生又愚又痴、碌碌奔命、为人驱使;右下方是饿鬼道,此道终生为自己的贪婪和憎恨所束缚,无论吃下多少都永不满足;最下面是地狱道,包括八热地狱、八寒地狱,是生前作恶之人受苦受难之地。
第四圈是佛陀十二因缘的形象体现,绘有盲人、瓦匠、猴、船、空宅、接吻、眼中箭、饮酒、稞、孕妇、临产、老人和死尸,分别代表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个部分,表示十二因缘,人生过程中任何生命在没有获得解脱之前都在这个过程中循环。
三、《六道轮回图》中的“人观”
人观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性命题,从外部而言,它是一种用于争论的学术研究单位;从内部着眼,它是人类行为能力的基础、自我理解的观念以及用以传达人类自我理解的表述方式。[11](P23-27)Grace Gredys Harris认为人观就是人主观上所认识的“个体(individual)”“自我(self)”和“社会人(person)”。①Grace Gredys Harris.Concepts of Individual,Self,and Person in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89(3)。转引自黄应贵:《人观、意义与社会》,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所1993年版,第1页。黄应贵从这三个维度进一步解释,“个体”指个人的生物层面,“自我”指个人对自己作为人而存在的经验,“社会人”指一个人在某一社会秩序中,被认为从事某一特定目的行为的创造者。②参见黄应贵:《人观、意义与社会》,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所1993年版,第1-8页。李笑频认为所谓人观,指的是一个民族或出生于其中的任何一位历史个体所持有的生命价值观念,对应于“物-人-心三元”,可以划分为自然观、社会观、自我观。[10]从这个意义上讲,人观研究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所处的世界的关系,与之相对应可以划分为自然观、自我观和社会观。《六道轮回图》以图像为载体呈现出人类学一直追问的哲学命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参禅,冥思苦想了七天七夜,思索解脱之道,终于超越了视听,超越了时空,觉悟到宇宙的一切真相,超越了一切痛苦烦恼。“六趣众生,轮回四生,循环三界,互相通达,这就是常说的‘六道轮回’”。[11](P310)用图像的方式表述出来就是六道轮回图,它以一个完整的意象暗示了人生的无常,预演了来世命运的种种可能性,看到了世代困扰和纠缠着人类的恐惧,传达了藏传佛教关于业力与因果报应的观念。[12]
(一)自我观:人与自身
在追问这个命题的时候,我们先要审思在藏传佛教哲学体系里“人是什么”。多识教授深入浅出地指出:人是由物质身躯和思想、感觉、行为、主体意识等五种成分(五蕴)组成的;人既不是单独的物质体,也不是纯精神体,而是物质肉体和精神识体的组合体;人的物质肉体和精神识体之间处于互相对立、相互依存、互不分离的对立统一状态;人死后只是粗分的物质和粗分的意识的分离,但细分色体和识体永不分离,作为不间断的生命种子续流,流转不息。[13](P10-13)这就是说人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物质的人在生死轮回之中,而精神的人一直存在,在六道之中穿梭、更迭、转化。所以我们常说:“活着就是一种修行”,其实是藏传佛教“诸法无我”自我观的一种体现。“无我”分为“人无我”和“法无我”,佛教通过提倡“无我”来消除对“我执”。《大智度论》卷二十二云:“一切法无我,诸法内无主、无作者、无知、无见、无生者、无造业者,一切法皆属因缘,属因缘故不自在,不自在故无我,我相不可得故。”③[日]《大正藏》第25册,第222页。
在《六道轮回图》中,鸽子、蛇、猪代表的贪、瞋、痴三毒被视为一切烦恼的根源,是“我执”,如果众生能做到“诸法无我”,则能摆脱诸烦恼、脱离苦海,成佛解脱。这种“无我”观深深地影响着藏族人的人生观乃至世界观。在藏族人的宗教生活里,每天煨桑、念经、诵佛、献供是必不可少的事情,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佛龛,甚至在家里修建佛堂。到寺院里转经筒、点酥油灯、磕长头也是日常生活中必须例行的头等大事,遇到重要的日子放生、吃素、朝圣更是每一个藏族人的信仰实践。佛教认为“三界犹如火宅”“轮回是苦”,称轮回为苦海,无幸福可言,若有幸福也是暂时的或相对的,轮回的生命没有真正的安乐。[7](P17)基于对生命轮回的认识,藏传佛教的信徒,不重今生,而重来世;不重物质,而重精神,认为今生受苦是为来世修福。这些身体实践都是藏传佛教因果说、因缘说、业力说教义的表征,煨桑、念经、诵佛、献供、转经筒、磕长头表示皈依三宝,不仅能愉悦精神、净化心灵,还能消净所积罪障,获得无量福报。
如今很多人去西藏旅游,有些人旅游程结束后就不愿离开,一待就是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些人或长或短地在西藏漂泊,被称为“藏飘”。他们大多是因为在现代都市中追求我的利益、我的地位、我的名誉等等“我执”而产生了爱恨情仇、荣辱得失等诸多烦恼。而在拉萨,藏族人都把追求精神的我放在第一位,物质的我无关紧要,只要能够维持生活,就不会执着地去追求名利。很多藏族人一生生活简朴,只要够吃、够穿就不再追求物质生活,而是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信仰,一步磕一个长头朝着神山、圣湖、佛塔朝拜。去过藏区的人肯定被他们虔诚的信仰所折服。在我走访过的藏区,经常见到很多人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但是他们仍然把供佛、朝圣当作有了积蓄之后首要的开支。在这种信仰和观念的影响下,“藏飘”放弃了自己原来富足的都市生活,而选择在西藏追求精神上丰富的自我。
(二)自然观:人与自然
人不是自然的主人,仅仅是自然的一员。藏传佛教以“普度众生”“利乐有情”为最高价值观,对一切生命表现出无限的慈爱和怜悯。即众生平等,自然界的一切动物、植物和人一样具有平等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权利。[7](P3)所以,要敬畏生命、敬畏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正如《六道轮回图》中所绘,人的一生可以分为十二个部分,都在“十二因缘”的过程当中,人生存的环境是由众生共同的业力和愿力所创造,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身边的一草一木、山川河流。因此,不但不能破坏我们生存的生态环境,也不能伤害飞禽走兽等一切有生命的生物,哪怕是不小心踩死了一只蚂蚁也会觉得是一种犯罪,要为它念经超度,以求赎罪。
藏族世世代代居住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恶劣,但是今天的青藏高原保持了最平衡的生态、最干净的蓝天和最纯净的湖泊。在原始宗教“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下,藏族人认为天有天神、山有山神、湖有湖神……世间万物皆有灵,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产生了神山崇拜、圣湖崇拜、土地崇拜、火崇拜等。在这些生态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十善法”,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嗔恚、不贪欲、不邪见。2015年是藏历木羊年,藏族一直有“羊年转湖祈福”的传统。在笔者转湖的过程中,环青海湖沿线蓝天、白云、油菜花拼接而成油画般的风景,随处可见“拉泽崇拜”,神山上随风飘扬的彩色经幡和飞舞的风马,沿着圣湖磕长头朝圣的信众用自己的身体丈量脚下的土地。还有很多藏族人自发组织的志愿者队伍在青海湖边捡游客丢弃的垃圾、捞掉到湖里的饮料瓶,这些身体的践行正是信仰的表征。
(三)社会观:人与社会
“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佛法认为宇宙是一个无限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存在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天体,我们生存在大千世界,在佛教里称为“婆娑世界”。宇宙没有绝对权威的主宰者,世间一切都是有生有死、变化无常的。佛教不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认为世间是上帝或真主创造的,而认为世界和生命是由五种因素构成的,即色、受、想、行、识五蕴。[11](P247)人是由五蕴相合而成,是类似于大宇宙的小宇宙,世界亦然。在生死轮第三圈中,人在六道之间循环,生而后死,死而后生,生生死死轮转不已。在藏族人的生死观中,死亡仅仅是此生的结束,并非生命的终结,身体的死亡是灵魂的重生,因为他们相信人是有灵魂的,生命是由灵魂所驱使的。在藏语里,身体被称为,意思是留下来的东西,今生受苦是为修得来生,今生在“人道”之中修行,是为能在来生轮回到天道或者阿修罗道。每次说的时候,像是在说“旅”,象征着今生就是一场旅行,身体只是一副皮囊,最后都要留下。“六道轮回说”深深地根植于藏族人心中,藏传佛教的信徒相信人有前世、今生和来世,如同车轮流转,今生只是生命轮回中的一站,并非生命的全部,生命在于轮回。
在十二因缘图中的最后一幅“老死”图中就画着一个背着死尸去天葬台的人,右边两只白鹤正在将身体分食,象征着死。藏族天葬的习俗就是把自己最后的皮囊奉献给秃鹫作为食物,为自己积最后的功德,可以投生到六道中最理想的境界。佛教认为:只有前世修行积善,转世后才会到天道、阿修罗道或者人道,反之,则会转世到饿鬼道、畜生道、地狱道。《观心本尊抄》中简洁地说:“数观他人之面,有时喜,有时瞋,有时平静,有时现贪,有时现痴,有时谄谀。瞋为地狱,贪为饿鬼,痴为畜生,谄谀为修罗,喜为天,平静为人。”[14](P44-45)这种葬仪被很多藏族选择并接受。基于藏传佛教《六道轮回图》中转世轮回的思想观念,众生虽然不能预知自己的来世,但是可以在图像中看到来世的六种命运,今生之所以受苦的原因,这就断除了我执和贪心,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
四、结语
《佛说六道伽陀经》中载:“归命一切佛,及诸菩萨众,愿开正智慧,忆念佛功德。归依三界尊,身口意三业,所作善不善,为彼作分别。彼人受果报,无有主宰者,三界天中尊,愿起于悲智,广为世间说,我今闻彼说。如依于轮回,观察业果报,佛说恶道因,贪嗔痴为本。若人行杀害,彼业随缠缚,决定堕等活,五百岁方出……由善得安乐,作恶获苦恼,老病死轮转,果报自如是。审观此三种,勿爱须舍弃,求福远离罪,了绝于色声,通达真实义,必至大解脱。”①[日]《大正藏》第17册,第452页。《六道轮回图》以图像为载体说明人类自古以来所追问的主题,以图说的方式呈现出人在世界的位置及其演变,把前世、今生和来世连接起来——我们从前世而来,今生在六道之中修行,生来就要受苦为前世赎罪,为来生积善,死后将再次进入轮回之中。众生的生存境界和宇宙的真实本相在图像中描绘的惟妙惟肖,像是一面明镜,启迪着众生。《六道轮回图》把天与地、生与死、因与果、前世与今生、欲望与禁忌、真实与虚幻、物质与精神、神圣与世俗等二元对立的元素统一在同一个世界中,生动形象地阐释出佛教“因果业报,转世轮回”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