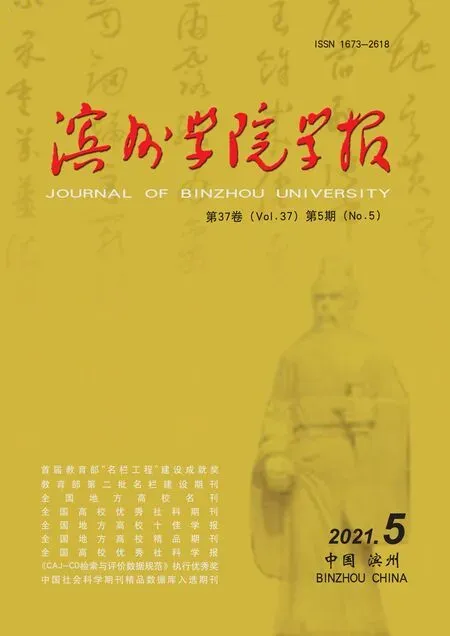功利理性:《吴子兵法》对传统兵学的推进与贡献
——兼论《吴子兵法》对《孙子兵法》的超越之处
姚振文
(滨州学院 孙子研究院,山东 滨州 256603)
吴起(?—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人,战国初年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与孙武并列立传,故后人多以“孙吴”并称。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法、儒三家思想,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均有极高的成就。
吴起是继孙武之后,既善于用兵同时又具有高深军事理论的著名军事家。然而,也许是《孙子兵法》(以下简称《孙子》)的光芒过于耀眼,以至于遮蔽了《吴子兵法》(以下简称《吴子》)在历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在大多数人看来,《吴子》只是中国无数兵书中的一部,充其量是《武经七书》中的一部经典,它的思想理论是远不能与《孙子》同日而语的。细而言之,《吴子》的成功之处只在于具体实践层面的战术思想,绝无像《孙子》那样的深邃的哲理与理论。苏洵尝言:“且吴起与武,一体之人也,皆著书言兵,世称之曰‘孙吴’。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词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然吴起始用于鲁,破齐,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复霸。而武之所为反如是,书之不足信也,固矣。”(《嘉祐集·权书·孙武》)苏洵认为,吴起在理论方面不如孙子,但在实践成就方面却是大大超过孙子,他以此说明兵书的不可信。
在笔者看来,仅仅以指导战争活动的实效性来概括吴子及其兵法的优势和价值,是远远不够的。《吴子》在战争观与治军两个重要层面的理论创建绝不亚于《孙子》,而在作战指导层面,吴子的论述虽然不如孙子那样系统而完善,但也有许多卓越见解和创新性的贡献,在某些方面也能超越孙子的认知。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吴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战争的规模、血腥及复杂程度已经大不同于孙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如果说孙子的战争观念还有前人“礼仪用兵”残留的浪漫成分,而在吴子的战争理念中,则是充分反映兵学本质的功利理性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功利理性是《吴子》一书的最大特色和价值,也是它推进传统兵学进而超越《孙子》的地方。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吴子》一书是战国时期诈力并行的社会风尚与吴子个人的智慧及强烈的功名欲望相融合的产物,因此,唯有以功利理性为核心,才能更好地审视它在中国兵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一、《吴子》较《孙子》思想更为突出的功利理性特色
有学者曾提出:“春秋兵学是先秦理性精神的主源头。”[1]这是因为战争活动最具有功利性(既可满足物质需求,也可满足荣誉需求),也最容易促进人类对自身现实活动的反思。比如,孙子不仅强调重战、慎战,而且公开倡导“兵以利动”“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火攻篇》)同时,为了实现战争活动的最大效益,他又大胆提出了“兵者诡道”原则,使原本扭曲的战争活动得以反正。这些都是孙子开启功利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
然而,春秋时代的军礼传统与贵族文化又使得孙子具有一定的浪漫主义气质。他虽然承认战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但同时又认为智谋可以化解一切困难和危险,《形篇》所谓“故其战胜不忒”,《地形篇》所谓“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谋攻篇》更有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境界。有学者曾指出:“与克劳塞维茨相比,孙子的战略主张表现出一种古典的优雅风度:在他那里,战争的主要内容是智谋,是理智的谋划与准备,是多种战略原则的艺术性运用……在颇大程度上,孙子兵法很难让人感觉到战争的暴力本性和其中的血腥、激情、仇恨和恐惧。”[2]
另外,孙子有著名的知胜思想,其在《谋攻篇》有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后在《地形篇》又谈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然而,孙子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隐含着一个悖论:我方“知彼知己”就能够“百战不殆”,那么对方也做到“知彼知己”的话,最后谁赢得了战争呢?很显然,这是智者的自信排斥了现实的理性,或言孙子对战争行为的活力对抗本质还缺乏深刻的体验和把握,这大概与春秋时期的战争比较温和、战场形势也没有那么复杂有关系。
然而,到吴子所在的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残酷和复杂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孙子的时代,动辄几十万人参战,决策者稍有不慎即有可能是覆军杀将、国破家亡。所以,吴子较之孙子对战争问题有着更为理性的认识:“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吴子·治兵》)
更何况吴子在性格上具有强烈的追求功名的欲望。他为了求仕可以散尽家财,为了学业可以母丧不归,为了被信任和重用可以杀妻求将,在道德层面留下骂名。然而,正是由于吴起这种强烈追求功名的欲望,使其能够理性对待战争问题,并始终以战争胜利或事业成功为根本目标,不为任何感情或道德所束缚,这是其功利理性的根本基础。
当然,更能够体现吴子功利理性精神的还是他兵书中的兵学思想和观点。论者比较《吴子》和《孙子》的差异,往往是强调前者注重战术,后者注重战略和哲理;前者以实效性见长,后者以理论性居优。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实事求是地讲,在兵学理论的建树方面,《吴子》在许多内容方面是超越《孙子》的。
比如,在战争观问题上,《吴子·图国》谈道:“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这与孙子的战争观一样,都是强调重战和慎战,然而吴起从文武关系的高度立论这一问题,并从仁义视角痛批非战的观念,这无疑是更为理性、成熟的战争观念。
再如,关于作战指导理论的问题,孙子的相关论述十分丰富,但核心的内容无非两个方面,一是“知彼知己”,二是“避实击虚”,前者是战争认知问题,后者是战争行动问题。而我们看《吴子·料敌》一篇的详细内容,无疑是紧紧抓住了这两个问题进行论述,正所谓“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简单的一句话,既是对知胜思想的高度认同,也是对避实击虚理论的极力推崇。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吴子从战场实践的角度,列举了遇到敌军时“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及“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吴子强调击虚过程中的关键是“知将”和“因变”,并逐步将“知胜”的范围扩展至士兵、地形、天时和整个军队的情况,深刻体现了战争谋略的多变性特点。“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
笔者的理解是,《孙子》对作战理论的论述固然提炼出了最基本的原则,也形成了丰富的内容体系。但《吴子》在某些方面的论述似乎更能直击要害,更具有操作性和实效性,但同时又不失理论性。这是其功利理性的又一突出表现。
在治军方面,吴子也有不同于孙子的真知灼见。如对于将帅的基本素质,孙子曾提出“智、信、仁、勇、严”的五条标准,并为后世所广泛认同。但吴子也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吴子·论将》)在这里,“文武兼备”是儒家的理念,“刚柔相济”是道家的主张,而对“勇”的特别论述又深刻体现了兵家的尚智意识,这是兵、儒、道三家思想融合基础上的将帅观。为了突出将帅素养的实践性、理智性要求,吴起还特别论述了“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吴子·论将》)
在军队管理方面,吴起同样是立足于兵家功利理性的视角,提出了许多超越《孙子》的观念和理论。比如,他的训练士兵的方法是特别实际而有效的,“故用兵之法:教戎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吴子·治兵》)
更值得注意的是,吴子还提出了简募精良、量才专用的思想。“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踰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吴子·图国》)如此选用的好处是,使士兵各尽专能,发挥优势,成为“军之练锐”,进而做到“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这说明,吴起已经具有培养特种部队的先进意识,其比孙子的选锋用锐思想更为全面、深刻。而且,在此基础上,他又依据“人情之理”提出训练“死士”的主张。“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忌其暴起而害己。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吴子·励士》)
吴子对军之“练锐”与“死士”问题特别重视,说明他对实际战争实践中两军的博弈之道有着深刻的体验和认识。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双方各有自己的进攻与防守策略,也各有自己的防御体系。一方若想通过进攻而取胜,最关键的是要通过“选锋用锐”,攻陷对方防御中的枢纽与核心,进而突破(或撕破)对方整个的防御体系。
在战争实践中,吴起正是以上述思想为基础,创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魏武卒。《荀子·议兵篇》云:“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很明显,这样的装备和速度都是在挑战人的极限。问题是如何保证他们自觉主动地战斗呢?“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也就是说,国家既要赐给他们田宅,又要免除他们的徭役,即使年老力衰之时,他们的福利也要保留。可见,吴子是基于对人性的把握而构建他的建军思想,这显然又是建立在功利理性的基础之上。
分析至此,我们就能够明白吴起何以能取得显赫的战功,缔造不败的神话。前389年,秦惠公出兵五十万攻打魏国的阴晋。吴起亲率五万魏武卒,外加战车五百辆、骑兵三千大败秦军。另外,《吴子·图国》中也记载了吴起在魏国的显赫功绩:“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二、吴起对儒家仁德的重视亦是其功利理性的突出表现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亦谈道:“彼孙、吴者,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暴乱昏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
在上述两个史料中,司马迁与班固都是从儒家道德伦理的视角,对吴起提出批判和指责的。事实上,吴起的功利理性并不排斥儒家的仁德观念,相反,它恰恰是吴起功利理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起接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他在离家游学之初,师从曾参之子曾申,后又从子夏受业,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其母丧不归、被逐儒门就怀疑其深刻的儒家教育背景,也不能因为其杀妻求将之道德恶行而认定其抛弃儒学。吴起初到魏国之时,就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向魏文侯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基本国策。这是吴起政治观点和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治国理念之兵儒融合的深刻体现。
在战争原因和战争性质问题上,吴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孙武的缺陷,他已经注意到了战争发生的根源及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所谓“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吴子·图国》)在这五种战争中,只有“义兵”是正义的战争,而其他几种都是非正义的战争,而吴子是最推崇义兵的,他与孟子、荀子一样,都强调“义兵至上”的战争观念,并与儒家之道、礼、仁等观念结合在一起。《吴子·图国》有言:“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
在战争制胜因素的问题上,《孙子》提出了“道胜”的概念,什么是“道”呢?孙子解释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而《吴子》则具体明确地提出了道、义、礼、仁“四德”的概念。而且,当魏武侯问及战争制胜的基本条件时,吴起回答说:“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吴子·图国》)
基于战争的暴力性和破坏性,孙子有著名的全胜思想,所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而吴子在《图国》篇中明确指出:“然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这样的论述较之孙子的主张,应该是更为深刻,更能促进人们对战争问题的反思。
吴子还提出了著名的“在德不在险”的著名论点。《战国策·魏策一》有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睾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
从这段话的基本内容看,吴起意在用“三苗氏、夏桀、商纣王不修德政而国破身亡”的历史教训,以告诫魏武侯要广修善政。西汉之杨雄曾因此高度评价吴起说:“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则太公何以加诸!”[3]366
总之,吴起在他的著作中,无论是论及治国之总纲还是谈论用兵之要领,均能袭用儒家“仁”“义”“礼”“德”等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以阐释自己的思想主张。事实上,在其治军用兵实践中,吴起也能从内心深处认同并肯定儒家思想对战争的指导作用,并能主动而自觉地将兵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融为一体。古人也因此认识到了《吴子》与《孙子》在这方面的差异:“起之书几乎正,武之书一乎奇。起之书尚礼仪、明教训,或有得于《司马法》者;武则一切战国驰骋战争也,谋逞诈之行耳。”[4]68“《吴子》之正,《孙子》之奇,兵法尽在是矣。”[5]16也正因如此,黄朴民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吴子》一书,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中国历史上‘兵儒合流’文化现象的滥觞。”[6]
值得强调的是,吴起在军事领域对儒家学说的认知和应用,较之孔、孟、荀的军事思想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孔、孟、荀而言,仁德是其思想理论(包括军事思想)的核心与根基。而且从孔子至孟子,其仁德观念始终是建立在政治理想层面,荀子虽然比较现实,但实际上也是将仁德的观念凌驾于现实之上。然而,吴起的仁德思想却是与战争功利密切结合,是建立在功利理性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兵儒两家在战争思想领域最大的区别所在。可以举一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案例予以深入分析。“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在这个案例中,吴起与士卒同甘苦的典型事迹确实令人感动,然而士兵母亲大哭的反常举动也令人不能不深刻反思这一问题。在笔者看来,吴起对儒家仁德的重视,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了义兵观念在聚集民众、凝聚民心、提高战力方面的突出作用,故而其功利性目的应该占主导地位,这符合他具有强烈建功立业欲望的性格特征,亦是其功利理性的突出表现。如前所述,司马迁曾指责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事实上,吴起所言与所行的背离是由当时政治军事活动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它恰恰是吴起本人功利理性的集中体现。
三、吴起“以法治军”及法家思想观念更集中体现了功利理性
中国自古就有“以法治军”的传统。孙武“演兵斩美姬”的故事充分证明了其内心“以法治军”的观念。他在《计篇》中将“法”视为庙算分析的“五事”之一,并在《形篇》中特别强调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正。”另外,孙子对军法阐释最直接的乃是《军争篇》的一段文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
然而,在笔者看来,如果比较《孙子》中的“人治”与“法治”的话,孙子应该是更重视“人治”。因为在孙子的观念里,“将”的作用应该是远大于“法”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孙子著述兵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求仕,他要向吴王展示自己的为将才能,并要特别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所以,读《孙子》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孙子在论述中时时会指向有关将帅的问题,这几乎体现于十三篇的所有篇章之中。
比较而言,吴子则是更旗帜鲜明地倡导“以法治军”的地位和作用。
在《吴子·治兵》中,当武侯问及“兵何以为胜”的根本问题时,吴起明确回答道:“以治为胜”,又问:“不在众寡?”,吴起则有了以下深刻的逻辑分析:“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吴子·治兵》)
在《吴子·应变》中,武侯又问及一个实战中的问题:“我军突遇强敌,士兵慌乱怎么办?”吴起仍然是立足于军法以破解困境。他说:“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摩左而左,摩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今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陈矣。”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吴子》重法的“杀气”。
在《吴子·励士》中,更有这样一段主旨鲜明的文字:“先战一日,吴起令三军曰:‘诸吏士当从受敌。车骑与徒,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故战之日,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这明确阐释了战争中“军令第一、服从至上”的基本原则,此种观念还可以从《尉缭子·武议》中得到佐证。“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谏曰:‘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曰:‘材则是也,非吾令也,斩之。’”
细读《吴子》,会发现类似上述“严明军纪”“以法治军”的文字随处可见。比如,“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败”“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吴子·治兵》),“不从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吴子·应变》);“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将之所摩,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矣”(《吴子·论将》)。
当然,吴子也不是视“法”为唯一的制胜因素。在《吴子·励士》中,武侯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严刑明赏,足以胜乎?”吴起的回答是:“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可见,吴子并不认为“严刑明罚”是治军的唯一手段,关键是要顺应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让士兵自觉主动地“乐闻”“乐战”“乐死”(更符合功利理性)。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实施最高层次的精神奖励。《吴子·励士》有言:“于是武侯设坐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减;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飨毕而出,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有死事之家,岁使使者劳赐其父母,著不忘于心。”
总之,《吴子》中对“以法治军”的提倡和推崇,是其功利理性的一个更集中的体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吴子作为著名兵家的同时,还是当时杰出的改革家和法家,这种身份更容易使他将当时的时代精神和法家思想观念灌输到兵家的思想理论之中,进而为功利理性精神提供更多有益的思想成分。
吴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法家作为主流学派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它和兵家都代表了当时生机勃勃的新兴势力,都充满着进取、刚健、自信、战斗的精神,都要为新的社会秩序开辟道路。更重要的是,兵家以现实功利为其主要的价值追求,而法家在这一方面比兵家还要现实和理性,所谓“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韩非子·备内》);“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韩非子·奸劫弑臣》)。以至于有学者论言:“韩非把一切都浸入冷冰冰的利害关系的计量中,把社会的一切秩序、价值、关系,人们一切行为、思想、观念以至情感本身,都还原为归结为冷酷的个人利害。”[7]就此而言,法家思想比之兵家思想更代表了战国时期崇尚进取和诈力的时代精神,也可以说法家在价值观的层面为兵家提供了一个功利主义的文化土壤。
吴起在功利理性方面超越孙子的优势,正在于他既是杰出的兵家,同时又是法家的杰出代表,并在当时的改革变法大潮中做出突出贡献。吴起在魏国担任西河郡守之时,就能修明政治,取信于民,并在军事上实行募兵制。而吴起在楚国的变革成就,更是轰轰烈烈。《史记·蔡泽列传》中有云:“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范雎亦评论说:“吴起事悼王,使死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图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战国策·蔡泽见逐于赵》)
《吕氏春秋·慎小篇》还记载了吴起立信的一段故事,这个故事不仅证明了吴起的法家作风,而且说明商鞅之“徙木示信”大概是效仿吴起。“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有人能偾表者,仕之长大夫。’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起仕之长大夫。自是之后,民信起之赏罚。”
总之,吴起的法家身份和法家观念,使兵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在现实功利层面达到了最深层次的精神契合,这也使得《吴子》一书更集中体现了兵家的功利理性精神。
四、结论
吴起与孙子在中国兵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应该是各有千秋。孙子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哲理基础,以兵者诡道理论为核心,以全胜为最高境界,构建了中国兵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兵学思想体系,其首建之功自当荣享“兵圣”之盛誉。吴起作为孙子之后继起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兵家亚圣),在战争观和治军层面的思想主张应该是不亚于孙子,而吴起独特的身份使《吴子》在兵儒、兵法融合方面的成就自然也不逊于《孙子》。更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兵家的功利理性精神是先秦哲学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吴子身处崇尚功利的战国时代,加之他的个人智慧及过强的名利欲望,故其在功利理性层面的执着追求,不仅推动了传统兵学的发展,也在这一层面大大超越了《孙子》思想。
从中国兵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古人(尤其是儒家文人)之所以有所忽略或贬视吴子的思想成就(事实上也影响了今人),大概与其“母丧不归”及“杀妻求将”的道德劣行有关。吴起是在战国时代兼并与统一的血雨腥风中涌现出的历史人物,吴起道德人生的失败固然是其追求个人功名的偏执性格所致,但更主要的是与当时战乱条件下私欲充斥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有关。因而,我们应该从兵学或兵家的独特视角(而非儒家的道德视角),重新认识吴子及其兵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功利理性恰恰是最能体现兵家思想本质的重要标志之一。事实上,孙子之所以被誉为兵圣,不也是因为其能够从功利理性出发,创新提出了“兵者诡道”的战争指导规律吗?
——刘家文
——徐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