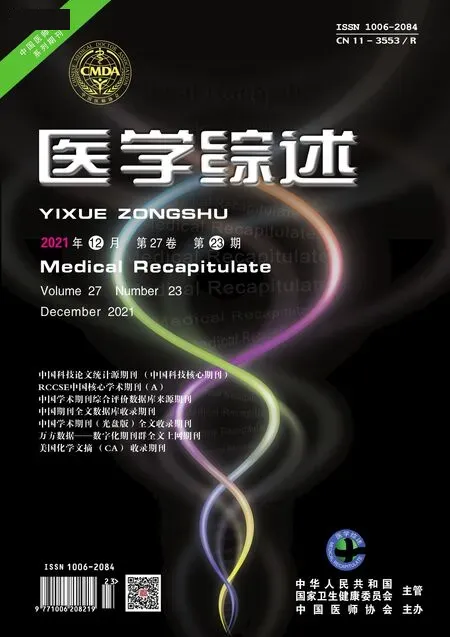缺血性适应在心血管外科的临床研究进展
蒋钦,魏大闯,黄克力,胡盛寿
(1.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脏外科,成都 610072; 2.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外科,北京 100037)
冠心病是当今成年人群常见罹患病种之一。现代医学的快速就医、急诊介入手术和抗血栓药物的治疗大大提高了急性心肌梗死的早期预后。心肌梗死治疗的关键是降低缺血再灌注损伤,后者直接影响心肌梗死的面积、心肌梗死后心力衰竭的进展[1]。与其相似的是,心脏外科体外循环手术患者的心肌同样经历了缺血与再灌注,此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缺血再灌注损伤。缺血再灌注损伤可产生多种病理生理性反应,目前尚无特异性药物。缺血性适应是由组织或器官间断、重复、短暂的缺血诱发的神经、体液改变,可对严重缺血再灌注损伤产生一定保护作用的内源性机制。缺血性适应不仅对心脏产生降低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还可对脑、肝、肾等重要器官产生类似作用。自从发现缺血性适应减轻再灌注损伤现象已有30余年,不仅其作用效应在多个物种相继得到证实,其分子机制逐步得到阐明,而且其应用亚学科范畴也不断得到拓展[1]。现综述缺血性适应在心血管外科各疾病领域的应用状况,分析化解临床转化应用难题的办法,探索缺血性适应临床研究的潜在方向。
1 缺血性适应临床应用现状
缺血性适应具有简便、安全、可重复应用等优点,是目前最有发展前景的心肌保护策略[1]。根据施行缺血时间与严重缺血的时间次序,分为预适应、间适应和后适应,预适应主要用于预防性减轻损伤(如心脏外科手术),间适应和后适应主要用于已发生缺血的补救性减轻再灌注损伤(如冠状动脉介入手术)。根据施行缺血性适应的组织的位置分为原位缺血性适应和远程缺血性适应。无论以上哪种分类,基础研究均表明缺血性适应可降低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2],但临床转化应用均有不同程度的困难[3]。
1.1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 有研究采用上臂施行4个周期5 min间断缺血的远程缺血预适应(remote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RIPC),结果显示,未有明显的临床指标改善效应[4-5],其纳入对象均为体外循环下手术的后天性心脏病患者。在静脉使用丙泊酚行择期体外循环手术时,RIPC不影响术后心肌酶水平、呼吸机辅助时间、重症监护病房停留及住院时间[4]。在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和附加心脏瓣膜手术未采用标准化麻醉和术后监护方案时,RIPC不能改变心肌酶水平、正性肌力药物使用量、重症监护病房及医院住院时间、6 min步行距离和生活质量评分[5]。研究显示,丙泊酚[6]和异氟烷[7]等麻醉药物能影响体液保护因子释放[8],β受体阻滞剂[9]可覆盖RIPC的作用效应,心血管合并疾病[10]和高脂血症[11]等混杂因素也可影响研究结果。虽然RIPC在冠心病体外循环手术下不能改善主动脉球囊反搏装置使用率等临床指标[12],但仍是一项临床应用安全的方法。一项心肌梗死患者的血栓性状态研究显示,RIPC不能显著改变凝血和纤维蛋白溶解功能,但可以降低心肌梗死后早期血小板反应性[13],该研究提示RIPC考虑用于冠心病旁路移植术降低血小板反应性,有利于增加桥血管的通畅率。另一种缺血性适应方案是缺血后适应,研究显示相比于术后直接开放升主动脉灌注,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通过3个周期(1 min/次)的阻断开放(缺血后适应)可以改善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所见的左心室射血分数,减少房室性心律失常发生[14]。
1.2心脏瓣膜手术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两大临床试验已纳入部分合并心脏瓣膜手术患者,结果表明在重要临床指标方面未显示RIPC的效用,但在排除冠心病的心脏瓣膜手术患者RIPC的效用在大多数其他研究中已得到证实[4-5]。研究显示,在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应用RIPC可降低术后心肌酶水平和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时间,以及肺损伤、肝损伤,炎症氧化损伤反应的发生[15-16],另一研究显示,术后早期多次使用缺血性适应不能降低心脏瓣膜术后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17],说明瓣膜手术应用RIPC对重要脏器的保护作用有明显差异。经皮主动脉瓣置换术后患者的心肌酶水平显示升高,使用两种不同类型的介入瓣膜手术患者开展RIPC研究,结果提示RIPC在两种介入瓣膜手术中均不能改善心肌酶和生存指标[18]。目前,在体外循环下行微创瓣膜外科手术开展缺血性适应的研究报道少见,如全胸腔镜下二尖瓣成形或置换手术[19]。一项回顾性研究提示,全胸腔镜下二尖瓣手术相比于常规正中切口入路术后心肌损伤标志物及炎症反应指标有所降低,是否是外周动脉插管诱导RIPC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20]。
1.3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 成年心脏病患者可能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影响心肌的基础血流及储备能力,而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多无冠状动脉问题。最早的RIPC临床研究对象即是先天性房室间隔缺损患者,样本数量也只有37例。研究结果显示RIPC效果微弱,但心肌酶水平、正性肌力药物术后支持使用量较对照组明显降低,由此看到了RIPC的临床转化效应方面的希望[21]。另一项研究显示,RIPC及缺血后适应对减轻室间隔缺损手术患者的心肌酶具有同等的保护作用[22]。RIPC可降低法洛四联症(tetralogy of Fallot,TOF)手术患者的心肌酶水平,减少呼吸机通气时间,说明发绀缺血缺氧并不能消除RIPC的影响[23]。另有研究表明,TOF手术患者心肌蛋白磷酸化水平比较高,RIPC不能改善心肌和白细胞蛋白磷酸化水平,预示RIPC不能改善TOF患者该项心肌能量代谢指标[24]。而另一项拟纳入120例TOF或室间隔缺损手术患者,开展双侧下肢RIPC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之中,以用于验证加强RIPC是否可以减轻发绀性或非发绀性患儿心脏的手术损伤[25]。
1.4心律失常外科手术 一项包括老年人健康受试者的研究表明,RIPC可以增加心率变异性、减低交感神经张力反射[26],表明RIPC应用在表现为以交感神经亢进、迷走神经削弱的心房颤动患者具有理论依据。研究显示,RIPC可降低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射频消融术后的复发率[27]。一项关于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的研究显示,RIPC可以降低术后心房颤动发生率,并可调控心律失常相关的微RNA表达[28]。而大样本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为主的临床研究,并未表明RIPC可以降低术后心房颤动发生率[4]。因此,有待针对冠心病手术患者开展RIPC随机对照研究,研究RIPC对术后心房颤动发生率的影响,并明确可能干扰RIPC作用于心房颤动转复的合并症、术式、麻醉方案等情况。风湿性二尖瓣疾病罹患永久性心房颤动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中显示RIPC可增加射频消融手术后心房颤动转复窦性心律的成功率[29]。
1.5血管外科手术 超过20%的血管外科手术(腹主动脉瘤、下肢动脉栓塞和颈动脉狭窄)可导致心肌酶升高,而应用RIPC不能降低此类患者心肌酶升高的发生率,也不能降低心肌酶升高的峰值[30]。另一项临床研究表明,RIPC可以降低行血管外科手术患者的心肌酶和B型脑钠肽的水平[31]。胸腹主动脉替换术通常需要停循环完成血管吻合手术,停循环期间多采用深低温作为神经保护措施,而长时间低温低灌注状态可导致脊髓神经永久性损伤等严重并发症。研究表明缺血预适应和缺血后适应均可减轻脊髓神经损伤[32],RIPC可保护由胸腹主动脉手术停循环导致的腹腔脏器缺血再灌注损伤[33]。
1.6心脏移植手术 由于以脑死亡为标准选择心脏移植供体导致供体严重短缺,因而循环死亡已形成心脏移植供体的实施标准。循环死亡的供体心脏均会经历循环停滞[收缩压<50 mmHg(1 mmHg=0.133 kPa)]的热缺血过程,此过程的时长是决定供体功能状况的主要指标[34]。为最大化恢复心脏功能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常在获取心脏后通过离体心脏灌注装置灌注心脏停搏液。缺血后适应可以减少移植心脏超氧化物的生成,产生像丙酮酸盐一样对心脏起到保护效果[35]。移植手术的供体心脏不受患者的自主神经支配,因此接受移植手术的心脏供体天然遭受了缺血再灌注损伤过程,这种特殊模式不仅可用于检验RIPC的作用效果,还能用于求证RIPC的作用机制。由于供体心脏与受体内自主神经无直接联系,供体心脏在应用RIPC后便只能反映受体体液因素的作用。研究显示,在接受心脏移植的受体术前及术中应用缺血性适应可以降低再灌注后6 h的心肌酶水平,但不能改善患者住院期间的其他临床指标[36]。
1.7细胞移植外科手术 缺血性预适应可以产生两个间隔时相的保护期,其中第一时相发生在预适应应用后大概是30 min,主要是通过分泌的小分子保护性物质起保护作用,如腺苷等;第二相发生在大概24 h后,主要作用基础是通过转录合成一些有保护缺血的小分子量蛋白[2-3]。有研究表明,第二时相合成的小分子蛋白可能与募集骨髓干细胞到缺血区域参与修复有关[37]。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联合经桥血管移植骨髓细胞治疗可改善心肌梗死合并心力衰竭患者术后的心脏收缩功能和6 min步行距离[38]。缺血性适应可以增加急性心肌缺血大鼠模型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移植效率[39],提高慢性缺血心肌的基质细胞衍化因子1的表达水平[40]。在心肌梗死模型开展细胞移植实验结果显示,缺血性适应可改变移植细胞在受体实体脏器中的分布比例[41],增加移植细胞在缺血心脏中的留置率,改善心肌远期收缩功能[42]。因此,对冠心病行骨髓细胞移植的患者开展RIPC的临床试验值得期待。
1.8心室辅助外科手术 通常RIPC的临床试验方案采用骨骼肌组织缺血。衰竭的心肌组织消耗更多的酮和乳酸,蛋白质水解率更高[43]。研究表明,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应用RIPC,虽不能改善患者的心脏收缩功能,但可降低患者体内的N端脑钠肽,增强骨骼肌功能,降低收缩压[44],提示RIPC可以调节心力衰竭患者的心肌-骨骼肌能量底物代谢,并调节其神经张力。迄今虽无缺血性适应在心室辅助方面的临床研究,但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行心肌再灌注治疗中,通过左心室卸负荷治疗30 min后再开通血管研究,观察此方法无不安全现象发生,说明减轻心室壁张力可以抵消缺血时间延长带来的不利影响[45]。接受心室辅助装置的心力衰竭患者通常室壁张力和交感神经张力较高[46],心室辅助可以通过卸负荷减轻心肌机械性张力。RIPC理论上可用于调节神经张力重塑结构方面改善远期预后。因此,RIPC在心室辅助方面的应用仍待尝试。
2 临床转化中的干扰因素
缺血性适应应用在心脏外科手术中所遇到的转化效应挑战,通常认为是高龄、合并症、药物等因素,加之不甚合理的试验设计综合所致[47]。缺血性适应根据其应用时相分为预适应、间适应和后适应,尽管三者在动物实验中都有证实其效用,而临床试验并未完全显示其功效。可能因为纳入的研究对象已存在冠状动脉缺血,且其病程时长、严重程度、生活环境及生活地域[48]等因素均可干扰其临床效应。部分患者还可能并发心力衰竭,这与正常群体存在心肌能量底物代谢方面的差异。心力衰竭患者的心肌-骨骼肌能量代谢平衡改变也可影响缺血性适应的效果。此外,缺血性适应的临床应用仍缺乏一个固定的范式,如血管加压带的缺血区域位置选择[49]、重复数量、单个周期时长等应用问题。另外,社会经济学因素也是影响缺血性适应的重要方面,研究显示,发达国家首次就医的冠心病患者的病变狭窄程度通常低于贫困地区[50]。因此,国内城乡之间、医疗资源技术的地区差异也可导致RIPC的作用效应呈现差异。鉴于缺血性适应的安全实用性,重复多次实施RIPC的临床效应也有待研究证实。
3 小 结
缺血性适应是一种安全且潜在有效的机械性心脏保护技术。目前缺血性适应在心血管外科临床的应用量较小,但其应用领域仍在不断扩展。缺血性适应在多种疾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与临床转化蓝图仍有较大差距,通过甄别生活方式、合并疾病、药物治疗及手术麻醉方案的交互影响,不断深入阐明其分子作用机制,筛选有益于开展缺血性适应的特定人群仍意义重大。当以改善心肌酶学指标为意义的传统观点遇到瓶颈时,将研究终点事件转向以血流动力学改变、心脏重构等指标改善时,研究缺血性适应仍将是一项值得深究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