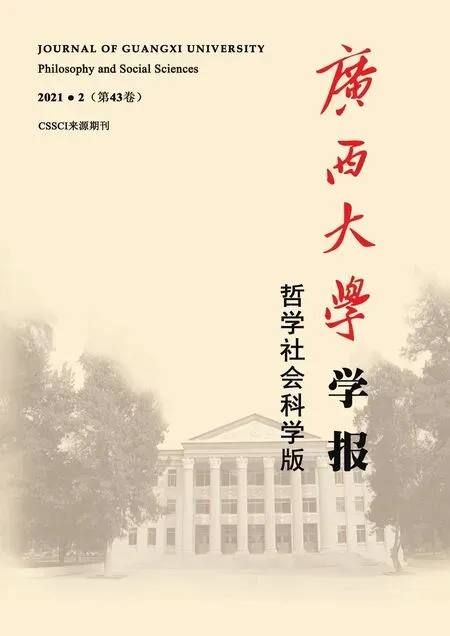图根特哈特对自身意识理论的循环困境的克服
胡文迪
在传统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中,“自身意识”是一个重要论题,它涉及认识的绝对自明性。笛卡尔和胡塞尔都将这种自明性视为知识的基础。但自身意识本身却面临着循环困境。简言之,这一循环困境指的是:首先,在自身意识活动中,已预设了活动主体,而这个主体却是自身意识需要认识的对象;其次,自身意识是回返到自身的认识活动,所以预设了认识行为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同一性,然而除非已经具有关于自身的认识,否则无法做出这一确认①关于自身意识之循环困境的具体讨论请参考:倪梁康.自识与反思(2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张任之.论胡塞尔现象学中自身意识的反思模式[J].世界哲学,2015(1):72–84;郑辟瑞.亨利希与图根特哈特的自身意识之争[J].现代哲学.2010(1):94–100。。
一、图根特哈特对自身意识的理解
图根特哈特把传统自身意识理论的认识模式均归为主客模式,并将这种模式表述为表象模式,“z”表象“x”在对这种表象模式的批判中,图根特哈特把矛头指向了海德堡学派②对海德堡学派的介绍可参考:倪梁康.自识与反思(2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655–656。。海德堡学派根据已有的相关讨论,认为自身意识陷入循环困境的原因在于“反思理论”③关于“海德堡学派”的自身意识理论,除了图根特哈特的说明,还可参考“海德堡学派”诸成员的著作和文章,如:Dieter Henrich.Self -consciousness,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A Theory[J].Man and World,1971(4):3–28;Fichte’s Original Insight[J].trans.by David R.Lachterman.Contemporary German Philosophy,1982(1):15–53;Manfred Frank.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knowledge:On Some Difficulties with the Reduction of Subjectivity[J].transl.by Bruce Matthews.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Critical and Social Philosophy,2014:2;迪特·亨利希、费希特的“自我”[J].郑辟瑞,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8(2):21–29;曼弗雷德·弗兰克.个体的不可消逝性[M].先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并在这一理论下拒绝了“x ≠z”的形式,接受了“x=z”的形式,也就是表象者与被表象者是同一个。当“x=z=自我”时,海德堡学派采纳了费希特的自身意识理论;之后,他们意识到费希特的自身意识理论仍有可能陷入循环,转而使用“x=z=意识”的模式——这时他们诉诸的哲学家是布伦塔诺——并提出“自身亲熟”这个概念[1]39-54。然而,在图根特哈特看来,无论x、z 指的是意识还是自我,都会导致循环困境。因此,要想最终克服循环困境,就不能再以这种模式讨论自身意识,而目前剩下的一种可能便是从语言分析哲学的角度来讨论自身意识。
对此,图根特哈特首先分析了“意识”这个概念。
根据弗洛伊德和胡塞尔对意识的不同定义,图根特哈特给出了一个相对宽泛的意识概念:“如果其状态是有意识的存在者拥有或者能够拥有对这个状态的直接知识,那么这个状态就是有意识的”[1]6①笔者认为,图根特哈特给出的这个定义已经是最初意义上的自身意识,因为这是意识对自身的意识到。可是图根特哈特并没有对此继续讨论下去,这实际上与他对自身意识的理解有关。。然而,这一纯定义并不能说明“自身意识”,因此需要从意识概念过渡到自身意识概念。为了实现这一过渡,图根特哈特借助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五研究”中“意向性”概念,即“意识总是朝向某物的意识”。不过,他认为“意向性”这个表达是一个比喻。因为在日常语言中,朝向某物总是意味着朝向时空中的客体,如果取消了客体的时空性质,客体就无法被看到。在他看来,这是传统的“看”的思维模式(即表象模式),这种“看”的模式会导致自身意识的无限回退。
所以,尽管“意向性”的说法是可以借用的,但是却不能以“看”的模式来建立意识关系。此外,“意向性”这一概念也不是通过朝向主体之内的“看”获得的,而是来自人类的语言结构。因此,意识、对某物的意识、自身意识等概念的含义都只能通过分析这些概念的使用来获得。
在语言表达中,与“意向性”相对应的是及物动词。及物动词的用法是:它须有宾语补充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这个宾语,是名词或名词化的句子,可以是日常所见的、处于时空中的实体,也可以是事态或处于某种状态中的事物。在简单断言句中,这一事态可被表达为“P”,比如“今天在下雨”(P)。然后可将其转化为名词化的句子,以“That P”的形式被表达出来。由此,简单的断言句“P”被名词化为“That P”,这个名词化的表达可以被当作陈述句的主语,也可以是被意指的客体。根据图根特哈特的看法,它在胡塞尔那里被称为“事态”,在语言表达中被称作“命题”(proposition)。当它做及物动词的宾语时,指的就不再是时空对象。这时意向性意识可被看作“命题态度”,即朝向命题或事态的态度(position)。由此可得出语言分析中“意向性意识”的含义:所有意向性意识都是命题性意识,或命题态度。图根特哈特说,“‘意向意识’所标示的这类关系通过以下方式区别于其他关系:这类关系是一个时空实体——一个人——与一个命题的关系,或者包含这种关系”[1]12。
把对“That P”(事态)的语言模式应用到“自身意识”,就成为“对我的某种状态的意识”。这种自身意识类似于对某个事态的意识,因此可以理解为一个人与一个命题“我φ”之间的知识关系。所以,自身意识就是“我对我自身的意识”,而“我对我自身的意识”就是“我对我自身的知识”,即“我知道,我φ”。因此,自身意识就是自身知识。
二、自身意识与自身知识
自身意识被表述为“我知道,我φ”,这是非中介的(immediate)自身意识。对这种非中介的“知”而言,人们不能问“我”如何知道“我φ”。因为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预设了回答模式,即传统的表象模式。在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的时候,是从认知的角度来提问的,回答模式则是“通过看/观察”。然而对于“φ”这种与个人自身有关的感觉或状态,它并不像“我”通过照镜子看见“我的眼眸是棕色的”那样,可以通过外观察直接看到。不仅不是通过外观察,也不是通过内观察看到我的“意识”的,比如通过“精神之眼”。
在对自身意识的讨论中,很容易陷入“内观察”的说法中。关于“内观察”,图根特哈特参照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批判来驳斥这一说法。
私人语言理论的错误在于预设了“φ”状态是可以内在地观察到的客体,并试图以这种方式说明“φ”这个词的含义。可是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个语词的含义在于它的使用方式。所以,“φ”的含义不在于指涉某种内在对象,而是它的使用方式,这种使用方式不是也不可能是私人性质的。所以,当使用“φ”这一表达时,它能被他人理解,并不存在任何只能为说者自己所知的“φ”状态②关于私人语言的讨论,除了Tugendhat,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determination(图根特哈特的《自身意识与自身规定》)[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6.“第五章”的讨论以外,还可参考: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论直觉材料与私人语言[M].江怡,译;张敦敏,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否定了私人语言,也就否定了与之相关的内观察。那么便不能就“我知道,我φ”提问“我是如何知道它的?”。既如此,该如何理解在“我知道,我φ”中表达的自身意识呢?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语词是怎样指涉感觉的?”[2]①尤其参考251、256条目。图根特哈特认为,当一个人处于某种状态,尤其是“φ”状态时,他就非中介地(immediately)知道自己处于这种状态,并能够说出“我φ”。所以,人们非中介地“知道”并表达出“我φ”②要注意这里的知道还并不是知识意义上的“知道”。。
图根特哈特在此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做法,没有把“我知道,我φ”当作认知性表达,而只当作表达性表达(expressive expression)[1]106③关于这个说法,还可参考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语词如何指涉感觉”的讨论。,这个表达性表达此时还不是知识,“说我者”处于φ 状态时,就会直接表达为“我φ”④图根特哈特认为“我φ”是一个表达性表达的说明,关于这一点的理解,还可参考:郑辟瑞.直观与语言分析——重温图根德哈特对胡塞尔的批判[J].浙江学刊,2008(5):34-40.。
关于“φ”状态的表达,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最简单的“自然表达”,每个人天生就会,比如疼的时候,就会哭。第二种是习惯性表达,受传统习俗制约,比如疼的时候,在英语中,相应地会喊“Ouch”,在汉语中,会叫一声“哎呦”;此外,还有肢体语言,比如耸肩。第三种表达是语言文字式表达,是通过学习获得的,比如疼的时候,会说“我疼”。维特根斯坦说,当教一个孩子在疼的时候说“我疼”,“他们教会了这个孩子一个新的疼的举止”[1]84,[2]。这个“新的疼的举止”代替了自然表达“哭”,所以虽然它是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它不是知识。显然,“我φ”属于第三种情况,它代替了对“我φ”状态的自然表达。因此似乎它只是一个表达性的表达,还不足以成为知识。
“我φ”是表达性表达,因此,对“我知道,我φ”在非中介的意义上提问“我是如何知道的”是荒谬的。这样的提问只在知识表达中才有意义。“我知道,我φ”就像疼的时候会哭一般自然⑤“鸟”与“疼”显然是两类不同的对象。我在这里使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例子,是想要说明“我知道,我φ”这个表达性的自身意识的非中介性,它就像“我看到天上飞过一只鸟”一样直观。。对于“我φ”,人们是非中介地知道、直接表达出来的。
另外,还要注意这里的“非中介的”(immediate)一词,图根特哈特将它同“直接地”(directly)相区分。“直接地”毕竟还有所凭借,比如在一般的认知性表达中,当问到“你是怎么知道有一只鸟飞过”时,人们可以回答“我看到的”,这是直接地知道。不过这仍是凭借眼睛看到的,还有所“中介”(mediate)。但继续追问“你怎么知道你看到了一只鸟飞过”,就没有意义了。当然,图根特哈特考虑到可能会有的反驳:无论在“我φ”句子中,还是在行为表达中,在这些句子中,我们具有的只是感觉的表达,而不是感觉本身。他反问道:“感觉本身是什么,关于这你所具有的是什么概念呢?当然,在感觉和感觉的表达之间存在着区别。但感觉可以如何在语言上被表达呢?让我们假设这一不可能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内在地观察到感觉;难道与感觉的表达相比,通过在一个对感觉的观察得到表达的句子中,我们会离感觉更近吗?”[1]108
的确,即使内观察是可能的,也并不会因此比感觉的表达使我们更接近感觉本身。因为无论是内观察还是外观察,都是中介性地、尽管是直接地(directly)观察,而感觉的表达则是非中介的(immediate)。
同样地,在“我知道,我φ”中,“说我者”“非中介地”(immediately)知道“我φ”,不需要凭借任何中介就“自然而然”地知道。无论这一状态表达是行为表达,还是语言文字式表达,“φ”状态、相应的行为表达以及“φ”谓词三者之间都必然联系着,它们是等值的。
但是,如果“我φ”仅仅是一个非知识性的表达性表达,就不能把自身意识说成是自身知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个人说“我知道,我φ”是很荒唐的,因为“我φ”只是代替自然表达的语言表达,不需要再有“我知道”这个短语。因为“我φ”是一种表达性表达,对它的怀疑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即它是不可怀疑的。比如小孩子疼的时候就会哭,对于哭或大叫,人们不能在知识的意义上怀疑其真假,所以它不是知识。[1]105,110但正因如此,作为表达的自身意识才得以逃脱传统自身意识理论所受到的责难。
不过,图根特哈特认为,在“我φ”这一表达中呈现出来的自身意识是自身知识。所以,在图根特哈特那里,当一个人处于“φ”状态时,他不但可以在表达性的层面上说出“我φ”,而且还能在知识层面说“我知道,我φ”,后者正是图根特哈特理解的自身知识。
那么,这种表达性表达是不是也是一种知识呢?有两个条件:
其一,这与“我”这个词的用法有关,这一用法能够在“说我者”与“他者”之间建立起联系。图根特哈特认为,人能够说“我”,是因为人能够使用命题语言。“命题语言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成就是单称词项”[2]13,单称词项的处境独立性使人能够指称个别对象,通过使用单称词项,说者就能够在众多对象中指定一个对象。在所有的单称词项中,指示代词尤为重要;而在指示代词中,时间副词和地点副词是语言系统中最底层的单称词项①单称词项中的指示词(index words)分为三类:指示代词(比如:这个(this)、那个(that)等)、人称代词(我、你、他等)、地点和时间副词(比如:这里(here)、那里(there)、现在(now)、然后(then)、今天(today)等)。图根特哈特把时间和地点副词也放在单称词项之内,是因为单称词项本身已具有了处境独立性,用单称词项指称个别对象,已经脱离了现实的时空环境。由于现实的个别对象有很多,每个对象要能够区别于其他对象,就需要一个语言构造起来的“时空环境”。因为要首先能够指涉世界,才能够指涉世界中的对象,而通过这些地点和时间副词,就可以确认说者指的到底是哪一个个别对象,在不同说者之间建立起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所以地点和时间副词是一些最底层的单称词项。对此,可参考:Tugendhat.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determination(图根特哈特著《自身意识与自身规定》)[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6:59–64.以及E.图根特哈特.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一项人类学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3–16。。这些最底层的单称词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总是成对出现,说者的“这里”从另一个地方看就是“那里”,其具体所指则有赖于“说我者”。
对于“说我者”来说,每一个使用“我”的人就已经预设了他人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说我者”不但可以用“我”进行自我指称,也可以用“他”指涉他人;而且当使用“我”这个词时,“说我者”也知道他人也可以使用“我”这个词进行自我指称,同时,“说我者”也可以被他人指涉为“你”或“他”。所以,如果要对“我”这个词做有意义的使用,就必须知道“我”这个词的含义,而这意味着,知道“我–他”之间必然的对应关系。
此外,代词“我”还有另外两个特征:
1.当“说我者”使用“我”这个词时,“我”这个词所指的对象不可能不存在。②这个特征,对“这里”(here)、“现在”(now)同样适用,但不适用于“这”(this),这也是“这”区别于“我” “这里” “现在”的地方。这一点显而易见。
2.“我”这个词的使用不能够被还原为其他指示代词,即不能通过其他指示代词来解释说明“我”,但可以用“我”来说明其他指示代词。所以,不仅“我”这个词的使用不可还原到其他指示代词,对其他指示代词的理解也要以“说我者”为基础[1]64-65。因为在命题语言系统中,通过指示代词,即便“说我者”与个别对象之间的位置关系、时间关系发生改变,也能够切近地指称现实中的事物,“说我者”因此可以对个别对象做出确认。在“说我者”作出确认时,需要时空坐标中的参照点,否则通过指示代词作出的确认就是没有意义的③这是因为,比如我们说“这里”的时候,如果没有说“我”者自身为前提,那么“这里”可以指称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指称任何一个地方,那就是没有任何地方被指称。。而“这里”和“现在”具体所指又要以“说我者”为参照点,所以“说我者”本身是确认所有事物的最终参照点,他不能再用“我”来自我确认。所以,代词“我”不具有自我确认功能。尽管“说我者”不能用“我”进行自我确认,却可以用它来进行自我指称,即“我”指称了一个可以从第三人称角度被观察或被认识的人。“我”是一个人称代词,所以它可以指代任何“说我者”,“我”代表的是指称某一对象的角度④这一段的分析,将会在第三部分中用来支持图根特哈特对“自身确认”的说法。。
从对代词“我”的分析,得出两个重要结论:(1)由于同一个事物可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单称词项进行指称,所以“我”这个词也同时暗含着代词“他”的意义,即用“我”这个词所指的事物也可以从第三人称角度用“他”来指称。所以,对于“说我者”来说,每一个使用“我”的人就已经预设了他人的存在,无论这个他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2)“我”这个词不进行自我确认,但是它指向单个的可被确认的人,这个确认可以从“他”角度进行[3]。
因此,他人就可以通过观察与φ 状态关联的行为表达,从第三人称角度说出“他φ”。而在“我φ”这个表达中,“说我者”非中介地从第一人称角度表达了“我”处于“φ”状态。由于“我”这个词的特征,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句子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所以“他φ”和“我φ”指称同一事态,而这意味着可以从第三人称角度对“我φ”进行确认,这为“我φ”具有一种知识结构提供了可能。
其二,当一个断言句表达一种知识时,这个断言句首先要遵循相应的使用规则,这时人们就可以说它是一个正确表达(即用对了)。此外,还要能够对其进行真假判断,对这个表达,人们能够用“是”或“否”来回答,这意味着可以谈论与此相关的知识。比如说“今天在下雨”,当的确在下雨时,一方面意味着表达者正确地使用了这个表达,另一方面,也同时表达了一种知识,因为“今天在下雨”是真的。这意味着,一个句子具有知识结构,有两个标准:(1)使用正确;(2)能够对其进行真假判断。
在前面提到的“φ”状态的三种表达形式中,第一种“自然表达”的形式只是“表征行为”,显然不能算作知识。第二种、第三种形式都受到规则的支配,人们能够谈论在使用这种表达时是否遵循了规则,可以说这个表达使用对了或错了。但是第二种表达是习惯性表达,不能判断其真假,因为当人们说一个人疼的时候喊出“Ouch!”是真的或假的的时候,这说的是他用对了或用错了这个表达①这一可能会有这样的反驳,在某人有某种习惯性表达时,我们也会说“这是假的”或“他装得跟真的一样”,我们似乎也做出了真假判断。但是这种真假判断不同于对一个陈述句的真假判断,只有后者才事关知识,而这与分析哲学对知识和真理的理解有关。。而对于第三种形式的表达,图根特哈特认为人们不仅可以说他用对了或用错了这个表达,还可以就其谈论真假,因为在“我φ”中,有人称代词“我”,而在习惯性表达中没有,而代词“我”的使用为“我φ”赋予了一种类似于在“他φ”中的认知性,即断言性。这种断言性意味着,在“我φ”中人们可以用“是”或“否”来回答,以确定它的真假。这使得“我φ”这样的表达性表达与第二种表达,即习惯性表达区分开。对后者,人们不会作出是或否的回答,最多只能说使用错误,但前者却有一种知识结构。
根据以上两点,可以得出“我φ”和“他φ”的性质是一样的,能够成为知识。由此,“我φ”首先是一个表达性表达,但这个表达却有一种知识结构,因此也能在知识的层面讨论它。所以,“我φ”是一种表达性的知识,即人们在说出“我φ”时,就表达了一种知识,也就是“我知道,我φ”,这是一种是非中介的知识。
这种表达性的知识区别于经验知识,但人们常常看不到这一点。图根特哈特说:“……我们如此强烈地被定位在观察的模式中,以至于我们假定不可能存在不以观察或类似于观察的东西为基础的任何的非归纳性的经验知识。”[1]118
在这种自身知识中,人们不通过内观察,就知道自己处于这种状态,这种“知”具有知识的性质;又因它是表达性的,所以继续追问“我是怎么知道它的”没有意义。注意到这一点,也可以使人们避免得出图根特哈特再次陷入循环困境的结论。
三、循环困境的克服
图根特哈特认为,自身意识理论的循环困境产生于传统的认识模式,所以要克服循环困境,只需放弃传统的表象模式即可。从前面两节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代替这种表象模式的是语言表达:“我知道,我φ”。而对第一个循环的克服,除了与自身意识是非中介的表达性表达有关,还与代词“我”的使用有关。第二个循环的克服,一样与代词“我”的使用有直接联系。
对第一个循环的克服:在自身意识的表象模式中,认识主体返回自身,把自身当作对象。“我”原本是一个代词,这时却名词化为一个对象的名称,即在传统的表象模式中,代词“我”转化为名词“我”,使认识主体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成为对认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但如果不再使用表象模式,不再以返回自身、把自身当作对象的方式认识自身,那么就不会有自身意识预设了要认识的主体的问题。所以图根特哈特的做法是把名词形式的“我”(Ich)还原为代词“我”(ich),然后将自身意识理解为“我知道,我φ”这种表达。当处于某种意识状态时,人们可以直接表达“我φ”,这是一种类似于自然表达的表达,当“我”处于某种状态时就非中介地(immediate)知道。而问“我为什么知道、我是如何知道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提问只针对“认知性知识”②这一点在本文第二节已经做了详细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另外,在“我知道,我φ”中,后一个“我”和“φ”不可以分开讨论。“我”是一个代词,可以指代任何“说我者”。它不是一个名词,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对象,能够用“我”来命名,毋宁说,人们是用“我φ”给某种事态“命名”。所以“我”和“φ”分开讨论,这在语法上不成立;而且,“我”和“φ”状态实际上也不是作为两个实体,而是作为一个整体,一个“说我者处于某种状态”的整体事态,非中介地为“说我者”所知。对这种不可分的强调,避免了把“φ”归属给“我”或者把“φ”确认为是“我”的状态时可能会导致的第一个循环。
对第二个循环的克服:第二个循环涉及的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同一性问题。如果放弃使用表象模式,并将名词化“我”还原为人称代词“我”,那么就不存在如何把“φ”状态归属于“我”的问题。
现在,新的“循环”不过是在“我知道,我φ”中,“我知道”中的“我”与“我φ”中的“我”之间的同一性问题,即“说我者”如何能把“我φ”这种知识归给自身。
根据第二节中对代词“我”的分析,已知“我–他”可以相互转换,而且代词“我”不能被用来进行自我确认,因此“我φ”是否归属于我、真假与否,不由我做出对“我φ”的确认是由他人做出的(即第三人称角度)。正是这个意义上的确认,“我φ”表达获得了知识特性。这种特性也不会引起“我如何把这种知识归属给自身”的问题。可以看到,在放弃表象模式而在语言分析中产生新的循环是一个假循环。
四、结论
在批评亨利希没有正确描述自身意识这一现象后,图根特哈特从对意识的分析出发,借助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将自身意识过渡到语言分析哲学的语境之下。在语言表达中,自身意识被表达为自身知识,即“我知道,我φ”。在维特根斯坦的启发下,对自身状态的知识被理解为表达性表达,表达性表达是后天学会的表达,和一个人处于“φ”状态时的自然表达或习惯性表达一样,“φ”句子的表达也与相应的意识状态之间有着必然联系。通过分析代词“我”的使用,这种表达本身具有知识的结构特性,因此“我φ”这种表达性表达成为“自身知识”。由于“表达性”,自身知识从“我”角度的获得是非中介的,对此不可做进一步追问;由于“知识性”,自身知识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表达”,而且还具有了知识形态,他人可以在通常的知识层面对其做出确认。图根特哈特揭示并区分了自身意识/自身知识的这种双重性。也正是因为对这种双重性的混淆,人们才在知识的层面无止境地追问这种表达性表达是何以可能的。
然而,在图根特哈特的自身知识理论中,除了语言分析这个视角,还暗含着一个前提条件,即自身意识的自明性。海德堡学派和图根特哈特的争论其实也在于具有“自明性”的自身意识可论证与否的问题①图根特哈特批判了海德堡学派的自身意识理论之后,海德堡学派的成员也做过有力回击。关于海德堡学派对图根特哈特的反击,可参考:D.亨利希.再次落入循环之中——批判图根特哈特关于自身意识的语义学解释[J].卢冠霖,译.待刊稿。Dieter Henrich.Noch einmal in Zirkeln.Eine Kritik von Ernst Tugendhats semantischer Erklärung von Selbstbewußtsein[G]//Mensch und Moderne,Festschrift H.Fahrenbach,Würzburg,1989:89–128;M.弗兰克.个体的不可消逝性[M].先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另外,海德堡学派与图根特哈特关于自身意识理论的争论以及扎哈维对自身意识的讨论,对理解图根特哈特的自身意识理论以及最终得出本文的结论都有所帮助,可参考相关文献有:Manfred Frank.Fragments of a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Self-Consciousness from Kant to Kierkegaard[J].trans.by Peter Dews and Simon Critchley,Critical Horizons:A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2004,5(1):53–136;Dan Zahavi.The Heidelberg School and The Limits of Reflection[M]//Heinämaa.S Consciousness:From Perception to Reflection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Mind,the Netherlands:Springer,2007(4):267–285;Subjectivity and Selfhood,Investigating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M].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2005;丹·扎哈维 .海德堡学派与反思的局限性[J].胡文迪,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38–47;丹·扎哈维 .主体性与自身性——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M].蔡文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张任之.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对舍勒现象学的质料价值伦理学的重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郑辟瑞.亨利希与图根德哈特的自身意识之争[J].现代哲学,2010(1):94–100。。海德堡学派试图论证这种自明性,而图根特哈特则直接以这种自明性为前提。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自明性的前提下,图根特哈特把自身意识理解为非中介的自身意识,传统意义上循环困境是假问题;而在知识层面,出现的困境又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