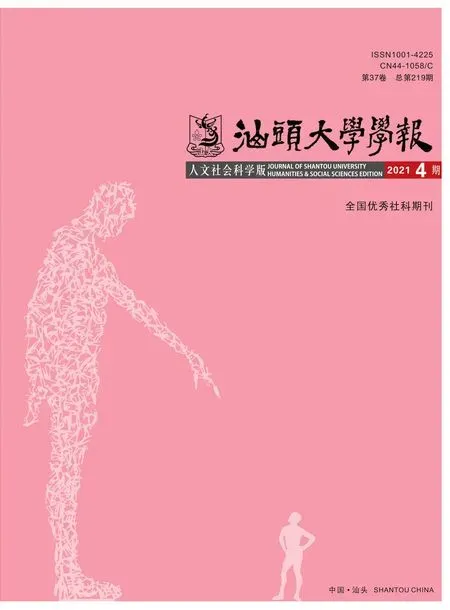吴福辉书简两通释读
刘 涛
(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在现有的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中,《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应该是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该著第一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7 年8 月出版。据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往事》所记,书的出版一开始并不顺利,曾找过一家出版社,但没有被接纳,“吴福辉说他认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高国平,不妨一试。于是便写信联系高国平。上海文艺社果然思想开放,不论资排辈,很痛快就接纳了这部讲师写的教材,准备出版。”[1]《三十年》撰写于1982 年至1984 年,这时,它的几位作者职称还较低,名气也不大,但高国平先生慧眼识珠,慨然接纳这部教材,可谓《三十年》之功臣,可谓几位作者之伯乐。因此,研究《三十年》,高国平先生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三十年》作者中,只有吴福辉认识高国平,关于出版事务的接洽,都是由吴福辉给高国平写信完成的。因此,这些书信对研究《三十年》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笔者收藏有吴福辉写给高国平的书信两封,一封写于1985 年3 月11 日,另一封写于1985 年6 月3 日。两封信写作时间相距不远,内容有紧密关联,所谈皆为《三十年》的写作、交稿与出版,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的预备、召开情况。鉴于这两封书信对研究《三十年》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笔者将它们整理发表出来,并做简要解释,以供学界同人参考。
一
第一封信写于1985 年3 月11 日,所用信纸和信封皆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专用,信封正面署“上海市绍兴路74 号上海文艺出版社高国平同志收”,背面邮戳时间为“1985.3.17”。信的内容如下。
国平兄:春节过得好吗?向贵社各位同志问候!奉上《丛刊》第一期两册,其中一册给辽民的。丁景唐同志另由编务同志发书。可能“论丛”方面与“丛刊编辑部”交换一本。其他方面有没有一定要赠书的,请通知我,再另设法。我们赠书范围比北京出版社小,可能更会考虑不周。你的书每期由我处理,一定会有的。
关于郭沫若的大作,已交执行编委审读,现已通过,只剩编委会审目录便可发稿(第三期)。我想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此期四月初便发排,七月可望出版。这篇稿子无论如何请放心好了,我会处理好的。
理群负责统文学史稿,正在进行。边统边抄,同时核对每章后面的年表。他和我最忙。最近他在北大内外要讲三门课程,又逢搬家(在北京南郊新区买的房子),实在赶不出来,所以,三月末交稿是不可能了,万望宽限到四月。我真想搬到北大去催。你看能否打乱你们的工作?
朱先生史纲在六月份左右交出一章,以便讨论,年末以前交稿。我和理群决心在搞完这本书后,再转去搞自己的专著。时间表也只能这样了。
五月份在北京开青年座谈会,据樊骏同志说,五十人左右。文学馆有一部分房子在改成写作间,届时,可能在我们这里开。不知上海方面通过学会有哪些同志一定来?您和贵社会有人来京吗?欢迎大家来这里聚谈聚谈。
福康有电话来,他已到京。我想近期内去看看他。
你最近在写些什么?还望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请多保重。
祝
编安
福辉
三月十一日
《丛刊》另寄,请查收。
书信开始,吴福辉首先向高先生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其他同志致以春节问候。这是出于中国人传统礼仪,因该信写作时间“1985 年3 月11日”,阴历为“1985 年正月20 日”,此时春节刚过不久。信中提到的“《丛刊》”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下简称《丛刊》)。“辽民”指“张辽民”,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她和高国平一样,是《三十年》的责任编辑。“论丛”指《文艺论丛》,该刊与《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鲁迅研究集刊》等刊物,都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文艺论丛》采用以书代刊形式,分辑发行,虽是综合性刊物,但现代文学研究部分所占比重很大,许多学术名家和新生代学人都曾在上面发表过文章。
“我们赠书范围比北京出版社小”一语包含信息量很大,其中“我们”指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丛刊》编辑部。这封信写于1985 年3 月,对于《丛刊》而言,这个时间显得很特殊。因为就在1985 年1 月,新改版的1985 年第1 期《丛刊》出版。《丛刊》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一开始名为“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后为扩大范围,去掉“高校”二字)的会刊,第1 期于1979 年10 月出版,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出版社合编,编辑部设在北京出版社,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从1985 年第1 期(1985 年1 月)开始,《丛刊》改版,北京出版社退出《丛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改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合编,作家出版社出版。为此,重组编委会,另建编辑部,编辑部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委会和编辑部的工作和作用被大大加强。①参见《改版致读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 年第1 期。这封信写作时间为1985 年3 月11 日,中国现代文学馆还在筹备过程当中,吴福辉参与了整个筹备工作。到15 天之后即1985 年3 月26 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郊万寿寺正式成立。吴福辉作为现代文学馆的工作人员,由王瑶先生指定,任《丛刊》编辑部主任。《丛刊》由现代文学馆接手后,由于经费紧张,印数减少,据董炳月回忆,《丛刊》印数最少的时候大约只有三千册[2]。《丛刊》1985年第1 期版权页所标印数为一万份,第3 期所标印数已降到八千。信中所说“我们赠书范围比北京出版社小”,可能与印数减少有关。
信中提及的“丁景唐”(1920—2017)为浙江镇海人,“左联”和鲁迅研究专家,著名出版家,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20 卷),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信中提到向丁景唐赠送《丛刊》1985 年第1 期,这是因为丁景唐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现代文学馆与上海文艺出版社有业务合作关系,除此之外,丁景唐作为作者在这一期还发表有文章。1985 年为“左联”成立55 周年,《丛刊》1985 年第1 期专门组织了一组“纪念‘左联’成立五十五周年”笔谈,由丁景唐、陈瘦竹、叶子铭、杨占升、张大明等人执笔,笔谈第一篇文章即为丁景唐《关于左联研究的意见》。
“关于郭沫若的大作”,指高国平撰写的《试论郭沫若早期史剧观》,该文发表于《丛刊》1985年第3 期。“理群负责统文学史稿”,这里的“文学史稿”指《三十年》。由此可知,《三十年》原定计划是1985 年3 月向上海文艺出版社交稿,但由于主要作者之一的钱理群过于忙碌,担任三门课程,且赶上搬新家,无法按时完成写作,原定计划被打乱,吴福辉向高国平提出宽限一个月,到4 月份再交稿。
“五月份在北京开青年座谈会”。这里的“青年座谈会”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1985年5 月6 日至11 日在北京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福康”指“陈福康”,也是《丛刊》作者,其《叶紫悼念彭家煌的文章》一文发表于《丛刊》1985年第4 期(1985 年10 月)。
二
第二封信写于1985 年6 月3 日,所用信纸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专用信纸,所用信封则与上封信不同,为中国现代文学馆专用信封,这说明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后,还专门印制了供单位人员使用的信封。信封正面署“上海市绍兴路74号上海文艺出版社高国平同志收”,背面邮戳时间为“1985.6.4”。信的内容如下。
国平兄:
最近忙吗?可好?不久前曾致一信,想已达览。兄之估计十分真确,你讲限期放宽至六月,现在看来只能是六月二十日左右了。最近我将一半之精力已投入该书。理群实在狼狈,弄到北大的专题课前一晚深夜方始备出,第二日昏昏沉沉便上讲坛。他为了统稿,下了大力,自己部分的修改却推迟了(大部分的章节都重新写过,有些章节重新调整,总论、三个概述及孤岛、沦陷区文学为新增章节)。现在,我们三人已全部抄清;理群需至六月九日全部改完自己的章节,并写出年表初稿;六月十日至六月十六日,全体总动员帮理群抄稿。我从现在起开始将“年表”统一遍,将“参考书目”统一遍,然后负责最后通读。你看,紧张不紧张?他们三人都在北大,所以只能由我一次次地跑去。幸亏馆里给我一个月假弄《茅盾全集》(十六卷),我是先将力量偷偷放在文学史上了。大家都是忙人,各条线索集于一身。集体写作在协调上颇费时间,实在不足取矣。
因为由我在理群统稿后再通读,稿件大部分已集中在我手里,謄写很清楚,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理群兄的字稍难认,不知謄出来如何,但他会尽力的。王先生说过,他的助手字从来不好,当年乐黛云老师如此,今日理群是也。理群的识见、功力显然比我们强,这是大家公认的。
王先生在医院中(治痔疮)便开手替文学史考虑序言,今已写出初稿,还要略略修饰一下。所以,我们六月二十日以后,一定一次性交稿,请放心。
创新座谈会开过。王富仁正在与文学馆合作起草会议纪要,将来登在《丛刊》上。在研究范围上,一致要拓宽,理群偕黄子平、陈平原在会上提出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设想,则近、现、当代熔于一炉,文学现代化之轨迹更清。其部分观点,将写入本文学史之总论中。研究方法将来恐怕是传统为一套,新的为一套(文艺心理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阐释学等为主)然后逐渐综合。用新的一套写文学史颇难,总要几年以后方能出世。如单用阐释方法写,也不能不顾及社会、政治、历史、美学评价,否则作家作品如何序列?写一论文,用一种单一的新法试之当然可以;写文学史似乎只能综合(但可突出一种方法,如勃兰兑斯之“主流”一书,从文艺心理角度切入,兼顾其他)。我甚盼在三年之间有方法全新的文学史出现。这次创新会,中青工作者能聚集一堂,检阅力量,加强交流,本身便是一件好事。我年来忙于杂务,参加会议后也深感落后,极想尽量摆脱馆内一些行政事务,多写点东西。
《丛刊》第三期已发稿多日,兄之大稿已在其中。不日便可读校样了。第二期样书这几日便能运至,兄与辽民的定当奉寄。此信不必复,二十日左右接书稿后再来信不迟。弟家中地址为“北京,左家庄,三源里街,25 楼3 门1104 号”,最近我在家中,有时寄到馆内会晚接几日的。代问辽民及室里同志好。
即询
编安
福辉
六月三日
与上封信相比,这封信包含信息更丰富,文献价值更高。
信件生动还原了《三十年》撰写、分工、交稿的具体情况。成书之前,《三十年》部分内容已在《陕西教育》上连载过。信中提及“大部分的章节都重新写过,有些章节重新调整,总论、三个概述及孤岛、沦陷区文学为新增章节”,说明《三十年》上海文艺版与《陕西教育》版之间版本差异较大,这种版本差异体现为三点,一是大部分章节重写,二是部分章节重新调整,三是新增“总论、每一编的概述和孤岛、沦陷区文学”。分工方面,钱理群负责统稿,吴福辉负责最后通读。“他们三人都在北大”中“他们三人”指钱理群、温儒敏、王超冰。“我们三人已全部抄清”中“我们三人”指温儒敏、王超冰、吴福辉。这封书信披露了《三十年》交稿最后期限是“1985 年6 月20 日”,而在写信之时(1985 年6 月3 日),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三人的稿子已抄清,而钱理群要到6 月9 日才能全部改完其负责章节并写出年表初稿,6 月10 日至16 日大家帮他一起抄稿。由书信我们还可窥知《三十年》撰写当中的一些细节,让我们更真切感知当时的历史情境,如钱理群为赶写书稿而无时间备课,“实在狼狈,弄到北大的专题课前一晚深夜方始备出,第二日昏昏沉沉便上讲坛”。他负责整部书稿统稿,“下了大力,自己部分的修改却推迟了”。因为编辑《茅盾全集》第十六卷,中国现代文学馆给了吴福辉一个月假期,但他却利用这段时间“将力量偷偷放在文学史上了”,这充分说明他对《三十年》修改和写作的重视。信中还特意提及“王先生在医院中(治痔疮)便开手替文学史考虑序言”。王先生即“王瑶”。《三十年》的写作与《陕西教育》向王瑶约稿有关。《陕西教育》邀请王瑶编写一套“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刊授“自修大学”中文专业的教材。王瑶把这个任务分派给他的学生们,这才有了《三十年》这部书稿的诞生。①参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往事》,温儒敏:《燕园困学记》,新星出版社2017 年版,第93-94 页。书信披露王瑶先生生病住院还为学生书稿写序、构思的细节,令人感动。王瑶为《三十年》写的序标注写作日期为“1985 年5 月24 日”。据6 月3 日这封信中“今已写出初稿,还要略略修饰一下”一语推断,“1985 年5 月24 日”这个日期应该是他的序言初稿完成日期,而非定稿日期。
“创新座谈会开过”中“创新座谈会”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这封信谈到1985 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的一些情况,对研究这次学术会议有重要史料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召开,地点是北京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时间是1985 年5 月6 日至11 日。陈平原称这次学术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3]。这次会议的参加者皆为现代文学研究界初露头角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以后大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会议提出的多个议题,如现代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问题,文学研究方法的革新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的关系问题等,对此后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过广泛影响。此次会议上,陈平原就“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做了专题发言。陈平原坦承“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最早是老钱提出来的,就专业知识而言,他远比子平和我丰富。那时我还是个博士生,老钱已经是副教授,比我大15 岁,之所以推举我做代表,是因为这个机会对年轻人来说太重要了。老钱说,既然是创新座谈会,就应该让年轻人上阵。这是80 年代特有的气象与风度——相信未来,相信年轻人,关键时刻,尽可能把年轻人往前推”[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也明确提出:“这个设想是由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北京大学)共同提出的,陈平原代表他们三人在会上作了发言,比较详细地报告了他们计划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规划。”[4]这封信为陈平原的叙述提供了旁证,对《纪要》的内容也可做些补充。信中提及“理群偕黄子平、陈平原在会上提出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设想”,特意把“理群”摆在前面,说明在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过程当中,钱理群起了比较关键的引领作用。“其部分观点,将写入本文学史之总论中”中“总论”指《三十年》的第一章《绪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质和历史位置》(以下简称《绪论》),这一章的撰写人为钱理群。《三十年》最初在《陕西教育》连载时是没有《绪论》的,最开始的第一讲为温儒敏执笔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陕西教育》1983 年第10 期)。《绪论》是成书之时最后添加上去的,与其他章节相比,这章在写作时间上反而比较靠后。写作这章时,在与陈平原、黄子平的私下讨论中,钱理群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已有了初步想法,于是,他便把该命题中所包含的一些核心要点写入了《绪论》。例如,《绪论》多次提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反复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只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是中国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觉醒、大奋起的产物,同时又是东西方文化互相撞击、影响的产物,因而形成了共同的整体性特征”[5]。《绪论》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的主导性文学观念为“改造民族灵魂”,这决定了现代文学的思想启蒙性质;应该重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与世界现代文学发展的同步性,重视通过与传统文学、世界文学的纵横联系来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自身特质。这些观点,也正是陈平原代表他们三人在创新座谈会上所提出的。王晓明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和在会上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视为“重写文学史”的“序幕”,认为:“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们第一次看清了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既成格局的重要意义。”[6]如果此说成立,那么,1987 年出版的《三十年》就可视为“重写文学史”的具体实践。因为钱理群已经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些主要观点写入《三十年》的《绪论》,并使之成为贯穿性的思想主线。
研究方法革新是创新座谈会的另一核心议题,带着对此问题的思考,吴福辉信中还论及研究方法创新与文学史写作的关系问题。20 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方法论热兴起后,西方的各种研究方法如文艺心理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阐释学等纷至沓来。面对轮番上阵的各种新方法、新理论,吴福辉的态度是冷静的,他认为写论文采用一种新方法是可行的,也期待三年之间有运用新方法、新理论撰写的现代文学史出现,但同时又认为运用单一的新方法、新理论进行现代文学史写作行不通,因为文学史研究不同于文学批评,它是一种综合的历史评价和分析,“如单用阐释方法写,也不能不顾及社会、政治、历史、美学评价,否则作家作品如何序列?”因此,文学史写作只能采用多种方法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和创作现象进行综合研究和评判,这对文学研究者其实是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十年》采用集体写作方式,对于这种方式,吴福辉表示了自己看法,认为“集体写作在协调上颇费时间,实在不足取矣”。《三十年》最初撰写者为四人,修订后改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撰写者减少为三人。此书虽属集体写作,但每位作者的个人风格都能体现出来,与多人集体编撰的文学史还是有所不同。但即使如此,吴福辉对此种集体写作的方式还是持保留意见,更为看好个人独立编撰文学史,为此,1983 年他曾撰写《提倡个人编写文学史》一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 年第1 期),缕述个人编写文学史的好处和优势。后来他以一人之力独立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1 月第1 版),就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
这份书信还可使我们窥看到作者内心的隐微部分。信中提及:“这次创新会,中青工作者能聚集一堂,检阅力量,加强交流,本身便是一件好事。我年来忙于杂务,参加会议后也深感落后,极想尽量摆脱馆内一些行政事务,多写点东西。”这段话前半段讲的是创新座谈会上全国青年才俊聚会、交流、研讨的情形,后半段则流露出惶恐、不安、失落之感。“深感落后”,这几个字不能仅看成是作者自谦和客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给吴福辉出过一本《春润集》,这是一部自选集,按编年形式收录作者自己认可的文章。笔者注意到,“一九八四”“一九八五”两个年份出现空档,没有文章。这两年吴福辉不可能没有任何出产,但他没有选入。也许这两年的空白留给了《三十年》,要知道这正是几位作者忙于此书写作、修改的时间。
书信是对当下情境的记录。通过书信,我们可抵达鲜活生动的历史原生态,复活并再次经历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通过吴福辉这两封书信,我们可触摸感知到《三十年》撰写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召开的一些具体细节。因而可以说,它们是研究《三十年》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的珍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