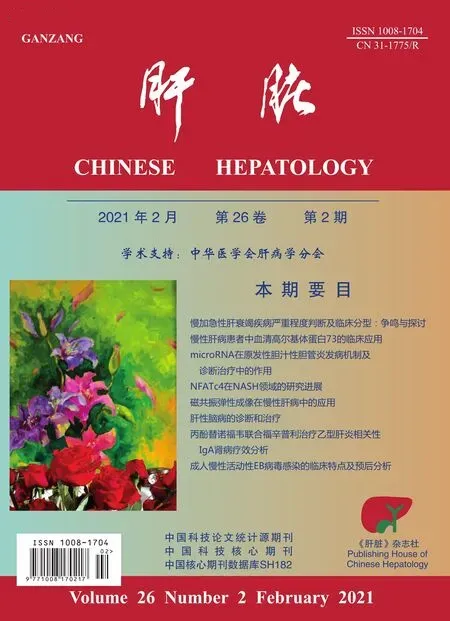以肝肿大为特征的肺结核 1例
林根琼 陈立畅 周惠娟 谢青 赖荣陶 蔡伟
患者,男性,58岁,因“反复间歇发热2月余”于2020年7月27日就诊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感染科。患者2020年6月初体温升高,最高达39 ℃,无畏寒,无咳嗽、咳痰,无胸闷、气促,无恶心、呕吐,无尿频、尿急,无皮疹、关节疼痛。就诊于当地医院,查胸片示“肺炎”,予输液与口服药物(青霉素、阿奇霉素、酚氨咖敏片、左氧氟沙星等)治疗10余天,复查胸片示“好转”,但仍有反复发热。6月23日,体温高达40 ℃,就诊于上海中山医院,查胸部CT示“肺炎已愈”,查血常规示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稍升高,余无明显异常(具体报告未见)。6月24日第一次入住我院感染科,先后予莫西沙星、头孢哌酮钠舒巴坦抗感染及保肝、抑酸、控制血糖、控制血压等支持治疗。在我院完善相关检查:腹部B超示“肝脏大小形态正常,肝囊肿;胆囊壁增厚水肿;脾脏无异常;腹膜后淋巴结肿大(之一约25.6 cm×11.3 cm,淋巴门结构不明显)”;PET-CT未见后腹膜淋巴结有代谢增高表现,显示“脾脏内多发点状、团片状代谢增高病灶,恶性病变可能,SUV值11.7(低于盆腔内考虑炎症改变的SUV值19)”;腹部增强MR示“脾脏存在契形异常信号,脾梗死可能”。当时考虑“细菌栓子导致脾梗死可能大,致间歇性菌血症”,抗菌素升级为美罗培南,暂不予脾脏穿刺。抗-HCV (+) 、HCV RNA 1.55×105IU/mL 、GT 6n型,考虑“6n型慢性丙型肝炎”,予索磷布韦维帕他韦抗病毒治疗。T-SPOT.TB A抗原 41/B抗原 12,多次痰中未找见抗酸杆菌,患者诉有肺结核治疗史,考虑“既往结核感染”。7月9日患者出院,出院时体温37.5 ℃,至外院继续完成抗菌疗程。7月20日患者再次出现高热,最高体温40 ℃,伴有畏寒、咳少量白色粘痰、恶心及头部不适,予服新癀片及左氧氟沙星片后每日可热退3~4 h,之后仍回升至39 ℃左右,遂于7月27日第二次入住我院感染科。患者自发病来近2个月,体质量下降约10 kg。既往史:高血压病史17年;冠心病病史1年余,分别于2018年11月和2019年2月行PCI术;糖尿病病史4月;确诊慢性丙型肝炎1个月;否认肾脏病病史。有长期饮酒史,现戒酒1年余。其父母及姐姐有高血压及冠心病病史,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史。第二次入院查体:神清,精神可,肝掌(+),无蜘蛛痣,皮肤巩膜无黄染、瘀点瘀斑,两肺未闻及干湿啰音;腹平软,未见静脉曲张,无压痛、反跳痛,肝于右锁骨中线肋缘下11 cm可触及、剑突下3 cm可触及,质硬,脾肋下未触及,移动性浊音阴性,肝肾区叩击痛阴性,墨菲氏征阴性,双下肢无水肿。陆续完善相关检查。血常规:C反应蛋白 43 mg/L,中性粒细胞% 72.1%、淋巴细胞% 16.3%、单核细胞% 10.7%,余无殊。肝功能:前白蛋白 77 mg/L,ALT 223 IU/L,AST 114 IU/L,γ-谷氨酰转肽酶 237 IU/L,总胆红素 13.8 μmol/L,白蛋白 29 g/L;肾功能未见异常;免疫球蛋白示IgE 221.0 IU/mL,余阴性;自身抗体(ANA、ENA、ANCA、肝炎相关抗体)均阴性;红细胞沉降率正常;铁代谢示缺铁表现,铜兰蛋白阴性;β-1,3葡聚糖、内毒素、降钙素原均阴性,甲、乙、丁、戊型肝炎病毒阴性,抗-HCV(+),HIV、梅毒抗体均阴性,外周血新型隐球菌乳胶凝集试验阴性;肿瘤标志物示CA-125 60.3 U/mL、CA-199 36.5 U/mL、铁蛋白 2 162.0 ng/mL;甲状腺功能基本正常;扁桃体分泌物、中段尿培养、血培养均阴性,尿、粪检查阴性,呼吸道常见病毒阴性。复查T-SPOT.TB A抗原 47/B抗原 21,多次痰涂片未找见抗酸杆菌。腹部B超示“肝肿大(长+厚 109 mm+75 mm,右叶斜径 175 mm),肝内胆管轻度扩张,脾稍厚,门静脉增宽,肝囊肿”。心脏超声示基本正常。胸部CT示“间质性肺炎改变;两肺气肿,两肺斑结节、索条影,右上肺钙化灶;两侧胸膜增厚”。浅表淋巴结B超未见明显异常。上腹部+盆腔增强CT示“脂肪肝;脾稍低密度影,拟炎性病变可能”。腹部增强MR示“肝脏肿大,肝损改变;脾稍大伴铁沉积,脾脏楔形异常信号,拟炎性病变可能;胆囊壁水肿;少量腹水;肝门淋巴结肿大;肝脏囊肿”。住院期间,患者曾出现一过性胸闷气促、氧饱和度下降。相较1个月前的腹部影像学检查,肝脏显著增大,且有右上腹压痛。为明确是否存在肝脏淋巴瘤或其他浸润性疾病行肝穿刺活检。因长期发热,完善骨髓穿刺,骨髓涂片及基因、流式细胞学均无明显异常。同时详细追问病史,家属回忆10年前曾患肺结核,予抗结核治疗2个月。结合患者未规范治疗肺结核病史,8月3日查痰X-pert示“检出结核分枝杆菌,量低;未检出利福平耐药基因”。患者发热原因考虑为“结核”,予转上海市肺科医院进一步治疗。出院诊断:1、感染性发热(结核可能);2、肺结核(痰X-pert阳性);3、高血压;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状动脉支架植入后状态);5、慢性丙型肝炎;6、酒精性肝炎;7、2型糖尿病。
患者出院后病理报告回报。骨髓穿刺病理未见明显异常。瑞金病理科肝脏穿刺病理:慢性肝炎,炎症2/4级,纤维化1/4期,局灶汇管区见少量多核巨细胞,免疫组化未提示淋巴细胞异常表型,未检测到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的DNA核酸片段,需考虑病毒性或药物性。复旦大学医学院病理系肝脏穿刺病理:结合临床HAV-HEV(-),提示DILI,请临床询问服药情况以进一步确诊。追问患者发病前无明确可疑药物服用史,故药物性肝损伤暂不予考虑。
讨论结核病是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感染性疾病,可累及全身多个器官,以肺结核最为常见,占各器官结核病总数的80%~90%。肺结核临床类型主要分为:1、原发性肺结核,2、血行播散性肺结核,3、继发性肺结核,4、气管与支气管结核。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发热、盗汗、乏力、咳嗽、咳痰、咳血、腹痛、腹胀等,也可表现为肝肿大[1]。找到结核分枝杆菌为诊断本病的金标准。
本例患者肝穿刺病理可见淋巴细胞、上皮样细胞和多核巨细胞组成的微小肉芽肿形成。肝肉芽肿性病变多见于多种疾病:(1)感染:最常见于肝结核,尤其是急性粟粒性结核,病理上肉芽肿多分布于汇管区,可不出现干酪样坏死,抗酸染色阳性率不高[2],其他还有鸟分枝杆菌感染、隐球菌感染、组织胞浆菌病、球孢子菌病、血吸虫病、麻风病、布氏杆菌病及Q热;(2)肿瘤:尤其易见于淋巴瘤和肾癌;(3)自身免疫病,多见于结节病和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韦格纳肉芽肿和风湿性多肌痛亦可见;(4)药物,包括别嘌呤醇、磺胺、氯磺丙脲、奎尼丁等;(5)特发性结核。
本例肝脏病理特征及免疫生化指标不支持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尤其是肝脏淋巴瘤,病史中无相关可疑药物服用史,不考虑药物性肝损伤,有饮酒因素,但本例表现不符合酒精性肝炎。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和既往结核未规范治疗,不能排除肝结核。肝结核为全身播散性结核的表现之一,在所有活动性结核中仅占1%,其中79%为粟粒性肝结核、21%为局灶性肝结核,胆道结核罕见。肝脏血运丰富,动、静脉乃至淋巴管途径均可致结核菌播散至肝脏。若结核菌由肺感染灶经肝动脉入肝,则主要表现为粟粒性病变;若通过门静脉或胃肠淋巴管自肠道入肝,则主要表现为局灶性病变。结核性肝脓肿通常由局灶性肝结核进展而来,但也可继发于粟粒性肝结核。肝结核临床表现通常无特异性,常见的表现为肝肿大、发热、呼吸系统症状、腹痛、体质量减轻等,本例患者存在以上5项临床表现(包括干咳、胸闷气促),一些较少见的临床表现有脾肿大、腹水、黄疸等。当患者合并以下临床表现或检查结果时可考虑肝结核,需综合诊断[3]:(1)长期不明原因的发热、盗汗、消瘦、乏力、食少等一般结核杆菌感染症状;(2)慢性上腹部或右上腹的隐痛、肝大、压痛或右上腹结节,肝区包块;(3)实验室检查有轻中度贫血,血沉加快,结核菌素试验阳性,可出现肝功能异常;(4)有结核病史或结核接触史,发现肝外结核病灶,并排除肿瘤或细菌性肝脓肿等疾病;(5)诊断性抗结核治疗有效;(6)腹部B超或CT等影像学检查等提示肝内占位性病变。诊断肝结核的金标准仍为病理组织检查。肝结核的基本病理改变为肉芽肿性病变。粟粒性肝结核的肉芽肿特征为:肝小叶内直径0.6~2.0 mm的结节,弥漫分布于整个肝脏。局灶性肝结核的肉芽肿特征:门管区周围直径>2.0 mm的结节,局灶分布。肉芽肿可为坏死或非坏死(干酪样或非干酪样),约在51%~83%肝结核组织中发现典型的干酪样坏死改变。但由于肉芽肿见于多种疾病,肝脏病理见肉芽肿表现仅有提示作用,并不能确诊。需对病理组织行微生物学检查,包括抗酸染色、PCR。肝组织抗酸染色阳性率仅25%、PCR阳性率86%。由于临床上诊断肝结核存在较大困难,病理也可误诊,故临床上需综合判断,尤其是根据抗结核治疗后肝脏的变化进行诊断。
本例患者予利奈唑胺及莫西沙星二线抗结核药物治疗2 d后体温明显下降,4 d后肝肋下缩小至8 cm,压痛显著减轻。转上海市肺科医院继续抗结核治疗,6个月后患者康复。抗结核化学治疗是结核病最主要的治疗方法,整个疗程分为强化期和巩固期两阶段,主要药物包括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乙胺丁醇等。治疗过程要遵循“早期、适量、联合、规律、全程”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