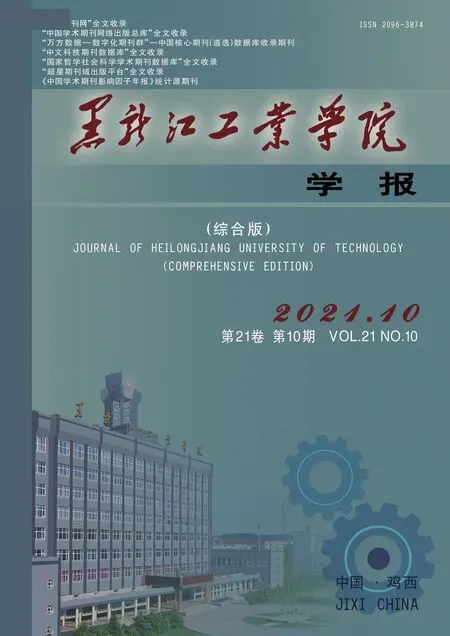新时代嫩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困境与改革之路
张良祥,朱 顺,吴 巍,修 月
(1.齐齐哈尔大学 体育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2.黑龙江工业学院 体育学院,黑龙江 鸡西 158100)
嫩江流域是我国东北重要的自然-人文区域,既是边疆地区,又是民族地区。嫩江流域体育是一种以沿岸沿线城市为支撑点,以流域为空间载体的区域体育类型。近年来,随着嫩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迁,民族传统体育面临代际传承缺乏、文化认同淡化、文化内涵扭曲、资源恶化,开发不利、文化自信缺失等诸多不利因素。这些困境成为制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痛点,因此,在体育强国建设的新时代,深入探索嫩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改革之路[1],对推动我国民族体育文化研究和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繁荣与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嫩江流域地貌及生态环境介绍
嫩江流域位处我国东北松嫩平原西北部,嫩江发源于大、小安岭之间的伊勒呼里山南麓,左岸为广阔平坦的松嫩平原,右岸为绵延高耸的大兴安岭。其上游地貌多表现为山地或连绵成片的丘陵,中下游与松花江呈“Y”字形分布,多为波状沼泽、沙丘平原或草原。嫩江流域全长1 089公里,共有20多条支流(其中较大的有10条),总流域面积为283 000平方公里。嫩江右岸7条支流均发源于大兴安岭东麓,流经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省境内[2];左岸3条支流均发源于小兴安岭西麓,流经的区域全部在黑龙江省境内。
嫩江流域生态环境为中下游地势较为平缓,多为草原和湿地,土壤肥沃,草原茂盛,湖泊棋布。上游多为山林峡谷,河谷狭窄,森林茂密。嫩江流域良好的绿色生态环境是各种飞禽、水生动物和野生动物的理想生存和栖息之地。得天独厚的丰富生态资源为游牧民族捕鱼、狩猎等创造了有利条件。
嫩江流域是丝绸之路东北区的西北部经济带,是东北经济区向俄罗斯、蒙古开放的前沿地带,进入新时代,嫩江流域凭借地缘优势和交通优势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俄旅游合作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拥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
二、嫩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任何文化在产生、演变和发展过程中,都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体育文化也不例外。生活在嫩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凭借其特殊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和气候特征孕育了一百余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浓厚民族风格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中部分项目入选市级、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如,满族珍珠球、达斡尔族“波依阔”等。
1.曲棍球文化
曲棍球运动在达斡尔人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他们最喜爱的体育运动,其又被达斡尔人称之为“波依阔”[3]。民间曲棍球比赛是达斡尔人重要节日、集会、喜庆日的必备活动。达斡尔人曲棍球比赛多用毛球或木球,在平坦的土地或草地上,人们来往打着毛球或木球,夜间比赛用的是火球,火球是将桦树上已硬化的白菌打成数孔,注入松明或将空球浸油,球被点燃后在两队争夺中来回飞舞,如同夜空中的流星,划出一道道火线,别具情趣。曲棍球杆也是姑娘们出嫁时送给心上人精美的礼物和美好的赞美与期望。如今,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随处可见人们参与曲棍球这一项运动,不管大人还是孩童,人人都可以挥起球杆一显身手。这就是达斡尔人对“波依阔”运动千百年的情怀。“一个自治旗,半支国家队”的辉煌、多次全国冠军殊荣与辉煌历程、30多所曲棍球基点学校、数以万计不同年龄的曲棍球爱好者造就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国家曲棍球夏训基地”和“曲棍球之乡”的金色名片。
2.赛马文化
赛马作为一种古老特殊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承载了多方面的民族文化内涵,体现了各民族族群的集体情感,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符号、精神载体[4]。每当春节和传统民俗节庆活动等大型场合,几乎都少不了原始而独特的赛马主题活动,丰富多彩的赛马是最具观赏性、最为激烈、最具吸引力的比赛,此活动已成为了古往今来各民族最喜爱、最持久、最普遍的群众性活动。人们在赛马活动中,享受马匹带来的快乐,如,挥杆套马和绳索套马、枪枢、马赛、马上射箭、马上角力、叼羊、超越障碍、马球和赛“米日干车”等各种马术竞技表演。赛马活动多由青壮年参加,比赛方式分集体和单骑,竞赛时,剽悍的选手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此向众人展示马背上各种骏马腾空、平衡、支撑、倒立、空翻、转体、跳跃飞身上马等高超、惊险的骑马功夫。未婚青年骑手时常用英姿矫健的高难度骑术向姑娘们展示其勇敢、顽强、拼搏的精神,传达情感,以期博得姑娘们的青睐与追逐[5]。赛马文化活动多以速度、马上娴熟技巧和集体密切配合来决出胜负,获胜者将受到奖赏。
3.射箭文化
射箭文化是多民族,多文化交流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活化石”。骑马挎弩,弯弓射雕既是族人们狩猎生存的技能,又是抵御外敌的手段工具,它包含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聚集了文化价值。弓箭作为狩猎文化的古老工具成为男女老少必带标配,族人们从小就喜欢拉弓射箭,孩童,幼年时就跟随父母在长期游牧生活中用长辈们制作木质的小弓箭射杀飞鸟、灰鼠等小动物,善射仿佛成为了他们的天性[7]。随着年龄与力量的增长,弓箭也由小变大,到了十六七岁即可离开父母进行单独狩猎活动。东北冬季寒冷且漫长,当大雪封山时,猎手们的生活就是“以打牲射猎为本”,射猎林中獐、狍、野鸡、野鹿等动物,以收获猎物多少显示其射技本领。在传统民俗节庆活动中,射箭比赛多以树木、草靶为目标,进行立射、骑射和远射。如今,射箭已从以防外敌侵略、野兽袭击畜群和依赖弓箭捕杀动物维持生活,发展到目前竞技运动表演和休闲健身方式,构成了纷繁灿烂独具一格、多元一体的中国传统射箭文化体系。
4.摔跤文化
摔跤作为一项古老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是各民族最为普及,深受广大青少年男子所喜爱的体育游戏。形式多样的摔跤活动主要在青壮年中盛行,是捕鱼之暇、婚礼和节庆里不可缺少的一项娱乐助兴活动[7]。每当进行摔跤比赛时,族人们,纷纷来到田间地头或江边的沙滩上,参与这一活动。在展示对抗、力量与技术的同时,增进了思想交流和感情沟通。如今,摔跤已从过去为了求得生存,获取食物和进行自卫中演变成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国际竞技运动表演项目。
5.冰雪文化
地处寒温带的嫩江流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每当寒冷漫长的冬季来临时,生活在黑龙江流域大小兴安岭和中下游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土著居民自制滑雪板“骑木而行”在林海雪原中追击野兽、相互雪嬉和冰嬉[8]。族人们乘坐皮爬犁或“脚贴木板”等活动器具,板乘雪力,从山坡上或江的坡坎上飞奔而下,享受着滑行速度和滑行远度带来的刺激和快感。打雪球、打爬犁和赛“狗拉雪橇”也是知冰识雪的鄂温克族和赫哲族人喜爱的一项有趣游戏。“雪地走”也称走百病[9],是满族妇女脚穿底垫10厘米左右高度的鞋子或木履结伴在雪地中进行速度和耐力的比拼。
三、新时代嫩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
1.受地域生态和文化环境的制约,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淡化
良好的体育文化是以区域的政治稳定、良好的经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作为最基本的保障。由于嫩江流域生产与生活环境变迁的冲击,多元文化混杂,聚居民族众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沿江民众的小农意识、宗教意识、小富即安的思想观念仍将存在,加之旧势力、旧习俗从经济、文化、观念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及道德观念。在现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由于对嫩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理念的理解和传播重视程度不够,加之,以时代为特征的各种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传统文化产生的明显冲击,使建立在流域内团结基础上和传统生活习惯上的文化认同出现了明显淡化。缺乏代际传承,文化断层和认同淡化造成当今民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接触的人群不多,甚至鲜少有人知道,更谈不上宣传、保护和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信。
2.教育传承和保护弱化,创新驱动不足导致活态保护机制缺乏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参与人群太少和创意性开发不足,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教育的推进和有效实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及信息技术的冲击,已使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文化熏陶、技艺传承方式和传承环境已经瓦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几无可寻[9]。如何创意开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元素与民族乡村之间地方生态文化资源相互融合的良性产业链条和新的文化业态,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有机融合,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市场优势,实现文化资源的创新和增值成为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趋势。
3.深受西方体育文化因素的影响,缺乏宏观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整体规划体系
就现代文明尤其是西方后现代文明而言,区别于传统体育文化的新式的娱乐休闲体育文化,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和努力,促使传统体育文化从文化环境、生存土壤到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断裂,造成原有的传承动力和文化认同“基因”缺失,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便走进了“崇洋媚外”的不良之路[8]。致使“西化”的体育生活方式登上了现代体育历史舞台,成为新时代体育文化发展的主流。由于缺乏宏观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整体规划体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软实力、话语权此时显得不够自信,传承路径受阻,逐渐走向了注重“竞技化”和“专业化”,忽视了大众性,与群众、原生态文化渐行渐远,走入了“脱离文化生态圈的不归之路”和“失根断流”,甚至灭绝的危险境地[10]。因此,嫩江流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须要科学制定整体发展规划,以唤醒民众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自觉意识,才能实现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
四、新时代嫩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改革途径
1.深入挖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加大对外传播力度与广度
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在区域政府的顶层设计主导下,联合相关主管部门,体育部门,社科院,地方志编撰单位,民间文化研究者,学会及当地沿线的乡镇负责人等携起手来,形成合力深入推进嫩江流域民族体育文化资源研究。组织人员查阅历史资料、文化档案,寻访后人活动,寻找家谱、相关传说和故事,注重收集整理相关习俗史料,编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口述史和资料集,建立专项民族体育文化资料档案。同时,通过与大中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与交流,引进外部智力资源,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式,从民族、宗教、历史等多角度举办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加强交流和合作,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大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对搜集民间口述史料、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等,借用现代人工智能和信息化技术,拍摄、录制形成音像资料、纪录片、抖音或3D网络游戏;出版有关嫩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普及性通俗读物、文学、电视、电影、戏剧、动画等相关作品。在电视台、报纸、互联网(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等媒体或VR实景直播和快闪表演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展示与推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高民众的认知度,扩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影响力,从而最终以一种活跃与可持续的方式实现对嫩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宣传的最大化。
2.大力发展民族节庆,打造地域品牌
节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各地、各民族相互交流的平台,是通过习俗的力量,以约定俗成方式世代相传民族故事的重要载体。嫩江流域作为民族地区,有诸多著名民族节庆活动,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中国莫力达瓦曲棍球节”,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那达慕大会”,齐齐哈尔梅里斯区达斡尔族的“库木勒节”,齐齐哈尔讷河市鄂温克族的“瑟宾节”,齐齐哈尔市富裕县柯尔克孜族“诺鲁孜节”,黑河市、加格达奇市鄂伦春族的“篝火节”,佳木斯市、同江市赫哲族“乌日贡节”,黑龙江绥化市、双城市、鸡西市、宝清县锡伯族“西迁节”,牡丹江市、同江市满族的“虫王节”等等。
开放办节就是要深挖流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内涵,寻求生存空间,找准定位,扩大民族节庆的时空效应,建立“主客共享”链条,将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要素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相交融。充分发挥民族传统体育所具有的健身、娱乐身心、增强民族自信心等价值功能,实现“差异共舞和多元共生”。通过强化策划和多方市场化运作,将多种属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元素,如,骑马、射箭、摔跤、曲棍球等活动嵌入到地域节庆之中,打造一个地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色体验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地标和体验风情园“打卡”地,增加大众获得感。从而达到公众对嫩江流域的认知,对嫩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实现传统民族节日社会效益和商业价值的双赢。
3.活化利用学校场域,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
学校场域不仅是文化传承主阵地,也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薪火相传的“根”,在推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学生是行为主体,需要青少年的积极参与和担当。在当今社会,青少年对现代体育的了解远远超越对本土传统体育的熟知,认知的谈化需要活化利用学校场域优势来贯彻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贯穿国民教育”。
首先,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纳入学校体育课堂,积极建设完善的课程教育体系。在引入嫩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资源时,需要进行大胆改革与创新,要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在保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核的基础上,编写适合本校区域特色的校本教材时,将民族传统体育内容与新时代审美与休闲特征充分融合,使其在规则性、趣味性等方面满足现代生活和体育运动的需要和回归自然、追求文化传承的心愿。
其次,通过运动会、夏令营等方式加强青少年对中华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识与了解,在潜移默化教育中,让其感受民族传统体育的博大精深和魅力,增强青少年的区域民族文化认同感。
4.加强多元业态融合,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与延续的存在基础,也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关键。在新的历史时期,仅仅单纯强调保护在农业时代形成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不够的,要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制定嫩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多元共生规划。借力嫩江流域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优势资源,借助流域民族村寨舞台,给本土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植入现代化的文化基因,打造以现代康体健身、娱乐性等活动和项目为支撑的多元化发展新态势。
在嫩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开发上,注重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等三地进行跨界合作,畅通“微循环”。共同开发旅游线路、旅游产品、研发体验型的旅游运营模式、将自然资源与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相结合,形成以嫩江流域文化为脉络,融入文化、旅游、体育等元素为一体的流域旅游文化产业链。同时,借助“冰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推动,成立“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旅游联盟,扩大开放合作融入“双循环”。通过联合、联动方式,共同谋划开发民俗文化村、建设民族体育文化点,开发嫩江流域体验线,让民族体育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与旅游和民族民俗节庆相融合,通过跨界跨项融合,打造一个多种文化生态、多个民族、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全域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旅游品牌文化传播之路,如,2020年列入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讷河市兴旺鄂温克族乡索伦村,黑河市东北地区最大的民族主题公园“中俄民族风情园”就是将冰雪文化、民族风情、乡土人情等元素融入传统村落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中的典型。
结语
站在新时代发展的新起点上,我们应以新的视角、态度和思路去认识、探寻和发展嫩江流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抓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基因”和“血脉”,充分激发“江”的活力、释放“域”的潜力,做足做好嫩江流域民族体育文化的文章,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在本土扎根,在现代体育文化自信里站稳脚跟,让嫩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