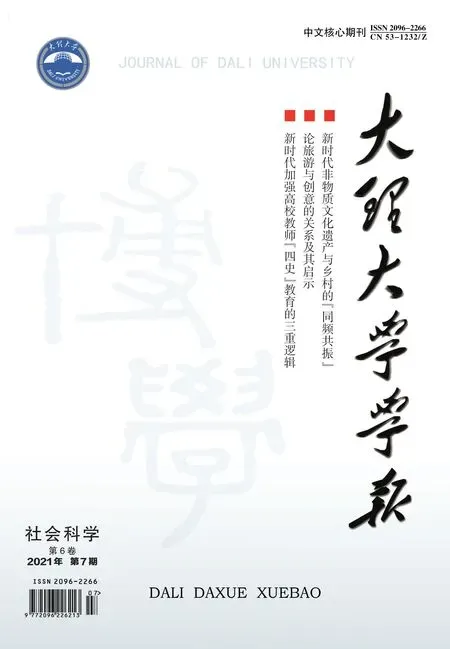日本妖怪文化的传播媒介和再创造机制
——以造型化妖怪为中心
韩 威
(太原工业学院外语系,太原 030008)
“妖怪”一词,在西方语言体系似乎找不到对应词汇,任何一个西方词汇都不足以精确代表这一东方概念。日本妖怪形象众多,大部分源自中国,后经与本土文化融合,逐步演变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妖怪”。直到今天,日本有关妖怪的研究和妖怪题材的文艺作品不但没有衰退,反而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形成了妖怪消费文化。妖怪题材书籍、动漫、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妖怪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生根发芽。
关于妖怪的定义,人们尝试了从多元视角进行解释,以民俗学角度出发,妖怪可以是超越了人类对客观事物的理解的一种奇怪现象,也可以是一种拥有超凡能力而能够引起怪异现象的事物,是自古传承下来的民间信仰。一切恐惧皆源于无形的未知,唯有物化“未知之物”,才能化解由“未知”所产生的恐惧和无力感,故人们以“妖怪”为名来解释未知事物,把依据常理无法判断的现象归结为妖怪作祟,想出各种破解“妖术”的方法,实际意图在于借由某种仪式达到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目的。即“妖怪”系人与自然连接的纽带,是人类与自然沟通的入口。小松和彦认为“日本文化中的妖怪文化有着其独特的文化发展轨迹和历史作用”。他把妖怪文化大体分为事件性妖怪、超自然性存在的妖怪和造型化的妖怪。事件性妖怪是人们无法解释的现象性的妖怪,即事件性妖怪实际是一种“现象”;超自然性存在的妖怪简言之即人类无法解释和控制的超自然性妖怪,也可以是被“妖格化”了的事件性妖怪。造型化妖怪,即被视觉化、有了固定形象的妖怪〔1〕。
妖怪文化得以在日本蓬勃发展,主要原因在于造型化妖怪通过多种载体,经时代洗练,其形象在继承传承性妖怪的基础上不断被再创造并被大众广泛接受。本文首先通过梳理日本妖怪学的发展,把握妖怪学研究动向,再以造型化妖怪为中心,考察造型化妖怪在日本各历史时期的传播媒介,进而分析其形象再创造的机制,讨论日本妖怪文化从民俗文化到大众文化过渡的过程及意义。
一、日本的妖怪学发展
“妖怪学”作为术语是近代以来才有的概念,在此之前一直以非正式的研究形式存在。最早来自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以及妖怪题材的绘画,随着人们的收集整理,妖怪世界才逐渐系谱化。
真正引入“妖怪学”术语的是被称作“妖怪学鼻祖”的明治时期哲学家、教育家井上圆了(1858-1919)。他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全国各地搜集妖怪传说和资料,最终形成了《妖怪学讲义》〔2〕。井上着重从科学角度出发揭示“妖怪”产生的根源,目的在于普及科学知识。井上圆了之后,柳田国男等学者相继针对日本妖怪进行了有体系地整理和研究,使妖怪系统化。
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1875-1962),在研究民间风俗信仰时,探讨了妖怪传说的民俗学意义,将其视为理解日本历史和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重要线索之一〔3〕。把妖怪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来探讨的方法论对后世妖怪学研究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其编著的《全国妖怪事典》涉及妖怪名目之庞大,也为今后的妖怪学扩展研究奠定了基础。柳田把妖怪文化传承的研究范围集中在农村,宫田登(1936-2000)则从“都市妖怪”即现代“妖怪”入手,分析其形成原因。他认为是城市人口促成了现代妖怪形象的变化〔4〕。妖怪学者继承和发扬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开始从大众文化视角出发进行“妖怪”研究。
当代“妖怪”学者小松和彦尝试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在所谓的文化的“黑暗”领域从事重新捕捉日本民俗社会及文化的研究。京极夏彦指出,动漫等通俗文化中的“妖怪”会取代学术上的“妖怪”,使“妖怪”失去其本来面目〔5〕。可见,“妖怪”这一概念并不是亘古不变的,其形象也具有可塑性,随社会进步,传播媒介的演变不断被再创造,因此,以动态的眼光来把握妖怪文化就变得十分必要。
综上所述,日本最初的妖怪学研究目的在于将“妖怪”作为迷信加以铲除,以达到普及科学、文明开化的目的,符合明治时期的时代背景。当然,“妖怪”和妖怪学并未随科学普及而消失,根深蒂固的民间妖怪文化传承促进了从民俗学角度出发的妖怪学研究,民俗学妖怪研究反过来为传统妖怪文化的继承提供有力支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妖怪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从田野扩展到都市,几十年来民俗学视角占主流的妖怪学研究状态也有了新的突破,当代“妖怪学者”尝试从文化人类学以及大众文化侧面钻研“妖怪”,进而分析妖怪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与人,证实了只要人类存在“妖怪”便不会消失,为妖怪文化的持续性和妖怪形象不断被再创造提供理论基础,可见妖怪学经历了民俗到大众化的过程。将“妖怪”作为学问进行研究,日本妖怪文化的生命力之旺盛可见一斑。
二、明治以前造型化妖怪传播媒介及再创造机制
妖怪画是造型化妖怪形象的具体体现,如前文所述,明治时代全面西化、崇尚科学的社会背景将妖怪作为科学的对立面而被排斥,导致妖怪画创作几近停滞。明治时代过后,日本社会趋于稳定,经济、科技发展的同时一度出现“妖怪”热潮,且与明治以前造型化妖怪在传播媒介、创作机制、受众群体方面有显著差别,基于此,本文以明治时代为分界点,讨论日本造型化妖怪再创造的机制及其传播媒介的变迁。
中国文学传入日本的同时,大量画作也传入日本,日本绘画一边接受、融入中国绘画技巧,一边形成了自己别具特色的风格。飞鸟·奈良时代,日本绘画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技法方面,主要以模仿中国绘画为主,在日本美术史上称这一时期的绘画为“唐绘”,用以区分平安时代开始出现的以日本风物为主要题材的“大和绘”。随着佛教传入日本,唐风的佛教壁画成为日本绘画的主要形式,用以表现佛教教义,其中一些绘画出现了动物、鬼怪等内容,为之后妖怪画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这些佛画主要起到弘扬佛法、宣扬教义的作用,其鉴赏性次之。
平安时代,唐代影响衰落,日本绘画风格渐渐强调国风,主要以日本贵族生活为题材,表现日本民族独有的审美情趣、本土四季风物的“大和绘”开始登上日本绘画舞台,其受众也主要为贵族阶层。大和绘线条柔和、色彩艳丽,充斥着和风唯美主义情节、尽显物哀,日本绘画开始区别于唐绘,有了日本民族独有的风格。此时的绘卷中,作为“配角”的、被视觉化了的妖怪形象在日本美术史上正式登场。妖怪被造型化作为文学作品的配图跃然纸上,无疑是日本妖怪文化的重要转折点。
室町时代,艺术进一步发展,绘画方面融合了南宋水墨画的风格,日本人“幽玄”“空寂”的美意识正在此时成形。妖怪文化经长期的积累和酝酿终于崭露头角,表现在绘画上即幕府供养着一批专门从事妖怪画的御用画师,他们从日本各地收集志怪传说,据此绘制妖怪形象,供幕府、皇室及贵族赏玩,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被后世称为妖怪画开山鼻祖的土佐光信,其《百鬼夜行绘卷》笔触流畅细腻,具有南宋水墨画的气质。后世很多画师也选择了百鬼夜行题材,他们一边借鉴土佐光信的作品,一边扩充“百鬼”数量、逐渐使百鬼队伍“发扬光大”。室町时代是武家现世主义思想的萌芽时期,不仅妖怪画作为消遣被幕府、皇室及贵族阶层赏玩,就连“妖怪”本身也成为权谋、政治统治的工具,以武士为主导的统治阶级一边敬畏、祭拜着神明、妖怪,一边将其作为工具加以利用。
江户时期,稳定的社会背景、发达的商品经济促进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町人文化的崛起。町人指日本近世居住在都市的工商业者,是日本近世都市文化的中坚力量,以其为主要受众的新的艺术形式——浮世绘便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浮世绘自然也成为该时期“妖怪”的主要载体。江户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妖怪画师要数鸟山石燕(1712-1788),他从民间搜集大量妖怪素材并将其整理成图鉴,创作了《画图百鬼夜行》《今昔画图续百鬼》《今昔百鬼拾遗》《画图百器徒然袋》四册妖怪画卷,共包含207种妖怪,其作品极大地影响着后世妖怪画家和学者,确立了后世妖怪形象的原型。
显然,明治以前的妖怪造型最初基于民间传说、口传故事,经由画师创作依次通过唐绘、大和绘、浮世绘等媒介使其形象和种类固定化,妖怪的传播载体和受众共同经历了由雅到俗和大众化的蜕变,妖怪不再是人类的“恐惧”,反而成了人们娱乐的对象、表达感情或诉求的工具。
三、明治以后造型化妖怪传播媒介及再创造机制
明治以后,日本社会经济富足、科技极速进步,市场指引下的大众传媒产业随之迅速发展,妖怪文化也通过妖怪图鉴、漫画、动漫、游戏等多种媒体形式实现多元化发展,而造型化妖怪形象的再创造为日本妖怪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以下将结合实例,探讨造型化妖怪再创造的机制。
(一)20世纪60至80年代:妖怪的“二次创作”
妖怪漫画第一人水木茂(1922-2015)无疑为现代妖怪形象的成立作出了突出贡献。1968 年水木茂的《日本妖怪大全》作为《周刊少年Magazine》的增刊被出版发行,涉及妖怪种类98种。为考察其中妖怪形象的创造机制,按照《日本妖怪大全》中的妖怪形象和名字“是否引用了前人妖怪画作”“是否引用了前人妖怪主题著作”的情况,统计如下。
98种妖怪形象中,有62种借鉴了前世画师创造的妖怪形象,同时也保留了对应的妖怪名称。被借鉴的画作中,有57 种妖怪形象参考了鸟山石燕《画图百鬼夜行》,其余5 种源自竹原春泉《绘本百物语》;只引用了名字的妖怪17种,均出自柳田国男的《妖怪谈义》;水木茂还参考与画作同时代的资料,将一些以往妖怪画中的无名妖怪赋予了固定的姓名。如将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师歌川国芳的妖怪画《相马古内里》中未命名的巨大骸骨命名为“荒骷髅(がしゃどくろ)”。《日本妖怪大全中》的妖怪很多都在水木茂的代表漫画及同名动漫作品《鬼太郎》中登场。
从以上统计可知,水木茂笔下的妖怪形象并不是天马行空,大部分是自古传承下来的“妖怪”并有据可循。他是在收集、整理相关妖怪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本人特色对妖怪形象进行“二次创作”,后以漫画、动漫、杂志等载体进行传播。水木茂对于造型化妖怪形象的再创作,是在民俗学基础上成立的。把先前不同时代的妖怪整合在同一传播媒介,便形成了京极夏彦提出的“通俗妖怪”的概念,民间传说中原本没有形象的“妖怪”被赋予具体形象从而实现造型化,并通过多种媒介,经由画师的不断创造,使其形象最终固定下来。
(二)20世纪80年代:既存妖怪形象与原创妖怪形象的共存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日本漫画、动漫产业发展进入佳境,以其为主要载体的妖怪题材作品亦层出不穷。此时造型化妖怪形象的再创作机制出现了新的突破,故事情节中出现的妖怪,既有以民间各地自古传承下来的妖怪为蓝本进行再创作的妖怪,又存在完全由漫画家原创的妖怪形象。如1993 年到1996 年《周刊少年Jump》上连载的《地狱老师》,该作品中有古已有之且传承至今的日本知名妖怪“河童”“座敷童子”等民俗学意义上的妖怪,同时也出现了“厕所里的花子”“食人蒙娜丽莎”等完全由作者原创的妖怪形象。在日本妖怪题材作品中,让既存妖怪与原创妖怪共存的方式已经成为妖怪作品中人物设定的模式之一,如椎桥宽的连载动漫《滑头鬼之孙》就是以水木茂动漫作品《鬼太郎》中的妖怪统领“滑头鬼”为素材诞生的。可见,造型化妖怪形象的创造过程,便是在既存妖怪形象的基础上不断加以再创作的过程。
(三)21世纪以来:原创妖怪形象占主导地位
21 世纪以后的妖怪作品在情节上显现出了两个显著特征:一个是讲述人类与妖怪共存的日常生活,一个是重在塑造妖怪的“萌”。在妖怪形象创作方面也显现出原创性妖怪占主导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绿川幸的动漫作品《夏目友人帐》,描述了天生能看到妖怪的主人公夏目贵志在把友人帐上的名字交还给妖怪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个暖心、悲伤、感怀的怪诞故事。陪伴在夏目身边的妖怪“猫咪老师”的招财猫形象憨态可掬,实则却是名为“斑”的具有强大妖力的妖怪。其中的妖怪绝大多数为作者原创,妖怪名字和形象源于日常发生的怪异现象和剧情中妖怪的本身特征。如被称作“三铃(みすず)”的高级妖怪,形似木马,两只耳朵上分别有三个铃铛,所到之处必先闻铃响,因此而得名。另外,跨漫画、动漫、游戏三媒体的妖怪题材作品《妖怪手表》中出场的人物设定,绝大多数均为前所未有的原创妖怪:会附身让人健忘的帽子形状妖怪叫“健忘帽”;会控制电视信号的妖怪叫“电波小僧”,以上可以推断,原创妖怪形象与名称的创作机制源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怪异现象,原创的妖怪虽然是全新的形象,但其创作过程并未偏离前文所提到的妖怪定义,即“妖怪可以是超越了人类对客观事物的理解的一种奇怪现象,也可以是一种拥有超凡能力而能够引起怪异现象的事物”。
四、结论
本文以造型化妖怪形象为中心分析了日本妖怪形象再创造的机制和其传播媒介变迁。小论通过先行梳理妖怪学的发展状况,以及从古至今造型化妖怪传播媒介的变迁,即唐绘→大和绘→浮世绘→漫画→动漫→游戏,得出:日本的妖怪学、妖怪传播媒介乃至妖怪文化及受众群体,均经历了由民俗文化到大众文化、由雅到俗的变迁,这与日本每一阶段的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结合实例,总结造型化妖怪再创作机制如下:①基于民间传说、口传故事使原本没有形象的妖怪造型化。如土佐光信、鸟山石燕、竹原春泉笔下的妖怪形象,也可被称为“一次创作”,确定了后世许多再创作妖怪形象的原型。②以鸟山石燕、竹原春泉等前世妖怪画师作品为基础的再创造。如水木茂笔下的妖怪形象。其原型绝大多数源自石燕和春泉的一次创作。其后,水木茂对于妖怪形象的“二次创作”又成了当代漫画家们“三次创作”“四次创作”的原型。可见,造型化妖怪形象创造的重要机制之一,便是在既存妖怪形象的基础上不断加以个性化的再创造。③完全原创的妖怪形象。见21 世纪之后的妖怪题材作品。虽是原创妖怪,其造型化的创作机制却始终不能偏离妖怪最初的定义:超越了人类对客观事物的理解的一种奇怪现象,或拥有超凡能力、能够引起怪异现象的事物。
造型化妖怪形象的再创造,是民俗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融合作用下的产物,民俗意义上的妖怪通过现代媒介被大众接受、喜爱、消费并产生经济、社会效益,使妖怪文化发展成为大众文化,妖怪的大众化反过来又为民俗妖怪形象的继承和发扬提供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