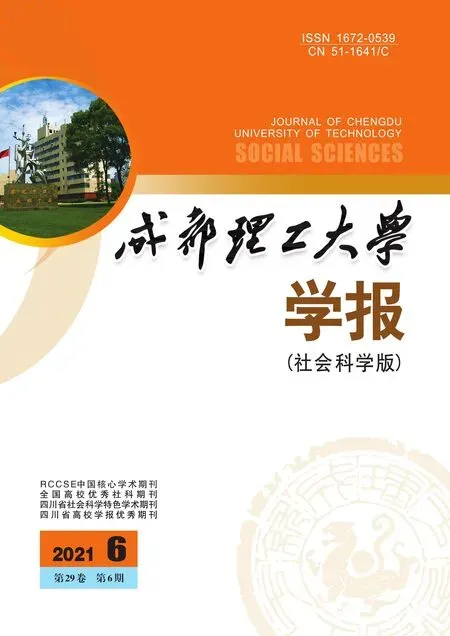“心物内外”与“公私之别”:朱子“格致”方向新释
胡晓艺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91)
“格物致知”向来是理解朱子哲学与心学、理学分殊的关键,是中国哲学史的旧瓶,也装入近代引入“哲学”学科后的新酒。从“格物”方向再次考察朱子思想,可见出理学心学功夫处的差别以“心物内外”理解的不同为大关节。由“心物内外”引发“公私之别”的思考,对朱子的心性问题、理气问题、形上形下问题,可有新的“豁然贯通”。而人心—外物—天理的三层关系之异,正是宋代开始的近世中国私情与公理的关系张力的表现。物理与人心的差别通过理气形上形下的方式哲学地展示出来,分殊为难是朱子思考的关切,道体与常情、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仍然是古今中西哲学前沿的一贯的问题,也正是今人“格致”的方向所在。
一、朱子“格物”方向考辨
朱子“格物”的方向问题可从“格”字的训诂看出,朱子改郑玄注、孔颖达疏中直接将“格”训为“来”,将“格”训为“至”,为心“推极”物,但又以“来”收物于心。比较朱子注与郑玄注、孔颖达疏的区别:孔颖达《礼记正义》中,郑玄对“格物致知”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孔颖达疏为:“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格,来也。”[1]1673朱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
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格,至也。物,犹事也。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未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之而至其极也”。[2]5
朱子取了前人对于“物,犹事也”的注释,而把“格”从“来”转而注为“至”,是一个关键,这两者实际不能分开理解。
《大学》八条目经前后两端的微妙差别在于“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到“物格而后知至”。这其中有三点关键:一是所有条目都是“其”(即代表自身)的努力,而唯有“格物”间不加“其”,这表明“格物”的功夫指向在外,不仅与己身有关,外物与其己相对。朱子延续前人注“物,犹事也”,“事”指人事,“犹”字说明自然外物的理解如同人事,这是一种对“物”的“拟事”,也就是对物的拟人,把人事的即人的生活世界的感知、道德、审美等判断加诸自然世界,或说把心之条理加诸物之条理,天地生意就是人心的生意。朱子所说格竹子也应是看到竹子的树叶下长、节节升高等与其他木植的不同处让人体会“道体之细”,也在人事中做到“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2]37。
明了“其”“物”与“事”所内含的人心—物理的关系,再析“格”与“致”的方向所包含的功夫与目的。郑注孔疏“格”都是“来”,与“格”的本义有关。考察《说文解字》,“各”与“(格)”为古今字,“各”与“出”对,“出”像草木往土上长出,是向外走;而“各”方向相反,像脚板向内,后来的字如“客”从“各”,他人脚板(夊)向自家门口(口)走来,正是外来者;与此相关的还有“宾”(賓),从贝,带钱来的是宾,不带钱的只是客,可见“各”的本义就是“来”“至”。“格”用的正是“各”的本义,即郑孔所采,自外而入内之意。段玉裁在解《说文》时,综合了“来”和“至”两种训释,进行了调和,段玉裁注曰:“以木长别于上文长木者,长木言木之美,木长言长之美也。木长皃者,格之本义。引伸之,长必有所至。故《释诂》曰:‘格,至也。’抑《诗传》亦曰:‘格,至也。’凡《尚书》‘格于上下’,‘格于艺祖’,‘格于皇天’,‘格于上帝’是也。此接于彼曰至,彼接于此则曰来。郑注《大学》曰:‘格,来也。’”[3]442但是段注没有注意到汉语形声字的声旁往往兼有“意义”,因而“格”既然取“各”音,便不会不与“各”的本义有关。因而,“格物”是使外物之理入心中,结合前面的心物关系,即是让心之本有的“至善天理”关照于物,再通过穷物之理体会天理,最后达到豁然贯通一理于心之明德,还是物入于心中,即物“来”到心中。只是朱子更强调了先明“心之理具”,再求物理之同,最后再回到心中。通过这个功夫,最终实现“心与理一”的境界,方是实在。
二、“格”“致”的方向与“心物内外”
以上探讨可以见出朱子训“格”正体现朱子教人功夫论的用心,此处论述可再结合“致”与“至”的区别予以确认。
《大学》前文为“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子注“诚意”为“实其心之所发”,“致,推及也”,而后文是“物格而后知至”,“致”变为“至”,朱子注为“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2]5。前后联系,说明朱子认为“致”是“知”(即明德之识,人心受于天之正理)推及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要通过“格物”,即于人事观照的自然之物中穷至,通过“一物一物豁然贯通”,到“吾心全体大用无不明”,就是“知至”,从“致”知的过程完成了“至”心,所以后一段“物格而后知至”的“格”就有“格”的原初“来”之意,从物入心,表明了这一过程的完成结果,因而前面的“致知”过程在后一段变为“知至”。
“格”的方向正是朱子功夫有“持守涵养未发”和“格物致知未识”两段。前一段是“存心”,后一段是“致知”。《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朱子《章句》言:“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2]37这正是与阳明“致良知”的“致”的方向相区别处,正可以看出心物内外之别。阳明在答复顾东桥的书信中说: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合心与理而为一,则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不言而喻矣。[4]37
阳明以为理解了朱子晚年之论,其实还是误解了朱子心物之意。对于朱子,物不在心中,外物与己心有别,但“只是一理”,也误解了朱子外求于物的“理”不仅仅是物理,也是天理细密能与人心贯通处,而阳明格竹子之物理不通,是因为前面缺少朱子所说涵养心理,自然不可能豁然贯通。对于阳明,“格致”的方向不在物,而在心,物只在心中,与晚年“致良知”一致,从心向外发于物,心发出道德关切,良知心理包含有物理,继续生发出对物理的探寻,心外无物,又是由物入心。只是物的功夫较少,后学容易以己心之发即为天理之显。但良知的开显,直悟本体,“意发于心即实”有着直达天地的能量;朱子的格物致知通过涵养内心之理,再通过外物之理的求索豁然贯通于吾心全体大用,“格物所以致知,物才格,则知已至,故云在,更无次第也”,“格”至最终还是“来”,即从外入于心。《朱子大全》载李孝述言:“物未格,便觉此一物之理……似为心外之理…及既格之,便觉彼物之理为吾心素有之物。”朱子批曰:“极是。”[5]66由于朱子未发前更注重对心意的反观,已发后更注重对物的穷究功夫,“意发于心应实”则更有持守恒常的力量。
朱子与阳明“格”“致”的方向皆是人心,看似功夫上的侧重不同,却是对本体价值世界理解的差别。只是朱子之功夫的重点在通过格物,看到物物的道体细密处,看出人心并不直接同于天理,物在心外,说明人与物不同,也说明物与物不同,因而要一物一物格,体会分殊中的天理一贯,体贴物理以正“己”(“其”)意,最后反观人意,见得天理在心;阳明之致良知,则是物在心中,说明物与己相同,物与物也相同,“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实际事事物物都是吾心良知,如“南镇观花”,“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4]107-108。一己之情发显处就直接感知外物,良知使得外物“明白起来”,是花是草是竹均不重要,“物”的“明白”根本是“人”的存在的“明白”[6]。阳明“心外无物”即是象山“吾心即是宇宙”,因而只要良知发显开去,指向物便直接“致”心体,而不需一物一物“格”去。
三、“心物内外”与“公私之别”
通过“格”“致”方向的考察,可以看出,心学与理学的分歧应不是“心—物—心”的方向分殊,而首先是心物内外问题。对于朱子而言,他强调“格”要先“推及”于物,再“来”到内心,对于阳明而言,“致良知”是直接把吾心之良知送到事事物物,这种差别可以看出朱子与象山阳明所理解的心性结构不同。心学之心即是性,性即是心,心即是本心,性即是情,所发现出都是一体一贯;而朱子主张心性分殊,特别注重的心朱子的心不仅是“天命之性”的存在之所,是“虚灵不昧”的功能本体,也是物质构成的形气之体[7]。正是由于心作为性的物质性的落实处的存在,而引出“理气”“形上形下”等一系列关于心性问题的辩论。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是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史上各家学派借以说明自身哲学体系的重要思想案例。
无论是心体与性体、形上与形下的说法,都说明了“心物内外”是心学理学纷争的关键,前辈学者已有诸多翔实细密的论说,此处将“心物内外”的问题从“公私之别”的角度再做一层引申思考。
朱子心性结构不仅是一形而上的“理”世界,已经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但这不是说朱子认同陆王心学的心统贯一切,朱陆鹅湖之辩后,朱子更加强调“认心为性”不可,在后来“无极而太极”之辩中,心性问题通过“理气”“形上形下”问题使得理学与心学的矛盾更加凸显。理解朱子与心学对这一问题的分殊,有一则材料最紧要,即是在“无极而太极”之辩的书信往来中,朱子借“阴阳”—“太极”之异对于心—性“一而二,二而一”的强调,朱子说:“性犹太极也,心犹阴阳也。太极只在阴阳之中,非能离阴阳也。然至论太极,自是太极;阴阳自是阴阳。惟性与心亦然。所谓一而二,二而一也。”[8]87其中的关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发生,朱子与陆王相比最大的致思关键就是此处的“而”。这个“而”从哲学纯思的角度考虑,与老子之道“一生二”,与庄子“浑沌开窍”,甚至与费希特“自我设定非我”的致思均有暗相会合处,需要专门进行哲学思想史的梳理。此处从近世社会的“公私之别”来探讨“而”的“分—离—合”。
朱子强调理气“不杂”,强调心—性有别,反映的是不以我心为人心,不以我情为物理的思考,强调我心与外物的分殊,近世社会的“公私之别”所引发的物理与人心的差别,反映的道体与常情的分殊,通过理气形上形下的方式哲学地展示出来,理一分殊,分殊为难,正是朱子思考的关切。
以内藤湖南肇端,宫崎市定继成的京都学派“唐宋变革说”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下列三个时期“上古”(远古到后汉中叶)、“中古”(三国至唐中期,特点为贵族政治)、“近世”(唐宋之交,贵族政治没落,君主独裁政治兴起,进入平民社会),与西方古典、中世纪与近代社会相对应,中国史自唐末进入近世社会[9]361。近世社会的重要表现就是私我意识的发显,坊市界限被打破,个体的言说方式通过市井化的词曲说书等方式进行表达,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区隔通过科举制的定型巩固而被彻底打破,社会走向了一种民意的共和。“公私之别”反映一种最高价值统摄生活世界人情复杂的困境,“私情”的差异化已是近世生活开展的一个问题,情境化的棒喝与顿悟并不足以保证私情间分殊的调和,朱子的思路是,借助“天理”予以保证最高价值,天理是最高的无私的“公理”,其不动,则自有公道在;其发用,如“无极而太极”,在分殊人物之情中,各具一太极。程颢“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已注意公心,后湖湘学派张栻等人以“公”释仁,哲学思想史反映时代状况,朱子认为论“公”则注意与“仁”一起说,需“以公体仁”,但不可“以公为仁”:
若以爱无之溥为仁之体,则陷于以情为性之失,高明之见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无物我之私便为仁体,则恐所谓公者漠然无情,但如虚空木石,虽其同体之物尚不能有以相爱,况能无所不溥乎?然则此两句中初未尝有一字说着仁体。须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为能体之,非因公而后有也。故曰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10]1412。
正因“公”到人情社会之“私”中,有一段处理普遍与特殊的张力问题,所以朱子并不以公即是仁,而强调“以人体之”,即是强调性理亦是发乎人情,“仁是生物之心”,这正是朱子又在“不杂”后强调理气“不离”的原因。理气不离,根本是理不离气,是性源于情,绝不可“世有以公为心而惨刻不恤者,须公而有恻隐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11]2454;但人情不一,各有情状,人心相隔,情不能以己度人,发乎公正,只有经功夫的涵养,才能达到心与理一,理气不离不杂的境地,但教人次第,不应“指出教人”(说孟子),不宜“说煞分明”(说茂叔),因而朱子强调从人事上做去是自然,从物事上格去是门径。
朱子的“公”思想,是一种对仁本体的形而上的思考,也是一种以超越情境化的人情世界的“漠然无情”的“理一”,对传统中国社会以私情关系“分殊”为社会运作一般法则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虽然是“哲学”的“形而上”的,但却是中国思想史中较为欠缺的一度。历史的发展是“天理作为公理”的一面被统治者刻意忽视,只取“天理统摄人心”,而朱子逻辑的脉络“天理保障人心”,即“形上保障形下”,“公道保障私情”的一面,正是中国近代社会如梁任公的等思想家在批判中国传统社会缺少“公”思想中所忽视的。“世有以公为心而惨刻不恤”,近代的传统批判以朱子之警觉语为程朱理学的代名词,但历史的缺位并非思想本身的缺位[12]7,朱子的形上世界具有它的力量。
阳明思想在近代的开端,以私情之发为合理纠正了朱子天理思想被滥用的弊病,开显了中国思想中的个体主体性的自由的一度,为熊十力、牟宗三等诸先生所推重。心学以本心之发即“沛然莫之能御”,道德心的动力的充足性即得以保证,道德心蕴含理知之心,良善中有良知良能,良知也可以“坎陷”出科学知识,这种方案是“古典的”“中国的”;而朱子思想中的理气世界的“不杂之公”与“不离之情”则为引入西方“哲学”范式的冯友兰等学者所看重[13]。冯友兰先生一直到去世时仍然强调朱陆之辩的关键是“朱子有形上形下两个世界,而象山只有一个世界”[14]982,正是与其对西方逻辑之思的引入相关,则“分殊为难”,反而需要“理一”才得以保证,“无邪之思”保证“有私之情”。“哲学”正是这种思维的训练,这种方案是“近代的”“世界的”。
然而,哲学“空无一物”,理智“不近人情”,“理一”如何“分殊”,如人跨马,毕竟两橛,知行何不一;正如良知如何“坎陷”一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后学多狂徒。道体与常情,普遍与特殊,存在的重建与此在的安顿,仍然是古今中西哲学前沿的而一贯的问题[15],也正是今人“格致”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