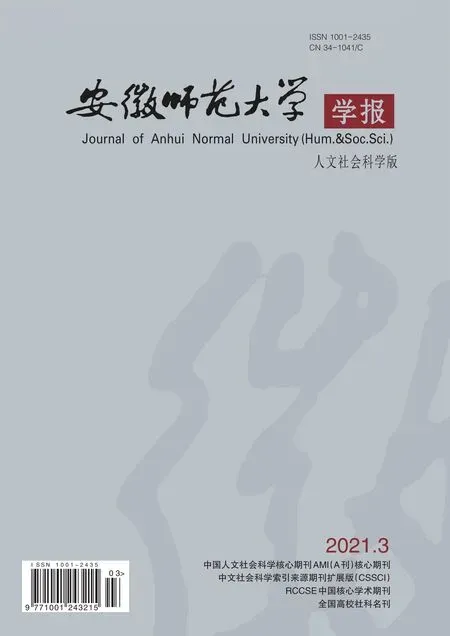战时中国的屈原纪念与文学镜像(1931—1949)★
高 强,李永东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每逢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遭遇危机时,人们总是期望有人来挽救他们,尤其热衷于回望和寻找传统中的英雄形象来应对现实困境。抗战时期,中国面临外敌入侵,民族国家遭受极端戕害,对传统英雄的呼唤自然是水到渠成之事。屈原便是广大战时中国知识分子热切召唤的重要传统英雄人物,相关情形在屈原忌辰的纪念活动和言说之中体现得尤为鲜明。有关战时中国的屈原纪念已经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由屈原纪念而产生的一个新兴节日——“诗人节”,更是成为了研究的重点。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把屈原纪念放置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语境中,探究战争语境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对屈原这一特定的资源加以召唤和重塑?从而具体呈现了怎样的传统征用策略?屈原纪念又对战时中国文学风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民族国家危难与屈原高尚人格的召唤
屈原无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声名最为卓著的文人,其忠君爱国的“忠臣”形象则是古代中国对屈原诠释的主流话语。清季民初,特别是“五四”以降,忠直淳厚、规矩端正的“忠臣”屈原逐渐被还原为“个人”屈原,称赞屈原作为独立个体的个性、情感、自由与独立成为新的言说中心。[1]随着屈原向杰出文艺作者和独异个体的回归,屈原与国家的牵连逐步弱化。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军变本加厉侵袭中国,全民族深感亡国沦丧的危机,屈原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的伟岸角色又被重新唤醒、激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即有人撰文深情怀念起了屈原的伟大人格:“汨罗江畔的屈原,和地狱中的但丁,漂泊在海上的拜伦,都是一样的态度,雄立天地间,与日月争光而无愧色!我爱屈原,我爱他那种伟大和崇高的精神,和那种不断地向无限中追求的力量,这世界一般的大文艺家,都是由这种精神超越现实,而在想象世界中,创造一种新天地!我特别赞赏屈原的杰作,希望世人不要仅仅品题他的词藻,而必须崇仰他的伟大的人格!”[2]对屈原伟大人格的记取和赞誉,是被侵略的现实语境激发的结果,它反过来又为人们反抗侵略的现实诉求提供了精神支持。随着战事愈演愈烈,这种思路越发明显。如李啸狱以诗歌形式告诫人们被日本侵略蚕食的中国和屈原生前面临的情形别无二致,以古鉴今,极有必要学习屈原的高尚节操:“民族贪廉关气运,士夫贤懦致穷通。炎黄向诩多高节,寇迫今兹讵不同。”[3]般若则在《吊屈原》诗歌中将纪念、汲取屈原高尚人格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透彻表达:“志士啊!/你抱着救国救民和改造社会/的志愿!/你不怕一切困难和危险,/你不怕嫉妒和恶人的谗言,/只求真理是否实现,/我钦佩你伟大的态度,/我敬仰你高尚的人格”;“志士啊!/你虽然死了,/芳名千古流传,/我们凭吊你——/不是怀念你文学的天才,/不是追忆你清高的志气,/悲吾民族兮,/有斯人而不遇!/我们凭吊你——/有成仁取义的精神,/不作偷生畏死的沙弥,/不学吟风弄月的词客!”[4]
当然,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人们对于屈原的认识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大唱赞歌的纪念语调之外,也不乏表面看来“不和谐”音调。名为天真的作家发现当时因爱国而自杀的青年,一天天的增多,他提到了一个二十岁的东北少女在武汉投江以及本埠大同学生程淡忘投海反抗压迫两个事例,这些自杀的青年在作者看来“都可说是屈原的继承者”。然而,作者表示当前人们纪念屈原应该学习他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不应该追步屈原也走上自杀轻生的道路,“端午纪念屈原应求生不应求死”。“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屈原的精神,并不是他的行为……我认为今日一方面既无皇帝的淫威,一方面又有民众的势力,无论如何还是需要奋斗到底,我们的口号应该是,除非被杀决不自杀,以免敌人嘲笑我们太不争气;并且不但为了爱国要如此,对付其他一切困难也要如此。”[5]虽然与一般知识分子力赞屈原人格高贵的昂扬笔调有别,天真的屈原纪念稍显冷峻,不过殊途同归,其最终目的同样是为了借助屈原纪念来强化民众的抗争力量。
端午节原本是为纪念屈原而创设的节日,但随着时间流逝,纪念屈原的意图渐渐淡化,端午节转而成了众多民俗节日大家族中的一员,端午节的一系列习俗也仅仅被视为欢度节日的享乐行为。这种情况在1930年代也开始有了一定改观。1934年的端午节,有感于外敌日迫和他国纷纷加紧军事训练,严独鹤呼吁国人在端午节玩龙舟竞渡时,应该“注意国际间的竞渡”,即“世界各国筹备充实海军”的竞争现象。[6]原本民俗意义的龙舟竞渡开始被赋予了民族国家力量展示和竞争的现代意蕴。严独鹤的吁求很快即得到了落实,于是我们看到1939年的端午节,国民政府便在重庆举行了大型水上运动会,孙科、孔祥熙等高官大员亲往参加盛典,组织、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到各种水上比赛中,进而勉励民众将类似的竞争团结精神发扬开去,投入到民族国家反抗日寇的战场上,练就强健的身手和体魄,担当起“复兴国家民族之重任”。[7]在此,可以明显地发现龙舟竞渡等民俗已经被转化成了强健民族体魄的意义,悼亡屈原的端午传统节日也被借用来进行国殇纪念和强化民众的抗争精神。
对屈原的纪念明显属于一种历史记忆,而人们的记忆行为和记忆选择,通常来说都是由现实遭遇所促发的结果,“我们总是从今天的社会环境、今天的需要、兴趣和利益出发对过去进行重塑”。[8]106换言之,人们为何在特定时段开始记取特定的历史内容,与他们的当下处境和现实需求息息相关。1930年代,屈原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引发了越来越强烈的共鸣,有关屈原纪念的言说日渐密集,都是因为日寇入侵后国家受难情形逐步严峻的现实遭遇造成的。而人们对屈原的纪念又主要张扬他的人格力量,其目的则是为了通过对传统的回望和接续,把类似的人格力量深深植入中国民众心底,振奋全民族的抗战精神。
二、宣扬爱国诗人的屈原形象与民族抗战的精神策励
1930年代的屈原纪念还是文人们的分散性纪念,随着“诗人节”的设立,1940年代的屈原纪念则被纳入了比较正式统一的轨道,加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种种负面声音和艰难的现实图景显现出来,作为应对和鼓劲之策,知识分子们便更加积极地投入于纪念屈原的活动和言说之中。此时的屈原纪念也从30年代张扬人格道义进一步上升为宣扬民族爱国诗人的屈原形象,来为民族抗战提供更加强劲的精神策励。
关于诗人节的倡议者和时间,众说纷纭。高兰回忆说,1941年他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组织的一次诗歌晚会,会后他和陈纪瀅、光未然、李嘉、方殷、臧云远、臧克家七人在街上漫谈,交流有关抗战诗歌的看法时,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诗人节,来更好地动员诗人的战斗力量,发挥诗歌的战斗作用,并决定以农历五月初五,也就是屈原沉泪罗江的日子来作为诗人节。这个倡议后来得到了郭沫若和老舍先生等几位前辈的支持和赞助,很快便被文协接受了。[9]常久的回忆明确指出方殷是诗人节的首倡者。[10]郭沫若颇为含混地表示诗人节是1941年由“好些做诗的人”[11]83组织设定的。老舍则在其第一届诗人节的记述文章中写到,诗人节是1940年端阳节在文协纪念屈原的一个晚会中,有人不经意间提出来的。[12]老舍此文是第一届诗人节的即时性记述文章,他的说法应该较为可信,也就是说诗人节应该是在1940年端午节文协的一次晚会中定下来的,而此一节日的明确首倡者则难以确证。
不论如何,1941年5月30日农历端午节这天,是第一届诗人节面世的日子。这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群体性的名义发表了《诗人节缘起》的宣言式文章,称赞屈原艺术和人格的伟大,认为在抗战的炮火里忍受着苦难的当下正是“体验屈原精神的适切的时代”。伟大诗人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豪放的热情,爱国的深思”,现在决定把屈原殉国的日子拿来“作为中国的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的精神”和借助屈原的艺术经验来“育成中国诗歌的伟大的将来”。[13]312效法屈原精神和孕育中国的伟大诗歌,正是屈原纪念和诗人节纪念的两大意图,对此,柳亚子以简洁的语句形容道:“把屈原怀沙自沉的日子,作为诗人节,不但有文学上的意义,还有政治上的意义。”[14]之后的屈原纪念,便主要呈现为表彰屈原的文学意义和政治意义两个维度。
就屈原的文学意义或者说创作启示来说,人们所重点强调的是一种关怀社会的创作视野和刚强不屈、富有战斗力的艺术风格。臧云远力赞屈原是中国诗歌园地里的“白杨树”,他“不因哀怨显出自己的渺小,不因牢骚显出自己的急躁,不因幽美秀丽的境地的包围,而沉沦在自我迷醉的小池子里,像那小鱼儿似的在人海里游泳”;在屈原的诗歌中,“找不到一星儿妥协的灰尘,永远放散着真与美的性格的光彩”。[15]尉迟允然希望借助屈原纪念,能够使得“屈原的灵魂浮上来,浮在每一瓶墨水上,每一个歌喉上”,进而“让那些惨白的、粉红的、暗灰的、痨病的、软骨的文字和声音沉下深渊去”。[16]
在人们看来,屈原的诗歌创作堪为抗战诗歌创作的榜样。于是,纪念屈原,以屈原的创作来烛照抗战文艺的诸多不足,更是纪念和言说屈原文学意义的重要思路。借用陈纪瀅的话来描述,便是借纪念屈原来“检阅检阅自己”,看看“究竟自己的诗文发生了些什么作用,是不是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于抗战?怎样扩大诗歌影响,使诗歌更有效地担当起抗战的宣传任务?新诗质的提高和如何展开创作”?[17]于是,我们看到1944年的第四届诗人节,重庆诗人们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内召开纪念座谈会,主席胡风即在致词中宣称:“诗人节不一定仅为纪念屈原,亦可藉以检讨抗战以来之诗歌之写作。”接着,众多诗人纷纷以诗的语言发言,以屈原为榜样揭示抗战诗歌的一系列问题:何其芳称有若干诗人已入军队为士兵,到乡村作保甲长,生活可更深入;臧克家高呼今日诗人不如屈原,不仅人瘦,“灵魂也瘦了”;王亚平报告抗战以来之诗坛现象,希望注意研究批评;臧云远畅论题材的忘我及为谁,要求“拥抱现实”。最后胡风作结论,希望今后能够产生更多“康健的及有条件的乐观的诗篇”[18]。黄药眠在诗人节谈到屈原时,评价离骚和楚辞的伟大,就认为其不仅建立在魅丽的辞藻上面,而且“建筑于对人民的热爱和对于事业的忠诚上面”。反观抗战时期的中国作家,颇多“娱情于山水,放浪于形骸,或沉湎于声色的赋诗饮酒之中”,与屈原相比“是多么渺小呢”![19]
虽然纪念屈原,表彰和学习屈原作品的魁伟风格是战时中国作家的关注重点,但纪念屈原决不局限于诗歌艺术领域,正如尉迟允然所说:“这节日不仅是‘诗人’的,而是全民族的。”[16]全民族的屈原纪念,就是纪念和张扬屈原的政治意义或者说精神价值,咏叹屈原那种忠爱祖国、不畏强权、不断战斗的品性。关吉罡表示在抗战建国前途进行中的人们,不但应该重新认识屈原,而且要学习屈原那种“坚强伟大的风格,刚健不拔的操守”,悼念其为妥协投降的封建官僚残害致死,而“予以崇高的民族先进之敬礼”。[20]林若明确赋予屈原以“爱国诗人”的美誉,称屈原是“我们国家的荣誉”,他的作品中间“完全为爱国爱民的政治情绪所充塞”,“屈原是一个世纪参加政治斗争的战士,所以他的诗,无一不是政治社会的产物”。在民族多难、国家多事的今天,人们要以“屈原的忠诚爱国的心,眷念民生的哀情,坚强不屈、崇高伟大的人格,不避艰危敢说敢谏的精神”,来唤起“整个民族的敬仰和纪念”。[21]
爱国诗人屈原的精神气节,更是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反抗妥协、反抗投降的重要武器。尉迟允然认为屈原宁愿自杀也不投降的行为,无疑是战时中国民众的精神榜样:“我们的态度如榴火,我们的精神像蒲剑,向我们的敌人以及我们阵容中的败类,不留情的攻击,扫荡,中华民族决不会灭亡的。我们情愿像屈原那样死,不愿像楚怀王那样妥协——妥协就是正中张仪‘连横’的骗局。向暴秦投降,因而也就是灭亡了!”[16]屈原生前饱受楚国内部一些同胞的中伤污蔑,这些中伤污蔑屈原的人们在时人看来,便是卖国投敌、残害忠良的败类,在抗战时期依然可见其踪影。所以,纪念屈原,识别国家内部的“败类”同样是人们的言说重点。方殷以诗歌形式写到:“屈辱的事/仍一代一代地发生/你那陷害者底同族/仍在这苦难的土地上/播埋着伪善的毒种……”“呵,江水一直无情地流去/流去了忠贞圣洁的你/却未曾流去/那人间底罪恶……”[22]倪志操告诫人们纪念屈原就要注意提防阵营内的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之流:“今天当我们国家多难之秋,汨罗河畔战云密布,同时在抗战的阵营内,尚潜伏着不少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之流,我们缅怀先哲,纪念一个伟大的民族战士,实有无限的感慨,愿我全体同胞,皆要以楚国的衰弱为殷鉴,效法屈原的精神,提高民族的气节,一心一意严肃抗战的阵容为争取祖国自由生存而奋斗。”[23]
老舍曾记述过第一届诗人节纪念现场的布置,“正中,国父遗像下,悬起李可染画的屈子像,像前列案,案上有花及糖果。左壁榜曰:‘庆祝第一届诗人节’;右壁题:‘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12]屈原像被置于国父遗像之下,象征着屈原已被装扮成了民族国家的精神符号;而反抗侵略的标语口号则是此一象征内容的具体说明。徐贡真在其关于“诗人节”的《建国历》中解释设置诗人节的缘由和意义时说:“抗战以来,国内诗人咸感屈原诗风人格,两俱不朽。于爱国诗人中最早最著,丁兹大敌当前,国势砧危之际,允宜矜式前贤,用励来者。”[24]纪念和张扬屈原的“诗风人格”,正好是抗战时期屈原纪念的两个维度。谈论屈原诗风,希望抗战诗歌也能学步屈原走出自私的狭小天地,关怀民瘼,不断揭露和批判侵略者的阴谋,最终目的是希望抗战诗歌能够成为战斗性充沛的诗歌,希望抗战时期的诗人能够成为屈原那样的战斗性充沛的诗人。而颂赞屈原的爱国精神和不屈的人格力量,以屈原和楚国的遭遇告诫抗战时期的民众提防一切妥协卖国的言行,更是借助屈原纪念来动员全民族的抗争力量和振奋全民族的抗争精神。张扬爱国诗人的屈原形象,便成为了民族抗战的精神策励。
在此有必要提及的是诗人节、屈原纪念和国民党的关系。现在流传下来的有关抗战时期诗人节和屈原纪念的言说大多集中在左翼作家和中共文人一方,似乎国民党是诗人节和屈原纪念的“缺席者”。而后来更有不少人将诗人节日渐冷清的原因归咎为国民政府的刻意阻抑。如郭沫若在1946年便回忆道:“一九四一年在重庆的一大部分做诗的人不期然地把旧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立地便得到普遍的响应。但只公开地纪念了一年,以后便只好由少数人静悄悄来举行纪念了。原因是文运大员不高兴这个举动,据说是,节日很多,为什么要把端午定成诗人节?诗人很多,为什么要纪念屈原?在这前后关于屈原也就展开了政治上的斗争。”[25]75郭沫若所贬抑的“文运大员”指的是以张道藩为统帅的国民党文化工作运动委员会的相关人员。常久在新时期更是语气强硬地批评说:“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高潮一次再次的袭来,诗人们的各自分散,这个‘诗人节’也就无人再提了。”[10]事实上,如前所述,屈原纪念在1930年代便深受国民政府的重视:诗人节是由文协发动提倡的,而文协又是一个具有强烈官方背景的机构,诗人节的设置不可能没有经过国民政府的首肯和支持。更重要的是,在1941年第一届诗人节的相关纪念活动中,随处可见国民党官方要员的身影。其中既有于右任、冯玉祥这样的“党国元老”,也不乏梁寒操这样实际主管宣传的党政要人。[26]国民党官方报刊《中央日报》更是曾以大量版面来纪念屈原和言说诗人节,前面引用过的包含诗人节的《建国历》也是发表于国民党的官方刊物《文化先锋》上。凡此种种,均证明了诗人节和国民政府的密切关系。国民政府并未小觑诗人节,反而曾一度支持、看重诗人节,相关人员也曾竭力通过诗人节的言说将屈原纳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中。不过,在1942年以后的诗人节庆典中,“官方调门却悄悄的降低了”,诗人节纪念和与之相关的屈原纪念主要是“在一些私人圈子中举行”[27]的情况确也属实。这种情况实与抗战时期深刻复杂的政治话语交锋有关。
1942年3月5日到20日,陈铨的戏剧《野玫瑰》在重庆上演并引起了轩然大波,《野玫瑰》公演结束后,《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中共文人的一系列文章,对《野玫瑰》大加批评,指责该剧对汉奸思想“持着宽容的态度”,是法西斯主义者流“自己写给自己的‘悲剧’”。[28]4月下旬,国民党教育部学术审议却授予《野玫瑰》三等奖,共产党方面的批判声音则越发强烈。在此情况下,共产党便精心策划了郭沫若戏剧《屈原》的演出。1942年4月3日,《屈原》开始在重庆各大剧院上演,引发了一轮观戏热潮。见此情况,国民党方面由潘公展等要人亲自领衔出面,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屈原》的文章,斥责戏剧《屈原》有违历史真实性,是不忠实的胡编乱造,并斩钉截铁、不容商量地宣布,如果有人敢为《屈原》叫好,如果有人认识不到《野玫瑰》的好处,那么这个人只能算是“白痴”。《野玫瑰》和《屈原》就这样成为了国共两党争锋相对的“对手戏”,两个话剧的演出也演变为抗战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两个政党的政治斗争”[29]。而就在国共双方围绕着《野玫瑰》和《屈原》相互争执之际,正是第二届诗人即将到来之时,有人便理所应当地把《屈原》的上演视作“纪念第二届诗人节的伟大贡献”[30]63;更有人回忆称:“《屈原》在重庆是由中华剧艺社以纪念第二届‘诗人节’的名义来公开上演的。”[30]151在此情况下,诗人节和屈原纪念自然会遭到国民政府的冷遇。抗战时期,类似的政党话语争执交锋的情形多有存在,它们对许多抗战文学(文化)现象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后来者重新谈论相关文学(文化)现象时,应该注意其背后复杂的历史原因。
三、萃取人民诗人的屈原形象与革命诉求的道义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抗敌御侮是全民族关注的中心话题,屈原纪念也就被纳入这一轨道之中。虽然有冷热程度的区别,但是借助屈原纪念来号召国民反抗外侮,鼓舞军民士气的意图则是相似的。随着抗日战争结束,爱国诗人的屈原形象逐渐隐退,人民诗人的屈原形象则取而代之。纪念屈原,萃取人民诗人的屈原形象,进而成为中共革命诉求的一股重要的道义力量。
虽说抗日战争时期的屈原纪念主要被用于鼓舞民众对外敌的抗争精神,不过,在这种纪念主潮之外,也有零星文人借助屈原纪念来向内对政府官方施行批判。譬如孟超在诗人节纪念屈原时,联想到了同样在旧历端午习俗上所供奉的一位神祇钟馗,进而语含讽刺地说,钟馗只是给皇帝祛除肉身上的病痛,所以颇受恩宠;而屈原则想医好社稷之忧、国家之疾,甚至全国百姓的灾害,“那当皇帝的就未必会有苦药利于病的精神了”。“钟馗只除明皇的身体上的病,屈原却偏要去怀王的政治病,这结果自然钟馗可以啖鬼,而屈原反被鬼所啖了。”[31]显而易见,作者通过屈原和钟馗遭遇的对比,试图揭露的是直面国家弊病、怀抱家国之忧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往往处境艰难,而无视现实隐忧、甘为当权者仆役的知识分子则生活优渥的现象,这番言说实则是对现实之中国民政府压抑知识分子批判性声音的暗示和讽刺。
当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的一系列问题暴露无遗,尤其是在收复日伪敌占区过程中,国民政府官员大量谋取私利,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民众生活日渐恶化,种种原因让“战争后期滋长的反政府情绪变得更加强烈”[32]485。这时的屈原纪念,明显成为人们表达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场域。上海《益世报》在纪念屈原的社论中写到:“我们悼念这位伟大的诗人,最惋惜是他当时所处环境的恶劣。他以‘嫉王之不听,谄陷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几句话反映当时楚国政府是怎样昏庸的政府,社会是怎样混浊的社会。这样政府,这样社会,牺牲了忠信爱国的人才,也断送了楚国国家的生命。今天纪念屈原,举出这段历史,想爱国爱和平的人,当无不对此伟大诗人,表示痛惜和敬佩。愿请国人,今当国难深重之秋,格外重视这段历史的教训。”[33]谢冰莹首先赞扬屈原的死是“为国为民”的壮烈行为,接着以屈原活到现在更会义无反顾地选择自戕的假设,来批评政府的无力和现实的黯淡。“设若屈原活在现代,眼看着贪污成了‘好听’的名词,汉奸能活动做官,老百姓嚼草根,吃树皮,吃观音土,吃死人,出卖自己的孩子,到最后,一群群饿死在马路上,在田野里,尸骨无人收敛,遗族无人过问;但另一方面,都市在畸形地繁荣,一栋栋的洋房从瓦砾堆里建筑起来了,数不清的汽车横冲直闯地在向行人示威,一桌酒席动辄就是几十万,在跳舞场里,更是挥金如土,连‘活动’一个参议员骑马也要几百万几千万……这种种的现象,他还能活下去吗?”有鉴于此,谢冰莹便喊出了“改良社会”的呼声:“在今天,我们悼念屈原的忠魂,更有无限的感慨,汨罗江畔不知增加了多少饿殍冤魂?许多忧国忧时和屈原同道的人们,都深深地慨叹着:‘这社会,如果不改良,我们还能活下去吗?’”[34]
一系列现实问题使民众开始失去对国民党统治能力的信任感,而中共方面则适时提出了“人民民主”的政治主张,作为自己的革命口号和目标。相应的,屈原纪念在左翼作家和文人那里便被塑造成了“人民民主”政治主张和革命诉求的道义性支持力量,“人民诗人”的屈原形象的萃取模式便是这一点的集中体现。1945年诗人节到来之际,《新华日报》专门开辟了“诗人节专刊”,专刊中便有文章开始呼唤为人民而写作的政治诗人:“在这人民的世纪里,一切的文艺都应该为着人民,所以评判一首诗的好或者不好,首先就必须从人民的观点出发。”[35]闻一多在1946年诗人节的纪念文章中,从阶级身份、《离骚》的形式、《离骚》的内容和人格四个层面正式把屈原塑造命名为“人民的诗人”。首先,在阶级身份上,屈原虽和楚王同姓,却不是一个贵族。因为屈原早已从封建贵族阶级中“被打落下来”,变成了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所以在身份上,屈原便“是在王公们脚下被践踏着的一个”,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员;其次,屈原的代表作《离骚》的形式,也是“人民的艺术形式”;第三,在内容上,《离骚》“怨恨怀王,讥刺椒兰”,“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屈原在此“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最后,屈原的“行义”而非他的“文采”,是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主因,正是屈原以作品和实际行动唤醒了“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的反抗情绪。闻一多称许道:“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36]这之后,众多文人便沿着闻一多的思路讴歌“人民诗人”的屈原形象,热烈鼓吹人民本位的革命精神。峙人赞扬屈原以其“民间化了的”的诗歌,“唱出了他的反抗和愤怒,唱出了他对民族的热爱,唱出了人民的疾苦”,“这对于当时流离失所饱经屠戮的人民来说是亲切的,有感染力的,因此而获得了人民的热爱”。[37]王璞也称“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热爱人民的诗人”,“在人民心目里,他那不屈的气节,热烈的情感,以及关怀民生疾苦,痛恨官僚腐败的性格,却正是完成光辉诗篇,成为人民底诗人的必要条件”。[38]
霍布斯鲍姆有言:“对于旧用途的调整发生于新的环境中,并且是为了新的目的而使用旧的模式。”[39]6从1930年代重新召唤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屈原伟岸形象,到1940年代屈原被知识分子集束式的言说张扬成“爱国诗人”的典型,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屈原被左翼文人构设成“人民诗人”的榜样,屈原形象的生成及其演变,正是“新环境”与“新目的”联手调整“旧用途”的一个范例,体现出鲜明的传统形塑策略。“新环境”与“新目的”的影响力和操控力之大,使得郭沫若在前后两个阶段对屈原的评价可以来一个急转弯。尽管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同样颂扬屈原是“为殉国而死,并非为失意而死”,称赞“屈原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拜的一位伟大的诗人”。[11]23但在正面揄扬之余,郭沫若又批评屈原不能领导民众起而抗争是一种彷徨无力的表现:“但他既有自杀的勇气,为什么不把当时的民众领导起来,向秦人作一殊死战呢?……屈原虽然爱怜民众,但他却没有本领来领导民众。他被放逐在汉北的十四五年,详细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他似乎是始终成为了忧郁的囚人。他念念不忘的是君,是当时的一般执政者,是自己的怀才不遇。他只认识在上的力量,而不认识在下的力量。”[40]73-74但随着时势的转变,在“新环境”和“新目的”的统摄要求下,郭沫若在抗战胜利后很快便转向了对屈原的全力讴歌,他也转而正面评价屈原和人民的密切关联性:“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痛哭流涕,而怨天恨人,而克制自己,不作逃避现实的隐遁,试问不是真正尊重人民、爱护人民,而且这尊重爱护之念既深且切的人,谁个能够这样?屈原无疑是一位政治性很浓重的诗人,而他的政治观点就是替人民除去灾难,对内是摒弃压迫人民的吸血佞幸,对外是反抗侵略成性的强权国家,要依人民的意见来处理国政,团结善邻,对于强权拒绝屈膝。”[25]76
正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屈原纪念所张扬的“爱国诗人”屈原形象对抗战时期的诗人和诗歌有特殊的指引作用一样,解放战争期间所萃取的“人民诗人”屈原形象也呼唤相应的诗人形象和诗歌样态,此即“询唤人民诗人”[41]和“人民诗歌”。纪念屈原,询唤“人民诗人”和“人民诗歌”又主要表现为形式与内容两个层面。
就形式而言,表现为指出屈原的作品大量汲取民间形式,深受人民喜爱,进而要求当下的中国诗人在写作时也要广泛吸收各种民间艺术养分,以期能够产生真正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诗歌”。郭沫若便赞赏屈原的诗歌形式“完全采取的是民歌民谣的体裁”,并将之“扩大了,更加组织化了”。正因为屈原的诗意识是“人民意识”,诗形式是“民间形式”,所以屈原才成为了“彻内彻外的一个人民诗人”。今天要想和人民同步调的诗人们,必须“遵守这样的道路”。[25]77端木蕻良更是认为屈原汲取民间艺术养分所创作的诗歌具备了“朴野”的力量,对中国诗歌而言,只有吸收类似屈原诗歌的那种“野生力量”,只有“去掉那些因袭的有教养的苍白的家畜奶汁养育下的气质”,转而“吮吸野狼的奶”,才是正确的出路。屈原是靠对各种民间传说的化用强化诗歌力量的,而目前的中国诗人则应该认真吸收“我们的民族蕴藏的极丰富的宝藏”,诸如地方戏、大鼓、靠山调、民歌风谣、弹词、双簧、崩崩、坠子等等,“人民的诗篇必须用人民的语言来说出”。[42]走向广阔的民间艺术天地,最终目的无疑是希望诗歌能够深入人民大众心田,因此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届诗人节,许幸之、穆木天、任均、陈伯吹、周牧人、劳辛等上海诗歌工作者们便借助诗人节的屈原纪念,进一步讨论诗歌如何走到工厂、农村、部队、街头,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挥诗歌的力量”[43]。在三四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那里,以“方言土语”为主要代表的“民间化”价值几乎获得了“某种政治神圣化和历史目的论的崇高意味”[44]63,在40年代中期以后,“民间化”的文学“净化运动”则随着中共的政治声势迅速推向了全国。上述纪念屈原,要求作家诗人们深入民间的论调正是“民间化”的文学“净化运动”的重要脉络。
就内容来看,纪念“人民诗人”的屈原形象对中国诗人的启示则是更加坚决地摒弃浪漫自私的风格,以诗歌的形式反映和鼓舞人民反抗专制、投身革命的行动,让“人民诗歌”成为“人民革命”的号角。怀淑批评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诗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迷乱”,即“对敌人的力量作了过高的估计,过分地夸张了处境的困难,而畏缩地放下了武器,使诗歌的主题落进了与实生活毫无关联的虚无缥缈中,甚至与庸俗、瘫痪和丑陋相连,这使诗歌创作不仅仅不能作投枪,对人民的翻身斗争有丝毫帮助,反而使读者困惑,使读者步入忘却现实的迷宫中去”。解决这种“迷乱”的方式首先“要清醒地看今天的翻身的斗争,要清醒地看美蒋及其封建制度的必然垮台,与人民胜利的远景”,然后学习屈原那样“全心全意把诗歌当成献身于人民的武器”,“在战争的现场当中”写作,使诗歌成为“协助或进行实际斗争”的武器。[45]《诗歌月刊》在纪念第六届诗人节时,以“本社”的名义宣称:“历史已经不容许章依萍、戴望舒之流存在了,也就是说,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作品被历史淘汰了。这证明,诗人不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诗人之所以‘多愁’与‘善感’,并不是‘愁’情人不来,‘感’恋人远去。而是‘愁’社会的黑暗,‘感’政治的腐败。……诗人懂得这些,诗人要将所愁所感的高唱起来了,想用他们的声音去唤起那些被蹂躏的奴隶们,那些迷恋于私情的青年们,那些被压迫的群众。”[46]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的屈原纪念所萃取的“人民诗人”的屈原形象,起着号召中国诗人创制“人民诗歌”的重要作用,而创作“人民诗歌”的最终目的则是支持和激励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诉求。这一思路,郑振铎曾以诗歌形式予以了深刻的描绘:“诗人唱些什么?/他不再叹息的唱,人生如寄,日月如梭;/他不再傲慢的唱,杏花疏影,老子婆娑;/他不再自怜的唱,茜纱窗下,寂寞绮罗。”“诗人唱些什么?/他唱的是人民世纪的新歌,/为这人民世纪而作,为这世纪的人民高哦。/他讥嘲着进步阻碍者的愚蠢与罪过;/他揭发着黑暗势力的灰色的网罗;/他愤怒于无理性的压迫与统治的烦苛;/他悲叹着夫死子散,农田荒芜,无目的的内战尽管延拖;/他沉痛的指责着贪污遍国,官肥如鹅;/他诅咒着黑暗,却把定了光明之舵。/他高吭的唱着人民的觉醒与人民争斗,/奔腾汹涌,若东下之长江大河;/他激昂的唱着民主力量的巨大,浩浩荡荡,若怒海之扬波。”[47]
“通过提及一种‘人民的过去’、革命传统、它自己的英雄与烈士”,[39]16常常成为革命者为他们的革新提供支持的有效策略。萃取和称颂“人民诗人”的屈原,正是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有意识提及和重新塑造的英雄形象。正是通过对“人民诗人”的屈原这一道义性支持力量的征用,加之“人民民主”的开明化的政治革命主张,“人民诗人”的屈原形象和“人民道路”的革命诉求,很快便得到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拥护。
四、结 语
1948年,署名辛郭的作者在《中华时报》发表诗人节纪念文章,指出“把‘屈子’做了传教的招牌”[48]是诗人节的重要景观。若略去作者文中的贬抑色彩,则此话不仅适用于诗人节,还是对1931—1949年整个大的战争语境下中国屈原纪念的真实写照。从中性意义来理解,战争语境下的屈原纪念正是把屈原当做了一系列的“传教招牌”。1930年代外敌入侵、国家危机的现实语境促使人们重新召唤出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屈原伟岸形象,展开了新一轮的屈原纪念热潮;到了1940年代,随着诗人节的设置,屈原纪念的声调越发热烈昂扬,1930年代那种分散性的屈原人格精神表彰,发展成了集束式的“爱国诗人”屈原形象的张扬,屈原纪念被明确赋予了民族抗战精神策励的国家性意图;抗日战争结束后,左翼作家和文人则进一步萃取出了“人民诗人”的屈原形象,纪念屈原进而被征用来为“人民革命”提供了道义性的支持力量。从人格伟岸的屈原形象,到“爱国诗人”的屈原形象,再到“人民诗人”的屈原形象,随着时势变迁,人们纪念屈原的言说重心随之变更,屈原所承担的“传教招牌”的具体指向自然也“旧貌换新颜”。前后各异、不断变化的战时中国屈原形象是战争语境下文学发展诉求的镜像式呈现,更体现出各种现实力量对特定传统资源进行召唤、形塑与征用的纪念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