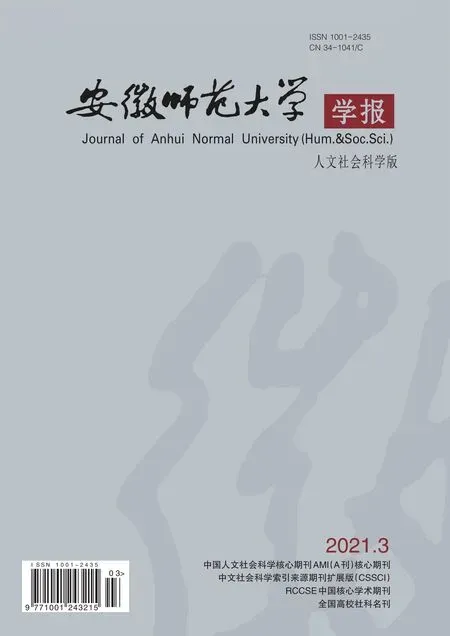论孝定李太后崇佛与晚明佛教复兴*
——以福建宁德支提寺为例的考察
何孝荣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孝定李太后(1545—1614)是明神宗生母,在万历初政及“国本之争”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是明代为数不多且较有政治成就的后妃。她狂热地礼僧建寺布施,是晚明佛教复兴的重要推手。福建宁德支提寺作为所谓的天冠菩萨道场,万历年间得到孝定李太后的大肆崇奉布施而复兴,成为晚明佛教复兴的一个样板和组成部分。
迄今对孝定李太后崇佛的研究,主要有陈玉女、笔者及聂福荣等的论著①参阅陈玉女《明万历时期慈圣皇太后的崇佛——兼论佛、道两势力的对峙》,载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3号;拙著《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335页。,分析了李太后崇佛的各种表现。论述晚明佛教复兴者,有夏清瑕、陈永革、戴继诚及魏道儒等人论著,着眼于剖析晚明佛教复兴的表现特征、佛学思想、禅宗流派复兴等。而对于孝定李太后崇佛促进晚明佛教复兴,包括她对支提寺和天冠菩萨道场的赏赐布施及其佛教复兴,尚缺乏阐发。①参阅夏清瑕《晚明佛教复兴的特点及倾向》,载《五台山研究》2002年第1期;陈永革《经世佛教与出世解脱:论晚明佛学复兴的困境及其反思》,载《佛学研究》2002年卷;戴继诚、赫丽莎《晚明佛教:短暂的辉煌与深远的影响》,载《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魏道儒《中华佛教史·宋元明清佛教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70—327页。本文通过考察孝定李太后对福建宁德支提寺崇奉布施促进该寺和天冠菩萨道场佛教的复兴,来展示晚明佛教复兴中孝定李太后的助力,揭示晚明佛教复兴的诸多面相,深入解读明代佛教史、社会生活史。
一、唐宋时期天冠菩萨道场的打造和支提寺兴废
福建宁德支提寺和支提山在中国佛教中是所谓的天冠菩萨道场,经历了唐宋时期自僧人讫朝廷的长期打造,逐渐为僧俗官民等崇奉礼拜。
(一)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的佛经来源
支提寺位于今福建省宁德市西北40公里的霍童镇支提山。“支提山”之名,则出自一部重要佛教典籍——《华严经》。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佛陀成道后在菩提场等处,藉普贤、文殊各大菩萨显示其因行果德如杂华庄严、广大圆满、无尽无碍妙旨的佛教经典。《华严经》在中国有三个译本,分别是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六十卷本、唐武周时实叉难陀译八十卷本、唐贞元时般若译四十卷本。其中,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因文义最为畅达,品目也较完备,在汉地流传最盛,八世纪以后华严学者大都依其讲习疏释,并创立华严宗。通常所说的《华严经》即指此译本。
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记载:
尔时,心王菩萨摩诃萨于众会中告诸菩萨言:佛子!……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已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东南方有处名支提山,从昔已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天冠,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1]卷45
即心王菩萨在法会中对诸菩萨说,山海之间有二十二处菩萨住所,其中东北方有清凉山,是文殊菩萨与其眷属诸菩萨一万人居住说法之处;东南方有支提山,是天冠菩萨与其眷属诸菩萨一千人居住说法之处。而佛驮跋陀罗译本、般若译本则未提到支提山。
此外,《杂阿含经》《摩诃僧祇律》也提到支提山。《杂阿含经》称“有众多比丘住支提山侧,皆是阿练若,比丘着粪扫衣,常行乞食”。[2]卷50“阿练若”又译作“阿兰若”,意为比丘住处。《摩诃僧祇律》记载,持律第一的尊者优波离“在支提山中住”。[3]卷30无论《杂阿含经》,还是《摩诃僧祇律》,所记支提山都是没有多少特色的僧人住处。而《华严经》支提山为天冠菩萨和其眷属诸菩萨一千人住所,是一个大型菩萨道场,给信众以神圣和震撼之感,又因该经在中国广泛流传,遂为僧俗人等所熟知和重视。
那么“支提山”“支提”是什么意思呢?华严宗第四代祖师澄观注曰:“支提山者,此云生净信之所。有舍利者为塔,无舍利曰支提。或山形似塔,或彼有支提,故以为名。”[4]卷47《一切经音义》也解释:“支提本是塔庙之名,此云山,似之故,因为号。”[5]卷22即支提本意为没有埋瘗舍利的塔庙(方坟),支提山因其山形状如之而得名,是佛教徒礼拜而生净信之处。
(二)唐朝至吴越国时期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的初步打造
中国古代佛教学者在翻译和阐释佛经时,往往刻意将其中一些佛教场所比附、指实到中国,以吸引中国僧俗人等信奉,传播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之一。如澄观疏注:“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昔云既指清凉为东北,则东南影响吴越。然吴越灵山虽众,取其形似者,天台之南赤城山也,直耸云际,赩若霞起,岩树相映,分成数重,其间有白道猷之遗踪,或即当之矣。”[4]卷47即《华严经》所说的东北方清凉山为山西代州五台山,而东南方支提山则是浙江天台赤城山。前者得到中国僧俗人等认可,五台山被打造成为文殊菩萨道场,而后者赤城山被比附为支提山在后世则影响不大。
约在唐末至吴越国时,僧俗人等开始将福建宁德霍童山打造为支提山和天冠菩萨道场。霍童山据说本是神仙霍童所居,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之首。而佛教僧人也看中了这块“福地”。《宋高僧传》记载:
释元表,本三韩人也。天宝中,来游华土。仍往西域,瞻礼圣迹,遇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表赍经栖泊,涧饮木食,后不知出处之踪矣。于时属会昌搜毁,表将经以花榈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殆宣宗大中元年丙寅,保福慧评禅师素闻往事,躬率信士,迎出甘露都尉院,其纸墨如新缮写。[6]卷30
这是霍童山被比附为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的最早全部记载。
上引记载充满神异。一是元表年岁。他于天宝年间来华,即使按天宝十五年(756)起算,到唐武宗最早颁布禁佛令的会昌二年(842)终计,起码相隔八十五年。加上他在朝鲜出生、出家、修行等,则其藏经时在九十五岁以上,这很难令人相信。二是他“遇心王菩萨”。据《金刚三昧经》《华严经》记载,心王菩萨为佛陀弟子,二人同时代。[7]365;[1]卷45排除宗教神异,心王菩萨绝不可能在佛陀圆寂一千二三百年后仍存于世,并与僧元表在“西域”相遇。因此,我们怀疑,元表事迹及霍童山被指为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可能是唐朝后期,即上引所谓唐宣宗大中元年(847)保福寺慧评禅师“迎出”《华严经》时编造出来的,“其纸墨如新缮写”或可透露出一些信息。
这一比附得到朝廷认可并崇祀则在吴越国时。南宋李弥逊《支提山天冠应现记》说到:“南海之滨,有大宝山,名曰支提,众山围绕,于其中闻有大菩萨号曰天冠,与千众俱。往昔吴越有大檀那谥曰忠懿,建阿兰若,集瞿昙子,庄严佛事,是诸菩萨现诸实相,令诸众生起诸信根。”[8]卷22即吴越国末代国王——忠懿王钱俶在此建寺,崇祀天冠菩萨。后《淳熙三山志》抄录《宋高僧传》相关记载(但把“慧评”误为“惠平”,“都尉院”写作“山下都尉寺”),称“钱氏起废为寺,号大华严”,并收录钱俶在宋太祖开宝九年(976)作疏:“国家自辛未年中,爰舍金帛,命所司建精舍,仍铸天冠菩萨梵容,斤斧功成,藻绘事就”,“及差灵隐寺副寺主辨隆为寺主”。[9]卷37钱俶于开宝九年二月朝见宋帝,太平兴国三年(978)正式归降,其新建大华严寺的“辛未年”为其统治吴越国末期,时当北宋开宝四年。
可见,经过僧人比附、编造神异,小朝廷认可、布施赐额,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在唐朝后期至吴越国时期初步打造,大华严寺即支提寺为其核心。
(三)宋朝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打造完成
宋朝时期,支提寺僧人继续进行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的打造。前引《宋高僧传》的记载,如元表归宿、与慧评的交代、钱俶何以知晓等,简单粗疏,并不充分完满,神异色彩也不足,因此说服力并不强。宋代寺僧遂对此加以改编增补,宣扬说,元表得心王菩萨指示,携《华严经》住霍童山那罗延窟,“旦夕披诵,金光发现”。法师元白闻之,往见,元表曰:“吾所诵《华严经》也。汝就龙王借一片地以卓庵,吾即付汝”。元白“遂陈悃,果感龙王涌沙填地”。元表“乃现神通,腾空而去”。元白“出甘露寺,邀都尉司僧慧平、慧泽,率乡老迎请此经,具奏闽王”。闽王“阅遍,复进钱王”。钱王“宣问灵隐寺了悟禅师”,“于是遣沈相国同了悟禅师来闽寻访”。了悟清耸等入山,见到化成大寺和天冠菩萨千躯,甚至还和他们“栖宿共话”。钱王叹异,“敕了悟相地建剎,装塑三宝及天冠千尊、心王菩萨一尊,化诸有情,同登佛道”。[10]卷4这样,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叙事里增加了“法师元白”,使其从元表处得到指示,且各展示出神异,再由元白等报告给闽王,闽王奏报钱王,钱王派清耸禅师与沈相国往探,结果他们真的在霍童山中见到变幻出来的寺庙和天冠菩萨千躯。虽然仍多与史实相牴牾,却建构起一个较为严密、完整的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传承叙事,而且活灵活现,让人不得不信。
钱俶建大华严寺,“延了悟禅师居之”。了悟即僧清耸,晋安郑氏子。出家,“初参法眼”即法眼宗创宗人文益禅师,“后因阅《华严》感悟,承眼印可”,为吴越国王室礼敬。钱俶“命于临安两处开法”,“后居灵隐上寺日,署了悟禅师”。他奉命与“沈相国”到宁德,据说见到天冠菩萨及化成寺。钱俶“大惊叹,敕有司建寺”,以为住持,“称开山祖云”,“嗣法眼益禅师”。[10]卷3不久清耸回灵隐寺,“命记室隆禅师继席”。[10]卷2“记室隆禅师”即僧辨隆,先在灵隐寺依清耸出家,后“闻悟师卓锡支提复归,侍巾瓶,命典书记,因称记室云”。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7),辨隆“以钱王之命,继主法席”。[10]卷3清耸为禅宗法眼宗僧,兼弘华严,辨隆为其弟子,二人先后上堂说法。
宋朝皇室重视天冠菩萨道场。雍熙二年(985),宋太宗敕赐大华严寺改名为“雍熙寺”,“分太平寺金字经一藏赐之,岁度僧四人”。[9]卷37淳化元年(990),宋太宗召见辨隆于便殿。辨隆阐述禅理,宋太宗赐号“佑国记室禅师”,并赐紫衣、绢、钱及田四庄等。[10]卷3政和五年(1115),雍熙寺“更律为禅”,即由律宗寺院变更为禅宗寺院。六年,宋徽宗改赐寺额为“政和万寿寺”。[9]卷37
大华严寺(雍熙寺、政和万寿寺)所在山位于“霍童万山中”[11]卷12,“在霍童之右”,[10]序随着皇室的提倡和崇奉,以及僧人宣传、打造,天冠菩萨道场信仰日益为民众所接受,皇室、官民将该山称为支提山。《宋史》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宁德县支提山石上生芝草十五本”。[12]卷63南宋初期担任过户部侍郎的李弥逊作《支提山天冠应现记》,《淳熙三山志》登载“支提政和万寿寺”在“支提山”。南宋《释氏通鉴》明确指出:“福州支提山乃天冠菩萨道场。”[13]卷12而寺院名称,最晚在南宋时民众已俗称其为支提寺。《淳熙三山志》记载:“西湖新买官地砧基簿十本,内四本藏之本州及三县架阁库,六本藏之雪峰、鼓山、东禅、西禅、支提寺、紫极宫常住,永远照用。”[9]卷4此后,支提寺俗称一直沿用,至清朝康熙年间真正改名“支提寺”。
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收成受旱涝灾害影响最大,因此祈晴求雨基本上是官府、民众求神拜佛的最重要目的和仪礼之一,受到崇奉的神佛往往需要具备此“灵异”。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既被打造,就势必要回应和满足官民祈求保佑,尤其是祈晴求雨的愿望。南宋时,福州府“亢旱日久”,官民“发心远诣支提山,迎请千圣天冠菩萨圣象,入府祈求甘雨”。结果菩萨显灵,“大施润泽,连日滂沱,三农遂获有秋之望”。后菩萨“法驾还山”,天仍阴雨,官民竟再祈求天冠菩萨停雨放晴,“以全圣力者”。[14]卷23这些表明,僧俗人等对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的打造工作基本完成。
二、元朝至明朝中期天冠菩萨道场的衰微圮废
元朝至明朝中期,虽然最高统治者多崇奉佛教,但关注、垂念天冠菩萨道场者很少,加上个别时期国家政策、地方形势的变化,支提寺和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时兴时废,但总体上衰微不振,直至圮废为墟。
(一)元朝支提寺修建和天冠菩萨道场兴废
元朝时期,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为僧俗人等认可和崇拜。但是,由于最高统治者崇奉藏传佛教而压制汉传佛教,以及福建和宁德地方小环境的变化,支提寺也曾遭毁废。如至元二十年(1283),建宁路总管黄华叛乱,政和万寿寺毁于兵火,“佛像、宸章、碑记灰烬,无有存矣”。[10]卷4据说,当地民众盗窃铁天冠菩萨像铸釜,“洪垆鼓锻,相好俨然,惟流水若汗液状。锻炼数四,终不能坏”。乡民惊惧,“仍送还山”。[10]卷6这既反映了支提寺被毁废破坏,也可以看出民众中的天冠菩萨信仰。
次年,元世祖敕愚叟澄鉴禅师重建。澄鉴为本县人,年幼出家,“参无文璨禅师,遂入其室”。后历主各寺,“学者望风而至”,是一位知名禅僧。他奉敕重建支提寺,“历十五载,始得复命”。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赐号“通悟明印大师”。澄鉴又“以其羡置竹、福田二庄,为寺修造之费”。[10]卷3这样,支提寺殿堂修复,寺院经济增强,天冠菩萨道场又一定程度地兴旺。不过,钱俶所铸赐天冠菩萨像却难以恢复,所谓“后寺毁于黄华之难,像亦遭劫火。元重兴,获三四于故址”。[10]卷1
(二)明朝前期帝后赏赐修建和支提寺短暂兴盛
明朝建立后,明成祖大力提倡和保护佛教,取消“僧、道限田制”,在南京兴建大报恩寺、静海寺等寺院,多次举办佛教法会,编撰佛教著作《神僧传》等,并两次编集、刊刻《大藏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崇信藏传佛教。皇后徐氏也崇奉佛教,在南京兴建唱经楼,“唱念佛曲,化导愚氓”[15]卷24,还与明成祖一起伪造《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为他们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提供“合法性”[16]。对宁德支提寺,永乐五年(1407)宦官周觉成“建大殿”,明成祖赐额“华藏寺”,“诏无碍禅师住持”。[10]卷2无碍为霍童陈氏子,“少从明极和尚薙染,住仁丰、凤山二剎”。明成祖命其住持华藏寺,“赐紫衣一袭”。>[10]卷3徐皇后则重铸千尊天冠菩萨像,“高尺许,赍至山中,仍建宝阁于佛殿之西,以祠焉”。[10]卷4元末以来接近毁废的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在明初得以重建为“敕赐支提山华藏禅寺”。
借助明成祖、徐皇后的布施赏赐,无碍禅师大力经营,“殚心竭力,开本山井尾田,播种二石。其徒祖靖继之,播种五石,东至院前堂池,南至大坑,西至墓后垄,北至大岭,以为佛殿长明灯资。”[10]卷2支提寺再次兴复,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恢复兴盛。
(三)明朝中期支提寺和天冠菩萨道场毁废
明朝中期,虽然最高统治者仍多崇奉佛教,但历朝帝后没有关注支提寺和天冠菩萨道场者。而国家佛教政策的变动,地方动荡,也波及支提寺、天冠菩萨道场。
先是,正德十五年(1520),宁德邻县古田县有张包奴起事,“据古田鸡啼寨,剽掠四境”。古田县尉钟奎带兵镇压,“逐贼至寺,时属夜半,昏黑不辨。僧恐有诈,不敢开户,止宿于山门之外”。钟奎大怒,“又惧不能平贼,遂以鸡啼为支提,文饰其罪”,即将发音接近的“鸡啼”“支提”混淆上报,诬称支提寺僧参与起事。“监司信之”,遂檄宁德知县桂宗美毁寺。桂宗美“虽力白其冤,寺亦遭毁”。[10]卷4《支提寺志》也记载:“宗美知其诬,白之,虽置勿问,而僧众厄于残暴,不能守矣。”[10]卷2寺僧逃散,寺院逐渐荒废。
嘉靖时期,明世宗推行禁绝佛教政策,清除宫中佛像,焚烧佛骨等物,拆卖各地私建寺院及荒废寺院,停止开度僧人,严禁僧人设坛传戒说法,打击了佛教。[17]在宁德,嘉靖六年(1527)倭寇劫掠,支提寺再“遭兵燹”,殿堂焚毁殆尽,“唯祖堂岿然独存,实伽蓝呵护之灵”。[10]卷2不管伽蓝怎么“呵护”,支提寺已经圮废至极。弘治《八闽通志》尚记载,宁德县支提寺等四十三寺“俱存”。[18]卷79到了嘉靖《宁德县志》则称:“寺观近例多废”[19]凡例,支提寺“今废”![19]卷2
支提寺寺院经济也遭毁废。宋太宗时,赐以大印庄、太平庄等处四庄,“共计四十六顷零”,支提寺是十足的寺院大地主。至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丈量本寺田册”,有田十六顷三十六亩[10]卷2,寺院经济仍很强盛。正德年间,“寺毁业荒”,田产被民人分占,“官佃纳租”。至嘉靖二十二年,御史陈豪题准,变卖支提废寺田产,“价银二千九百余,解京助工”。[20]卷2其后,嘉靖三十二年,僧人一阳来支提寺废址,“于乱烟荆莽中结茅独守,二十余年不倦,山场赖以有存”。[10]卷4他“志存兴复”,但是“力不从心”。[10]卷3支提寺、天冠菩萨道场变成了废墟。
三、孝定李太后赏赐修建和支提寺、天冠菩萨道场的佛教复兴
万历年间,明神宗生母孝定李太后狂热地崇奉佛教,再次对支提寺加以赏赐、修建,支提寺、天冠菩萨道场佛教得以复兴。
(一)孝定李太后狂热崇奉佛教
孝定李太后,顺天府漷县(今北京通州)人。嘉靖年间选入宫,为明世宗第三子裕王朱载垕王府宫女。嘉靖四十二年(1563),李氏生子朱翊钧。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朱载垕册封为贵妃。隆庆六年六月,明神宗朱翊钧即位。七月,尊为“慈圣皇太后”。时明神宗年方九岁,因此李太后严厉管束教育,是内廷的实际主宰者,在外她信任和支持大学士张居正辅政,推行改革。《明史》称:“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21]卷114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后,神宗亲政,李太后基本不再干预军政大事。但在“国本之争”中,她两次隐忍而终发,先后迫使神宗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命福王常洵之国,使拖延已久的“国本之争”得以解决。因此,她是明代为数不多的较有政治成就的后妃。[22][23]万历四十二年二月,李太后去世,谥“孝定”。[21]卷114
明神宗冲龄继位,李太后“忧勤鞠育,为祖宗社稷、天下重器所寄”。[24]卷21为了“资福”去世的穆宗、保佑小皇帝神宗及大明王朝,她“大作佛事”。明神宗亲政以后,她安居养老,仍狂热地崇奉佛教,欲借佛教力量保佑皇室康宁、宗社安定。其崇佛表现有:
(1)大肆修建寺院。李太后“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21]卷114她不仅自己出资,而且经常裹挟年幼的明神宗、其他后妃、王子、公主及宦官、宫女等共同布施。据不完全统计,李太后带领神宗人等修建的寺院,北京十八所,外地二十余所。[2]299-335建寺数量众多,殿堂佛像庄严,花费帑金巨大,在中国古代是空前的。
(2)礼敬皈依僧人。李太后“崇重三宝”[24]卷27,其大肆修建寺院,皆以礼敬之僧住坐。不仅如此,李太后还给僧人大肆赏赐佛教法器法物以及金钱、田地、冠服等生活用品。一些名僧、高僧死,李太后往往赐祭葬、建塔。她皈依高僧憨山德清,甚至要延清德清入宫,“面请法名”。德清不敢,“绘像命名以进”。她“悬像内殿”,令神宗“侍立”,“拜受法名”。[25]卷上
(3)频繁举办佛教法会。万历初年,李太后等多次在京城普安寺“建立斋坛”,内经厂宦官“效为佛事”者还从而学习。[24]卷29李太后又在各地“大作佛事”,“天下名山自五台始,延高僧十二员”。[24]卷22万历十八年,僧如迁奉李太后懿旨,“于慈寿寺开净土法门,在会者千二百众”。[26]卷43华严宗高僧镇澄,李太后“命于都城千佛寺讲所著《楞严正观》,又于慈因寺讲演诸经”。[24]卷27她频繁举办法会,祈求皇室安宁、明王朝统治稳固。
(4)编集、刊刻《续入藏经》,颁赐《大藏经》于各地寺院。李太后“亲阅藏经,深得佛祖之意”[27]444-446,有感于明初的《永乐北藏》(636函)收录不全,遂命编刊《续入藏经》41函,一起颁赐全国各地寺院。如万历十四年,神宗“敕颁十五藏,散施天下名山”[24]卷53。万历十七年,李太后又捐内帑银两,于汉经厂刷印二十藏,“散施各省名山寺院”。[28]卷8据不完全统计,万历年间李太后与明神宗颁赐给各地寺院的《大藏经》近五十部[2]315-322,花费难以数计。此外,她还经常赏赐单部或多部佛经给一些寺院、僧人。
孝定李太后狂热地崇奉佛教,在万历时期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皇室崇佛风潮。当时人说她“信佛甚殷,布施甚广,京师人称佛老娘娘”。[25]卷上
(二)孝定李太后对支提寺赏赐修建
孝定李太后对天冠菩萨也信奉甚殷,多次布施赏赐,修复支提寺,礼敬寺僧。
1.派遣僧人圆慧重建支提寺,改赐寺额为“万寿禅寺”。
万历元年,据说李太后“一夕兆梦僧人前导,至一高岳,名曰支提,有千天冠示现”。醒后,她命宦官在京城寻找梦中的导引僧人,结果在吉祥寺找到了大迁圆慧,“携之复命,命图形以进,酷肖梦中”。李太后召见圆慧,“谈称懿旨,敕行来山,重兴古剎”。[10]卷4这样的说法也是神异,不可尽信。我们怀疑,李太后阅读或听说过《华严经》及疏注,知悉天冠菩萨道场、支提寺和僧人圆慧(甚至是宦官和圆慧合谋而哄诱李太后),于是编造出这一神话,再派宦官去找到圆慧,命他前往修复支提寺。
圆慧,字大迁,京师军籍。嘉靖六年(1527)十九岁时,依京师吉祥寺临济宗高僧翠峰德山禅师出家。寻受具足戒。“立禅三年,誓明大事”。其后四处游方,“居终南,徙伏牛,游淮浙,历陕蜀,参拙牛、秋月、大休、白云、太虚六十余员善知识”。再到峨嵋山谒性天禅师,得印可,“付以 衣 法”。[10]卷3他“复 回 都 下,博 涉《华严》”[10]卷4,是一位兼弘华严的禅宗高僧。
圆慧奉敕重建支提寺,“命工度材,凡七载告竣,殿宇廊庑,焕然一新”。[10]卷3原本沦为废墟的“华藏禅寺”,至此神宗改赐为“万寿禅寺”[10]卷2,明显寓含为李太后及朱明王朝祝釐之意。
2.赏赐《大藏经》及冠服仪仗等。
万历十八年春,圆慧“诣京复命”,李太后“迎居慈寿寺”。[10]卷2慈寿寺位于京城外八里庄,万历四年李太后带领潞王、公主等捐建,择礼敬老僧觉淳“主之”。[29]卷13李太后“又赐园一区,庄田三十顷,食其众”。[30]卷12作为李太后主建的皇家寺院,该寺“亦称上方兜率院,方丈布地,无非氈锦,供佛果馔,悉四方珍物”[25]卷上,“华焕精严,真如游化城乐邦”[31]卷27。李太后将圆慧迎居于寺,“遣近侍张近朝左右供奉”[10]卷3,可见其礼敬。
不久,圆慧要求回山,李太后慰留。圆慧再住八个月,复请回山,李太后才同意。万历十八年底,她派慈寿寺僧万安赍送“敕赐全藏六百七十八函,金冠一顶,五爪金龙紫衣一袭,黄盖一把,御杖、金瓜锤、龙凤旗各一付”[10]卷2,前往支提寺供奉,并护送圆慧。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万安等入闽,福建巡抚赵参鲁“因疏请留经于[省]城之开元寺”。[32]卷16具体原因,据寺志记载,赵参鲁“以支提居万山中,艰于祝诵”,“遵旨奉《龙藏》及御器并师于本省开元寺供养”。[10]卷2而据实录记载,赵参鲁奏报说,支提寺附近有宝丰、遂应二个银矿,容易招致采矿者私聚,生出变乱。因此,他要求“将支提寺僧移入省城寺中,并申矿禁”,“部覆,从之”。[33]卷234不久,礼部又题称,“近福建有僧妄称钦差,欲重建支提寺,以觊银坑之利”,称圆慧要重建支提寺,私采银矿,易致祸乱,神宗“命严逐重治之”。[33]卷234但支提寺僧并未迁,圆慧也未“严逐重治”,而是“遵旨奉《龙藏》及御器并师于本省开元寺供养”。[10]卷2这样,李太后赐给支提寺的《大藏经》等及圆慧都被留奉于福州开元寺。万斯同《明史》称“参鲁怒毁寺,徙其僧。大迁闻,逸去海上”[34]卷331,记载不实。
万历二十一年,圆慧再次入京谢恩,李太后“传旨慰劳”。他在京“居五阅月,奏归,仍赐紫衣四袭,敕中使王文送至江南”。次年,安庆诸绅衿留住,圆慧“遂有终焉之志”,但弟子“坚请回山”。[10]卷3八月,圆慧去世,寿八十六,腊六十七。
3.赏赐渗金大毗卢佛像等。
李太后崇奉天冠菩萨,念念不忘支提寺。万历二十五年,她又“遣内官张文赍赐渗金大毗卢一尊,绕座千佛重一千斤,供大殿中”。[10]卷2其实,李太后这次赏赐还有“《华严》《楞严》《般若》《金光明心地》《涅槃》《报恩经》各一部,龙文幡二合,铜钟磬各一件”。[32]卷16
4.明神宗再赐《大藏经》。
明神宗孝事李太后,对其崇佛多有“助施”。万历二十七年,他“念皇太后前赐支提寺《藏经》,已从守臣之议,移镇城郭,复命所司刻印全藏,特差内经厂掌坛御马监太监赵永赍送支提”。[32]卷16新赐《大藏经》至,为支提寺“镇山”。
(三)支提寺和天冠菩萨道场的修复和佛教复兴
孝定李太后对支提寺的修复赏赐,促成了支提寺、天冠菩萨道场佛教的复兴。
第一,支提寺修复,山中庵院林立。圆慧奉李太后命重建支提寺,得到地方官员、僧俗人等重视和支持。经过七年经营,“一时殿阁寮舍,备极雄丽”。其后,李太后又陆续赏赐,进一步建设支提寺,使其成为远近闻名的皇家寺院。藉此身份,支提寺继续得到明朝皇家赏赐和僧俗人等修建。皇家赏赐如,崇祯九年(1636),田贵妃“遣替僧华严赍赐铜准提一尊,时留供辟支银千两,修皇忏祝圣”。僧人修建如,万历三十一年,圆慧上首弟子住持明启等“募缘重建”大殿,“极尽华美”;十二楼,原为斋堂,寻焚毁,崇祯十一年僧性敏“募福州弘衍林公建为僧寮,曰七透”;雍熙堂,即祖堂,崇祯十二年僧真隆“鸠众重建”;禅堂“窄狭”,崇祯十三年僧性敏“募宪副林公弘衍重建”[10]卷2。可见,支提寺从此修建有人,保持兴盛。
与此同时,僧人来山者日多,在山中也陆续建复了不少庵院。所谓“嗣后说法开士日盛,各各选胜,辟静居焉。西有那罗、辟支岩,东有安溪、法华、师子窝,南则金灯精舍、东湖南峰庵、天冠坪,而北紫芝庵”。[10]卷4仅《支提寺志》“庵”条明确记载的万历至崇祯年间建复庵院就有十余所。[10]卷2支提寺和天冠菩萨道场走向繁盛。
第二,高僧说法授徒,僧众汇聚修习。圆慧作为来自京城、兼弘华严的禅宗高僧,奉敕重建并住持支提寺,提高了支提寺、支提山的声誉和佛学水平。他“戒行精严,接物应机,不假文字”[10]卷3,声名远播,“四方弟子,山中云臻”[10]卷4。他“度众甚多,惟择有功行者十六人住山,分福、寿、康、宁、祖五房,余各遣化一方,为倡导之师云”[10]卷3,培养出大批弟子。
一些高僧居山修习讲法。《支提寺志》作传的明朝高僧四位,即前期无碍禅师,万历时圆慧禅师、真受法师、真常律师。真受,字(号)天恩,汀州吴氏子。万历三年(1575)二十七岁时,来支提寺,圆慧推荐寺僧明香为其师,“薙染受具”。真受“常问义学于冬晖法师,而得其传。复叩心印于一山大师,尽得其旨。又与三淮师为友,朝夕咨决。由是,渐、顿之教,泮然无疑”。“冬晖法师”为讲宗僧人,“一山大师”为知名禅僧,“三淮”为“三怀”之误,即明末兼弘唯识的华严宗高僧雪浪洪恩。万历十一年,真受别构精舍于支提山金灯峰下,“四方争迎,开讲无虚日矣”。他“见地超脱,言行端凝,至于诱诲学者,不假辞色。凡主讲席一十九处,所著《心性录》、《金刚解》、《心经要集》行世”[10]卷3,是一位禅、讲兼通的高僧。真常,字(号)樵云,漳州周氏子。幼年出家,“律身清苦,过中不食。思诸佛以戒为师,行持不怠”。万历二十七年,真常来支提山,依辟支岩“缚屋以居”,“与其徒如信处之志坚,啖虀茹蕨,不求世营,凡十余年所”。后往住开元寺,“四方云衲争依之”,“为四众广授木叉大戒”。万历四十年,回辟支岩,“扩充殿宇,顿成奇观。由是,缁素不惮寒暑,而往参焉”[10]卷3,是律宗高僧。
圆慧、真受、真常等高僧弘传禅宗、华严宗、律宗等各宗派,支提寺、山成为僧人汇聚、佛教兴旺之所。时支提山“亡论住山焚修之众,即十方参禅之僧,与夫游人羁客,日不下千余指”。[10]卷4明末有官员游支提寺,见“诸僧皆披夹衲,左右侍,说无生话”。[32]卷16所谓“无生”,即涅槃的道理,即指佛法。天恩真受法师居金灯精舍,“徒子莫不学通内外,义明顿渐”[35]卷10,具有一定的佛学水平。
第三,官民皈依信向,布施礼拜。圆慧得到宁德乃至福建官民人等信奉礼敬,“其时,三山王参知应钟、林方伯懋和诣师,征诘奥义,赞赏不已。及当道刘中丞尧诲、商直指为正、郑观察善,并诸藩臬大臣、乡搢绅先生,莫不延之上席”。官员信奉礼敬圆慧如此,普通人就更不用说,“海内缁素,望风皈向,参请殆无虚日,座下恒绕数千指”。[10]卷3真常居辟支兰若,“远近僧俗,望风皈信”。[10]卷2真西在山中“结茅住静”,“道俗向化”。[10]卷2各位僧人能够建寺立庵,都是皈依信向的官民布施捐舍的结果。时人谢肇淛即说圆慧“以无上法宝,引导当途诸宰官,为天冠菩萨重建华藏寺于宁德县之支提山”。[35]卷16僧超宗募捐“建六度堂于支提之说法台”,有商孟和“愿舍百金,而诎于赀,乃作画百幅以代之”。[36]卷2
另外,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的“神异”,也吸引着官民信众前来礼拜崇奉。自宋代以来,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就有“圣钟铿鸣、天灯烨煜,求以诚心则应”“岁旱祷雨颇验”等“灵异”。[19]卷2此为嘉靖《宁德县志》所记。万历年间支提寺、山建复后,这些“神异”仍得流传。如祷雨祈晴灵验之说,清人记载说:“寺前有五龙潭,祷雨神应。”[11]卷12再如“天灯烨煜”,万历二十五年,宦官张文赍送大渗金毗卢佛像等至寺,据说“虔祷三昼夜,越夕,果现于峰前。初见一灯,须臾为二,渐至三十有六。久之,得四十九,错落虚空,照耀山谷”。再如秦川张大光游山,宿金灯精舍,据说“忽见殿庭晃耀,遽出视之,圆光大如车轮,起峰顶,倏合为一,复散为三”。张大光合掌赞叹,“踊跃无量”[10]卷6,成为虔信的护法宰官。
第四,赎田置产,寺院经济强盛。寺院经济是佛教、寺院存续的经济基础。明代中期,支提寺寺废田失,寺院经济毁废。因此,圆慧重建寺院,同时着力恢复寺院经济,募缘赎回寺田:万历元年,“观察邹公善、邑侯韩公绍赎回原田二百亩”;万历五年,“大中丞刘公尧诲赎回三百亩零”;万历十五年,“大方伯陶公大顺、按察司张公偲、县尹徐公文翰、延平丞吴公某先后捐俸,共赎田五百余亩,咸以供僧”。这样,十余年中,支提寺已经赎回“霍童并本山四处”寺田一千余亩。诸檀越“更议赎各庄之田”,圆慧“坚辞,恐田多粮广,有妨净业”,“议遂寝。”[10]卷2其后,天启三年(1623),本县石堂信士林奇玉又买得二十四都堂边田十四亩零,“喜舍千冠座前香灯并祭田,祈求子孙昌盛者”。[10]卷2支提寺山场,正德年间被“乡民恃强侵占”。万历二十一年,寺僧如提控告,“抚院许、按院刘审断归寺,仍给示立界,禁止再占”。[10]卷2而山中庵院也垦田购地。如天恩真受法师建金灯精舍,“又于山坳芟草柞木,垦田数段,于是香积不匮,撒速恒足”。[35]卷10
由于孝定李太后的崇奉赏赐,寺僧圆慧等人艰苦经营,支提寺、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在万历以后得到修复,佛教复兴。人称“[大]迁[圆慧]师兴复于前,[明]启等缵继于后,朝廷宠锡,山川光重,八宇精蓝,无有逾此”。[10]卷2乾隆《宁德县志》仍称“寺复振兴,至今称盛焉”。[20]卷2
四、结论:孝定李太后狂热崇佛促进了晚明佛教复兴
中国佛教在历经明朝中期一百余年的衰微之后,到了万历年间,出现了声势浩大、发展迅猛、席卷全国的复兴浪潮,这就是所谓的“晚明佛教复兴”。它是千余年中国古代佛教史上回光返照式的一抹亮色,同时也是近代佛教的曙光。晚明佛教复兴的动因无疑是当时佛教内部的振兴自救,但是官民信众人等的檀助,尤其是万历年间孝定李太后狂热地崇奉佛教,也提供了强劲动力。万历以后支提寺、天冠菩萨道场佛教的复兴,正是一个极好的诠释。
第一,什么是“晚明佛教复兴”?
晚明佛教复兴是针对明代中期甚至元代以来佛教衰微而言的。唐朝“会昌法难”以后,中国佛教走上了衰微的道路。五代、宋朝时期,佛教各宗派仍能有所发展和创新,稍显振兴。但至元朝,统治者崇奉藏传佛教,贬抑汉传佛教,且尊教抑禅,使“禅学浸微,教乘益盛”。[37]卷22而所谓的“教乘益盛”,前注魏道儒书称,教僧们宣讲的仍是“唐代各宗注疏讲经”,“殊少创新”。
明太祖、明成祖支持和崇奉汉传佛教,使佛教各宗派都获得一定程度的振兴。不过,明朝佛教政策也导致佛教进一步衰微。明太祖要求僧人重视佛教经典学习,且为统一思想,“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15]卷2,使禅僧向义学靠拢,讲僧也“以融合诸宗学说为特色,专弘某一派或某一经的人极少”。[38]277尤其是明太祖将寺院、僧人分为禅、讲(指华严、天台、律等宗派)、教(专做经忏法事者)三类,使教僧(赴应僧、经忏僧)专业化,严令只许他们为民间做法事,于是佛教内部出现了向有可靠收入的教僧的倾斜,明代中期以后“占到整个僧侣总数的将近半数”[39],佛教也被斥为“死人佛教”“经忏佛教”,社会形象和声誉低落。加上明代中期最高统治者主要崇奉藏传佛教,大肆鬻卖度牒,嘉靖年间推行禁佛政策,使佛教越发衰微,“自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阒寂”[40]13,宗派不振,传承艰难。嘉靖年间停止度僧,禁止新建、修复寺院,甚至下令变卖毁废寺院,佛教衰微至极。
晚明佛教复兴是明清佛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学界对此有一些专门探讨。前注夏清瑕文指出:“佛教在经过宋元及明中期前的相对沉寂后,万历年间出现了一种较为盛行的复兴气象,主要表现为高僧的辈出、寺院的繁兴、义学的兴起以及僧侣融入主流文化之中,佛法充当社会精神支柱等。”[5]前注戴继诚等文认为:“寺院重建与扩建是晚明佛教复兴的突出表现”,“晚明佛教复兴另一重要表现是教内外僧众再次掀起研究佛教经典的兴趣”,“晚明四大师与禅宗诸大德是晚明佛教复兴的核心与纽带”。有学者强调,万历年间不仅涌现出“晚明四大师”等佛教高僧、名僧,“而且还出现了佛教宗派、佛教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复兴景象”,高僧、名僧“以重修佛教寺院为弘法中心,带动了当地佛教的发展”,“寺院僧人与佛教居士都致力于佛教著述的编纂汇集与刊刻流通”。[41]16-18还有前注魏道儒书从僧人佛学思想、所属宗派、集聚方式等角度指出:“明末佛教复兴运动自然划分为两股潮流,或者说两个阵营。一股潮流主要在都市城镇里奔涌,是以所谓‘明末四大高僧’为代表的‘佛教综合复兴运动’;另一股潮流主要在山林村野中流淌,是以临济、曹洞为主体的‘禅宗复兴运动’。”总之,学者讨论的晚明佛教复兴,主要表现为寺院繁兴、高僧辈出、宗派兴起、僧侣融入主流文化、居士佛教发展等方面。
第二,孝定李太后狂热崇佛促进了晚明佛教复兴。
晚明佛教的复兴,无疑是当时佛教内部的振兴自救,当然也离不开官民信众人等的檀助。笔者在考察明代南京寺院及佛教时,曾有阐述。[42]194-197、[43][44]而在官民信众的檀助中,尤其以孝定李太后的狂热崇佛给当时佛教复兴以强力推动。
以寺院修建而言。万历年间,李太后在京城及各地修建寺院近四十所。这些皇家寺院的修建,强势带动了官民僧俗人等在京城及各地修建寺院之风,使明代中期以来相当多的圮废寺院得以修复重建。有僧人称,李太后“承悲愿力,现国太身,兴隆三宝,建大法幢,使域内名山皆成宝地,寰中胜迹尽化伽蓝”。[24]卷22时京师“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赡养之腆,则又十边储而三之”。[45]40-41
以高僧、名僧而言。万历前、中期,京师高僧、名僧汇聚,“学道人如林,善知识则有达观、朗目、憨山、月川、雪浪、隐庵、清虚、愚庵诸公,宰官则有黄慎轩、李卓吾、袁中郎、袁小修、王性海、段幻然、陶石篑、蔡五岳、陶不退、蔡承植君,声气相求,函盖相合,莫不曰髯公语语,皆从悟后出,遂更相唱叠,境顺心纵”。[45]33-34慈慧院、慈悯庵、千佛寺、卧佛寺等“皆具讲席,名僧居坐,善信如云,四处听讲者千百计”。[46]卷中这些高僧、名僧中,不少人是李太后礼请而来,还有的是为京城佛教兴盛环境而来,所谓“走京师”,“上者参宿访耆,证明大事,次者抱本挨单,文字润泽,下者趋骛宰官,营办衣食”。[45]41他们在北京参访听法,修学结士,赢得名声,不少人也成为高僧、名僧,奔向各地,再把佛教复兴的种子撒向全国。还有一些外地高僧、名僧未曾入京,但李太后也予以赏赐布施,礼敬表彰,对其说法授徒颇有助益。
晚明高僧、名僧各据一方,传法授徒,或棒喝呵骂,倡导禅宗,或讲经解疏,弘传教门(指讲宗诸派),或高扬禅净一致,禅教兼弘,诸宗整合,于是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以及唯识学、净土教等宗派、学说重新有了讲授传承,“禅教律净一时并兴”。[41]350魏道儒书称,主体则表现为以“晚明四大师”为代表的“佛教综合复兴运动”和以临济、曹洞为主体的“禅宗复兴运动”二股潮流,改变了明代中期以来的佛教面貌。至于僧侣融入主流文化、居士佛教发展,则与高僧、名僧辈出及宗派兴起等有因果关系。这些,无疑都与孝定李太后狂热地崇佛有一定关系。
另外,李太后发起编集、刊刻《续入藏经》,并将其与《永乐北藏》一起赏赐给全国各地寺院,对各寺院殿堂修建、经藏配备、寺僧研习佛经乃至寺院声誉提高也有极大的助益。
孝定李太后狂热地崇奉佛教,且长寿安居,明神宗又孝事之,对其崇佛加以纵容和支持,使得她崇佛持续时间长,布施赏赐力度大,涉及地域范围广,影响深远,超过历史上的其他后妃和明代帝王,前注拙著称其“对汉传佛教不能不说是一个强大的刺激,一些沉寂已久的佛教宗派又呈现兴盛状态,佛学研究也比以往繁荣活跃许多,促使其从明代中期以来衰微中走向复兴”。
第三,孝定李太后对支提寺的赏赐布施,促进了支提寺和天冠菩萨道场的佛教复兴,是李太后狂热崇佛推动晚明佛教复兴的极好诠释。如前所述,支提寺、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因李太后的崇奉,敕命京城高僧圆慧前往重建,并改赐寺额,又赐佛像、《大藏经》等,带动了支提寺和天冠菩萨道场的重建和后续修建,支提寺、山从明代中期废墟中一变而为“殿阁巍然,缁流踵至”。[10]卷4禅宗、华严宗、律宗等兴起,官民僧俗人等崇信,支提寺和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佛教复兴,成为晚明佛教复兴的一部分。清人缕述支提寺、山兴废指出:“考自唐、宋,而元而明,再经毁废,都缘劫运而变更;三度兴隆,皆荷天恩之浩荡。”[10]序支提寺、天冠菩萨道场佛教的复兴,是孝定李太后狂热崇佛、推动晚明佛教复兴的极好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