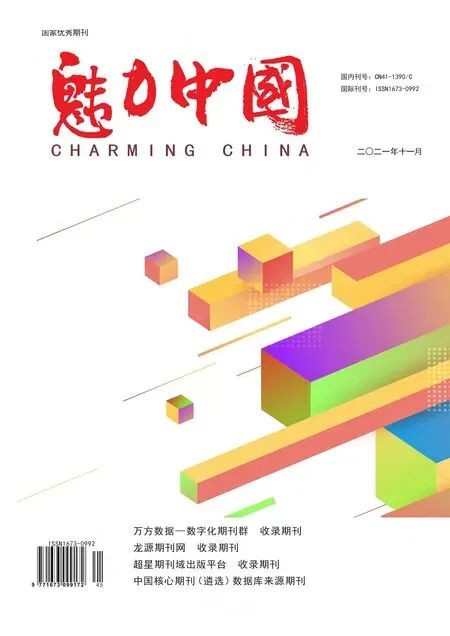中国国家治理新思路与国际法新局面
曾小芮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1)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当今国际格局日异月殊:新冠疫情对世界格局造成猛烈冲击,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增加,国际组织造法问题冒头,国际法碎片化特征明显……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发展自然的与国际局势融合在一体。要应对国际挑战,抓牢国际机遇,中国国家治理必然要立足当前的国际背景,明确治理理念,统筹治理模式,提升治理能力。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国际法正是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的需要。国际法作为国际正义的标志,为建立国际秩序开展国际合作提供框架,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机制。为保障中国国家治理理念的优越性,统筹国内外格局,提升中国国际治理能力,必须要善用国际法,同时,我国国际法的国内研究也需要顺应时代发展,开创新局面,为增强中国话语权,更好地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一、中国特色与国际法理论的创新
我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国家治理的理论层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国际法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积极因素,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理论提供方向指引。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为专制制度服务的国际关系体系,以《维也纳公约》为例,马克思视其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突出的国际法假象之一”。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时提出一系列基本准则: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宣言》中号召工人阶级追求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其次在普法战争背景下发表宣言将和平视为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在有关英美冲突的系列文章中提出和平解决争端的准则。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也在俄共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国家间关系准则。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有大量鲜明的国际法理念值得借鉴,其对于和平的追求,对于霸权主义的批判,都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政策为我国在新时代国际法学的形成确立了指导方针。如“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要求清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再如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特色国际法理论提供重要框架。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为中国国际法理论注入了更多灵魂。邓小平关于主权与人权问题提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后又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发展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进入21 世纪以来,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领导集团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观点,对当代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指引价值和意义。中国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理念,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方式促进全球共享发展;通过系列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和机制倡导国际法治思想和理念。
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时期中国政策是有重要的导向标,既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法理论提供了支持也提出了期许。国际法从前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是一套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构建起来的体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应当反思现存的国际法观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不一味推崇西方的国际法思想而是在学习和反思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体系,在国际法上也要有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当然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在关注理论构建本身的同时还要着眼于中国理论的世界市场,扩大中国理论的世界影响力,提高接纳度。
(一)在制度层面,首先,镇街非税收入的执收没有具体法规支撑,财政部虽然发布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但相应的实施细则等有关具体的规章制度没有及时配套。其次,镇街实现的非税收入未真正纳入非税征缴系统,仅仅靠财政部门的调度上缴,具体上缴收入的是什么内容、应收多少、是否足额征收等等,财政部门无法具体掌握。
二、时代挑战与国际法方法的创新
[80] [美]帕特里克·克罗宁:《南海地区的权力与秩序:美国南海政策的战略框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1期,第36页。
国际法有文化内涵,成为一种国际关系的话语,代表着国际交流的方式,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外交形象和文化实力。法律的语言功能也被尼可拉斯·奥努夫所提及:法律规则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自身就有行动的性质,因此塑造者人们的认同,形成了一种文化圈,沉淀着社会的秩序。在国际社会文化圈中,国际法是国际法主体交流的工具,各个国家通过国际法阐述自己的立场,进行沟通磋商和交流合作。由于中国不能够妥善地用法律的话语表达中国的立场,导致很多国家、公众对于中国的态度存在误解,认为中国算不上是一个文明、容易对话、容易相处的国家。这也导致了其他公众认为中国很傲慢,不懂得规则、不尊重规则,不按规则办事,从而增加了中国威胁论的扩散和影响。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和平友好传统的文明国家,中国本身并没有蔑视规则或者挑战现有国际规则的企图,但是由于对于国际法的不熟悉,没有用国际法这种语言工具来清晰阐明自己的立场造成了一些误解。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国际法这种话语工具,更广泛和深入地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同时让国际社会了解和信任中国的立场。
从研究方法来看,国际法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采取文献调查法、观察法、思辨法、历史研究法、概念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以公约、条约文本、国际法案例或事件为重要研究对象,强调逻辑自洽。这种研究方式固然有优越性但是是否可以引入更多可量化指标来提升论证的科学性,例如对国际法院或海洋法法庭判决进行梳理并形成数据统计。其次,虽然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法观和研究方法,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往往不自觉采取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偶尔会忽略整体性原则和实践性原则,忽略系统各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或浅尝辄止未能深入实践。此外,国际法研究似乎缺乏跨学科动力。为回应社会时代新发展,要求重新审视学科分工、综合知识并跨学科。总之,国际法的研究需要不断扩宽领域,走在国际前沿以引导国际发展趋势,同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并尝试引入其他学科的新思想、新方法,尝试进行科学化、数字化分析。
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已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故国际法研究也应当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和国家的需求。近年来,国际法学者研究的主要领域在海洋法、空间法和国际法基本理论。国际法基础理论研究经久不衰,依旧保持着相当的数量。与此同时,国际法新领域逐渐崛起,网络空间法研究占到5%,外层空间研究占到7%,资源与环境研究占到7%,对于北极地区等特殊区域的研究也在进行,可见国际法发展的迅速性和国际法领域的开阔性。
三、国家需求与国际法角色的创新
我国一方面要面对以“中国威胁”为代表的国际压力,一方面又提出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推进合作共赢开放体系建设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目标。国际法作为调整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方式,理应肩负起满足中国国际发展需求的重任。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旋律的时代背景下,国际法不仅是以惩罚为内核的约束者,还应该通过其内在的价值和理性发挥指引和评价作用。国际法是衡量行为的规则体系,就必然体现出其排序与指引的功能。国际法具有引领和劝导的功能,在理论上不仅能强制国家约束国家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国际社会的思想、文化去塑造国家。国际法与国内法相比缺乏强制性,碎片化程度高,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研究不能仅仅从法律规范性的角度进行,应该注重国际法角色的转化。
从近期国际法研究方向来看,虽然重点突出,紧随时代潮流和现实需要,但是领域还是稍显单一,传统国际法分则中的重点如国际人权和人道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国际争端解决研究尚存在缺失。就海洋法而言,文献资料虽然相对丰富,但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数量算不上充沛。研究视野难免局限,部分文献也存在缺乏新颖性或现实性的问题。
由于国家具有硬实力上的软法和软实力上的硬法的特点,国际法研究不仅要注重其规则层面上的效力,关注国际法的约束力,通过国际法解决争端,同时应该重视国际法话语功能,通过运用国际法并提升运用国际法的能力为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遵守国际法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促进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良好的国家形象又为中国国际行为提供方便,减轻发展压力,同时,国际质疑和舆论朝好的方面发展又会反过来促成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为了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中国必须充分利用国际规则提升自己的合法性,通过解释和发展国际法证明中国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让国际社会逐步接受中国,理解中国,信任中国。
那几年,我和妈妈还有外婆生活在一起,日子温馨又平静。那段时间也是妈妈创作最顺利的一段日子。她用很多篇童话记录了我成长中的点滴。童话里的主角是小动物,也是我。她接连出版了一系列儿童作品,多篇儿童诗入选了小学语文教材。
四、结语
十九届五中提出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从制度层面勾勒蓝图。一反面正视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的时代背景,在总结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优势的同时提出我国国家治理发展的目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对外政策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增加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目标。国际法不可避免地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应在国际法理论,国际法研究方法,国际法角色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为我国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相应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