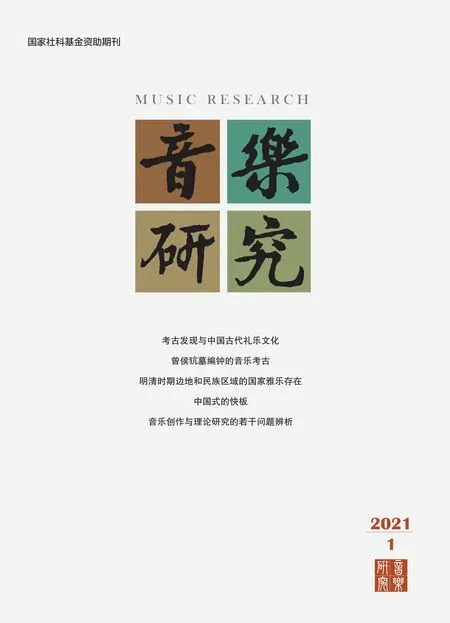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
文 方建军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关论作踵出不绝,贡献了许多研究成果。总体而看,目前的研究大多基于传世古代典籍,侧重于文献记载的诠释分析,而对于考古资料的运用则不是十分普遍。本文主要依据考古发现资料,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物质构成角度,对礼乐文明和礼乐文化,礼乐文化溯源,“礼辨异”和“乐统同”,以及“礼坏乐崩”的实质等问题试加探讨,不当之处,恳予指教。
一、礼乐文明和礼乐文化
目前学界将礼乐文明和礼乐文化并称,常将二者互见和混用。实际上,礼乐文明和礼乐文化在概念上还是有所区别。从考古学的观点看,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标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文字的发明、铜器(冶金术)的产生、城市和大型礼仪建筑的出现。这三项文明产生的标准,在学界业已获得普遍认可。
从文明产生的三个标准衡量,商代已经完全进入文明社会。不过,商代的甲骨文已是发展比较成熟的文字,它基本是商代晚期的考古遗存。从理论上讲,在甲骨文之前,古代文字应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和阶段。考古发现有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器物刻划或书写符号①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晚期陶扁壶上的朱书符号,山东邹平丁公出土龙山文化晚期陶盆上的刻划符号。参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85—388 页。,有些学者认为是早期的文字,当然还存在一定的争议。目前这些仍在探讨之中,但无论如何,文字的产生应早于商代晚期。
青铜器的制造,在夏代和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产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有夏代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爵、斝、盉、鼎等,青铜乐器则有铜铃;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晚期墓地发现有陶寺文化早期的乐器铜铃。而大型礼仪建筑,在夏代和新石器时代晚期均有发现,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大型宫殿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宫城和宫室建筑,陕西神木石峁皇城台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峁文化古城遗址即是。②有关考古发现情况及资料出处详见后文。由这些考古发现综合而看,古代文明的基本要素和条件在夏代应已具备,若加上可能是早期文字的书写和刻划符号,则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应可上推至新石器时代晚期。
相较于文明而言,文化的定义甚多,其间当然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而言,文化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这两个层面需要社会来加以维系,即文化是社会的复合体。从考古学观察,作为文化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其产生可以早至旧石器时代,如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和骨器等生产生活用具,洞穴绘画艺术以及骨哨、骨笛等乐器即是。③参见方建军《音乐考古学通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 年版,第43、121—122 页。因此,文化的产生要早于文明,它通过特定人类共同体习得和传承下来,并包含于文明发展之中。
由上所述,中国古代文明包含有礼乐文明,如商周青铜器里的青铜乐器,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音乐史料,商周大型礼仪建筑遗址内发现的乐器等,均表明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整体文明的组成部分。然而,作为文化的礼乐,则早于古代文明而出现,并延续传留至文明发展阶段。这从以下对礼乐文化的溯源可以看得出来。
二、礼乐文化溯源
众所周知,礼乐文化在古代中国的确立,有一项标志性的事件,即“周公制礼作乐”。这一史事在《左传·文公十八年》 《礼记·明堂位》和《逸周书·明堂》均有记述,其中以《礼记·明堂位》所载最为详瞻: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至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8 页。
说明西周早期确实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的问题是,礼乐制度乃至礼乐文化是否即始自西周早期。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来简要梳理礼乐的含义。
礼乐应分为礼和乐两个部分,与此相应,礼乐制度也分为礼制和乐制两类。
就周礼而言,有广狭之别。狭义的礼指吉、凶、军、宾、嘉五礼,广义的礼是指在宗法社会中按照人们的身份地位而制定的政治等级制度,各级职官包括周代姬姓贵族和非姬姓贵族。乐则是配合礼而建立的用乐等级制度。
礼制主要表现在礼器的配置和规格,形成所谓列鼎制度;乐制主要表现为乐器配置和乐队编制、舞队佾数和乐舞曲目的规定和限制,在钟磬编列上形成所谓“乐悬”制度,在舞队规模上则是佾数的差别。如 《周礼·春官·小胥》云:“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大夫判悬,士特悬。”汉代郑玄注:“宫悬四面悬,轩悬去其一面,判悬又去其一面,特悬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宫室,四面有墙,故谓之宫悬。轩悬三面,其形曲,故春秋传曰请曲悬。”⑤同注④,第795 页。而舞队佾数的规定,依《左传·隐公五年》所说,是“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⑥同注④,第1727—1728 页。。
由上可见,以精神文化为主体的礼乐文化,分别具备礼和乐的物化形态,在考古学上表现为随葬礼器和乐器的配置组合样式。礼器组合的最高规格是“九鼎八簋”,钟磬编列的最高规格是“宫悬”,而舞蹈人数的顶配则是“八佾”。另据《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述,郑人曾用乐师、编钟、编磬和女乐贿赂晋侯,晋侯将其一半赐与魏绛,“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礼也。”⑦同注④,第1951 页。显然,最能体现礼的乐器配置是钟磬之类的“金石之乐”。由此观之,礼乐文化包括形而下的“器”和形而上的“道”两个层面。正如《左传·成公二年》所说,“器以藏礼”⑧同注④,第1894 页。,“器”蕴涵着礼的精神文化内涵。乐器不仅是演奏音乐的工具,而且成为拥有和享用者身份地位和权力的标志,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上述礼乐制度和内涵,基本属于周代的情形。现在不妨依此来逆推和追溯礼乐文化的早期发展状态。
先看西周之前的商代。安阳殷墟发掘的商代墓葬,从商王、王室成员到贵族奴隶主和方国首领,等级差别十分明显。体现在墓葬形制和规模上,有商王级别的四条墓道十字型大墓,贵族奴隶主的两条墓道中字型大墓和一条墓道的甲字型大墓。当然这只是常见的墓葬形制,其中也有例外,如殷墟妇好墓和郭家庄M160 虽然都是长方竖穴墓,但墓主人却分别为商王配偶和贵族奴隶主。这些高规格的墓葬,不仅有青铜礼器出土,而且还有金石之类的乐器随葬,乐器品种有青铜编庸(铙)、编磬、特磬、埙、鼓等。安阳殷墟商代墓葬的礼乐器组合,影响波及周边地区,如山东青州苏埠屯商墓M8 的礼器组合,就与殷墟发掘的商墓基本一致,所出乐器同样为三件一组的编庸和一件特磬。⑨参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发掘报告》,载《海岱考古》(第1 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254—274 页。
与商代高等级墓葬相比,迄今发掘长方竖穴墓累千,但仅有少量陶礼器、生产工具或兵器等随葬,没有乐器出土,说明墓主人身份等级较低,应属商代社会中的平民。⑩参见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72—73 页。此外,殷墟发掘的无墓圹和无葬具的奴隶墓葬,也都没有乐器随葬。凡此均表明,“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⑪同注④,第1249 页。的礼乐规范,早在商代晚期即已得到严格实施。
从商代墓葬出土的青铜编庸和石磬看,金石之乐的乐器组合已然形成。青铜礼器和金石乐器的物质构成显示,商代晚期礼乐制度的发展已经比较完备。由此看来,载籍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当可视作周公对旧有礼乐制度的改造和重整,而并非礼乐即始自西周早期周公之时。
《论语·为政》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⑫同注④,第2463 页。说明周礼因袭殷商,商礼承自夏礼,并且均加以增减调整。从考古学观察,夏代二里头文化的高等级墓葬,不仅随葬有青铜礼器,而且发现有石磬、铜铃和陶埙等乐器。虽然这时期石磬还是单件使用的特磬,铜铃也未见有成编者,但金石之乐的乐器构成已见雏形,只是目前资料有限,夏代乐器的具体组合尚不清楚。但是,礼乐文化在夏代的存在应是无可怀疑的史实。
夏代之前已进入新石器时代。关于这时期的礼乐文化,由于青铜器制造尚不普遍,青铜乐器更为罕见,故不宜完全照搬后世金石之乐的乐器配置来比照和分析。另外,这时期的礼和乐是否相互依存和结合,抑或相互分离和独立,它们是否具有同时同构关系,也不宜完全用后世礼乐的概念相比照,而应从音乐遗迹和遗物所体现的礼乐文化意义做综合考察。
这里先举前面提到的山西襄汾陶寺和陕西神木皇城台两项考古资料为例,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礼乐文化试加探索。
在陶寺墓地当中,有五座规模最大的一类甲型墓集中在一片,前后距离各1 米上下。五座甲型墓均有乐器出土,其中有的还随葬有彩绘蟠龙纹陶盘,其龙纹形象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意义。四座甲型墓出土特磬、鼍鼓和土鼓,三座墓随葬成对的鼍鼓,并伴出一件特磬和一件土鼓。一座墓随葬鼍鼓、特磬和土鼓各一件,另一座墓仅有鼍鼓、土鼓各一件,无磬出土。⑬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编著《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 年版,第441—456、671—673 页。可见磬、鼓应属特定的配器方式。
与随葬品丰富的甲型大墓相比,数量众多的中、小型墓则随葬品较少甚至十分贫乏,表明陶寺文化早期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应已出现,甲型墓的主人生前应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可能属于拥有特权的首领类人物。乐器在甲型大墓出土,当是墓主人较高身份地位的反映,并蕴涵一定的礼器意义。陶寺墓地还发现有铜铃、陶铃、骨簧和埙等,表明陶寺文化人类已拥有若干不同品种的乐器。
石峁皇城台古城遗址面积逾400 万平方米,其中包括大型宫室建筑遗迹,以及作为建筑装饰构件的石雕,石雕之上刻有人物、动物、“神兽”和符号等形象。⑭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考古》2020 年第7 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2016—2019 年度考古新发现》,《考古与文物》2020 年第4 期。在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第四层“弃置堆积”内,出土有乐器骨簧,同出乐器有骨笛(哨)、骨管和球形陶哨等。该遗址出土有陶器、玉器、骨器、卜骨和少量锥、刀、环等小件铜器,另外还发现有陶鹰、壁画残片等艺术品。综合看来,遗址核心区域已具备早期宫城性质。再结合石雕、陶鹰和乐器等判断,石峁古城的考古遗存已包含礼乐文化的物质构成。
据14C 测定,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400—公元前2300 年,石峁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公元前1800 年,二者的年代上限相差不大,它们大致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的尧舜时代。笔者曾推论,中国古代“中”的音乐思想应源自尧舜,在《论语》的《尧曰》《中庸》以及清华简 《保训》中均能见其端绪。⑮参见方建军《〈保训〉与“中”的音乐思想本源》,《中国音乐学》2016 年第1 期。《尚书·舜典》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⑯同注④,第131 页。是舜帝令乐官夔掌管音乐事物并加以传授的记述。现在有陶寺墓地和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可证尧舜时代礼乐文化应已得到初步创立。
据上所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资料已显示出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大型墓的主人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并掌握一定的权力。大型宫城、宫室建筑、乐器以及石雕、壁画等艺术品的存在,说明古城之内拥有执掌最高权力的人物,礼乐文化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均已出现。这时的乐器已有金石之类的铜铃和石磬,而铜铃则是后世钟体乐器的滥觞。此外,这时期还发现有击奏、拨(抻)奏和吹奏乐器,从总体上表现出礼乐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当已进入初创阶段。
关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是否存在礼乐文化,可试举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骨笛及有关器物为例来加以探究。我们知道,贾湖遗址发现的骨笛多出于墓葬,个别出于灰坑(一件半成品)或探方(二件残品)。骨笛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相对固定,大多置于墓主人的大腿侧,个别放于墓主人的手臂旁。骨笛摆放位置的非随机性,显示出这种乐器的宝贵以及与死者的密切关系。据14C 测年,最早的贾湖骨笛的时代距今约9000 年。⑰参见张居中《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447—448 页。贾湖文化分三期,骨笛多为二期物,个别为一期和三期制品。据14C 测年并经树轮校正,一期为公元前7000—公元前6600 年,二期为公元前6600—公元前6200 年,三期为公元前6200—公元前5800 年。
出土骨笛的墓葬,共存物有生产和生活用具,如陶壶、石斧、石凿、骨簇、骨镖、穿孔石饰、牙削、骨匕等生产生活用具。此外,有九座墓还伴出有龟甲和叉形骨器,其中骨笛与叉形骨器共出的有五座,骨笛、龟甲与叉形骨器共出的有二座。龟甲内有的装有数量不等的石子,有的装有骨针和骨锥之类,个别龟腹甲和叉形器上还刻有图形符号,如M344 和M387 所出即是。
高广仁指出,内装针、锥之类的龟甲当与医巫有关,或具有原始宗教的功能,是死者生前佩带的灵物。⑱参见高广仁《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载《海岱地区先秦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96 页。贾湖墓葬中的龟甲,内装石子者可以摇击发声,具备摇奏乐器的一般特征。发掘者认为,龟甲和叉形器应非一般生产和生活用品。出土骨笛的墓葬比其他墓葬随葬品丰富,且伴出有龟甲和叉形骨器,显示出墓主人较高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有可能是巫师或身兼巫师的某种特殊人物。因此,骨笛不仅是一种乐器,而且还可能与龟甲和叉形器一样,作为施行巫术的法器,从而具有一定的神秘意义。⑲参见方建军《中国史前音乐的仪式性因素》,《音乐研究》2004 年第4 期。同时说明,贾湖遗址的乐器功能和用途可能并非单一,墓主人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使乐器包含一定的礼器性质和意义。由此而看,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萌芽,当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
综合上述,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形成,具有十分久远的历史传统,它萌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初创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于夏代,奠立于商代晚期,西周早期之时由周公加以改革重整,并在后世得以继续发展。
三、“礼辨异”和“乐统同”
在礼乐关系和礼乐功能之中,有“异”和“同”这对概念。礼的主要功能是将社会不同等级的人区别开来,即所谓“辨异”,而乐则在其中起到协同调和作用,即“统同”。二者具有对立统一和互为补益的关系。如《乐记》的“乐论”和“乐情”篇讲道: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⑳同注④,第1529、1530、1537 页。
上引礼乐之“异”“同”论说,在《荀子·乐论》中表述为“乐合同,礼别异”㉑廖名春、邹新明点校《荀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97 页。。“乐合同”,实则与“乐统同”同义。礼的功能是明确“天地之序”,故“群物皆别”;乐的功能是“天地之和”,故“百物皆化”。其实礼就是为了相异相别,以达到“相敬”的目的;乐则由“统同”而达到“相亲”“上下和矣”乃至“天地之和”的目的,重点强调的是“和”。关于“乐文同”,《乐记·乐论》说:“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㉒同注④,第1530 页。可见“乐文同”大概应指“乐曲的音响形态,即音乐的旋律和曲调”㉓方建军《楚简〈采风曲目〉释义》,《音乐艺术》2010 年第2 期。。
这里要考察的是,“礼辨异”和“乐统同”的思想观念,是否或如何体现在礼乐文化的物质形态。就“礼辨异”而言,考古发现的墓葬资料提供了大量青铜礼器配置组合的证据,从随葬品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对此不少学者已做有深入研究,此不烦举。这里仅结合音乐考古发现,对“乐统同”观念的物化形态试加考察。
有关“乐统同”的物质构成,从墓葬出土随葬乐器,尤其是最能体现礼乐文化精神的钟磬类金石之乐上显现出来。
先看商代墓葬的出土乐器情况。商代的钟类乐器编庸,其组合绝大多数是三件,目前只有妇好墓出土五件,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墓葬M1083 出土四件。编庸三件组合的形式,无论在商王或贵族奴隶主墓葬,基本属于通例,已经成为固定的组合模式。商代特磬与编磬共存,但由于大多残损失音,故其固有组合目前尚不清楚。不过,从编磬的出土情况看,“三”这个数字好像也是常数,如殷墟妇好墓编磬和故宫博物院馆藏“永余”等刻铭编磬均为三件。
值得注意的是,商晚期墓葬出土的埙,其数目一般也是三件,且形制为一大二小,两件小埙的尺寸基本相同。从测音数据看,商墓出土的三件组合编庸,一般为三音列,但各墓所出在具体调高、音级构成和音程关系上自有不同。三件埙之中的两件小埙,调高与大埙不同,但也是以三件置于墓内。看来,“三”这个数字在商代乐器组合中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商代以编庸和编磬所代表的金石之乐,在不同等级的墓葬都有相同的件数组合,这或许就是后世“乐统同”观念的肇端。
西周时期,金石乐器所体现的“乐统同”现象可谓发展到极致。考古资料显示,陕西地区的西周早期编钟都是三件一组,如宝鸡发现的三座国墓葬,墓主人为三代伯,所出编钟均属此类组合。㉔参见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 年版。从编钟的组合与商晚编庸同为三件看,二者或许具有继承发展关系。当然,其他地区西周早期编钟的组合件数也存在变例,如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M111 所出编钟为四件,即其一例。㉕参见湖北省博物馆等《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 年版。
西周早期三件一组的编钟,由于大多保存状况欠佳,故其音列结构尚不清楚。西周中晚期之时,编钟一般都是八件一组,如著名的中义编钟和柞编钟即其佳例。这些编钟不仅外在的组合相同,而且内在的音阶结构也一致,即正、侧鼓音的音响可以构成“羽—宫—角—徵”四声羽调模式,音域达到三个八度加一个小三度。编钟的组合,不因作器者或拥有者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有所变易,从周王到以下各类职官,均为同样的件数和音阶结构。㉖如㝬钟、五祀㝬钟均为周厉王自作编钟,其形制纹饰与西周晚期八件组合编钟相同,目前仅各出一件,估计其原有组合也应为八件。参见方建军《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年版,第256 页。
如此看来,西周编钟所体现的乐制,似乎与礼制要求的等级区别相抵牾,但若从音乐实践角度考量,这一现象则不难理解。编钟作为礼的载体,虽然是拥有者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但由于它是乐器,是表达和演奏音乐作品的工具,故其组合件数和音阶结构,不能因拥有者社会地位的个体差异而改变,否则就无法合乎实用,最终达不到“乐文同”的目的。从此而看,“乐统同”表现在西周编钟的组合上,就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件数和音阶结构的整齐划一。
类似的乐制情况,也见之于编磬的组合件数和音阶结构。目前西周编磬发现不少,但大多残碎破损,无法通过测音来获知其音阶构成。不过,由少数保存较好的实例,或可略知其组合件数和音阶结构。如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93、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 和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M27 等,所出编磬都是十件,其中芮国墓葬M27 编磬业已经过测音,其音阶结构为五声宫调模式,即“宫—角—徵—羽—宫—商—角—徵—羽—宫”。十件编磬还可分为左右两组,分别构成“宫—徵—宫—徵—宫”和“角—羽—商—角—羽”两种音列模式。也就是说,十件编磬的使用可合可分。㉗参见方建军《新出芮国乐器及其意义》,《音乐研究》2008 年第4 期。西周晚期编磬的组合形式,在东周时期得以继承发展。当然,东周编磬除十件组合外,还存在其他组合形式,但十件一组已是成套编磬的基本构成内核。
东周时期的编钟,通常以九件组合方式出现,正鼓音的音阶为五声徵调模式,即“徵—羽—宫—商—角—羽—商—角—羽”,显然较西周八件组合的编钟增加了商音。当然,东周时期钟磬编列的规模扩大,一套钟磬之中可以分为若干组,但每组钟磬依然保持常规的音列结构或在此基础上有所损益。例如,曾侯乙编钟由若干组统配而成,编钟悬挂于曲尺形钟架,另一面摆放和悬挂编磬。多数学者认为,曾侯乙钟磬的规格,属于《周礼》所述的轩悬(曲悬),乃诸侯级乐悬。曾侯乙编钟一架共65件,编磬一架共32 件,乃迄今规模最大者。然而,各组钟磬的音列或音阶结构其实是在九件编钟和十件编磬基础上的发展变化。因此,虽然东周时期钟磬规模扩大,但每组钟磬的音阶构成依然是同一性占据主流,这其中即包含有“乐统同”的因素。可见,“乐统同”在东周时期的金石乐器之上继续保持下去,但有相当的发展变化。同时表明,《周礼》所谓乐悬制度,恐非指西周钟磬,而是就东周钟磬而言。
由上所述,礼乐制度所规定的等级差别,主要体现在钟磬制造的大小精粗和质量优劣,同时也反映在分组和件数的多寡,以及钟磬编悬规模的大小。不少钟磬在音列组合上如出一辙,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乐器演奏实用性的限制。钟磬之类的乐器并非作为摆设,而是用来演奏音乐作品,因此,它必须具备一定的音列或音阶结构,而不可能随意增减数目,否则就无法应用于音乐实践。
四、“礼坏乐崩”的实质
“礼坏乐崩”,史籍多称“礼崩乐坏”。其实“礼坏乐崩”一词出现稍早,如《论语·阳货》云:“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㉘同注④,第2526 页。“礼坏”与“乐崩”尚为分说。二者合称见于《汉书·武帝纪》:“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㉙《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122 页。
“礼废乐坏”一词大约在汉代出现,如《史记·礼书》说:“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㉚同注㉙,第1024 页。以“废”代“崩”,实则语义相近。又《风俗通义·声音》云:“周室陵迟,礼崩乐坏,诸侯恣行,竞悦所习。”㉛[东汉]应劭著,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217 页。后来,“礼崩乐坏”一词代相沿袭,传承不绝。
一般认为,“礼坏乐崩”始于春秋时期,或以为早至西周晚期。作为颇具贬义的词汇,“礼坏乐崩”主要指传统的礼乐制度遭致土崩瓦解,与之相应的器用等级制度出现违规僭越。据汉儒何休所注,周礼用鼎制度,天子九,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或一(《公羊传·桓公二年》)㉜同注④,第2214 页。。俞伟超和高明认为,这些鼎制只在西周中期以前实行过,西周后期到春秋时期即发生改变,各级贵族不断僭越,诸侯用九鼎,卿或上大夫用七鼎,下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㉝参见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 年第1—2 期,1979年第1 期。
关于乐崩,常引用的文献可举《论语·八佾》,其开首云:“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㉞同注④,第2465 页。表明打破舞队佾数的规定是不能容忍的。与此同时,钟磬编列的乐悬制度也受到冲击。可见,乐崩即下级官员僭用上级的乐制规范,“礼坏乐崩”就是礼乐规矩的失守,表现在礼乐器之上即鼎制和乐悬的僭越。正因如此,历代统治者几乎一致认为,“礼坏乐崩”就是对礼教纲常的破坏,是当时出现的社会乱象。但历史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还是从考古发现入手来加以考察。
西周晚期之时,编钟编磬的组合并未出现大的变革,不仅在中原地区周文化范围具备较为统一的编组模式,而且南方的楚国编钟组合也仿中原乐制,如山西天马曲村晋侯邦父墓M64 出土的西周晚期楚公逆编钟,㉟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8 期。不仅形制与中原所出基本相同,而且也是八件合为一组。
东周时期,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变革,乐器品种增加,以钟磬为主的金石之乐在中原地区的编配组合,既具有同一性,又呈现多元化。尤其在非中原地区的诸侯国,钟磬配置更具自身特点。如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中晚期楚墓M1、M2 和M10,出土编磬均为十三件,㊱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版。与中原地区通行的十件组合相异。据《周礼·春官·小胥》所言,“凡悬钟磬,半为堵,全为肆。”郑玄注:“钟磬者,编悬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左传·襄公十一年》杜预注“悬钟十六为一肆”㊲同注④,第795、1951 页。。这些说法均与考古发现不符,实际钟磬的堵、肆件数,每因时代、地区和墓葬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由此说明,东周礼乐文化的物质构成应是同一与多元并举。
总体而看,周代的礼乐制度主要遵循传统的礼乐规范,但是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发展变化。非中原地区的国、族,可能形成自己的礼乐体制,如楚、吴越、巴蜀等,其礼乐文化虽然受到中原影响,但仍保留自己的特点,表现出礼乐文化的区域差异。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自然会出现礼乐制度的僭越、失序乃至更新。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这当是促进音乐文化发展变化的动因,而不应视为阻碍音乐事物发展的藩篱。
这里还应提到“郑卫之音”。我们知道,“郑卫之音”作为东周时期“礼坏乐崩”的标志,遭到传统势力的极力批驳和反对,历代典籍均斥之为“亡国之音”“乱世之音”。孔子更直言:“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㊳同注④,第2525 页。。与“郑卫之音”相类的,还有“桑间濮上之音”,同样被视为“亡国之音”(《乐记·乐本》)㊴同注④,第1528 页。。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㊵同注㉙,第1326 页。可见,桑间和濮上同属卫地,应包括在“郑卫之音”流行的地理范围之内。《乐记·乐本》云:“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知乐则几于礼矣。”㊶同注④,第1528 页。据此看来,在当时的统治者眼中,“郑卫之音”和“桑间濮上之音”不是包含礼的“乐”,而是属于较低层面的“声”和“音”。
东周时期郑国的音乐考古发现,可举河南新郑春秋时期郑国祭祀遗址为例。该遗址掘获青铜礼器坎和青铜乐器坎多座,出土乐器有编钟、编镈和陶埙等。青铜乐器的组合多为编镈四件,编纽钟十件。如乐器坎K4 所出十件编纽钟,其正鼓音连奏为“角—徵—羽—宫—商—角—羽—商—角—羽”音阶结构。㊷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 年版,第957 页。显然,除首钟为角音之外,其余九件编钟的音阶结构,与东周时期常见的九件组合完全一致。由此可见,郑国编钟的组合依然遵循一定的乐制规范。
东周时期确认为卫国的乐器发现较少,这里试以河南淇县宋庄墓葬M4 所出为例。该墓随葬编钟八件、编磬九件,同样具备一定的乐制规范。㊸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淇县宋庄东周墓地M4 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5 年第4 期;方雪扬 《淇县宋庄M4 出土编磬测音研究》,《中国音乐》2019 年第3 期。从墓葬所处地理位置和出土遗物看,M4 可能属于卫墓。因此,历代统治者排斥的“郑卫之音”,在目前出土的郑国和卫国钟磬上,恐怕还看不出有何“乱世之音”的表征。这些情况说明,郑、卫两国的出土乐器,属于宫廷音乐的范畴,而非“郑卫之音”的代表。“郑卫之音”和“桑间濮上之音”,不能等同于郑国和卫国的全部音乐,而应是民间兴起的一种新音乐。从文献记载看,当时的统治者并非毫无例外地厌恶“郑卫之音”,如魏文侯听古乐时唯恐昏昏欲睡,而听“郑卫之音”则不知疲倦(《乐记·魏文侯》)㊹同注④,第1538 页。。可见,“郑卫之音”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以往学界多从文献史料研究“礼坏乐崩”的实质,其中不少学者认为礼乐并未崩坏,相反还得到更大的兴盛发展。㊺参见杨文胜《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了吗?》,《史学月刊》2003 年第9 期;项阳《对先秦“金石之乐” 兴衰的现代解读》,《中国音乐》2007 年第1 期;李宏锋《礼崩乐盛——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礼乐关系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本文通过考古资料的分析,再次说明“礼坏乐崩”并非礼乐文化的倒退和衰败,而是融同一性和多元化于一体,在变化革新中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