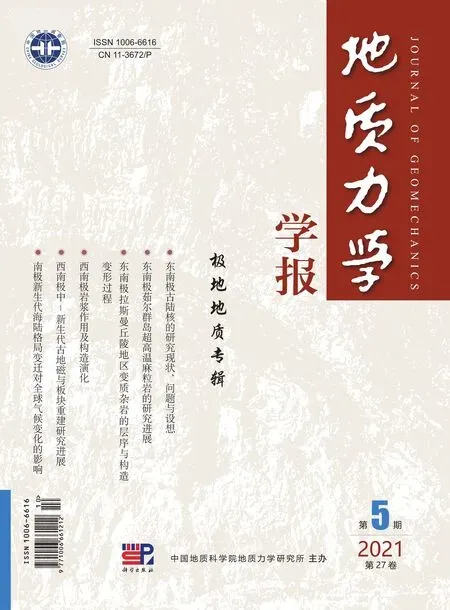中国参与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前景与方向
杜星星刘建民
1.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2.自然资源部古地磁与古构造重建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
0 引言
北极地区油气资源的勘探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最早的油气勘探活动始于1923年,美国海军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邀请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对阿拉斯加海军石油储备4号区域(NPR-4)进行调查。1960年以后,北冰洋沿岸国家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挪威和丹麦在北极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勘探活动,相继发现了多个大型油气田,其中一些油气田的开发为所在国家带来了重要的经济利益。根据IHS公司数据统计表明,截止到2020年8月北极地区共发现油气田数量高达792个(张凯逊等,2020)。北极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被发现后,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英国、中国等多国研究机构都对其油气资源量开展了评估工作,虽然评估结果不尽相同,但获得学术界认可并广泛引用的是美国地质调查局2008年的评估结果(USGS,2008)。结果显示,北极地区待发现油气资源总量达4120亿桶油当量,占全球待发现油气资源总量的22%,其中石油900亿桶(123.3亿吨)、天然气47万亿立方米(423.0亿吨)、天然气液440亿桶(60.3亿吨),分别占全球待发现石油总量的13%、天然气总量的30%、天然气液总量的20%。北极地区待发现油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的南喀拉海-亚马尔盆地、美国的阿拉斯加北坡盆地、挪威和俄罗斯的东巴伦支海盆地和丹麦的东格陵兰裂谷盆地(麻伟娇等,2016)。从地理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俄罗斯、阿拉斯加、挪威、格陵兰和加拿大。北极地区油气资源总结起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海上油气资源比陆上占比高,约占北极油气资源总量的84%;二是天然气比石油占比高,约占北极油气资源总量的70%;三是俄罗斯较其他北极国家占比高,约占北极油气资源总量的60%(雷闪和殷进垠,2014)。北极地区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意义不仅体现在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等),还拥有多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 (如铁、锡、铜、钯、金、铅、锌、钼、金刚石等)、生物资源、交通资源等,诸多资源的存在还体现了北极的经济价值和航运价值。除此之外北极地区气候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巨大影响体现了它的科研价值,北极地区土地资源的归属也体现了它的地缘政治价值和军事安全价值。
中国作为油气消费大国,石油和天然气进口量逐年攀升,对外依存度高。据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数据统计,2020年即使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依然保持较高水平,表观消费量分别为7.36亿吨和2.43亿吨,进口量为5.42亿吨和1.02亿吨,比上年增长7.3%和5.3%,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3.6%和42%。为维护国内能源安全,建立多元化能源供给渠道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北极地区已逐渐成为中国油气进口的重要来源地之一,参与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利用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也是中国开展 “一带一路”建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必然走向。文章分析了主要北极国家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未来发展前景,结合中国目前参与北极油气开发利用的情况,对未来中国如何参与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利用提出建议。
1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历史和现状
北极地区油气资源的开发始于20世纪60年代,已开发的油气田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的南喀拉海-亚马尔盆地和蒂曼-伯朝拉盆地与美国的阿拉斯加北坡盆地,总体特征表现为:陆上开发多海上开发少,国际油气公司合作开发多单独开发少。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美国、挪威和加拿大一直在进行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各国开发特点各不相同。主要北极国家重要北极油气田的开发情况见表1。在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新国际形势下,全球多家油气公司陆续宣布减少上游投资,暂停新的油气勘探项目,北极地区也不能幸免。国际能源署(IEA)近期发布的《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能源投资可能比上年减少20%,其中油气投资减少幅度巨大达到32% (IEA,2020)。从中长期角度来看,2020年油气行业上游资本支出的减少不仅会影响2020年预计启动的项目,还会影响未来几年计划投产的项目,比如一些项目可能延迟,另一些项目直接取消投产(王佩,2020)。

表1 主要北极国家重要北极油气田的开发情况表Table 1 Development status of important Arctic oil and gas fields in major Arctic States
1.1 俄罗斯
俄罗斯是北极圈内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历史最悠久和开采量最多的国家。俄罗斯于1969年最早建成世界最北端的天然气管线,起点位于米颂扬斯克油气田,终点到诺里尔斯克市,长约671千米。俄罗斯在北极圈内最早开采的米颂扬斯克油气田(1969年)和梅德韦日尔气田(1972年),比美国阿拉斯加北坡普拉德霍湾油田的开采(1977年)还要早8年和5年(付超等,2019)。据俄罗斯能源部评估结果,俄罗斯北极地区可开采油气总量包括130亿吨石油和87万亿立方米(783.1亿吨)天然气。
随着俄罗斯境内老油区油气产量的逐年下降,北极地区成为俄罗斯能源的重要发展方向。近年来俄罗斯北极陆上区域的油气开发一直在加速进行。2018年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基里尔·莫洛佐夫指出,俄罗斯北极地区的石油和凝析油约占俄罗斯总储量的四分之一,天然气占俄罗斯总储量的70%以上,并且近几年俄罗斯北极地区天然气开采量稳定,2017年开采量约占俄罗斯天然气总产量的83%(胡丽玲,2018)。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开发主要集中在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刘乾,2019),尤其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其储量约有125.2万亿立方米(1126.9亿吨)天然气和669亿吨凝析油。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油气项目主要为俄罗斯三大油气公司所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拥有一批巨型气田,如乌连戈伊、扬堡、梅德韦日耶、扎波利亚诺耶、博瓦年科沃、哈拉萨韦、鲁萨诺夫等,其中前三个气田在很长时间内保证了苏联和俄罗斯的天然气开采,在这三个气田产量下降后,扎波利亚诺耶 (2001年)、尤尔哈罗夫 (2003年)、南俄罗斯 (2007年) 和博瓦年科沃 (2012年) 气田弥补了俄罗斯天然气的产量。俄气公司产于该地区的天然气主要以管道气形式输往欧洲。俄气公司在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石油开采主要包括新港油田项目和梅索亚哈油田项目,两项目都于2010年大规模开发,前者设计产能800万吨,后者设计产能650万吨。诺瓦泰克公司在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开展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LNG)项目于2018年三条生产线全部投产,总产能1650万吨。该公司在亚马尔项目邻近地区以乌特连气田为基础的北极LNG2项目也于2019年正式启动建设,预计三条生产线2026年全部建成投产,年产量1980万吨。俄罗斯石油公司主要资产分布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万科尔油田群,该油田群总储量为4.9亿吨石油和740亿立方米(6661万吨)天然气,年产量约2000万吨。万科尔油田群开采的石油自2011年起经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运往亚太地区,中国是其主要出口国家。俄罗斯北极大陆架唯一开发的油气田是位于伯朝拉海的普里拉兹洛姆诺耶油田,可采原油储量4640万吨,于2013年投产,预计产量每年500万吨,最高峰值可达800万吨(郭俊广等,2017)。
受疫情影响,俄罗斯2020年油气行业大幅减产和降价,据统计俄罗斯油气收入当年下降了约50%。但俄罗斯政府和大型油气公司并未放弃对北极地区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曾宣布于2020年7月联手在北极地区勘探油气资源。
1.2 美国
虽然美国也是最早开始北极油气勘探开发的大国之一,但近年来各类资源在北极地区投入较少,导致目前北极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能力等多方面都相对落后(张祥国,2020),发展进度上远不及俄罗斯。美国北极地区油气资源主要集中在阿拉斯加北坡盆地,美国地质调查局2009年数据显示,该地区待发现可采原油244.9亿桶(33.6亿吨),天然气29.1万亿立方米(261.9亿吨),并且大部分位于盆地北部,海上分布较多(Attanasi and Freeman,2009)。2011年美国海洋能源管理局 (BOEM) 对阿拉斯加陆架区油气储量进行了评估,发现其油气资源潜力巨大,石油(包括凝析油)和天然气待发现可采储量分别超过260亿桶(35.6亿吨)和3.7万亿立方米(33.3亿吨),并且大部分位于盆地北部的楚科奇海域和波弗特海域。楚科奇海域石油和天然气待发现可采储量分别为154亿桶(21.1亿吨)和2.2万亿立方米(198亿吨),波弗特海域为82亿桶(1.2亿吨)和0.8万亿立方米(7.2亿吨)(BOEM,2011)。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阿拉斯加北坡先后发现了陆上特大型油气田普拉德霍湾油田和库帕鲁克河油田,两油田储量约占该地区石油储量的81%和天然气储量的75%。70年代,阿拉斯加建成了自北向南长约1300千米的阿拉斯加输油管,将阿拉斯加北部的石油运往南部港口,再转运至美国本土和世界其他地区。在80年代普拉德霍湾地区日产原油量曾高达200万桶(27.4万吨) /天,所生产的原油约占当时美国原油总产量的四分之一。90年代后该地区原油产量开始下滑,现今普拉德霍湾油田及其周边小油田产量都包括在内还不足50万桶(6.9万吨)/天,四分之三的输油管道处于空置状态。
2020年受疫情影响,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大幅消减油气开支,美国石油行业上游资本支出削减幅度达到420亿美元,从原计划的1478亿美元削减至1059亿美元,约占全球总削减规模的42%(王佩,2020)。美国海博国际律师事务所数据显示,2020年已有超过30家美国石油勘探和生产企业申请破产(人民网,2020)。对于阿拉斯加北极地区,许多投资商表示不再为新的石油勘探生产提供资金。虽然美国于2020年8月批准在位于阿拉斯加州的国家北极野生生物保护区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但一些能源分析师质疑在当前市场氛围和新一届政府领导下,这类项目能否顺利推进。
1.3 挪威
作为油气生产大国,挪威对北极油气资源开发一直积极性很高。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08年评估结果,挪威巴伦支海石油和天然气可采储量分别为110亿桶(15.1亿吨)和11万亿立方米(99.0亿吨) (USGS,2008)。根据挪威石油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挪威巴伦支海油气资源量约为25.35亿立方米(228万吨),相当于挪威大陆架63%的油气资源都位于巴伦支海 (孙秀娟,2019)。自2001年起挪威油气产量逐渐下降,2010年挪威解决了与俄罗斯的海上分界争端后,挪威北极地区油气勘探开始顺利展开。2017年挪威石油管理局表达了对巴伦支海提供官方支持,从此挪威油气勘探重心从传统的北海地区向北转移,全球各大油气公司对巴伦支海域和挪威海域开始进行积极的地震和钻井工作,只是近几年暂未发现大的油气田。
挪威巴伦支海四大油气田项目近年来先后投产或提上日程:储量11.47亿桶(1.6亿吨)的白雪公主天然气田于2007年投产,年产量57亿立方米(513万吨);储量2.5亿桶(3425万吨)的戈利亚特油田于2016年投产,设计最高产能3650万桶;储量6.5亿桶(8905万吨)的挪威最北部的Johan Castberg油田于2018年6月获批,预计2022年正式投产,届时该油田年产量可能占到挪威石油总产量的25%;储量4.4亿桶(6028万吨)的维斯廷油田的开采计划也正式提上日程。除此之外,位于挪威大陆架1274米深的Aasta Hastin凝析气田于2017年开始开发,John Sverdrup油田于2019年投产。
受2020年疫情影响,挪威海上油田、陆上工厂和船厂等地安全事故频发,韦斯特伍研究集团的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挪威附近海域的勘探项目被削减30%(人民网,2020),但北极附近海域油气勘探投资减少幅度较小。
1.4 加拿大
加拿大作为北极地区领土面积第二大的国家,其北极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波弗特海的北极大陆架,但勘探开发工作始终进展缓慢。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加拿大北极地区油气盆地就曾开展过积极的地质勘探工作,但之后钻井工作由于环境考虑和储量低等原因被迫暂停。据美国和加拿大联合地震资料估计,波弗特海约有80亿桶(11.0亿吨)石油和1.6万亿立方米(14.4亿吨)天然气。虽然加拿大一些大型油气公司一直呼吁在波弗特海进行油气开发,但实际情况是加拿大北极地区无论陆上还是海上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工作近年来均已完全停滞,部分原因是由于国际油价下跌以及加拿大西南部省份(如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等)的油价较便宜并且供应充足造成。加拿大北极地区主要运营商加拿大帝国石油(Imperial Oil)公司和英国石油(BP)公司在2016年宣布,将无限期暂停在波弗特海的开发,原因包括低油价、开发技术和运行周期等多方面因素。加拿大政府从2016年起更是暂停签发新的北极地区海上石油勘探许可证,这也使得加拿大北极地区的石油钻探活动几乎全部停止。受2020年疫情影响,加拿大多家油气公司选择撤离或缩小业务规模,有些甚至需要政府的帮助才能渡过难关。
2 中国参与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历史和现状
早在2011年通过中俄原油管道运输,中国就使用上了俄罗斯北极万科尔油田产出的石油,项目建成后俄方预计20年内每年向中国输出1500万吨石油。中国开始正式进入北极油气领域作业是在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中石油公司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在巴伦支海和伯朝拉海3个油田的勘探作业协定(Upstream Online,2013)。2013年10月中海油公司曾入股参与冰岛东北部“龙区”海域的油气勘探工作,但于2018年初因技术、资金、周期等原因以失败而告终。2016年10月中海油公司开展北极海域地区勘探活动,利用最先进的12缆物探船“海洋石油720”历时100天首次圆满完成了北极巴伦支海两个区块的三维地震勘探作业(国企管理,2019)。中俄合作开发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LNG)项目于2013年9月正式启动,中方参与公司中石油占股20%,中国丝路基金占股9.9%。2018年7月来自俄罗斯北极亚马尔的首船液化天然气通过北极东北航道历经21天抵达中国中石油旗下的江苏如东LNG接收站,首次运载的液化天然气量为6.8万吨。亚马尔项目的3条生产线都顺利投产后,54%销往亚洲市场,剩余出售给欧洲,保证每年销往中国400万吨液化天然气,期限为 30年。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于2014年5月启动2019年12月建成正式投产通气,该项目预计向中国每年供应天然气380亿立方米(3420万吨),期限为30年,总供气量超过1万亿立方米(9亿吨)。在亚马尔项目良好合作基础上,中俄北极LNG2项目于2019年9月也正式启动,中石油和中海油公司各占股10%。该项目预计2026年3条生产线全部投产,年产能1980万吨。2020年7月产自俄罗斯北极新港油田的首批原油从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出发,穿越三大洋,经过47天抵达中国烟台港,首船运量14.4万吨。从上述中国参与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的案例来看,近年来与中国开展北极油气合作的国家主要是俄罗斯,两国合作方式逐渐变得多样化,从购买油气产品到参与到油气勘探、项目融资、工程建设、油气田开发、产品运输等项目运行的各个阶段。
3 中国参与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景展望
北极地区油气资源除了潜在资源量大之外,经济价值也相当可观。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北极冰雪的融化,北极更多陆地区域油气资源可供勘探开发,而海冰的减少也使北极航道通航时间延长从而节约油气资源的运输成本。随着新冠疫情被不断控制,全球经济复苏,油气价格上涨,北极部分国家和地区成熟的基础条件可以实现油气资源国际合作开发,并达到双赢的可行性。
3.1 参与意义与前景
中国油气消费量大,对外依存度高,通过多渠道进口油气资源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必要途径,而北极地区潜在丰富的油气资源无疑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虽然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开发面临着高成本、高风险、高技术要求,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北极地区油气开发依然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获得经济利益。中国购买北极油气产品,是通过参与国际市场资源再分配来实现自身利益,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参与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无论参与到勘探或开发亦或运输哪个环节,都有助于推动参与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经验积累,提高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即使中国企业仅仅参与北极油气项目上游投资,也比单纯的购买油气产品能够掌握更多的主动权,从而避免受到外界国际形势影响,保证国内油气资源长久持续的供应。深入参与北极油气开发,还可以提升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能力以及在北极事务协调中的话语权。在参与北极油气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中国也在不断的积累经验和教训。如果未来国际油价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线以上,北极油气开发有利可图,积极参与开发不仅保证了中国油气的多元化供应,还实现了企业盈利;如果国际油价始终低迷,参与新的北极油气项目开发可以适当放缓或保持观望态度,将企业的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世界上其他易采、可采地区油气资源面临枯竭,无论油价高低,迫切的市场需求都会促使北极地区油气资源开发势在必行,而参与过北极油气开发并有过成功经验的国家更容易尽快参与其中占得先机。
3.2 参与合作的国家
综合分析主要北极国家北极油气资源开发现状及其未来发展前景,同时考虑其与中国的国际合作关系,选择合适对象开展长期的北极油气合作。与俄罗斯相比,美国价格低廉的页岩油气产量占到美国油气产量的一半以上,而相对高成本的阿拉斯加北极地区油气产量却在不断萎缩。美国政府对北极油气开发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一方面认为北极油气资源开发会对气候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又批准北极油气勘探计划,并规划建造破冰船积极布局北极(刘方琦,2016)。新华社消息称,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内政部于2018年宣布了2019年—2024年外大陆架油气发展计划,建议向油气开采行业开放美国超过90%的外大陆架区域(新华网,2018),其中包括阿拉斯加沿岸油气区域。但美国想要“重返北极”,无论经济还是技术等方面都可能困难重重,就连北极地区重要的交通工具——破冰船,美国也仅有1艘,而俄罗斯目前拥有17艘。不仅如此,拜登政府提出的新的绿色能源政策也会限制美国油气勘探开发项目的开展。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严重影响了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但部分学者认为在能源领域两国有较强的互补性,甚至通过能源合作可以缓和中美贸易关系(封红丽,2018;苏轶娜,2019)。
挪威企业对于在北极石油资源的开发,无论资金还是技术方面都比俄罗斯企业要强,其近海油气勘探、设计、开采、数字化等能力都是世界一流。挪威油气行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油气出口占挪威出口总额的60%以上(钟传剑,2016)。正是由于挪威经济深受油气行业影响,一旦出现国际低油价就会导致油气收入锐减、大批海工平台闲置、油气勘探领域投资显著下降,但油气企业并未停止北极油气开发的步伐(刘方琦,2016)。中挪关系正常化以来,中挪能源合作目前只停留在油气产品买卖层面,未来可以探索在能源勘探开发、海洋工程、航道开发运输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加拿大油砂占其国内石油总产量60%以上,近年来加拿大北极地区油气勘探活动几乎全部停止。加拿大政府更注重北极地区主权和保护北极环境,对资源和航道等高政治领域问题极度敏感(朱宝林,2016)。若考虑未来中加北极地区油气合作短期内可能难以实现。
在北极国家中,俄罗斯的北极油气资源最丰富、开采量最多,其北极油气开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虽然俄罗斯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俄经济对油气行业的依赖已在逐渐降低,但近年来俄罗斯出台的多个与北极相关的政策文件中,均把北极能源放在了重要位置(郭培清和曹圆,2016)。俄罗斯2020年发布的最新的《2035年前俄罗斯北极地区发展战略》指出,“确定能源发展新目标,促进俄社会经济发展,满足国内需求,扩大出口,巩固和保持俄罗斯在世界能源市场地位”。俄罗斯提出的能源战略新任务,即以亚太地区带动能源出口多元化和大力发展液化天然气。俄罗斯预计在2035年前,俄石油和凝析油年产量保持在4.9~5.55亿吨,天然气年产量增至8500~9240亿立方米(7.7~8.3亿吨),液化天然气产量提高到7200~8200万吨。同时俄罗斯的2035年北极战略中不仅支持能源行业,更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来带动偏远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如公路和铁路建设、北极航线的港口建设及与其有关联的工业区建设等,预计到2035年将北极航线建设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运输动脉。受环境、经济、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开发程度依然较低,未来可持续开发前景广阔。当前,中俄北极油气合作进展顺利,亚马尔项目被称为“北极地区国际能源合作的典范”,两国间具有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具体表现为两国高层交往频繁,中国连续 9 年保持俄罗斯第一贸易伙伴国地位(林香红和翟仁祥,2020)。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在稳步提升。中俄两国要素需求的互补性是能源合作的基础,两国政治高度互信是能源合作的有力保障(郝宇彪和田春生,2014)。中国自2013年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中俄能源合作一直在加快推进。中俄原油管道、亚马尔LNG项目、北极LNG2项目、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先后投产或启动,此外西线和远东天然气管道项目也提上日程,若两项目能达成协议并按期投产,未来10年俄罗斯运往中国的天然气将有望超过800亿立方米(7200万吨)/年,超越澳大利亚成为中国天然气进口的最大来源国(张茂荣,2020)。石油合作方面,俄罗斯一直是中国原油进口的重要来源国之一,但目前北极油田的贡献在其中并不显著。开展中俄油气合作,是将俄罗斯油气资源与中国市场进行优势互补,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互利双赢的选择。中国需要进口油气资源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因此希望能够在俄罗斯境内开展投资、贸易、服务等合作;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则需要出口油气资源,因此希望进入中国境内的下游油气市场。疫情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短期内将会加大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市场的需求和资金支持的依赖。
3.3 重点合作领域和方向
在全球绿色低碳经济大背景下,中国也在加速能源结构转型。中国表示,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天然气作为相对清洁的化石能源和能源转型中重要的过渡能源,在中国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将会逐渐增大,未来消费市场潜力巨大。近年来中国天然气需求不断上升,国内供需矛盾严重。满足国内日渐增长的生产和生活需求是中国天然气产业发展的首要导向。有学者通过建模得出,中国在2030年天然气进口量将达到2245亿立方米(2.0亿吨),对外依存度将会突破国际警戒线50%高达51.46%(郑明贵等,2021)。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发布的《国际能源展望2019》报告指出,全球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市场将会继续扩张,预计到2035年液化天然气需求将以每年3.6%的速度增长(EIA,2019)。据海关总署数据统计,2017年中国LNG进口量首次超过管道天然气,之后二者差额逐渐拉大,可预见LNG在未来中国天然气市场的良好发展前景。由于管道气长距离运输(>4000千米)的经济性不如船运LNG,因此在全球天然气供需不平衡的背景下,相比管道气LNG贸易将会快速增长(李剑等,2020)。与管道天然气相比,LNG进口还具有操作灵活、调配方便、接收站建设周期短等优势,对中国而言LNG还是国内冬季天然气市场的供应主力(潘月星和赵军,2018)。据海关总署数据统计,2015—2020年间澳大利亚一直是中国最大的LNG供应国,2020年其进口量占比高达46%,约4676万吨,而俄罗斯LNG进口量占比仅不到3%。但近日来中澳关系紧张可能会导致中国LNG进口渠道受限,二者对比俄罗斯LNG发展潜力巨大,在中俄已有合作基础上加强、深化合作未来可期。俄罗斯的北极LNG对于亚洲国家的优势还体现在,在同类型供应商中它的价格几乎最低,又有国家政策支持,地处北极地区低温亦是液化处理的有利条件,北极航道通航时间的逐渐延长也会改善物流条件并降低向亚洲的运输成本。欧洲原本是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最重要的市场,出口占比达70%~80%,但近年来俄罗斯天然气在欧洲市场却频频受阻(袁海云等,2018)。除了国际天然气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外,比如中东、北非、美国等国都对俄对欧天然气出口带来压力,美国对即将于2019年底竣工的北溪2号管道的制裁也对俄对欧天然气出口带来巨大影响。因此俄罗斯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出售天然气,在此背景下中俄在天然气领域可以开展更广阔和深入的合作。而对于北极石油的开发,据俄罗斯评估机构测算,北极石油钻探成本始终徘徊在每桶100美元左右,还不包括运费和税费等其他成本费用。对疫情影响下的国际能源市场来说,短期内开发北极石油经济上并不可行。
在参与北极油气开发合作方向上,基于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成功合作基础,建议未来可以从投资、技术、运输等几方面开展合作。一是项目投资。亚马尔项目总投资270亿美元,除了中国股东中石油公司和中国丝路基金提供的入股资金外,其余190亿美元融资金额由中国工商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了120亿美元,占比63%,展示了中国企业强大的资金实力 (张晓东,2017)。以中国企业的资金优势参与未来俄罗斯北极油气开发是一种优势互补的合作方式。二是技术入股。虽然亚马尔项目建造天然气工厂需要的 142个模块中,7家中国企业承揽了120个,占比85%;项目建设及运输产品所用的30艘船舶中有7艘是中国制造(张晓东,2017),中国企业还建造出了世界首艘极地甲板运输船;甚至宏华钻机设备制造公司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极光”号极地钻机,打破了俄罗斯和美国的技术垄断。但是在北极LNG2项目开展过程中,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却并不占优势,韩国大宇造船厂承接了全部的破冰船订单,诺瓦泰克公司准备自己制造该项目的多数模块。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企业未掌握真正关键的、重要的核心技术,不具备全球市场竞争力。未来参与北极油气开发,加强与俄罗斯的科研技术合作,提升企业技术水平,以技术入股方式参与合作,凸显企业竞争力才能获得更多的主动权。三是参与航道建设。北极航道的开通不仅对俄罗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从俄罗斯北极地区海上进口油气资源也大大缩短了行程,节约了运输成本。对国际贸易主要依靠海上运输的中国而言,北极航道不仅能快速通往俄罗斯,还能连接欧洲和北美市场,航道的开通和迅速发展对于中国加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起到重要作用(王洛等,2014)。积极参与俄罗斯北极航道建设、发展北极航道将为中国未来参与北极多种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便利,同时也对中国的海上航线多元化和海运通道战略安全起到积极作用。
4 结论
北极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已引发全世界的关注,主要北极国家俄罗斯、美国、挪威目前仍在积极的勘探和开发。中国作为油气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俄罗斯北极地区近年来成为中国重要的油气供应地之一。为分散能源进口风险,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参与北极油气开发,比单纯购买油气产品更能掌握主动权,从而保证油气资源的长久持续供应。在未来不同的国际能源形势下,具有成功参与北极油气开发的经验能让中国及时做出应对之策。综合考虑主要北极国家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未来发展前景,建议与俄罗斯开展长期的北极天然气开发合作,并从项目投资、技术入股、航道建设等多个方面开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