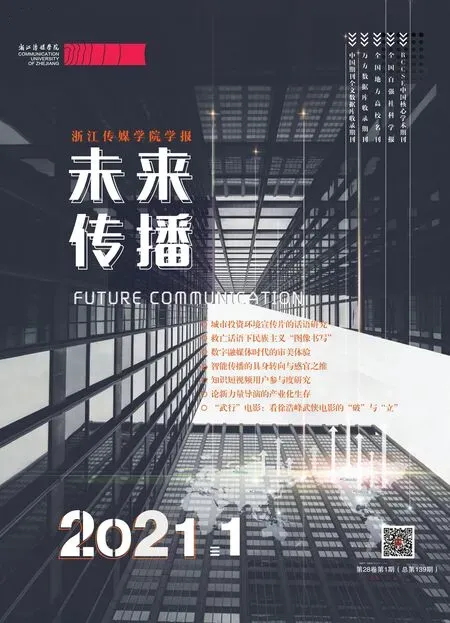“武行”电影:看徐浩峰武侠电影的“破”与“立”
黄望莉,崔芳菲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200072)
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特有的电影类型,历经百年的发展演变,造就无数经典,成为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武侠电影“锄强扶弱”“为国为民”的主旨立意便深得民众认同,而“飞檐走壁”“上天遁地”的影像呈现更是迅速吸引大众的目光,成为这一类型叙事的重要“奇观”。此后电影技术不断发展,为武侠电影提供新的感官体验与叙事可能。然而,近年来的武侠电影在技术主义的裹挟下,已经超出原初武侠电影中对中华武术本身的动作美学展示,愈发趋向于利用特技手段追逐极致炫丽的动作打斗与视觉效果的呈现。面对银幕之上模式化、类型化的视觉“盛宴”,观众已经渐生厌倦,因而造成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困境,“其美学困境集中表现为超极限奇观背后生存感兴及其深长余兴的贫乏,在美学效果上表现为眼热心冷,出现感觉热迎而心灵冷据的悖逆状况,仅达到初始的‘感目’层次而未进展到‘会心’层次”[1]。
近些年,以小说家/编剧和导演身份进入电影创作领域的徐浩峰通过其自编自导的一系列颇具纪实风格的“武行”电影——《倭寇的踪迹》(2011)、《箭士柳白猿》(2012)、《师父》(2015)、《刀背藏身》(2017),以“开宗立派”之势闯入大众视野,为武侠电影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打上“徐氏”标识的武侠电影以其对武林这个行业偏重纪实的影像表现、含蓄节制的叙事策略以及对武林的末世宿命感的表达突显了独特的作者气质,开拓了中国武侠电影新的影像美学探索。
一、“武行”电影:作者的强势突围
徐浩峰的“武行”电影不同于传统武侠电影,其着眼点更多的是要解释“武行”作为一个行业的存在,“武人”作为一个阶层的存在,“武林”作为一个时代的存在。所谓武侠电影,在陈墨所著的《刀光侠影蒙太奇——中国武侠电影论》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即有武有侠的电影,亦即以中国的武术功夫及其独有的打斗形式,及体现中国独有的侠义精神的侠客形象,所构成的类型基础的电影。”[2]之后又在其论述中将定义的边界做了模糊化处理,提出“不论是侠义、功夫、武术、武打,统统称为武侠电影(武侠片)”。如此说来,徐浩峰的武行电影依然被囊括进武侠电影的序列中,但因其“作者化”风格的凸显,便挣脱了传统武侠电影的窠臼而创立起来。“武行”电影是由徐浩峰自己命名的:“我所谓变‘武侠电影’为‘武行电影’,因为电影拍的都是对其他人提供人生经验的参考。这是大众电影,大众电影一定要完成这个。你看我拍武行里的行规,人在规矩下怎么运行,人的思维方式什么时候可以爆发,这是其他行业现实生活中可以参考的。”[3]所以当时的武人在行业规范和时代发展中所做出的决定、选择和改变是影片最为明显的故事线索,而影片通过挖掘武行人在真实历史中的生存状态,去折射时代并给予现代生活以借鉴,是它的可贵所在。
自2011年执导《倭寇的踪迹》开始,《箭士柳白猿》(2012)、《师父》(2015)、《刀背藏身》(2017)四部影片,皆为徐浩峰自编自导,集中体现出其“武行”电影创作的全新理念。这种作者风格的形成与他本人的经历有着必然的相关性。在执导电影之前,徐浩峰已是成熟的武侠小说家、影评人,有着家传武学功底,中学时代接受系统的绘画训练,之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正统的“科班出身”。自身经历让他将文人、武人、电影人这三个身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他对武侠电影独特的思考。总体来看,徐浩峰对“武行”这个概念的展示主要体现在偏于纪事化的对武术功夫和种类的知识性展示、各个武术行当的武学理念的传递,尤其是对武行中的“样”的推崇等,体现了中国武侠电影中的精神文化特质。
影片《倭寇的踪迹》作为其“武行”电影的开山之作,以“有史可依、有据可循”的武学魅力和疏离留白的美学气质先声夺人。影片故事在充分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具备有源有头的武术积淀,淡化程式化、舞台化的武打动作编排,去除威亚、特效等高技术概念的视觉呈现,强化纪实影像风格,“硬桥硬马”的一招一式,还有作为电影文本所必需的视听技巧运用,展示出沉静孤高的氛围营造和真切深远的精神文化内涵。其后的《箭士柳白猿》《师父》《刀背藏身》等作品,在武林体系的建构和武人心路的探索方面更加深入。“在《1962年关于作者论的笔记》(Notes on the Auteur Theory in 1962)这篇文章中,萨里斯提出了评价一个电影导演是‘作者’的三个标准:①导演是否能够具有娴熟的电影拍摄技术(the technical competence)。②一个电影导演必须有鲜明的个人‘标记’(signature)。即一个作者在自己众多的作品中,有着一些重复的风格与特征,形成明显而统一的个人特色。③一个导演在拍摄电影时,他自己的理念和老板交代的剧本间会产生冲突。萨里斯称这种冲突给电影带来的是一种‘内在意义’(interior meaning)。”[4]从这一角度来看,徐浩峰对于影片有着娴熟的视听创作技巧和标新立异而又自成一家的风格都帮助其表达了武行电影的独特底蕴。
用徐浩峰自己的话说,“每一部影片都在介绍武行中的一种兵器,或者武行中的一个门派”。如《倭寇的踪迹》中,戚家军旧部梁痕录要为戚家军刀法正名,“给戚家军留个影子”;《箭士柳白猿》是关于江湖是非的仲裁者“箭士”的故事;《师父》中,陈识北上天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咏春拳”博一个身份;而尚未在国内公映的《刀背藏身》是围绕“长城大刀”发明权的争夺展开的。实际上徐浩峰的电影是在拍“武行”,而非“武侠”。他故意将“武侠”这一传统概念边缘化,着意呈现的是一种实在的行业和从事该行业的特定群体,力图以电影的方式再现这一行业和这一群体在历史中的真实存在。在情节铺陈上,徐浩峰的电影会借用一个兵器的典故,阐述一种武学理念。因为“在东方世界里,械斗一定是大于拳打脚踢的,兵器是一个习武之人的尊严。只有受人尊重、有身份的人,才能配上一个兵器,整个东方世界都是这样的”[5]。《倭寇的踪迹》展示了骑兵式的“刺”和“撩”;《箭士柳白猿》中明面上是柳白猿射出了力道均衡的四箭,实则是通过射箭展示拳力,同时也表现了长枪的使用要结合拳力;《师父》中则让咏春拳与长棍、短刀等兵器结合在一起,实现近身打斗;而《刀背藏身》是讲中国军方1933年长城抗战的大刀术。正如徐浩峰自己所说,“刀法是防御技,刀背运用重于刀刃,因为人在刀背后”[6],而“力上刀尖”正是刀术的精华所在。《倭寇的踪迹》中描绘抗倭刀,形似倭刀,刀头一掌开刃,可将长刀变短刀;《师父》中也出现大量兵器,仿若图谱一般在历史的纵深和观众面前铺陈开来,电影将原著中武打设计的拳斗改编成械斗,八斩刀有着很强的造型性,由它引出日月乾坤刀、三尖两刃刀、岳飞刀、方天画戟等,其后又上演子午鸳鸯钺对阵战身刀的巷战对决。兵器和武术技击是徐浩峰“武行”电影中“吸引力”的根基。
与传统武侠电影中江湖只作为一个虚无泛化的背景不同,徐浩峰“武行”电影里的武林有着真实具体的形态,如武行作为一个行业是如何运作的。武林的气派、武行的气质体现在传统的“样”上。武行中的“样”是其礼法观念的外化。武行规矩众多、井井有条,甚至追杀之中都带着分寸,《师父》中邹馆长率武行众人追杀陈识,见陈识逃脱后,便当机立断“老规矩,逃了,就等于死了,事情完了”。放一条生路并不是力所不及,而是既给了陈识以一条生路,又不会致天津武行留下以多欺少的骂名,还要对武行看似仁义之举心存感激。而真正应该感激的是武行的“样”,即武行的规矩和讲规矩、知分寸的武人。武人知礼通情,讲究体面,“武人文相”是武林的“样”,是武学修炼到顶端之时,以武入道而德并天地的境界,也是“武行”电影追求的气质所在。《箭士柳白猿》中武行仲裁者柳白猿的第一次正式亮相便让观众见识了武林气派和处处体现出的“样”:武行中两方争端,见仲裁者柳白猿三年未出,欲起冲突之时,柳白猿人未到箭先出,随后出现在画面正中,由三重院落将其框定在内,柳白猿的帽檐与第一重院落的阴影重合,只见其形,未见其人;接下来景别变小,画面中只有两重院落,柳白猿在画面中占比更大,面部轮廓逐渐清晰;紧接着画面回归三重院落构图,镜头固定不动,柳白猿面向镜头(观众/武行争端两方)走来。整个出场段落构图均衡规整,主要人物位于画面正中,主体突出,光线明暗对比强烈。柳白猿作为武行仲裁人的气势、公正与决心在段落中尽显无遗。在整个仲裁过程中,柳白猿仅说一句“认识这个,就行了”;双方和解,柳白猿一句轻巧的“知道错,就相互敬杯茶吧”。这背后潜藏着的依然是一种“样”,即规矩赋予人的一种疏阔而笃定的理念,遵循这种理念让人动了真情,也使人觉得完整。
二、“分寸感”:含蓄节制的叙事策略
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曾在讨论美国西部片时说到:“这种类型片过去已臻至完美,或者说已经达到了经典性,这意味着它必须奋力创新以保证自己的生存。”[7]武侠电影也面临同样的命题,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无数电影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凭借各自的才华保持着武侠片的活力与激情。在传统武侠电影的“旧规矩”面前,徐浩峰的“武行”电影选择了既有继承保留,又有突破创新,这便是其电影中处处体现出的“分寸感”。
徐浩峰对“分寸感”有着某种天然的执念。对于武术之中蕴藏的“分寸”,他直言:“追求技术,追求美感和危机,就是丧失分寸感,而真正对观众形成心灵震撼的是分寸,而不是泛泛的视觉刺激。尊重实感——从真实的武术里开掘出新的动态,是补救美感之法。”[8]在他所著的《坐看重围——电影〈师父〉武打设计》和《刀与星辰》影评集中,“分寸感”一词出现的频率可谓相当之高。的确,艺术品质的高低,艺术意蕴的深浅,不在于它是否思路广集,面面俱到,而在于它沁入内里的分寸感,那是一种张弛有度的释放与节制。分寸感在此便被视作一种“仪式”,而仪式研究的泛化隐喻即“仪式成为人们行为、观念、情感的载体,暗含社会深层的意义和价值”[9]。仪式,原意为“手段与目的并非直接相关的一套标准化行为”,尽管人们日常可能意识不到,但已在无意识的过程中被仪式裹挟。徐浩峰导演的作品中,有大量的仪式运用,如武林中人的比武场面,准备、打斗、结束、行礼,皆被塑造为极具仪式感的场景。《箭士柳白猿》中武行仲裁者柳白猿平息武行纷争的方式是以分毫不差的力量与速度于房梁之上射下不偏不倚的四箭。这四箭和背后的功力便是仲裁人的底气和决心。武人当然要用“武”来处理行内争端,但这个“武”是自身的修为与功力,与诉诸暴力无关。这高贵的武德和分寸感就是武行、武人所遵从的仪式。这种对于仪式的运用,便是一种文化的渗透,使得非仪式行为代入心理认同之后具有了类似仪式的价值和功能。仪式性观念的注入以及仪式化景观的塑造,使其作品成为一种另类的奇观呈现。而分寸感中所蕴藏的含蓄节制便是这一仪式化表达的核心所在。
传统武侠电影的美学特征为“武之舞”,武术的展示是舞蹈化的。但在徐氏“武行”电影中,看不到“武舞”,看到的只是武术,那是一招制胜,一击致命的,它的美感在于极有分寸感的时间差带来的凶险之美。没有舞蹈化的灵动飘逸,甚至是缩手缩脚的,但这才是武术真实的实战常态。基于此,徐氏“武行”电影用纪实风格的长镜头来表现转瞬即逝的武之凶险,这种冷静的旁观视角,通过画面展示出了徐浩峰电影中的武林所特有的沉静孤高、旷达隽永。对于武侠电影必不可少的暴力元素,徐浩峰武行电影中亦没有血浆漫天的生死对决,而是以节制含蓄的方式,拿捏武行人利与理、情与义之间的分寸。“武侠电影的叙事策略并不在于渲染暴力,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消解暴力的残酷性,这样才能够真正赢得观众的喜爱。”[10]《师父》中,邹馆长代表天津武馆十九家出面请连踢八家武馆的耿良辰喝茶,武行众人皆拿茶而不说话,这时邹馆长说,“摆茶就是为了不说话”,这十九家武馆视陈识和徒弟耿良辰是敌是友,既不动武,也不说话,全看是拿了两边的茶,还是中间的;徒弟耿良辰“踢馆”比武,用八斩刀做武器,那就在身上绑上皮筋,看皮筋哪里划开,口子深浅,以定胜负;陈识在巷战对决中“伤人不伤命”,面对追杀他的武馆弟子,仅是留了道疤,告诉他“这道疤,我留的”,其实是让武馆弟子记住这些武学真传;而片中白俄舞女、茶汤女和师娘等女性角色的加入,以女性的柔美之气,调和阴阳,美化视觉,同样起到了消解暴力的作用。暴力不是武行(武侠)电影的目的和追求,它只是所必须包含的一种外化表象。
此外,作为武侠小说家的徐浩峰,其电影的台词表达更是将“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言有尽而意无穷”,时刻体现含蓄蕴藉的叙事策略。古人说话简洁内敛,意义深刻,这是个传统。正如《诗经》所体现出的文学传统和美学意义,话说三分,剩下七分靠体悟,话说得太满,趣味也就没了。《师父》中赵国卉对陈识说“这不是我最好的命,我最好的命是跟着巴西人到南美种可可”。其实赵国卉最初答应和陈识在一起,只是因为陈识给了很多的安顿钱,她说这话的意思也是在告诉陈识,“如果你给的条件我不满意,我是不会跟你走的”。这种把金钱交换放在第一位的婚姻结合,历来为社会道德所不齿。所以同样的意思要换一种简单戏谑的表达,不仅让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也让台词更加话里有话,还给某些必须要表达的事物行了方便,达到风过枝头已是春的效果。同样在《倭寇的踪迹》中对于世家子弟和人性尴尬的讽刺也在台词的运用中有着令人称道的表达。世家子弟将异族舞女关入水牢,意欲作恶,却依然道貌岸然地说:“我们不是坏人,只是起了邪念。”结果则在内斗中消磨殆尽,一一殒命,究其原因便是色欲熏心而又佯装做派,借世家子弟的口为自己辩解一句,反倒更是加深了黑色幽默的讽刺意味。无需过多笔墨,仅这一句台词,便将这副丑恶嘴脸勾勒而出。正如徐浩峰导演自己所说:“我想做的文化批判,一直都不是那种特别狠的,要归结于民族性、人性恶的东西。中国文化的悲剧是自己把自己搞乱了,在和平年代仍然使用革命年代的思维,老是想着一个阶层推翻另一个阶层,文化和行为准则都会乱。在我的小说里,没有你死我活,我不想表达人性之恶,我想说的是人性的尴尬。”[11]既如此便更是要点到为止,台词中耐人寻味的“分寸感”便如这般。
三、“刀背”藏“身”:冷兵器时代的历史宿命
武侠电影中对“侠义”世界道德规训的表述是永恒的叙事母题。一个阶层的毁灭,一种阶级的推翻,究其根本往往是一种道德被另一种道德替代。徐浩峰电影建构了一个具象的武林,但同时也在呈现一个逝去的武林。武人的坚持、武行的尊严,往往在现实世界中被不断冲击、零落,最终敌不过被取代的历史宿命。《师父》中军界接管武行,就喻示武行规矩、文化道统势必经过一番洗礼,甚至不复存在。统领津门武馆十九家的邹馆长说出了武行必将没落的事实——“20年来,军阀崛起,掏空了乡村、商会、铁路、银行,小小无言的武行怎能独存?”昔日光景不复,众人蝇营狗苟,邹馆长深知武行最终的结局,但她唯一能做的只有带领武行把“好日子过一天是一天”。军界接管武行是她谋的出路,同样也是时代的规训,而武行必将走向末路是无法挽回的悲哀,也是传统冷兵器必须迎接的宿命。
《倭寇的踪迹》中,戚家军旧部梁痕录要为戚家军刀法正名——“给戚家军留个影子”,最终虽打过四家门口得以开宗立派,却依然被迫离开乌衣巷,他以明志之势想要守护的戚家军军刀也只能被丢弃在冷暗的兵器库里;《箭士柳白猿》里的双喜寻求的是“内省”。导演本人在访谈中也提到“柳白猿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自省的故事,水是东方人内心的意象,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面,溪水声就等同于人的心声。柳白猿对于自己的姐姐,有一种道德上的内疚、忏悔之情。他向溪水中射了四箭,射到水里的箭就等于射回到自己的内心里去了。这表明柳白猿已经悟道,解除了内心的纠结。”[12]而最终柳白猿还是失败了,江湖已不再需要他,他败给了时代 ;《师父》中,陈识北上天津的主要目的是想为“咏春拳”搏一个身份,虽然最终得以开馆,但陈识依旧不得不离开天津。这三部作品都以武人个体命运,折射时代的风云变幻,体现出强烈的武人自尊和对旧日不再、传统已逝的叹惋。《倭寇的踪迹》中抗倭刀最终被丢弃在阴暗的兵器库,梁痕录也带着赛兰远下苏杭;《箭士柳白猿》中柳白猿在对决中失败,失去了一条腿,也失去了武行仲裁人的身份;《师父》的结局是陈识走了,也带走了武林最后的生气。武人对于武林的留恋,是势单力薄且无可奈何的,但武人心中遵循的武学传统和他们的精气神却依然坚固而深沉,正如《箭士柳白猿》的结尾匡一民说:“满世界的人都在追求投机取巧,比武是不多的没法取巧的事,我想,求一场比武。”纵观徐浩峰的电影,都表现了在大环境势不可当的时代激流的冲击下,传统侠义文化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礼崩乐坏的悲哀与无奈,江湖已逝、武林落魄的辛酸与无力。
人在武行规矩面前,实在渺小;武林在时代洪流的冲撞下,脆弱不堪。武林落寞,江湖已远,纵有保持着武人风骨与节操的英雄,愿意找回武术的宗旨,礼乐的尊严,可在那个风雨飘摇、文脉断裂的乱世,往往于事无补。纵然用尽了所有的气力,最终也敌不过时代的翻页。徐浩峰以电影为一棱“刀背”,以此“藏身”,呈现着一个逝去的武林:曾经有一群武人,他们坚守着高贵的武德,有着自己的理想信念;曾有一个叫做武行的社会阶层,他们有着规范化的管理程序,有着令人敬畏的行业准则。由他们组合成了一个具象的武林,并不虚幻飘渺,而是曾经真实存在。
四、结 语
“纸上文章贵,毫端血泪多。”当下的武侠电影,面对来自商业市场的压力,充斥着夺人眼球的特效。徐浩峰以作者姿态登场,他极具纪实风格的“武行”电影,没有耀眼的明星,没有快速的剪辑,没有繁复的特效,只有旁观者视角下冷静、节制的镜头,选择用有史可依的武学拳理、有据可循的技击兵器来呈现“武行”这一行业真实的生存状态,为武行寻一个历史归宿。破与立的方寸之间,徐浩峰的着意点似乎并不是要拯救经典武侠电影,而是要为中国武侠电影打开一个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