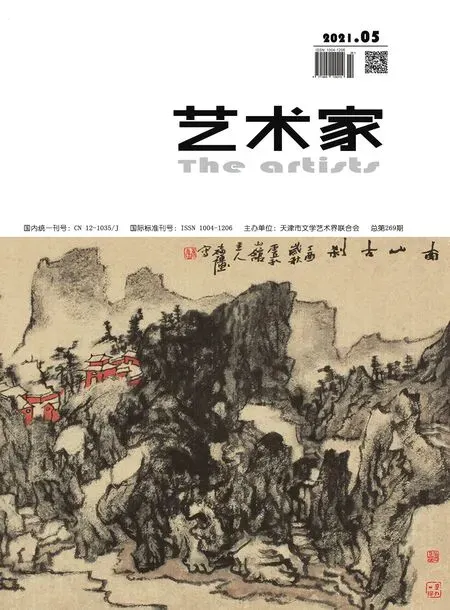贵州城市书写:从街巷到商区
——戴冰的短篇小说研究
□李得平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戴冰是贵州文坛近些年来活跃的作家之一。2015 年8 月28 日,全国各地数十位当代文学评论家齐聚贵州,召开了“贵州作家群高峰论坛”,对贵州文学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贵州省宣传部、贵州省文联首次以“黔山七峰”的群体命名方式推出了贵州文坛上创作突出的七位作家[1]。戴冰以自己的“另类”和“先锋”创造了贵州文坛上“新”的风格。目前,对于戴冰的研究以中国知网和《双重经验——戴冰小说选集》的评论附录部分为依据,一共有15 篇研究评论文章,主要集中在对戴冰小说集及单篇小说的研究和探讨。这些评论文章从作品世界表现、叙事艺术、都市城市等视角探析了戴冰小说的价值和意义。首先是关于戴冰在小说里集中表现的宿命下的历史君王及不衰世相的现实人生活,如石荔《小说之翼——读戴冰中短篇小说集〈惊虹〉》等。其次,关于叙事艺术,研究者认为在戴冰的都市文学中多出现片段式叙事方式,而在幻想型小说中主要运用的是幻想和想象的手法,如周湄《时空重叠中的枝蔓——戴冰与他的年代》。最后,主要运用城市的视角去研究戴冰的城市小说中对“城”的想象及背后的价值意义。比如,唐江在《探寻平衡的都市寓言——论戴冰的小说创作》中,从都市的视角出发,认为戴冰的小说中所追求的都市寓言的“探求平衡”特点是由主题的模糊、隐晦、不易把握及恍惚迷离的叙事逻辑构成的。
对于戴冰的城市研究而言,首先,街巷中的世俗文化不能只停留在世俗化大众的城市生活上,而应该关注到这座城市的世俗化大众的背后是否还具有更加深刻的寓意。其次,商区的发展被认为是物化的双重欲望结构,将在商区里的欲望作为主要的论述点。但在商区的发展中,并不是只有单纯的欲望,这种商业圈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应该具有两面性,同时这种欲望的出现与产生的原因是有待探索和思考的。
一、对贵阳街巷神秘的书写
街巷在戴冰小说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如《桃花》中的渣渣坡、《斜视》中的圆通街、《小楼纪事》里的石板街等,这里的街巷非常真实,时间和空间的准确构建,使得街巷的文化显得立体而有触感。除此之外,对街巷文化的书写让我们感到它的真实感的是市民生活中的琐碎杂事。戴冰似乎想要表达的是街巷文化中世俗的一面,这也是街巷文化鲜明的部分。但戴冰的随笔《博尔赫斯的花园——读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中认为:“在虚构的作品中插入精确的数据以及真实的人名,也许是想使虚幻的事物不至于显得太虚幻或者可以显得更虚幻。[2]”博尔赫斯对戴冰的影响深远,这对理解戴冰在创作中的主旨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戴冰在书写作品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味地想要表现真实,而是希望不过于虚幻。神秘不仅是博尔赫斯的眼光,在戴冰的小说中更重要的是表现虚幻,而这种虚幻的表达是由神秘主义来构建的。
神秘街巷的书写。首先是在思想内容上,把现实的世俗生活神秘化,街巷是现实的世俗生活展现的空间,但《桃花》中尼姑吴老太的死亡,在市民的眼中透露着蹊跷,本身就给吴老太的死增添了神秘的气息。其次,在叙事策略上,采用因果断裂营造叙事陌生化效果。在戴冰的这些街巷作品中,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小说的因果,这种因果链条的缺失使得戴冰的作品里总是让人读起来感到不好理解和陌生,造成了叙事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比如,《桃花》只告诉了我们“谁也不清楚李碧华和她的祖母是从什么地方搬来的,为什么会搬到这样一个僻远的地方来,就连佃房子给她们住的丁大毛也说不清”[3]。李碧华作为这篇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对于其刻画,作者似乎有所隐瞒,如李碧华和吴老太是从哪里来的,最终李碧华为什么失踪,为什么吴老太是尼姑却有李碧华这么大的孙女等,在这些具有因果联系的链条里我们只看到了结果。戴冰在其作品中有意建构神秘意象,比如,在《追逐》一文中,“楼道”这个意象显得尤为特别,楼道的时空感非常强,时间已是黄昏,楼道比较昏暗,同时楼道有6 层楼长,楼道的“长、暗”使得楼道的恐怖感立马被营造出来。戴冰在这篇小说后面的赘语中写道:“我相信人心中有些东西,只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惊鸿一现,就像幽暗深渊里稍纵即逝的光影,比潜意识潜得更深,比幽暗更幽暗,它们跟一个人的经验无关,跟理智无关,但也许更接近一个人灵魂的真实图景。[4]”这里的楼道里隐含的潜意识似乎是戴冰有意为之,更增添了接近灵魂的神秘本质。
程光炜在《如何理解“先锋小说”》中指出:“即使在一九八O 年代,上海的文化特色仍然是西洋文化、市场文化与本土市民文化的复杂混合体,消费文化不仅构成这座城市的处世哲学和文化心理,也渗透到文学领域,使其具有了先锋性的历史面孔。[5]”戴冰出生于贵州贵阳,他的作品所展现出来的街巷的神秘似乎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神秘特质,以及叙事的缺乏因果等,无一不指向“先锋”。这种“先锋”而“另类”的写作是生长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贵阳的戴冰不仅受到同时代作家的影响,也掺杂着他自己对“城”的独特理解。先锋文学的出现和城市是分不开的,那么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贵阳,市场和本土文化交融的贵州首府地理位置也给戴冰的小说创作带来了可能性,加之戴冰童年的经历,在描写神秘时,作者总会把这种神秘带入真实的时空场景里,让人觉得可感可触却瑰丽奇崛。
二、对贵阳商区发展的辩证思考
在戴冰短篇小说中,商区的描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作品中一个个以商区文化为标志的建筑,如舞厅、咖啡屋、发廊、大厦、音像公司。这些带有商区特色的地点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快”和“多”。比如,市中心的音像公司、咖啡屋、舞厅、发廊等。据他的统计,仅仅1985 一年,全县的发廊就从原来的五家增加到30 家,个体经营的服装店、鞋店、化妆品店及首饰店也随之以每季度五到八家的速度增长[6]。这些带有商业气息的建筑在短时间内占据了这个城市的中心,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大众文化是后工业社会中随着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市场商品领域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现象[7]。当这种我们称为现代文化的商区文化进入城市后,最初,人们的确在里面重新焕发了生机,音乐梦和个人的价值得到了认可,但是商区文化中除了有利的一面,也透露出矛盾的一面。
一方面,商区发展为青年们带来了新的生机。在戴冰的早期小说《我们远离奇迹》中经常塑造音乐知识青年的形象,随着音像公司的磁带给这些音乐知识青年的音乐带来新的活力,如流行音乐、摇滚乐等,他们在这些新的音乐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想法和道路,“有天代羽借到一盘《1987 年钻石金奖颁奖仪式》的录像带,在比利时的国土上,那群愤怒的歌手重新激发了远在东方的我们,我们重新开始狂热的练习”[8]。在贵阳这座城市的土地上,摇滚乐给这些音乐知识青年带来了属于他们的音乐梦,除此之外,个人的价值在这个商区找到了新的价值。在《头发的故事》中,马天最开始是一个除了头发好连父母都嫌弃的人,连自己也瞧不起自己,但是发廊经济的发展给他的好头发带来了肯定和认可,马天更是得到了一种慰藉。同样,《短夏》里的“狒狒”曾经是一个刀疤和管制工具一样多的社会混混,他通过开咖啡屋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且他还有关于未来的梦。
另一方面,商区发展带动了消费文化的盛行。首先,商业圈的形成给城市带来了更多的冲突。商品生产的扩张,引起了,为购买及消费而设的场所等物质文化的大量积累,其结果就是商业圈的形成。戴冰的作品中出现的磁带、咖啡、小商品、精美的小刀等都属于商品,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价值和交换价值,同时这些商品不断地扩张生产。但是,仅有商品的生产不足以形成商业圈,所以承载这些商品消费的场所也孕育而生,如音像公司、舞厅、咖啡屋、百货公司等,这些商品及其场所便逐渐形成了商业圈。与此同时,这种商业圈所带来的是现代的商业文化,冲击着城市具有的传统文化价值。戴冰早期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父辈和子辈的冲突矛盾,往往是子辈想要追求摇滚音乐,而父辈认为考大学才是正途,由此引发了商业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除此之外,在《城的故事》中,两种不同文化甚至引发了一个城市的两个区的孩子之间的冲突大战,同时,受传统文化熏染的老人们试图通过复兴来重新唤起一切风俗,与这种新的商业文化进行对抗。商业文化以市场为导向,但总有人试图在音乐上脱离市场而寻求自我的音乐终极价值,最终只能是失败。比如,邓剑放弃舞厅的要求,想要追寻摇滚乐终极意义,这使得邓剑最后走向了毒品而无法自拔;秦天放弃了自己的音乐天赋来触碰C4 的终极追求,使得自己的好嗓子最终废掉……他们都渴望放弃市场对音乐的主导性因素,但是最终不能免于被毁的人生。
戴冰说:“如果要问贵阳与周边地州市显著的分别是什么,我以为在于城市化的进程……这个过程中城市外观的变化固然重要,但对一个作家来说,也许他更关注的是城市化进程中人心的进程,是人心在这个过程中所承载的繁复景象和人性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曲折与斑斓。”商区的发展,一方面为文艺知识青年的音乐梦注入了新的生机,使其个人价值得到了认可;另一方面使得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日益显现,消费商品及消费文化的盛行成为划分社会的唯一标准,同时追逐感官刺激等审美被人们广为接受。商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但是如何平衡、如何最终化解矛盾又成了新的问题。
结 语
区域文学的特殊性就在于,从社会的行政区域划分,发现区域文学发展中的固有规律。“黔山七峰”也是以行政区域贵州为贵州作家群命名的文学研究现象,其中的代表作家之一戴冰,有着丰富的个人体验,加上现代主义对他的影响,造就了他对城市不同面貌的书写。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贵州城市和历史上的贵州城市已然不同,改革开放的巨大浪潮所带来的文化价值冲击着这座城市,戴冰在其小说作品中所描绘的街巷、商区都是一种文化场域和地域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