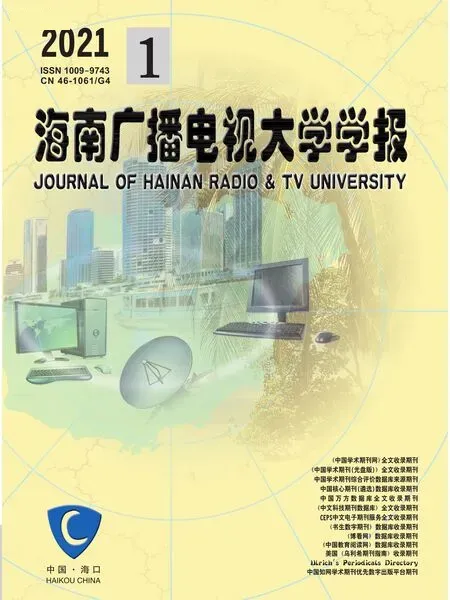论苏童《妻妾成群》叙事空间与颂莲悲剧成因
吴俊熹
(福州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小说被巴赫金称为“艺术时空体”。他认为文学叙事中的时间必须在空间当中汇集、流动才能成为可见之物。20世纪以来的现代、后现代小说因其打破既往小说叙事的时间线性规律从而使得小说的空间特性更加突出。《妻妾成群》故事脉络简单、题材古老,但苏童作为一个以“想象力”著称的作家,通过对文本叙事空间的巧妙编织与虚构,使得历史题材焕发出新的生机。
苏童将《妻妾成群》中人物活动、情节发展主要放在了陈家府内空间中,作者似乎有意将府外空间隐藏起来。但实际上,文本中所呈现的府外空间与府内空间形成了二元对立关系。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相反,当今的社会空间往往充满矛盾性的相互重叠、彼此渗透。而《妻妾成群》中出现的两个并置空间也并非完全中断,它们相互渗透、交叠,最后才呈现出冲突对立的尖利姿态。颂莲也就在两个空间的相互倾轧当中一步一步走向崩溃。
一、府外空间——精神原乡与自由想象共同构成的“神圣空间”
应该说,府外空间是《妻妾成群》当中最重要的地理坐标之一。在《妻妾成群》当中,府外空间并非一个简单的乌托邦世界,其本身也是泥沙俱下的。对于颂莲而言,府外空间是她出生、成长的地志空间,同时也是给予她生存压力、迫使她进入陈府的社会场所。但是“记忆所由产生的特定的物理环境,对人类的记忆具有广泛的影响[1]473-474”,而且记忆并不是大脑对原生事件的储藏,意识事件才是记忆主要涉及的内容。府外空间的客观事实在颂莲大脑一系列的加工、选择、编码之后被美化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并不如何美好的府外空间却是以一种美好精神原乡的姿态存在于颂莲的记忆当中。而颂莲始终是以精神原乡为参照系来体认陈府之内的生活、事物的。所以颂莲在府内常常寻找来自精神原乡的空间意象,从而给予自己慰藉和生存勇气。而且在府内空间中,颂莲又不断给府外空间叠加有关自由的想象,最终,府外空间发酵成精神原乡和自由想象的共同体——神圣空间。接下来,我们将从精神原乡和自由想象两个方面分析颂莲的神圣空间。
进入陈府是颂莲经历了破产、失学、丧父之后做出的选择,实际上也说明了颂莲在府外空间曾经得到物质富裕、家人疼爱的美好生活。所以,当颂莲面临生活危机时,她难以接受这种巨大的落差:
“颂莲记得她当时绝望的感觉,她架着父亲冰凉的身体,她自己整个比尸体更加冰凉。灾难临头她一点也哭不出来。那个水池后来好几天没人用,颂莲仍然在水池里洗头。颂莲没有一般女孩莫名的怯懦和恐惧。她很实际。父亲一死,她必须自己负责自己了。在那个水池边,颂莲一遍遍地梳洗头发,借此冷静地预想以后的生活[2]8。”
这种异乎寻常的冷峻,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颂莲内心深处无法表达的绝望和痛苦,还看到了府外空间并不美好的一面。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意味着孤独、贫穷,而学业无望、继母冷漠则代表着理想破灭、信任消失。这种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打击已经威胁到了颂莲记忆中精神原乡的美好形象,所以颂莲才在做工与嫁人之间选择了嫁给有钱人做小。也就是说,精神原乡和府外空间并不等同,精神原乡是嵌套在府外空间当中的。颂莲逃离府外空间的行为既可以说是迫于生存的无奈,又可以说是为了维护精神原乡的主动选择。由此,我们才能明白颂莲为何要去给他人做妾,否则,不管是儒家诗教人生观还是新兴知识分子人生观都无法给此行为一个合理解释。这次逃离退守的选择,留在颂莲身心之上最深刻的烙印是信任丧失,以至于她后来在陈府之内也因信任缺失而回绝了自我救赎的可能。
府外空间中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西餐社。西餐社是类似于空间门槛的特殊存在。颂莲和陈佐千在西餐社初次见面,但陈佐千第一次去找颂莲是吃了闭门羹的,这种行为极其符合颂莲知识分子身份。西餐社是颂莲自己的选择,这也恰好说明颂莲是以精神原乡当中的自我形象——女性知识分子作为参照系来体认这次约会的。西餐社场景中出现了一系列密集的意象:细雨、绸伞、蛋糕、蜡烛、火苗,这些唯美的南方图像构成了一个诗性空间。王德威曾这样描述苏童构造的南方世界:“南方纤美耗弱却又如此引人入胜,而南方的南方,是欲望的幽谷,是死亡的深渊[3]。”西餐社所有唯美的意象,其指向也是堕落与告别——蜡烛熄灭、火苗消失、生日过完。这次见面既是颂莲和陈佐千的开始典礼,也是颂莲和府外实体空间的告别仪式。
家宅和西餐社是营造颂莲府外空间最重要的两个意象,颂莲无意识地摘取其中美好、温暖的图像构成了自己的精神原乡,甚至拒绝承认府外空间所具有的藏污纳垢性质从而采取了逃跑策略。在这一过程中,精神原乡渐渐从府外空间中剥离出来,但同时被剥去的还有颂莲对人的信任和直面生活的勇气,最终府外空间也就成为了高悬在颂莲心中乌托邦式的精神原乡。
当颂莲进入陈府之后,不被府内空间接纳的她只能在精神原乡中追寻力量与安慰。法国哲学家巴什拉认为“家宅”不但能够安放回忆,而且能够安顿梦想:“由于有了家宅,我们的很多回忆都安顿下来,而且如果家宅稍微精致一点,如果它有地窖和阁楼、角落和走廊,我们的回忆所具有的藏身之所就更好地被刻画出来。我们终生都在梦想中回到那些地方[4]6。”对此,海德格尔也有类似看法,戴维·哈维指出:“海德格尔的反响在这方面很强烈。‘空间包含着被压缩了的时间。这就是空间的目的之所在。’对记忆来说最重要的空间就是家——‘把人类的思想、记忆和梦想结合起来的最伟大的力量之一。’因为正是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才懂得了梦想和想象[5]273。”颂莲的精神原乡是以“家宅”为原型的,当她在陈府当中苦苦挣扎的时候,她对于自由的想象不断叠加在精神原乡之上,久而久之,精神原乡又容纳了她关于自由的想象。最后精神原乡与自由想象合为一体,构成了独属于颂莲的神圣空间。
颂莲初进陈府,经历了毓如的漠视鄙夷、卓云的笑里藏针、梅珊的横刀夺爱。她被夹在怅然与悲哀之间,彼时她在紫藤架旁联想到的是自己在府外空间的学生形象。颂莲向陈佐千讨要项链,发现陈佐千眼中的自己和其他姨太太并无差别,她感到自身理想形象的破灭,而后,她看到飞浦时又想起了大学里那个独坐空室拉琴的男生。颂莲备受冷眼、孤独失宠之时,出现在她脑海中的自我形象是母亲怀里的小女婴,她用来为自己庆生的食物是来自府外空间的四川烧酒和卤菜。总之,精神原乡和自由想象是颂莲在府内空间遭受挫败时的力量源泉。而梅珊与府外医生的地下恋情、常年在外经商的飞浦与颂莲的暧昧关系,带给颂莲的则是关于恋爱、性的自由想象。这些有关性、恋爱的自由想象都来自于府外空间的渗透,投射在颂莲的精神原乡之上,也就成就了颂莲个人宇宙中的神圣空间。
二、府内空间——肉体监狱与心灵陷阱的异托邦空间
颂莲在秩序井然的陈府中苦苦挣扎、明争暗斗,但最终沦陷崩溃的悲惨故事是整本小说的叙事主线。所以在《妻妾成群》中,陈府构成了文本当中的显性空间。对于颂莲来说,陈府是一个包含了肉欲、钱欲等多种物质需求的特定场域,也是颂莲的行动域。但这种物质需求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对于男性的依附之上,显然,府内空间就如同一个豢养金丝雀的鸟笼,是衣食温饱之处,更是禁锢的囚笼。
颂莲是陈家的四太太,府内空间也就是颂莲的婚姻生活场所,而这种婚姻关系的本质是肉体交易。府内空间的竞争是残酷的,四个女人争风吃醋、相互竞争,颂莲在府内能凭借的只有她令陈佐千迷恋的新奇性体验、在床上的热情与机敏。左拉对于西方世界十九世纪的婚姻有过这样的论断:“就这样变成了讲究实利的爱情,草草交易,就像交易所里的买卖一样[6]368-369。”而府中的颂莲同样是以肉体为资本进行交易,从而得到府内空间的物质满足。从陈府角度来看,陈佐千并不在乎女人们的内斗、心理需求、性需求,仅将女人视作自身肉体欲望的发泄场和生殖工具。陈佐千也并不希望女人出现不符合自己要求的行为,而想要掌控肉体就必须从精神、心灵上规训一个人。所以掌管府内空间的陈佐千建立的是一个以控制肉体为目标的全景敞式结构——肉体监狱,此空间对女性的规则是:一个女人能给予的肉欲体验、感官刺激越多,她的物质条件、身份地位也就越高。
在作为肉体监狱的府内空间当中,仆人是极为重要的运作机器。仆人主要有三个作用:监视、规训、惩罚。仆人监视着颂莲的一切,如雁儿偷窥颂莲房事、梅珊的女仆打断颂莲房事等。初进陈府时,颂莲被仆人们判断出的身份是陈家的穷亲戚。仆人的反应似乎是府内空间对颂莲的下马威,颂莲用以回击的寒意并无作用,仆人依旧笑话她。这是府内空间对颂莲的第一次规训,颂莲穿着学生装,而仆人们却问颂莲是谁呀?怎么这么厉害?这种集体无意识行为是府内规则的外化,即女性知识分子在府内空间与其他攀附男权的女人并无差别。当梅珊外出偷情被发现后,仆人又起到了惩罚作用——将梅珊扔进井里。陈佐千本人也曾多次直接对颂莲的行为表达不满,如陈佐千一把推开当众亲吻他的颂莲,他认为颂莲作为一个女人不应该抽烟和戴帽子。这些都是对于颂莲肉体的规训,在府内空间当中,女人除了用肉体争取陈佐千的宠幸、迎合陈佐千的癖好以外的肉体行为都是不正当的。如此,就构成了一个以陈佐千为中心、以众多仆人为零件的肉体监狱。
苏童曾这样说《妻妾成群》:“痛苦中的四个女人,在痛苦中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像四棵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绞杀,为了争夺她们的泥土和空气[7]124。”女性在肉体监狱中依照规则竞争,非常规的竞争关系使得女性表现出弗洛伊德所说的“偏执症”——被迫害妄想、嫉妒妄想和夸大妄想。而后,她们将这些系统化的妄想症落实为相互厮杀、争夺物质的手段,同时还总结出一套适用于府内空间的扭曲畸形的心灵法则。毓如的法则是视如无睹、置若罔闻,卓云的法则是毫无原则、谄媚奉承,梅珊的法则是撒泼耍赖、母凭子贵,雁儿的法则是暗送秋波、阴毒诅咒,女人们凭借各自法则获得了在陈府空间当中生存的物质和地位。这些以心灵异化为代价的法则同样影响了府内的颂莲:颂莲在陈佐千50大寿这天反思自己是什么,颂莲并不喜欢府内的自己,但她很快就认为这种反思是耍小性子而且对她的生活有害无益;梅珊也曾劝颂莲以生育换地位,所以颂莲在发现自己那摊污血时备受打击;颂莲还学着卓云放弃底线,对陈佐千说:“今天你想干什么都行,舔也行,摸也行,干什么都依你[8]76”。心灵法则不仅异化心灵,而且异化人际关系。女人为了用肉体争取更大利益而形成了相互监视、迫害关系。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颂莲逼雁儿吞草纸一事:在颂莲受到冷落又怀胎无望时,她恰好看到雁儿用于诅咒她的草纸,颂莲“浑身颤抖着把那张草纸捞起来,她一点也不嫌脏了,浑身的血液都被雁儿的恶性点得火烧火燎[8]63”,在这样非人状态下,她逼迫雁儿吃下那张恶心肮脏的草纸。令人更加惊奇的是,雁儿为留在园内选择吃下草纸,我们在这对主仆之间的对话、行动中,好像看到了两个畸形异化的女人——两个怪物在相互博弈。颂莲这种丧失理性与人性的状态,正如尼采所言:“若往一个深渊里张望许久,则深渊亦朝你的内部张望[9]119。”果不其然,受迫害的颂莲也恶毒地害死了雁儿。这些心灵法则如同欲望陷阱,与肉体监狱相互补充,既鼓励女性以肉体换取利益,又让女人忙于内斗而失去反抗的可能。
米歇尔·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中曾提出一个“异托邦”概念,“异托邦”是存在于真实空间又超出这一空间并表现出迥异性质的空间。府内空间使得颂莲并未远离故土却与故乡遥不可及;让女人忘掉曾经、放弃未来,只考虑如何以肉体换取当下利益。府内空间超出常规空间,通过肉体监狱和心灵陷阱的严密监控,从而使得府内空间与府外空间的连续性中断,也就构成了一个异托邦世界,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10]354”。
三、二元对立的空间冲突与颂莲悲剧成因
张从皞认为:“异质性和差异性空间的二元并置是苏童小说空间安排的基本逻辑[11]。”《妻妾成群》同样存在空间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的空间形式反映了现代社会价值文化与传统封建道德秩序的矛盾,又同颂莲内心沉迷物质欲望与追求精神理想的纠结心态互为呼应。对颂莲来说,空间冲突的结局是神圣空间的破碎,而后她发疯崩溃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具体讨论空间冲突与颂莲悲剧成因之前,我们必须注意到府内空间包含的特殊空间——花园。府内空间通过肉体监狱和心灵陷阱进行严密监控,中国传统建筑又是体现权力、身份的高度秩序化空间,而花园是处在正常伦理秩序边缘的另类空间。正因为花园具有这样的边缘性质,所以在花园中才能容纳具有逸出府内空间倾向的行为和想象。首先,颂莲在园中的住所是后花园的南厢房,这是一个远离陈府中心(饭厅)的地志场所,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部分肉体、心灵的规训。所以在花园当中,颂莲能与飞浦相遇、相知、相爱、分离,颂莲能窥见梅珊与医生的暧昧动作。正是这些不能被府内主流空间容忍的行为带给了颂莲关于自由恋爱、自由逐爱等联系着府外空间的想象。但花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空间,花园仍然是府内空间的一部分,颂莲在花园中也接受了监视、规训、惩罚。所以花园本身就蕴含着空间冲突性质,而具有复杂性质的花园也同样是颂莲复杂性格的空间化象征,花园的边缘性质也表明了颂莲在府内空间边缘性地位。
花园作为性质复杂的空间,既是府内异托邦世界的一部分,又容纳了向往神圣空间的颂莲,那么此处的空间冲突就会表现得格外明显。颂莲是穿着白衣黑裙的学生装被抬进花园的,而后她却遭到了在场仆人的嘲笑,这实际上就是府内异托邦对颂莲神圣空间的示威,颂莲按照府内空间规则换上旗袍后才恢复了气色,后来雁儿也因不满朝学生吐唾沫,学生装与旗袍的对立实则反映了其背后空间的冲突。颂莲始终是以精神原乡作为参照系来体认生活的,她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想象也是如此,她认为自己在陈佐千眼中是和其他女人不一样的,所以颂莲在索要项链时听到陈佐千提及其他女人会十分不满、在陈佐千提出变态要求时会放声哭泣,但是陈佐千作为府内空间的掌权者只不过将颂莲看成一个肉体交易工具——婊子,双方认知上的对立冲突也就反映了文化层面的空间冲突。陈佐千还曾专断地收走了颂莲从府外带来的至亲遗物——箫,箫实际上是颂莲精神原乡中关涉亲情的空间意象,此后颂莲对雁儿的凶狠、对陈佐千的冷漠实则是对府内异托邦世界践踏她精神原乡的报复。但颂莲还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空间冲突后,陷入了府内空间的心灵陷阱,她剪到卓云耳朵、间接害死雁儿。但是受害的不仅仅是卓云和雁儿,颂莲用以体认生活的参照系——精神原乡也逐渐崩塌了。颂莲初进陈府,在井边联想到的是女学生形象,而颂莲精神原乡中的自我形象正是女性知识分子,但是在府内空间扭曲畸形的心灵法则影响下,现实生活中的颂莲在追求物质、地位的过程中逐渐异化了。花园中的井就像一面镜子,颂莲每一次临水自照都反映出她异化之后的形象,但是以女性知识分子形象体认自我的颂莲并不敢承认自己的堕落,反而不断安慰自己(剪到卓云耳朵之后认为是自己不小心)。井中的自己与精神原乡是相悖的,而精神原乡对颂莲极为重要,所以颂莲对于井的恐惧才会不断加深。当雁儿的死讯传来,颂莲再也不能自欺欺人,所以她感觉自己“死到一半”,实际上就是颂莲用以体认生活的精神原乡正在崩塌。
颂莲在欣赏菊花时初见常在府外经商的飞浦,在受到冷落时得到飞浦的安慰,后来还借由飞浦联想到了大学里的男同学。颂莲与飞浦两人身上都具有府外空间的某些特质,所以才会相知相爱。飞浦还带给了颂莲自由爱情的想象,甚至帮助颂莲找回了丧失已久的信任和勇气。但两人都处于府内空间的肉体监狱当中,受到严密的监视和规训,所以在颂莲和飞浦相处时,总是被来自府内空间的力量打断,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空间冲突,而这种空间冲突集中体现在颂莲向飞浦表白时:颂莲的心里有一种陌生的欲望,但此时飞浦的激情只能徒劳地在眼里汹涌澎湃,他的身体只能僵硬地维持原状。飞浦的身体失控是肉体监狱长期规训所致,飞浦内心涌动的人性已难以突破长期被规训的肉体。梅珊和府外医生的地下恋情则是带给颂莲自由想象的另一个途径,但梅珊的命运却是被投入井中。物伤其类,兔死狐悲,此刻颂莲的自由想象也已完全破裂。
由此,构成颂莲神圣空间的精神原乡和自由想象都在空间冲突中消解。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对于神圣空间有过这样的解释:“教堂作为宗教徒的神圣空间,就是他们世界的基点和人生意义的来源[12]398。”神圣空间的崩溃意味着颂莲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她用以体认世界的过去经验和想象未来的生活期许。对于《妻妾成群》,苏童曾说:“是不是把它理解成一个关于‘痛苦和恐惧’的故事呢[7]125?”颂莲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神圣空间,为此,她逃离了自幼成长的府外空间而进府做妾。她的“痛苦和恐惧”实际上是对于神圣空间破碎的痛苦和恐惧,当颂莲神圣空间在空间冲突中消亡时,其悲剧命运也就无可避免了。
《妻妾成群》是苏童1990年前后完成的中篇小说,女性知识分子颂莲神圣空间破碎、无处容身的悲剧遭遇似乎折射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无处安放理想的精神迷惘和心灵阵痛。苏童以旧瓶装新酒方式,将书中考察人性的叙事空间与现实生活的历史空间勾连起来,用一夫多妻的古老题材表现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从而赋予这一历史题材更深刻的时代内涵。同时,苏童《妻妾成群》远离历史叙事的线性思维,在架空历史的空间中展示了个体生命的忧郁凄凉,也是一次对空间叙事的艺术探索。